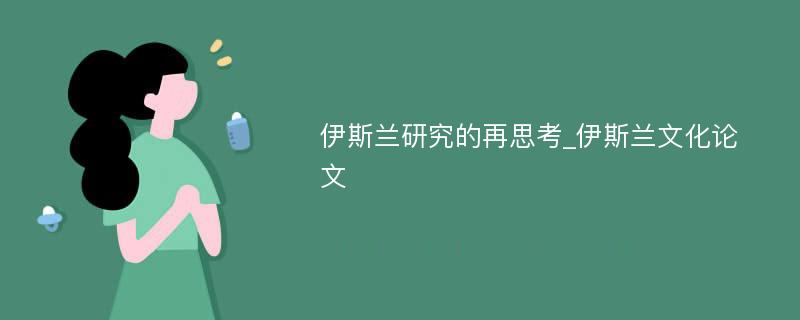
重思伊斯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斯兰教,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但反观自身,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却贫瘠得令人难过。在当下,鼓励和推动锐意、自由和富有成效的对伊斯兰教的思考愈发显得迫切。所谓的伊斯兰复兴主义垄断了有关伊斯兰的话语,而我所说的“静默的伊斯兰”——那些相比于政治运动的激烈示威,更注重与绝对主宰安拉之间的宗教联系的虔诚信士的伊斯兰却并没有得到社会科学家们足够的关注。我所说的伊斯兰,还是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们的伊斯兰,而现如今,他们批判性的进路几乎未能被引入被各种激进意识形态挤占的社会和文化空间,重重的阻碍正摆在他们面前。 作为一名伊斯兰思想史学家,对我而言,从印度一路延伸到大西洋之边,存在着一个文化空间。这个空间,无疑因它纷繁的语言和族缘文化而极尽丰盈。同时,它也受到了两个轴心思想传统的影响:古老的中东文化,其中为希腊思想留有特别的空间;再就是众先知所晓喻的一神教。我学会了在这个广阔、丰盈、错综复杂的空间中去探究伊斯兰教,将社会所面临的诸多新情况和穆斯林传统中诸多鲜活的元素加以整合。这里我特意强调自由。“重思伊斯兰研究”可能会让人觉得我在重复众所周知的“矫枉/纠正(isahi)”立场——19世纪以来赛莱菲学派表现出的那种革新思想。但我希望避免在现代的激进批判性思想,不论它用于何种主题和改革(islahi)派思想,放在伊斯兰传统中来看,它是一种神秘的态度,混杂了针对宗教洞见的相关问题而采用的历史学的进路之间进行对比。 在当下,对伊斯兰或其他任何宗教的思考所代表的主体智识努力,须以一种新的认识论视角去对历史和神秘并蓄的知识体系的特征和复杂性做出评估。我甚至要说,在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兴起逾三百年之后,历史和神秘这二者依然在我们的现代思想中彼此互动、缠联着。无需固守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在当下思考伊斯兰远比任何东方主义的学术性探讨都要紧迫且意义重大;(思考伊斯兰)研究这一事业的终极目标是要通过将作为一种宗教和一种社会-历史空间的伊斯兰教设为样例,进而为比较文化研究发展出一套新的认识论上的方略。现在,该是时候结束两种独断的态度——一种来自信仰者有关教义的断定,另一种则是实证主义者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假定之间毫不相关的对峙了。 “重思伊斯兰研究”这项事业,如果能被达成一致的话,必然是有一批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当政者和经济生产者在前赴后继地努力。我很清楚,悠久而深厚的思想传统不会因区区一些个体提出的若干论文和建议就被改变、甚至修正。但是我也坚信,思想,自有其力量和生命,它们中的一些至少可以幸免于,甚至穿越那些由失控的信念和专横的意识形态所垒筑起的高墙。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该从何入手呢?那种可以表达出既能够整合进我们的现代科学心智,同时又能融入穆斯林的宗教体验的伊斯兰教的,合意的声音或可被接纳的理论,又该到何处去求索呢?或者换句话说,既能清晰有力地表达出伊斯兰教的现代洞见,同时又能对(伊斯兰)共同体产生像沙菲仪的《法源论纲》和安萨里的《圣学复苏》那样的影响,是否是可能的?我之所以提到这两部巨著,是因为它们阐明了我所想要推动的那种智识上的动议,也即,整合,正如沙菲仪和安萨里所做的那样,将新的学科、新的知识,新的历史性洞见整合到伊斯兰教中来,因为伊斯兰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存在者的人类所享有的一幅精神性和历史性的洞见。 新思维的工具 在伊斯兰的传统思想中,传统和正统性都是未被思考、未被详加阐述的概念。在什叶派、逊尼派、哈瓦利吉派等各个社群中,传统被化约成了对它们各自认为是“可信的”文本的收集。如果再加上《古兰经》和圣训,以及各个学派中沙里亚法和法典得以从中衍生的方法论,我们就有了关于伊斯兰传统的三条主轴的细分。我想引入一个概念,“兼容并包的经外传统(exhaustive tradition①)”,它是在各个社群所因循的所有圣训集(collections)之间的一种批判性的现代碰撞中逐步形成的,其中,那种可以追溯到经典权威(比如逊尼派的布哈里和穆斯林;伊玛目派的穆罕默德·库莱尼、伊本·巴拜韦和艾布·贾法尔·图西;哈瓦利吉派的伊本·易巴德等)那里的“正统”约束并不被看重。伊朗伊斯兰革命曾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用以追求乌玛的政治团结。各方收集而来的宗教语料(corpuses)和像教义学(Usul al-din)字面意思是“宗教的基础/原则”)和教法学(Usul alfiqh)这样新生且连贯的学科的理论阐释之间的历史性交锋,仍是尚未被探究的必要工作。 在这种基于对“法则、原则(Usul)”的新定义的“兼容并包的经外传统”概念之外,还有如今在人类学中被使用的“传统”这一概念——它指的是所有习俗、法则、制度、信念、仪礼和文化价值的总和,它们构成了每个族群语言群体的认同。这个层面上的传统也以“习惯(‘u r f)”或“惯例(‘amal)”的名义被部分地整合进了沙里亚法中,但却是由教法学家们的方法论或“原则(usuli)”所加以遮盖或合法化的。传统的这一面相也可以用“因循/仿效(塔格利德,taqlid)”这个阿语词汇表达,但是“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个概念要是在我提到的这个视角下进行再阐释的话,就只能用“逊奈(sunna)”这个词来表达了。 同样,“正统性”这个词涵盖了两种价值。对信士而言,它是一种关于宗教的可靠表达,因为它是由“虔敬的先贤(al-salaf alsaiih)”所教导的;“正统派”的著述会将其他群体描述为“支派(sects)”。而对历史学家而言,正统性指的是同一政治空间内相互竞争的群体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宗教的运用,正如逊尼派支持哈里发制(它是后来被教法学家所合法化的),并称自己为“逊奈的追随者和团结的乌玛(ahl al-sunnawa-al-jama 'a)”。其他所有的派别都被赋予了有争议、格调不高的绰号,比如“拒信派/变节派(rawafid,rejectors)”、“出走派(khawarij)”和“内学派/隐微派(Batiniyya)”。而伊玛目派则自称为“无谬性和正义的追随者(ahr'ismawa-al-'adala)”,这又是与逊尼派相对的另一种“正统”。 尚未有人做过这样的努力(伊智提哈德),将“正统性”和宗教相分离,前者会被用作一种富有战斗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奋争,进而被政权强行当作一种工具,来将政权和“价值”合法化。而后者则是一条得以探求绝对者的路径。这种努力是我们的另一项任务,不仅对我们重思伊斯兰研究的这项现代事业是如此,对于其他宗教也是同样。 从不可思到可思 伊斯兰教被呈现,并作为一个关乎信仰与不信仰的确切体系而得以延续,是不会屈服于任何批判性的质询的。因此,它将思维空间分为了两部分:不可思的(unthinkable)和可思的(thinkable)。但起初,这两个概念都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哲学性的。这两者的相对支配空间会随着历史而变化,而且会因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异。在沙菲仪将“逊奈”和“根源(‘Usuli)”这两个概念体系化之前,伊斯兰思想的很多方面都还是可思的。但在沙菲仪的理论取得了胜利,还有之前所说的真实可信的“圣训集”被详尽阐述之后,它们变得不可思了。类似地,与《古兰经》官方定本(mushaf)的经文收集的历史过程有关的问题,也在哈里发的官方压力下变得越来越不可思了。在判决了伊本·舒布德(Ibn Shunbudh,公元10世纪)之后,法官伊本·穆贾德做出了最后一项关于禁止讨论被接受为正统的奥斯曼定本的读法的官方决定。 我们可以举出第三个典例来说明可思是如何被主导的政治-宗教团体所转化为不可思的。穆阿太齐赖派通过他们的创制(伊智提哈德),将“(《古兰经》是)安拉创造的言语”这一关键问题变得可思,但是伊历5世纪(公元12世纪),哈里发卡迪尔将“《古兰经》是自存的”作为他的著名信条(‘Aqīda)来推行,以之作为“正”信,进而又将这个问题变得不可思了。 正如我们所言,自智识上的现代性在西方得到阐述以来,伊斯兰思想中,不可思的或者未被思考的(部分)就被扩充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出的关于宗教的所有理论,在当代的伊斯兰思想那里要么依旧被无视,要么就被以“不相关”为由而加以拒斥,根本没有加以智识性的论证或科学性的考量。 在我们世俗化、现代化的社会中,传统的宗教确实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各种世俗宗教在工业化了的社会中兴起,像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制下的很多新流派。如果我们透过这些新近的世俗宗教所设立的新参量来看天启宗教的话,就不得不引入新的标准,将宗教定义为一种普世现象。传统的观点认为宗教全然是安拉启示、创造和降示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那些由取决于每个群体、共同体或社会中有效的文化价值和表征的社会-历史进程所创生的社会学的宗教理论来代替这种观点。我们必须重思与宗教的本质和功能有关的整体问题,既要用到传统的神圣起源理论,也要用到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生产的现代世俗解释。 对伊斯兰教而言,这意味着要重写整个伊斯兰史。它既是一种天启宗教,也是那些它过去被、现在仍被接受为一种宗教的社会的历史演变之众多因素中活跃的一种。东方学家已然开启了这项研究,甚至在伊斯兰教兴起的贾希利叶时期探寻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但是我却没听说,在这条历史学家的进路中,有哪位东方学家提出了其中暗含的认识论方面的逻辑问题。对于一种是作为天启而被降示和被接受的宗教,历史学家对它的起源和功能的呈现所引发的后果,尚未有任何智识性的努力对它加以考量。 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智识和文化的架构,进而将历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所有对天启宗教的呈现整合进一个思想体系,并逐渐与人文和社会研究相脱离,让有关教义学的思考来统领它。 启示与历史 《古兰经》坚守着人类去聆听、领悟、反思、洞彻、理解、调和的必要性。所有这些动词都指向了那些可以导向一种理性化的智识活动,而这种理性化的基础则是由拯救史所揭示出的存在性范式。中世纪思想衍生于一种由神圣智慧所保证的本质的、实体的、不可变更的理性概念。现代知识则与之相对,其基础是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空间的概念,而它不断地在社会行动者的活动之中被建构和结构。每个群体都力图支配他者,它们不仅会利用(国家控制的)政治权力,还会将自身的文化体系呈现为一种普世文明。从这个视角来看,《古兰经》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表达,其中,一小群信士被赋予了权力。这一进程是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同时也是心理的。通过它,《古兰经》表现为启示,并且被特定的个体和集体的记忆所接收,进而在变革的社会——历史空间中不断地被再生产、书写、阅读和表达。 历史是启示在现实中的化身,后者被宗教学者(乌莱玛,'ulama)加以阐释,并在集体记忆中得到保留。对于群体所接受的社会秩序和历史进程,启示维系着赋予它们一种“超验的”合法化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只有在那种基于社会想象的认知系统没有被新的、貌似更可信的理性所取代时,才能够被维系,而那种理性是与一种别样的社会——历史空间组织相联系的。这便是我们所熟知的(伊斯兰)哲学家和教义学家,或教法学家之间之所以存在分歧的一个缘由。 自从那种智识上的现代性被暴烈地引入,穆斯林社会中在继承而来的“可思”与那种“未被思”之间的斗争变得更加紧张了。但如我们所见,16世纪的西方社会,同样的斗争也在知识和行动的范式中展开了。斗争的结果是优先顺序反转,并被启示所固化。经济生活和思想顺从于伦理——宗教原则,一直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体系取得胜利,传统社会中的象征性交换不再被实践,取而代之的则是收益原则。 在这个新的价值体系内,与市场的技术性规则和生产力的效能控制相比,伦理性的思考变得无关紧要。民主制将权威的来源限制在了一种在形形色色的专业性或政治性团体构成的不同环境中得到表达的“熟识(acquaintance)”之中。而权威的超验性起源则不再有人问津。进而,启示的问题被消解了;但是,它既未在智识上得到解决,也没有作为一种以所谓现代思想中盛行的实用理性为依据的貌似可信的真理而得以维系。所有的关系都建立于国家、群体和个人的相对权力之上;建立在形而上学或宗教洞见之上的伦理原则,则失去了它们的吸引力。然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必须依据改革派的思想,回归“被启示”的真理。我是在强调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伦理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决裂。与此同时,“科学的”知识也并没有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来控制或利用社会性想象。相反,在那些利用现代大众传媒来散播他们从宗教性(在穆斯林社会中)或世俗性,再或一种二者相混合(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权中)的意识形态中获取的口号的政论家那里,社会性想象被前所未有的动员了起来。 有鉴于这样一种体验,问题再次被提出:我们应该根据被启示的话语而将知识伊斯兰化,还是说我们应该将伊斯兰教放在探求普适意义的语境下加以考量?众多的道路再一次被踏上,让我们带着信心、希望和(智识的)清明去上下求索吧! ①Tradition在伊斯兰研究的语境下一般指圣训,也可指代经外教义,这里视语境译为经外传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