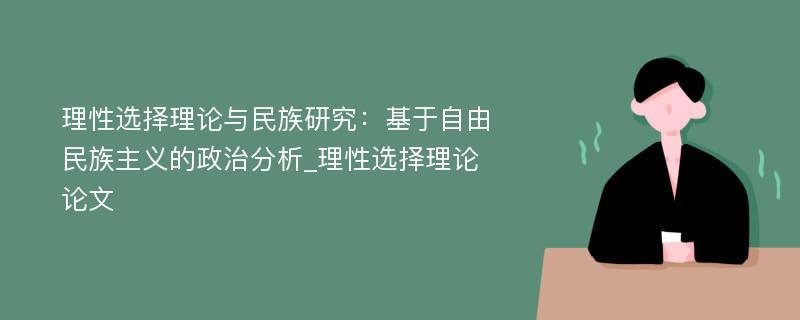
理性选择理论与民族研究辨析——基于自由民族主义的政治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政治学论文,理性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人类社会及其个体“理性”与“非理性”的探索,贯穿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而建立在自由主义理性假设之上的理性选择理论,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几乎成为一种普适的分析框架。基于政治学视角,理性选择理论是否适用于民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研究,至今在国内学界没有深入的探讨。
一、理性与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由于人类具有以推理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因之被归之于人类。”① 从哲学角度看,作为实践过程中相互关联的环节,手段的合理性(有效性)与目的的合理性(正当性)表现为同一理性的两个方面。② 因此,对于理性的探讨首先是基于对人具有“理性能力”的假设。
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理性”即韦伯所说四种社会行动理想类型③ 中的“目的合乎理性”与“价值合乎理性”,理性选择理论所考察的个体行为主要对应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行动”与“价值合理性行动”。传统经济学关于人的行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被称作“公共选择”或“理性选择”。经济学分析之所以在社会学界被作为普适的方法,在于它“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④
理性选择理论是基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是有理性和利己假设的一种政治学分析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所说的“理性”,就是解释个人有目的行动与其可能达到的结果间的联系的工具性理性。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上的:(1)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2)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3)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4)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理性选择之特征可以概括为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⑤ 在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内有“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⑦“集体行动的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⑧ 三个著名的悖论。就实质而言,这三个悖论均指向同一个问题,即个体的理性选择往往导致集体行动的非理性。
二、理性选择理论与民族研究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只有在判断自身能够通过行动得到利益时,才会加入集体活动;集体行动的问题也同样在关于个体的动机中得到回答。因此,依照理性选择理论,实践中的集体行为,完全取决于行动者个体对参加集体活动所得利益和降低成本的考虑。了解理性选择理论关于集体(民族或族群)及其行动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辨析理性选择理论是否适用于与民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研究。
(一)理性选择理论的民族观
对于大多数理性选择理论者来说,他们并不认为存在所谓的“民族现象”。如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就认为民族关系与阶级、宗教或身份关系并无本质上的区别。⑨ 希尼沙·马兰赛文科(Sinisa Malesevic)认为,族群间的区别主要是文化和生理上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个体聚合成一个群体以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在理性选择主义者看来,个体就是在一个国家里不断地竞争有限资源、经济特权、财富或社会地位的行动者。在这一竞争过程中,民族的区分(意味着个体享有相同的文化资源,诸如语言、习俗、发音、肤色甚至饮食习惯等),往往能够使个体在获取利益时付出相对低廉的代价。⑩
在自由主义的视野中,完全独立的自由人并不存在所谓的边界问题,但是在人们结为不同的群体时,文化差异的巨大功能远远超越了地域对于形成人们群体的功用。如自由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文化权利”是“群体权利”的基点一样,理性选择主义者也认为一个群体试图划定一个相对固定的边界以使文化的差异成为群体识别时可资利用的资源。因此,在理性选择主义者看来,民族(或族群)作为一种资源迫使个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入集体行动之中。与此相应,民族(或族群)的划分只是个体为获得利益而加以操纵的一种社会资本。
关于“民族认同”,理性选择主义者们所关注的是,个体在理性与自私的行为中是如何利用所谓的“民族认同转换”策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一个生活在科索沃和马其顿的族群在1991年声称本群体属于埃及人,而且在南斯拉夫进行人口普查时他们同样要求登记为埃及人。(11) 但就其族群而言,他们与埃及人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他们声称自己是埃及人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选择能够使其族群在当地的民族格局和民族政策下得到更多的利益。
理性选择主义者关于“民族”的认识可以归纳为:(1)民族是个体可供利用的社会资本;(2)“民族划界”是个体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而假借文化差异的个体行为;(3)“民族认同”只是个体换取利益的策略选择。总之,理性选择主义者认为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民族性(ethnicity)并不是原生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可变的过程。换言之,民族性对于分析族群关系、族群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不仅仅是群体固定的“文化内容”。正如伯顿(Banton,1994)指出的:“人类社会民族关系的改变通常并不是因为人们改变了对所在族属的评价,而是因为改变了被民族伦理关系所统治着的观念。”(12)
(二)对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民族研究的评价
希尼沙·马兰赛文科认为,为了延续社会学的宏大解释力,理性选择理论家们有意使他们的假设更加中性和可变、模糊和不精确,并且也选择了一条注重实效的简化主义路线。(13) 尽管目前这种简化主义路线通过归纳个人的行动、信仰和特性对个人行为做出的解释,在表象上看仍是可行的,但问题是,将该理论应用于民族研究时,理性选择理论提供的所谓“实践性的”和“可靠性的”解释,是否真的有效呢?
马兰赛文科的观点很明确,他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一个虚假的、被建构的命题,该理论最大的缺陷在于解释力的贫乏。他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力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质疑:第一,由于理性选择主义的所有分析是建立在对理性的假设和行动者明确的意图与自私的动机之上的,所做研究仅为了验证这一预设的结论,故而理性选择理论解释的循环反复使它必然走向死胡同;第二,在使用理性的概念和意图性的方法上存在明显的问题;第三,理性选择理论家们忽视了个人选择中的文化因素,因为个人的行动不仅是由活动的结果所激发的,而且也是由活动本身的意义所推动的;第四,理性选择理论将政治行为和政治人完全用经济学的方法加以解释,使得其不仅忽视了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而且也忽视了政治因素。基于此,他得出结论: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在研究诸如民族仇恨、族群冲突等族群关系方面有可取之处,但由于并非所有的人类行动都是理性的,所以理性选择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民族研究。(14)
下面,结合马兰赛文科的观点,笔者从自由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对理性选择主义者关于“民族”的观点展开评说,并对理性选择理论关于民族的认知进行剖析。
1.什么是民族?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理性选择理论的立场与民族建构论(nation-building theory)有某种契合之处。民族建构论者主张民族是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被建构出来的,而理性选择主义者则认为民族是理性的“经济人”为了私利聚合而成的群体。二者都强调民族的非原生性,并且认为民族文化与自我意识在形成民族的过程中属非核心因素。
在民族研究者沃克·康诺(Walker Connor)看来,民族主义永远不可能只是对集体利益的理性追求,它更多地是对“族群-民族”的热爱,而不是忠诚于疆域化国家的爱国主义;“族群-民族主义”是一种永远不能被理性来解释的。他认为民族就是有共同祖先的人们群体,其最终是建立在感受得到亲缘联系基础之上的;民族的本质是一种在其成员潜意识信念中的心理纽带,这种心理纽带联结一个团体的成员,并使这个团体的成员有别于其他团体的成员;共同祖先的信念也非依赖于事实和理性,而是建立在强大的和不讲理性(不是非理性)的成员们的感情基础之上的,所以只有大部分成员具有民族意识之后,一个群体才能成为民族。(15)
在民族主义者关于“民族”认识的基础上,自由民族主义者塔米尔认为:“如果一个群体既展现出足够数量的共同而客观的特征——比如语言、历史、领土等——又展现出对于其独特性的自我意识,那么,这个群体就被界定为民族”。(16) 也就是说,只是凭借个体主观的意愿与理性的选择偶尔聚合在一起的群体,因缺乏同质性而不能称之为民族。米勒(Miller)认为,若要形成民族必须具备五个要件:(1)民族成员是相互承认又分享信念的人;(2)民族的认同是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认同;(3)民族的认同是能发生主动行为的认同(an active identity);(4)民族认同要求一群人定居于一块固定的领土上(homeland);(5)民族认同要求民族成员共享“共同的公众文化”(a common public culture)。(17) 米勒指出,人类结为某种形式的群体(比如社群),其成员可以通过某种对于共属群体的认同来化解承担群体义务与追求个人利益的选择困境,并逐渐产生出一种平等观念甚至会进一步强化原有的人际关系;但是,对于民族(族群),其成员可以享有许多其他群体所无法产生的互惠作用,诸如保护整个民族的故土,继承历史先人的美德,以福利制度扶助弱者,等等。“这些与公民权利义务有关的‘互惠’如果没有‘民族性’加以支撑,将不可能获得实现。”(18)
从民族主义者以及自由民族主义者关于“什么是民族”的回答中可知,文化与其所支配的观念是形成民族的根本所在;民族并非个人选择的产物,也非个人意志所能解构的;一个民族成员的任何选择既源于又受制于本族文化与观念;所谓自由的、理性的选择在民族成员的选择中是不存在的。再回顾理性选择理论关于“什么是民族”的回答,不难发现理性选择论者关于民族的论调过于简单、绝对,既不符合民族形成过程的基本常识,也缺乏分析民族问题的整体感。
2.关于民族成员身份及其选择。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来考察个人的社会关系与群体归属是十分重要的,但前提条件是假设个体能够与自己的社会角色、归属拉开距离。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个体的社会角色与群体归属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宿命而无法选择。如罗尔斯(Rawls)所说:“我是谁是由我所继承的历史、我所占据的社会地位以及我所从事的‘道德事业’回答的——既为我回答,也为别人回答。”(19) 其实,在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存在的问题是关于个体的道德身份与群体身份获得途径的分歧。在两者的分歧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个人如何选择的问题。在自由民族主义的视野里,个体是社会存在中的个体,个体的自主性必须凭借自身所属的群体来实现,所以个体的道德身份的获得受自身所属群体的限制,而个体身份的获得又推动了对自身所属的群体身份的评价。卢克什(Lukes)和金里卡(Kymlicka)将人们的身份形成模式总结为严格的“发现模式”、“群体选择模式”、“道德选择模式”和“严格的选择模式”。(20) 但无论何种选择模式,都极度关注个人的生活环境、历史传统,以及文化对于个体选择的约束。这些个体身份形成模式都与理性选择主义关于“理性”个体自主地选择自身所属的群体身份的假说大相径庭。即便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在进行选择时也无法超越社会基本的评价体系。由此可见,理性选择理论关于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并不完全适用于个体的群体身份选择。
对于个体的民族身份的选择,自由民族主义者耶尔·塔米尔所主张的是“严格的选择模式”。在这种选择模式里,实际上也否定了理性选择理论家关于民族(或族群)作为一种资源迫使个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加入到集体行动之中的论断。塔米尔认为,“选择一个新的民族身份的个体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使自己更加接近这个目标,但是不能保证自己能够在事实上实现这个目标”;全盘转换群体成员的民族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依赖于各种因素,而“个体的意志只是其中之一”;“成员身份是建立在接受与相互认同基础上的”,若想使别人确信一个人已经成为自己群体中的一员是身份转换最困难的方面。(21) 因此,“个体既可以依据群体的选择模式也可以依据道德的选择模式行事,这间接的意味着严格的选择模式的合理性,这种模式假设个体既可以反思他们的民族身份也可以反思他们的道德身份,而不要求他们同时或激进地进行这样的反思”。(22) 金里卡也认为,“文化的权利之所以受到尊重,正是因为文化的成员身份是我们的身份认同中一个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特征,而不是选择的结果”。(23)
由以上所述可知,民族(或族群)的形成以及成员身份的获得是一个漫长的文化积淀与意识形成并传承的过程。“严格的选择模式”使得任一民族(或族群)的成员不能轻易地选择或取得其他民族(或族群)的身份,个体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聚合到一起的群体也因缺乏相互认同与同质文化而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的民族(或族群)。
3.社会情境背景下的个人选择能力问题。自由民族主义者并不排斥和否定民族成员的选择能力,由于受伦理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自由民族主义者突出“强调选择的可能性与重要性”。(24) 他们认为民族成员的资格提供了一套信仰、利益和行为方式的能力,以及一种连贯的、透明的、有意义的环境,在这个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因而也是可以预言的环境中”,个人是有能力做出选择并获得自我管理能力的。(25) 在这里,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分析路径与理性选择主义者有明显的不同,自由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个人选择,是建立在民族成员与自己所属的民族之间以及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的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主义者则是完全强调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加入民族群体,以分享民族身份所带来的资源与利益。
自由民族主义者对“民族身份”的原生观点并不赞同,他们认为“民族中的成员身份是选择的,因为个人可以离开他们出生的国家而创造一种新的民族归属。这使对民族文化的忠诚与对民族义务的承当转化为自愿的行为而不是命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26) 也就是说,个人一旦选择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就必须自愿地承担延续本民族的生存、维护本民族成员的福利、繁荣本民族的文化等义务,并且在成员间相互的义务与关爱下生发出进一步巩固本民族的道德观念。从这个角度看,承担民族义务决不是理性的“经济人”所愿意接受的,民族道德观念的凝聚力也不是冰冷的经济利益关系所能产生的。可以说,在阐释民族义务与道德伦理方面,理性选择理论明显缺乏解释效力。
4.关于“民族自决”。就民族自决而言,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参加群体生活、获得群体身份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无需(或被迫)为他人和群体承担责任与义务。如果依据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来研究民族及其未来,那么民族文化的传承则只是个人获取私利的副产品而终将被“理性人”放弃,作为他们获利基础的群体(民族)也将因“搭便车”的盛行而逐渐瓦解。这种推理在现实社会中是无法得到有力印证的。在民族“文化自决”问题上,依据理性选择理论同样无法得到完美的解答。相反,自由民族主义强调在社会情境下的个人选择,主张“民族自决权应该被看做一种个体权利,依赖个体把自己联系于一个特定民族群体并公开表达这种联系的一种自主决定”。(27) 而为了行使正当的“民族自决权”,个人身份的形成必须是通过他所享有的民族身份来实现;维护民族权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赋予了个体自决的权利;个体必须被赋予表达他民族身份的机会;个人享受公共生活的能力必须是个体自主的;所有的民族平等地拥有“民族自治”是民族自决权充分实现的前提。(28) 从自由民族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论述看,它一方面彰显了自由主义的个人自主取向,另一方面也将民族群体文化与民族义务结合起来。与自由民族主义相比较,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于作为民族(或族群)集体行为的“民族自决”与民族利益,明显缺乏解释力。
5.关于民族及其成员的责任与义务。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源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主张,尽管自由主义者强调政治义务是自由和理性的行动者自愿承担的义务,共同体(民族国家)也因此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大量的不承担义务的公民的存在使得“契约”理论必然陷于某种困境。此外,作为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或族群)与其成员的关系以及民族与国家间的责任与义务关系,也无法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得到完美的解答。
考察自由民族主义者的观念可知,“民族认同”是民族构成的要件,这种认同的“文化”与“情感”成分居多,不能纯粹以“理性”来考量。沃克·康诺指出:“对国家(state)的忠诚,乃是社会政治范畴,大部分属于‘理性自利’原则;而对于民族的忠诚,则直观感受要多于理性选择,乃是基于共同血缘的情怀。当两者无法协调时,通常对民族的忠诚要强于对国家的忠诚。”(29) 而且由于个人对于国家的“特定的政治义务建立在普遍的、道德的正当理由基础上的尝试业已证明是不成功的”,因此自由民族主义者主张可以把人们对于国家而承担的政治义务的本质理解为“团体承诺”,这种团体承诺是通过某种归属感的“协作性的义务”的方式来实现的。(30) 而所谓的“团体”,在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形态就是民族(或族群),团体承诺就是民族集体对于国家的承认与义务的承担。“协作义务”的归属感是独立于国家的道德性质而出现的。诸如某一群体(受到过所在国家的群体虐待)的一些成员依然支持错待了自己的国家,只要他们依然保持对国家的归属感,那么他们就觉得自己有义务维护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说,“协作义务”不是建立在“同意,或者感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归属感与联系感的基础上”的,(31) 这种“协作性的政治义务”更多地是把国家看作归属认同的焦点而不仅仅是理性选择理论家眼中维护成员私利、公平分配资源的工具,并且也再一次证明了民族国家的政治义务的非理性;它所表现出来的是高度的基于政治认同的民族归属与联系,亦即个人所属民族对于民族国家的“集体承诺”,而非基于自由理性选择的国家与个人的“契约”关系。
三、结论
在自由主义主导现代政治思潮的时代背景下,自主与理性是人们行为处事的基本价值取向。研究以张扬个人主义为主旨的自由主义与以群体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当前的时代课题,而在自由主义的语境下理解、重新建构民族主义也是时代所需。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个人自由是以某些重要方式与个人的群体(民族)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同时,群体的特别权利也能够促进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之间的平等。(32) 而所谓的“某些重要方式”或“特别权利”,在自由民族主义者的视野中则是“文化权利”。一个群体或社会的文化之所以有价值,不仅在于其成员无法选择且必须接受自己出身的社会文化(即文化归属),更在于只有通过其所处的社会文化,人们进行的一系列选择才可能有意义。可以说,自由民族主义关于“文化权利”是群体权利的观点搭建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沟通的桥梁。在自由民族主义的分析模式下,一个民族的自决权的实质就是文化权利的实施。为了保护这种文化权利,在不触动现有国家政治格局的情况下,民族可以以独特的文化认同为基础实行“区域的自治”,这种自治的本质是“文化自决”而非“政治自决”。这既保证了少数群体文化较之主流文化的公正与平等,也利于促进文化的多样性。
关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讨论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论题,在自由主义的话语里,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理论中无疑暗含着对人是“理性”的肯认。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极大地影响了理性选择理论,并使之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社会分析理论。但是,通过对理性选择理论关于“民族”的认识以及基于自由民族主义对之的分析,我们发现理性选择理论对于民族研究存在重大缺陷,最为严重的缺失就是以个人主义为基准的价值取向与以维护独特的文化共同体——民族(或族群)——利益间的矛盾。基于理性的“经济人”的选择与基于“民族认同”的民族成员的选择,在出发点与最终的归宿上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依据理性选择理论关于“民族”的认知来处理当下的民族问题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而在行动上则可能是有害的。虽然一些学者主张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修正与完善,(33) 但是由于其个人主义取向的前提假设,仍然不足以弥补理性选择理论对民族研究的缺陷。
总之,理性选择理论虽然对群体研究的某些方面有所裨益,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它并不适用于作为历史、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研究;而自由民族主义关于少数群体文化是群体差别权利的观点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完全吻合。可以说,自由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与分析模式不仅对于研究当下民族与民族内部成员之间、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更加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操作性,也为民族政治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注释:
① [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英文版主编,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78页。
② 杨国荣:《理性与非理性——以人性能力为视阈》,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③ 在社会学理论中,韦伯区分了4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的行动、传统的行动。从合理性角度看,韦伯认为,只有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行动才属于合理的社会行动。详见[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6页。
④ [美]加里·贝克尔著,王业宇、陈琪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7页。
⑤ 丘海雄、张应祥:《理性选择理论述评》,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⑥ “公地悲剧”:假设一片草地为多户牧民所有,如果大家都只管放养而不管养护,草地必然沦为荒地。如果大家达成放养三个月、休养三个月的协议,则可保证草地的延续;如果有人趁休养期偷偷放养而破坏协议,就可以一家独占草地;若是人人都来偷偷放养,必然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损毁。详见华世平主编:《西方人文科学前沿述评·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⑦ “囚徒困境”:两人作案被抓,但警方没有确凿证据。于是警方向两个囚徒提出,如果甲揭发乙,则甲获自由而乙将获刑10年;如两人均交代,每人需服刑1年;如两人均拒不交代,两人则因警方无证据而获自由。在权衡利弊之后,囚徒均选择了交代罪行。该困境实则是讲个人理性的选择会导致集体行动不理性的结果。详见华世平主编:《西方人文科学前沿述评·政治学》,第31页。
⑧ “集体行动的逻辑”:如果集体行动的结果会使个人受益的话,个人会参与集体行动;但如果集体行动的成果不能排除非参与者享用的话,个人参与的激励机制就不存在了,理性的个人就会“搭便车”。详见[美]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钟开斌、王洛忠、任丙强等译:《政治科学新手册》(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761页。
⑨ Hechter,“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in John Rex and David Mason (eds.),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⑩ Sinisa Malesevic,“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Ethnic Relations:A Critiqu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5,no.2,1 March 2002,pp.193-212.
(11)(13)(14) Sinisa Malesevic,“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Ethnic Relations:A Critiqu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5,no.2,1 March 2002,pp.193-212.
(12) 转引自Sinisa Malesevic,“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Ethnic Relations:A Critiqu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5,no.2,1 March 2002,pp.193-212.
(15)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3—74页。
(16)(20) [以]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59、9—10页。
(17)(18) 转引自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7—48、49页。
(19) 转引自[以]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第9页。
(21)(22)(24)(25)(26) [以]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第16、23、79、79—80、83页。
(23) [加]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67—168页。
(27)(28)(30)(31) [以]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第66—67、615—618、134—137、139页。
(29) Walker Connor,“A Primer for Analyzing Ethno National Conflict”,in S.A.Giannakos (ed.),Ethnic Conflict:Religion,Identity,and Politic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2,p.36.
(32) [加]威尔·金利卡著,马莉、张昌耀译:《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全体权利理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33) 详见陈彬:《简评理性选择理论:困境与反思》,载《东南学术》,2006年第1期。
标签: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