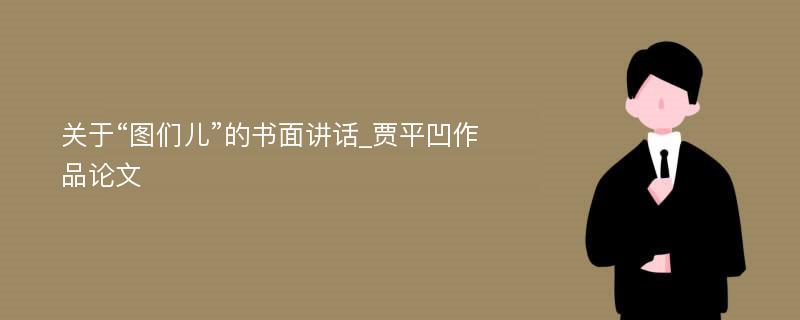
笔谈《土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土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土门》是贾平凹近期创作的长篇小说。问世以来,读者中或褒或贬,众说不一,这本身就说明作品提供了广阔的批评空间。为此,本刊特邀我市几位学者和青年学生,对《土门》各抒己见。旨在活跃本刊学术空气,以飨读者。
《土门》的文化心态
在当今的小说作家中,大概很少有人像贾平凹这样,引起众多争论。不光他此前的《废都》等作品,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土门》,也一样是众说纷纭。这主要是由贾平凹那种浓郁而复合的文化心态所决定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贾平凹是由乡村迁移到城市而又未割断与乡村联系的作家。城市与乡村的强烈对比,现代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巨大冲突,促使他思索中国的社会问题,《土门》就是一部以寓意性的艺术方法探寻我国改革、转型期人们的心灵状态的一部作品,作家深层次的审视思考,使《土门》具有了某些形而上的特质和玄机。
从文本中透视出,一条积淀深厚的独有的文化血脉主宰着贾平凹的身心,《土门》从语言到意境都可读出古典文化的浸润。但情绪线又活用了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其中又不乏隐喻和象征,作品走着一条兼收并蓄、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
作家复合的艺术心态催生出《土门》复合型的环境和人物。仁厚村置于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的边缘,城乡的结合部。并且,村落又正处于拆迁建楼的特定时刻。
《土门》中的人物形象没有达官贵人,匆匆行走的依然是吃五谷杂粮的芸芸众生。具有戏剧性甚至荒诞色彩的是,仁厚村村长成义有着典型的农民心态,开肝病诊所挣了钱,就用来修碑,立牌坊。同时,成义竟是一个因热心于公益事业而盗窃秦俑头宝贵文物的飞天大盗。成义的形象让我们想起贾平凹极圆熟地玩过的土匪系列。成义与《美穴地》中的柳子言、《五魁》中的五魁,有极大的相似、相通之处。他有危害社会秩序的一面,又有以淳朴的情感带领村民守卫故园的一面。守旧违法与甘于献身是实实在在地糅和在一起的。
贾平凹用整个生命体悟这个世界,在他的作品里,传统文化,宗教佛理,审美情趣都是交融在一起的。比如,佛家转世的观念,被贾平凹在《土门》中加以放大,并多次出现。如书中那条“亮鞭”的俊狗阿冰,便被描写成是某位漂亮农伙的转世。贾平凹以叙述人的口气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狗命,与狗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者说,我们的前世就是狗变的。”
作家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是超然的,以非功利、非道德的眼光去看待现实发生的一切;一方面又是体认与参与的,以一种感伤的情绪解释改革时期的阵痛。
不可否认,在贾平凹的文化心态中,有对农业文化的亲情感。但他深深知道,城市文明事实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决不可以逆转和倒退,而应着眼于寻求城市文明的健康良性发展。当然历史的必然要求和现实的需要间发生激烈冲突时,悲剧是肯定要产生的。传统的守旧心态也只能在迅猛的现实发展面前土崩瓦解。
作品让我们体悟到:在改革中,旧秩序旧观念的革除和新观念新秩序的重新建立,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心理结构重新安排的过程。拒绝这个过程,尾骨恐怕会很突出的。
那么,可以有理由说,贾平凹的复合型文化心态,正是其传统的情感体验与现代的理性意识所构成的深层冲突。也只有经受了生活的深层苦难,并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人,才会有这种惊心动魄的痛苦描写,并使其中掺有类似于黑色幽默的喜剧感。痛苦于是就成为作家的生命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在《土门》的文化复合中,农业文明重于城市文明,阴气盛于阳气,主人公梅梅表面是个女人,但其心态与行为却有着浓厚的男性特征。这是十分令人困惑的。
再读《土门》
小说《土门》叙述了仁厚村被西京城吞并而消亡的故事。这是否给人以两种生活方式、两种文化形态争斗和嬗变的启示呢?
小说里的现实自然是作家虚拟的现实,但这种虚拟也必须以客观现实为根基,反映着现实的某些本质真实。现实主义文学是这样,即使西方所谓超现实的种种文学流派,也不能逃避这个规律。如果我们把《土门》放在客观现实的座标上进行一番审视,给人的就不是什么文化启示,而是一团疑惑和迷惘。
首先,仁厚村是小说着意拼凑的一个寓意符号。作者不惜挖掘几百年来的文化陈迹,来强化仁厚村的文化意味。问题在于是什么文化意味呢?这里有对三皇五帝、天地宗亲师的盲目崇信,弥不漫着由曾文公家训相沿成习的村规民风。显然,这些都属于封建文化的范畴,而且是封建文化中最陈腐、最破败的意识和观念。身处90年代的仁厚村人对这些文化糟粕恪守不悖,哪还有一点当代农村的新鲜气息呢?西京城又怎样呢?更是充满着野蛮、盲目、堕落、阴郁等弊病。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惑:这是当今的一座现代城市吗?当然,这也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但是,存在不等于真实,更不等于本质,因为这种存在只能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方面,而现实生活的另一面,即光明、健康、令人鼓舞的一面(在笔者看来,这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是客观存在),是被作者忽略了,还是被作者故意抹煞了?这种只见假恶丑,不见真善美的虚拟,能反映时代的真实吗?能揭示时代的本质吗?
当然,作家写什么是作家自己的事,但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精神展示,精神吁求。作者不仅虚拟了这样的仁厚村和西京城,而且还人为地把它们拉到一起,让它们进行一场生死较量,并以仁厚村的消亡为结局。这样,作者就完成了自己整个精神图式的建构。这个图式内含着作者的什么精神意图呢?是在作两种文化形态的比较、选择吗?如果说是比较,一个是落后、陈旧、专制的仁厚村,一个是野蛮、堕落、凶恶的西京城。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比较,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是选择,选择谁呢?是回到仁厚村,还是走向西京城?可见,作者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比较选择的余地,即任何选择都是令人失望可怕的。实际上,作者的意图并不在这里。在作者看来,仁厚村与西京城的较量,只不过是一场丑陋与丑陋之间的较量,这里面,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没有标准,没有规则,至于谁胜谁败,何去何从,就变成一件毫无意义的事。那么作者到底想告诉读者什么呢?实际上是渲泄了一种世纪末的颓废情绪,即一切都令人悲观无望,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是虚无。可以说,这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一条意脉。请看,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就提出了“人的归属问题”,到结尾给以解答:人们像仁厚村人那样,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存身,无立足之地,唯一的归宿是回到母体的子宫里去。虽然小说以“神禾塬”的传说作了暗示,但“神禾塬”也同样是个虚幻的若有若无的影子。这样,一切皆虚无的情绪意识便成了小说的贯穿意识,统领意识。这大概就是小说中所说的“健全的意识”吧。拿这种意识,能挽救仁厚村的落后吗?能医治西京城的弊病吗?显然都不能。
勿庸讳言,我们处在一个多种文化融合、碰撞的时代,往往真假并存,美丑混杂。人们在这种文化驳杂、观念混乱中要作出自己的选择,的确需要有健全的意识和观念。一切有良知的作家应当提供鉴别真假、善恶、美丑的艺术参照。《土门》所展示的虚无意识,对精神正常的读者来说,有什么参照价值可言呢?只能泯灭读者对美好和未来的一切向往和期待,而走向悲观厌世、虚无绝望的泥淖。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虚无是一种消极没落的思想意识,有百害而无一利。只有科学的自觉的意识,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称得上健全的意识和观念,才能挽救人们的灵魂,从混乱盲目中走向清醒和自觉。
如果说《土门》给人以启示的话,那就是:作家的世界观、思想意识对文学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便有什么样的作家和文学。这已经被全部文学史所证明。不管作家们提出多少条理由来回避这一点,也不管社会上盛行多少种文学思潮,它仍然是横亘在作家面前的一个铁门槛。只有那些以科学的世界观和进步的思想意识来拥抱时代的作家,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者。同时,善良的读者们需要那些反映时代真实,能给人以鼓舞和信心的文学作品,而不需要虚无和绝望,这是人民的期待,时代的要求,文学为了满足这种期待和要求,作家们只有以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以科学的态度去观察生活,进行创作,才有可能。这是不容怀疑和动摇的。所谓文学走出低谷,变困惑为清醒,从而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契机大概也就在这里。当然,这已经远远超出读《土门》的话题范围。
社会的真实还是观念的图解
贾平凹的《土门》,讲述了农业文明的载体仁厚村如同一条小舟,在工业文明的浪涛中被击得粉身碎骨。仁厚村的“大脑”成义为护卫这条小舟殚心竭力,甚至不惜以身试法,被子弹敲碎了脑壳。
成义誓死护卫的是什么?死得值不值?
在我看来,成义们护卫的是虚幻的“集体”,是没落的、与历史背驰的文化。仁厚村中弥散的不是“商州系列”中的温柔敦厚、清澈纯朴,而是封建宗法文化排泄出来的垃圾:邻里之间鸡争狗斗、飞短流长;权力阶层拉帮结派、勾心斗角;权要对平头百姓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成义唆使高丰打连本的嘴巴,开除眉子的村籍等,让人又见识一次封建专制或极左政治的幽灵。坦率地说,尽管成义为了他心中的桃花源,为了仁厚村而把自己送上了祭坛,但我觉得这不是崇高,而是滑稽,不是悲壮,而是可怜。仁厚村并不仁厚,成义也不是成就大义,他使人想起清朝灭亡时那些以身相殉的遗老遗少们。这或许就是女主人公突出的尾骨的隐喻吧。
我一直景仰贾平凹是负责任的、有深度感的当代作家,甚至他那如农民般的朴拙相貌也给人以信赖感,于是总是企盼他再次捧出有力度的新作,但《土门》却令人失望。
中国农民在计划经济时代,比之城里捧铁饭碗的职工,他们是二等公民。因此,让自己或孩子谋取一个“大粮本”,近乎一种神圣的理想。于是改革开放后户籍政策放宽时,他们不惜以重金来“农转非”。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农民又是最重实际的,他们不会为什么“耕读人家”、“山明水秀”(这是旧文人的理想)而放弃可以发财的机运,更不会去誓死保卫穷贱苦累的旧生活。因此,《土门》便在社会真实的明镜映照下透出了假。即使是为了表现传统的惰性,也不能用纸糊的砖瓦去盖楼。
新潮时装被模特们穿上后在电视上朝过相,立刻便引起大众的模仿与流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有回归原始(寻根意识)的潮流,如艾略特在《荒原》中怀念没有污染的远古的宁静和飘逸仙女的田园氛围,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表现对原始纯朴的怀恋和对纯粹自然的崇拜等。这些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引发了热闹的寻根文学景观,于是便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白桦的《远方有个女儿国》,铁凝的《哦,香雪》,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这类讴歌原始纯朴或传统美德的作品在精神上与文化学中的国粹派有某种联系,这是文坛与学苑的呼应。但传统文化中有美丽也有丑恶,鲁迅曾激烈地斥为“吃人”文化。因此有人对当代新儒家以及寻根文学等冠之以社会转型期的“新保守主义”。扎西多曾调侃贾平凹作品的意识深层“拖着一条油腻腻的辫子”。不知贾氏是为避嫌还是创作上萌发新的契机,于是便写了《土门》,传统的“尾骨”和“亮鞭”在新文明大潮中不堪一击。但依我之愚见:传统文化是立体的,其精华与糟粕、正面与负面血肉相联在一起,对文化的二元分析往往导致片面;由此,好的作品也应是立体的。“商州系列”中对传统的肯定和《土门》对传统的否定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平面化展示,因而便缺乏文化底蕴的厚度,失去了生活的仪态万方、变化无穷。《土门》的编辑按语说:“以革命和自由的名义筑造专制的祭坛……这就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激烈反弹的氏族文化本能”。但血缘文化一定是现代文明的阻力吗?国内外学者总结东亚四小龙起飞之因,曾认定“五缘文化”为助推力,其中便包括“血缘”和“乡缘”。今日温州人在本土、外乡乃至于外国靠血缘家族的亲合力使钱袋越来越大。生物遗传基因的链条只要稍微打乱排列次序加以重组,便立即产生新的生命形式。文化诸因素在不同的社会背景、机制下的重组,亦有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因此作家和文化学者都不能以静态的平面的思维视野去观察与界定社会文化。立体的思维才会有立体的作品,才会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巴尔扎克的“百科全书”,才会有当代文学的超越。我仍在期待着贾平凹。
《土门》的探寻情结
《土门》是一部给人以沉重感的小说。《土门》中的范景全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怎样才能当个好小说家呢?
作家必须对自己时代的戏剧性事件有充分认识,每当他能或者知道应怎么做时,就必须坚决站在某一边,但他也必须不时地坚持或继续保持某种与我们历史相关的距离。如果必须分担时代的灾难的话,那他同时也必须使自己离开这种灾难,以便考察那种灾难并赋予它以形式。一方面,谴责当受谴责的东西,要嫉恶如仇,坚决有力,另一方面,最终也应赞扬仍值赞扬的东西!
范景全是一个学农业而写小说的人,是一个使自己离开这种灾难,以便考察灾难并赋予它以形式的人物。从范景全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贾平凹的影子。贾平凹从商州乡土山野走向了西京楼群,也藉此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化。作者能够把农业文明浸润下形成的“乡村美、都市丑”的审美观念置于脚下,在《土门》中用比较客观的眼光去面对现实,实属不易。
仁厚村是一个文明与野蛮共存的小村,以成义、梅梅为代表的村民固守着这块未被改造的土地。他们如原始部落抵御外族入侵一般,古墓、云林爷治疗肝病的药引、市长题名的村牌楼、明王阵鼓等就是矛、戈、刀、戟。同时仁厚村的骂街、内讧、为狗“阿冰”和别人聚殴、搞“堆粮袋桩”的低级游戏等一系列表现又揭示了他们自身的劣根性。这些都喻示了仁厚村被改造的必然性。落后就要挨打,而今天,处在工业文明包围圈中的落后显然就会被改造。仁厚村最后在无可奈何中接受了城市文明,就是佐证。这一结局是否说明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的全盘肯定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立于时代的高度,作者承认这种改造的必然性,但他并未由此走向完全认同工业文明。因为“都市对在传统美学中浸淫已久的文化人来说,不仅意味着被林立的大厦逼窄的天空,被灰色的立交桥遮拦的景观;还意味着工具理性的冰冷尺度和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西京城内警察捕杀无证狗的冷漠的脸孔,骚乱的球场,赶时髦的表现以及卖淫嫖娼、倒卖房地产等现象可看作是“工具理性的冰冷尺度”和“物欲横流”的注释。作者在《土门》中并没有非此即彼地看问题,而是全方位地观察社会,理性地审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是在这种观察和审视的基础上,作者推出了“神禾塬”。这个地方“有完整的城市功能,却没有像西京的这样那样弊害……更没有农村的种种落后,那里的交通方便,通讯方便,贸易方便,生活方便,文化娱乐方便,但环境优美,水不污染,空气新鲜。”显然,这是一个农村与城市对接后形成的文明的理想化模式,一个未来社会的文明的蓝图。“神禾塬”的完美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一个理想方向,同时,“神禾塬”的提出又体现了作家对社会的深刻观察、思考和剖析,体现了作家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一个作家首先面临的是观察社会,研究社会状态,他观察的结果被写入小说,被小说纳入的部分有多少可以成为正在形成的历史,小说本身的价值就有多大。”《土门》这一段话至少表明了作家某一时期的创作观。或许,《土门》终将因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文化冲突的艺术表现以及“神禾塬”这一完美的社会形态的呈现而形成其历史的和社会的意义,从而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吧。
循环与错位
我欲切近《土门》,扣响其门扇,窥见其堂奥。于是,我读这部作品循环形路线前行、上升,遂于首尾衔接处旁逸出去,经过隧道的黑暗,赫然便见一门,此即土门也。但是,土门——是什么呢?依海德格尔所说,艺术的本质应该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土门》作为艺术作品,也必得守护、持有和敞开着什么吧?思考这种方式,是有趣的。
我称《土门》的结构为Q形结构。《土门》借这种方式完成艺术循环,并衍生出一条孱弱的乌托邦尾巴。作品起首近乎展示地描绘了屠狗的场面,中间意味深长地穿插了一段凶杀案的描写,这样,屠狗与杀人巧妙地联系起来,形成了映照,奠定了作品的基调。“亮鞭”的土狗阿冰,侥幸逃离了这场劫难,它引领我们到仁厚村,经历了仁厚村人的种种怪诞之举,之后便匆匆地奔赴终点。作品的结尾重现了杀人与屠狗的场面:仁厚村的统治者成义被枪毙,阿冰也被残忍地勒死。至此,观照之眼遍观了梅梅的种种精神苦难,重新置于原来的起始点上。显然,这种闭锁结构见出一种意志,一种机智和一种情感,但结尾对起点的仿同并未增添新的意义,如同回旋曲那样,原来的旋律又被重新奏响着——人是土命,像狗那样。被连根拔起的人,就如同丧家犬,免不了恐惧、忧伤、愤怒和彷徨。这,大概就是《土门》呈示给我们的吧?
Q形结构的小尾巴是《土门》的尾骨,如梅梅的尾骨一样,虽然显得突兀和矫情,但却并非没有意义。在《土门》的最后一节,有一段关于母亲子宫的幻想。梅梅于走头无路之际,联想起在母体内的舒适之感,认母亲的子宫为自己的家园,这个家园却又叠印上“神禾塬”三个大字。“神禾塬”在作品中借范景全之口只出现过一次,它是苍白无力的,曾被成义所否定。但此时却与对母亲子宫的幻想联系在一起,显然就有了乌托邦的味道,它是不可能给漂泊无根的人以家园之感的。
在我看来,母亲子宫的譬喻恰好揭示了“土门”的意味。土地可不就是我们的生身之本和永恒的母亲吗?《圣经·创世纪》中耶和华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四肢着地的云林爷则对梅梅这样说:“你从哪儿来就往哪儿去吧。”《土门》后记中说:“土与地是一个词,地与天做对应,天为阳为雄,地为阴为雌。”将诸种意思在鉴赏基础上参较领悟,“土门”的含义似乎就昭照若揭了。母亲是土地,“土门”是母亲生养之门,在此对女性生殖器官的描写均应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来领悟。人立于土地,在土地上行走,土地蕴育了人的根本,《土门》这个寓言所守护的,大概就是人的存在之根吧。
《土门》的叙述方式,就是完成其Q形结构的具体方式,欲进入《土门》,读者须得借助梅梅的一双慧眼。梅梅是作品中极特殊的一个人物,她思想她行动她抒情她议论,整部作品都以她的口吻写成,是她的手记一样。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中,男性作家取了女性的视点,揣摹了女性的心理来写作,并不鲜见。比如《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都是写得好的。但是《土门》却是通篇都采用梅梅这个视点的。梅梅处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位置上,她既要扮演故事中的主角,又要不时抽身出来叙述这个故事,这就给整个作品增添了一种反思的追忆往事的色彩,迷离恍惚的感受,梦境般的意识流动。这些大概都缘于此吧。
我称《土门》的视点为彩色视点,这种彩色是由集叙述者与参予者二任于一身的梅梅提供的。她既然参与到事件当中,她的叙述就不能不带上她的情绪、意志和认知色彩。《土门》提供了富有色彩的事件,读者对色彩的感知,恰好是通过梅梅这双有色的眼睛看到的。由上述道理可知,对《土门》视点的分析,与对梅梅这个人物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重叠在一起。因此,通过对梅梅形象的分析,对《土门》视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就被提供出来了。读罢这部作品,有一种奇怪的感受,从某种角度来说,作品中次要人物的形象反倒是比较丰满易于感知的,比如着墨不多的老冉的形象。而主要人物如成义、梅梅、云林爷的形象却很难树立起来。以梅梅为例,她既不是成功的典型,又不是失败的典型,从典型理论入手恰搔不着痒处。实际上梅梅是个运动的视点,是置入作品中的艺术假设。在此意义上,我称《土门》的视点为伪女性视点,梅梅的所作所为正好揭示了她的非女性特征。具有寓言意味的是,梅梅生着突出的尾骨。尾骨的表层象征意义很容易得到分析,在此层面上它是一种“返祖”现象,如同隐埋在仁厚村地下历史久远的石碑一样,是对仁厚村古老传统的一个讽喻,随着仁厚村的挣扎,它还会进一步发育。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它倒并不具有什么魔幻色彩,而是梅梅的男性表征,是退化变形予以伪饰的男性生殖器。
在《土门》中,性的错位是被刻意地安排的,如阿冰极具女性的漂亮,却有着一条“亮鞭”;成义强壮剽悍的男性躯体却嫁接着一只女人的手;老冉虽是男性,却不时流露出女性般的柔弱,梅梅虽是青年女性,却像男人一样思维和行事。因此,尾骨的这一象征意义即使潜藏于无意识层面上,却也是客观真实的。伪女性视点的成立是借倒错法来实现的,《土门》的Q形结构也是靠倒错法来完成的。设若没有男与女、人与物、城与乡、神与人、古与今的错位,《土门》还能剩下什么呢?伪女性视点的采用,给《土门》带来了乖戾阴郁之气,仁厚村既不仁,也不厚,充满着浮躁、困扰与乖张。这一视点贯穿着整个《土门》,造成了一种笼罩一切的主观性,人物极好发议论,实际问题往往得到抽象化处理,在辩驳中明确宣示出来。因此《土门》虽然涉及了尖锐的现实问题,但很明显,它并不致力于提供什么方案,在我眼里,它反倒是远离了这些,营造了一个现代寓言。
我欲切近《土门》,经此一番思考,不知是否真的近了。也许,一切都是误读。我知道《土门》在守护着某种价值。于作品中它是被赤裸裸的声调刺耳地言说着的。这种言说的浮躁形式恰恰揭示了生存的窘迫。海德格尔说过:“安居是凡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但是凡人往往刻意求取安居的本质,孰不知越走越远,无家可归的困境正在这里。仁厚村即使不被从大地上拔除,仁厚村人也久已失却其根了。“大地取司负载,成就春华秋实;大地延展为岩石流水,生发为植物动物”,大地负载我们,我们亦必将开启土门,进入大地中的安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