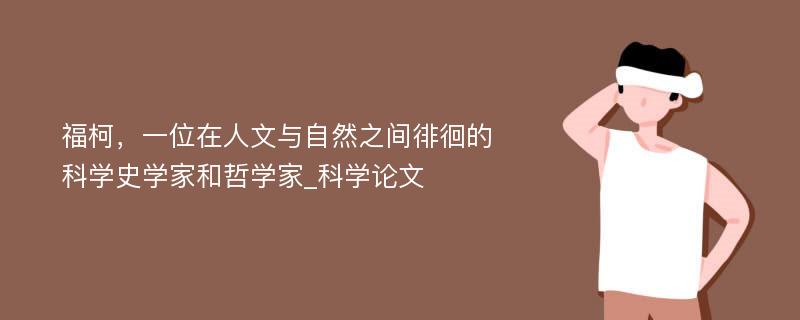
徜徉于人文与自然之间的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福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史家论文,哲学家论文,人文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福柯是纯粹的人文学者还是科学史家或科学哲学家?对他定位似乎是困难的。例如,他在《词与物》一书中同时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了研究。而《临床医学的诞生》似乎是地地道道的科学史著作。与之有些相似的《古典时期的疯狂史》则很难说是科学史著作了。但这些著作无疑都具有思想史性质。《规训与惩罚》便被认为是一部社会思想史著作。如果说以上著作可以差强归类到某个学科的话,那么福柯最后未完成的著作《性史》就使人难以确定它到底属于那个领域了。划分领域然后研究几乎是一种学术习惯,而福柯完全打破了这种习惯,徜徉于人文、社会与自然之间,并把扭转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传统划分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之一。本文试图探究福柯与科学的关系,并考查他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思想。
1 学术之路:从科学与人性开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这位可与黑格尔相提并论,并且最深刻地创新了思想形象[1]的哲学家的学术之路是从对科学的关注开始的。当然他关注的不是自然科学的哲学、科学理论的结构等问题,他关注的是科学的政治地位和科学所能传递的意识形态功能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可归结为两个词:权力与知识”[2]。这些问题正是福柯的成名作《古典时期的疯狂史》(1961)的写作背景。也就是由这部著作开始,福柯确定了他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对象。他曾经这样谈到:“如果对像理论物理学或者有机化学这样的科学提出它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关系问题,是否过于复杂?可能的解释标杆是否放得过高?相反,如果换成精神病学,问题是否更容易解决?因为精神病的认识论曲线比较低,还因为精神病学实践与一系列制度,直接的经济要求,以及具有社会调节作用的政治急需联系在一起。”[3]这样一种取向导致了他后来的一系列研究。
福柯与科学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表现在他的求学经历上。他除了拿到哲学专业学位以外,还获得了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学士学位。在求学期间有过在医院实习的经历,曾经给病人做过脑电波的测量实验。这些为他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法国的学术环境和科学史家对他的影响。法国哲学机构(教学和研究部门)与众不同的一点是逻辑学家很少,自然科学史学家很多[4],而且科学史在法国的当代文化争论中占有核心位置[5]。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然科学史家亚历山大·科瓦雷(Koyre)、加斯东·巴什拉(Bachelard)和乔治·康纪莱姆(Cangulhem)等。福柯继承了巴什拉的科学观。概括地说,他吸收了巴什拉把研究那些模糊而受到忽视的领域作为他挑战科学史的正统观念的方式[6]。康纪莱姆对福柯的影响,可以从福柯在1965年6月写给康纪莱姆的一封信中看出来。福柯写到“假若那时没有看过您的著作,我肯定不会完成以后的研究”。[7]“那时”是指《临床医学的诞生》写作之前,“以后的研究”即是指对临床医学的研究。康纪莱姆对不连续性主题的重新提出和对生物学中概念史的研究深深地触动了福柯。福柯认为“物理学史上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时刻,是理论的形成与建立,但是在生物学史上,有价值的时刻乃是对象之建立和概念之形成”。[8]
福柯的学术生涯与科学史有着深厚渊源,但他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史家,甚至德勒兹认为“福柯从未成为历史学家,福柯是创造另一种历史关系的哲学家”。[9]福柯通过历史研究讲述他的哲学[10],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科学史研究讲述的。对历史的研究使得福柯的哲学显得厚重而有说服力。他通过对空间上局部、时间上确切领域的历史研究,达到了对现代哲学地批判。他重新考问主体、质疑人性。与此同时,也得出了关于科学哲学的一些重要命题,如学科的产生、科学知识的集体生产。在福柯身上充分体现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互相依存的特征。历史研究为其哲学提供根据,而哲学显现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但是,在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上,“它们之间的距离曾经非常遥远。历史学家认为在他们的研究中处理认识论问题是不适当的;哲学家则认为无须‘俯身’求教于历史记录”。[11]劳丹批判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这种分离关系,并预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结合是发生在科学思想史中的。福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结合的典型。
虽然福柯的学术生涯与科学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他也与利奥塔一样是出于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人性的关注而研究科学的。作为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只不过是作为思想家福柯的一个方面。他其实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者,这表现于他在科学史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上。法国的科学史学者主要对科学对象的建构问题感兴趣。福柯提出的问题是:人类主体怎样使自身成为知识之可能的对象,通过哪些合理性形式,通过哪些历史条件,以及最后,付出了什么代价[12]这个问题贯穿了福柯的主要著作,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其中最具科学史性质的是面对医生的病人这一特殊主体和客体。病人作为人本身是认识世界的主体,而作为医生研究诊断的对象又成为客体,病人同时具有这两种身份。那么人们怎样才能说出生病主体的真实?福柯在科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充满人性的问题。
福柯虽然是从科学史入手,从思考科学的政治地位和科学所能传递的意识形态问题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然而这只是他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权力-主体问题思考的切入点,他并没有停留在科学史研究上。福柯感兴趣的是人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人是知识的主体,但是当人作为病人的时候又同时成为了知识的客体。人这一特殊的不同于普通物质的研究对象,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领域。这一领域处在人与自然对立的中间。但是主体的人成为了研究的客体,在正常人看来他也就缺少了人性,而多了物性,也就是可以被当作物来对待。而历史上同时既是客体又是主体的特殊的人是精神病人、病人、被监禁者。福柯的研究由此越来越远离科学史,越来越成为一位通过各个方面来阐述知识-权力-主体问题的哲学家。正是从同时具有这两种性质的领域开始,正是这研究对象与众不同,使得福柯从科学史开始,却踏上了越来越远离科学研究的道路。对人性和主体的关注成为了他研究的主题。
2 学科的产生与对科学权力的批判
福柯认为,“18世纪是一个使知识纪律化的世界”[13]。也就是说一方面形成了挑选知识的标准以排斥假知识、非知识,另一方面又对知识内容进行规范化、同质化和等级化处理。最终形成的是某种公理化知识或者集中化具有内在组织的知识。这样就把每个知识按学科分类进行整理,于是出现了科学知识的学科化。科学知识学科化的一个结果是:科学成为文化中具有独特个性的一部分而独立出来。福柯就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界定了科学,他认为“科学是我们文化中一部分的事实和限制”[14]。科学学科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科学与哲学的真正分离。福柯认为:“哲学作为创立者和基础的角色消失了,哲学从此不再在科学知识和知识进程中有任何实际作用。”[15]科学的学科化在拒绝了哲学的同时,就开始了唯科学主义之路,也就为后来形成哲学向科学靠拢以及发展出不依赖科学的哲学,这样一种科学与哲学关系埋下了种子。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就是他这种观点的一个案例。此书主要讲述了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医学知识的同质化、规范化、划分和集中的工作。虽然18世纪的科学不像它前面的17世纪也不像后来的19世纪那样成果璀璨,但是完成了由哲学到科学的彻底转变。福柯也正是在对知识纪律化或者学科化的分析当中,得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集中的权力”的观念。
福柯认为知识的纪律化,国家干预起了较大作用。他认为:“国家在知识斗争中通过四个步骤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干预。首先,取消和贬低人们认为无用和不可通约的且在经济上昂贵的知识;其次,在知识之间进行规范化,以使其相互配合,在它们中间互相交流,打破秘密的障碍和地理的、技术的限制;第三,按等级划分知识,可以说让一些知识套入另一些知识,从最特殊的和最具体的同时也是从属的知识,直至最普遍的形式,直至最形式化的知识,它们同时也最具有知识的包容性形式和直接的形式;最后,是金字塔式的集中,使对知识的控制成为可能,保证了对知识的挑选,使其可以既自下而上地传播知识的内容,又可以自上而下地传达占优势的对整体的指导和组织。”[16]
科学知识的纪律化主要是在大学中完成的。福柯在此揭示了大学除了挑选学生之外的又一功能,即挑选知识。“大学通过事实的垄断和权力来扮演挑选的角色,这使得不是诞生和形成于这个大致由大学和官方研究机构构成的制度领域内部的知识,即在这以外诞生的处于原始状态的知识,一开始就自动地或者被排斥或者先验地被贬低。”由此,知识、大学和权力的内在关系显现了出来。现代大学出现的一个结果是“业余学者消失了”[17]。这是18和19世纪的著名事件。它与16、17世纪的情形正相反,那时除了一些医生,实际上没有哪个一流科学家具有大学教授职位,就连剑桥大学的牛顿虽然在大学工作,但是他的科学著作却是在英国皇家学会这一实际上是私人组织的帮助下出版的[18]。当时的大学与天主教会有密切联系,大学中的教师几乎都是牧师,而大部分学生将来都会任神职。在大学中既不讲授也不学习科学知识,这表明科学在那时还不是社会中的主流。业余学者的消失,表明科学知识进入大学并占据了文化的主要地位,并与国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福柯认为学科的产生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科学知识的纪律化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化。他采用谱系学方法来解构科学所具有的集中权力。他认为谱系学是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不合法的知识运转起来反对整体理论的法庭”[19],甚至认为谱系学是反科学,是对具有集中权力知识的造反,而不是反对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这个集中权力与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福柯对知识集中权力的反对,来自反对背后控制挑选知识的权力机构,反对独裁权力导致的巨大荒诞和恐慌。他通过对精神病人、对罪犯的研究,来批判知识的集权。正是福柯对这种局部性、被忽略的知识的研究,对中心性知识的攻击,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批判中心性强调边缘性的一个显著例证。
3 科学知识的产生与发展——认识型与转变
福柯的“科学史”没有常规地描述伟大科学家的工作。当然并不是说,福柯认为可以忽视科学巨人们在科学史上所具有的地位。他只是认为科学史上对个人创造性的谈论已经太多了,无须他多说,或者他不想再就此说什么。他试图另辟蹊径研究在科学发现、科学发明中默默起作用的规则类型。这项工作主要是在《词与物》中完成的。他在《词与物》中提出了特定时空中具有特定的“认识型”(episteme)的概念。这一概念形容了词与物被组织起来的无意识的知识空间[20]。
福柯的认识型概念是他论述知识生产和发展观念的基础。福柯认为知识生产是一种集体实践,个体及其知识在此需重新定位[21]。他以18世纪末的医学为例,如果随便翻开一本1770-1780年的医书,读上二十几页,然后再看二十几页1820-1830年的一本医书,就会发现经过四、五十年后医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人们谈及的内容还是说话的方式,以及人们的眼界和看问题的角度都有巨变。这种作用就是集体实践的结果,或者说是无形学院的结果。从这可以看出科学巨人和普通大众都是科学史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如果说伟大的科学家是求知海洋中的一座座山峰,那么普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海水。不同的历史时期,海水的成分不同,也就是有着不同的认识型。以往的科学史主要看到了这山峰,而福柯要做的是研究这构成海洋的海水。
福柯对认识型的研究使他非常自然地怀疑起科学、知识是循着某条“进步”的路线,服从于“增长”的原则和汇聚各种各样知识的原则这样一种习惯性认识。他认为认识型只是在不断的转变,而且转变前后的认识型是不可通约的。这种结论就是他对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精神病学、医学等历史发展地研究得出来的,认为它们的变化节奏根本不遵循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和缓而又连续的发展图式[22]。
福柯的这些论述与库恩科学革命的观点非常相象,其认识型概念与库恩的范式概念,几乎异曲同工。福柯提出了科学知识的集体生产论断,而库恩则提出了常规科学的概念,这两者都注意到了科学研究中默默无闻而又人数众多的普通科学工作者。他们注意到了科学发展的内在结构。
4 科学与知识考古学
库德曾经提出的问题“何为启蒙?”是20世纪中期法国哲学界争论的主要内容。福柯的一系列“科学史”研究就是他对启蒙问题的反思。利奥塔与福柯都非常注重这一问题。他们是巴黎高师的同学。利奥塔通过分析科学知识的合法化问题揭示了启蒙的虚妄性,然后着重描述20世纪中后期最发达国家的科学知识状况。福柯却彻底批判了启蒙运动中科学知识与宗教迷信、文明与愚味的严格对立,并揭示进步与理性的虚妄性。而这种结论的得出就是福柯研究现代科学形成时期历史的结果。福柯的科学史是一种“另类”历史,因为他反对那种已经成为常识的进步理性的科学史。
福柯的考古学是一种广义的知识史研究。这种研究从话语实践入手,不注重思想流派研究。福柯认为话语实践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他对知识的界定就是“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23]。由此可见科学知识在福柯那里只是知识的一部分。
福柯的考古学对科学的考察也是通过话语实践开始,不研究思想流派,这样就避免了主体的问题,同时也就开通了对集体生产知识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福柯创造出了认识型概念。认识型是一种在既定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24]。这样的整体是一个复杂状态,但是对其分析可以发现各种科学之间的关系。这是那种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所难以做到的。精神病学是一个典型的话语实践成分复杂的学科,正如福柯所考证的那样,具有科学性的医学知识在其中所占的成分是很少的,而其他的政治、经济的话语实践占据了很大部分。精神病学、医学、化学及至数学等形成了科学知识比例不同的学科,由此揭示出了科学的层次性。
福柯对科学、半科学和非科学的考古,不但揭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还揭示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史乃至科学哲学的景观,即科学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有一个最终的共同目标。一门科学的科学史随着它的现状不断变化而显现出多种历史过去,多种连续形式,多种重要的等级,多种决定论网络及目的论[25]。科学史也是当下与过去视域融合的一种“效果史”。在此福柯与伽达默尔的历史观正好一致。科学哲学会随着科学史的丰富化,变成有各种声音在讨论的领域,形成百家争鸣的状态。其他地域的科技文明也在这种讨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福柯的工作因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
收稿日期:2002-03-18
标签:科学论文; 科学史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福柯论文; 哲学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临床医学的诞生论文; 词与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