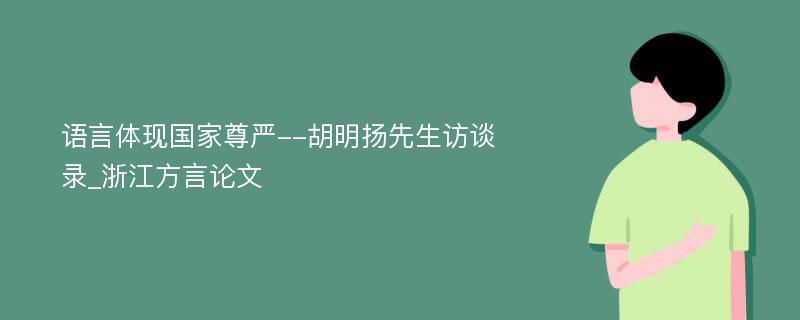
语言文字体现一个国家的尊严——胡明扬先生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文字论文,一个国家论文,尊严论文,访谈录论文,胡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刊编者的话】胡明扬,中国人民大学语言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1948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参加革命从事外事工作;195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英语教学,任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对外语言文化学院名誉院长,并先后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顾问。2011年6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六岁。本文系《雅言》报记者在胡先生逝世前对他做的专访。特刊发此文,以兹纪念。
语言文字热点问题
1.汉语拼音:可进一步研究、完善
记者:胡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和您聊一下关于语言文字的话题。首先,您觉得最近的热点问题是什么?
胡明扬(以下简称“胡”):现在热点问题就是繁简问题,还有对汉语拼音的批评。汉语拼音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在要解决读音问题、规范化问题。现在要推广普通话,拼音应该起一定作用。外国人学汉语,拼音也应该起一定作用。我们已经清楚拼音不是文字,那么如何把汉语拼音变成文字,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了。现在拼音文字化在网上十分流行,流通也更方便了。实际上好多外国留学生,都是用汉语拼音来发送中文。但是使用汉语拼音有个毛病。最早是1946年的时候,在东北铁路上就用汉语拼音,但仅仅几个月就停止使用了,因为不能区别同音字。那时在解放区用拼音,只需几个礼拜,不认字的农民就会写字,这对扫盲有很大作用。现在有些字读不出来,用汉语拼音标注一下即可。但是它缺点还是很显著的,一个是不区分声调,好多同音字就无法区分。即使区分了声调,依旧有很多同音字。文改会,也就是后来的国家语委根本就没人研究这些东西。
现在计算机上的拼音输入法,就给同音字研究提供了方便。拼音输入就是同音输入,需要人为选择。计算机上的拼音输入法就给研究直接点明了哪些同音字需要解决,哪些不需要解决。有些同音字只出现在不同语境里,那就不需要解决,有些在任何语境里都可以用,就必须解决。输入一个“gong shi”,就有很多双音节的同音字。以前有些人为了宣传,说单音节的有同音字,双音节的没有。这个说法太绝对,其实双音节同音字有很多。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把声调解决。以前有人用字母来表示声调,例如重叠韵母。除了韵母之外,声母方面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一个入声字,把它的尾巴写出来,规定凡是后边的“b、d、g”都不发音,那不就解决了?就表示一个闭音节,不发音,那么方言地区也能用了。吴语地区,凡是“b、d、g”都是一个紧的喉音,那么北方人就需麻烦,要记一下。北方人有入变三声,不好办,总是要记一记。任何一个语言,总是要靠记忆。口语不太需要记,而书面语就要记忆。书面语是有传承的价值,所以付出一些代价是值得的。但总要有人去研究怎么做最好。
还有一个问题,韵母的韵尾,比如“平安”的“安”和“尼姑庵”的“庵”,一个写成“an”,一个写成“am”就行了。广东话就是这样。可以根据古音去区分同音字。统计一下哪些同音字出现频率高,首先需要解决,哪些很少出现,就不理它,依据上下文去理解。不过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在研究这个课题。这样我们对拼音文字问题,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解决。
2.简化汉字:并不妨碍传统文化的传承
繁简问题,我认为这里面还有政治问题。最近马英九说“识正书简”,即“识繁写简”,就是印刷用台湾地区的正体字。于是新加坡就着急了,因为新加坡用的是我们的简体字和拼音,所以问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动。因为这一改动,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当然我们政府表示不会。
有的教授就直接表示要恢复繁体字以及批评“简化字割断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说简化字割断了传统,那么繁体字也早就割断了传统,要恢复繁体字,不如再彻底些,恢复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早就变化了。
简化字对年轻人看古书造成一定影响。比如说年轻人读古书,就不容易看懂。如“鬥爭”的“鬥”字,写成一斗两斗的“斗”。但简化字的好处很多。现在学写字容易得多,也易于扫盲。事实上使用简体字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不大,从1956年开始推广简体字,对我这个从小学繁体字的人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都看得懂。至于要读古书,那么就得去学用繁体字了。问题是我们现在不是民国初年,又有几个人读古书?连中文系的人都不读了。真正读古书的人,连甲骨文、金文也要学,这个专业性很强。应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否则就会对民众产生很大的煽动性。针对这一类的热点问题,《雅言》至少要给同学们做出解释,以免产生一些误会。
3.语言规范:是社会交际的需要
记者:您觉得除了拼音方案的完善,还有其他方面值得研究的东西吗?
胡:当年要实行拼音文字闹得很厉害,幸亏周恩来总理出来说话。他说,汉语拼音、汉语规范化还有拼音文字都是对的,但现在要废弃汉字,还不是时候,应以推广普通话、规范化为主,同时可以继续研究拼音文字。这个政策后来就被定下来了。“可以继续研究”,说了“可以”研究,却没有人研究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马上拿出来派上用场。文字改革委员会,现改称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就有人说“文字改革死亡了”,不认为规范化、推广普通话是文字改革,文字改革就是马上一步就改成拼音文字。实际上拼音文字不成熟,现在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工具。黎锦熙先生拿拼音文字写过日记,后来自己都认不得了。整理他的日记时,他的学生也认不出来,里面有些人名、事情,时间长了都忘记了。
语言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工作要继续做。为什么要规范化?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到了广东去,你一点广东话都不懂,你简直没法说话。现在推广了普通话之后,再去就没问题了。记得我在1987年去广东,要问路,问路人一句,他说一大通,你根本听不懂。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有人说在新加坡人家普通话说得比咱们还好。去年我去香港参加语言规范化的会议,他们香港大学现在毕业时必须还要再拿一个普通话合格证。这样,普通话推广就很好了。但普通话一推广,各地方言渐渐有消失的趋势,这也是个问题啊。但对于规范化,我们也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像1956年第一批简体字推广,但后来几次就有些过分了。我当时写了篇文章说,大的方向是正确的,具体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过分了。规范化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公共场所尽量提倡,这样互相可以交流,但回到自己家里可以讲方言啊,谁也不能干涉,这样就好了。做事情也都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这不是哪个语言学家别出心裁要人们使用规范语言,这是社会的需要。当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以后,这是必须要有的。在封建社会,这个不成问题,两个村子之间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互相听不懂。但现在不行,否则问个路都成问题。
有人说语言是发展变化的,所以不能规范化。这是很有问题的。正因为语言是发展变化的,所以语言是可以规范化的;如果不是发展变化的,那我们现在说的就都是古代甲骨文时代的话,上万年不变,就用不着规范化了。
正是因为世界各国进入现代以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像欧洲搞规范法则最出名的是法国,因为他们也有方言问题,北部的和南部的,南部的接近意大利,北部接近德国,互相交流也是有困难。规范语言主要是为了交际,一个民族统一以后,如果语言不统一,那么这个民族等于就不统一吧?法国最早成立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科学院最初的目的完全就是搞语言的规范化,我记得它是1661年左右成立的,它们的任务就是搞语言规范。后来法兰西科学院出版了一部规范辞典,但它这个辞典不一般,收词较少,但它主要收常用词,都是一些基本词汇,特别是学校教书会用到的。这样他们规定全国都必须用这部辞典进行教学,法国经过两三百年的规范化才达到现在这个水平。现在基本全国都能通用。规范化是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想一下子搞成也是不行的。像英国的规范化晚于法国,但现在还有方言啊,而且方言还是相当不同的。
4.语言文字:体现一个国家的尊严
记者:当下国内许多地方文字使用混乱,中文外文掺杂在一起用,不伦不类,这是对母语的不尊重。您怎么看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母语和外语的关系?
胡:我认为现在我们一些领导比旧社会的上海还要洋化,崇洋媚外。有一些没有必要用英文的地方还要用英文,比如“世界经贸组织”,中文里有这个翻译,是很好的翻译了,却一定要用WTO。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北京电视台”,一定要用“BTV”,北京人“V”的发音不会发,发成“味”的音,我说听起来就像鼻涕的味道。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翻译成“Night News”也有问题。英文里Night是睡觉后的晚上,睡觉前都叫Evening。
解放初期,上海有很多学校,讲课的时候,不是全部用英语,但是术语都是用英语的。后来国家规定,一律要改为汉语,因为教学语言是一个国家的尊严就都改过来了。现在提倡双语教学,还要求每年都检查,重点院校有多少课程改成所谓的“双语教学”。所谓“双语教学”也就是英语教学。
记者:您的英语是从小就学了吗?
胡:没有,从中学开始学的。小学开始学英语的,只有上海,因为当时上海是殖民地嘛。
记者:所以说从小就学英语没有用。我现在就想举一个例子,陈望道先生学外语是十几岁在中学才学的。他后来能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好多东西。现在许多从小就让孩子学英语的,是一些官僚和大款以让孩子从小移民为出发点的教育。
胡: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朱生豪先生,是中文系毕业的,也没有留过学,可见当时大学的公共英语的水平多么高。
这种事情就主要是教育部的问题。教育部很重要,这一次上海五个大学入学考试不考语文。我本来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都说语言学家失语。人家把矛头都指向上海的这些学校,包括复旦大学。因为别的地方自主招生考试都没有这样做,只有上海。他们首先要声明,这不是我们语言学学者的意见。
5.寄语《雅言》:突出重点、关注热点
记者:这次带来了《雅言》的合订本和最近几期,请您提点建议。
胡:主要是两点意见。一是重点不够明确,《雅言》应该以语言规范化问题为主。此外还应注意热点问题。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繁简问题,及对汉语拼音的批评这些热点问题,《雅言》应该做出积极的回应和客观的解释,尽可能地减少人们对这方面的误会。当然提倡普通话和语言规范化是根本任务。
通才和通才教育
1.1953年教育改革的流弊
记者:近年来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在教育界逐渐成为普遍认识,中学、大学也相应地做出了一些改革措施,您的求学经历是从私塾到教会学校,解放后教学科研半个多世纪,我们想听听您对当前教育的看法。
胡:我最近在两个地方讲过这个问题。一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在苏州办的国际学院。还有在北大纪念王力先生,办了一个王力学说讲座,请我去讲了一次。我就讲语言专业的学习和研究。这里面主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1953年的教育改革,现在反思来说,是失败的。它把大学都拆散了,本来复旦大学是文、理、工、农、商、学都有,之后是理科全归交通大学,文科全归复旦大学,结果文理就不通了。学生知识面很窄,甚至到了有的学生学隋唐历史,唐虞夏商周他不管,宋元明清也不管了。有一个教古典文学的老师教《离骚》,学生提问:“老师,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回答:“这个我不管,你们问古汉语老师去。我只管人民性、阶级性、思想性。”这样的话,将来毕业出来学生还行吗?只讲“人民性、阶级性、思想性”,句子是什么意思却不管。这还能学得好吗?学文科的,理工科知识一点都没有,特别是数学不行。我们这一代已经不行了,王力先生也在文章里公开说明自己数学知识欠缺。我也写过文章说自己的数学一塌糊涂。但是我们至少还知道古今中外。现在是古不通,中外也不通,文理呢,理工科一点知识都没有。这一点就是我们1953年教育改革以后,太专了,学中文的不学外文,学文科的不学理工,所以现在要做出什么创新的,没有可能性。现在的创新都是交叉科学,学文科的一点数学基础也没有,你怎么办?学中文的一点外文也不懂,你又要吸收外国理论,你没有看过原著,那怎么行。1953年的教育改革是学苏联的,苏联是1917年的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百废待兴,特别要发展工业。但发现学机械的大学生,到了工厂不会开机器,设计也设计不了,必须要经过一两年工作以后才能够完成。在工厂呆了一两年之后,有的学生有了发明创造,但刚从学校里出来,连机器都开不了。所以这种教育要不得。苏联要求学生毕业出来马上就能开机器,所以就推行了专业化。我们1953年也是一样。革命胜利以后,百废待兴,要搞建设,于是就推行专业化,让学生毕业出来以后马上就能开机器。机器能开了,但别的什么都不会了。
记者:培养的就是一个匠人,而不是一个学人。
胡:最典型的学养全面的一个人,就是赵元任。他是个音乐家,写《叫我如何不想他》,还有《卖布谣》,这是音乐。他的学历很奇怪,他没上小学,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所以请了前清的举人秀才教他国学。一开始就上中学,之后大学就去了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学的是物理学。他后来读到博士时,又有物理学,又有数学。他后来回国在清华大学教书时,是物理学教授、数学教授。上个世纪2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要到各地讲学。清华大学年纪大的先生们就让赵元任去做翻译。那个年代国语没有推广,赵元任到各地去讲,人家听不懂,就突发奇想,就决定到一个地方,就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是常州人,长期住在北京,国语和常州话都可以,别的方言他不会。他学国学,学音韵学,知道方言之间有语音对应规律,这个字这么读,那么同一个韵,大概也是这么读。于是他到一个地方,就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学会当地方言。这样在全国走了一圈,回来他改行了,研究方言了。所以我觉得,中外古今文理兼通,所以才有创新。知识面不全面,不可能有创新的人物。
记者:比如陈望道先生他主要是读文的,但他在东京留学的时候,专门读了一个东京物理学校。
胡: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瞧不起前人。前人的学问比我们广。
2.大学的职能是通才教育
胡:西方就分两种教育,一个叫通才教育,一个叫专业教育。大学里是通才教育。“University”的意思是各种学科都在一起,像个宇宙一样都包括了。而学院是专科的。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是校长的级别是哪一级的,学校就叫大学,另一个级别的,就叫学院。这一弄全乱了。然后我们就改成现在的情况,学文科的,一点理科的知识都没有,学理工科的,一点文科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大学生培养出来怎么办?这个牵扯到两个,一个是通才教育培养的白领阶层,是资本主义国家培养白领阶层,专科学校是培养工人阶级的,最高级别也就是技师。而我们的结果是学生全培养成蓝领了。
苏联现在都改了。我在1981年在哈尔滨开会的时候,蒲通修副部长就谈到,苏联到1960年发现这个问题了,改回去了。所以苏联后来大学也是通才教育,我们是1980年开始改,理工科改了一改,文科在人民大学试着改,改了几年不行,又改回去了。为什么呢?人民大学办的是大文科班,本科、硕士、博士通的,教的就像过去一样的全面的教育。可是当时人民大学的教授本身是50年代专科学出来的,他教不了。文科教历史的,教隋唐的只能教隋唐,别的都教不了。所以试三年停了。苏联改回去以后效果还不错,有很多发明创造。我就讲一个具体例子,我认识一位1960年以后在苏联留学的朋友,得了膀胱癌,也很严重。医院不开刀,给她的膀胱里注射结核菌,结核菌把癌细胞全部吃掉,然后就往膀胱里打治结核菌的药,到现在就好了。人家就能想到这个,那些学专科出身的,怎么可能想到这个呢?所以这个就说明创造性的人才必须基础好,基础好还有个好处,找工作容易,现在大学生找工作不是难吗?要有了这样的基础,找工作就不难了。我们现在还是个大问题,将来学生出去不仅工作难找,找到的也很难有创造性。这个问题我关注的比较多。
现在要讲中国传统文化,连《论语》都没有念过,讲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连外国的书都不能自由看,你还讲什么吸收外国的知识?
我在《外国语》杂志上写学习外语教学的往事谈。后来我遇到北京大学英语系的主任胡壮麟,他和我说:“胡先生您写的文章我看了,您写的东西和我们现在的教育全拧着呢。”我上的是西洋文学,重点是西洋文学,但语言必须学,没有语法课,也没有口语课。当年我在殖民地的教会大学里读书,有他的语言要求,你一到那学校里,不管是买东西还是在办公室里办公,全都是用英文的,逼得你也懂了。我后来三十年在外交部做翻译工作,之后去教英语,这对我很简单。等到1984年的时候,我到英国到美国,我根本就不用讲稿,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3.回顾治学经历:从西洋文学到汉语研究,兼清史研究
我学的是西洋文学,可我工作最早是在外交部,再前面是军管部的外事处,然后到了人民大学一开始是教英语,后来到中文系教语言学,之后又到清史所搞了六年研究。你就算让我到哲学系,我也能行,只要稍微让我复习复习过去的书,比如《庄子》这样一本书,是文学呢?是历史呢?还是哲学?《论语》是古汉语读本呢,还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读本?说不清的。我的感觉是很深的。我从事英语教育有一段时间之后,响应党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第一篇文章是大批判文章,扣帽子打棍子,批的是什么呢?批的是吕叔湘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是现代汉语里的“动词和宾语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永远也说不清的”,我就说:“这就是资产阶级不可知论。”后来一方面教英语,我们的教研室主任很好,就是《汉英大辞典》的编者吴景荣,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英国留学回来的。我写的中文文章,他在教研室会议上说:“很好,胡某人写的文章很好。”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老校长要成立一个语言文学系,并且还要求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所,把我就调到语文系。“文化大革命”,下放劳动。劳动回来以后,人民大学处于一种半解散的状态,成立清史研究所后,把我调过去了,又研究了六年清史。我研究了两个课题。一个是关于沙俄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第二个是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
可惜后来到1978年人民大学教学恢复,我就又回到语文系,继续教语言学理论。我本来也不是从事理论工作的,但是教学上要求也没办法。我只好从古希腊那些语法著作一本一本看过来,做笔记学习翻译了一些东西,写一些文章都是很具体的。比如我写了《说“打”》,很长的一篇文章。我是搜集了从东汉这个“打”字第一次在文献里出现,一直到民国初年,看了很多书,搜集了六千多个例子,在文章里用了一千多个。要分历史时期,就请吕叔湘先生指导我,他就帮我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打”字有一百多个意象。这都是很具体的工作,所以我在吕先生的指导下,我是不写从理论到理论的文章的,我写的文章都是有具体材料的。这样的研究一直持续到后来,因为我也比较支持文字改革的工作,所以成立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时,我就作为一个委员,一直到现在。
我给你们讲了这些,就是做一个参考。学习要把基础打好。
汉语来源探索
记者:胡老师,您近年来在探究汉语根源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胡:是的。这几年我的兴趣在于汉语探源方面。汉语是哪儿来的呢,我初步的想法,汉语是一个混合语言,不是从头就有的。混合语言,过去大家的看法是当年黄帝这一族,和长江以南炎帝这一族混合,这也对,但不只这些。如果就这两个民族混合起来,那么有些问题我们就说明不了。现在都认为黄帝这一族和藏语有关系。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藏语也好,南方那些民族语言比如百越语也好,修饰语都在后头。可是我们汉语的修饰语在前面,这怎么解释?所以我觉得,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民族,我们过去没有重视,就是辽宁西部的赤峰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是母系社会,是公元前4600年左右,因为发现有女神庙。从历史记载来看,黄帝部落和蚩尤部落作战,一开始打不过,就到红山这个地方向九天玄女求救。这个玄女是掌握兵权的,在玄女的帮助下,一下就把蚩尤打败的。那么这个九天玄女怎么和红山文化有关系呢?因为从考古发现来看,红山文化的南面就是仰韶文化,挨着的。他们从西边来到这个地方,村子是挨着的,没有作战,关系比较好。可见他们逐步就和红山文化的先人混合了。红山文化肯定有语言,就是阿尔泰语,阿尔泰语的修饰语就放在前头。这才能说明汉语的修饰语前置现象。
记者:这倒是一个很新颖的观点,有这方面的证据吗?
胡:这就需要考古的发掘和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了。历史记载明确的混合语,就是吴语,周文王的太伯父,泰伯和他弟弟仲雍,带了一帮人,到了江苏省的梅里,当地人拥护他们当国王,成立了吴国。这个“吴”字什么意思,就是鱼。为什么叫鱼呢?他们是渔猎民族,抓鱼的。那么混合之前,当地一帮人是什么民族的呢?现在不能下结论,但是我推想,非常可能是傣族。就是现在泰国的民族,国内叫傣族。我有两条证据,一条是吃甘蔗的时候,用刀先挖一下,然后割断,这个动作在我们家乡叫做“勒”,“勒”这个字在傣语里和我们的发音和意义完全一模一样。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我家乡——海盐的童话故事,有的至今和傣族的故事大体一致。
傣族有个民间故事叫“没意思”,说以前有个人是钓鱼的,有一天钓来钓去钓不到鱼,后来钓到一条,眼睛是长的,他放掉了,钓了三次,都是长眼睛的鱼,都放掉了。他不知道,这条鱼是龙王,这龙王感谢他,把女儿嫁给他。县官贪财,问钓鱼的要金鲤鱼,公主就给他。县官看上了她,就想为难公主,要一个“呒介拉啥”。龙王就送他一个野兽,这个野兽的名字就叫“呒介拉啥(没意思)”,吃的是炭火,拉的是黄金。这个事情被县官知道了,县官就把野兽拉走了。然后这个野兽吃了炭火,就不拉了。然后就继续喂,还是不拉。最后吃多了,放了个屁,放出一把大火,把县官县衙统统烧死了。这个故事和我们家乡的一模一样。这个故事我早年在《中国民间文学》上已经发表过,是用家乡话写的,外地人不一定看得懂,但意思完全一样。我们方言的“没意思”叫“呒介拉啥”。“呒”就是“没有”,“介”就是“这个”,“拉啥”就是“以及等等”。这个话,我们小时候躺在床上要睡觉了觉得没意思,妈妈就说“那我就给你讲个呒介拉啥”,就讲这个故事,完全一样。民间故事的绝不是偶然的,所以我认为这一片可能就是傣语,和周文王他们的语言混合的。那么周文王他们的语言是什么语呢?过去认为都是藏语。我认为不对。因为你没法证明周文王和藏语有关,反而能证明他和姜太公有关系。姬、姜两氏世世为婚姻,姜太公的后代就是羌族,“姜”和“羌”,一个是姓,一个是民族的名称,其实是一个字。羊字底下,写个“女”字就是“姜”,写个“人”字就是“羌”。羌语当中有个特点,它的人称代词是单数,有变格,藏语没有,藏语是用助词表示的。而我的家乡话里的“我”和“他”,现在还保留着变格。我第一次发表的研究的正式文章,就是关于我家乡话的人称代词。这篇文章的影响连赵元任都知道了,来引用。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怎么我的家乡话有形态变化呢?我们家乡说“我打他”和“他打我”是不一样的,说“我打他”的时候,是“我依打伊”,说“他打我”的时候,是“伊倷打我”,主格和宾格不一样,我这篇文章在《中国语文》发表以后影响也很大。汉语里是没有变格的,我查了藏语也没有,后来查到羌语就有。而且它也是单数变化,复数不变格的。在七八年前,《南昌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陈昌仪和肖萍,讨论江西的赣语当中的吴语,也就是江西和浙江相挨的北边的六个县,人称代词单数都是变格现象。所以非常可能周文王他们说的话是更接近羌语的,而不是藏语。但我们也就主要是在和藏语进行比较,为什么不和羌语比较呢?羌语有个缺点,就是没有文献。
记者:非常感谢胡老师接受我的专访,您的谈话让我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