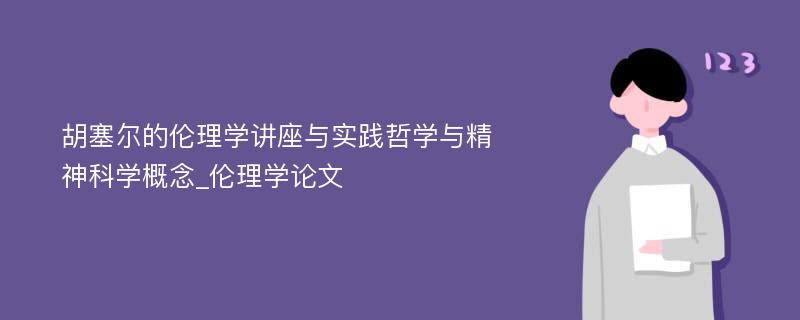
胡塞尔的伦理学讲座与实践哲学和精神科学的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讲座论文,观念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塞尔通常不被视作伦理学家或道德哲学家。这首先是因为他生前在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方面发表的文字和所做的公众讲演极少:他于1917年在弗赖堡大学为当时参战者课程班所做的3次“费希特的人类理想”①讲演以及1923/24年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的三篇与伦理学部分相关的“改造”②文章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无法忽略的是,胡塞尔一生中所开设的伦理学以及伦理学与法哲学的课程却相对较多。事实上,还在早期于哈勒任私人讲师期间,胡塞尔便多次开设过伦理学的讲座。虽然他最初在1889/90年冬季学期计划开设的伦理学讲座由于只有两位听众而被迫放弃,但此后在1891年夏季学期,他便开设了有15位听众的“伦理学基本问题”讲座。此后胡塞尔在1893、1894、1895、1897年的夏季学期都开设过以“伦理学”或“伦理学与法哲学”为题的课程。1901年到哥廷根担任特编副教授后不久,胡塞尔便于1902年夏季学期开设了题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讲座和练习课。他指导完成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是关于伦理学的研究:卡尔·诺伊豪斯(Karl Neuhaus)的“休谟的关于伦理学原理的学说”(1908年)。此后他还于1908年的冬季学期、1911年、1914年的夏季学期开设过伦理学课程。1916年移居弗赖堡之后,他又分别在1919年、1920年和1924年的夏季学期做过伦理学的讲座。③如此算来,胡塞尔一生开设的伦理学课程与他开设的逻辑学课程相差无几。
然而胡塞尔为何在伦理学方面始终坚持述而不作呢?其中原因或可从胡塞尔的一个解释中得知一二。这个解释虽然是针对感知、回忆、时间现象学问题的讲座而发,但显然也适用于伦理学讲座的状况。在1904/05年冬季学期“现象学与认识论的主要部分”的讲座开始时,胡塞尔就“一门感知、想象表象、回忆与时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做了如下说明:“我当时[在《逻辑研究》中]无法战胜这里所存在的异常的困难,它们也许是整个现象学中的最大困难,而由于我不想事先就束缚自己,因此我便宁可完全保持沉默……在我作为作者保持了沉默的地方,作为教师我却可以做出陈述。最好是由我自己来说那些尚未解决、更多是在流动中被领悟到的事物。”④据此类推,我们可以说:伦理学问题始终属于那种只是在流动中被胡塞尔领悟到、但尚未解决的事物。他只愿意以课堂传授和讨论的方式,却不愿意以公开发表文字的形式来处理这些问题。
在目前已出版的四十多卷《胡塞尔全集》中,至少有两卷是以胡塞尔开设的伦理学课程讲座稿和相关研究文稿组成:第二十八卷:《关于伦理学与价值论的讲座(1908-1914年)》与第三十七卷:《伦理学引论(1920和1924年夏季学期讲座)》。它们都是胡塞尔生前未发表的文稿。事实上,在这些文稿被整理发表之前,胡塞尔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不问伦理的哲学家,就像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常常被视作不问政治的、不问历史的思想家一样。
胡塞尔在伦理学思考方面最初受到的影响来自他的老师弗兰茨·布伦塔诺。他在维也纳随布伦塔诺学习期间听得最多的课程并非其逻辑学或心理学的讲座,而是其伦理学和实践哲学的讲座:每周五小时,前后两个学期,即1884/85年和1885/86年的冬季学期。这个讲座的文稿后来作为布伦塔诺遗稿以《伦理学的奠基与建构》为题于1952年整理出版。胡塞尔在此课程上所做的笔录与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在其《伦理学引论》讲座中,胡塞尔多次引用的便是他自己对布伦塔诺实践哲学课程所做的这个笔录。⑤在维也纳期间,胡塞尔还在1885年的夏季学期参加过布伦塔诺开设的关于“休谟《道德原则研究》”的讨论课。⑥除此之外,胡塞尔显然也仔细阅读过他老师生前于1889年发表的另一篇伦理学报告《论伦理认识的起源》。在1913年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在论及实践理性与伦理认识的明见与真理问题时特别说明:“布伦塔诺的天才著作《论伦理认识的起源》在此方向上做出了首次推进,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对这部著作表达我最大的谢意。”⑦因此可以说,胡塞尔熟悉布伦塔诺在伦理学方面的所有思考和表述。同样也可以确定:胡塞尔不仅在逻辑学和认知心理学方面,而且在伦理学和情感心理学方面也深受布伦塔诺相关思想的影响。除此之外,在其伦理学思想形成过程中,他也从狄尔泰和费希特著作研究中获得诸多收益。⑧
狄尔泰主要是通过其“自身思义”的方法作用于胡塞尔。他们两人的关系在《逻辑研究》时期表现为:狄尔泰在方法上受胡塞尔的现象学本质直观描述分析方法的影响,希望用这种与他的“自身思义”相应的方法来为精神科学和生命哲学奠基。胡塞尔最初是将现象学的直观描述方法运用在意识的横向结构上,但后期在向发生现象学、人格现象学、历史哲学和精神科学方向的扩展思考中,胡塞尔越来越多地将“自身思义”这个作为“生命重要性的宣示”的狄尔泰哲学“主导概念”⑨运用在对意识的纵向发生结构的直观把握上。⑩胡塞尔在1919年夏季学期做了“自然与精神”的讲座,随后又在1919/20年夏季学期的“伦理学引论”讲座中插入了“自然与精神”的“附论”,原因就在于,胡塞尔在这里是在与精神科学的内在关联中讨论伦理学问题。(11)
费希特对胡塞尔伦理学思考的影响与其“事实行动”的概念相关。胡塞尔在哥廷根时期便对费希特的思想有所研究。弗赖堡大学在一次大战中为参战者举办了一个课程班,同时也为胡塞尔本人提供了一个表达他本人民族主义思想的机会。但在这个伦理学的思考方向中,现象学的伦理学与费希特的行动哲学之间缺少了内在的联系,胡塞尔更多是在一种“伦理学化的形而上学”(12)的意义上说话。他要求“所有理论最终都应当服务于实践,服务于‘真正人类的尊严’”,他坚信,“理论建基于实践生活之中,并且作为生活的一种持恒‘功能’而回溯到这个生活之上”,如此等等。胡塞尔在这里表达的内容以及表达的方式令人联想起他自己对布伦塔诺的实践哲学讲座所做的批判性回忆:“它们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批判辨析的论述,却仍带有独断论的特征,即是说,它们给人或应当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确定获取了的真理和最终有效的理论。”(13)当然,费希特的这个影响在胡塞尔的伦理学思考与实践中只代表了一个暂时的、附带的经历与取向。他很快便结束了在这个方向上的激情冲动。即使儿子沃尔夫冈在一战中阵亡,深感丧子之痛的胡塞尔在战后伦理学讲座中也没有额外的情感流露。在1919年9月4日致阿诺德·梅茨格的信中,胡塞尔写道: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任务不可能在于提供政治建议和发挥政治影响:“我没有受到召唤去作追求‘极乐生活’的人类的领袖——我在战争年代的苦难冲动中不得不认识到了这一点,我的守护神告诫了我。我会完全有意识地并且决然而然地纯粹作为科学的哲学家而生活。”(14)的确,从总体上看,除了这次战时讲演之外,胡塞尔的伦理学讲座,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都是在“科学的哲学家”的思路中展开的。
就战前的胡塞尔伦理学讲座而言,在作为《胡塞尔全集》第二十八卷出版的《关于伦理学与价值论的讲座(1908-1914年)》中不仅纳入了1908/09年冬季学期、1911年和1914年夏季学期的三个讲座稿的主要内容,而且也包含了胡塞尔从1897年至1914年期间撰写的最重要的伦理学研究的文稿。
由于1897年胡塞尔作为私人讲师在哈勒开设的讲座只留下四页纸的残篇,因此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与此相对,1902年夏季学期的伦理学讲座则十分重要,尽管缺少了系统的部分,但从胡塞尔的其他阐述中可以得知,它已经包含了胡塞尔战前伦理学思想的基本思路与要素。还在1901年到哥廷根任特编副教授之后不久,胡塞尔便曾集中地思考过伦理学和价值论的问题。他阅读康德、休谟的伦理学著作,也阅读海尔曼·施瓦茨的《意志心理学》,写下一系列关于价值判断、感受学说、中意、意愿、愿望的研究手稿。1902年夏季学期,他在其伦理学讲座中,“第一次对一门形式的价值论和实践论的观念做了批判的和实事的实施”(15)。
从胡塞尔这个时期的伦理学讲座稿来看,他的思路基本上跟随亚里士多德与布伦塔诺的阐述。他与布伦塔诺一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将伦理学视为关于最高目的与关于对正确目的之认识的实践科学。他也讨论这样的问题:伦理学的原则是认识还是感受(或情感),如此等等。他的整个阐述也是通过先后两条途径来进行的:首先是否定的—批判的途径,而后是肯定的—系统的途径。就前者而言,他将休谟视为情感伦理学的代表,将康德视为理智伦理学的代表,他对二人分别深入地做了批判分析。他一方面批评休谟没有看到:感受并不能成为伦理学的原则,而只构成其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他也批评康德的绝然律令是虚构,既不是直接明见的认识,也无法从中导出伦理的戒命。胡塞尔试图用现象学的方式说明感受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伦理学的奠基,同时避免自己最终陷入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对于胡塞尔来说,道德概念的起源虽然是在某些情感行为中,但道德法则却不仅仅是统合的归纳,它们是‘建基于相关情感行为的概念本质之中’的先天法则。”(16)
在伦理学基本问题上的这个做法与胡塞尔讨论其他问题时的现象学进路完全相符:以原初的意识体验为出发点,通过内在反思将这些意识体验作为认识对象来把握,并通过本质直观获得其本质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本质结构。在这个基础上,胡塞尔可以确定在对逻辑—数学法则的认识与对道德法则的认识之间的相似性。因此他提出在逻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一种类比论的观点。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涉及逻辑学法则与伦理学法则的本质相似性,涉及它们各自在形式的与质料的先天法则之间的本质相似性。这个想法实际上最早在胡塞尔1903年10月11日致W.霍金的信中已经得到勾勒。胡塞尔在这里列出的工作计划中分别讨论“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与纯粹理性批判”以及“伦理学中的心理主义与实践理性批判”。以后这个方面的思考结果在胡塞尔1908/09年夏季学期、1911年与1914年夏季学期的伦理学讲座中得到详细的论述。但对此公开的表达只能在1913年出版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第139节“所有理性种类的交织。理论真理、价值论真理与实践真理”中找到,而且是以极为扼要的方式:胡塞尔在这里指出,理论真理或理论明见与实践真理或实践明见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行的或相似的关系,但后者奠基于前者之中,因此在问题的解决方面,后者也须以前者的解决为前提。(17)
在概述这个问题时,胡塞尔没有忘记对他的老师布伦塔诺表达谢意。(18)这主要是因为布伦塔诺在描述心理学研究的领域中所做的基础工作直接对胡塞尔的纯粹价值论、形式伦理学等等想法发生影响。布伦塔诺将所有心理现象划分为独立的表象与附加在表象上的判断以及同样附加在表象上的情感,后两者构成我们的真假概念与善恶概念的源头。(19)在这里,逻辑认识或理性与伦理认识与理性之间的相似关系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这一卷所包含的伦理学讲座结束于1914年。十分巧合的是,胡塞尔1914年夏季学期伦理学讲座的最后一节课是这年的8月1日,而这天恰恰是一次大战的德国宣战日。胡塞尔自己在讲稿的边上对此做了标记。(20)战争期间他没有再做伦理学的讲座。只是在1916年从哥廷根转到弗赖堡任教之后,他才于次年为当时参战者课程班做了上述以“费希特的人类理想”为题的通俗而公开的伦理学讲演(在1918年重复了一次)。这三个讲演看起来是划分胡塞尔前后两个阶段伦理学讲座教学的界标,本身却并不属于这两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
随着一次大战的结束,胡塞尔于1919年夏季学期在弗赖堡大学重新开设了其伦理学课程,但这年的课程只是在“自然与精神”的标题下进行的一个讨论课。而1920年夏季学期开设的“伦理学引论”则是在重新加工后篇幅增长了一倍多的伦理学讲座。这个讲座当时在弗赖堡大学的礼堂举办,最初至少有三百以上的听众。后来在1924年夏季学期,胡塞尔又以“伦理学基本问题”为题将此讲座重复了一次。讲座的文稿后来以《伦理学引论(1920年和1924年夏季学期讲座)》为题,作为《胡塞尔全集》第三十七卷出版。相对于第二十八卷的胡塞尔战前伦理学讲座稿,我们可以将这个第三十七卷的伦理学讲座稿称之为胡塞尔战后伦理学讲座稿。“这个讲座的特点在于,它依据对伦理学史上各种核心立场的批判分析而引入胡塞尔自己的伦理学。因而它既提供了胡塞尔对哲学史的创造性处理的资料,也提供了二十年代初期他的现象学伦理学的发展状况的资料。”(21)
与战前伦理学讲座比较单一地集中在亚里士多德、布伦塔诺、休谟与康德思想上的情况不同,战后伦理学讲座将讨论范围还进一步扩大到了柏拉图、伊壁鸠鲁、边沁、霍布斯、笛卡尔、洛克、费希特、克拉克、穆勒、卡德沃思、沙夫茨伯里、哈奇森、摩尔等人的道德思想体系上。
但更重要的变化在于,胡塞尔在1913年之后的超越论现象学的思想转变的结果也从认识论的领域转移到了伦理学的领域,而后进一步从结构现象学转移到发生现象学。所有这些都在胡塞尔对人格主体性的结构的观察与把握中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这里有狄尔泰影响留下的明显痕迹。胡塞尔在讲座中提到狄尔泰时说:“在这个意向生活中,自我不是他的意识体验的空泛的表演场,也不是他的行为的空泛的发射点。自我—存在是持续的自我—生成。主体存在着,同时在始终发展着。但它们是在与它们的‘周围世界’的发展的持续相关性中发展着,这个周围世界无非就是在自我的意识生活中被意识到的世界。”胡塞尔在这里之所以提到狄尔泰,正是因为“狄尔泰在其1894年关于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著名柏林科学院论文中要求一种新的理解说明的心理学作为精神科学的基础,与此相对的是一门以自然科学方式进行因果说明、但没有能力进行这种奠基的心理学”(22)。可以清楚地看出,胡塞尔在这里更多是想完成他自1913年以来便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中提出的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观念相关的现象学的本体论构造分析的总体构想。(23)
因此,胡塞尔在战后伦理学讲座中是在自己的纵意向性研究、发生现象学研究的系统中,在人格心理学、主体发生学、精神科学的背景中思考和讨论伦理学问题的。也可以说,此时站在胡塞尔背后的较少是布伦塔诺,而更多是狄尔泰。故而胡塞尔在战后伦理学讲座稿中较少谈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认识法则与伦理法则的相似性,而更多地讨论自然的、逻辑的维度与精神的、历史的维度之间的差异,讨论朝向稳定结构的认识现象学与朝向变换历史的生成现象学之间的差异。据此也就可以理解,胡塞尔为何会在战后伦理学讲座中特别附加了“自然与精神:实事科学与规范科学·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附论”。
当然,实践哲学的思考角度与精神科学的思考角度是否必定相互排斥,是否可能相互补充,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问题。从附论的副标题“实事科学与规范科学·自然科学与精神”中可以看出,胡塞尔显然已经留意到在伦理学基本问题讨论中的这两个背景的关系问题。
最后还有一些故事或许值得一提:虽然胡塞尔的伦理现象学思想在他生前并未公开发表,而只是在讲堂上为学生与听众所熟悉,但它们在那个时代便曾引发过一些并不寻常的效果。例如1908年,曾计划在胡塞尔指导下做任教资格论文的特奥多尔·莱辛将胡塞尔讲座中的相关伦理学思想扮作自己的“初学者在一个无人进入的领地中的摸索尝试”加以发表,从而引起胡塞尔的强烈不满,几乎要公开发表文章对其欺骗行为予以揭露。(24)再如,胡塞尔的另一位学生海德格尔曾在《存在与时间》中感谢“胡塞尔曾亲自给予作者以深入指导并允许作者最为自由地阅读他尚未发表的文稿,从而使本作者得以熟悉至为多样化的现象学研究领域”(25)。可是此前在1923年致雅斯贝尔斯的信中,他已经在暗中讥讽胡塞尔在这方面的原创思想:“当然没人会理解他的‘伦理数学’(最新奇闻!)”(26)——在这两个案子里,伦理学问题已经直接成为伦理问题。
①参见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多特雷赫特,1989年,第267~293页;另可参见倪梁康译《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323页。
②胡塞尔为《改造》杂志撰写了五篇论“改造”的文章,发表了其中的三篇。参见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22-1937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七卷,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多特雷赫特,1989年,第3~94页。
③洛特(Alois Roth)在《埃德蒙德·胡塞尔伦理学研究——依据其讲座稿进行的阐述》一书中详细列出了胡塞尔一生在伦理学方面的教学活动,同时也给出了胡塞尔的相关伦理学讲座稿与研究稿的基本信息(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海牙,1960年,第X页)。
④胡塞尔:《感知与注意力》,《胡塞尔全集》第三十八卷,施普林格出版社:多特雷赫特,2004年,第4~5页。
⑤(22)胡塞尔:《伦理学引论(1920和1924年夏季学期讲座)》,《胡塞尔全集》第三十七卷,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多特雷赫特,2004年,第137、104~105页。
⑥参见胡塞尔《回忆弗兰茨·布伦塔诺》,参见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多特雷赫特,1989年,第267~293页;倪梁康译《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⑦胡塞尔:《胡塞尔全集》第三卷,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海牙,1989年,第290页。——奥斯卡·克劳斯在布伦塔诺《论伦理认识的起源》(费利克斯·迈耶出版社:汉堡,1955年)的编者引论中所说“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迫切地指明了这篇论著”(第VII页)应当是个记忆差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从未提到过布伦塔诺的这本书。
⑧关于这两方面的影响的论述还可以参见斯潘(Christina Spahn)《现象学的行动理论——埃德蒙德·胡塞尔的伦理学研究》,科尼西豪森和诺伊曼出版社:维尔茨堡,1996年,第30~39页。
⑨这是胡塞尔在为兰德格雷贝博士论文《威廉·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理论(对其主要概念的分析)》[Wilhelm Diltheys Theori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Analyse ihrer Grundbegriffe)]撰写的鉴定中的表述。参见舒曼编《胡塞尔书信集》十卷本,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多特雷赫特,1994年,第四卷,第377页。
⑩笔者在《现象学的历史与发生向度——胡塞尔与狄尔泰的思想因缘》(《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一文中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11)(23)笔者在《纵横意向——关于胡塞尔一生从自然、逻辑之维到精神、历史之维的思想道路的再反思》(《现代哲学》2013年第4期)一文中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12)参见斯潘《现象学的行动理论——埃德蒙德·胡塞尔的伦理学研究》,科尼西豪森和诺伊曼出版社:维尔茨堡,1996年,第35页。
(13)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多特雷赫特,1989年,第341页。
(14)对此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参见奈农和塞普为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撰写的“编者引论”,《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多特雷赫特,1989年,第21~28页。
(15)参见舒曼《胡塞尔年谱》,《胡塞尔全集·文献》第一卷,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海牙,1977年,第68~72页。
(16)(20)(24)参见梅勒《编者引论》,载胡塞尔《关于伦理学与价值论的讲座(1908-1914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八卷,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多特雷赫特,1988年,第XIX、XLV、XXIV~XXV页。
(17)胡塞尔:《胡塞尔全集》第三卷,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海牙,1989年,第290页。
(18)参见胡塞尔《胡塞尔全集》第三卷,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海牙,1989年,第290页,注1。
(19)参见布伦塔诺《论伦理认识的起源》,费利克斯·迈耶出版社:汉堡,1955年,第20~23节。
(21)参见波伊克尔(Henning Peucker)《编者引论》,载胡塞尔《伦理学引论(1920和1924年夏季学期讲座)》,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多特雷赫特,2004年,第XIII页。
(2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尼亚耶出版社:图宾根,1979年,第45页,注1。——这里所说的“尚未发表的文稿”,主要是指在1913年已经完成、但始终没有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的文稿,即包含精神世界构造分析方面的文稿。
(26)参见《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书信集(1920-1963年)》,皮泊尔出版社:慕尼黑,1990年,第42~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