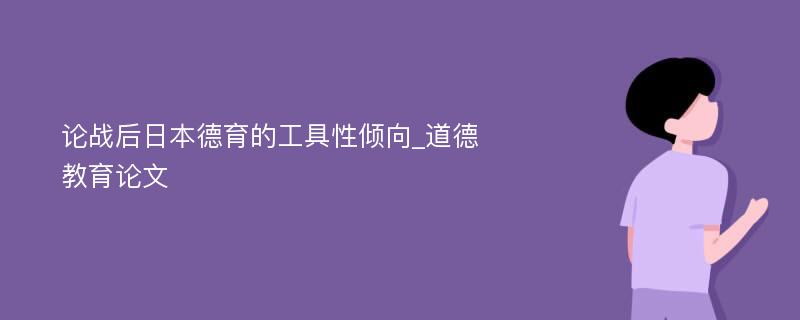
论战后日本道德教育的工具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论战论文,日本论文,倾向论文,工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0/3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110(2006)03—0040—06
自古至今,日本就是一个社会本位的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第一次教育改革时期(明治维新~二战结束),明治政府面临着解决民族危机和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大课题,制定了“富国强兵”的总目标。这一时期的日本教育主要是以“立身出世”、“治产昌业”、欧美化、现代化、工业化来达到“富国”的目标,以“建设高度国防国家”来达到“强兵”的目标。在第二次教育改革时期(二战结束~20世纪60年代末),在否定“强兵”、专心致力于“富国富民”这一社会总目标的情况下,日本教育主要是以实现数量的扩充、大众化、平等化和标准化为目标来普及和发展教育。在第三次教育改革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日本政府为了落实政治大国的国策而采取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为落实科学技术立国国策而加强心灵教育,为落实文化立国国策而促进儿童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等。总之,从明治时代至今,日本一直强调教育要为实现国家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道德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秩序保证,又通过提供动力支持,在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由于过分强调了国家主义政策对道德教育的导向作用,强调道德教育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工具性价值,日本的道德教育才忽视了对主体性价值的研究,沦为政治、经济等的工具。本文主要探讨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道德教育的工具化倾向问题。
一、道德教育作为政治的工具
在第一次教育改革时期,日本政府从修身科的设立到《教育敕语》的颁布,不断加强道德教育,最终使道德教育成为二战期间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惨遭战败的政治工具。这一时期,道德教育中充斥着政治性,“政教一体”的现象特别严重。二战后的道德教育是在对《教育敕语》和修身科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占领军总部、美国教育代表团和日本各界的建议和要求下,日本政府以《教育基本法》取代《教育敕语》,以社会科和生活指导取代修身科。“政教一体”的现象不如战前那么明显,道德教育也不像二战期间那么受重视了。然而,在道德教育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治化倾向。下面我们就主要从原因和表现两个方面探讨战后日本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倾向。
(一)道德教育政治化倾向的主要原因
1.对《教育敕语》和修身科的批判不彻底
二战后对《教育敕语》和修身科批判不彻底的具体表现是:对《教育敕语》和修身科的批判大多停留在政治的视角上,还没有上升到从道德教育理论的视角进行深刻分析与批判的阶段。日本学者色川大吉认为,《教育敕语》之所以能够支配日本国民的思想,是因为它不仅宣扬了国体的思想,而且将国体观念和国民的通俗道德联系在一起。[1] 在色川看来,即使从世界观上批判了《教育敕语》,也不可能排除在通俗道德中渗透的国体思想。村井实认为,战后对修身科的批判主要是围绕着“修身科的内容,特别是军国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封建性和非民主性”等展开;[2](p.45) 而这些批判,只是停留在关心政治的视角上,没有上升到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对《教育敕语》还是对修身科的批判,日本教育界多从对二战反省、反对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角度来进行,还缺乏从道德教育理论的角度来进行理性的反省和考察。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日本学术界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教育敕语》和修身科对道德教育的危害已经渗透到内部,不是废除了二者就能清除其影响的。例如,废除了《教育敕语》,并不能废除通俗道德中渗透的国体思想;废除了修身科,却不能避免特设道德课的设立,不能避免政府通过灌输有关道德观念,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企图。
日本教育界对《教育敕语》和修身科的认识不深刻,批判不彻底,是造成战后道德教育政治化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教育敕语》和修身科是“政教一体”的产物,是道德教育政治化的集中表现。对它们的危害认识不清,批判不彻底,必然导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道德教育政治化的新发展。
2.道德教育对政治的依附性
在政治对道德教育提出要求,要求道德教育作为其工具的同时,道德教育也开始依附政治,成为政治的附属品。一方面,道德教育受到来自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道德教育也“需要政治为自己谋得便利和空间”,[3](p.45) 因此甘愿成为政治的附庸而失去其自主性。对此,村井实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从明治初期开始,日本的道德教育就不是从教育理论的反省和考察的角度,而是从培养‘好的日本人’的角度,从服从政治目的的角度发展而来的。正因如此,对修身科的批判,当然就只能从政治的视角来进行;也正因如此,从理论方面的批判就不可能充分。”[2](p.48—49) 可见,从明治开始日本道德教育就依附于政治,失去了自主性,忽视了对主体性价值的研究。而这正是造成战后日本道德教育界缺乏反省和考察的眼光和理性,缺乏从政治当中分离出来的勇气和能力的客观原因。也正因如此,战后日本道德教育才会受政治的影响颇深,被政治所左右。
为什么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道德教育就不能独立,而要依附于政治呢?这主要与日本的政治文化以及处于政治文化背景中的日本国民的心态有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文化的主流是“服从型”,处于这种文化形态社会的大多数日本国民是顺从天皇及其政治机构统治的“臣民”。二战后“现代性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确实也取得了显著发展”,但“传统的顺从型政治文化要素”依然“顽强存在”,因此,“当代日本的政治文化可谓以参与型为主流而保存强有力的服从型要素的混合形态,即是‘顺从的参与型’;处于这种政治文化形态的社会里的大多数日本国民不妨称作‘顺从的政治参与者’”。[4](p.225—226) 可见,在这种“服从型”或“顺从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的背景下,“臣民”或“顺从的政治参与者”很难为道德教育的独立而奋争,而只能服从政治的目的,甘作政治的工具。
(二)道德教育政治化倾向的主要表现
由于上述原因,“二战以后,教育尽管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但日本社会的政治价值优先的特征和道德教育的政治主义色彩,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5](p.103) 具体来说,道德教育作为政治工具的主要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1.强化国家主义和天皇制的内容
日本的国家主义晚于欧美主要国家,在19世纪中叶形成。二战前,它被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同义词。日本统治阶级利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观,动员人民为其侵略政策服务。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早在6~7世纪时,日本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就被称为“天皇”。此后,王位一直相传在皇室之中,朝代从未中断过。天皇制作为把天皇置于最高支配地位的统治体制,需要献身天皇、效命国家的重整体精神与其相一致,而且,在漫长的天皇统治期间,日本人也极容易把天皇视为国家的人格化的象征。[6](p.196—197) 可见,无论是国家主义还是天皇制,都与“国家”有密切的关系,都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二战以后,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宣传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教育敕语》被废除,以国家主义、天皇制为主的修身科教育也被取消。然而,5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国内右倾势力的抬头,在道德教育中加强国家主义和天皇制内容的政府报告纷纷出台。例如,1951年天野发表《国民实践要领》,强调“爱国心”和“天皇”的观点;1966年中教审发表《理想的人》的咨询报告,提出要培养具有纯正的爱国心,敬爱天皇的国民等。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政治显示出右倾倾向,有关国家主义和天皇制的道德教育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例如,在1998年日本的课程标准《学习指导要领》“有关自己与集体以及社会关系的内容”中,要求小学中年级学生“喜爱我国的文化和传统”,高年级学生“珍惜我国的文化和传统”,“热爱祖国”,“具有作为日本人的觉悟”;[7](p.90—93) 要求初中学生“具有把自己看作是日本人的自觉性,热爱祖国,为国家的发展尽心尽力,并为继承优良传统、创造新文化做出贡献。”[8](p.99) 在对天皇制的拥护方面,主要表现对国歌的推崇。日本国歌《君之代》一开始就以“吾皇圣明,泽被万载”的歌词和庄严肃穆的旋律,使日本国民在“天皇崇拜”观的指导下,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民族认同感。[5](p.98) 在1989年的课程改革中, 文部省规定把中小学入学式和毕业典礼上唱《君之代》歌作为一项义务,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对天皇制的拥护。
2.强化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
日本新保守主义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其基本理念是恢复旧的国家观与民族观,强调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自豪感。冷战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社会整体保守意识的加强,使新保守主义的理念在90年代后的日本政治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其主要表现有:第一,从国家利益出发,倡导“普通国家”(日本应拥有大国的国际权利和向海外派兵的权利),并积极推动日本在国际社会发挥独特作用;第二,全面否定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为日本争做“政治大国”树立良好形象;第三,修改宪法。其目的主要是突破制约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瓶颈”,以便日本成为能够为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普通国家”。[9]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政府通过强调学生道德危机的严重性,在全国免费发放《心灵的笔记》作为道德课参考书、强化义务劳动、强调尊重日本传统、文化等间接的方式来加强道德教育,强化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例如,文部省从2002年开始向全国的中小学发放道德课的辅助教材《心灵的笔记》,名为为教师进行道德课教学提供便利,实则是政府加强对道德课控制的一种措施。又如,2002年7月,中教审发表了《有关青少年的义务劳动和体验活动的推进方法和策略》的咨询报告,其中,对如何加强儿童的义务劳动进行了具体的规定。这种做法歪曲了“义务劳动”的“自愿”性质,是一种强制性的道德教育措施。
二、道德教育作为经济的工具
在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道德教育,主要是以培养人才的“忠诚、勤劳、节俭、献身等品格凝聚而成的日本伦理精神”,[6](p.222) 对日本经济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强调道德教育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同时,日本的道德教育自身也被异化了。下面,我们就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道德教育作为经济工具的具体表现。
(一)重视培养重整体的精神
我国学者吴潜涛认为,重整体精神这种东方伦理的一般特征,“在日本民族那里呈现出具体的形态:为整体而献身的忘我精神。”[6](p.191) 饶从满认为, “日本的整体精神具有变通性。整体、集团的范围既可外推,又可内缩。”[5](p.100) 总之,重整体精神在日本民族中可用“为整体献身的忘我精神”来归纳,其中的“整体”既可以是家庭、家族、小集团,又可以是国家、天皇制。这种重整体的精神既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结晶,又是长期以来道德教育不断强化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府一面推行以修改宪法和重新武装为基调的政策,一面开始追求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在此背景下,文部省吸收了产业界“适应日本工业社会需要的道德应是民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道德”,“而要很好地进行这种道德教育,就必须在学校开设道德课”等意见,[10] 从1958 年开始在小学和初中开设道德课,对学生施加民族主义、功利主义的道德教育。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了教育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的趋向。当时经济界要求教育界要确保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高才能劳动力,而这种高才能劳动力不仅要具有相应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应具备适应能力,对企业具有强烈的归属意识和“爱社精神”。为此,中教审1966年发表了《理想的人》的咨询报告,提出了“理想的日本人”的标准。其中,“作为社会成员”和“作为国民”集中体现了政府对道德教育培养重整体精神的要求。报告指出,“作为社会成员”,应该是埋头工作、为社会福利做贡献、发挥创造性和尊重社会规范的人;“作为国民”,应该是具有纯正的爱国心、具有对于象征的敬爱之念和发展优秀的国民性的人。[11](p.243—246) 可见,道德教育就是要培养为日本国家和社会献身、忠于国家、忠于天皇的日本人。70年代以后,强调重整体的精神仍然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1974年5月, 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提出了“五个重要”、“十个反省”的德育论。其中,第五个“重要”就是“热爱国家、社会”。[12](p.278—279) 在他的德育论的指导下,1977 年的课程改革强调“特别要养成遵守日常的社会规范的态度”,要求更加重视“自主自律和社会团结、尊重劳动、热爱自然和人类、服务精神、纪律和责任、爱国心与国际理解等等。”[13](p.143) 80年代以后,在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影响下,在学生道德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重整体精神的道德教育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例如,在1989年和1998年的课程改革中,文部省通过“有关自己与集体以及社会关系的内容”来强调集体精神和国家利益。在强调集体精神方面,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要求小学低年级学生“喜欢参加学校和班级的活动”,中年级学生“和大家合作,为建立快乐的班集体而努力”,高年级学生“和大家合作,为建立更好的校风而努力”;[7](p.91—93) 要求初中学生“具有把自己看作是班级和学校一员的自觉性,和大家合作,为建立更好的校风而努力”。[8](p.99)
(二)重视培养努力奋斗的精神
在日本文化中,既强调个体为整体服务的献身精神,要求个体要为群体和社会的利益而“克己”;又强调个体自身努力奋斗的精神,要求个体要为个人的“立身出世”而“扬己”。所谓“立身出世”,是表示(在社会上)成功、出息和发迹的含义。日本的“立身出世”虽然鼓励个体通过努力和他人竞争,达到在社会上成功、出息和发迹的“扬己”的目的,但却是以考虑到整体利益,不损坏整体利益为前提的。只有这样,个人的努力奋斗才能构成整体的力量,为日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的“克己”是个体的“扬己”的前提和条件,个体的“克己”和“扬己”是日本民族在世界之林中“扬己”的前提和条件。
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强调爱国心教育的同时,培养个体努力奋斗的精神得到了加强。1951年11月,文部大臣天野贞祐在《朝日新闻》上介绍了《国民实践要领》草案,指出:“只有在逆境中学会忍耐,拥有爱心,坚持正义,才能看到世界的光芒”;[14](p.215) “应该尊重勤劳的美德,并形成勤劳的习惯,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为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的财富。”[14](p.219) 可见,在天野看来,作为日本人,应该学会忍耐和勤勉。1966年,中教审发表了《理想的人》的咨询报告,提出了理想的日本人的标准。其中,“作为个人”,应该是自由的、发展个性的、珍惜自己的、具有坚强意志的和具有敬畏之念的人;“作为社会成员”,应该是埋头工作、为社会福利做出贡献、发挥创造性和尊重社会规范的人。[11](p.239—245) 在此,作为个人的“具有坚强意志”的品德和作为社会成员的“埋头工作”的品德都与努力精神有关,都提倡个人努力奋斗、不放弃、坚持和忍耐的精神。如果将《理想的人》与《国民实践要领》比较,不难发现它们在日本人所应具有的努力精神方面的品质是何其的相似:前者强调“具有坚强意志”,后者强调“忍耐”;前者强调“埋头工作”,后者强调“勤勉”。在《理想的人》的精神指导下,1977年的课程改革特别强调道德教育,强调“自主自律和社会团结、尊重劳动、热爱自然和人类、服务精神、纪律和责任、爱国心与国际理解等等。”[13](p.143) 其中,“自主自律”、“尊重劳动”和“服务精神”等内容,都体现了努力奋斗的精神。20世纪80年代以来,培养个人努力奋斗的精神仍然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1989年和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都强调培养儿童坚持性和忍耐性,培养儿童为了达到目标而努力的精神。例如,在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中,要求小学低年级学生“认为是好的事情的,就好好地去做”,中年级学生“认为是正确的事,能够有勇气地去做”,高年级学生“树立较高的目标,并怀着希望和勇气、坚定不移地为达到目标而努力”;[7](p.90—92) 要求初中学生“怀着希望和勇气,向着更高的目标,坚韧不拔、意志坚定地努力。”[8](p.98)
总之,二战结束以来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一直以“富国富民”作为国策,使教育成为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富裕和科技进步的经济工具。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国策的指导下,极端重视培养学生重整体的精神和努力奋斗的精神,一方面培养学生为整体而忘我献身的忠诚心理,一方面又注重培养学生通过努力获得成功和实现自我。通过这样的道德教育,起到通过个人“小我”的努力和忍耐,达到实现国家“大我”的发展和腾飞。然而,由于过分强调通过个人努力而达到出人头地、“立身出世”的目的,造成了学生为考试竞争而拼命,以致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由于过分强调牺牲“小我”而发展“大我”,许多学生的个性被压抑,人格被扭曲,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教育存在的痼疾,进行了第三次教育改革。然而,从本质上来说,道德教育还是“科技立国”的工具,还是注重其为经济服务的工具性特征,还没有从根本上对千差万别的个体赋予更多的人文关怀。
以上我们主要从日本道德教育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两方面来阐述道德教育的工具化问题。事实上,日本道德教育还存在着作为文化工具的问题。从明治维新到现在,在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日本采取了“和魂洋才”的文化方针。“和魂”是大和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也即日本化的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洋才”则指的是西洋的科学技术。为了贯彻“和魂洋才”的文化政策,道德教育一方面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一方面又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道德观念的教育,有选择地传播一些西方文化。具体来说,在继承和发扬日本传统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等级观念和集团主义精神的宣传和教育等。自古以来,等级观念和集团主义精神就是日本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二战以后,等级观念和集团主义精神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为促进日本社会的稳定与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由于它们过分强调等级关系和集团主义,压抑了学生的个性,伤害了学生的人格。在有选择地促进西方文化的传播方面,主要表现为对民主、自由、平等、竞争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等。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平等、竞争等民主意识的培养,一方面为消除封建残余、建立民主和平等的日本社会、树立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打下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学生为了追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而放任自己,丧失基本的规范意识,染上抽烟、喝酒、吸毒、援助交际、不上学等不良行为,甚至欺侮他人、用暴力伤害他人等。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道德教育一直在国家主义政策的导向下,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工具,在日本社会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道德教育只重视了道德教育的社会性功能——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发展,为社会整体关系的协调而服务,忽视了道德教育的个体性功能——“自我与他人和谐关系的建立”和“独立自我本身达到某种内在的平衡”。[15](p.236) 诚然,道德教育具有社会性的功能,但是只重视社会性功能,而忽视其个人性功能,显然是不全面的。鲁洁教授深刻地指出:“只有当德育在个人关系领域内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德育才不是把人作为工具来培养,而是作为目的来培养,德育才赋予它原应有的本质的意义。这种德育才不致使被教育对象视作为‘异己’、‘异化’了的德育,才能成为对象们衷心自愿接受的德育。”[16](p.327—328) 可见,只有重视了个体性功能,道德教育才有可能不被“异化”,学生才有可能不被当作工具,而被当作目的来培养;只有将道德教育的社会性功能和个人性功能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
“道德教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从价值哲学的观点看,一种特定的实践活动及其主体既具有工具性价值——满足其他实践活动及其主体之需要的属性,又具有主体性价值——满足自身需要的属性。主体性价值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的价值,是‘创造价值的价值’,……是内在价值,是工具性价值(外在价值)的源泉。”[17](p.406) 因此,主体性价值是道德教育的首要价值,否认或忽视了道德教育的主体性价值,将使道德教育成为消极的、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客体,由此而发挥的工具性价值也是消极而被动的。日本道德教育要想真正解决道德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只有改变道德教育被动的工具性状态,使其作为主体积极投入到现实生活中,积极干预并超越社会生活,发挥道德教育主体性价值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6—02—24
标签:道德教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个人努力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