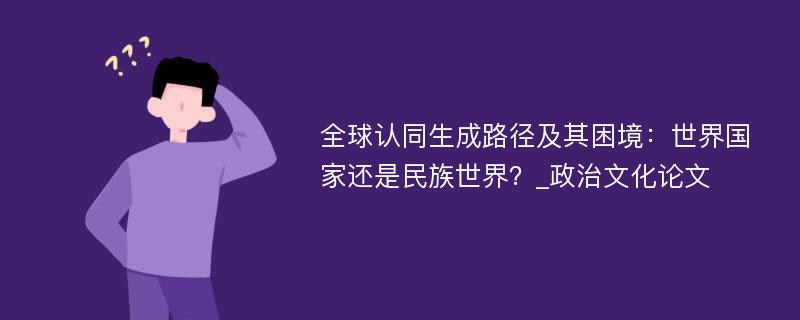
全球认同生成路径及其困境分析——世界国家还是国家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世界论文,路径论文,困境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国际共管、共治、共赢、伙伴关系、相互依存等概念早已超越了纯理论的话语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并得到越来越多主权国家的认同。早在十多年前,世界各国领导人分别就消除贫困、饥饿、疾病、人类安全、民主、人权、治理、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歧视等议题,发表了《千禧年宣言》,以创建一个美好和平的地球家园。然而,现实中大国关系的跌宕起伏、地缘政治的扑朔迷离、恐怖主义的泛滥、无核化谈判几陷僵局、贸易保护主义屡禁不止、国家因债务危机面临的可能破产、气候协议谈判几经搁浅,甚至维基“泄密”效应引发的政治冲击波等事实,似乎让人们质疑《千禧年宣言》的实现可能性、质疑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的健康发展。相互交织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多种因素给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重建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人类的安全与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的临界点。人类不得不面对以下问题:如何协调国家利益与全球安全之间的关系,比如在行动上兑现《千禧年宣言》所做出的承诺?如何促进区域共同体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避免地缘政治思维的回归?如何确实促进联合国改革,比如就常任理事国问题及国际安全议程达成共识?如何认识宗教对现实政治的杠杆作用,特别是其化解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作用?
不难发现,隐含在以上问题之后的是认同问题。问题的症结主要涉及了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区域认同与全球认同实现的相互关系问题。① 本文的一个假设是:既有认同不仅仅是对以往认同的继承,也是过渡到未来认同的前提和条件;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区域认同与全球认同的实现有碰撞、分离、甚至冲突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着天然的重叠、交叉和融合的另一面。总的来说,人类的认同朝进步的方向发展,全球认同的实现是一种历史必然。基于此,本文将围绕全球认同生成的路径和困境展开,即通过对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区域认同、全球认同几种体系认同生成和转换的论证,试图阐述认同的生成是一个历史和进化的过程,其过程不乏矛盾、迂回、冲突但又始终在进步和完善。为了避免论证过于抽象和空洞,本文适当结合历史和现实中的案例进行了说明。
一、国家认同
之所以把国家当作一种认同,是因为国家不仅是实在的物,具有人口、领土、政权机构、军队等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量化的东西,更重要的它又是一种历史的观念,或者说“在某些更重要的意义上,国家更多是一种为群体所共有的观念——一个想象的共同体”。② 必须承认,国家认同并非是固有的,因为国家的生成并非呈线性发展而是集体认同不断进化的产物。
在远古时代或前国际体系阶段,人类的意识处于茫昧或混沌阶段尚不足于具有认同意识,③ 因为在现代国家主权认同生成前,人类社会或许经历了混沌认同、原始认同、古典国家认同的漫长历史时段。众所周知,三十年战争后所签订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从法理的层面第一次将民族国家当作一种集体认同的产物并被承认与倡导。当时,尽管这种认同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相对过去的教皇治权而言,对基于王权的国家认同终于占了上方,特别是它为以后新型的现代国家认同生成做了较好的铺垫。显然,这正是政治学者将三十年战争当作一个国家性能从宗教国家到世俗国家转换的分水岭。试想,设若国家的组织形式一直徘徊于教皇或国王的治权,那么“教皇即上帝”、“朕即天下”不可能过渡到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
进一步说,从国家认同对国际体系构成的贡献看,对国家的认同构成了组成国际社会的要件(在很长的时段内,国家曾是唯一的要件),所以才使国家具有了“民族性”、“地域性”和“排他性”,而在体系层面对国家的认同又构成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和国家内部的有序运行。须知,国际体系生成的条件是单元体之间在利益、安全、合作、互动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和就此达成的基本认同,遑论是通过暴力或和平的方式。
然而,就进程而言,特别是在体系层面,对国家这一组织形式的认同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它在认同上升的路径中担当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也正是国家存在的法理性之所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国家的认同一以贯之,或者说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使得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亘古不变呢?即从体系的变更而言,这种无政府性是否意味着单元体的安全保证只能通过“均势”、“结盟”,或“帝国”、“霸权”,或“战争”、“暴力”的方式实现——使得基于全球利益认同的实现成为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
诚然,就现阶段而言,国家对安全的认知、感觉或觉悟是层次不齐的。并非所有的规范、条约能得到有效实施或贯彻,其原因不是机制本身存有问题,就是被个体意义的国家利益所凌驾。显然,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集团倾向乃至意识形态将在相当长时段内存在或延续,这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特征。所以说,对威胁的认知、安全的博弈,对挑战者的警惕,以及在金融、信息、技术、领土、资源等领域的争夺将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但这并非说对国家认同从内容到形式是亘古不变的。
亚历山大·温特曾在其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作过一个精炼的假设:无政府文化并非呈单一的形式,霍布斯式文化过渡到洛克式文化、康德式文化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可建构的过程。就认同过渡而言,认同在不断提升、发展和进步。这种推断告诉我们,认同的生成是一个过程,既有的认同并非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更。显然,尽管国家认同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并非意味着主权将在短时期内消失。当下的世界或许仍处在一个“后主权认同”状态,其特征是单元体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相互发展。④ 在这个时代,国家认同的理念已经超越了霍布斯倡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思维框架,超越了马基雅维利给当政者提出的“不择手段”的警示,超越了汉斯·摩根索等所标榜的“权力政治”时代。简言之,在单元体层面,“软实力”与“硬实力”并存,在体系层面,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已成为一种文化而得到广泛认同。这是对传统国家认同的一种提升,也是对主权理念的一种更新。
在“后主权时代”,国家认同从内容到形式不再固守一种模式。国家之间在为解决安全困境创制了不少范式,特别是在对待安全认知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已成为一个普遍承认的社会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安全理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敌对到合作,从个体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到全球安全的转变,一系列话语如“利益攸关者”、“首脑峰会”、“伙伴关系”、“相互依存”、“地球安全”的生成,在合作机制上从“西方七国俱乐部”(G7)到“20国集团”(G20),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世贸组织(WTO)的过渡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社会事实”之后彰显了不仅是单元体对自身安全与利益认知的变化,而且隐含着单元体对体系和平或非暴力过渡的一种期盼。因此,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从组织、形式、内容等方面,国家认同还将发展和进步,国家利益、国际利益与全球利益的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或许这正是促进健康的国际关系与和谐世界生成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认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维基“泄密”效应给中东地区带来的政治动乱应引起主权国家的高度重视。就促进单元体关系和国际体系的进步而言,处在体系前沿的国家或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有责任、有义务推动有利于整个人类和地球安全认同的生成。
二、宗教认同
宗教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始终贯穿人类的历史、国家制度及世界秩序的发展。因此,在历史中,它不仅构成了一种理想,也促成了一种制度。⑤ 宗教学家费齐诺说过“我们每个人或许都禀有一种本能或宗教意识,以将我们引向美、真理、正义……”⑥ 事实上,这种理想、制度或者意识使得宗教真正成为一种认同,并使之与国际关系与国际体系的健康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向来具有和平或暴力的两面性,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的精神总是与体系的转换:技术、权力结构以及社会的组织形式相辅相成。比如,之所以有人将公元前6世纪、公元12世纪及18世纪称作三个“伟大的精神世纪”(grands siecles de l'Esprit),是因为这三个世纪不仅给人类的思想带来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国家形式、国际体系的变化。⑦
从现实政治看,宗教认同是导致国家认同变异甚至夭折的最主要因素。某种程度上讲,国际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变异为宗教关系,因而,使得宗教认同直接对主权机制形成挑战,或许这正是“新中世纪主义”衍生不灭的重要原因。一位伊斯兰学者曾用“3D”(din-religion,dunya-life,dawla-state)来形容宗教与生活、国家之间不可分割的法理联系,因而无视宗教政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既不现实也不可能。⑧ 因此,有人说21世纪是“精神的伟大时代”(The Great Century of Mind)。⑨ 宗教认同将在国家生活和政治运动中起领先的作用并对全球化形成挑战。诚如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所指出的“在这个令人沮丧和失控的场景下,个体的人不得不寻找其认同即宗教、族群、地域重新组合”。⑩
既然国家认同、区域认同是合理的,表现为一种进步的、共在的认同,那么为什么宗教认同还会发展、复兴至与国家认同相对峙,甚至还会催发恐怖主义的泛滥?
构成这一二律背反的现实有多种原因。其中,冷战结束是宗教认同回归的一个重要原因。意识形态、超级大国的利益相争曾掩盖了宗教认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因而,冷战后宗教曾迅速填补真空并一度造成世界动荡。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冷战后全球化、技术进步(如克隆人、破解生物基因密码、机器人等冲击了宗教的神秘性危及到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和环境危机(比如跨国公司不负责任的开发及气候污染等造成的冲突与纠纷。从结构上讲,还体现在国际制度上的“营养不良”,即“失败的”或“无效的”国家为宗教政治的回归提供了发展的温床。
从认同的角度而言,这种认知或感觉造成了一种宗教认同危机。比如,有学者分析道:“当下宗教的复兴可以被诠释为一种对身份、真实性以及社群的诉求,这也意味着赋予个体和社群生活意义。”(11) 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表现赤裸裸的权力政治给穆斯林世界造成的生存危机,特别是美国偏袒以色列,发动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所导致的冲突不断、危机频生。二是穆斯林世界在价值上感受到的威胁。西方主流价值的泛滥,造成了认同的遗失或危机。而在理论上的“文明冲突论”又使穆斯林世界有一种西方优越论的感觉,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文化至上理论只不过是逐步消除伊斯兰文明的一种“宗教阴谋论”(religious conspiracy theory)。(12)
因此,在穆斯林世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力量要复兴或重振伊斯兰主义,这正是原教旨主义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不难理解,有人也把原教旨主义称作一种“基于宗教的政治运动”。(13) 曼纽尔·卡斯特曾指出:宗教原教旨主义,无论是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还是印度教、佛教,都是构成这个麻烦时代个人安全和集体运动的强大力量。而组织体的摧毁、机制合法性的遗失、规模型社会运动的式微都与身份或认同危机有着重大关联。(14) 不可否认,宗教极端主义致力于一种极端的、排他的和至高无上的宗教认同,致力于建立一种神教统一的政体;它蔑视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采用威胁、恫吓、暗杀、甚至战争等恐怖行为以期达到其政治的目的,可以说这是对国家认同最大的挑战。所以,偏激的宗教认同(邪教或极端宗教主义)会给当下国家制度和世界秩序带来的威胁和挑战,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从另一方面讲,重塑或者回归认同又不能采取过激的特别是暴力的手段。因为价值是构成一切认同的内核,而武力或暴力与价值的力量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从本质上讲,既然认同是导致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在现阶段寻求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全球认同之间的相切点就显得意义重大。主权国家要有意识地鼓励和引导宗教政治朝健康的方向发展,真正从宗教多样化、多元化的角度来促进、辅助或完善国家制度;特别是对大国而言,要倡导换位思考,反思全球化过程中给中东国家、民族的经济、社会及其宗教信仰带来的冲击。因为在众多穆斯林看来,全球化事实上是对“南方”殖民化、贫困化、剥削化和西方化的一个过程。这些基于宗教特别是来自“南方”政治运动事实上是对上述几种形式压制的一种反抗,因而被称之为“恐怖主义”。(15) 不难看出,这种反抗隐含着寻求、回归伊斯兰认同的一种情绪或期盼。
诚然,这并非说宗教认同将亘古长存,或者说鼓励或赞同复兴、回归某种单一的宗教。宗教认同是历史的一个产物,它也必将在历史中发展、提升并最终汇入其他主流的或进步的认同。宗教既是一种“模式”、“畏惧”、“信仰”,也是一种“观念”、“导向”、“哲学”、“伟大的客观事物”和“态度”,一种如同卢克莱修所言的“外在的”和西塞罗所称的“内在的”观念体系。宗教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的需要。(16) 因此,宗教本质保证了宗教在教义上的通约性、可建构性及宗教最终消亡的趋势,其原因在于:
首先,宗教教义具有兼容性。威尔弗雷德指出:“在历史上没有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曾创立过一种宗教”,几种主流的宗教都标榜真、善、美,宗教至少是人类对美好愿望的一个认同。(17) 在知识(智慧)获取上,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有着一个共识:所有的人类,不管他们来自哪里、贫富和境况如何都有权获取知识。(18) 一位诗人写道:“它们[宗教]汇入一盏灯,但是闪烁着不同的光芒”,所以在这个宗教仍对政治生活起作用的时代,主权国家须认识宗教的多元性、多样性对当下国家制度和全球秩序的积极作用。(19)
其次,从发展的角度看,宗教也具有可建构性。威尔弗雷德以把宗教称之为一个“累积的传统”或“历史性的积淀”,(20) 而且正因为“这种累积的传统完全是历史性的,但历史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人类的动因,而人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超验者开放的”,同时它也是人的行为产物,具有“多样性、不固定的、增长着的、变化着的和累积的”,以可以摸得着的形态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21) 所以“一个宗教传统也就是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在持续不断地建构中的历史性的建筑物”,那些开明的、进步的宗教都是在变革和修正中发展的。
从认同的过渡讲,宗教的消亡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又是个必然的过程。因为“宗教的终结”也就是“神的终结”,或者说人类的精神与“神”的意旨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即“‘神’的情谊与人类的情谊达到了统一”。须知,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数千种宗教,最后留存下来并发挥影响的屈指可数,我们应该深信“随着我们人类意识之内容的增长,我们的意识之形式正在经历着,并仍将要经历某种演化或进化”,(22) 而且“整个人类的宗教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变得更加迅速、更加明显和更加具有共同性了”。(23)
18世纪英国有位作家说过:“只有人才能正确地研究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地球的救世主”是人类自己而不是任何无形的上帝,宗教的终结不是任何上帝的胜利,而是“神”的意志与人意识的认同或统一,因此有理由相信宗教认同会逐步融合于全球认同。
三、区域认同
区域认同作为全球化的一个产物,其运作模式和发展趋势对未来的国家构成、世界体系演变关联密切。冷战后,一体化的效应迅速发酵,特别是欧盟的发展及其他区域共同体的发展表明,区域共同体对于国家安全的塑造和全球政治、经济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美洲、非洲、亚洲继后都有了一定意义的“共同体”,哪怕在形式和功能上还欠完善,但是,这种态势促进了全球政治、经济制度的健康发展,或者说是全球化不断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有理由相信,作为实现全球认同的一部分,一体化还将在功能、组织形式、互动及集体意识等方面继续进步。可以断定,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这是因为,区域认同不仅是全球化的一个必然产物,而且也是人类走向未来共同体的一个必然过程。
然而,这并非无视问题的存在和共同体面临的挑战。我们尚需对存在的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判断,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仅要影响到未来的认同,对国家制度、国际体系及世界安全带来隐患,而且最为紧迫的是对当下的区域认同产生影响。
以欧盟为例,作为一个举世公认的区域认同的产物,它为主权国家实现共同安全与合作提供了一种范式,但同时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不得不引起关注:其一是主权国家对欧盟的认同问题,或者主权让渡可能产生的问题。例如,英国所持的消极态度是最明显的例子。而在欧元诞生后,这个问题又几经周折,特别是在对《欧洲宪法》表决上,欧盟原创国法国、荷兰甚至几度犹豫,但最后还是向前推进了,《里斯本条约》最终得以签订、通过。这个过程学界已有很多成果。眼下的问题是土耳其问题,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能否成为成员国,最大的问题不是民主、市场的问题,而是穆斯林国家与基督教国家能否“合二为一”,即认同问题。它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传统的“欧洲主义”在作怪。无论土耳其如何标榜其在地理上如何与欧洲接近,在欧洲人看来,土耳其始终是一个亚洲国家。另一个则是由宗教问题引起。在欧洲人看来,土耳其毕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这种历史情结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在欧洲人的潜意识里,宗教分野将会导致国家、民族甚至文明的冲突。显然,克服宗教优越论、淡化宗教认同是解决土耳其问题的一个关键。
其二关乎共同体内部的运作认同。共同体是否夭折、失效?即是否回归欧盟成立前的,甚至倒退到19世纪均势横行的时代,这些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曾经有一段时间,问题主要集中在共同体内部决策的民主赤字问题,这个问题争论由来已久。(24) 近期似乎又转向了经济或金融问题。不可否认,在经济危机面前,欧盟试图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拯救面临危机的欧元市场,然而担心欧元崩溃的风险似乎并没有减小,继冰岛、希腊之后,爱尔兰又面临危机,这种危机是否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否蔓延到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然后袭击亚平宁半岛的意大利?欧元崩溃是否真得面临从“不可想象”走向“不可避免”的结局?其实,几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并不可怕,这是区域一体化中的正常现象,关键是国家利益与共同体利益之间能否真正融合,是否互相信任?如果出现群体危机,那么整个机制是否会破产值得担忧,欧元区“分家”很可能会造成欧盟分崩离析,“多极之一的欧洲”将在世界中失去应有的地位。如果这样,这已经不单是经济问题、国家问题,而是世界政治、经济危机,而且关系到主权制度、单元体的互动及国际体系的运行。所以欧洲和整个世界都有责任避免这种崩盘的出现。
其三是一体化过程中的权利政治角力,或者说传统地缘政治对一体化的影响。从历史上来说,欧洲自近代以来就是地缘政治的思想发源地,在实践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众所周知,欧盟一体化的原始思路即来源于超越均势的思维以期对德国进行“集体管制”,可以说,欧洲一体化从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式微地缘政治的目的并有机地促进了整个欧洲的安全与繁荣。(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缘政治”思维在欧洲式微了,却在美洲开始兴风作浪。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上,美国似乎不能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安全困境”。就发展健康的区域认同而言,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是无法回避的。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美国对中国与欧盟国家日益接近的担忧。尽管欧洲的主要大国在整个冷战中是美国的主要盟国,尽管在冷战后中欧在意识形态、知识产权等领域存有分歧,但客观地说,中欧关系发展比较顺畅,中欧之间建立了各种合作论坛,中欧峰会频繁,贸易额也不断上升,甚至土耳其这个过去要求脱亚入欧的国家最近也表示要做入亚的转换准备。这种“反叛行为”正是导致美国对中国政治心理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不仅在中欧合作上心存不悦,对中国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发挥的作用开始怀疑,个别媒体和政要人物不惜在东南亚制造“中国威胁论”,甚至不惜制造“杀手锏”阴谋论。(26) 可以推测说,2010年在东亚、东南亚区域的一些不和谐现象与制造“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效应不无关系。
显然,战略心理的变化引发了美国对中国的错误知觉。2005年,在美国兰德公司发表的《中国与全球化》的报告中,尽管对中国有偏见,但客观而言,美国对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持乐观态度,当时还是有意鼓励中国在全球化中日益发挥作用。然而,面对中国近几年的发展尤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似乎又陷入传统地缘政治的思维。
在全球化的场景中,建立一种有利于共同安全的联合体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陷入一种机械主义式的思维。众所周知,相对于传统的世界而言,世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地缘政治即通过实力或结盟谋取国家利益的做法既违逆历史潮流也不现实。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增加扩展了单元体之间的联系性,也推进了体系层面的复合相互依存,主权国家都有责任推进这一进步的认同。故之,“竟合”不仅是中美关系的一种常态,也应是我们这个特殊时代的一个常态。(27) 从认同转换而言,泛亚、泛欧、泛美都只是暂时的,从这个意义看,欧盟的发展范式值得参照。全球主义已是大势所趋,国际关系已上升为“全球主义的国际关系”。从相互依存的角度看,国内与国际市场已真正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而欧盟在这方面为主权国家的联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因此,从全球相互依存的角度而言,沃勒斯坦的结构理论尚未过时,中心和边缘任何一个环节发生脱落都有可能发生连锁反应。因此,大国不仅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其自身经济体制和增长点进行调控,而且须学会在全球经济结构上做出合理布局与合作。
四、全球认同
相互依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整个人类处在茫茫海上的同一条船上,更重要的是“人类活动和交往的高密度既增加了现实中的相互依赖,也推进了全球意识的形成”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28) 布赞曾谈到:我们也许可以期望互动密度的增加带来的压力将让世人比过去更快地醒悟。……打破这一明显绝境的可能途径是制定出涵盖了所有层次——个人、国家、地区和体系的——安全政策。(29)
从深层次看,体系文化的生成对全球认同的生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诚然,国家文化、地域文化将存在,但这并非影响全球文化的形成。多样性、广泛性、包容性本身也许就是全球文化认同的一个特征。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呼吁一种更高级、更完善、更进步且有利于整个人类健康与发展的“世界文化”。笔者十分赞同彼得·卡赞斯坦在其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一书导论中所持的理念:社会行为体的文化、身份(认同)、政策、传统及偏好等与国家安全、利益和世界秩序、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关系,文化观念和文化体系在成熟的国际体系下对全球认同的生成起着变量性作用。(30) 因此,有学者倡导“文化公民身份”与世界性的问题、文化多元性联系在一起。文化公民身份对“世界、民族、城市及自我”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文化成为一种“资本”,且对秩序与治理发挥着影响。(31)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认同并非等于文化的一致。就全球认同而言,并非只有千篇一律的文化,否则便曲解了文化认同的实质。同质性和异质性的文化对认同的生成均有意义,因此认同并非等于同化,至少不是强迫的同化。在体系层面上,文化认同更重要的表现在国家形式变化方面,而指导国家形式变化的是理念、价值、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类在共享安全与繁荣上的认同。文化的认同过程类同于国家身份的扩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社会的自组织特征及社会进化的目的性所决定的。文化身份的形成“既是自组织的过程,又是选择的过程;既是既定的,又是被建构的;既是自上而下的,又是自下而上的”。(32)
就全球认同的生成而言,我们关注的是文化认同给整个体系带来的变化,特别是体系的变更是以和平的方式抑或暴力的模式转变。以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欧洲协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生成与转换为例,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文化从“暴力的合法性”、“秘密外交”、“民族自决”、“普遍的集体安全”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文化对体系变更的一个最好说明。(33)
从认同变量对体系转换的意义看,如果某一种认知得到普遍的共识并得到普及,那么这种对于体系的普遍人便构成了一种“集体认同”。当这种认同在体系内得到认可、普及和推崇的时候,它就会呈“胶着”或“恒定”的状态,并表现为一种“势能”,施动者或单元体在认同的推动下产生有目的的进化,从而也为过渡到下一种文化或世界体系打下基础。如前所述,亚历山大·温特对“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之间的转换做了十分精彩的注解,从体系认同过渡而言,19世纪到20世纪的国际体系演变与生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34)
接下来的问题是,全球认同的实体以哪一种形式或模式出现?诚然,预测未来向来是不讨好的,但是这项工作又不得不作。国内外政治学者就此已做过许多论述,像“世界政府”、“国际国家”、“全球主义国家”、“世界国家”,甚至“霸权国”、“帝国”等等,不一而足。在前学的基础上,笔者曾对世界国家的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个粗犷的描述并推断:全球认同的发展必然要走向某类“世界国家”。(35)
世界国家何时出现?就体系层面讲,世界国家的生成是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在许多层面,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世界性”了,比如“联合国”、“欧盟”及方兴未艾的国家与区域性合作,这些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或许这些都可以算作世界国家的一个“雏型”。当然,一个成熟的或完全的“世界国家”还距我们十分遥远。温特曾预言说,世界国家会在100—200年出现。(36) 就目前的单元体之间互动与国际体系的运转而言,要实现完全的世界国家还有许多挑战,有许多亟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不仅涉及第一层面地问题,也涉及第二层面地问题,如对权利、利益、暴力等内容和形式的界定和使用问题。(37)
就当下而言,在共建国际秩序方面已经到了重建全球认同的关键时刻。主权国家特别是大国应该负起责任,要学会负责任地干预历史。全球认同所倡导的是施动者能超越民族国家或地区利益,站在服务于全球利益的高度进行国家和国际制度建设,所以人类既要干预历史,而且要提高干预的质量。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危机引起的动荡效应应该引以为戒。因此,在当下要充分保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健康运行,保证主权国家在法理层面的有序运转,保证大国在解决国内冲突和全球治理上的正常协调。反之,其中任何一个机制的破产将有可能造成现行世界秩序的崩塌。
总之,从进化的历史看,如果说人类已经历了混沌认同、原始认同、古典国家认同、主权国家认同、后主权国家认同(正在经历)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国家的出现是迟早的事。无论是从现实需要看还是从人类发展历史看,对世界国家的认同是人类发展史上必然经历的一个时段,或者可以说是上述几种认同的历史必然,从这个意义讲,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区域认同必然要回归具有全球意义的认同。由是,世界国家的生成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结论
全球认同问题宏大而抽象,绝非本篇幅完全所驾驭,本文只是围绕全球认同生成的路径和困境做了一个浅显的梳理。就本文的观点完善而言,笔者尚需进一步向学人请教、向书本学习、向实践求证。笔者深信,全球认同正在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尽管现代国家从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超主权”、“超国家”、“后主权”是事实,然而,地缘政治、领土之争、安全困境仍将在长时间内左右国际政治,特别是围绕“主导权”或“霸权”之争将持续下去,战争和冲突还将继续存在,但这并不影响整个体系文化的进步。就此而言,未来的国际体系变更或许以非暴力的形式或模式出现。人类的创制物是一个谱系,具有传承性、延续性,而集体认同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变量性的作用。
国际关系理论不可能不关注认同对国家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变量意义。尽管国际关系理论不仅仅是一种预测理论,学者和政治学家仍有必要加强理论对现实的阐释力。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超越大国争霸的逻辑、超越历史的回归的观点或假设。就我国而言,在实践层面要深刻理解全球化场景下中国外交的含义,如同王逸舟教授所指出的“不能仅仅专注于博弈、格斗、争锋的各种技巧,只讲斗争的一面,忽略不同行为体彼此间重大关切的兼顾,在新形势波动时便忘记对‘和谐世界’与‘和平发展’的承诺”。(38) 需要加强对理论不充足性的研究,并用多元的视角融“中、西、马”为一体,穿行于不同的理论岛之间,在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探寻全球主义的国际关系。(39)
总之,世界政治本来就不存在一种可选择的菜单,就当下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现实困境而言,人类需要在建构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国际制度和全球秩序上达成认同。全球认同的组织形式、全球认同不应仅囿于主权利益、宗教利益、地区利益,而要立足于全球利益、全球安全和全球发展、利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显然,这种理念与联合国倡导的《千禧年宣言》是一致的。
注释:
① 历史是一个过程,人类任何新型的共同体都是在继承和扬弃中发生的,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区域认同既构成了当下主流的认同,同时也是导致未来认同的主导变量。关于对全球认同的界定,笔者曾尝试从二元的角度做了阐释:全球认同不仅为一种理念、实体,而且是一种态势和进程,其立足点在于整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全球利益。张全义:《世界国家生成机理初探: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40—46页。
② [英]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闫健、李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③ 布赞把研究国际关系的历史推回到4万年前,他把人类的远古阶段称为前国际体系阶段。参见[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造》,刘德斌主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④ “后主权认同”主要是相对于威斯特法利亚主权理念而言,它可以是后主权国家、多层次的地缘治理;同时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时间划分上,仍归属于“现代国家认同”的范畴,因此从体系过渡和全球化进程的角度,笔者将2000年当作后主权认同进入常态的一个开始。张全义:《世界国家生成机理初探: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研究》,第248—252页。
⑤ 威尔弗雷德在谈到基督宗教的生成时指出,“[所以],这里是一个体制化的过程,概念性的具体化过程。概念、术语和关注的重心,从个人性的定向转变成了一种理想,接着又转变成了一种抽象,最后则是转变成了一种体制”。参见[加]威·坎·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董江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47页。
⑥ [加]威·坎·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第38页。
⑦ 原文为法语。三个伟大的世纪分别指公元前6世纪前后东西方思想家或诸教的产生(佛教、老子、孔子及柏拉图、毕达格拉斯等)、第二个世纪是发生在公元12世纪文艺复兴的前夜、第三个世纪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变化。Darwis Khudori,“Key Issues Related to the Rise of Religion-base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Darwis Khudori ed.,The Rise of Religion-Based Political Movements,A Threat or SAA Chance for Peace,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mong the Nations? Bandung Spirit Book Series,ICRP(Indonesi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2009,p.27.
⑧ Siti Musdah Mulia,“Portrait of Religion-Based Organization and Violence in Indonesia in the Era of Reform,” in Darwis Khudori ed.,The Rise of Religion-Based Political Movements,A Threat or SAA Chance for Peace,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mong the Nations? pp.89-90,150-151.
⑨ 原文为法语“grand siècle de l'Espirit”,See Darvus Khudori,“Key Issues Related to the Rise of Religionbased Political Movements,” op.cir.,p.25.
⑩ 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宗教对塑造人类未来世界之重要性。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他揭示了基于身份的社会运动对全球化挑战之主导作用。他将宗教当作认同,其中也包括具有宗教背景的运动,并将其当作基于身份的运动。参见Darwis Khudori ed.,The Rise of Religion-Based Political Movements,A Threat or SAA Chance for Peace,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mong the Nations? pp.27-28。
(11) 约翰·L·埃斯波西托在他的论文《宗教和全球事务》中总结到:“宗教的复兴不仅表现为一种精神,而且也体现了社会和政治的觉醒……当下宗教的复兴可以被诠释为一种对身份、真实性以及社群的诉求,这也意味着赋予个体和社群生活以意义”。参见Darwis Khudori ed.,The Rise of Religion-Based Political Movements,A Threat or SAA Chance for Peace,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mong the Nations? pp.89-90,138.
(12) 米·萨伊夫埃·安瓦认为,“……文化危机也时常与坚信阴谋论理论联系在一起……基督徒和犹太人之所以设定打压伊斯兰教的议程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基于他们对古兰经文字和主观上的诠释。其二是基于他们对西方的认知,即西方倾向于沿着获取世界霸权的路走下去,这其中也包括对穆斯林世界的霸权”。参见Darwis Khudori ed.,The Rise of Religion-Based Political Movements,A Threat or SAA Chance for Peace,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mong the Nations? p.147.
(13) 一些学者在“原教旨主义”的理解上有不同看法,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王俊荣倾向于用“宗教极端主义”这种称谓。关于对原教旨主义概念的争议,以及“原教旨主义”的分类以及特征(作者给出了29条详细说明)等可分别参见“Workshop on‘the Rises of Religious Extremism:Impacts and Responses’(297-300),”Wajahat Masood,“A Prognostic Critique of Fundamentalism,A Case Study of Pakistan,”in Darwis Khudori ed.,The Rise of Religion-Based Political Movements,A Threat or SAA Chance for Peace,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mong the Nations? pp.89-90,102-103.
(14) “Workshop on ‘the Rises of Religious Extremism:Impacts and Responses (297-300)’,”Wajahat Masood,“A Prognostic Critique of Fundamentalism,A Case Study of Pakistan,”op.cir.pp.28-29.
(15) Wajahat Masood,“A Prognostic Critique of Fundamentalism,A Case Study of Pakistan,” in Darwis Khudori ed.,The Rise of Religion-Based Political Movements,A Threat or SAA Chance for Peace,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mong the Nations? pp.73-77,85.
(16) “他们将‘宗教’这一名称赋予了信仰者卷入其中的抑或潜在的信仰者将要面对的那种体系——起初是一般性的体系,但随后更多的则是各种观念的体系。”参见[加]威·坎·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第19—23、25页。
(17) 威尔弗雷德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没有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摩尼除外?)曾‘创立过一种宗教’,抑或说‘宣扬过一种宗教’”;“然而,那被称之为诸宗教的东西在历史上的确是变化着的,则是一个可以观察得到的和重要的事实。”[加]威·坎·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第284、299页。
(18) Darwis Khudori,“Key Issues Related to the Rise of Religion-base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Darwis Khudori ed.,The Rise of Religion-Based Political Movements,A Threat or SAA Chance for Peace,Security and Development,among the Nations?,p.27.
(19) See Siti Musdah Mulia,“Portrait of Religion-Based Organization and Violence in Indonesia in the Era of Reform,” op.cir.p.140。
(20) 所谓“累积的传统”是一种“历史性的沉淀:寺庙、《圣经》、神学体系、舞蹈模式、律法与其他社会体制、习俗惯例、道德法典、神话等;指的是任何能够从一个人、一代人传递给另一个人、另一代人的东西以及任何能够为历史学家所观察得到的东西。”[加]威·坎·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第334页。
(21) [加]威·坎·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第336、338页。
(22) 同上书,第275页。
(23) “整个人类的宗教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像它每一天都进入新的一天一样,尽管现在变得更加迅速、更加明显和更加具有共同性了。”[加]威·坎·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第390页。
(24) 欧盟内就民主决策问题一直争论不休,2005年,欧盟还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The Commiss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Period of Reflection and Beyond:Plan D for Democracy,Dialogue and Debate”(委员会对意见征询期及之外的建议,民主规划D:对话与辩论)针对民主程序问题进行意见征询;E.O.Eriksen & J.E.Fossum eds.,Democr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Integration through Delibera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0.
(25) 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梅特涅、俾斯麦、威廉二世至因《20年危机》而出名的爱德华·卡尔等堪称“均势”的倡导者,而继后的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又在实践上验证了这一传统理论,所以不难理解均势曾对欧洲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体系形成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26) The Editors of The New Atlantis,“The Assassin's Mace,”The New Atlantis,Number 6,Summer 2004,pp.107-110.See http://www.thenewatlantis.com/publications/the-assassins-mace.
(27) 作者爱德华·卡尔等20多位研究者在《中国崛起之威胁》(The Dangers of A Rising Nation)一文中指出:“中国和美国注定是对手,但不一定是敌人”,21世纪的中美是“竞合关系”。http://news.sohu.com/20101210/n278211583.shtml,2010-12-10.
(28) [英]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第136页。
(29) 同上书,第343页。
(30) [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刘铁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31) [英]尼克·史蒂文森:《文化公民身份:世界性的问题》(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7、126—150页。
(32) 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大国的社会化:东亚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崛起》,朱锋、[美]罗伯特·罗思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33) 张全义:《世界国家生成机理初探: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研究》,第269—282页。
(34) 笔者曾就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与温特的三种文化的关联请教过亚历山大·温特。总的来说,温特赞同这一分析路径,但他又指出:“在我的理解中,维也纳体系不应该划归为霍布斯文化体系范畴。……在19世纪,大国基本上就‘主权下的管理’达成了‘认同’,所以说维也纳体系应归属洛克文化体系之下……不过,我同意你(笔者)对联合国文化体系的描述,把冷战体系称之为康德文化体系的异化。”参见张全义:《采访亚历山大·温特:探究建构主义的‘问题领域’》,《国际观察》2007年第1期,第71—79页。
(35) 张全义:《世界国家生成机理初探: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研究》,第283—325页。
(36) 在《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一文中,温特把国家制度的演变为5个阶段,它们是“国家体系”(a system of states)、“国家社会”(a society of states)、“世界社会”(world state)、“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和“世界国家”(world society),并断言“世界国家在100—200年的出现是极有可能的,”参见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9,No.4,2003,pp.491-492,517-518。
(37) 中国的两位学者冷晓玲、李开盛曾对温特的这一理念进行过评介,尽管笔者不完全赞同其分析视角,但文章对“世界国家的不可能”所作的评述十分值得借鉴。冷晓玲、李开盛:《论世界国家生成的不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6期。
(38) 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自序)。
(39) 王逸舟教授多年来关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对提升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认识,比如,借用多元视角研究国际关系、对中国国际关系的10点“不足性”意见,以及首次提出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倡议等,这些观点对于提升中国自身的发展及创建和谐世界是非常有益的。参见王逸舟:《探寻全球主义的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国际文化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全球化论文; 欧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