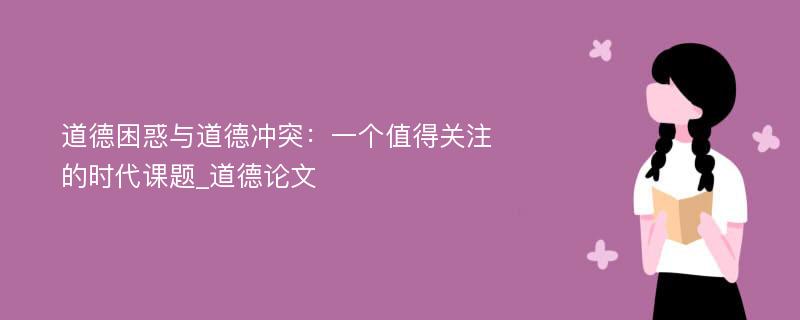
道德困惑与道德冲突———个值得重视的时代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课题论文,困惑论文,冲突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变革的时代迫使人们对变革着的社会生活进行反思和把握。不管这种反思和把握,采取理性思维的形式,还是诉诸非理性的情绪表达,都是人们为了摆脱对变革的困惑与迷惘所作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自身在变革过程中成为主体。例如,时下学术界对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就可视为理论界同仁为把握变化中的现实生活的一种学理化努力。然而,争论诸方似乎都疏于对现实的和历史的道德发展状况的考察。事实上,任何理论上的困惑与冲突,恰恰是现实的困惑与冲突的一种映射,同时也带有某种历史的回声。现实的道德本身就处于困惑与冲突之中。正视这一现象,并给予理论上的说明,对于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关系问题的讨论,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
在西方,道德困惑问题,曾经骚扰着大大小小的思想家。不过,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来研究,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危机,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的沦落与重建成了众多学科思考的主题,道德困惑问题的研究顺乎自然地趋于热烈。在此之前,倒是一些时刻关注着人类发展命运的文学家,比较早且极为敏锐地描述了人类在道德领域所面临着的困惑。莎士比亚在其著名的悲剧《麦克白》和《裘力斯·凯撒》中,都是将主人公置于深刻的道德困惑中来描述他们的痛苦、勇敢和狡诈的。麦克白一心要做苏格兰的国王,而这,只有靠谋杀现任国王邓肯并把这种弑君重罪转嫁到邓肯的两个儿子马尔康弟兄身上才能实现。然而,“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情;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生前的美德,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鞭策我实现自己的意图,可是我的跃跃欲试的野心,却不顾一切地驱使着我去冒颠踬的危险……”。一面是自己的勃勃野心,一面是仁慈贤达的国王,麦克白在这两种力量面前长久地不能自拔。在《裘力斯·凯撒》中,主人公勃鲁托斯同样面临着这种尖锐的困惑:要么杀死凯撒,——但这又的确极难为他,他很爱凯撒,并且这样做,很有可能成为众人讨伐的对象;——要么顺从凯撒,扶助其专制政权,而这样做的代价是让全体罗马人都过奴隶的生活,这是他引以为耻的。对于这种麦克白或勃鲁托斯式的困惑,西方学者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派援引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思想基础,一派则以康德为祖师。根据康德的形式主义准则,谋杀是绝对的错误,是“恶”,因而,勃鲁托斯是不能得到原谅的。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只有当中庸的政治结构本身是正确的,暗杀才是错误的;一种暗杀的条件或背景能够使暗杀相对地正确大于无条件地错误,因而,勃鲁托斯是可以原谅的,他的行为是基于为人类命运着想的长期的善良动机和价值目标。为此,康德主义者又加以反驳……。显然,这类困惑在伦理学家那里并未得到解决,麦克白或勃鲁托斯是否可以得到原谅?
英文中的Dilemma一词,源自希腊文“Dis”(“两个”或“两次”)和“lemma”(“假设”或“命题”)。最初,专指一种修辞学或逻辑学意义上的推论形式。这种推论的形式的前提包括两个假言命题,一个选言命题,结论不是选言命题,就是一个直言命题。例如,你对朋友做出了某种承诺,后来发现,如果你保持并实现这种承诺,结果将是坏的。但是,如果你破坏这种承诺,则将会在朋友面前失去信誉,甚至有可能失去一位朋友。此种情况下,要么信守诺言,要么破坏诺言,而对于行为主体来说,两种选择都于他不利,但又无其他途径可寻。这一事例就是一个典型的复合结构性困惑,它有特定的形式:“如果p则q,如果r则s,但不是p就是r,因此,不是q就是s”,简示为,pq,rs,p∨r,∴q∨s。后来,Dilemma突破了逻辑学的含义,被“用来描述在两种对等的方案中进行抉择的困境”(〈前苏联〉福鲁劳夫主编:《哲学辞典》,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4年英文版,第111页),此种规定已经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困惑有相通之处。当然,实际的困惑情形,尤其是道德困惑则要复杂得多,人们常常不是面临着两种选择,而是多种选择,每一选择对人来说似乎都不是最佳方案,或此时是最佳方案,彼时或为坏的方案。
道德困惑主要表现为:首先,道德评价上的困惑。如所周知,道德评价就是一种善恶评价,然而,当人们尚未形成明确的善恶意识,或者,当人们的善恶意识发生变化时,人在对自身和他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时,困惑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究竟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道德评价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矛盾是造成人们在道德评价过程中困惑的内在原因。一方面,在特定社会中,道德评价的标准必须是确定的,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条件下,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二者不可颠倒。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任何行为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都有赖于诸多条件因素,当道德评价把这些条件因素考虑在内时,就不能简单地判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了。因此,另一方面,道德评价标准又是很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在变革的时代,在新旧交替激烈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尤为明显,道德困惑因而不可避免。
其次,道德价值目标上的困惑。由于道德价值体系所特有的稳定性,新旧体制交替的变革初期,建立在旧有道德价值体系基础上的道德目标的权威性受到挑战、怀疑,而新的道德目标又尚未展开。“上帝死了,权威失灵了,偶象崩溃了”即是这一阶段主体的道德观念状况的典型概括,混乱、无序都在所难免。虽然,道德价值目标仍要建立,但毕竟已失去往昔那种统一的恬静与优雅!
再次,道德困惑反映到人们的情感系统中,就会使人处于痛苦、不知所措乃至疯狂的煎熬之中。在这一阶段上,人的情感变得复杂化,同一主体,对同一客体的态度也许会在瞬间就来一个大转弯,原来喜爱的不再感兴趣,原来憎恶的,而今却觉得可爱之极。人们的道德感的偶发性、不稳定性加剧,甚至变得不可捉摸。
最后,行为趋向上的困惑。由于旧有的道德目标受到怀疑,而新的道德目标尚未明确,从而人的行为趋向也会走向非正常化,——脱离原来的行为轨迹,表现出左右摇摆的状况;行为不再是人们的理性所能控制得了的,——旧理性失落,新理性还未形成,——而带有极大的盲目性、自发性,且无定型;主体对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预测能力大大降低,因而在多种行为方案面前常常感到举棋不定。
道德冲突与道德困惑总是相伴随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困惑是道德冲突的结果与表现,而道德冲突则是道德困惑的进一步发展。从个体的角度看,道德冲突主要表现为:其一,规范与行为之间的冲突。规范与行为,既相统一,又有不一致。规范来源于人们的行为实践,同时,规范又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在道德价值体系处于稳定时期,规范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是主要倾向,二者不仅有逻辑上的联系,而且有心理、情感上的联系。人们信奉某一规范、标准,总是自觉地使自身的行为符合这一规范和标准。然而,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人的道德价值体系发生裂变的情况下,规范与行为之间的失衡就成为必然了,人们信奉了某种规范,却未必以这种规范来指导自身的行为,甚至,他的行为时常是违背他所信从的规范、标准的。其二,双重人格的冲突。所谓双重人格,指个体身处变革时代,新旧价值体系激烈交替的时期,却又很难超越困惑和冲突,从而在人格上发生的变异现象。表现在:人们时常在传统价值观念、传统道德所支配的社会关系、群己交往中,认同某种社会角色、塑造自身的人格形象,而在传统道德无能为力或无法触及的世界中,则选择另一种相反的角色,形成另一种人格形象。双重人格的冲突可以看作人们试图在不触动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情况下寻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适应的痛苦和挣扎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未必是所有社会主体都愿意承受的。
二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道德困惑、道德冲突,作为道德发展过程中的特定阶段,其产生不是偶然的,归根到底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结果,是社会有机体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必然。
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某种经济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的反映。就此而论,从来就没有超功利的道德,即使是康德的形式主义道德准则,仍然代表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利益,所谓“人为自然立法”、“人为自身立法”、“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不正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追求个性独立的一种愿望吗?问题在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利益关系要形成一定的道德,毕竟要借助于诸多中介环节;道德,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毕竟有其特定的方式。人们常说,道德即规范,规范即约束,即限制,这就表明,道德反映并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往往是以否定性为媒介的。自然,这种否定性关系不是机械的、简单的,而是辩证的否定,否定中包含积极的肯定的环节。倘说道德具有超功利性,即与经济关系的不同步性,只能做出这样的合理解释:道德反映并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并不必然地采取亦步亦趋的单纯论证和辩护的方式,相反,更多地倒是体现为对当下的经济关系的批判与否定(即规约);而从根本上说,这种否定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相反,倒是更加有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否则,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产生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能够产生对所谓节俭、勤劳等美德的推崇,就是不可思议的了;从历史上看,真正对经济发展有害的,反而是那种庸俗的以单纯论证和辩护为特征的道德。因此,道德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有矛盾就是不适应,所谓适应,就是无矛盾,就是要求道德为经济做论证和辩护。马克思曾尖锐地抨击了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道德的虚幻性,但同时,马克思又特别强调,这种虚幻的道德的产生前提并不是虚幻的,也就是说,这种虚幻的道德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却是真实的,不仅如此,他和恩格斯还不断肯定在每一社会形态中真正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劳动人民的道德在推动历史发展方面的伟大作用,这类道德在每一历史阶段上,都是真正批判的、辩证的否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道德的批判性、否定性的根据和标准,在于是否促进人本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标准,从总体上说,恰恰是与生产的不断发展、交往的不断扩大所蕴涵的价值目标相一致的。困难在于揭示,这种最高标准上的一致性在每一历史条件下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这就需要结合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进一步探寻道德发展的规律,我认为,对道德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考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我国哲学界,人们习惯于将道德作静态的分析,而多少忽视对道德的历史性动态考察。例如,在目前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中,相当多的论者都是把市场经济与道德作为两个预设的前提来立论的,而将这两个前提做了“完成式”的处理,仿佛我们已经建立起了足够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然后再从这种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说到底是从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引伸出我们应该建构什么样的道德,而将最重要的前提——我国体制转轨时期正在变化着的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的实际忽略掉了。也有的论者忽视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的辩证性质,只是简单地将市场经济与道德划界,“各自为政”,仿佛我们已经有一套完备的道德价值体系,足以抵御市场经济的诱惑和侵袭,此种“一厢情愿”,与前一种观点表面上看似乎很对立,实质上,从方法论上看有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对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缺乏历史的动态的考察。
将道德置于动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考察,就会看到,每当社会有机体处于激烈的变革时期,道德状况会与社会稳定时期呈现出质的差异,道德困惑与道德冲突反而是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道德困惑与道德冲突最集中地发生于大变革的时代。这时,生产的发展、交往的扩大、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必然冲击着旧的经济关系及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关系,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革,并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重组。然而,变革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新旧力量在相当长时间内往往处于纵横交错之中,这是造成道德困惑、道德冲突的根本原因。以我国广大的农村为例,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一大批农民开始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开始大量渗入农村,但在不少地方,商品经济与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却是“和平共处”的,这一客观现实也使得人们的道德状况往往呈现出困惑和冲突的境况。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态度,必然冲击着人们的道德领域。新科技革命将人的活动、人的关系、人的需要引向了广阔的世界,新的世界、新的关系、新的需要,必然带来新的道德伦理问题,对于这些新问题,人类基于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是很难进行评价的,更谈不上提出解决方案了,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尚处于胚胎之中,人类只有与困惑、冲突相伴。比如,当代西方社会学界、伦理学界、医学界争论颇为激烈的“试管婴儿”是否是一个道德主体?“安乐死”合乎道德吗?计算机作“恶”谁应承担道德责任?等,便是颇令人困惑的问题。如关于“人工流产在道德上是否正当”这个问题,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判断,每一种道德判断又都是可以成立的:如一种判断认为,“当母亲怀我时,我可不让母亲人工流产,除非是死胎或有严重损伤。对我是这样,我如何能前后不一致地否认这种我自己要求有的生命权利呢?如果我承认母亲一般有权进行人工流产,我就破坏了推己及人的箴言”。另一种判断认为,“每个人对她或她自己的身体拥有某些权利,任何别的人都没有权利干扰我们实现对自己身体的愿望。因此,当胚胎基本上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时,母亲有权作出自己是否要人工流产的决定”。在这两个价值判断中,每一个论证都是合理的,但它们又是不可通约的,它们分别以不同的道德观念为逻辑背景,这些不同的道德观念又都有其哲学根源,前者可追溯至康德的思想,后者可溯至杰佛逊、卢梭等人的思想。(参见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页)
从人类思维的发展看,人的自我意识是导致道德困惑的主观条件。任何客观的矛盾,任何复杂的境遇,假如未被人们意识到,或者说,假如人们身处于困境之中而未能自觉,困惑是不会降临于人们的观念之中的。当人们的道德价值体系处于稳定时期,困惑是不可能产生的,一方面,客观条件尚不具备,另一方面,人们的自我意识,特别是人们对自身已有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反思意识因为暂时的统一与稳定而被遮蔽起来了,人们还不可能意识到自身的道德价值体系的优劣,还未对之发生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困惑总是与怀疑相伴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道德困惑与道德冲突,为我们认识道德发展的规律、特性提供了极好的素材,虽然,就现实生活而论,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承受这样的境遇。不过,我认为,这样一个现象,这样一个阶段,在人类道德发展的某一交接点上出现,有其客观规律性,尽管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此有各种不同的价值评价。而且,这样一个阶段,对于新型道德价值体系的产生、发展又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可以这样说,道德困惑与道德冲突是新型道德价值体系的发酵剂。没有困惑和冲突,旧道德的大厦不会发生倾斜和动摇,任何新的道德、新的力量都不可能产生,即令产生出来,也会被旧道德吞没,或者与之同归于尽,而建立起来的往往是旧道德的变种;没有困惑和冲突,新的道德价值体系不会在多种势力的鼎足相持中乘隙而入,不会获得人们的认可,更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支配地位。可以说,道德困惑、道德冲突意味着人类向着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迈出了一大步,它意味着人们不再受某种僵死的或永恒不变的道德体系的支配,而开始怀疑、思考和否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奉若神明的东西,开始解放自身。当然,不可否认,困惑与冲突会带来道德领域暂时的分裂、混乱,甚或造成道德发展过程中的危机现象。比利时学者埃德蒙·拉达尔在论述危机与文明的关系时说:“同文明进程相反,危机作为断裂环节出现,它的威胁几乎是经常的。不过,这样一种危机感出现之前,总是先有文明状态的出现。”(《危机与文明》,载《第欧根龙》中文版,1987年第1期)
自从人类的道德价值体系产生以来,人类就面临着道德的困惑、冲突这样一个尖锐问题,同时,人类为了摆脱这种困惑和冲突,也做出了种种不懈的努力。就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大体上有四种解决道德困惑与道德冲突的方案。第一种方案主张,当道德困惑形成、两种道德价值体系发生冲突的时候,牺牲一方而保存另一方,即用一种道德克服另一种道德。不过,这里仍然有区别。在新、旧道德之间发生冲突时,有的强调,新的服从旧的,——中国儒家伦理基本持此态度;有的则主张,旧的服从新的,——西方道德观念的发展基本持此立场。第二种方案主张,发生冲突的两种道德体系都走向灭亡,人类走向道德的“空寂”时期,在废墟和空地上建立起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这一方案的倡议者是尼采等人。第三种看法认为,发生冲突的两种道德价值体系都保留,这是一种没有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第四种,是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界颇为流行的看法,以美国学者露丝·芭柯恩·玛克里斯为代表。R·B·玛克里斯认为,“道德困惑的真实存在是无疑的,但这并不表明一个包含两种支持互不相容的行为的准则的内在的不和谐,毋宁说意味着独断地行使这些原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该管理我们的生活,合理安排社会结构,以将道德冲突降至最低程度”。(“Moral dilemmas,deliberation,and Cheice”,载美国《哲学杂志》,麦克米兰公司出版,1985年3月号,LXXXII卷第3期,第139页)这实际上是一种“回避冲突”的方式,然而,“生活不像图片游戏,在其中我们能够‘stack the cleck’(洗牌作弊、搭桥)来避免冲突”。
这四种看法都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每种看法都有它自己的“根据”,但四种看法的“根据”又都有共同之处,即非历史的“根据”。不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并非全是共时性的“即兴表演”,如果仔细追溯,都有其历史的(或阶级的)来由;舍弃了历史的分析,历史的东西仍在起作用,而强调了共时态的相互作用,这种共时态在将来仍将成为历史。割断了历史性,道德将成为不可谈论的“神秘”。有人就公开提倡“宗教性道德”,而新儒家则将宋明理学或心学的东西拿到今日讲“终极关怀”。当然,也不能互视共时性,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必然成为道德冲突的原因,也成为道德困惑的根源之一。具有以否定性为媒介的道德本质,必然在现实中开辟自己的道路;它的否定性特征,也必然最终否定掉“多元价值、和平共存”的虚伪性,这种虚伪性在否定性的批判中显出尴尬、局促、不安。这也就为社会的主导性道德价值的合理性、正义性的充分实现和扩展准备了条件。
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冲突、困惑也只有在这种基于实践的“范导”性主要是“重构”中逐步获得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