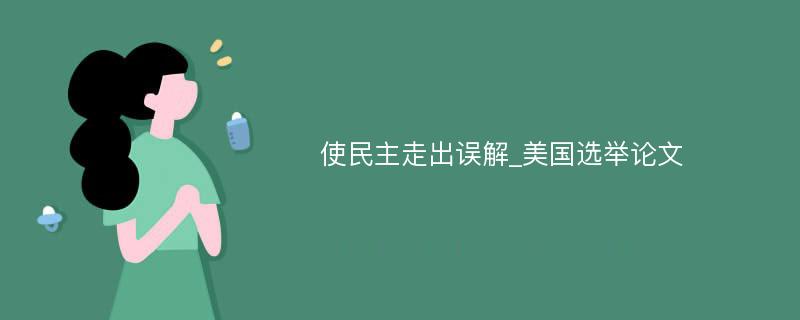
让民主从误解中摆脱出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解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5-0019-05
曾世逸:房教授您好,您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最近您出了一本新书《民主政治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这本书的容量并不太大,但所论述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您还特别强调,要与西方争夺民主话语权,建构中国自己的民主理论与话语系统。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和意图。
房宁:我们的民族正走向现代化、走向复兴,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又必须承认,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还缺乏经验,尚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我们的理论认识,相对于蓬勃发展的民主实践还是比较欠缺的。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番景象。我们在经验不足,理论、话语体系还相当稚嫩却面临着一个强大的话语体系——西方的民主话语体系,也就是曹锦清教授所说的“译语”体系。我们的民主实践应该借鉴西方的经验,将之作为参考。但无论如何西方的理论都不能成为中国实践的指导。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中,西方的民主话语形成了强势,实际上已构成了对我们民主政治实践的干扰。甚至可以说,西方民主话语流行已经妨碍了人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有些人对中国民主政治实践视而不见,患上了“民主色盲症”。这是很成问题的。
要构建中国的民主话语体系,首先应当着眼于中国的民主实践,以中国的经验为基础。中国学术界的民主问题研究应当完成一种转型——从直接使用西方话语体系,转移到中国的经验层面上来。应当转变我们的视角,从中国的民主实践中梳理中国的经验,最终构建起中国自己的民主话语体系。我希望中国学术界关于民主问题的研究,开启一个经验性阶段,这将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阶段,而徘徊于现在这种状况是没有出路的。当然,现在也有许多学者在做经验性研究,比如一些学者在做乡村建设、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研究,就取得了不少成绩。
我自己近些年也作了一些努力,这本书,就是试图把民主问题的视角拉回到实践层面、经验层面,以中外实践为基础探讨中国的民主理论。这是我研究民主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我的追求。
挑战流行:民主问题的五大误解
曾世逸:读您的书,感觉您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您质疑了一些您认为“似是而非”的观点,提出很多被误解或被忽略的重要问题。您似乎认为现在流行的观念中对民主问题有很大的误解?
房宁:是的,我的确认为在受西方话语影响很深的情况下,我们知识界的思维在很大程度受到西方话语的束缚,在民主认识上造成了不少错误的知识。因此,从西方民主话语体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对于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
曾世逸:能不能具体谈谈人们对民主有哪些误解?
房宁:我认为现在至少流行着五种误解:
第一个是把选举等同于民主;第二个,也是人们常说的:民主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可以防止最坏的;第三个是认为民主是普适性的政治制度;在这三种关于民主观念方面的误解之外,还有两种比较具体的知识方面的误解:一个是认为多党制能够遏制腐败;再有一个是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扩大党内民主是一种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
曾世逸:这些好像都是比较流行的看法。
房宁:那就算我挑战流行吧(笑)。
不要把民主等同于选举
曾世逸:请您具体解释一下第一个误解——“把民主等同于选举”。
房宁:很多人若明若暗地持此看法。选举确实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和全部。
从理论上说,民主政治有两个基本要义:分权制衡与多数决定。这两点,可以从西方民主政治历史发展中归纳出来。比如,一般认为西方议会民主制的起点是《大宪章》,《大宪章》的核心就是分权制衡。分权制衡可以说是从13世纪到17世纪——欧洲民主政治孕育时期的民主基因。到了英国革命,17世纪40年代后,这时提出了民主政治的第二条要义:多数决定或者说人民主权。可见,从理论上看,选举政治只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而不是实质,更不是全部。
曾世逸:有些人可能并不认为选举是民主的全部,而是民主政治的首要特征。很多人也把竞争性普选作为民主国家的第一条标准。从理论上来说,能否站得住脚?
房宁:仅从理论上来判断是非,本身就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从现实、经验层面提出问题。从现实看,坦率地说,我认为在中国,竞争性选举并非当务之急——当然并非永远不能。我这样说可能会令人失望,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我只能这样说。即使问一百遍,我还会这样回答。
从现实看,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这是社会关系急剧变化和调整的时期,社会矛盾、问题丛生。从欧洲及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竞争性选举等民主形式并不合适这一时期的社会需要,竞选加剧社会矛盾,经常动荡,也经常被中止。这样的历史事实说明,民主形式的优劣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一种民主形式究竟好不好,要看社会发展的阶段,要看需要和条件。
况且,竞争性选举本身有个痼疾,即“金钱政治”的问题,这在西方民主政治中非常明显。在竞争性选举中,那些掌握很多经济资源的人和集团,必然要利用这些资源去影响和控制选举,控制社会公共权力。在商业社会中,“金钱是政治的乳母”,没有巨额选举经费就无法获得候选人提名,也无法进行竞争宣传、争取选票。选举的实质过程是:金钱掌握媒体,影响民意,最终操控选情。这已经是体制化的现象,是商业化社会的必然现象。
中国今天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一部分人也掌握了大量金钱,他们也正希望利用手中的金钱去影响政治,去换取权力。如果在这个时候中国实行竞争性选举,那么正好给金钱与权力结合提供合法形式,很有可能形成大规模的金钱对政治的介入。我想这并不是民主的价值取向。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关心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人们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如果类似于这样的重要问题都没有考虑或没有考虑清楚,就讨论民主政治、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那不是十分轻率吗?
曾世逸:人们会说,转型时期进行民主选举、民主转型,即使短期内会有一些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民族还是有利的。很多人可能会指出台湾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成功例子;还有人说,俄罗斯虽然前几年比较困难,但现在出现了强劲的反弹。
房宁:台湾是个恰当的例子吗?台湾的民主恰恰是黑金的政治,恰恰证明了其民主选举的失败。台湾人民已经开始厌倦了黑金政治,“红衫军”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还应当去问一问俄罗斯人民:为所谓的“民主”付出整整一代人的代价值得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十余年的严重动乱与衰退,俄罗斯陷入了“寡头式民主自由体制”。在几次调查中,50%以上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不是“民主社会”,民主化在俄罗斯遭受了失败。这才是俄罗斯人民真正的感受,美国也是这样看的。其他转型后的东欧国家如何?他们变成了欧洲的附庸,在苦苦哀求欧洲的富国打开一个门缝,“民主”把一个个民族变成了乞求者。他们的内心是不平静的。
1999年,普京总统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沉痛地指出:“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近年来,普京总统提出了“主权民主”的重要思想,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是俄罗斯人民在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后,对民主得出的重新认识。而自以为是、装模作样的西方却认为俄罗斯的民主脱轨了。俄罗斯发生的事情,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曾世逸:我们是否还应该注意到:人们之所以强调选举问题,是因为不选举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是因为现实问题这么严重,所以才特别重视选举。
房宁:这是一种简单的、反映式的思维方法,把一个宏大的社会实践看成像一道练习本上的数学题。解数学题是抽象的,但现实不是抽象的。很多问题之所以存在,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而不只是一个原因;也不能说解决这一个问题,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有人说竞选能解决问题,也许可能。但是事情不是一对一的,不是单纯的。政治现象、政治问题都很复杂。解决问题,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多种条件和多种后果。将针对一两个问题,就提出重大的政治改革要求,这样考虑问题的人头脑太简单了,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不懂历史,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在历史上,政治进程从来的单一的原因促成的,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即使实行竞选,很多问题也照样存在,而且还会带来新的问题,这在很多国家的历史、现实中都有明证。
民主曾经带来最坏的结果
曾世逸:还有些人可能会说,选举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但可以解决更多问题,正所谓:民主不是最好的,但可以防止最坏的。
房宁: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种误解。说民主可以防止最坏的,只是一种想象,是一种简单的推论,而不是历史事实与真相。
民主政治出现在西方少说也有两三百年了,在多数时候这种论断都是站不住脚的。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西方的政治体制才逐步稳定下来。也就是说,在其诞生以来的多数时候,民主不是最好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最坏的,因此被人们多次抛弃。
比如法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不久变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第二共和国又变成了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差点变成了第三帝国,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更是历史上出了名的不稳定,政府更迭大约半年就一次。只是到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作了一些调整,加强了集中,才逐步稳定下来。而已经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从1789年到现在,大多数时候民主政治“doesn't work”。如果当年法国的民主能行,人们是不会选择帝制的。第二帝国的皇帝是法国人选出来的,路易·波拿巴可是得90%以上的选票呀。
法国议会民主发展的坎坷经历表明,当议会民主严重不适合于社会发展要求时,它就可能变成没用的东西,甚至是最坏的东西,而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这样的历史背后反映的是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并不适于采取议会民主和多党竞争。类似的例子还有德国。
民主带来最坏的结果,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文革”。当然有人会说“文革”不是民主。这也许正说明我们把民主理想化的倾向。不能说一件事情干坏了就不是民主,好的结果才是民主。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就是现在一些人所要求的自由民主,言论自由吗?
曾世逸:有人可能会说,历史上的这些情况,都是民主政治尚不成熟、不完善的问题。民主政治完善了,再不会出现那些坏结果了。
房宁:所谓民主制度完善不完善,主要不是看其本身。重要的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条件,离开特定条件,完善与否是假问题;不具备条件,民主可能导致严重的结果。
民主政治没有普适性
房宁:上面这个问题还涉及到我讲的第三种误解:民主政治的普适性问题。有人认为把西方“完善的民主制度”搬过来就行,问题是当你的条件不成熟时,别人完善的制度拿到你这里就不完善了,正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古人都已经懂了。
讲到民主的普适性,我认为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观念层面,我们称之为民主观念;一是实践层面,我们称之为民主政治。我认为民主观念是有普适性的。尽管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对民主的阐释和理解有区别,但它包含普适性——我是说“包含”,而不是说民主观念大家都一样。中国与美国的民主观不一样,英国的跟美国的也不一样,法国的跟英国的差得更远。但尽管各国民主观念千差万别,其中还是有共性的,有共通、一致的地方,这就是人民主权观念,也就是人民对公共权力的主张,或者说大家都认为公共权力属于人民或社会多数成员。
这种观念我认为是一种普适价值。但如果说到民主政治,就很难说有普适性了,因为它是历史的、具体的、特殊的。也就是说,即使表面上这些制度可能有类似之处,但它是各个民族经过试错、筛选而逐步形成的。不仅国家之间民主政治有区别,而且即使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其民主政治也不一样。
一个国家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所谓的“国情”,包括自然禀赋、经济发展程度、历史文化传统等。
二是这个民族当前面临的任务。比如西方民主政治,它解决的任务是什么呢?是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s)的关系问题。而中国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中国不是说不要解决老百姓的权利问题,但首先是民族复兴的问题,是富国强兵富民这样一些任务。所以其政治制度必须有利于这个任务的完成,否则就不行,就立不住,就会垮台。比如俄罗斯,它曾经建立了一套民主制度,但现在他们重新做出了选择。制度是人选择的,但选择不是任意的。人们是在历史给定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选择的。
三是国际环境。人们都希望中国更加自由、开放、民主,我也一样,但是别忘了有个美国的存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遏制和“西化”、“分化”,必然制约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有没有美国,中国的民主政治大不一样。柏拉图早就注意到了民主政治引发的“外援”现象,他说过:“就像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只要遇到一点儿外邪就会生病……一个国家同样,只要稍有机会,这一党从寡头国家引进盟友,那一党从民主国家引进盟友,这样这个国家就病了,内战就起了。”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民主政治,尤其是竞选可能成为引起外国干预、影响本国内部事务的一个因素。
曾世逸:与您的这个观点相反,一些人认为,美国不是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制约因素。如果中国与美国一样实行了民主政治,没有了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房宁:这种看法太幼稚了吧?!看看俄罗斯吧,美国因为俄罗斯变成“民主国家”而不再遏制俄罗斯了吗?
多党制会使中国的腐败问题更严重
曾世逸:请您再谈谈多党制的问题。
房宁:一些人认为多党制是治理腐败的灵丹妙药。但历史恰恰证明,多党制恰恰是使腐败加重的原因。
正如我在书中所讲,美国民主政治中两党制的出现,曾引发了美国历史上非常严重的腐败,并且延续了80多年。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党分赃制”及其带来的腐败问题。在“政党分赃制”下,不仅执政党要谋一党之私,一上台便尽力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攫取资源,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而且各级官员个人的腐败更是变本加厉。
其实西方对腐败问题的处理,不是靠多党制,而是靠行政内控,即行政监督和行政权力制约机制。这样才逐步解决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当然不是说西方已经没有腐败,比如日本安倍内阁的“农水相”连续出现腐败问题,接连三任“农水相”完蛋了。
曾世逸:一些人认为多党制能够遏制腐败,往往与腐败问题在一党制下得不到有效遏制有关。
房宁:如果说中国有严重的腐败问题的话,原因就是一党制吗?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一党制,但原来并没有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问题。很明显,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不是因为一党制,而是出现了市场经济这个变量——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不搞市场经济。有人因为腐败问题而不要一党制,为什么他们不因此而不要市场经济呢?
如果我们查查腐败大案要案的资料,不难发现其轨迹,中国的腐败问题其实是1992年以后才明显地严重化的。腐败问题与市场经济有明显的关联,而与一党制没有必然联系。治理腐败问题,关键是解决市场对权力的腐蚀问题。这主要是个技术性的问题,是怎么监督的问题,当然也有教育的问题。公共权力会带来腐败,但也不能因此而不要公共权力。
曾世逸:您在书中提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越性是有先进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但是,这个优点也常常在另一方面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弱点——易于形成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官僚主义。”怎么防范和解决这一问题?
房宁:一党制肯定有其问题与缺点。在革命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有风险的,入党对个人没什么好处,因此那时加入者大多数是纯洁、无私的。只是执政以后,特别是现在,一些人入党,可能是为利益而来。这样的人加入党组织,就难免带来腐败问题。就党的整体而言,唯一执政党地位会使之无私,而多党制条件下的政党恰恰是有私利的。一党制条件下,执政党就没必要因政党竞争而谋私利,正所谓“王者无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私利的——这恰恰是一党制带来的,但是,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党员可能谋私。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主要问题是怎么去抑制其党员,特别是干部的谋私问题。
扩大党内民主并不稳健
曾世逸:谈到党的问题,请您再分析一下“扩大党内民主是稳健的民主改革路径”这个观点。
房宁:扩大党内民主,是最近讲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可能跟即将召开的十七大有关。有一种观点认为,扩大党内民主,引入竞选制,是比较稳妥的策略,“先党内后党外”嘛。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原因很简单,党内党外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在党内搞竞争性选举,必然促使各级干部从党外寻找资源,党内竞争就会变成党外竞争。有关这个问题最近的教训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党内斗争相持不下,于是从党外寻找资源,发动群众。作为文革象征性起点的“五一六通知”,还只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很快就变成了全国性的红卫兵运动。党内两派力量都借助群众力量,都纷纷动员红卫兵,结果造成群众斗群众的“全面内战”。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来看,“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界线也就是从“五一六”到“八一八”。
发展党内民主是十分必要的,但正确的思路应当是扩大参与、落实权利和加强监督,而不是加强选举的竞争性。
收稿日期:2007-09-10
标签:美国选举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美国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党内民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