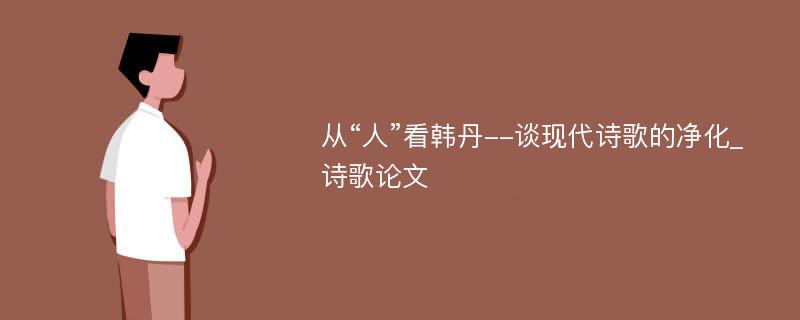
菡萏照人——漫谈当今现代诗的纯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菡萏论文,当今论文,照人论文,现代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提出了“诗思”、“诗感”、“诗语”三个诗的相关性问题,并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了现代诗的纯化问题。作者指出,应该用清爽、清纯、清冽的语言去写诗,让语言通过诗而超越实用功利性和所指的偏狭性,获取诗意的丰富性;也应让诗通过语言而精当、鲜活地命名心灵的思与悟,呈示生命和存在的本真性。
如今确实是诗意贫乏的年代。实用理性、权力话语和消费浪潮的多重压力,已使诗歌风光不再。中国的当代诗人往往敏于感知世俗生活的冷暖,随不断变幻的热点而变换姿态,现在则从“众声喧哗”转为“孤独者”、“边缘人”了。诗人开始受到他嘲:诗中有黄金屋吗?写诗能写出个拿破仑吗?
但艾青早就说过,他特别喜爱阿波里奈尔(Apollinaire )的名句:“当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节仗我也不换。”80年代时艾青应邀访问意大利,临行前给他制作名片——当时他已恢复了许多头衔,他执意只让写上:“中国诗人 艾青”。
一个民族没有诗是真实的大不幸。一个国家没有众多出色的诗人,是文化的灾难。
在我看来,中国诗坛(包括港澳台)当前的景观是:作品铺天盖地,精品寥若晨星。尽管每年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的诗作达七、八万首,但实际上这种表面繁华景象,被著名老诗人郑敏教授称为“繁荣中的消亡”。“消亡”之说似有过之,“消寂”之谓堪可坐实。真正足以震撼的精典太少了。
“铺天盖地”而又“寥若晨星”,准是诗歌自身出了什么毛病。就目前主流而言,多数人从事的是现代的、自由体的书写。我们的问题是:真的是现代了吗?达到了心灵的自由和诗性的自由了吗?是诗的美抑或诗的反美?能写什么就是什么、称它为诗就是诗吗?
不断的自我反省是走出迷茫、追求超越的前提。我以为,如下的通病正在侵袭我们现代诗健康的肌体:
思绪的蓼扰化;信息的砂砾化;诗意的平涂化;想象的贫困化;语言的浑浊化。
在20世纪的中国诗界,现代自由诗是从内容到形式作为和传统旧诗词的对立与反叛而产生的诗歌新品种。它应顺时代潮流,以接近民众的白话语言折射现实与人生,以打破旧格律的束缚而创造自由的律动为形式革命之目标,慕企现代诗歌意识及表达方式同新世纪共脉博。一代又一代的新诗人在与历史、命运、生存、灵魂、精神的遭逢中,前仆后继、孜孜矻矻、血崩高蹈,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留下了辉煌与缺憾,留下了迄今需要接力探索的诗学命题。而回眸本世纪下半叶——即离我们较近的当代,可否这样说:我们的现代自由诗,大体上是始而直白,继而朦胧,当下则有些晦暗、杂乱、浑浊了。
古典已离我们遥远,但古人的智慧仍可发覆。唐释皎然著《诗式》,对于诗的品藻,有“菡萏照水”一说,寓意甚深。菡萏即荷花,浮翠水面,密节交接,膨大成藕,其华鲜艳,出污泥而不染也。我想,与自然界总能量守恒原理相仿佛,诗歌和艺术创作的最高使命也是从万千现象的零乱中梳理秩序,臻于清爽、清丽、苍深清秀,雅健有法,一如菡萏照水般有审美的快感。现代诗固然是对“典雅优美”原则的打破,使更多富于动感的素材和话语得以入诗,但诗之美须以审美力及其对人的震撼力为准。那种极端的流里流气,“无法无天”的任性书写,能达到灵魂的高度和精神的范本,使读者感动得刻骨铭心么?
应当说,对于现代诗仅仅在“懂”与“不懂”上加以讨论,往往是懵懂不审的批评错位。如果确认,古典诗、浪漫派诗总体上是在意识层面上艺术地与理性地美化了人的精神,那么现代诗是在“上帝死了”以后,侧重于面对世界的纷乱复杂,在现代人充满矛盾、受扭曲、无秩序、一半是理性一半是非理性的心灵深处,用一种所谓“搅翻的方式”触摸、体验和表现瞬间的忧伤或狂喜,从而以更本真同时也不正规的策略向人的灵魂逼近。但“显”中有“隐”,“杂”中有“纯”,表面繁复的背后仍和冥冥中一种可知的东西相联。我赞成澳门著名诗人陶里的说法:“鉴赏现代诗的态度是把它看作一个整体,不能把它分析到支离破碎。”(《认识现代诗》)鉴赏如此,创作也同样如此。
现代诗在以复杂世界为背景的现代人心灵深渊中探险,自然比摆弄流通量极大的惯性概念、名词、术语、意欲要困难得多。尤其对一些年轻诗人,超越迷茫、把握现代、提升品位,恐怕需要相应的深层学识结构和沉思。在这里,我愿意提出三个相关性问题,和诸位一起探讨。
一、关于诗思
把思想绝对地排斥在现代诗之外,或者以为写诗可以胡思乱想,是一种浅薄的误解。
正是纷杂的现实世界为诗提供着思索的张力。诗与思的绾结,又因其总要涉及人生的忧患与苦难、人性的困惑与渴念、生命的根基与本真、生存的此岸与彼岸等问题而成为可能。本世纪重要的现代诗人,从艾略特、里尔克、聂鲁达、奥登等等到中国的闻一多、戴望舒、艾青、穆旦等等,在他们“陌生化”的作品中,莫不浸淫着对自己的、民族的和人类的命运的思考。“我思故我在”,他们都出色地担当了“大地之子”、“人之子”兼思想者的角色。
诗歌历来有母题的呈示。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古典的、浪漫的和现代的母题——这里仅就总体而言,且有些不免交叉。“古典”母题通常有:羁旅、乡愁、戌边、游仙、生死、咏史、山水、玉石、酬答……。“浪漫”母题通常有:爱情、友谊、纪游、梦幻、箴言、告白……。“现代”母题则通常是:生死、命运、磨难、灵与肉、美与丑、罪与恶……。更着眼于对人本真的生存状态作诗性的解剖和透视,因而也是对灵魂更切实、并抛却种种伪饰的接近。现代诗的“思”往往重暗示,不喜欢太过浅露和直白。皮相地看现代诗是反理性的,实际上好的现代诗隐藏着深邃的理性。
这种“诗思”,十分强调艺术的超越性思维。
一是对当下实事的超越。中国当代诗歌有过泥乎实、陷于“写中心”“贴标签”(如大陆五、六十年代)的教训。近些年有些现代诗照样挤到一股道上对某些时髦题材、素材、资料进行跟踪式的“热处理”。一些诗名为“新潮”而实则刮起干燥的热风,充塞着社会日常生活中庸俗的刺激、莫名的琐碎、砂砾般的细节,成为实事表象的繁冗堆积。现代诗切忌开杂货铺,记流水帐。现代诗的功能也不在于统计砂砾的数量,而是穿透沙滩渴望见到绿洲,触及那被平常之物所遮蔽的“绿洲”的力量。诗的“境界”是一种心灵状态、一个审美磁场,总要求诗人有超常的思维,透过可视、可数的客体事物的表层,去沉思潜在,去领悟自然、宇宙的深邃邈远与个人的相对渺小,去发现和言说“第二世界”——诗与艺术的世界的奥秘。因之,现代诗人能否机智地对“写实”予以规避与超越,是一种诗性的考验。
二是对因果逻辑的超越。因果逻辑是一种线性思维,讲究示意的明确性,叙写的连贯性,梯次的合理性,所谓“起、承、转、合”也就成为规范。然而诗歌毕竟因内在知性意蕴而具有多义性和随机性。尤其是现代更为复杂的境遇与更见模糊的心绪相对应,势必要超越固有的逻辑和秩序,以意义的不确定、意象的自由交迭、意绪的弹跳腾跃以及时空的变换等等为策略,留出“空白”而为读者提供“期待视野”和二度创造的可能。那种“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整体氛围,那种“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过去了,阵雨喧闹的夏季”(杜运燮《秋》)的次序颠倒,并非反常出轨,乃是对诗所需要的“情绪逻辑”的尊重与恪守,也不难看出诗人思索的面容。钱钟书先生所言极是:“诗之情味与敷藻立喻之合乎事理成反比例。”(《管锥编》)但“反常”往往是寻求更深层次的“合道”。那种在反“逻辑”旗号下的失控与杂乱,那种废弃深度隐喻的横冲与直撞,同诗思所要求的使生活心灵化、使时间空间化相去甚远。
现代诗不应是当下俗事的认同与复述。它入世而昭示深渊,出世而抚慰生灵。在入世与出世之间高蹈,思,使诗歌坚实而超前。
二、关于诗感
我们的不幸往往是被迟钝和惰性所击败。许多作品在不断地重复他人也重复自己。
现代诗可谓一种寻求“陌生化”的艺术。诗人如果只写人们熟悉的、喜欢的、通俗的东西,只能是一种迎合,是低水平的重复,也是对诗与艺术认识上的倒退。诗歌是情操熏陶,不能随随便便地乱写或模仿可以达到的。
从生活经验到诗的创造,中间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是诗的转换,或称中介。诗歌的多元而又有机相连的审美要素,都在这一转换、中介中,凝集起来,并爆发诗意之光。
诗感就是现代诗实现“诗的转换”的重要一环。
徐志摩在《诗镌放假》一文中说:“‘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许多现代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并不受经验主义逻辑思维的左右,相反,往往将经验、知识、逻辑置于一种“背景”的地位,而给生活中隐在的潜意识以较大的活动空间;往往是感情的跳跃带动思绪的激活,思绪的激活又促进感情的腾挪,相辅相成;往往是思绪和思路网状幅射,浮想联翩,如同旋转的钻石在不同时空、不同角度发出异彩。此时此刻,一旦找到契机,找到触媒,找到灵感,那自由了的潜意识和创造力会在“瞬间”奔突,那心脏、血脉、肉体、话语很自然地谐调起来,在奇妙和美妙的运动中产生出一首诗来。
我想提醒诸位注意的是,我用了“背景”和“瞬间”这两个词。它们是关联的。现代诗人那种在瞬间的、犹如泉涌、犹如电光石火的激动,自然是一种可贵的心灵经历;但如果这一激动是缺少“背景”亦即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经验的提升作基础的激动,那么,很容易滑向滥而失真或浅而失实的高调、浮声。“瞬间”须以“背景”作支撑,“背景”也在“瞬间”展示其深意。
不妨举两则同是写“瞬间”感受的诗例,看看诗感份量的轻重。有一首诗作写“一丝美丽焚燃在心跳底急梦处”,称灵魂的不可磨灭性“凝住这一刻”。而这“瞬间”,是所谓“有如驾急河乘恺悦底脆梦流到相思草角底静回处与最后的人琴在有欢与无欢底接线中——奔灭”。这大概是写爱情和生死的感受。语言的拗口蹩脚且不去说,问题是在某种神秘的气氛中令人迷惑不解,故弄玄虚而使诗感达不到一种生命的证明。另一首诗亦名为《瞬间》:
“所有失落的春天/都在这一瞬间归来/所有的花都盛开,果实熟落/所有的大地都海潮澎湃‖生命曾是一盆温吞的炭火/突然迸发出神奇的光彩/所有的日子都将充满意义/所有的等待都不再痛苦难挨‖像云携一个梦款款走近/像星含两颗泪缓缓绽开/生命因这一刻而进入永恒/世界因这一刻而真实存在。”
这春雷爆发式的诗感,是经历漫长的“失落的春天”后的瞬间狂喜。“所有的等待都不再痛苦难挨”写足了沧桑,“所有的日子都将充满意义”点明了未来。“瞬间”与“永恒”在诗里难解难分。诗风敦素,直抒胸臆,却又有相当现代的“背景”与沉思渗溶其间。
诗威是一种悟性,它应是超迈的、独特的。从这里出发,诗人在想象中拓边掠土,在文本中翻云覆雨。当然不是唯新是鹜。诗感要对象化和审美化,才能避免无名的、单纯原动性的发泄,而在有所拒绝又有所撷取之间获致平衡,显出应有的质地来。
三、关于诗语
诗歌是很难翻译的,尤其是中文汉语诗歌。诗人、旅美学者叶维廉考证过王维的一行诗“涧户寂无人”曾有四种译法。一云“涧边的草庐是寂静的,没有人在家”;二曰“谷中的房屋荒废,里面没人”;三云“隐在峡谷中,无人注意”;四曰“没有任何人家住在荒谷中”。诗意情趣在上述诸种翻译中失落了。美国有一种毛泽东诗词的译本,把“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译作“唐宗宋祖,文化修养不是太高,未能充分欣赏《国风》和《离骚》”;把“数风流人物”句中的“风流”,理解为花花公子;把《西江月·井冈山》中的“黄洋界上炮声隆”一句译成“在黄色海洋的边上响起了隆隆炮声”,好像是一支海军陆战队要登陆了。如此翻译,不仅味同嚼蜡,且是可笑的文化错位。
这种现象也说明,具有深厚民族文化传统的中文汉语,太有特色,太富暗喻和弹性,太凝结感性具像和悟性内涵,太能从可见之物达不可见之境,也太能提供一个开放的解读空间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范诺洛萨曾在《汉字作为诗歌的媒体》(1908年)一文中确认:“诗歌的语言总是波动着,一层又一层的弦外之音,和与大自然的亲和。在汉语中这种暗喻的可见性使得这种诗语的质地提高到最强烈的程度。”又说:“诗的思维通过暗示来工作,将最大量的意义压进一个句子,使它孕育,充电,自内发光。在汉语里,每个字都聚存着这种能量在其体内。”
我以为,中华民族当今的现代诗人之所以应该重视对汉语这一民族瑰宝的再认识、再发掘以及创造性的运用,是因为新诗在其发展进程中,对于母语的优越性,曾经乃至今日尚有所忽视。当年胡适之学贯中西,读书破万卷,首创白话诗,的确功不可没。但胡博士在推动“诗体革命”时带着明显的社会启蒙和普及教育的功利性。在这种历史进步文化现象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个矛盾的问题,即他一方面坚持适应时代生活的“活语言”,一方面却又将唐诗宋词及更古的典籍贬为“死语言”而不屑一顾。这种急躁的意向在当时可以理解,却经不起学理和时间的推敲。无论是文言诗或白话诗,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原始语言。既然用汉语创作,语言是一条长河,一个形式系统,鼓吹“一切从零开始”,无异于用热情替代一切,仍是不可取的一种“拥护/打倒”二元对立的思维偏向。今天是否像苏轼所批评过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上欧阳内翰书》)呢?值得我们正视和研究。
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写道:“我们关心的是说话,而说话又驱使我们去纯洁部落的方言”。为了这种纯洁,现代诗需要以很高的审美敏感爱护母语,防止其衰危、扭曲及污染。我们既反对词藻的老化、教条、贫乏单调,也戒拒言说的粗鄙、刺耳、玩世不恭;既警惕行文的迳直、浅漏、大而无当,也废弃抒写的梗阻、念咒、乱施魔法。
现代诗的创造是一次性的——那吸聚的经验、智慧、直觉、触角、记忆、艺术以及表现,似乎总是非重复性的、令人惊奇的第一次言说;但对于它的理解与鉴赏则是非一次性的——那足以领悟天、地、自然、人的意旨,那恒久性的内蕴深长思之。我们把这种寻索视作诗的生命。
最后,我想说,关于现代诗的成败得失,人们已经谈论甚多,但我还是需要重申:这一诗域体现自己时代历尽创伤的良知,也是才俊集聚之地。在当今迷漫着世俗习气的氛围里,现代诗创造者们的寂寞、清静和雅健,尤如守护一座精神的孤岛。这不应令人悲伤而应深感骄傲。中国的圣贤历来重道德文章,我深信道德第一,诗文第二。而为诗为文,其根基与前提,是对传统、对历史、对曾经发生与正在发展的事件和事实有所感悟,是不断拓展视野和思维且以新知充实自己,是在诗学观念和技艺上天久日长地磨炼自己,而后才可能“天高任鸟飞,海阔纵鱼跃”,才可以谈得上创新或“前卫”。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现代”与“传统”截然对立起来,是不明智的。
记得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中说:“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是一根支柱,一根栋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于世。”那么,愿我们的诗人站到现代精神的高地,追求卓越,追求菡萏照水般的鲜亮,凸显现代人的人格器度和文化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