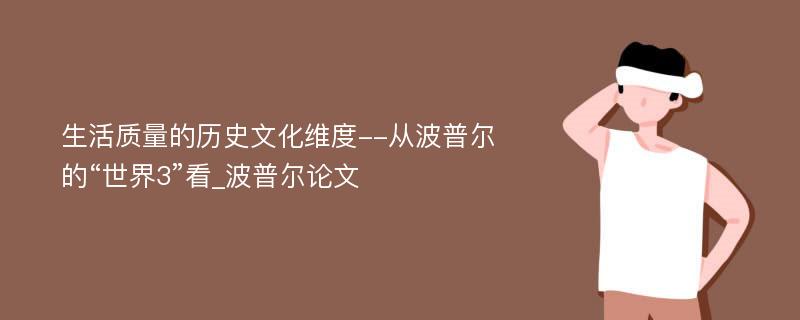
生活质量的历史文化向度——从波普尔“世界3”的观点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文化论文,生活质量论文,观点论文,世界论文,波普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终极原则。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综观几十年来的生活质量研究,不外乎以下三种角度:客观角度;主观角度;或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从波普尔三个世界的观点看,以上三种生活质量的研究都有一种缺陷,即只考虑了“世界1”和“世界2”里的生活质量,而没能考虑到“世界3”里的生活质量问题。从波普尔“世界3”的观点来看,生活质量应具有一种历史文化向度。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人类恰恰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这样,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去研究生活质量,自然构成了生活质量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就是试图沿着这种思路,来探讨生活质量的历史文化内涵。
一、以往生活质量研究的角度及其缺陷
1933年,由威廉·奥格朋负责指导研究工作的胡佛研究中心发表了两本《近期美国社会动向》,着重探讨了美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动向,这被认为是对生活质量问题最早和最重要的尝试之一。1958年,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认为“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对生活水平的全面评价,因此而被看作是生活质量问题及其研究的始作俑者。此后,各国的学者们对“生活质量”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综观这些研究,主要有三种角度,即从客观角度、从主观角度、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一些学者从客观角度进行生活质量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是从这种角度研究生活质量的,他的生活质量的概念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内容。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认为,“生活质量是反映人们生活和福利状况的一种标志,它包括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内容。生活质量的自然方面是指人们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等等;生活质量的社会方面是指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生活服务状况、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等等。”此类学者对于生活质量的理解是从影响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方面进行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则从反映人们生活舒适、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和研究生活质量。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将生活质量定义为“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注:林南、卢汉龙:《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结构模型探讨》,《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认为,主观的生活质量和客观的生活质量都能反映出人们生活的好坏,因而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但也只是片面的合理性,最好的办法是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给生活质量下的定义就是:“生活质量是人类为满足各方面需要而进行的全部活动所需生活条件的概括和总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它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社会提供人们生活的充分程度和人们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注:徐愫:《生活质量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前苏联学者对西方“生活质量”理论侧重于主观方面的研究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西方研究的前提是承诺了它的所有公民都是苦于商品和服务剩余、苦于物质上有保障的人,而实际上,在西方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生活于官方承认的贫困线以下。他们将居民的健康问题置于生活质量的核心地位。对居民的身心健康问题进行研究,这实际上也是从主观、客观两方面结合来理解生活质量。
从以上各种角度去理解生活质量,各有优缺点。从客观方面理解生活质量,设计一套生活质量指数或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进行评估,比较容易实际操作,而这又失去了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从主观方面理解生活质量,在评估时,虽也能设计出一套指数或指标体系,但不易于实际操作。值得指出的是,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分别理解和研究的生活质量并非总是一致的,有时甚至会大相径庭。因为每一个体所追求的生活目标都不尽相同,所以不同个体对同一客观条件生活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就不一定相同。客观指数高,人们的主观感受却并不一定好;人们的主观感觉好,却并不一定通过很高的客观指数表现出来。如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人对清心寡欲生活的满意度也很高,其生活质量就高;而如果给予他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却剥夺他的信仰自由的话,他的生活质量也不可能高。同是从客观角度理解生活质量,采用不同的指数研究,得到的生活质量也会有很大的出入。例如,用莫里斯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对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所得数值分别为75和42,然而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却相差不大(注:引自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把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结合起来研究生活质量,无疑可以得到更为真实的情况,然而这种结合却给人以外在的感觉,就是将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机械地结合起来,以达到“全面”的新角度,一个新的“辩证”合题。
综观上述三种角度,其实完全可以归结为两种角度,即主观角度和客观角度,也就是从自然的、物理的方面和精神的、心理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生活质量的问题。而人类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和多样态的统一体,除了自然物理世界和精神心理世界之外,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一书中还为我们讲述了“第三世界”的存在。他说,“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客观内容的世界”(注: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第三世界”即指的是客观知识世界,亦即历史文化世界。在我们看来,上述的从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以及主客观相结合的方面去理解的生活质量都属于世界1和世界2里的生活质量问题,而没有涉及世界3,即语言文化世界里的生活质量问题。
二、“世界3”里生活质量问题的合法性
这种“世界3”里的生活质量又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非常重要。波普尔在论述“世界3”的时候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第三世界的成长做贡献……我们大家都想掌握这一世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脱离它而存在,因为大家都使用语言,没有语言我们几乎不成其为人……它对我们的作用,比起我们对它所起的创造作用,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了,更加关系到我们的成长”(注: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下面我们再举一个已经举过许多次的例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1994年的一部电视专题片中有一段记者采访一位16岁放羊少年的谈话。“你为啥放羊?”“赚钱。”“赚钱干啥?”“娶媳妇。”“娶媳妇为啥?”“生娃娃。”“生娃娃作啥?”“放羊。”正如一位学者对此所做的评论:“如果这段对话不是发生在人类准备‘跨世纪’的1994年,而是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1894年,甚至一千年前的994年,又有谁会感到时间上的‘错位’呢?”(注:孙正聿、李璐玮:《现代教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我们不会感到时间上的错位,我们只能说他的生活质量不高。这位牧羊少年,如果真的赚了钱、娶了媳妇、生了娃娃,他对他的生活无疑将是满意的,即“世界1”里的生活质量和“世界2”里的生活质量都是很高的。可是,我们还是不能说他的生活质量是高层次的,原因不在于他不具备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不在于他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不高,而在于他没能融入20世纪末的生活状态之中。也就是说,他在“世界3”里的生活质量是低层次的。
“世界3”里的生活质量问题根源于人类生活的本源、人类生存的本性。人类的生存本性具有两重性:一是人的自然性,一是人的超自然性。人的自然本性决定了人首先要维持生命的自然存在;人的超自然本性又决定了人注定要追求自然存在的意义。人类生存的两重性在逻辑上不是对立的,在时间上也没有先后。人类的这两重生存本性是统一的,自然本性是以扬弃的形式包含在超自然本性之中的。因而,“发展”构成了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命活动表现为追求生命意义的“生活”。这就构成了人的生命活动和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区别所在,即这种区别体现在:人除了要维持生命存在之外,还要追求这种生活的意义。这种区别不仅仅意味着,人要在生存活动之外“生活”,即人要在生命之外追求生活的意义;而且,更主要地,这种区别意味着,人类的生存活动本身就是生活,即人类维持生命存在的方式本身就具有意义。人们维持自然本性的肉体生命的方式就是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的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就是能够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人类必须首先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才能保持自身的肉体生命存在,仅凭这一点,就有了相当的意义),但物质生产活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人们进行其他意义追求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意义追求活动。甚至在有的时候,后者还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欧洲,改革之后的宗教认为,一个人通过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占有的财富越多,他就越有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除了上帝的选民,其余人类都注定要受到诅咒,永世不得超度。这样,物质生产活动就成为为上帝尽天职的事业而具有了崇高的意义。“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生活的意义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换句话说,人的全部活动都是生活活动,在生活活动之外,人类一无所有。人类生活于世界之上,就要力争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力争使自己生活得更好。
这就是生活的“本源”。只有理解了生活的本源问题,才可能更好地理解和研究生活质量的问题。人类的生存方式就是“生活”。因而人类不仅必须而且必然要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使自身活得更有意义。人类生活的好坏也就是人类的生活质量的高低。每一个人,无论是“原始人”、“古代人”、“近代人”,还是“现代人”,都会自觉地追求生命的意义,自觉地提高生活的质量。所不同的是,不同时代的人对生命意义的觉解是不同的。
三、生活质量的历史文化内涵
我们认为,以往三种生活质量的研究,由于离开了人类生活的本源来研究生活质量,所以没能考虑到生活质量的历史文化内涵。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人类恰恰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这样,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去研究生活质量,自然构成了生活质量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因为人类不仅要生存于世界之上,还要追求这种生存活动的意义。人类追求生活意义的过程就是人类创造历史文化的过程。“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有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页。)人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又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因而能够生活于文化继承与文化创造相融合的“意义世界”,亦即人类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中。卡西尔认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就是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加达默尔也认为,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不是个人占有历史文化,而是历史文化占有个人。而波普尔把他的第三世界作为人类文化的特有疆域,则着重指出了人之为人的文化品质特征。人不是生活于世界之外,而是生活于以自己的历史活动所创造的世界之中。这就表明,“人类不是以自己的自然存在而是以自己的历史活动所创造的社会—文化存在为中介,而构成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注: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页。)。以历史文化为真实根基、标示客观知识的“第三世界”是真实存在着的,人类的生活世界确有多个层次,既然如此,那么生活于多个层次生活世界中的人类,其生活质量的视角也应该具有多个向度。“世界3”里的生活质量揭示的就是生活质量的历史文化向度。
“世界3”里的生活质量如何衡量呢?其标准在于个人融入所生活时代的生活状态的程度,个人占有同时代历史文化的程度,亦即个人对其生活状态的觉解程度。冯友兰先生说,“人与其它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人们的生活状态是以特定的历史文化为内容的,它包括人的具有时代性特征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一个人只有与自己时代的历史文化相统一,他才能生活于自己时代的生活状态之中,他才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从主观的生活满意度方面去评估“世界2”里的生活质量,不容易实际操作。而从人的生活状态方面去评估“世界3”里的生活质量就更加不容易实际操作。
冯友兰先生按着从低到高的顺序,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等级: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其次是功利境界,然后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293页。)如果按照冯先生的理论,这位牧羊少年所能达到的最多只是功利境界,而不可能达到更高的境界,因为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缺乏更多的觉解。人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性的存在。他生活于某一具体的历史时代,但并不必然具备符合该时代特征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因为前者是一个“自然时间”概念,而后者是一个“历史时间”概念。生活于某一具体的历史时代而又没有处于该时代的生活状态中的人,不管他拥有多么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不管他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多么满意,他的生活质量也不可能是高层次的。要想拥有更高层次的生活质量,必须对与生活时代相适应的生活状态有更多的觉解。有高度觉解的人,“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禅宗有人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293页。)。
生活于同生活时代相适应的生活状态中的途径与方式,就在于普及和升华教育。一个人只有受到适当的教育,才有可能融入自己时代的历史文化中去。池田大作认为,“教育的根本课题是在于说明和回答人类应当怎样存在,人生应当怎样度过这些人类最重要的问题”(注: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9年版,第58页。)。冯友兰先生说,学习(哲学)的目的“就在于使人成为人,而不是某种人”。使人成为人,也就意味着使人融入自己时代的历史文化中。“教育是个体向历史、社会和时代认同的基础,又是历史、社会和时代对个体认可的前提。教育是个体占有历史文化与历史文化占有个体的中介。”(注:孙正聿、李璐玮:《现代教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当然,这里教育也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从客观角度进行的生活质量研究,在其列出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也包括了教育指标。但这些教育指标是围绕着教育年限与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多少的关系,或是教育年限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而进行的,而不是针对教育与个人对生活状态的觉解程度的关系进行的,即不是针对“世界3”里的生活质量问题。
我们这里提出的“世界3”里的生活质量,并不是为了否定“世界1”和“世界2”里的生活质量。恰恰相反,我们是在充分肯定它们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揭示了生活质量的新的向度。在当今条件下,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不应仅仅注重物质财富的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满意度的增加,即仅仅注重“世界1”和“世界2”里的生活质量,更应注重“世界3”里的生活质量问题。从前面放羊少年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一个人在“世界1”里和“世界2”里的生活质量都是很高的,但由于“世界3”里低度的生活质量,其总体的生活质量也是不可能高层次的;那样的生活也不是全面的、自由的生活,而只能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生活。如果仅仅注重“世界1”和“世界2”里的生活质量,而缺失了“世界3”的维度,是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
注释:
①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