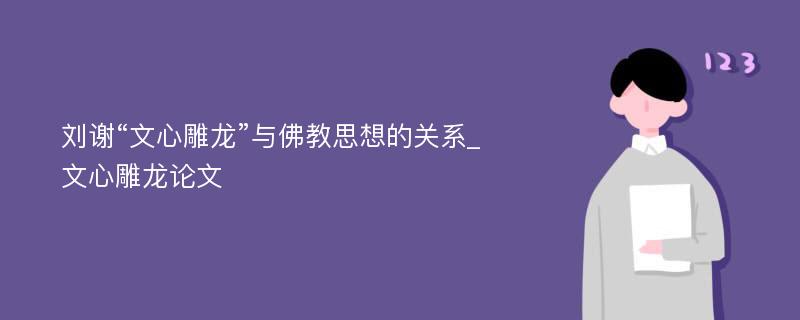
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思想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文心雕龙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刘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心雕龙》和佛学的关系是大家有过很多研究的老问题。不过,究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大家有很不同的观点。总起来说,强调有佛学思想影响和否定有佛学思想影响的说法,都有相当的片面性,不够公允。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认为首先要承认两个客观事实:一是刘勰从青年时期开始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而且是精通佛学的,他随僧佑在定林寺整理佛经,研究佛学,长达十余年之久,后来虽然进入官场,但是并没有离开佛学,仍然参加了很多佛学活动,最后还是成了佛教徒。他还以写佛教的碑志闻名,这也很值得注意。二是《文心雕龙》中确实没有多少佛学词语和概念,也没有很明显的、很直接地运用佛学思想来论文。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是很突出的。也许正是这两个问题,使研究者对《文心雕龙》和佛学的关系有了很分歧的看法。其实,我们应该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来理解这种现象:第一,儒家文化在中国是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化思想,它在每个时代都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具有深刻的潜在影响,即使在玄佛思想占有比较主要地位的南朝也是如此。第二,在那个时代,佛学和儒学不是对立的,而是完全可以互相兼容的。崇敬儒学和信仰佛学并不矛盾,它是可以同时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当时梁武帝就曾经提倡三教同源,也就是儒、释、道三教同源。第三,那时佛学的传播是要借助中国本土文化的,当时特别是借玄学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所以是玄佛合一的。而且从中国文化发展的特点来看,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包括外来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吸取有益内容,不断融合的。所以我们不要用那种似乎不同文化思想一定是互相排斥的观点来看问题。这样我们也许可以比较符合实际地来说明《文心雕龙》和佛学的关系。
我认为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虽然没有有意识地运用佛学思想来论文,但是实际上《文心雕龙》的写作还是潜移默化地受到佛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些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理”说和佛教的联系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共有七处涉及“神理”的概念,而在他的两篇佛学著作中涉及“神理”概念共三处,它们的含义是否一致,有什么联系,是我们研究《文心雕龙》和佛学关系的十分重要问题。很多研究者把《文心雕龙》中的“神理”概念说成是“自然之理”,其实是不符合刘勰原意的。现在我们先看《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市石像碑》(注:此引自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下“附录”中之“别著”。《灭惑论》原载《弘明集》卷八,《石像碑》全文见宋孔延之《会稽缀英总集》卷16。)这两篇佛学著作中的“神理”概念。
彼皆照悟神理,而鉴烛人世,过驷马于格言,逝川伤于上哲。
——《灭惑论》
夫道源虚寂,冥机通其感;神理幽深,玄德思其契。
——《石像碑》
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建安王,道性自凝,神理独照,动容立礼,发言成德,英风峻于间平,茂绩盛乎鲁卫。
——《石像碑》
刘勰一共用了三次“神理”的概念,都是指神明的真理。第二例即指至高的佛理,第一、三例是指对佛理的领悟。这个“神”不是神妙或自然的意思,而是指神佛,“神理”是神佛的最高原理。这一点大概是没有很大争议的,但是,这里的“神理”和《文心雕龙》中的“神理”是否是同一含义,则分歧就很大了。现在我们再看《文心雕龙》中的七处“神理”:
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原道》
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
——《原道》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原道》
《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
——《正纬》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明诗》
五色杂而黼黻,五音比而《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情采》
造化赋形,肢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丽辞》
在这七处地方,《原道》篇中三处“神理”,其实最为明显是说的神明的原理。第一例说“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正是说上天神明授予人类的启示,告诉人类什么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理,这就是最早的“人文”,“人文”之源正是来自于上天神明。河图洛书并非人类的创造,而是上天神明的意志之显现。第二例讲从伏羲到孔子都是研究“道心”和“神理”,取法乎河图洛书,从而对“人文”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里的“神理”和第一例的“神理”自然也是完全相同的。第三例赞语中所说的“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则是概括第二例的意义来说的,意义也和第二例相同。《正纬》篇中所说的“神理”就是指“神教”,也就是神明的教诲,而纬书本身就是体现天人合一思想的,这“神理”的意思和《原道》篇所说是完全一致的。《明诗》篇赞中所说的“神理”,是讲诗歌的起源是和人类的产生同步的,它也是天人合一的产物,“神理共契,政序相参”,前者指天,后者指人,说明诗歌是天神之理和人君之治相结合的结果。《情采》篇讲五色、五音、五情皆是神明早已设定好的天理。《丽辞》篇讲人的肢体都是对称的,宇宙间事物也都是对称的,这是造化和神理的自然表现,这个神理也是指上天神明赋予人类和万物的特点。可见,《文心雕龙》中的七处“神理”和刘勰佛学著作中的“神理”含义是相同的。过去之所以很多研究者把“神理”作为自然之理来解释,是因为要强调刘勰的思想和佛学没有关系,或者是为了说明刘勰的所谓唯物主义思想,实际上这些说法是不符合刘勰本意的。
当然,说“神理”的意思是指神明的原理,还不能证明它和佛学的关系,因为很多儒家也是主张天人合一,也是有神论者。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和刘勰的《灭惑论》和《石像碑》联系起来,就可以知道刘勰所说的“神理”和他的佛学思想是确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刘勰协助僧佑编撰的《出三藏记集》一书中看到“神理”一词也有相当广泛的运用,其含义和刘勰上述十处的含义是相同的,而且很明显是指神佛之理。如《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第四》中说:“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P12) 这里非常明确地说言辞所表达的“神理”其“理契乎神”。僧佑《出三藏记集卷第二》中说:“法宝所被远矣。夫神理本寂,感而后通,缘应中夏,始自汉代。”[1](P22) 这里的“神理”自然也是指佛家的神理。又于《慧远法师传》中说:“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致敬。其神理之迹,固未可测也。”[1](P568) 这也是指慧远对佛的神理之传播所产生的影响。“神理”一词是当时佛教的通用词语,刘勰既精通佛学经典,他自然也清楚地知道“神理”就是指的神佛的至高原理,它并不是万物内在的自然之理,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二、六朝玄佛合流和刘勰的本体观
刘勰的本体论思想大家都是就《文心雕龙》的《原道》篇来考察的,这当然是不错的。刘勰认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就是“道”,所以凡“天文”、“地文”、“人文”,或者是“形文”、“声文”、“情文”,乃至虎豹等动物之文和草木等植物之文,无不是“道”的体现。对于这个“道”的含义,历来大家争议很多,或谓是儒家之道,或谓是道家之道,或谓是佛家之道,或谓是以儒家为主而兼有其他各家之道,理解是相当分歧的。不过,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并没有明确地讲这个“道”是哪一家的“道”;第二,刘勰在《灭惑论》中非常明确地讲了儒家、道家和佛家在“道”的问题上是可以相通的,原理是一样的,他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不仅佛道和儒道是一致的,而且道家之道和佛家之道也是一致的。“梵言菩提,汉语曰道。”“权教无方,不以道俗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故能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这就把儒家和佛家的道看作是共同的一致的东西,只是因为地域差异,运用不同,而在表现方式上有所差别,一是理论的,一是通俗的。显然,刘勰对儒道和佛道的地位放得都是比较高的。“然至道虽一,歧路生迷。九十六种,俱号为道,听名则邪正莫辨,验法则真伪莫辨。”因为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道”,从表面上看其真伪往往不易分辨,但是一考察其内在原理,则是否非常清楚。他的《灭惑论》是批评道教《三破论》的,当然认为道教之道是邪而非正的,但是他在抨击道教之道时,并没有把它和先秦道家之道混淆起来,而是清楚地对其作了区分。他指出“寻柱史嘉遁,实惟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这就说明刘勰认为道家的虚静无为在本质上是和不过,因为“三世弗纪,慧业靡闻”,故而只能是“导俗之良书,非出世之妙经”。至于道教的“道”则不过是骗人的小道,虽“标名大道,而教甚于俗;举号太上,而法穷下愚。”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勰所说的“道”实际是包含了儒、释、道三家兼通的特点的。
但是,《文心雕龙》中所体现的刘勰的本体论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原道》篇。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论说》篇中评价魏晋玄学中的崇有和贵无两派学说时提出的看法。他说:“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玄学中的这两派都是讲的本体论问题,刘勰对这两派都有所批评,认为他们是“徒锐偏解,莫诣正理”,也就是说,他们各自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并不能达到对宇宙万物本体的全面而正确的理解。他认为玄学的这两派都不如佛学的般若境界更为高明。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的佛教是借助于玄学来传播的,玄佛合一是这个时期思想史发展的重要特点。从刘勰对玄学的有、无之争的观点来看,他所说的佛学中的“般若之绝境”,应该是和僧肇的思想比较接近的。六朝时期般若学属于佛教的大乘空宗,其基本思想是认为一切事物的本性均为空无,故称为空宗。但是般若学在发展过程中,又有所谓“六家七宗”之说,也就是对“空”或“无”的理解有所不同,形成不同的派别。六家是指:本无、心无、即色、识含、幻化、缘会。因为“本无”派内部又有两派“本无”和“本无异”,所以说是七宗。其实,这六家主要是三派:本无、即色、心无,其他的几派均可归入即色派。本无派的主要代表是道安,这是般若学的核心,所以汤用彤先生在《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广而言之,则本无几为般若学之别名。”本无,是从玄学的“以无为本”而来的,但是和玄学思想又是不同的。道安的本无说认为宇宙间一切都是空无的,本来什么也没有,万物的本性也是空无的,不但没有老子的“有生于无”,也没有王弼的“本无末有”,“夫人之所滞,滞在末有,若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认识到一切全是空无,不滞于末有,则方能止息一切思想上的障碍,进入到佛家的“涅槃”、“真如”精神境界。“本无异”宗的代表是竺法琛,他认为无可生有,有生于无,这和老子的观点有点接近,“本无”宗把他看成是“异宗”。“即色”派的代表人物是支道林,他本姓关,名遁,他是当时的清谈家,他的说法是“即色是空,非色灭空”(注:见南朝陈代慧达《肇论疏》所引。),不是物质消灭后才是空,物质本身就是空的。他不承认物质是客观存在。一切物质现象(也就是色)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它生、住、异、灭,瞬息万变,不可能有独立的“自性”,所以是空的。“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2] 一切事物的形相,如青黄等颜色,只是人们感觉到才有,它本身是不存在的。“识含”宗以于法开为代表,认为“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惑识二谛论》),把三界看作是梦幻,而皆起于心识。“幻化”宗的代表是道壹,认为“一切诸法,皆同幻化”(《神二谛论》)。“缘会”宗的代表是于道邃,认为“缘会故有”,“缘散即无”(《中论疏》引),因缘会合就是“有”,因缘散失就是“无”。这三种都是由“即色”宗派生出来的。“心无”宗为与“本无”、“即色”并立之第三派,以支愍度为代表。他的看法是承认客观事物是存在的,“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注:见僧肇《不真空论·不真空论第二》,《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4页。)。慧达《肇论疏》说:“竺法温法师《心无论》云,夫有,有形者也。无,无像者也。有像不可言无。无形不可言有。而经称色无者,但内止其心,不空外色。但内停其心,令不想外色,即色想废矣。”这一派和般若学的空宗思想是不大一致的,所以遭到很多围攻。
般若学的空无义此后又在僧肇和慧远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僧肇有著名的《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收入《肇论》一书中。僧肇是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主要助手,但是他的主要贡献是在佛学理论上。他从当时已经翻译过来的龙树著作中,吸取了其中观学说的精华,在分析六家七宗的得失基础上,把般若空宗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的《不真空论》是意思是“不真”即空,他用龙树《中论》的观点,从“非有非无”的本体论出发,论述了世界的“不真”即“空”的本质。“非有”是说现实世界从根本上说是不存在的,“非无”是说世界从现象上看又不能说是完全不存在的,只是它所存在的是一个假象。“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物不迁论》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绝对地静止不动的,但不是只有静没有动,而是“必求静于诸动”,从变化中去认识不变。汤用彤先生说:“称为《物不迁》者,似乎是专言静的。但所谓不迁者,乃言动静一如之本体。绝对之本体,亦可谓超乎言象之动静之上。即所谓法身不坏。”此“即动即静”之义亦即“即体即用”,“非谓由一不动之本体,而生各色变动之现象。盖本体与万象不可截分。”《般若无知论》则说因为般若无知,所以无所不知。他说:“夫有所知,则有所不知。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因为世界是不真而空的,所以认识世界也不要那些具体的知识,只要有无知之心就可以知道一切。僧肇的本体论是认为无非真无,有非真有,这正好解决了玄学中贵无和崇有两派的“徒锐偏解,莫诣正理”的缺点,也就是刘勰所说的“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的境界。刘勰受龙树思想的影响很深,这点我们将在本文下节中详细论述,而僧肇的思想正是对龙树本体论思想的发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中说的“道”,显然也是包含了佛道在内的。
三、龙树的中道观对刘勰《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折衷”论文学研究方法,是直接受龙树中道观影响的产物。龙树是公元二三世纪时印度的佛学大师,他的《中论》是以偈语的方式来写的一部十分重要的佛学著作,原有500偈,汉译为446偈,分二十七品,为佛教大乘空宗的主要经典。《中论》在中土最早有姚秦时鸠摩罗什翻译的青目注释本,有著名高僧僧睿的序和昙影法师的序。后来有吉藏法师的《中论疏》,对《中论》本身和青目注释都作了详细的疏解。《中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而它的核心是阐明一种观察宇宙事物的方法,也就是所谓“中道观”。这种方法的特点就是要求人们要超越两端,不即不离。一般人理解事物往往只看到事物对立的两个极端,例如生死、有无、来去、善恶等等,因此就容易落入一端,而龙树则要求超越这两个极端,而看到事物不陷于这一端、也不陷于那一端的复杂性。《中论》的宗旨集中表现在它的第一偈中的“八不”:
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
我们平常看待事物常常会落入相对性,有无便有有,有生便有死,有来便有去,有善便有恶,有美便有丑,有上便有下,有高便有矮,……,当我们落于一边的时候,实际上也落到了另一边,强调善的观念时,就有恶的观念存在着,赞扬美的观念时,就有丑的观念存在着。龙树则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复杂多变的因缘所决定的,是没有完全纯粹的东西的。因是指个体本身,缘是指外在的事物和环境,它们都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的,他们的配合也是无穷无尽的。善不是完全都是善,恶也不是完全都是恶。因此,他提出: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不生不灭,是说的事物的存在和非存在问题。事物产生的时候也是它消灭的时候,它消灭的时候也是它产生的时候,随因缘而转化,所以实际上是没有生也没有灭。常和断,说的是时间的永恒和非永恒,不常就是无常,从时间的不断变化来说,事物是没有常性的,不可能是永恒的。事物无常而相续,所以又是无断或不断的。既非永恒又非非永恒。一和异,说的是数量的统一和差别,事物从执常性的角度来看,好像是统一的、独立的个体,实际上它又是不断变化而有差异的,所以是非一的。但是,事物虽然不断变化,却还有它的相续性,所以又是非异的。这就是不一也不异。来和出,说的是时空中的来去运动相,其道理也是一样的。事物的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比如,火是哪里来的?不是从木材来的,也不是从火柴来的,也不是从手来的,也不是从氧气来的,而是诸多因缘聚合的结果。火灭了,它去那里了?是因缘离散的结果。这就使我们想起了苏轼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声的有无也是琴弦和手指因缘聚散的结果,也是不来亦不去。所以正如吉藏所说:“不来来,不去去。”故而龙树得出的结论是:“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寂灭如涅盘。一切实非实,亦实亦非实。非实非非实,是名诸佛法。自知不随他,寂灭无戏论。无异无分别,是则名实相。若法从缘生,不故名实相,不断亦不常。不一亦不异,不常亦不断。”“是故知涅盘,非有亦非无。”总之,他认为事物极端的两个对立面实际是不存在的。他否定了事物的两个极端,认为只有超越了事物的两个极端,善于不即不离,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论,其最特出的地方是要求对任何事物不要有绝对的看法,不能偏于一边,陷入一个极端,要认识到事物的复杂多变,而给以符合实际的解释。刘勰毫无疑问是非常熟悉龙树的《中论》的,他协助僧佑编撰的《出三藏记集》中曾收入僧睿的《中论序》和昙影法师的《中论序》,在《鸠摩罗什传》中也说他曾翻译《中论》等龙树的著作。我认为龙树《中论》中的“中道观”对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刘勰之所以能写出这部伟大的著作,能够提出那么多深刻而有价值的见解,是和他所采取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有直接关系的。他的这种“折衷”论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和儒家、道家、玄学的方法论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受的以龙树《中论》为代表的佛学方法论的影响。刘勰在文学批评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持论非常公允,绝不偏于一端,能够客观地、全面地来看待问题,这可以说是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的。他对当时文学理论批评上一些历来有分歧的争论,都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哪一方面,而是善于吸取对立双方观点中的正确的合理的因素,提出自己比较稳妥的持平之论。譬如,“芙蓉出水”和“错彩镂金”是两种尖锐对立的美学观,刘勰是比较欣赏以自然清新为特征的“芙蓉出水”之美的,但他又不否定以人工雕饰为特征的“错彩镂金”之美的。他主张要在重视人工雕饰的基础上达到自然清新的理想境界。所以在《隐秀》篇中提出文学创作要以“自然会妙”为主,又要辅助以“润色取美”,认为这才是最高的美的境界。在《辨骚》篇中总结汉代对《楚辞》评价的争议时,他也没有偏向于那一边,而是详细地分析了《楚辞》“同于风、雅”的四个方面和“异乎经典”的四个方面,充分肯定了《楚辞》既“取熔经意”又“自铸伟辞”的基本特色。特别明显的是他对当时文学创作中有很大争议的声律、对偶、用典等,都不偏于一端,而能采取比较公允的态度,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很有深度的看法。对于声律,他既不像沈约等人那样,去制订繁琐的声病规则,但也不像钟嵘那样对声律理论全盘加以否定。他在《声律》篇里以探讨声律的美学原理为主,强调声律美的关键是要做到“和”、“韵”之美。对于用典,刘勰既不赞成颜延之、谢庄那样堆砌典故,以至使“文章殆同书钞”,也不赞成钟嵘对诗歌创作用典全盘否定,而是比较客观地在肯定用典的积极作用前提下,要求尽量做到不要诘屈敖牙,而要如同“口出”和自己说的一样。并且提出学识要“博”,运用典故要“约”,特别要注意选择之“精”,还要运用得“核”,也就是说,既要吸取用典的长处,又不能让它影响作品的自然美。在对待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言志”与“缘情”的争论中,他也没有简单地落入哪一边,而是善于把情和志统一起来。他在《明诗》篇中说:“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又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刘勰认为文学的本质不仅表现“志”,也表现“情”,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文学作品就好比一个人,“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学创作既是以“述志为本”的,又是“为情造文”的。刘勰在文学批评方法论上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善于采取“圆通”的见解而不绝对化,能全面而深刻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折衷”论不是调和折中抹稀泥的方法,而是能够根据客观的“势”和“理”,来科学地分析各方面的因素,从而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些都非常突出地体现了刘勰运用“折衷”的方法论所取得的积极效果。他这种善识“大体”,不执一端的文学批评,显然和龙树的“中道观”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
上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文心雕龙》和佛教的关系,但并不是说《文心雕龙》和佛教的关系就只有这些,实际上在其他很多方面还可以看到佛教和《文心雕龙》的联系,譬如大家讲得很多的佛教因明学对他的影响等等。总的说来,我认为应该对刘勰《文心雕龙》和佛学的关系作一个全面的稳妥的考量,用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认识这个问题,这对于《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也许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