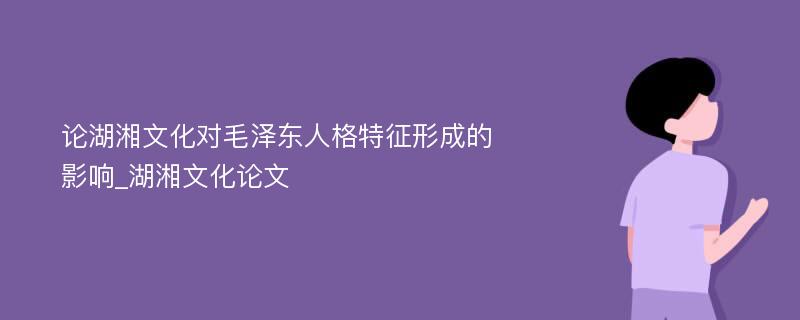
论湖湘文化对毛泽东个性特征形成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性特征论文,文化论文,论湖湘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有其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他既有“壮观的挑战人格,浪漫的反叛欲求,坚定的造反意志,超凡的思维方式”,又有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的质朴情怀;同情弱者,追求平等的侠士风度;讲求实际,崇尚艰辛劳动的务实精神;坚定自信,不畏强暴的伟人气概。毛泽东的这些性格特征的形成,除了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周围的环境影响有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对他的影响。毛泽东的许多个性特征都留存着湖湘文化的历史痕迹。湖湘文化“以禹墨为本,周孔为用”,主张社会变革,反对因循守旧;重视民族气节,崇尚艰辛劳动,提倡独智大醒;强调“民为邦本”,推崇务实精神。我们如果把这些思想内容与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作一类比,就可以从中找到他们内在的契合点,发现毛泽东的个性特征的源泉主要来自于湖湘文化的内在影响,可以说湖湘文化为毛泽东个性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精神养料,正是湖湘文化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才形成了毛泽东不同于众的鲜明个性,也才是他能够在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不朽的历史伟人。
一、湖湘文化的崇尚气节和变革意识是毛泽东挑战人格形成的力量源泉
要了解湖湘文化对毛泽东个性特征形成的影响,首先就必须了解湖湘文化发展的渊源。湖湘文化是集我国古代文化之大成的一种优秀文化,它兴起于湖南大地,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文化传统,而影响则波及全国各地。它的发展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屈原。“屈原瑰丽神奇的浪漫诗篇,庄子奥妙宏伟的哲理散文,深深地激荡和哺育着湖湘文化”。[1]到南宋时期,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轼等人继承了古代湘楚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吸收了理学的思辩方式,在湖南各地聚徒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到清代经过岳麓书院学生王夫之的阐微发幽,旁征博论,使湖湘文化形成了自己完备的思想体系,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文化流派。在这种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之下,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岳麓书院也因此赢得了“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美誉。这座“千年的学府”相继培养出一大批对近代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著名者如地主阶级经世致用派的代表魏源、陶澍。洋务派文化的代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资产阶级唯心派的代表谭嗣同、唐才常、沈荩,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代表杨昌济等。这些近代的湘贤名人,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对于学贯古今、博览群书的毛泽东来说,无疑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他们的功业和伟绩就成了毛泽东立志效仿的楷模,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也就在这种经世致用的文化氛围陶冶下培养起来。
湖湘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崇尚气节和主张变革。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以天下为己任,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爱国诗人屈原不忍见楚国灭亡而怀石投江;南宋胡安国、胡宏、张轼等人面对山河破碎,力肿“抗金御侮”,书写了“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的爱国壮举;王夫之在明末清初曾“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四十余年,著书达百种,共700万言,他书中的话“带着热,吐着火”,所流露的“对民族精爱具有感动后辈中国人,鼓励并召唤他们去行动的力量”。近代的魏源愤于外敌欺凌,民族受辱的现实,发愤编撰了《海国图志》,寻求“以夷制夷”的良方,以求中华民族并雄于西欧诸国,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毅然出洋留学,学成归国后,他热心于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杨昌济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屈原、胡宏、张轼、王夫之、魏源等人是一脉相承,由于杨先生尽力将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渗透到他的教学中去,因此给毛泽东等人以巨大的震动。青年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开始意识到自己肩上所 负的历史使命,思想意识有了新的转变。他与同学好友晤谈时“只及学问文章道德品行和国家天下的大事,从不涉及私人生活问题”。[2]他还仔细研究过谭嗣同的《仁学》,常去“船山学社”听讲座,“王夫之的民族意识特别引起他的注意”。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湖湘文化的启发、熏陶下,勃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激发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因而他能在橘子洲头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强劲呼声,在日记里面写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抒发了他不屈不挠的挑战个性。
如果说湖湘学派的爱国意识和爱国壮举给毛泽东的挑战个性提供了生命的动力,那么湖湘学派的变革意识则给其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社会改革的促进派,屈原虽遭放逐,仍不忘提醒楚怀王改革弊政,亲贤臣,远小人;胡安国面对北宋末年吏治腐败,奸佞弄权的弊端多次向朝廷倡言改革,认为“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张轼更多次向孝宗进言,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革新主张,王夫之、魏源也都是社会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魏源提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正是在这种变革意识的影响、陶冶下,萌发了毛泽东改革现状,追求进步的爱国意向,因此,他特别强调改革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必要性。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我尝虑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也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并认为“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往往是其思想意识、人生信仰的外化表现。毛泽东的挑战个性和反叛欲求正是湖湘文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变革意识驱动外化而成的显著特征。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了毛泽东拯救社会,勇于牺牲的力量源泉,而变革意识又是他坚信社会总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变革中得到进步。因此,毛泽东为了追求社会的进步,总是充满朝气地向各种恶势力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挑战。年少时他反对父亲的家规陋习和刻薄损人的行为;上学后又造学校校规的反,造省长和封建制度的反;成年后开始向整个旧世界开战;建国后几年向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挑战;晚年则发动红卫兵以阶级斗争为纲,打碎了他亲手建造的党和国家新秩序,试图重新塑造出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毛泽东的一生从未满足过现状,他厌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庸、和谐、不争、守成、世故、圆滑等种种心理与现象,他渴望通过挑战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以诗人的浪漫,抒发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以及“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的英雄气概。他的这种勇于探索、大胆革新、热烈追求新生事物的首创精神,正是近代湖湘文化显著特征的又一体现。毛泽东对《离骚》的钟情和重大决策前,多次回湘的举动,正是他想从湖湘文化的氤氲中重获少年时的壮志,吸收更多精神养料的潜意识行为。因为这块桑梓之地曾润育过无数的英雄豪杰,他能从中闻到屈原独吟江畔的概叹,听到湘军万马奔腾的嘶鸣,追忆到谭嗣同慷慨悲歌的豪迈气概,回味到少年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壮举,从而徒增了他迎接挑战的勇气。正如美国史学家罗斯·特里尔所言:毛泽东“极其痛恨一成不变,他认为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动,将来也永远如此。”“他从不自满,总是探索一个充满人性的、具体实在的社会主义”。[3]毛泽东强调的“造反有理”、强调的“武装夺取政权”、强调的“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以及“破旧立新”等革命思想正是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社会变革思想在他意识形态中的深层发展,从而铸造出了他不拘一格的挑战个性和反叛欲求。
二、湖湘文化的“民为邦本”与毛泽东同情弱者、追求平等的侠义个性
“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是湖湘文化中政治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非常留心于经邦治国、济世安民之道。湖湘学派的早期代表胡宏针对宋王朝推行“思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搜刮掠民政策,向统治阶级发出了“养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败亡也”的警告。他告诫统治阶级“治道以恤民为本。而恤民必先锄奸恶,然后善良得安其业;而锄奸恶之道,则以得人为本也。”[4]张轼也认为“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要得“吾民之心”,关键在于“不尽其力,不伤其财”。[5]同样,王夫之在总结明亡的教训后指出“民之视听明威,皆天,皆天之神也,故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而吉凶应之。”[6]他们把民心的好恶、向背看成是统治者政治统治兴衰存亡的根本。因此,王夫之强调人君必须坚持重民思想,贯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举天而属之民”的原则,做到“征天于民,用民与天。”[7]不可任意胡来,这样才能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谭嗣同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的宏愿。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又详尽论述了“民贵君轻”的问题。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则国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8]湖湘文化的这种“民本”思想通过杨昌济的言传身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就曾这样写道:“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也。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就已觉察到了人民群众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正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使毛泽东始终把对农民和农业的态度当成是品评人事的重要标准:少年时代,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在于他能否善待农民;大革命时期,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区别是对待农民和农民运动的看法;土地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他如何对待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抗战时期,一个青年是否是真正的革命派,就看他能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不断呼吁党员要眼睛向下,干部不要脱离群众,知识分子要接受再教育。建国后,他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热潮。他的经济思想也始终贯彻着“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组织人民”这一核心问题。早在根据地建设时期,他就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定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总方针,指出,不顾人民困难,不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顾向群众要粮要款要东西,“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9]毛泽东的这种民本思想外化到他的个性特征之中就往往表现为同情弱者、追求平等的独特形象。“有人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干部与群众之间,他向着群众;在党员与非党员之间,他向着非党员;在男人与妇女之间,他向着妇女;在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他向着小人物”。“他见不得农民受苦(尤其是贫苦农民,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烈军属),对两极分化的急切担忧使他人为地把本应稳定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一下子拉短,接着再人为地把本来设计好需要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在几年内一蹴而就。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头脑发热,实际上也有毛泽东对农民那种炽热情感在作怪,想为农民办个大好事,一步上天堂。”[10]毛泽东一生很少流泪,但是当他听到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他就忍不住要掉下泪来。正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毛泽东往往把自己的着眼点,放在关心群众疾苦方面,他担心贫富不均会使农民重新陷入贫穷受欺的境地,因而孜孜追求于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他渴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平等、富裕、合理的新社会。毛泽东总是告诫党员和干部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三十年代,他就曾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在他已经被神化的晚年,他又一次重复了这句话,只添了三个字:“包括我”。如果说湖湘学派的“民本”思想只是出于对农民同情而萌发出来的一种思想意识,目的只是警告统治阶级善待百姓,不要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那么毛泽东则把这种意识化为了自己具体的行动,作为自己终身施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人的个性特征总是受一定的思想意识所左右,作为伟人的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在路上遇到因女儿生病垂危而失声痛苦的农妇,忍不住涕泪相陪;手拿着警卫战士从农村带回来的又黑又硬的窝窝头,他边嚼边泪水四溢的情感流露,正是同情群众疾苦的心理反映,也正是湖湘文化的“民本”观念在他心灵深处映现而出的外在情感现象。因此,可以说湖湘文化的“民为邦本”思想铸造出了毛泽东同情弱者,追求平等的独特个性
三、湖湘文化的知行观与毛泽东的务实个性
崇尚实学,提倡力行是湖湘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生活于社会动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转型时期,因而他们非常注重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强调“言必征实,义必切理”的社会实学观。早期湖湘学者胡宏最讨厌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强调人的知识主要是来自后天的学习:“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识,习然后能,能然后用。”[11]张轼在继承胡宏知行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知行互发”的思想。他说:“致知力行,互相发也。盖致知以达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人们的认识过程,是知行辨证统一、互相发生作用。互相促进的发展过程。因而他主张“儒者之政,一一务实”。[12]王夫之把湖湘学派的知行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提出了“行先知后”,“即事求理”的著名论断。魏源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夫士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的新思想,阐明了调查访问对于知识分子产生正确认识的重要作用。杨昌济先生对此完全赞同。他认为:“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而力行尤要。”[13]毛泽东生长于湖南,自幼就深受湖湘文化“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想的影响。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就特别重视“能见之于事实”的“有用之学”。毛泽东常对同学说,读书,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而且还要会读“无字之书”。1917年7月中旬,他邀约萧子升和萧蔚然进行了一次走向社会的游学活动。他们沿途调查民情,拜访方丈,参观佛殿,常常风餐露宿,历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近千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大革命时期,他在借鉴湖湘文化“知行观”的基础上,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为了了解社会,他经常深入农村、城镇、工矿,考察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得出了“要消灭旧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吃人制度’,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农民群众结成联盟‘进行革命’”的结论,使中国走上了“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这些著作中都贯彻着一条根本的红线——实事求是。毛泽东把他青少年时代就相当熟悉并身体力行的这一古代格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进行改铸,使“实事求是”这一流传了2000多年的古代命题,变成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简明扼要的中国化的科学概括和通俗表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1937年,毛泽东在创作《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哲学著作时,就曾特地托徐特立从长沙找齐他所缺的《船山遗书》,由此可以证明毛泽东对船山哲学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实践论》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知行统一观”。这就更清楚地证明,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特别是对船山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务实个性正是他善于吸收前人的实践经验的结晶。当然这种继承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加以提炼和补充,从而形成了毛泽东具有独特时代特性的知行观。正如著名学者贺麟所言:毛泽东“不象朱熹那样把知行分为二截,也不象王阳明那样在当下的直觉里或内心的良知里去求知行合一。……他不象孙中山那样……去做知行孰难孰易的比较,他不象朱子、阳明两人皆同陷于注重内心修养而提出知先行后的说法。”毛泽东“扬弃了、发展了王船山忠爱祖国文化、继承和创造性地发扬中国传统哲学而形成的朴素唯物主义,也超出孙中山的革命民主思想。”[14]毛泽东对湖湘学派知行观创造性的改铸和运用,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务实精神。正是这种务实精神,使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不盲目照搬照抄,记条条,背本本,死死记住某些词句,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而是灌入中国的传统文化、融汇贯通,把马克思主义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因而它所起到的作用自然要比那些言必称希腊、罗马的“党八股”大得多,这就是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获得胜利的真谛。
作为领袖和伟人,毛泽东的个性不是单色调的,而是多元性的。他既是一个学者,博古通今,又象一位农民,平易朴实;他做事严肃认真,令人生畏,却又十分幽默风趣、和蔼可亲;他城府很深,精明、寡言,也很坦率、外露,让人觉得简单得一目了然;他很谦虚豁达,又很高傲、敏感;他很浪漫,又很务实;他很细致谨严、明察秋毫,又很粗犷洒脱,不修边幅;他很乐观,对前途充满信心,又经常忧时忧患;他既有成就伟业的耐心,又有当机立断,决不丧失机会的魄力”他渴望挑战,不守陈规,提倡造反,又同情弱者。毛泽东这种复杂、多重的个性特征,不可能只是一种因素影响的结果,而应该是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聚合体。但在这一聚合体中并不是每个因素都占有同样的比重。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湖南这块人杰地灵的沃土之中,自幼承受着湖湘文化的思想影响。而这一时期正是一个人个性特征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定型期。如果说家庭环境和后天的社会实践推动了毛泽东思维活动的形成和发展,那么湖湘文化则奠定了毛泽东个性特征形成的思想基础,在众多影响个性特征的因素中,它的作用应该是主要的。
收稿日期:1996-10-03
注释:
[1]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89页
[2]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51年11月版第72页
[3]〔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重版第255页
[4]《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8页
[5]《道学三、张轼传》《宋史》三十六 中华书局第12771页
[6][7]参见陈远宁、王兴国《王船山的重民思想》《求索》1991年第5期
[8]《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56页
[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894页
[10]晓峰、明军主编《毛泽东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76、277页
[11]转引自《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12]《答施蕲州》《张南轩先生文集》第21页
[13]《杨昌济文集》第365页
[14]贺麟《关于知行合一问题一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求索》1985年第1期
标签:湖湘文化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实践论论文; 王夫之论文; 知行论文; 杨昌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