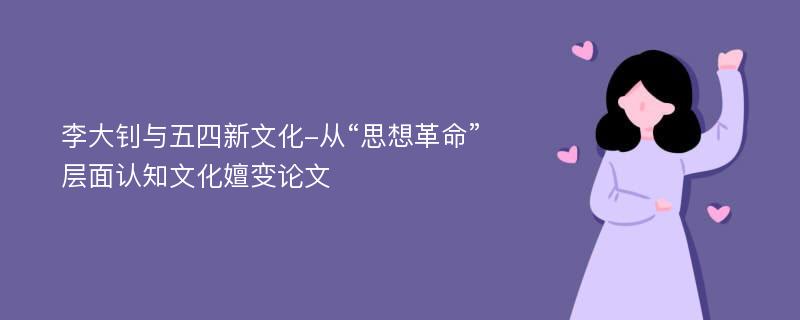
李大钊与五四新文化
——从“思想革命”层面认知文化嬗变
□侯且岸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 要: 坚持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以“思想革命”为认知起点,全面梳理李大钊独特的文化思想及其实践。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改造、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探究、对新旧文化联系的深刻阐释、对新式媒体《每周评论》的创造性应用,以及对马克思学说的独立思辨,都证明了思想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凸显了五四新文化的本质。
关键词: 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传统文化;李大钊
引子:五四新文化之本质——“思想革命”
2019 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 周年,也是李大钊诞辰130 周年。在此特殊的时刻,回顾李大钊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联系,梳理李大钊独特的文化思想及其实践,反思五四新文化的本质,对于新时代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仅有着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而且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猪喘气病又称猪霉形体肺炎,是由肺炎霉形体(支原体)引起的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各种年龄、性别、品种的猪都可发生。病猪表现为咳嗽、气喘、发病率高死亡率低,主要影响猪的生长速度。肺是主要的病变器官。急性病例以肺水肿和肺气肿为主;亚急性慢性病例常见肺部“虾肉”样实变。发病猪生长缓慢,饲料利用率低,增加饲养成本。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周作人对五四新文化内涵的认知和评价是我们特别需要给予重视的。早在1919 年3 月,他就曾撰写《思想革命》一文,深入剖析“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关系。从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时人所热衷的“文学革命”颇有微词,不满隐藏于其中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写道:“近年来文学革命的运动渐见功效,除了几个讲‘纲常名教’的经学家,同做‘鸳鸯瓦冷’的诗余家以外,颇有人认为正当,在杂志及报章上面,常常看见用白话做的文章,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可乐观的事。但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1]5他又发问:“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痛发时,仍旧胡说乱道的写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好比‘君师主义’的人,穿上洋服,挂上维新的招牌,难道就能说实行民主政治?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1]6针对上述问题,他断言:“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倘若换汤不换药,单将白话换出古文,那便如上海书店的译《白话论语》,还不如不做的好。因为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1]7-8
周作人非常看重自己这些在五四知识精英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以至于他在回忆录中还强调:这可是“由衷之言”,“‘言志’的东西”,“仿佛和那时正出风头的‘文学革命’即是文字改革故意立异,实在乃是补足它所缺少的一方面罢了”,是“‘划伦常’的一种变相”[2]。透过周先生的“强调”,今天我们需要思索的问题则在于:五四亲历者的上述认知为何没有能转化为后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价的基本取向?
海内外享有盛名的五四研究专家周策纵在全面分析了“对五四运动的各种阐释和评价”① 周策纵对各式各样的解释、各派的分歧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现代史上很难发现比五四运动更为复杂的事件。 以后,做出了自己的“‘五四’本质试析”。他指出,“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本质上,它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所以说它是思想革命,是因为它是以思想的变革是实现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前提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改革,同时还因为它是由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这种思想革命又进而促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3]491。
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民族的生存和独立。“为了实现这一点,‘五四’时期的改革者与前几代改革者不同的作法是,提倡中国在所有重要的文化领域,包括从文学、哲学、伦理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和西方化。他们从批判旧传统和以西方文明重估中国人过去的态度和实践开始,他们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科学和民主。因此,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挽救中国’”[3]491。
我以为,周先生的这些结论性分析完全符合五四运动真实的实际。在五四精英的设想中,就是要理性地看待人类文明,以西方文明为参照,通过思想的变革、观念的转变,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民族的思想力,再造文明,再造中华精神文明[4]。
相比较而言,多年以来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造成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意义的认知显然是存有缺陷的。必须承认,我们的研究还没有能把五四运动的本质意义深刻揭示出来,没有能把“思想革命”和“社会现代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也没有能真正搞清楚“思想运动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基本关系。那么,在我们的视野中,五四“思想革命”的意义应当表现在哪里呢?它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暴力革命”应当有何区别呢?其相互之间又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我们现今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缅怀五四精神所必须进行反思的问题[4]。
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毕竟是短暂的、过渡性的,联系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思想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1932 年,胡适曾发表《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一文,提出“建设时期的思想革命”问题,强调“建设时期中最根本的需要是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则一切建设皆无从谈起”[5]。他的这一思想已被中国现代历史所验证,确实发人深省。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改造
五四“思想革命”的意蕴首先集中体现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这种批判的误读,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想象中的“打倒孔家店”② 此口号系胡适所提出,相关分析参见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 。
相比较而言,李大钊的批判很有代表性,他的批判思想是在日本留学时逐步形成的,首先着眼于政治文化批判。
我们知道,“民彝”思想是李大钊政治哲学的核心部分。通过对“民彝”思想的分析,可以展现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改造,揭示其政治哲学的深刻内涵。1916 年5 月,李大钊即将结束日本留学之际,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全面阐释了他的“民彝”思想。
建国以来,中国农药工业经过艰苦拼搏,开拓进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了初创、调整、发展三个阶段,走过了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取得了辉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改制、改革,不断创新,经济实力增长迅速,行业内不断涌现出新经验、新成果。尤其是近二十年,中国农药工业突飞猛进,取得持续长足的进步,已形成包括原药生产、制剂加工、科研创新开发和原料中间体配套的较为完整的农用化学品工业体系,为保证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和国家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自VR技术运用于新闻生产与传播以来,将VR技术更好地运用于新闻生产与传播中,对新闻报道实现最大强度的创新,一直是许多新闻工作者奋斗的目标。为不断更新观众所能接受的新闻报道形式,使得观众在VR新闻中享有虚拟技术带来的视觉冲击。发挥VR技术在新闻生产与传播中的作用,使得虚拟现实技术趋于成熟,让其在众多自媒体发展的阶段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时代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科技发展带来更多的新产品与相应的专业人员。
尽管如此,随着巴黎和会的进展,李大钊也在观察着黎明会方面的变化,尤其是“新人会一派的青年”的加入,以及他的老师、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对黎明会的批评。五四之后的两个月中(从5 月26 日-7 月20 日),他在《每周评论》连续发表了近20篇短评,分析黎明运动的发展变化。同时,也直率地批评了福田德三对“侵略主义”的暧昧态度。在7月13日发表的《忠告黎明会》一文中,他写道,“日本的黎明运动,总算是一线曙光的影子。我们对于他们,很有希望。但是看了福田博士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到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怪不得堺利彦一辈主撰的《新社会》,老早就劝黎明会中真正的黎明分子,先要在黎明会中作一回黎明运动”[27]。
相比较严复的认识,李大钊的分析别开生面,更趋理性化、理论化。李大钊很熟悉严复的著述和译作,在《民彝与政治》中,他直接引用过严复的一些观点,但他不同意仅将“民彝”置于“道德”层面的看法。他的系统论述实际上是由此展开的。李大钊同样从“民”之观念切入,但他着力于批判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改造,进而发出近代启蒙的最强音——尊重“民彝”,赋予“民”之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李大钊这样解释“民彝”:“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舜,好是懿德。’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於至善而止焉。爰取斯义,锡名民彝,以颜本志。”[7]267
在这个教育资源丰盛的时代里,我们经常会讨论什么样的父母才是合格的父母。站在父母的角度,或许是这些:孩子被人夸奖懂事有教养;有体面的一技之长;长大后事业有成等等……但放眼整个童年,站在孩子的角度,到底什么样的父母才是孩子认为最好的父母呢?
慈溪市国土资源局与环保和卫计局联合运用“工匠精神”夯实“三大国策”特色品牌,形成以政府资源为基础,以部门资源为主导,以社会资源为补充的资源投入和推进机制,积极整合资源,创新拓宽思路,改变国土资源“一家管大家用”的格局,通过建立“四众”平台——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汇众智、汇众力、汇众能、汇众资,以多方协同创新普法宣传新机制。开创品牌宣传新亮点、新模式,融入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团市委和FM106.4慈溪广播电台的力量,共同负责筹划2016和2017年度的国策大型活动。通过线上和线下两大宣传环节同步推出,力求达到宣传面积最大化。
他又说:“明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然则民彝者,悬于智照则为形上之道,应于事物则为形下之器,虚之则为心理之澄,实之则为之逻辑之用也。”[7]269
这些都是在讲“民彝”的性质。那么,“民彝”具有哪些作用呢?在李大钊看来,“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民彝者,民宪之基础”;“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缚民彝”[7]268,270,277。
在李大钊心目中,“民彝”不仅是不可剥夺的,而且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是区别近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根本之所在,是宪政的基础。又因为它是一种民之固有、与生俱来的东西,它所产生的创造力不应受到束缚。
如果我们将“民彝”这样一个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政治哲学概念放到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下解读的话,可以看出,李大钊给这个晦涩、古老的概念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其中最根本的有两点:“民彝”是民之意志的体现,“民彝”是民之权利的象征。这种意志和权利的统一是民所固有的“秉彝”。而以“彝”释“民”则更表示民的神圣。因为“彝”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表示法度、权威,只有最具权威性的东西才能够成为“吾民衡量事理之器”,成为宪政的基础和捍卫共和的思想武器。
1917年1月,李大钊在《甲寅》日刊发表《孔子与宪法》一文,又一次明确使用了“民彝”这一政治哲学概念。这次,他抨击“天坛草案”中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规定,斥责它为“束制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自此,李大钊在以后的文章中没有再使用过“民彝”。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民彝”思想和追求。随着整个世界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中国民主革命的深入,李大钊开始使用新的政治哲学概念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不过,李大钊要首先甄别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概念。李大钊一直十分谨慎地对待源于西方的民主概念。他对民主概念做过研究,但他一般不轻易或者随意使用这一特定概念。“Democracy 这个字最不容易翻译。由政治上解释他,可以说为一种制度。而由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去观察,他实在是近世纪的趋势,现世界的潮流,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无一不是Democracy 底表现。这名词实足以代表时代精神”[8]。
为昌明“民彝”,李大钊疾呼要讲求“为我”“有我”,树立自主意识、自我权威,从而冲破专制主义的束缚。他把实现自由看成是一种权利,失却了自由,必然会失去权利。“失却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缺乏自主意识、“尽丧其为我”的国民“尊重史乘、崇奉圣哲之心既笃,依赖之性遂成于不知不识之间”。那些“忧乱思治之切者,骇汗奔呼,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因而使得“神奸悍暴之夫,窥见国民心理之弱,乃以崛起草茅,作威作福,亦遂蒙马虎皮”。袁世凯之所以得逞,实是国民“蔑却自我之心理有以成之耳”[7]278。
李大钊尤其重视思想自由,他效依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文章中大量引述经严复翻译的密尔的理论,强调“意念自由,既为生民之秉彝”。他还认为,“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9]404。他甚至表示,“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李大钊很少使用绝对这样的字眼,这里是一个例外,足见他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宪法与思想自由》是李大钊早期著作中最富激进色彩的文章之一。在此文中,他把自由视如生命,认为“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他疾呼,“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9]401。
李大钊把专制主义政治的腐败归因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历史传统的积储。在传统的束缚之下,国民只知“膜拜释、耶、孔子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使命”,“风经诂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7]274。尽管中国历史不乏值得夸耀于世的遗迹,但如果将历史传统“正若天经地义,莫或敢违”,“终以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下知,安之若命,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义必取于诗、礼、春秋”,那就必然使得“豪强者出,乘时崛兴,取之以盗术,胁之以淫威,绳之以往圣前贤之经训,迟之以宗国先君之制度。锢蔽其聪明,夭阏其思想,销沉其志气,桎梏其灵能,示以株守之途,绝其迈进之路,而吾之群遂以陵替”[7]276。因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历史就是乡愿与大盗窃国的历史,“学以造乡愿,政以畜大盗,大盗与乡愿交为狼狈,深为盘结,而民命且不堪矣”[7]276。这就是袁世凯得以窃国的根本原因。
有必要指出,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有其独到之处。然而他并没有感情义气用事,不加分析地抨击传统,即使对于孔子亦是如此。他认为:“圣人之权威于中国最大者,厥为孔子。以孔子为吾国过去一伟人而敬之,吾从亦不让尊崇孔教之诸公。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奉其自我以贡献于孔子偶象前,使其自我为孔子之我不可也。”[9]403我们“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0]。
李大钊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反思与批判特别集中在对“英雄主义”和“人治”的分析。如果说西方民主政治传统的特点是重法制的话,那么中国专制政治传统的特点就是重人治(英雄政治、贤人政治)。这是专制主义政治的核心,李大钊的反思始终围绕着这个核心,他从历史观的角度入手深入批判了英雄史观。他对近代西方思想家的英雄史观作了分析,认为英格兰史学家加莱罗(Carlyle)的英雄论“为专制政治产孕之思想,今已无一顾值”;美国文学家耶马逊(Emerson)的理论“终以神秘主义为据,以英雄政治为归”,“亦病未能取”。只有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Tolstoy)之说“精辟绝伦,足为吾人之捧喝矣”。因托氏主张“英雄之势力,初无是物。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7]279。李大钊反对英雄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英雄,而是在于“杀迷信人治之根性”,“此性不除,终难以适用立宪政治于美满之境”。他还认识到,“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7]281-282。
针对这种非理性认识,李大钊坚定地表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15]431
二、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探究
五四“思想革命”所涉及的重要文化命题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严复首先把向西方学习、开启民智的时代命题提出来,并认为这才真正是中国的“富强之本”[11]。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李大钊承严复之余绪,开启了培育新文明之新理路。从历史过程着眼,应特别重视他在两个时期的思想,即留日时期、北京大学时期。就著作而言,应认真研究《民彝与政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新旧思潮之激战》《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其中,《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可以视为中国版的新文明论(可与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之《文明论概略》相媲美)。其主要特点在于:深刻反思东西两大文明,深入剖析两大文明之特点,指出培育新文明的前提是自主地“迎受”西方新文明。要享“动的文明”之便利,启“静的文明”之蒙昧,努力使固有之文明“变形易质”,实现西方文明的中国化(这里当然包括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思)。
易非这样想着时,就不由自主起来了,反正冷,反正睡不着,不如起来活动一下,反而会暖和些。可当她穿好衣服时,她就毫不犹豫地向着青梅居的方向去了,一刻也不曾犹豫,仿佛她起来就是为了到那栋房子里去。
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推出《调和誊言》的同时,以《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为题,辩证地分析了文化上的“异”与“和”(和解),在文化认识方面开始摆脱简单化和绝对化,步入理性化。李大钊表示:“物质生活,今日万不能屏绝勿用。则吾人之所以除此矛盾者,亦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12]314李大钊特别指出:由静的生活适于动的生活,根本改变其世界观,“其事乃至难,从而所需的努力亦至大,吾人不可不以强毅之气力赴之”[12]314。
在东西文化的对比中,李大钊承认西洋物质文明的优越,说现代人能够“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12]313。他认识到西洋动的文明的优越之处从根本上源于科学。因此,他自觉高扬科学精神之大旗,要求有志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此种技艺与产业,足致吾人之日常生活与实验之科学相接近。如斯行之不息,科学之演试必能日臻于纯熟,科学之精神必能沦浃于灵智。此种精神,即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12]315。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李大钊抨击了时人由于排外主义作祟,而对现代西洋文化存在的蒙昧无知。他惊呼:“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12]317他“希望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12]317。
李大钊在这里所强调的“迎受”一词,揭示出一条重要的认知理路,即对西方文明要具有主动审视的态度,而绝不能盲从。力寻西方文明之长,以补中华文明之短。从近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来看,可谓切中要害的自信之言。这也是五四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13]。
在1919 年6 月15 日的信中,李大钊这样写道,“此次敝国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反对侵略主义,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公正的国民绝无丝毫的恶意。此点愿贵国识者赐以谅解。惟不幸而因为两国外交纷争问题表现之,诚为遗憾千万”。“我等日日祷望黑暗的东方发现曙光,故亦日日祷望军阀的日本变为平民的日本,侵略的日本变为平和的日本,黑暗的日本变为黎明的日本。在黎明的曙光中,两国青年可以握手提携,改造东亚,改造世界”[25]。
李大钊特别以印度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为例,证明“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他还明确表示:“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负有至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的生面。”[12]312这里的“变形易质”具有深刻的含义,可以说含有融合东西文化特点,创造中国特色新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贡献之义。
出于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李大钊预言,在这个过程中,“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12]313。但前提是,“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12]313① 我注意到,李大钊在这里所使用的论据来自中国留美学生会。 。
三、对新旧文化联系的深刻阐释
五四时期的文化讨论中,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很多人机械地把新与旧截然对立起来,割断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后者,将其彻底抛弃[14]。
应该说,李大钊这些系统的认识有着重要思想价值,“杀迷信人治之根性”既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问题,又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历史问题。
在李大钊的现实理想中,他憧憬,“国家莫大之福,莫若以新势力承继旧势力;而莫大之害,则必为以新势力攻倒旧势力”。如果是“非铲除旧势力也,乃新势力之自杀耳”[16]。
当时,与李大钊的上述观点引为同调的人是有的,但从思想深度和方法论而言,却是没有超过他的。处在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时期,尤其是伴随着各种外来思潮的大量输入,如何正视新与旧的存在,的确困扰着很多人,而最能激励人心的恐怕就是要彻底“推翻旧习惯旧思想”。当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① 参见《对蒋梦麟〈何谓新思想〉一文的附志》,《东方杂志》17卷2号。 。难能可贵的是,与普遍流行的看法不同,李大钊并没有简单化地认识问题、认识文化。他把新与旧看成是一个不可脱节、相互作用的整体,力主两者“并存同进”,以理性的态度审视新与旧。从整体文化意义上讲,他所阐释的确是一种科学的、具有包容性的、合乎思维逻辑的、建设性的认知理路。我们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思索,肯定会将历史(传统)与现实更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全力避免堕入武断的思维歧途,形成僵化的思维定势。但令人遗憾的是,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人为造成的悲剧,大致都根植于对新与旧的扭曲认识,留给后人惨痛的历史教训[13]。
深入探究新与旧的关系,自然离不开对两者基本性质的规定。李大钊告诫人们,我们“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17]38。因为“隶于新者未必无旧,隶于旧者亦未必无新也”。谈到区别新与旧的基本标准,李大钊说:“年龄、派别,举不足为区别新旧之准也。然则新旧之分,究将奚准?故黄远生有言:‘新旧异同,其要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春之叶,非其本源。本源何在?在其思想。’此殆可称为探本之论矣。”[17]38
显然,如果将“思想”作为划分新旧的基本标准的话,也就注入了理性的成分,划定了认知范围,触及到问题的本源状态,从而为进一步探究、规定新与旧的性质和关系提供了特殊的逻辑理路[18]。所以李大钊进而分析道,“然即人之思想而察之,有徒务进步而不稍顾秩序与安固者乎?有徒守秩序与安固而不求进步者乎?盖无有也。为其进步即行于秩序安固之中,秩序与安固亦惟进步而始能保也”[17]38-39。其实基于此理,应当明白:“世所称为新者,必其所企关于进步者较多之人也。世所目为旧者,必其所企关于秩序与安固者较多之人也。苟此解为不谬,则知此二种人但有量之殊,安有质之异?此其相较,正与进步与秩序、安固之为同质异量者相等。精确言之,新云旧云,皆非绝对。”[17]39据此,李大钊批评时人惯常的非理智作法,“何今之人口讲指画者,动曰某派也新,某派也旧,某人也新,某人也旧,似其间有绝明之界域,俨若鸿沟者然。别白泰纷,争哄斯烈,驯致无人能自逃于门户水火之外。相崎相峙,相攻相搏,而不悟其所秉持之质性本无绝异,且全相同。推原其故,殆皆不明新旧性质之咎也”[17]39。
毫无疑问,新与旧并存必然会引起矛盾,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甚至矛盾还很可能会激化[14]。李大钊并没有忽视这个问题,他把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归结为“矛盾生活”“新旧不调和的生活”。“此新旧衍嬗之交,一切之生活现象,陈于吾侪之间者,无不呈矛盾之观”[19]415。其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而且“由于累代之专制政治戕贼民性泰甚,以成此不自然之状态,并以助长好同恶异之根性,致保守势力过坚,但知拒而不知迎,但知避而不知引。重以吾国历史之悠久,有吾民族固有之文明,逮夫近代西方文明汹涌东渐,一方迫之愈急,一方拒之愈甚,遂现此不调和之象焉”[19]417。
那么,新与旧究竟应当如何相处呢?它们的常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在李大钊的思想世界里,两者并存之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调和”,新旧调和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的趋势。不过,这种“调和”有其特定之内涵,有其法则[14]。“调和者,乃思想对思想之事,非个人对个人之事。个人与个人,意见情感,稍有龃龉,可由当事者以外之第三者出而调停之,和解之。思想与思想,若有冲突,则非任诸思想之自为调和不可。盖其冲突之际,不必有人与人之交涉,即同一人焉,其思想亦有时呈新旧交战之态也。然则欲二种之思想,相安而不相排,相容而不相攻,端赖个人于新旧思想接触之际,自宏其有容之性,节制之德,不专己以排人,不挟同以强异,斯新旧二者,在个人能于其思想得相当之分以相安,在社会即能成为势力而获相当之分以自处,而冲突轧轹之象可免,分崩决裂之祸无虞矣”[17]39。
显而易见,李大钊在这里所倾力阐明的实际上是思想上的容忍,也只有容忍,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矛盾的激化。可以说,他所揭示出的道理,正是中国新文化建设最需要具备的基本精神[14]。
根据李大钊的认知思路,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起点就是“民彝”,需要给“民彝”重新定义,并且要努力超越传统伦理的窠臼,注入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内涵。
当然不可否认,实现新旧调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但它又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过程。为此,需要从以下诸方面着手努力。第一,要真调和,要两者的调和,既要“有容”,又要“有抗”[14]。李大钊说:“凡能达于调和之境者,溯厥由来,成于自律者半,他律者亦半,而第三者之调停不与焉。自居于一势力者能确遵调和之理,而深自抑制,以涵纳其他之势力,此自律之说也,是曰有容。自居于一势力者,确认其对待之势力为不能泯,而此对待之势力,亦确足与之相抵,遂不得不出于调和之一途,此他律之说也,是曰有抗。分此皆虚伪之调和,非真实之调和,支节之调和,非根本之调和,绝无成功之希望者也。”[17]40
第二,要努力发挥创造力,去发展新的生活,包容覆载旧的生活,使其“不妨害文明的进步”[14]。李大钊认为,“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然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20]289。而反思中国当时的文化现状,特别需要“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20]289。中国应当“急起直追,逐宇宙的文化前进”。而“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碍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受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20]291-292
我们必须认识到,新文化的创造特别需要理性的支持。李大钊提出,在新旧之间要有充分的“道理的对抗”。现实之中国,“新的旧的,都是死气沉沉。偶有一二稍微激昂的议论、稍稍新颖的道理,因为糜有旗鼓相当的对立,也是单调糜有精彩,比人家那如火如荼的新潮,那风起潮涌的新人运动,尚不知相差几千万里?那些旧人见了,尚且鬼鬼祟祟,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他们总不会堂皇正大的立在道理上来和新的对抗。在政治上相见,就想引政治以外的势力,在学术上相遇,就想引学术以外的势力。我尝追究这个原因,知道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势力,摧除对面的存立。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15]432
文化要获得全面发展,就必须在理念上倡导和发扬“和而不同”的精神。李大钊在他的文章中着重以日本近代思想界的变化为例,说明种种思想共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强调:它们虽然有着“公同进行的方向”,“可是各人取那条路,还是各人的自由,不必从同,且不能从同,不可从同”① 参见《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李大钊在这里同时分析日本文化存在的同样问题,涉及“黎明会”与“黑龙会”。 。
李大钊对新旧文化关系的深刻诠释构成了他特有的文化观。这一观念回应了当时中日两国思想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他主张理性认知文化矛盾,立主新旧“并存同进”,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范式② “新”的古义十分简单。据《说文解字》,“新,取木也”,从斤,特指砍伐。又据《段玉裁注》,引申为“凡始基之称”。这同另一个字很相像,即“变”。“变”晚出,其义为“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时间概念,引申为“更始”),有“除旧更新”的说法。归根到底,都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关,标志着政权的更替。然而问题就出在“始基”上,建立“新天下”不言自明。与“新”相对的字一般认为是“旧”。在《说文解字》中,义为“鸱鸺”,即猫头鹰。取其声音为“故音”(过去的声音)。此鸟怪,其音预示“不祥之兆”。民间有“新桃旧符,驱邪扶正”的说法。由此,我们就明白了“新”与“旧”之对立的由来。“新”的概念对当下的人颇具诱惑力,人们对“新”充满无限的期待和美好的憧憬,甚至是梦想,附着价值判断。事实上,“新”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旧”亦如此),对它不应该赋予强烈的功利目的,它更不能成为正确、先进和创造的标志。 。他特别倡导理性的调和,坚持原则,不失最大限度的包容,促进不同文化的融合,这就为正确解决文化转变中的继承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方法论,乃至认识论。李大钊的这一文化理论创造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思想印记,启迪后人,从中汲取历史的教益。
四、对新式媒体《每周评论》的创造性应用
五四“思想革命”不仅激发了深刻的思想反思,而且也引发了思想工具的变革——新媒体的创建。1923 年,胡适在通信中谈到现代报刊的作用。他高度评价了白话刊物《新青年》③ 该杂志为月刊,自1915年9月15 日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 的作用。他认为,“一份刊物代表着一个时代”,也可以说,“创造了一个新时代”④ 1923年10月,胡适《给〈努力周刊〉编辑部的信》说:“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 。今天,我们在深入了解五四时代时,亦想到了一份具有更为普及功能的报纸,它同样“代表着一个时代”——《每周评论》① 周报,或称星期日报。美国最早的周报诞生于1796年,到1890年,已经有250多家,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每周评论》创刊于北京,学界同仁轮流主编,每星期日出版,四开一张,分四版,采取报纸的形式,由每周评论社出版发行。参加的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钱玄同、刘复、马裕藻、沈尹默等)交5 块大洋(银元)做开办经费。《每周评论》发行所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编辑所则在景山东北京大学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它与《新青年》相互补充,成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报刊之一。
在北大语料库共找到用例29条,“买不了”之后所带的宾语有:二斤、一双袜子、菜、骨灰盒、一只鸡、一件衬衫、什么、生命、衣服、多少粮食、三斤好刀鱼、什么东西、人情、这个钱、我的心、那么多东西、书、东西、四瓶香槟酒、卵子大的天,有些还进入了框式结构“连……都……”中。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召集《每周评论》创刊会议。他提出,要创办一份“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周刊(《新青年》为月刊,以长篇文章居多)。《每周评论》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在保守派眼中的“过激派”)人物之手,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21]。
陈独秀撰写的《发刊词》说:“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他认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第一个好人”,因为他主张“平等自由”[22】。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每周评论》的政治取向,与苏俄基本上没有关系。
《每周评论》创办后,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笔名明明,发表了40 多篇文章。其中短评论居多,长篇文章有《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阶级竞争与互助》等。从《每周评论》第2 号开始,就有了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评论,以及关于美国提议组织“国际联合会”的讨论。这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干预前,两组血压水平差异性不大,P>0.05,干预后,观察组舒张压、收缩压分别为(78.92±2.88)mm Hg、(121.76±3.29)mm Hg,均低于对照组,P<0.05,具体数据如表二所列:
尤其是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后,《每周评论》增加了有关会议的报道和评论。李大钊就在会议期间专门写了《国民仲裁》《平民独裁政治》《过激乎?过堕乎?》《放弃特殊地位》《秘密外交》《普通选举》《光明与黑暗》《强国主义》《小国主义》等国际评论,表明了自己独特的国际政治见解,阐明了对形势发展的判断。这在舆论封闭的中国真乃破天荒之举。
1919年5月11日(周日),《每周评论》第21号发表了《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详细报道了“五四事件”的由来② 周作人在回忆录中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在谈到《每周评论》的作用时写道,“‘五四’的情形因为我不在北京,不能知道;但是一个月之后,遇见‘六三’事件,我却是‘亲眼目睹’的,有些事情便在《每周评论》上反映出来”。“警察对守常(李大钊)说道:‘你们的评论不知怎么总是不正派。有些文章看不出毛病来,实际上全是要不得’”(《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8、362页)。 。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四日事件以先的酝酿”“四日上午的学生代表会(五项决定)”“四日的示威事件(下午一时半开始)”“曹章陆方面的所见所闻”“被捕学生的经过”“杀气腾腾的国耻纪念日(政府禁止国民大会)”“各团体的活动”“亲日主战派的眼中钉(查办蔡元培校长,黑暗势力和教育界全体开战的起首)”。这为后人深入了解“五四事件”的全貌,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史料。
6 月11 日,陈独秀与高一涵等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巡警和便衣侦探逮捕,一时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与民愤。为了声援陈独秀,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0号发表短评《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回应读者来信提出的问题。“常常给我们点光明”的“只眼”(陈独秀的笔名),“好久不见了”,还我独秀,给我光明。一时传为佳话。
《每周评论》第12 号从《晨报》转载了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这是李大钊关于五四新文化的代表作,影响深远。他在文章中阐明了自己的文化调和立场,确信新旧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15]431。
6 月28 日,巴黎和会的签约仪式举行。在此之前,国内各地民众纷纷组团赴京请愿,敦促政府拒绝签字,但到24 日,政府仍指示中国代表团准备签字。李大钊在尚不知道最终结果(中国代表拒绝出席签约仪式)的情况下,于29日在《每周评论》第28号上连发四篇国际评论:《不要再说吉祥话》《新华门前的血泪》《哭的笑的》《威先生感慨何如?》,表达了对“国际正义”的失望,告诫人民勿忘国耻。
1919 年1 月26 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6号同时发表六篇评论,即《政客》《国民仲裁》《平民独裁政治》《过激乎?过堕乎?》《乡愿与大盗》《放弃特殊地位》。在这些犀利的政治评论中,他明确而深刻地指出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弱点和中国政治的弊端所在,富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每周评论》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还表现为在该刊进行过两次关乎中华民族发展方向和历史命运的重要讨论。一次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一次是有关“东洋兄弟携手创造新文明”的讨论。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号,终至第37 号。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第28 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31 号)、《三论问题与主义》(第36 号)、《四论问题与主义》(第37 号),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第35号),知非① 即蓝公武(1887-1957),著名教育家、翻译家。 的《问题与主义》。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胡适坚持,应“多研究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李大钊则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回应胡适。胡适说,我本来想做此文,“现在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吧”[23]。8 月24 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
胡适笃信实验主义,对当时社会所流行的“空谈主义”一直存有一种特有的、极度的反感,再加上北洋皖系政客们的参与② 例如当时安福系主要成员、众议院议长王揖唐(1877-1948),1948年9月,以“汉奸罪”被处决。 ,就使得这种反感更为强烈,从而直接导致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胡适也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意思,所以特别说明,请读者们不要误会他的意思,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
从学理讨论的角度着眼,胡适非常重视李大钊和知非的意见,将他们视为挚友。在讨论中,李大钊坦然承认,“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向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者注)后发生的觉悟”[24]51。
通过与胡适的讨论,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24]51。
胡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梁金泉,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谢伯阳,湖南省政协党组成员、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会长葛洪元,解放军总装备部通保局原局长、解放军少将杨小平,以及胡耀邦同志的其他亲属、胡耀邦同志和李昭同志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与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相关领导、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挖掘和弘扬胡耀邦同志的家风与廉政思想,探索廉政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措施。此次研讨会也是浏阳市第一届“廉政文化周”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活动之一。
我的青春似乎总是和夜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今天,我刚从监狱出来,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走进熟悉的城市,只能选择夜晚。这个夜晚,我要去三个地方。首先要见米米,我为她进的监狱,再就是我的哥们儿一浩。我还要去哥哥嫂子那里,如果他们愿意,那里也许还会是我的家。
在开采金矿之前,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矿山矿岩,研究矿岩产状、力学性质、构造、开采对矿山产生的影响,对开采金矿可能引发的负效应进行预测,例如:是否会改变岩体。与此同时,需要及时的填充和加固处理移动岩体或者已经塌陷的岩体,避免出现塌陷托大。在完成采矿之后,需要综合性处理开矿造成的废弃地,通过治理使废弃地能够达到种植开垦的标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2]。
当五四学生运动初见平息,李大钊就立即给自己的老师——日本著名民主主义学者吉野作造写信,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知识分子联手,坚守新亚细亚主义,共同开创东亚新文明的愿望。
李大钊相信不同文明不止是对立,完全可以融合,实现新的超越。为此,他寄希望于创造“第三文明”。作为“本身之觉醒者”,“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东西文化调和融会的结果,最后可以产生“第三种文明”,这自然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又一次飞跃。李大钊期待中国能为创造第三种文明、为人类文化做出第二次贡献。但是,其前提条件是:中国人必须对于“遗袭之习惯”,不论“若何神圣”,都要“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并且还应该“时时创造,时时扩张”[12]315。
李大钊在这里提到的“贵国识者”正是当时由吉野作造和福田德三创立的“黎明会”人士,以及他们竭力推进的黎明运动。时光回到“一战”后的第一个元旦,李大钊在刚刚创刊不久的《每周评论》发表新年献词,做出自己的国际评论。他说,“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26]375。“1914 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1917 年俄国革命的血、1918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即《圣经》中的人物诺亚)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26]376-377。
从中日关系角度看,李大钊希望东洋兄弟携手创造文明,“共创一种‘新亚细亚主义’”,取代传统的“大亚细亚主义”。他寄希望于两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日本的“黎明会”和中国的“少年中国学会”进行合作。他主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衰落,李大钊力主在新亚细亚主义的旗帜下迎着民主的世界潮流,改造“东洋文明”。 1919 年2 月,他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祝黎明会》,赞许吉野作造、福田德三、今井嘉幸提出的黎明会纲领,呼吁“把东洋民族的精神打成一气”,使得“东亚的兄弟们偕手同行”,“认清这共同生活的道路”,与西洋文明平等竞争、并驾齐驱,以创造新的世界文明。他认为,“现在平和会议(指“巴黎和会”)正在开议,我们东洋民族有许多对于世界文化进步的责任,对于世界共同生活的要求,都不能够作一致的主张,向同一方面共同努力,这真是莫大的遗憾”。因此,东洋文明的崛起与发展是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期盼。他真诚期待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从此摆脱黑暗,共同走向光明,致力于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改造。
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主要是在微观层面上进行研究,或者是以整体观念来看待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但是对一些宏观理论例如怎样对待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怎样重写文学史,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立场等问题叙述不甚明了。笔者认为,对具体作家作品等重新研究评价之所以会成为“重写文学史”的重心,关键在于“重写文学史”表现出了诸多的自觉特点。
1914 年,是时身为“约法会议”议员的严复曾做一提案,倡导“建立民彝”,推崇“忠孝节义”,坚持以“德”立国。他提出,“公等以为吾国处今,以建立民彝为最亟,诚宜视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而即以此为立国之精神,导扬渐渍,务使深入人心,常成习惯”[6]。这里的“民彝”,主要强调的是“民德”“民性”“趋于至善而止焉”[7]267,以达善治。很显然,这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的延长① 在《殷周制度论》中,王国维认为,周人典礼,“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故知周之制度,实皆为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此之谓民彝”。“礼藏在尊爵彝器的神物之中,这种宗庙社稷的重器代替了法律,形成了统治者利用阶级分化而实行的专政制度”。 。
参加本次调查的藏族大学生均来自中国海洋大学,共计63名,其中有效问卷62份,分别由20名男生和42名女生组成,他们的年龄在20至24周岁。
李大钊所寄予厚望的“中国的黎明”,是此时正在筹备组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它同《每周评论》一样,是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潮、再造文明的工具。由于五四学生运动的出现,耽误了它的成立进程。“少年中国学会”同时下的中日争端也有关系,它的成员主体是留日学生。当时,大批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放弃学业归国,急需有人出面组织,聚集力量。李大钊作为学长,责无旁贷。况且,留日期间他曾组织“神州学会”,也是留日学生总会的负责人。如今,日本“黎明会”的建立,更推动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组建步伐。
1919 年8 月31 日,《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封禁,前后共出版37 号。那么,《每周评论》为何如此短命(不足一年,只有八个月)?值得深思。我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它作为当时中国最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思想启蒙的时代使命,敢于表现自我的个性,并且开时事评论、国际评论之先河。但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确实是超前了,超出了当政者容忍的限度。虽然《每周评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它在中国近代新闻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是划时代的,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还应认识到,思想启蒙需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其中必须要给时事评论、思想讨论以巨大的空间,这样才可能达到思想的真正解放。
五、对马克思学说的独立思辨
从五四事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有必要做出必要的沟通,否则人们难以全面认知五四运动的本质及其意义。我以为,有一条重要理路一直未被打通,这就是五四之目标“再造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首要的历史使命,是在“迎受”外来文化中对马克思学说具有“思辨性创造”。
通观整个1919年,李大钊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创造,是主持《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① 刊于6卷5号、6卷6号,实际的出版时间为1919年9月、11月。收入《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这是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富有奠基作用。
李大钊开宗明义,首先说明他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本意。“‘马克思主义’(他专门用引号标注,有其用意。笔者注)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为此,“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28]2。
人们一定会问:这篇文章最为深刻之处何在?依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李大钊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唯物史观(经济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些内容,我们不能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已经给予正确的认知。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从误读中进一步凸显出李大钊思想的先觉与深刻[29]。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明确谈到理论与现实(实在环境)的关系,甚至对马克思有所批评。“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28]23。要知道,正是有了特定的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28]23-24。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没有把“阶级竞争说”看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素之一,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限定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28]18。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确实感到有些问题尚待深入探讨:一方面,两者具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28]19。
李大钊敢于独立思考,率直指出马克思学说中存在的“偏蔽”。他说:“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始至不能实现。”[28]22-23
深入感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价值还体现在李大钊特有的理性精神。我们看到,该文的题目首先突出“有我”。“我”字当头,展现了五四反奴性的理性精神[29]。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感召下,李大钊一直有自己遵从的立言原则。在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年之前(1918年),他在《强力与自由政治——答高元君》一文中郑重提出了他的原则,这一原则又与胡适有关。他说:“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30]这段话所透露的是李大钊对待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是他独立的个性化追求。正是缘于这种追求,他在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时能够保持着自我认知的、独立的思辨状态[29]。
李大钊向往新世界,憧憬新生活。为了实现文明的再造,他无私奉献,不惜牺牲生命。1919年8月,李辛白在北京大学创办《新生活》周刊,李大钊为该刊撰写了60 多篇短文。是年11 月,他为《新生活》撰文《牺牲》,明确阐释了自己的人生观。“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31]。八年之后,为了“高尚的生活”,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无私无畏,献出了自己年仅38 岁的生命。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思想与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两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不可脱节。在特定意义上,思想是文化的核心内容,而文化则是思想的载体,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都必须通过思想的转变、思想的升华反映出来。我们运用这一方法论,拓宽了视野,超越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般认识,并推进了对其研究的深度。
参考文献:
[1]周作人.思想革命[M]//谈虎集. 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
[2]周作人回忆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357-358.
[3]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4]侯且岸.思想革命:对五四运动本质和意义的省思[J].北京党史,2009(3):36-37.
[5]胡适.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M]//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8.
[6]严复.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M]//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344.
[7]李大钊.民彝与政治[M]//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在北京中国大学的演讲[M]//李大钊全集:第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
[9]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M]//李大钊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0]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M]//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29.
[11]严复.原强[M]//严复集:第1 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5.
[12]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M]//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3]侯且岸.李大钊与中国先进文化[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4):12-18.
[14]侯且岸.李大钊的新旧文化观[N].学习时报,2004-05-17.
[15]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M]//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6]李大钊.辟伪调和[M]//李大钊全集:第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26.
[17]李大钊.调和之法则[M]//李大钊全集:第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8]侯且岸.培育“和谐文化”推动文化繁荣[J].新视野,2008(4):70-74.
[19]李大钊.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M]//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0]李大钊.新的!旧的![M]//李大钊全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1]侯且岸.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6):51-55.
[22]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M]//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53.
[23]胡适附记[M]//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6.
[24]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M]//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5]李大钊史事综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430.
[26]李大钊.新纪元[M]//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7]李大钊.忠告黎明会[M]//李大钊全集:第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89.
[28]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M]//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9]侯且岸.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探幽[J].北京党史,2016(3):9-17.
[30]李大钊.强力与自由政治——答高元君[M]//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1-302.
[31]李大钊.牺牲[M]//李大钊全集:第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7.
LI Dazhao and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to Understand Cultural Evolution from“Ideological Revolution”
HOU Qie-an
Abstract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nsistency between logic and history and taking“ideological revolution”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understanding, this article sorts out Li Dazhao’s unique cultural thoughts and his practice comprehensively.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s criticism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is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is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s, his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media Weekly Review, and his independent speculation on Marx’s doctrine, this article will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ught and culture deeply,and reveal the essence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Key words ideological revolution;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traditional culture;LI Dazhao
中图分类号: K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21(2019)06-0001-12
收稿日期: 2019-09-20
作者简介: 侯且岸(1953-),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孙艳霞)
标签:思想革命论文; 五四新文化论文; 传统文化论文; 李大钊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