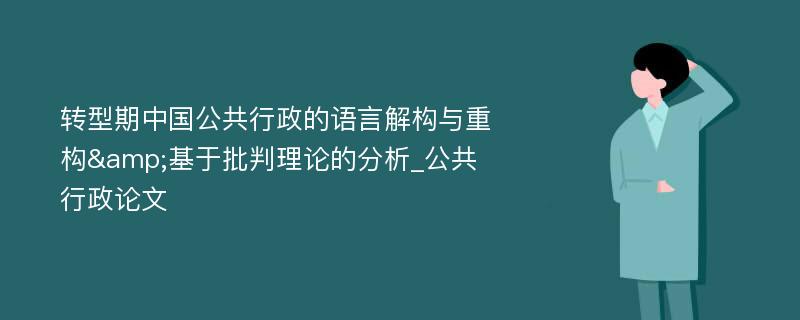
转型期我国公共行政语言解构和再造:基于批判理论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立场论文,理论论文,语言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4)04-049-(6) 批判理论的哲学渊源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现当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将其发扬光大。批判理论多样性与异质性色彩浓厚,表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理论发展阶段上,也表现在对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关注程度上,还表现在思想倾向、研究方法选择上,因而往往难以确定某种理论是否具备典型的批判性①。塞蒙特利和阿贝尔为此指出:批判理论“并不能由一套封闭的原理所界定,同时它也反对将其还原为一系列的共同特性。仅可总结出存在于批判理论家们构想中的‘家族类似’特征,其与针对社会现状提出的系统、内在的批评具有紧密的联系,这些批评旨在预期和实现日常生活中的平等和公正……批判理论力求消灭压迫和社会不公正,以提升人性的完整(自治)、促进个人的自由”②。 批判理论发现和消灭不公正、不自由的一个重要路径即在于解构语言。“解构一直都被比作对一幅绘画进行X光透视以便显现潜在的图像,而且这个不同的目的导致在解释和解构之间的强调重心从同一转向差异。”③语言背后果真有“潜在的图像”?这种“潜在的图像”也果真有可能内蕴着不公正?批判理论引人深思之处正在于此,其从解构我们日常接触并且往往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和传播的语言入手,揭示其背后社会不公和不自由。要之,批判理论提醒我们对于语言功能须作更为深刻的理解:“语言不只是思维、认知和思想交流的工具。它也是构成我们世界观的观念、方法、直觉、假设和欲望的制造厂;语言建构了我们。”④换句话说,语言主宰、俘虏了我们。甚而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自己被主宰和俘虏,亦不会思考这样的语言究竟有何不对,很快也跟着娴熟地运用起来。 维特根斯坦使用“语言游戏”的概念强调语言的言说是行动或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⑤。批判理论即旨在戳穿这套游戏的真相,尤其标志现代性的“理性”据以表达的各种语言或其生产、排列方式。批判理论因而也可谓反理性的理论,甚至称其为理论都显得不妥,因为理论本身即为一套自洽的理性化语言体系。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公共行政学者如拉尔夫·胡塞尔、迈克尔·哈蒙、罗伯特·登哈特、全钟燮、法默尔、福克斯和米勒、麦克斯·怀特等开始引入批判理论,试图将其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哲学基础。他们经常采用的研究路径即是对于传统理性官僚制行政各种流行语言的隐秘深处和内在逻辑作出解构。“解构概念对于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是一种重要的资源”⑥。法默尔强调,在公共行政语境中,解构能被用来质疑我们据以建立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前提基础,为试图使公共行政思维摆脱官僚等级观念和由于偏见束缚的准则扫清道路⑦。运用解构这一犹如“释梦”的办法,官僚制行政各种看似天衣无缝、科学客观的理性语言——效率至上、专业主义、价值中立、等级命令、理性决策,以及这些语言的叙说方式乃至由其串接的现代公共行政历史悉遭批判理论学者质疑或否定。 解构本身不是目的。全钟燮指出,解构意在支持实现基本制度变革的努力,主张批判性地综合制度问题和人类价值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的)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有价值导向立场,以及人类本性中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等传统二元对立要素⑧。法默尔说得更为直接,批判理论解构官僚制行政就是要确立一种反行政精神。所谓“反行政”,是一种旨在否定行政官僚权力并且否定韦伯式理性——等级观点的管理方法,它表明的是一种赞成论战性、多元文化论和多样性的观点⑨。 批判理论对于西方官僚制行政做出解构的努力,发人深省。能否借用于对转型期我国公共行政的思考?对此,笔者持肯定态度:一方面,应看到转型期公共行政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性特征,例如各地纷纷致力于推进绩效评估以提高行政效率,强调职责分工和依法行政,是否可以绕过西方官僚制行政曾经走过的弯路?这就可以借鉴批判理论来分析;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可贵之处在于反思的立场,在于对各种惯用语言解构的努力,挖掘其背后的隐秘机制,从而拨乱反正,凸显人本与公平导向的服务型行政,而这对于当下我国转型期公共行政研究而言,正是亟待加强的方面。 维基百科对于“语言”一词的定义是:就广义而言,是一套共同采用的沟通符号、表达方式与处理规则。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一理解,将公共行政语言大体区分为三个层面:(1)语言符号,即为各种语汇及其组合;(2)语言方式,此为语言表达的途径或样式,批判学者有时也使用“话语”一词来代指;(3)语言取向,寓于语言之中的语法、特征和规则。 批判理论借用于转型期我国公共行政语言的解构,就可以围绕这三个层面一一展开。具体则可以选取最能刻画和代表转型期公共行政的各种流行语言作为解构对象,从中一窥问题所在。 1.隐匿假象的语言符号 批判学者认为,权力和语言不可分割,权力通过语言来实现。语言是实施权力的工具,也是获得权力的关键。每个社会层面都存在着一些特别的语言,它们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控制和支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由此不难理解,法默尔为何主张将解构公共官僚机构的语言视作揭示公共行政问题的动力机⑩;解构官僚机构经常操弄的各种语言,方可识破其实际上仅是官僚机构单方面的创造物,官僚机构凭借所拥有的权力、权威资源,将这些语言以一个个听起来简捷动人的符号施加于组织成员和社会公众,直至后者烂熟于心,无力分辨这些语言符号其实是服务于官僚机构权力需要的,本质上是权力语言符号,其背后很可能隐匿了有益于官员但却不利于公众尤其弱势群体的假象。 转型期我国公共行政可归于行政生态学者里格斯所言“棱柱形模式”——形式上逐步确立了现代理性规则,内里却还是传统“潜规则”起作用。这使得公共行政各种语言符号更具假象,掩盖了不合理或有损权利的方面,例如强调官员是“公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不少官员却仍喜好“父母官”的旧称,将自身实际凌驾于公众之上,并且真正致力于“为上级服务”;将官员独立管理某项事务称作“负责”,但这仅仅表明由某人享有对于该事务的独断权力,而非意在由其担负相应法律或公共责任;在正式法律文本里使用“公民”的权利概念,其他场合却又习惯以“百姓”、“群众”等称呼公众。尤以“群众”一词最为常用,不仅与“干部”一词形成等级对立,在各种群体性事件中,“群众”一词更被一些官员解读为“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喜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形容参加者的无知与随波逐流。“群众”与“百姓”作为集体性称谓,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其中的个人成为没有任何独立的法律地位、民主权利的义务主体”(11)。 2.官僚独白的语言方式 福克斯和米勒认为,传统理性官僚制治理模式在战后高级现代主义时期——工业经济趋于成熟,文化和政治上的专家治国论与选举模式的程序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流行的那25年,达到了发展的巅峰。然其标榜“中立的公共行政永久的处方”(12),排斥价值理性,对于工具理性十分强调,由此导致其成为一个严重缺乏沟通的体系,或者说,它就是一个话语霸权的体系。在理性官僚制话语霸权体系内,自上而下的指示、指令必须逐级执行,不容许有任何讨价还价,更不允许提出怀疑和表示异议。鉴于此,在理性官僚制“独白式的对话”基础上产生的公共政策,只能是政府和官僚精英们的政策偏好,而不是公民一致认同的公共政策。同时,这种独白式的对话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和民主政治背道而驰的。鉴于此,福克斯和米勒明确宣告,“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传统的治理已经死亡”(13)。 官僚独白的语言方式(亦即话语)并非仅存于西方公共行政,在我国公共行政中亦有体现。但这较少源自我国公共行政的理性化(事实上,很多人同意当下中国理性官僚制远未形成),而是更多源自我国社会长期官民二元对立、行政高度集权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建国后又受到苏联体制的影响进一步固化和强化。在我国公共行政中,最能表现官僚“独白”方式的语言,当属“组织上决(规)定”、“上级决(规)定”、“党和政府决定”,这些语汇鲜明体现出“组织”与个人、上级与下级、政府与公众之间决策权和话语权的不平等,并且带有不容置疑的压迫性口气:对于组织、上级、政府所决定的事情,唯有服从,不可以讨价还价。如此官僚独白,极端形式干脆即为“我决(规)定”,例如2003年嘉禾县珠泉商贸城野蛮拆迁现场张贴标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从中不难揣摩这一意味。我国公共行政官僚独白的语言方式结果之一便是,各种行政规章中,公民多被称作“行政相对人”或“行政对象”——仅仅是行政决策被动接受者,而非参与主体。 3.男性气概的语言取向 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批判学者注重引入性别视角来反思和检讨传统官僚制行政的男性语言取向。这一取向集中体现于官僚制鼻祖马克斯·韦伯对于官僚制的赞誉之中:“经验往往表明,从纯技术的观点来说,行政组织的纯粹官僚制形态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相比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组织,它具有精确性、稳定性、可靠性和纪律严明的优势。”“充分发展的官僚制与其他组织相比,正如机器生产与非机械生产方式一样。”(14)在韦伯此言中,可以总结官僚制行政的几个标志性语汇:效率、精确、稳定、可靠、纪律。这些体现工具理性的语汇尤其是作为官僚制中心目标的效率,成为“建构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中的合法角色的‘理论象征’”,“所有这些概念在定位上都是高度男性化的”(15)。因为“基于西方思想的深远传统,科学的严格和客观等同于男性气概,高效率的科学家就是那种不受困扰女性的个人情绪影响的男性形象”(16)。 男性气概的语言取向在我国转型期公共行政中同样有丰富表现,例如“发展是硬道理”、“保八争九”、“维稳是硬任务”等语言在各级政府部门中被高度强调;“一票否决制”、“一把手工程”、“领导挂帅”、“铁腕官员”等语言亦自上而下被要求或推崇。基于批判理论观点来看,这些转型期公共行政的主流语言均体现出明显的男性特征,代表着刚性、决断、自负和冷漠;致命缺陷则是,仅只强调体现工具理性的效率和稳定,强调行政命令和行政任务的达成,公平、人权、环境等价值理性的考虑则退居其次,或者事实上不作考虑,这些语言在当前各级政府行政过程中具有压倒性地位,虽曾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导致极其严重的社会不公,引发环境恶化、好大喜功、地方保护、“越维越不稳”、拍脑袋决策等各种非理性后果。 批判理论并非没有缺陷,棘手问题之一便是在批判理论之中出现了精英主义的、冷漠的和过度智识化的趋势。正如一些学者指出,批判理论往往过于强调其理论成分,而付出了牺牲实践的代价(17)。登哈特等学者将批判理论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之中,雄辩地阐发了许多关于公共行政批判性实践的洞见,但公共行政的批判理论几十年来却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无法取得重要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于批判劲头十足,指导实践的能力却微乎其微。 不过,这也许并非全部实情。就像古德塞尔在为福克斯和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一书所著序言中的评价:他们有助产士的灵感而不是葬礼的司仪(18)。在解构传统公共行政语言及其实践之中,批判理论学者实际上也反向指明了公共行政变革的希望所在——语言再造应作为改革公共行政的基础性措施,要推翻现有的各种不合时宜、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旧式语言,走向一种新的体现民主、增进治理、保障权利的充满活力的公共行政的语言。从转型期公共行政来说,对应上文分析: 一是要凸显权力语言符号的公共性,抵制假象。语言总是与权力纠缠在一起,展现与维护后者,这一事实难以改变,但可以增强权力语言符号的公共性,抵制其生产假象和不公正。现代西方公共行政张扬理性主义文化,构建法理型基础,从而可以确保权力语言符号的公共性;然而理性文化过于发达,最终却又抑制了权力语言符号的公共性,使其可以藏匿假象,制造不公,招致批判学者不满和解构。转型期我国行政部门所持各种权力语言符号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但与西方不同,其多半不是因为官僚机构高度理性化,而是理性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实现权力语言符号的公共性,反而要求进一步培育理性主义文化,推动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除此之外,官员应改变心智模式,在转型期复杂治理形势下,增强对于权力语言符号的自我批判能力,切实注意到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这可以增强官僚机构的合法性,反过来也是在保护官员自己。这不但需要通过体制内外互动进一步拓展NGO的发展空间,亦呼唤知识精英和大众传媒担负重责,与权力保持适度距离,前者有不寻常的思考能力,要勇于揭破官方权力语言符号背后的假象,捍卫公众权利;后者有发达的语言扩散能力,应注意到承担社会责任,对于传播官方权力语言符号持谨慎的批判态度。 二是从官僚独白走向多元合唱。福克斯和米勒分析批判了官僚独白的语言方式,进而借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现象学的方法和现代物理学的能量场理论,提出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主张设计一个多元参与和对话的“公共能量场”,作为制定公共政策而进行话语谈判的场所,公共能量场系由各种灵活的、民主的、话语性的社会形态所构成。其鲜明特征是对无政府主义和独白性的官僚制模式的抵制。为了抵制无政府主义,公共能量场对话语作了限定: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相关性;为了避免独白性的官僚制模式,公共能量场期望话语中的意义之战,例如存在平等的对抗和辩驳,而非和谐的异口同声。公共能量场另外还构造了四个话语原则以期真正推动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真诚;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自主参与;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也正是从这四个原则出发,公共能量场宁愿话语谈判的参加者是一些人而非多数人或少数人。与福克斯和米勒的主张相近,全钟燮亦反感于传统公共行政官僚独白的语言方式。强调社会知识广泛分布于组织、社区和世界上的每个地方,在后工业化不确定性丛生的情境下,行政议题的解决应采取社会建构的途径:体现和包容多元力量的参与,它们相互对话、学习,理解彼此不同的思想、经验和社会知识,并且通过地方分权发展共同的责任。这样的过程并不总能够获得有效率的产出,然而在公共问题的解决中,过程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产品(19)。 三是改造公共行政的语言取向,增添女性色彩。现代西方公共行政浸淫于理性化之中,使得自身在理论上、象征意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外在于女性的(20)。如此虽然赋予了公共行政“阳刚之气”,减少了情绪化,有利于增进效率;然而回避价值理性的考量,导致社会公平的缺失,排斥街头官僚与公众参与,过度崇尚制度的理性力量,未免又显得冷冰冰而不近人情。转型期我国公共行政虽然理性化程度并不高,然而基于对社会发展的工具理性追求,亦形成男性取向浓厚的各种语言,并且同样导致社会公平与代际公平问题的尖锐,排斥基层官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参与,造成大量“沉没的声音”(21),致使民生问题沉重。男性语言占主导的中西方公共行政所酿成的这些问题或消极后果,亦可总体概括为道德领导力的匮乏。公共行政女性语言色彩的加强正可以对此作出弥补,因女性通常被看做是道德的、自我牺牲的、有责任的;鉴于此,女性语言与男性语言正好相反,强调多些“阴柔之气”和情绪化,对于弱者显示同情心,对于底层政治和环境问题倾注热情。增强公共行政的女性语言色彩,一是要“去理性化”,抛除陈规陋习和各种僵化规定,反对刚性、冷漠的官方语体,加强语言的亲和力和情感力量,将社区、民生和环境问题作为话语重点,鼓励政策参与和政策论辩;二是完善宪制设计,让更多女性官员走向前台,与男性分享愿景,合作共事,形成性别混合型组织,这直接可以改变公共行政的话语格局,加强女性语言分量,彰显公共行政道德领导力。 与其他分析理论并无殊异,批判理论最不满意于传统官僚制行政过于理性化、排斥价值考量。然而批判理论有其超凡脱俗之处,其运用解构的方法,对于官僚制行政各种看似寻常实则遮掩假象、存在不公、不自由的语言做出检验,以此激发公共行政与社会变革。事实上,批判理论的语言解构方法同样可以借鉴于转型期我国公共行政的分析,后者所持各种流行语言无论符号、方式以及取向等方面均存在着亟待变革的方面,语言再造为此须作为转型期公共行政改革的基础性措施,如本文所析,应能增强权力语言符号的公共性,鼓励多元参与和政策对话,以及为公共行政语言注入女性色彩。 ①戴黍:《公共行政领域中批判理论的特质、缺陷及其实践性尝试》,《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2期。 ②戴黍、牛美丽等:《公共行政学中的批判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2页。 ③Farmer,D.J.Derrida,deconstruction,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97,41(1). ④[美]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吴琼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⑤[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范光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46-65页。 ⑥⑨Farmer,D.J.(Ed.).Papers on the art of anti-administration.Burke,VA:Chatelaine Press,1998,2~5. ⑦谢昕、张亮:《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精要探微》,《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9期。 ⑧[美]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孙柏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43页。 ⑩[美]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吴琼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11)周光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2)(13)[美]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4)M.Weber.Economy and Society,H.Gerth and C.W.Mills,1973,214. (15)[美]麦克斯·怀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吴琼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16)[美]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孙柏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17)Zanett,i L A..Advancing Praxis:Connecting Critical Theory with Practic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7(27):145-167. (18)[美]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序言。 (19)[美]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孙柏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75页。 (20)[美]麦克斯·怀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吴琼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21)《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人民日报》2011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