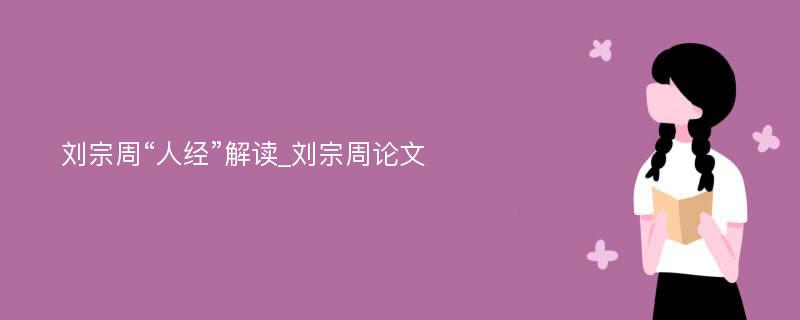
刘宗周《人谱》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刘宗周论文,人谱论文,析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整个宋明儒学的基本精神是确认人性,并进而通过对存于人性中的天理与人欲之张力的处理,以重建儒家人的哲学。刘宗周是宋明儒学的殿军,他三易其稿的《人谱》是宋明儒学的最后写本。这个写本不仅是对以往思想的简单总结,更是直面阳明心学之后晚明思想所出现的裂变所作出的回应,宋明儒学的最终归结便于这种自身的推进发展中完成。然就笔者所见,除吴宓于三十年代清华大学讲授“文学与人生”课程时将《人谱》列于“应读书目”(吴宓《文学与人生》第4页,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表现出特别的重视外,少有学者对刘宗周这一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作专门讨论。本文在借晚明儒学内外的问题以说明刘宗周《人谱》的性质之后,细论《人谱》,期望能展示出宋明儒学人学最终归结的精神旨趣。
一、推进儒学与回应邪说
王阳明之后,明代思想界的根本弊病是流于禅学,因果、僻经与妄说的杂入使阳明致良知思想扫地。当此时,认识到心学的流弊实肇始于王阳明思想本身并起而纠正的“大儒”是高攀龙与刘宗周。但高攀龙不仅不能克服心学的流弊,而且他自己的思想实半杂禅门。
阳明后学流于禅学,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为“识得本体,不用工夫”(《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253页),将识认视作工夫。这种认识产生的前提在于,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主张意是心之所发,明心见性的着力处是要体认意之未发前的气象,故即便是高攀龙这样在意识上完全自觉地持朱熹格物穷理的学者,其“所谓理者,求之人生而静以上”(同上书,第10册,第204页),终不免言语道断、 心行路绝。刘宗周则不然,他以为,认识终属想象边事,不足以成为人生的依据,因此强调日用工夫成为刘宗周力克心学流弊的关键,“慎独”成为其学说的标志。但是诚如黄宗羲所言,“从来以慎独为宗旨者多矣,或识认本体而堕于恍惚,或依傍独知而力于动念”(同上,第51页),刘宗周欲超越前贤,使宋明儒学关于人的哲学最终确立,必须另辟蹊径,使日用工夫落于实处。这一蹊径刘宗周选在了“改过”上。当然,工夫毕竟只是手段,必须有赖于性体分明,否则便是盲修。刘宗周从明确性体出发,进而确认从性体到改过的环节,最后才落实在格过思想的展开。这在刘宗周的思想中是一个整体,而集中反映这一思想整体的著作,首推他的《人谱》及其扩编《人谱杂记》。
《人谱》撰写的缘起,刘宗周在《人谱·自序》提到是因袁了凡《功过格》而引起。袁了凡系进士出身,刘宗周称他为“学儒者”,但他的《功过格》却因云谷禅师的接引而写成,与佛禅甚有因缘,同时他的思想还富有道教色彩(参见《袁了凡传》,《居士传》卷四十五,《续藏经》第145册),实际上是明季流行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式的人物。 刘宗周所以认为《功过格》有害于儒道,是因为《功过格》的思想基础是因果报应,行善与改过并非是因为善过本身,而只是一种获得酬报的手段。这种功利主义立场的行善改过,“猥云功行,实恣邪妄”(《人谱·自序》,《刘子全书》卷一,下引《人谱》,不另专注)。从《人谱》、《人谱杂记》与《功过格》的关系看,前者是对后者的回应,但不可将这种回应视作是单纯的拒斥,而应理解为是扬弃。“《人谱》一书,专为改过而作”(《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16页), 它是刘宗周为纠正王阳明“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同上书,第1册,第253页)的缺陷而提出的下手工夫。虽然注重后天修养、强调克己复礼是儒门的传统,但是儒家历来的着眼点是在张扬人先天具有的“善端”,即便是主张“性恶”的荀子,化性起伪的重心也是从正面标举礼的程式,使人努力依此修习而内化之。刘宗周有感于王学的流弊,一改儒家以往的修身路数,细密地疏理人类的缺点,确立起未曾有过的借改过以成人的方式,无疑是受到了《功过格》形式上的启发。只不过类似《功过格》的东西在晚明非常盛行,唯独袁了凡的《功过格》成为《人谱》撰写的契机,实是一偶然的机遇罢了。
二、《人谱》的结构与心性本体的展示
《人谱》共分三篇。其中,正篇是《人极图说》,是对心体,亦即人性本质的总述,故亦即是性体,它是整本《人谱》的总纲;续篇二是承正篇对性体的认识而详述性体流行各阶段的持养六事功课,亦即刘宗周“一生辛苦体验而得”的慎独工夫之所在,他名之为《证人要旨》;续篇三为《纪过格》,疏理出体现于六事功课中的微、隐、显、大、丛、成六类人生缺点,进而附以《讼过法》和《改过说》三篇,指示出涂辙可循的下手工夫。
《人谱杂记》总体上是取古人言行从《纪过格》各类缺点的疏理而类次编成,实际上就是续篇三的一个补充。但是其中存有粗细的区别,微、隐、显、大、成五类皆统而述之,没有针对各类中的具体缺点,只有丛过一类,刘宗周细列了其百种过错。
毫无疑问,《人极图说》是仿宋儒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而作,但主题作了更改。周敦颐是从论宇宙转至谈人生,而刘宗周则只讨论如何成人。但是这种主题的改变并非是刘宗周否定了周敦颐开始的整个宋明理学的理论框架,而是因着时代赋予的问题所作的一种深入,所以对于自己不讲“无极而太极”,改讲“无善而至善”的“人极”的做法,刘宗周作有一个解释,他讲:“统三才而言,谓之极,分人极而言,谓之善,其义一也。”
整个《人极图说》层次虽分明,但文字非常简约,隐喻性甚强,不宜作直接分析。事实上《人谱续篇二》,即《证人要旨》是对《人极图说》的具体陈述,故两篇更宜合而解读。
首句“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是对性体的确认,指示着“人极图”的取上一圈。所谓“心之体”,就是天地气化所生万物时赋予人的天命之性,它“不待安排品节,自能不过其则,即中和也”(《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890页)。因为心体的流转是一“不待安排品节”的过程,因此无所谓善恶可言,故可谓“无善”;然而心体的流转又具有无过、无不及的中和之德,故就此而言,又是“至善”。
然则无善而至善的心体究为何物?刘宗周以为,“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为什么呢?因为“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著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刘子全书》卷九《问答》)。换言之,在刘宗周看来,性体不应是一个空洞的虚体,而应存有定向性的潜意识。这样,性体既然本质上是这么一个“定盘针”似的意向,那么根本的工夫就必须从体认意向开始。刘宗周认为心体是“独”,所以对心体之根本的意向的体认,便是根本性的工夫“慎独”。然而于独处时下工夫,终究是一难事,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讲,性体未显的独处之时更象是闲居,因此刘宗周更以动静来显示性体的存在。
在这一层上,刘宗周对周敦颐的太极图作了细节上的更改。他把象征阳动阴静的太极图(即取坎填离图)拆成动、静分离的二图,另作别解。按照刘宗周的看法,“盈天地间皆气也,其在人心,一气之流行”(《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890页),故性体也可从阳动与阴静来进行体认,这便将工夫从至微的独体转落到比较显露的情与形上。性体的流转,即意向由潜在转成实在时,便产生出念,七情随之而著。如果此时“念如其初”,即符合性体之意向,那么由此念而引发的情便“返乎性”,由意而念而情的动是没有不善的,这动“亦静也”。这个过程是气之阳在起作用,对这个过程的体认便是“知几”。意向在精神中既然引发了念与情,自然便要于外在的容貌辞气之间有所体现。如果形于外的容貌辞气与诚于中的念情合若符节,则形于外的过程便与人之性命相合。此时作为心性之体的意虽呈以静,但“妙合于动矣”。这个过程系气之阴在起作用,对这个过程的体认便是“定命”。由于阳动阴合,见之于人,是先诚于中后形于外,故此有太极图的分离,且阳动在前,阴静于后。
凭此,人便行于整个人世之中,一切与身命心性相关的问题“一齐俱到”,但它们并非乱无头绪,而是“分寄五行,天然定位”,反映于五伦之中。本来,“学者工夫自慎独以来,根心生色畅于四肢,自当发于事业”,弘道于天下。而五伦正是其大者,故“于此尤加致力”。此处的工夫便是“疑道”。
因为“盈天地间皆吾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也”,故“其间知之明,处之当”,自然“无不一一责备于君子之身”。但是,“细行不矜,终累不备”,肢体受伤,即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则无所不爱;言义,则无所不宜;言别,则无所不辨;言序,则无所不让;言信,则无所不实。至此,乃见尽性之学,尽伦尽物,一以贯之。”此处的工夫为“考旋”。
最后,刘宗周强调,善无尽头,君子当“始于有善,终于无不善”如此才是“尽人之学”,反归性体,当然这样的境界已是“作圣”了。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以《证人要旨》帮助解读《人极图说》是十分有益的,但两者间所存在的根本区别断不可忽视。《人极图说》宗旨是从正面强调性体本善,人可以亦应当且必须存此性体,循此性体而起念、而生情、而形于容貌辞气、而发于事业,并存而存之;而《证人要旨》则着力指出在性体流转的每个环节中都存在着向善与过两方面发展的可能,因而它注重于如何抑制和消除向过的方面发展的可能,甚至直接借改过而迁善。由此亦可见,作为刘宗周思想的集中反映的《人谱》,虽然重心是在工夫上做文章,但于理论上是兼顾性体,并作了双向的发展的。他的思想的基调是,言本体是有善无过,言工夫是有过无善。然而本体尽管是有善无过,但刘宗周没有将它定义为一个虚体,而是赋予它以一种潜在的意向,这便要求工夫从本体上做起,杜绝了逃禅的漏洞。至于论工夫,由于他把视点聚焦在过错上,并且作层层揭示,因而彻底摆脱了心学固有的那份玄虚与粗疏。
三、罪过的产生及其类别
刘宗周论本体是有善无过,讲工夫则是有过无善,个中的原因是因为在他看来,“自古无现成的圣人,即尧舜不废兢业,其次只一味迁善改过,便做成圣人”。毫无疑问,强调工夫应当从改过做起,相对于以往儒者的手段,确实是更落于实处。但是刘宗周似乎并不是将此仅看作是入手的一种方便,而是更多的含有理论上的意蕴。他强调指出:“学者未历过上五条公案(即体独、知几、定命、凝道、考旋),通身都是罪过,即已历过上五条公案,通身仍是罪过。”这表明,论工夫强调有过无善,决不仅仅是出于实践上便于切实可循的考虑,而实含有对人的本质作罪过确认的观念。这样,论本体是有善无过,论工夫是有过无善便超出了具体的实践的领域,而产生出一个关涉到儒这一贯的根本立场上的严重的理论问题,即人性究竟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显然,根据刘宗周对心性本体的确认,性体是善的一元的。对此,刘宗周同样是时时强调的。在续篇三《纪过格》中他特意申述道:“人虽犯极恶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依然与圣人一样,只为习染所引坏了事。若才提起,此心耿耿小明,火然泉达,满盘已是圣人。”既然如此,刘宗周势必要于理论上来解释本体之善与何以会引来“通身都是罪过”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释也就是过的产生的回答。
刘宗周讲:“凡言性者,皆指气质而言也。或曰有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如曰‘气质之理’即是,岂可曰‘义理之理’乎?”(《刘子全书》卷十一)实际上,气质之中本含有义理,故人的心性只可作一元看。依照刘宗周的心性本体的术语,心之体在于意,意乃是恒具善的定向,这意向便是义理,故此义理实即是心之体,也就是性体。然而这个善的定向,即义理,必得依傍着气的流化,人的罪过便在这气的流化中产生,刘宗周讲:“惟是气机乘除之际,有不能无过、不及之差者。有过,而后有不及,虽不及,亦过也。过也,而妄乘之,为厥心病矣。乃其造端甚微,去无过之地所争不能毫厘,而究甚大。”(《续篇三·改过说一》)这里,刘宗周引入了“妄”。由这个“妄”,刘宗周似乎意欲表征着他的一个观念,即引起罪过的不是理,而且也不是气。气处于乘除之际,呈以动态,无过与不及实是流化中的一个片段,任何动态过程中的片段被抽出作静态分析,必不可能完美,因此其无过与不及本身不足以被认为是一种罪过,而只能构成为一种机会,真正的祸首是“妄”。而妄显然不属于原初的本体——理与气,这便无疑是从本体论上彻底根除了罪过的源头,确立起无可动摇的善的心性本体。
然而,妄是什么?刘宗周认为,“妄字最难解,直是无病可指,如人元气偶虚耳。然百邪从此易入,人犯此者,便一生受亏,无药可疗,最可畏也。”显然,这是一个隐喻性的解释,由这个解释,我们唯一可确定的只是,因为妄是无病可指,故而与其说妄是一种显性的过错,不如说是一种隐性的精神状态。这点可以见之于刘宗周所引的程子言,即“无妄之谓诚”。由于妄不可训,便以相反的一面来解,这就是诚。诚当然是一种精神状态,“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学》)。但是刘宗周进而强调,“诚尚在无妄之后。诚与伪对,妄乃生伪也。妄无面目,只一点浮气所中”。换言之,妄作为人的一种不良的精神状态,在发生上是先于“诚一伪”的,联系到上述的妄的产生,我们可以确定,妄是与善的心性本体相对应的精神状态。至于这种状态的性质,刘宗周描述为“独而离其天者是”。这里的“天”,作状态解,可训作“天然”,作实体解,它所指称的就是善的心性本体。因此,妄这种精神状态,性质上便是与善的心性本体相对立的人欲的萌发。如果印证于补充说明“妄”的《人谱杂记·体独篇》,则可见,慎独的目标就在于根除妄,即要无欲。
需要进而说明的是,在刘宗周思想中,妄就其本质而言,虽然是人欲的萌发,但妄更重要的是它尚处在“未起念以前”。易言之,妄不等于欲望,妄只是欲望还未萌发但却在趋近与诱发之中。这样,妄本身固然不是过,只是“原从无过中看出过来者”,但刘宗周仍是将妄定名“微过”,而且视之为“实函后来种种诸过”的“妄根”。在此,我们似可体会到,刘宗周是在着意培养或确认一种心理上的定视,即罪感。返观前文可知,这种罪感显然不是建立在外在的个人与社会的反应上的,而是有赖于内在先天性的善的心性本体的自觉,以及由于对善的本体的偏离而产生的感觉。毫无疑问,如此自觉地确立与培养罪感,是传统儒学中所没有的,而这正是刘宗周克除心学流弊的重要举措。刘宗周的哲学,核心在慎独;而慎独的落实,是在改过。改过如限于其本身,就会流于外在的就事论事,最终陷于形式化,《功过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结果的反映,而确立与培养起人的罪感,便能于意识中起正心诚意的作用,这样,改过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反向克制工夫,而且也是心性本体正向的趋近过程,因此,罪感的确立与培养,恰是为改过在理论上,同时也是在实践上奠定一块基石。
由妄根的生发,遂有层层展现的种种过错,刘宗周将它们归为“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成过”六类。在儒家思想史上,改过的要求应该说是自来已有的,但如刘宗周这样,对身心的过错作如此严细的分类,并有一个贯彻到底的理论者,是前无古人的。尤其是刘宗周对过错的分类,不是杂乱无章的罗列,而是将人的过错以一显见的因果链呈现。
在这一因果之链中,有几个环节对于理解刘宗周的整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见于七情的隐过。细玩刘宗周对七项隐过的定名,可以发现他在七情上都用了限定字,即溢、迁、伤、多、溺、作、纵,其意甚明,是失中的表示。这意味着在刘宗周看来,人情本身与心性在性质上是同属善的,只是功能上性内情外,严格而言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其次是见于五伦的大过。关于六过的定名,刘宗周都作有解释:微过是因其“藏在未起念以前,仿佛不可名状”;隐过是因其“过在心藏而未露”;显过是因其“授于身”;大过是因其“过在家国天下”;丛过因其繁多;成过则因其已成众恶之门。从这六过的定名中可见,大过的定名依据是比较特殊的,它不是根据过的状态,而是根据它的危害程度。而进一步观察刘宗周关于大过的排列,则可注意到,他所谓的家国天下,国与天下被虚搁,而家则是他关注的真正的点。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儒家传统的家国同体的观念,但如果我们把观察集中在刘宗周借改过来追求人的完善,那么不难看到,在刘宗周的改过实践中,家庭的地位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认为,“畔道者,大抵皆从五伦不叙生来”。于此更返观家国天下的一体,则家庭的关键性便能确切地说,是在于它成为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中介。最后便是已成“众恶门”的成过。在这里,刘宗周引入了“恶”这一新概念。对于过与恶的本质性的差别,从刘宗周对诸恶的定名,诸如“微过成过曰微恶”上看,表达现实化过程的“成”字被强调,这表明,在刘宗周思想中,过只是用于人们落实工夫的虚设的靶的,而非现实性的存在,一旦当它由潜在的转成现实的,则过便不复是过,而是恶了。过与恶不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存在方式上的差别。然而问题的重要处是在于,刘宗周并非因为过不是现实的,便轻视它的存在,而是正相反,他将工夫恰恰落实于这种潜在性的过的改正上。由此可见,刘宗周提出改过思想,根本性的目的不是针对着现实性的过失,而在于精神中培养起克念改过的意识,这一点复与前文所述的罪感意识的培养的趋向相印证与相吻合。
除上述以外,刘宗周关于过错分类的另一个特点是全方位地为个体行为制定了伦理规范。由于“丛过”是“坐前微、隐、显、大四过来”,是全部失范的个体行为的集中发映,故在此我们便着重以“丛过”为对象来加以讨论。“丛过”所列共百项,按照刘宗周的说法,这仍只是“各以其类相从,略以百为则”而已,远非个体具体行为中的全部过错。刘宗周列举整个丛过的方式,是“先之以谨独一关,而纲纪之以色、食、财、气,终之以学”。如果以今天习惯的用语来大而分之,则可以划为无意识行为与有意识行为两类。象列于丛过前面的“游梦、戏动、谩语、嫌疑”可以看作是无意识行为的典型例子,而有些行为则可看作是无意识行为的变种,象“无故拔一草折一木、呵风怨雨”等。在有意识行为中,刘宗周基本上是从两上方面来归类的,一个是个体性的行为,另一个是发生于交往过程中的行为。在个体性的行为中,刘宗周主要按照人的生理需要与精神需要来举例,前者如“好闲、蚤眠宴起、暑月袒”等,后者如“轻刻诗文、假道学”等。比较起来,对于发生于交往过程中的过失,刘宗周举的比较多,几乎涵盖了整个日常生活。毫无疑问,刘宗周的分类是不严格的。事实上,人的身心行为的分类法是可以千差万别的,而任何一种分类都不可能做到巨细无遗。因此应该承认,刘宗周对丛过的分类列举,在人的行为认识上是很有意义的。此外,在行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中,分析行为是属于自发的还是习得的,是非常重要的。据刘宗周“人虽犯极恶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仍然与圣人一样,只为习染所引坏了事”的说法,刘宗周是主张习得的,但他并没有就此作任何论证,这显然是因为在他的观念体系中,心性本善是一条公理。
刘宗周通过对身心行为过失的归类来确定伦理规范,从形式上看,是近似于感性化、或者是教义化的,换言之,刘宗周提供的似乎只是一种常识性的道德准则,不足以构成一种独立的道德哲学。但是,这样理解是不对的,因为刘宗周的工作是在接受儒家道德哲学的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按照这个传统,人的身心行为的正当性决不诉诸于任何外在的目的,而是基于心性本体的德性,以及由这种德性所决定了的义务,这是儒家义务论的道德哲学的标志,而且这种正当性或德性被认为是可以直觉地认识的;同时亦当承认儒家传统的道德哲学对于道德实践中的行为正当性的确定是明确的。虽然刘宗周的改过思想单独抽出来看,确实存在着感性化与教义化的特征,但当我们将它纳入儒家,尤其是晚明价值系统解体的背景中去认识,那么便应该高度肯定刘宗周改过思想的贡献。
四、改过的方法
刘宗周在细述人的过错的层层显现的过程中,改过的方法已相应地表现了出来。象微过,因“妄”无可名状,所以改过的方法只能是培养与确立起一种罪感意识,时时警惕,慎独而保其天真。至于隐过,虽显现于七情之动或溢、或纵,但它仍是“坐前微过来”,“微过之真面目于此斯见”,故改过的方法就“须将微过先行消煞一下,然后可议及此耳”。对这一基本方法,刘宗周附在《人谱》后的《改过说一》有明确的阐述。然而我们不难注意到,刘宗周的这一基本方法的核心并不是提出改过的具体方法,而是弄清楚过错产生和扩大的过程。换言之,在刘宗周思想中,过错的层层疏理与指认,实际上便是过错的改正,知过即是改过。显然,刘宗周在此无疑是肯定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刘宗周申述了他对知的看法。他指出,“知有真知,有尝知”。所谓真知,乃本心之知。也就是贯彻于行、不与行相分离的知。所谓尝知,乃是“习心之知,先知后行”,知与行是分离的,常人的知便属于此类。在功能上,真知与尝知也是不同的,“真知如明镜当悬,一彻永彻;尝知如电光石火,转眼即除”。但是刘宗周并不否定尝知的价值,他认为,“学者由尝知而进于真知,所以有致知之法”。在此,改过之法实际上被转换成了致知之法。而对于致知之法,刘宗周以为,就在于践履,就在于行。本来真知(改过)就是贯彻了行的知,而结果致知之法(改过之法)也就是要落实行,刘宗周似乎于理论上陷入了同语反复。
但实际我们不可作如是理解。对于践履的工夫,虽然刘宗周贯彻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与平天下这诸多的方面,但这诸多的方面都是由诚意、正心而生发。这样,致知之法固然不徒在知,而实在行,但此行主要不是指在实际的行为层面上展开,而首先是在心性的层面上进行。因此在真知的内涵中所包含着的行,实质上仅是心性的自明过程。
因此,刘宗周改过的着力处仍是在心性上下工夫,故此他要重新启用他的“讼过法”,即“静坐法”。对于静坐法,刘宗周曾加以废弃,原因是有人批评“此说近禅者”。然而他认为改过的关键是自明心性,那么静坐法便不失是可行有效的方法,当然将静坐区别于禅坐是理论是的一个前提。在这个区别上,刘宗周认同于高攀龙的见解。刘宗周称:“近高忠宪有静坐说二通,其一是撤手悬崖伎合俩,其一是小心著地伎俩,而公终以后说为正。”显然,前者是禅坐,后者是儒者之省察。刘宗周强调,静坐决非一无事事,而是借改过而祛妄还真的小心著地工夫。以冥想的方法来省察已过、涵养心性,这是宋儒以来即被强化了的修身方式,明代加以沿袭,但静坐法始终没能很好地与禅坐相区别,故而王阳明后来也提出以致良知、事上磨炼来取代原来提倡的静坐。刘宗周弃而复用,并且将静坐限定为一种改过自省方式,无疑是将阳明学在工夫上推进得更为笃实。
刘宗周关于静坐过程的描述(见《讼过法》),有两个问题值得说明。第一个是自省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个超越于自省者之上的启示者,即那个“鉴临有赫,呈我宿疚”,与自省者进行对话的存在者。对此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表明刘宗周的改过思想在最后的方式上趋近晚明传入中国的天主教,冥想自省虽然是入手处,但最终的觉醒有赖于外在的启示。二是根据刘宗周所讲的“乃知从前都是妄缘,妄则非真”,以及宋儒以来着力强调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认为妄与真非两相存在的实体,而只是同一实体不同的存在状态,那个在人自省时呈现出来并相规劝告的存在者并不是超越于我之外的存在,而只是与陷入“妄缘”中的我相区别的真正的我。笔者取后一种理解,以为刘宗周是坚持着儒家的立场,以为人始终是拯救自己的主人。第二个是自省过程具有着完整的神秘主义发展阶段。所谓神秘主义不是诸如预感、直觉、洞察、先知以及超感官感觉等等模糊的、不可思议的或“异常”的感受,也不是以显著情绪或入迷为主要特征的宗教感受,而只是一种统一的感受。这种统一的感受,用儒家的语言,便是“天地与我同心,万物与我同体”,也就是刘宗周所讲的“此心便与太虚同体”。在儒家思想史上,这种统一感的获得是笼统地以知性、知心来表达的,或许在一个具体的哲学家那里,如孟子,这个过程是非常真实的,但由于它的不可言说性,阻碍了这一过程为一般人所接受。而刘宗周改过思想的贡献恰在于在他的静坐法中,将这一过程明确地划分出净化、启发和最后的统一三个阶段,使得儒家传统的明心见性过程似一条非常真实可寻的途径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循此而行。
五、结语
至此,本文对刘宗周的《人谱》作了全面的讨论。由这种讨论,我们看到刘宗周虽然在根本的立场上始终坚持着儒家的传统,但思想的关注点是与前贤大相异趣的。作为宋明儒学的殿军,人的过错的分析、通过改过来重建道德生活,成为刘宗周人的哲学的精神所在。现实中的人的过错的普遍存在,这是儒家从不回避的事实,儒家道德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理论“克己复礼”完整地从外在的规范(复礼)到内在的要求(克己)建立起明确的价值系统与操作方式,但是,由于儒家哲学偏重于性体本善的立场,强调人于现实中完善性体,同时由于“礼”因时代的变迁而容易失去其作为行为规范的有效性,儒家自身的发展便不免导引出实践中的相对主义。因此,刘宗周依据人的心性行为的自然展开,来全面反省人于这一展开过程中所普遍存在的产生过错的可能性,实是为现实的道德生活预设了一整套警戒线。
毫无疑问,如果只是着眼于这套警戒线本身而论,刘宗周关于人的过错的层层展示在性质上与普通族谱中的训条无异。《人谱》的改过思想,真正的精神之处尚不在于人的过错的单纯排列,而是在于过错排列的形式后面隐涵着一个行为归因理论。我们在《人谱》中所看到的人的过错排列,是从一点不可言状的“微过”发展到众我清晰明白的“丛过”,但人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首先是细碎的“丛过”,而刘宗周的陈述,恰在于指出这如此多而碎的过错是可以层层上推,直至最初的源头。因此,行为归因理论致使刘宗周人学体系中的改过思想并不等同于普通训条,而是力主于精神上培养起罪感意识。与此相应,刘宗周的改过方法,实质上也是分别针对着两个层次的。
当然,刘宗周将自己关于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着力点选在人的过错的分析与改正上,并不是一个随意性的选择,而是面对晚明时期作为中国社会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所出现的内在裂变,以及与这种裂变交相辉映着的化外思潮的冲击而作出的回应。在儒家思想史的演变中能成为真正有意义的回应,必非简单重弹老调之所能,而务须续谱新曲。因此,儒学的正本清源,以及邪学的拒诉固然是刘宗周提出改过思想的直接目的,但改过思想则因其对宋明儒家人学的推进而成为儒家关于人的哲学的新内容。而从思想史的延续性讲,刘宗周的人学体系一方面以其强烈的改过思想的提出,使宋明儒家藉工夫的彻底落实而彰显本体的人学理论发展到极处,划上了一个句号;另一方面,这个终结因改过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相异于前儒的路向,无疑又进而成为儒学新的拓展的起点。
(本课题研究得到杭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流文教基金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