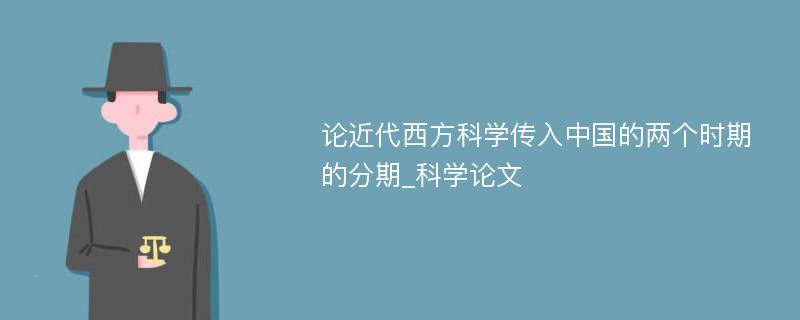
关于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两个时期分期问题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代论文,时期论文,两个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0)01-038-043
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总体有两个重要时期,即明末清初时期和清末民(国)初时期,已为学术界共识。但两个时期是如何划分的?传播主体与分期的关系怎样?两个时期起点与终点是如何确定的,及确定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这是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史研究中重要的分期问题,对研究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十分重要的。探究其科学合理回答,对中国近代科学的缘起和发展轨迹等研究有重要意义。把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分为两个时期可见之于诸论著,如王萍所著的《西方历算学之输入》一文中提出,“西欧学术进入中国,有两大阶段:一在十七世纪初叶(明万历年间);一在十九世纪中叶(清咸丰年间)”。[1](P208)龚育之认为,“西学东渐,大体上说是从明末清初开始,晚清时期又起了一个高潮”。[2](P1)以上两种说法均把西欧学术进入中国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强调了两阶段的大体时期。张荫麟在《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一文中把近代时期西方学术输入我国分为二期:“第一期,始于明万历中叶(1573-1619),盛于清康熙间(1662-1722),至乾隆中(1736-1795)而绝;第二期始于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间之讲求洋务,以迄今日。”[3](P1)张荫麟先生也给出两个时期各自的起点、终点的大致时间范围。虽然以上三位学者未明确指出近代西方科学输入的两个时期相应的具体起始、终点时间,但他们的关于两个分期的论断,特别是张荫麟先生给出两个时期各自的起点和终点的大致时间范围,对我们所进行的关于两个时期各自的起、终点的划分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分期的依据
对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阶段进行分期,必须有一定的原则、依据和理由。一般认为,由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形成是与近代西方科学输入紧密相联的,因此,有关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分期的论述,我们可作为重要参考。如许良英先生提出自然科学史的分期要遵从客观历史事实,而非先验原则。“要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任何先验的准则出发。”[4]这一原则也是科学传播史分期的重要准则。再如,樊洪业先生认为科学史分期除遵循一般科学分期原则之外,还必须考察中国科技史自身的特点:“应该是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中以中国传统科学为参照系来确定中国近代科学史的起点”。[5]强调科学史分期应选取参照系确立起点的重要性。张祖林先生把“考虑近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一种社会制度的特点”,即把体制化因素作为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分期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6]但是,科学传播的分期有别于科学技术史的分期,是与传播主体密切关联的。同时,从传播主体在科学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看,近代西方科学传播过程也是传播主体的活动过程,每个阶段都是伴随传播主体的存在及活动相始终。因此,考察传播主体的活动对于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两个阶段之分期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借鉴于以上几位学者提出的科学史分期原则并结合传播主体在科学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提出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两个阶段之分期的参考标准:1.参考科学技术史的分期原则,但同时注重科学传播的内在活动关联或内在逻辑联系;2.重视传播主体的活动与科学的关系,参考以主体的活动起止,或以与主体活动起止相关的明显标志事件为线索,分析判断分期的起止。在几个影响或决定主体活动的因素同时存在时,首先以影响、决定主体活动的内在决定性因素作为判断分期标准,而把外在因素作为判断标准;3.把所研究的历史阶段放到大的历史阶段或历史环境背景下,注重科学体制变化与科学传播分期的节点划分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传播主体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两阶段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并非从中国古代的传统科学中内生发展起来的,“中国的近代科学不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继承,而是西方科学传播的结果”。[5]而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每个阶段都是与其传播主体密切不可分的。秉航先生在《试论明末清初中国科学技术的若干问题》一文[7]中,认为从十六世纪末叶开始就不断有基督教传教士来华活动。伴随这些活动,特别是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也陆续地传来中国。
在明末清初时期,即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阶段,其传播主体为:西方传教士、少数中方传教士、朝廷部分官员。但主要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洋科学输入我国,我国学术界顿呈异彩焉。其输入之介绍人,为天主教之耶稣会士,其最著名者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我国学者则有徐光启、李之藻等。”[8](P18)中国学者余三乐在为美国人邓恩著《从利玛窦到汤若望》译著作序时说,两大文明第一次全面碰撞、交流和相互汲取营养,是由被誉为“巨人的一代”的,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及他们的中国朋友们所成就的。[9](P2)中国的天主教是由利玛窦传入的,利玛窦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了三项沟通中西的努力:1.尊重中国固有的礼教,准许教徒祭祖拜孔;2.结交上层儒士、官员,由上到下,争取打开局面;3.以当时的先进科学成果为皇朝服务,如舆地、历法等。这样做取得了成效,使天主教在中国站住脚,并逐渐传开。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明末清初间传教并非以宗教叩开中国大门的,而是以新奇的西学来吸引中国的士大夫,使他们产生兴趣,又以译书修历来打动中国朝廷,使之感到需要,就这样他们得以进入中国腹地和深入宫廷。两个世纪中传教士基本上循着利玛窦的方式在中国活动,其中有著作可考的教士约七十一余人,著作三百七十种,具有科学内容的一百二十种,在这些著作中仅利玛窦、汤若望、罗雅各、南怀仁四人就占了七十五部之多。”[10](P332)
这说明当时传教士在输入西学中是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其他人所不可取代的。“止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收四百六十三人,中国籍者仅七十一人,占百分之十五点三。”[11](P1041)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当时传播西方科学者以传教士为主,且主要以外籍传教士为主。
在第二阶段,即清末民初阶段,近代西方科学输入的主体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或谓中国学者)、留学生、传教士、西书翻译人员、新式学校教习、部分报刊编辑,但主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留学生。晚清时期,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强烈的使命感和浓厚的政治意识,使得一批批有识之士转而向西方文化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特别是洋务运动前后,爱国的热点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此情况下,这一阶段的近代西方科学传播的主体成分也发生了变化,留学生成为传播主体的一个重要群体。留学生群体对中国近代科学的贡献,是从19世纪80年代留美幼童开始,他们在爱国、救亡、独立、自由的新型社会思潮的推动下,怀着强烈的追求独立、民主、富强的爱国热情,以科技救国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积极介绍和引进近代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转化,中国近代科技的成长和由近代科技向现代科技的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留学生们积极弄潮,为传播西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东奔西走,上下求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业绩。”周棉在评价留学生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时,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贡献和特殊地位,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12]
三、两个阶段起点、终点的划分
根据以上提出的科学传播的分期标准,并参考科学技术史的分期原则,下面我们对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两个阶段做如下分期。
(一)第一阶段时间的起点、终点
本节主要讨论两个方面内容:第一,重点考察利玛窦来华所输入西方科学的内容,及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确定近代西方科学输入的第一阶段的起点;第二,考察康雍乾三朝禁教对传教士的影响,分析不能把三朝禁教作为划分第一阶段的终点的原因,认为1775年即在华耶稣会奉罗马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签署的通谕(该通谕于1773年签署,1775年送达中国耶稣会)被解散,作为第一阶段的终点较为合理。
1.第一阶段的时间起点
关于第一阶段的时间起点,如果我们要与历史划界和特定事件相联系的史学习惯相合,可以根据传播者所引进的知识体系、内容,及对中国传统科学体系的冲击所引起的渐变来区分。
就科学传播载体而言,传教士中被派来中国最早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据史料记载,利玛窦于明万历时航海至广东,被认为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13]16世纪,伴随着科学传播载体传教士来华,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也陆续地传来中国。“明季,利玛窦之入中国,实开中西交通之新纪元,利氏入中国前,虽亦有教士进入内地,然不作长居之计,不旋踵而即退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11](P692)历史学家方豪认为,“利玛窦,恐怕是自古以来,所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中最出名的一个”。甚至于所有十六七世纪传入的西学,“一律归之于利氏”。[4](P72)从利玛窦开始,一大批耶稣会传教士如意大利的艾儒略、罗雅各,德国的汤若望,比利时的南怀仁等陆续来华。伴随着传播主体的陆续到来,西方科学也逐渐输入。[15](P210)
从传播内容方面看,不仅科目覆盖面宽,而且数量也较多。无论在当时是“新”学还是“旧”学,利玛窦及其后来者们,根据自己在欧洲所受的当时为最高水准的科学教育向中国的士大夫传播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宇宙论、地圆说、世界地图、欧几里德几何学等。“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11](P692)数量上相对较多,传教士们以西方科学知识输入为重点,编译和翻译了天文、数学、几何、地理、农学等方面的著作近200余部。
更为重要的是,利玛窦所传播的西方科学知识,对中国固有的传统科学及知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输入的西方科学“对中国传统科学来说却是异质的、全新的,并且触及到科学观和科学方法的较深层,具有科学革命意义”。[15](P209)在未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之前,按照知识体系的划分,中国传统科学属于古代科学知识范畴,在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体系输入后,内因通过外因的作用,中国古代科学演变为近代科学。
在中西科学交流史上,利玛窦的开创性贡献可说是划时代的、多方面的。王国忠在《李约瑟与中国》一书中,引用科学史家李约瑟的评价,称利氏是“近代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位功臣”。[16](P430)张祖林把利玛窦来华作为中国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变的转折点。[17]
关于利氏来华的时间,按《利玛窦年表》[18](P633)记载为,明万历十年(1582年)4月15日奉远东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神父之命,前往马六甲,转往中国。8月7日于病中抵达澳门。1583年9月10日抵达广东省时首府肇庆。
鉴此,我们尝试认为,把1582年即玛窦来华作为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阶段的起点比较合适。从另一方面看,把利氏来华的时间1582年作起点,亦与张荫麟判断认为近代西方学术输入中国的大致时间范围相吻合。
2.康雍乾三朝禁教与第一时期的终点划分
科学传播活动在向前发展过程中除遵循一般历史规律外,还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联系或规律。传播主体及其传播活动的始与终,是分期时的重要参考点。因此,决定或影响传播主体的活动的历史事件是分期的重要依据,但在几个决定或影响因素中,我们更倾向把决定或影响主体活动的直接的内在因素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
下面通过探索教案、历法之争及三朝禁教的历史轨迹,分析认为教案、历法之争及三朝禁教对传播主体的存在及活动的影响是外在的,也是禁止的世俗性因素。期间,因诸方面原因客观上亦没能消除传播主体——西教士滞留在华,因此,把教案、禁教等时间作为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时期的终点不甚合情理。分析认为,相较于禁教等世俗性外在禁止性因素而言,宗教的教义、教理和教谕是内在决定性宗教因素,对教民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因此,把在华耶稣会奉教谕解散的时间1775年作为第一阶段的终点较为合理。
自17世纪中叶后,清初统治者在顺治、康熙两朝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采取了优容礼遇政策,因此,“明末以来由耶稣会士利玛窦开其端绪的西学东渐,并未因明清鼎革而中断”。[19]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发生了1615年南京教案事件、1629-1669年历法之争,这些都没有使朝廷采取禁教政策。传播主体传教士们的科学传教活动也得以顺利开展。然而,1704年罗马教廷圣礼部正式通过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决议,即所谓“七条禁约”,禁止中国教民敬孔祭祖。针对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的顽固态度,康熙决定采取强硬政策,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在1717年批准将天主堂改为“公庙”,传教士尽行驱逐出境。至此,中西礼仪之争完全陷入僵局,康熙朝对传教士的政策,从此便由优容礼遇而变为禁止限制,清中叶的禁教政策遂告初步形成。然而,康熙帝对传教士实行领票制度,禁止公开传教,但执行得并不十分严格,禁教令在康熙年间也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所驱逐的还只是未领票的传教士,“领票者仍可在中国居住”,凡怀有一技之长而又愿留居中国的传教士,履行手续向清政府领得永居票之后,仍可在各地过其宗教生活,所改变的是传教士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器重,在各省传教的耶稣会士,行动受到监视,发展教徒也受到限制。据统计,至康熙末年,各省的天主教徒,人数已达30万,拥有教堂、住院300座以上。[19]
雍正朝虽然采取了严厉的禁教手段,但由于1716年来华后一直佐理历政的日耳曼传教士戴进贤出面,直接向雍正帝上了一道“西洋人戴进贤等谨奏为吁恩垂鉴事”的奏折等请求,获得恩准,最终,仍然有在钦天监任监正的戴进贤、监副徐懋德等20余人,继续在京留用,担任修历。雍正朝采取了严厉的手段禁教,虽然留下者甚少,但这些传教士们身处宫廷高位,影响不可小视,且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为了在华立稳脚跟,纷纷表示效忠朝廷,争相引译西方科学。如戴进贤著有《仪象考成》、《仪象考成续编》及《黄道经纬恒星图》,设计赤道浑仪等。
乾隆朝时期,鉴于康熙治国失之过宽、雍正治国失之过严的教训,转而采取“宽猛互济”的政策。表现在教禁方面,乾隆初年对公开传教活动仍严行禁止,但对秘密传教则又网开一面,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因此,仅20余年之后,到了18世纪70年代,传教士又大量由澳门、广州渗入内地。1784年初,澳门主教区又先后派三批共19名传教士潜往直隶、山西、山东、湖广、川陕等地区。[19]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康雍乾三朝虽然采取禁教政策,但或因领票有条件居住,或因朝廷需要,或因对公开和秘密传教有别的政策或态度,以至于传教士人数在华禁而未绝,并且生存下来者也为了将来长期居留而更加高举科学传播旗帜,而将传教的目的隐忍,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朝廷禁教,对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而言,只是外在禁止性世俗因素,即使管住了人但管不住心。反之,教皇的教谕、通谕则是教士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天条和铁律,是控制教士们活动的内在决定性宗教因素。
1773年,教皇颁布敕谕,宣布取缔耶稣会。教皇的通谕于1775年传到北京,南京主教、兼理北京教务的南怀仁责成公布有关教宗的通谕,葡籍耶稣会传教士刘松林(Augustin von Hallerstein)与法籍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闻讯后“气愤而死”。因为“解散令既然来自教皇,传教士们只好服从”。[20](P108)在华耶稣会遂被解散。据统计,这时在华耶稣会士,“北京17人,江南3人、湖广6人、广州1人,共27人。这些会士均因耶稣会的解散而被还为俗人”。[21](P321-322)至此,随着传播主体耶稣会的解散,近代西方科技输入中国亦告一段落。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对比,我们认为第一阶段时间终点划分应该以1773年,即在华耶稣会奉教皇签署通谕而解散的时间比较合理,而非教案或康雍乾三朝禁教的发生时间。
(二)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第二阶段的起点、终点
本节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根据传播主体传教士的再来,确定西方科学输入的第二阶段的起点;第二,探讨把中国科学体制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节点作为近代西方科学输入第二阶段终点的合理性,确定第二阶段的终点。
1.第二阶段的起点
关于近代西方科学输入的第二阶段的起点,我们仍坚持划分原则,应与历史划界和特定事件相联系的史学习惯相合原则,根据传播者所引进的知识体系、内容,及对中国传统科学体系的冲击所引起的渐变来区分。
第二阶段的起点在某一时期而未给出具体时间点的有以下几种说法。如张荫麟先生认为“第二期始于清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间之讲求洋务”,即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开始。李恩民认为,“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社会的某些领域,主要是部分生产行业,初步采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西方的应用科学和部分基础科学的理论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出现了一些新的科学技术概念和观念。”“洋务运动可称为科技近代化的先声”。[22]宝成关先生认为,由于洋务运动使中国具备了经济和人才两方面的条件,从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开始系统地输入中国。他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大量输入,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的大量输入,还是自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的。[23]张荫麟、李恩民和宝成关三位学者,把洋务运动时期作为近代西方科学再次输入的起始点的大致时期判断,是以西方科学对于中国科学近代化形成或近代自然科学的系统输入为标准的。他们的研究成果是科学而合理的,给西方科学二次输入的分期提供了重要依据。
具体第二阶段以何时为起始点,我们还是以传播主体的活动足迹为线索。根据史料记述,晚清以来,传教士复来是从马礼逊开始的。1807年(嘉庆十二年)英国新教伦敦会马礼逊牧师于5月12日在纽约搭乘美国商船“三叉戟”号,经近四个月的海上航行,于9月8日抵达中国广州。“他的到来,标志着基督新教传华的开始。”[21]来华之后,马礼逊等出版西书、报刊,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畲了解世界情况的重要资源,所创办的教会学校,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亦开始了传教士在华人中进行教育活动的历史。熊月之先生对马礼逊来华之后产生的影响,做出的贡献做了深入研究,评价认为马礼逊来华“是一个历史的开端,近代西学历史上的许多第一,都是从这里开始的”。[24]需要指出的是,熊月之先生把1811年即马礼逊来华四年后,作为晚清的西方近代科学的输入时间起点,熊先生判断的依据是“以当年马礼逊在广州的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序幕的”。[24]诚然,从传播主体出版作品的时间角度判断肯定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换个角度,如果以历史人物活动的标志性事件作为判断标准,那么把马礼逊来华的1807年作为第二阶段的起始点亦是合乎情理的。从遵循科学史划分的习惯出发,也为保持与第一阶段判断依据以利玛窦来华时间为起始点的一致性,这里我们把马礼逊1807年来华作为再一个近代西方科学的输入历史时期到来的标志,也尝试把这一时间作为再一个历史时期的起点和开端。
2.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第二阶段的终点
关于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第二阶段终点如何确定,我们认为,在考虑传播主体的活动在科学输入分期中的作用时,还应考虑科学体制转换情况,因为科学体制转换必然导致科学型态转换。因此,我们在划分科学输入分期时,必须考虑如果出现导致中国科学型态转换的明显标志历史事件,则把这一历史转折时间点作为科学输入终点的适当合理性。如现代科学体制建立导致中国从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现代科学体制建立是转折节点。体制化是指某种社会事业形成相应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向现代科学技术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制化的完成。”[6]考察中国科学发展历史,我们发现,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制转换的标志历史事件,至此以后,中国科学型态发生了质的转变,即由近代传统科学转向现代科学。张祖林教授把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称之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制化完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从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变的重要转折点”。[6]随着中国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体制的转折,近代西方科学即从此进入了由近代到现代的中西方科学交流。现代科学体制的建立,亦即意味着近代西方科学输入的结束。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把“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时间1928年,划分为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第二阶段之终点是适当的,也是合理的。
四、简短的结语
通过考察,文中尝试提出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两个重要阶段:1582-1775年为第一阶段;1807-1928年为第二阶段。即是从利玛窦来华(1582年)到耶酥会奉教宗颁谕正式解散(1775年)为第一阶段,以马礼逊(1807年)来华到中央研究院1928年成立为第二阶段。正如科学史的划分,对科学传播史的分期亦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它不同于匠人手中锯斧之于木料,一刀两断,互无牵连。科学的传播与接受是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东西方科学的交流更是经历了碰撞、融合和会通,科学的内化在时间上有一个延递期,因此,即便我们做了起止的划分,但科学的传播、消化与吸收其延递性依然进行,所谓起与止的划分只不过是相对于高峰时期而言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