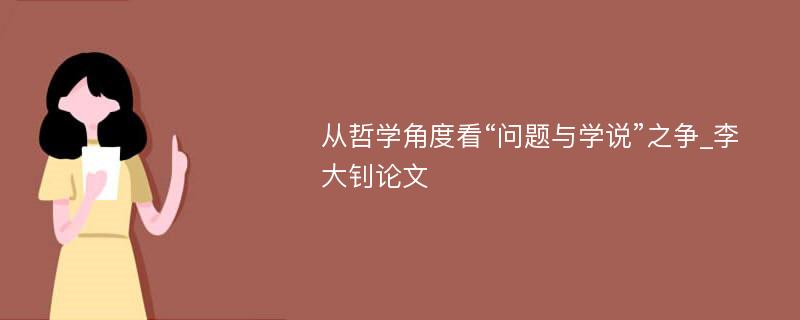
从哲学观点看“问题与主义”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哲学论文,观点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迄今已近一个世纪。从该争论的规模上讲,远比不上同时期的其他一些争论,如中西文化之争或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但其影响却并不比同时期的其他思想争论为小,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更为深远,现代中国思想史一般都会提到它,直到上世纪90年代,它仍以新的形式被人提出和争论。 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争论都是从政治上来理解和评价的,对“问题与主义”之争,尤其如此。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通史著作之所以大多提到它,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①“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一次不可调和的斗争。”②尽管这种未必符合事实的说法近年来得到一定的纠正③,但人们仍然认为这场争论事关“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以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④;事关用什么主义和方法来改造中国和救中国的问题。有意思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这么认为。⑤但对于这场争论本身的理论质量或理论问题,却如同在对待其他现代思想史上的争论一样,很少予以注意。这就使得我们对这场争论的反思有很大缺陷,未能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教训和理论教训,以至于在新的条件下,仍有可能不断重蹈前人的覆辙。为此,本文着重从哲学上考察这场争论,反思其中包含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而对可能涉及的政治是非悬而不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由胡适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引起的。胡适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引起这么一场争论,是因为它的确触及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时弊,即空谈、奢谈主义成风。如时人周德之后来在1926年所描述的:“自从‘主义’二字来到中国之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国民,是迷信‘主义’的国民。”⑥学生教授,军阀政客,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以谈“主义”为尚。 这也难怪。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现象就是以西学为神圣,以洋人为帝天。“主义”者,当然非吾家故物,乃国人心中“西学”之简称与浓缩,一谈“主义”,身价陡增,故热衷新潮者无人不谈“主义”,即便与时俱进,浑水摸鱼者也大谈“主义”,五四“新青年”之健者甚至说:“没主义的不是人。”“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⑦说此话的人也许没有想过,仅仅标榜一个不求甚解的主义也是一种“见风倒”,只不过是见主义风倒而已。 但促使胡适写他那篇引起争论文章的,却不是人们对主义的盲目崇拜,而是他觉得人们以对主义的空谈代替了对具体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他的目的不在思想文化上,而在政治上。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这篇文章不是思想文化评论,而是政论。⑧而参与争论的其他人(蓝公武、李大钊等),立论显然也更多关心的是政治问题,而非单纯思想文化问题,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但这不等于我们不能从更为普遍的哲学层面去反思这场争论。⑨ 平心而论,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并不错。空谈误国,是中国人的传统想法,倒不一定非要算在实验主义的名下。只不过现代人不是如东晋或明末士人那样空谈性理,而是换成空谈主义了。受过实用主义熏陶的胡适,向来主张“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⑩《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此并无进一步的申论,只是说“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11)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论述“多研究些问题”,而在主张“少谈些主义”。 为何要“少谈些主义”?理由有三。1.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2.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于事无补。3.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危险,容易被坏人利用。(12)不难看出,仅凭这三条理由,不足以证明要“少谈些主义”。因为谈“主义”未必一定是“空谈主义”,世界上谈主义的人甚多,未必都是“空谈”。即便中国人谈主义多为空谈,改为实谈即可,为何一定要“少谈”?逻辑上不太讲得通。这只能表明胡适本人的确对谈论主义没有兴趣,虽然不敢贸然完全否定主义的价值,但却真想限制主义的谈论。 然而,放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下,胡适的主张基本是正确的。中国人的确是满足于谈论各种主义,却很少深入研究自己热衷的主义。其次,中国人热衷主义是因为把主义当作包治百病的良药,而不顾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也就是国情,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指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13)的确是切中要害。至于说空谈主义会造成被人假借主义的名义做害人之事,自然也是对的。 可是,胡适的这些正确的想法,并非他个人的独到之见,实乃当时各派人物的共识。根据罗志田的研究,参与“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各方分歧并非后人想象的那么巨大,相反,他们有不少共同之处,“比较接近的大致有两点:一是中国必须借重西方的主义或学理,但却不能照搬,尤其是不能照搬资本主义;二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就是民生问题”。(14)不仅论战各方是如此,即便他们的共同敌人——主导当时北京政局的安福系政客——也是如此。(15)正因为如此,胡适才要在其文章中指名道姓与王揖唐辈划清界线。 近代中国危机深重,国势危如累卵,社会破败,民生凋敝,一派末世景象。在此情况下,要紧的是先解燃眉之急,其他以后再说。一切深入研究和思考都被视为迂阔不切实际,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是也。严复曾要孙中山从教育着手来救中国,孙的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16)很能说明当时大部分先进人士的心态——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思潮大行其道,解决现实问题成为人们行为与思想的绝对命令,除了少数文化保守主义者,莫敢撄其锋。既如此,胡适再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岂非多余? 不然。近代新派人物,或不甘被人称为“守旧”的人物,其思维再怎么功利或实用,总要打着一定外来“主义”的旗号,外来的“主义”是政治正确性与现代性的标记或证书,不能没有,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但是以主义作为政治正确性的保证的做法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言论的根据,完全不顾其产生的特殊性和其效用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把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知引证西人如何说,学问停留在书本上,从而导致第二个问题,即不去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以为只要用西式的“诗云子曰”代替传统的“诗云子曰”就能解决中国问题。胡适因此提倡“多研究些问题”,确切说,应该是“多研究些具体问题”,不为无见。 正因为如此,胡适的观点甚至得到陈独秀这样的人的支持。陈独秀在胡适文章发表的第二年,即1920年,便写文章进一步发挥胡适的观点:“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17)又对广州青年说:“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疑应为“作”)逋逃薮安乐窝。”(18)身为革命家的陈独秀同样觉得不能空谈主义,而要研究具体问题。 胡适的问题不在这里,不在提倡“多研究些问题”,更不在反对不顾中国实际,惟洋是从,流于纸上教条;而在他对主义和主义与问题关系之认识,与之争论者也都因此而提出质疑。 在西文中,“ism”(主义)可以指一个行动、一个过程或结果,如criticism,terrorism;也可以指一种状态或情况,如paganism;当然也可以指一种学说、一种体系,或一套原理和实践,如socialism,以及一种行为或特质,如heroism。但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主义”一般指某种学说、理论、哲学或意识形态。胡适及其与之争论者便是在此意义上理解“主义”这个术语的。事实上,胡适是把“主义”与“学说”、“学理”互换使用的。他从杜威那里接受了其工具主义的立场,把一切思想视为对付外在环境、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他并不认为相对具体问题而言,主义和学说是完全不必要的,他也并非主张人们不要去研究学理,他明确声明:“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19) 但是,归根结底,学理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20),这显然是在杜威工具主义思想影响下提出的一种观点。杜威的工具主义是一种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与传统科学实在论对立的方法论立场。它的主要观点是:概念和理论只是有用的工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是真还是假,或它们是否正确描绘了实在,工具主义否认我们可以评估理论的真理性;概念和理论的价值要由它们说明和预见现象的有效性来衡量。观念和理论既然是工具,是行动的指导,它们的有效与否就由实际解决问题是否成功来决定。 对于急功近利的人来说,工具主义的确非常有吸引力。它不问理论的真假,只问用它来指导行动是否成功,或用它是否解决问题。但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对于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例如,对于粮食短缺,可以用向国外购粮来解决,也可以用发展农业来解决。这两种解决都有效,但指导它们的观念或理论却是截然不同的。另外,很可能不同的人对于“有效”与“成功”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同的人对作为工具的概念和理论是否有效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对于是否只有某种主义才能救中国,人们从未达到过完全一致。另外,工具主义的立场就像任何相对主义的立场一样,是无法彻底贯彻的。如果工具主义用自己的立场来对待自己,它自己就会被否定,因为它既不能解释和预见各种现象,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工具主义只能严格限制在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范围,方有一定意义。 然而,胡适对于工具主义恐怕主要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并无深入的认识。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写道:“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21)又说学理是“材料”,“主义”是“参考资料”。(22)这首先在表述上就有问题。中国人一般不会认为“工具”就是“材料”或“参考资料”。当然,胡适很可能就是把“工具”理解为“材料”,这才能说:“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23)其次,对于杜威来说,工具主义是一个针对传统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主张,它主要是说明观念与理论在科学探究中的作用,具体而言,是强调它们解释现象和预见现象的效用。工具主义不是一种实践哲学的立场,它并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它不能成为实践哲学的原则。第三,杜威从来不认为观念和理论提供了解决具体问题的答案,而是把它们视为有待证实的假设。但胡适却认为它们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没有学理,就无法解决问题,“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24)如果这样,学理或主义就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没有它们,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那么胡适的主张就应该是:“先研究主义,再解决问题。”第四,也因此,他文章最后的结论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只有有了学理,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25),不就是要去研究学理吗?研究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解决法”终究不是一回事啊! 胡适文章处理的问题十分重要,但他的思维与表述却问题多多,因而别人的质疑与论辩是可以想见的。首先发难的是蓝公武。在日本学哲学的蓝公武的哲学思维水平显然高于胡适,这首先表现在他对问题的分析能力上。在他看来,要谈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先要分别分析两者各自的性质。他首先讨论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他认为有三个原因。首先是社会生活遇着了困难,这又表现为三种情形:旧制度与新理想的冲突;新生活与旧事物的冲突;社会中有扰乱迫害的事实发生。其次是因实际利害。最后是主观的反省。(26) 从蓝公武对问题起因的分析来看,他这里讲的“问题”与胡适一样,限于社会问题。他关于产生问题三个原因的分析,也无大错。只有在讲主观反省时,却是近代流行思路:中国人靠自己是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的,只有输入西方思想后,有了比较,方有反省。(27)这就过于武断了,黄宗羲并不知道西方思想,但对于“专制君主的毒害”,他却真“觉他不合理”。但问题起于反省,没有反省就没有问题,而反省又靠输入新的主义,因此,要研究问题,不能不先讲主义。这是蓝公武对问题起因分析隐含的逻辑结论。 但蓝公武没有直接这么说,而是进一步区分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提出抽象问题比具体问题更为重要,以此为主义的重要性铺路。但蓝公武对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的区分,不为无见。他所谓的抽象问题,并非指像某些哲学问题那样的狭义的抽象问题,而是指构成社会问题的价值理念的问题,只是他把这类问题叫做“共通的问题”:“凡是革命的问题,一定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点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问题,才能发生效力。”(28)“譬如选举权及自治权的问题,在起初的时候,决不是他内容如何的问题,一定是正当不正当及权利义务的理论问题。”(29)“古今无量数的人,为苦痛压迫的牺牲,因为这习惯的桎梏,宛转就死,尚不知其所以然,并没有人把他提出来做个问题。必定等到有少数天才有识的人,把他提作问题,加以种种理论上的鼓吹,然后才成一个共通的问题。”(30)他的结论是:先有抽象问题,后有具体问题;抽象问题比具体问题更重要。的确,没有抽象的价值理念,胡适文章中提到的卖淫卖官卖国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有有了人人都享有基本生活权利的概念,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才成其为问题。这是蓝公武关于问题的思路。 接着,蓝公武开始分析什么是“主义”。他认为“主义”主要是一种理想,而非方法:“世间有许多极有力量的主义,在他发生的时候,即为一种理想,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信仰这主义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并不考究他的实行方法。即如从具体方法变成主义的,也决不是单依着抽象方法便能构成,尚须经过理想的洗练炮制,改造成的。故理想乃主义的最要部分。一种主张能成主义与否,也全靠这点。”(31)蓝公武的这个观点,不无问题。有些主义,的确可以看作是“理想”,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但大部分主义(作为理论或学说)并非“理想”,如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结构主义、相对主义、现实主义,等等。还须指出的是,蓝公武对“理想”的理解,不同于一般的理解。“理想”一般是指人们寻求实现的某种完美状态。但蓝公武由于把“主义”和“理想”混为一谈,他理解的“理想”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是态度”。(32)这样,他实际上抽去了“主义”应有的“学理”成分。 不仅如此,蓝公武还否认主义与方法有必然的关系,“主义并不一定含着实行的方法,那实行的方法,也并不是一定要从主义中推演出来的”。(33)“故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间虽有联属的关系,却不是必然不可分离的。”(34)这里蓝公武讲的“主义”,显然是政治上的“主义”,即政治意识形态,而非一般的主义了。但我们知道,种种政治的主义,很少不含有一定的实行方法,相反,政治上的主义一定会包含其特有的实行方法,这些方法构成了它们的特殊内容和特征。例如,自由主义,总是会主张普选制和多党民主制;而社会主义,也总是会主张一定的国有化政策。而法西斯主义,总是采取个人独裁的统治方法。这些不同的实行方法对于相应的政治上的主义来说是必然的,人们往往就根据这些方法来判断和识别各种主义。否认主义与方法有必然联系,实际上抽空了主义,使它们变成空洞的招牌与口号,的确会产生胡适担心的情况,即主义变成政客用来骗人的抽象名词和口头禅,而无法“成为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 蓝公武是相信启蒙的,相信人们经过启蒙有了一定的觉悟与反省,然后才会有问题意识:“故吾们要提出一种具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必定先要鼓吹这问题的意义,以及理论上根据,引起一般人的反省,使成了问题,才能采纳吾们的方法。”(35)“问题的意义以及理论上的根据”当然不是方法,而是一定主义对问题的解释和该主义的“学理”或理据,这些显然不是蓝公武的“理想”概念所能涵盖的。而没有这些,“理想”除了是抽象名词和口头禅外,还能是什么?但蓝公武错误地认为,抽象性越大,涵盖力也越大,“归依的人数自然愈增多”。(36)但抽象不等于没有规定和空洞,这在哲学上是常识。没有规定,的确如胡适说的,王揖唐和胡、蓝都可以谈社会主义,但“用同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37)没有基本的规定,包括方法的规定,主义便失去了意义。 也许蓝公武自己觉得仅仅把主义说成是“理想”不免空洞,因而后来在进一步说明问题和主义的关系时作了一些补充。但这些补充刚好暴露了他对于主义的规定无法自圆其说。一是“主义是方法的标准趋向和态度”。(38)但他在前面刚说过:“一个主义,可以有种种的实行方法,甚至可以互相冲突,绝不相容。”(39)那么我们要问:一个主义如何能是种种互相冲突、绝不相容的方法的“标准趋向和态度”呢?二是主义是问题最重要的中心,“原为解决方法的标准,抽象出来,推行到他部分或是他种问题去,即是主义。”(40)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的中心,如何能抽象出来推行到他种问题去? 蓝公武的论辩文章的根本目的,不在澄清“问题”与“主义”,而是要论证,在中国这样一个“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自身不能发生新理想,则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41)在中国,“问题是全靠主义制造成的”。(42)这个思路一直支配着许多有“启蒙”情节的人,翻译、输入就是启蒙,就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至于外来不外来、适用不适用,那是次要的问题。在蓝公武这样的启蒙主义者看来,即便不甚适用者,“有益处也并非绝无。取长去短,以补他种主义之不足,亦未尝无效力可言。……若是概括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独断”。(43)蓝氏在今天,仍有不少同道。 但蓝氏最后的结论,却并不错到哪里去:要解决问题,就要先研究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44)没有理论,也可以解决问题,但往往是并不高明的解决。还必须说的是,“研究”决不等于“空谈”,“研究”必须包括对研究对象的审视和批判。可惜这些都不在蓝公武考虑之列。 相比之下,李大钊对问题和主义的思考要更为深入。在对主义与问题关系的理解上,李大钊比较接近蓝公武。他同样认为人们只有对现实不满,才能产生种种问题;而要对社会现实不满,先要有一个不满的根据,即“先要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45)这里说的“理想主义”,其实就是一套价值理念。并且,这套价值理念必须被多数人接受,才会产生社会运动。李大钊着眼的已不是个别孤立的社会问题,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或卖淫问题,而是创造一个理想社会的社会运动。在此前提下,“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46)这当然不是说什么主义都可以,而是说必须是具有理想色彩的主义才能产生改造社会的运动,才是合理的。 李大钊一方面像蓝公武那样强调主义的理想性,另一方面又赞同胡适的工具论主义观:“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47)这自然是不对的,主义决不是可以拿来就用的工具,即便是工具,也要根据目的来选择适当的,要砍柴就不能用锤子。而李大钊这里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只要能“用以实际的运动”,工具适用与否不成问题。的确有点胡适说的“目的热”和“方法盲”。这个毛病,在现代中国却是一种流行病。 像蓝公武一样,李大钊也认为只有先宣传主义,才能避免假冒。恰恰因为有假冒,才要先去宣传主义。但他并不认为宣传主义与研究实际问题是不相容的,相反,他认为两者可以同时进行。宣传主义并不必然导致放弃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但是李大钊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没有看到宣传主义的人首先得研究主义,研究主义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主义的学理层面,他和蓝公武都没有提及,这也许不是偶然的。胡适虽然提及,但也只是说说而已。中国的启蒙者总觉得自己不需要先被启蒙,他们都是先知先觉者,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只是以先觉觉后觉:“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它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48) 我们看到,李大钊完全同意并接受胡适将主义理解为“工具”和“材料”;所不同的是,他论述的重心是发动群众,形成社会运动,而非研究具体问题。对他来说,掌握工具就能解决问题;而在胡适看来,主义固然能帮我们解决问题,但还是先要研究问题,主义或学理首先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工具。这个区别不可忽略。不研究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对问题的正确解决是建立在对问题的正确研究基础上的。 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最根本的分歧在中国的问题能否“根本解决”上。从胡适的文章看,他是主张脚踏实地,对于具体问题一个个加以研究和解决。他认为不可能通过空谈某种主义一下子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解决。这应该说是不错的。有许多人说他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其实他是反对空谈一切主义。因为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当时主张根本解决的人相当普遍,在他们中间,也有反马克思主义者。(49) 根本解决的想法与近代中国人相信革命有关,总认为革命可以一下子改天换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近代中国,革命远比改良更有吸引力,这是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如此。李大钊在他的文章中就举俄国革命的例子来说明根本解决之可行和有效,当然,由于唯物史观的影响,他对革命的着眼点主要放在经济基础的变动上。因此,他心目中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会改变经济组织,“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50)但是,历史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站在“根本解决”论一边。单纯经济组织的变动并不能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并且,它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但李大钊决不是一个独断论者,相反,他即使在写《再论问题与主义》时,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并保证“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51)并且说到做到,后来写了《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被裁的士兵》、《归国的工人》、《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讨论具体的社会问题。但即使在这么做时,他也要比一般的人深刻,他能从“时代文明与社会制度的缺陷”上来看问题,而不是就事论事来谈问题。因此,“根本解决”在他那里并不仅仅是全部解决的意思,还有从问题的根本处入手的意思,这是他高于侪辈的地方。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根本处”是社会制度,不根本改变社会制度,问题就无法得到彻底解决。但不管怎么说,根本解决还是一种把主义当万能灵药的想法。反之亦然。 胡适在读了蓝公武和李大钊的论辩文章后,连续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和主义》作答。首先,他并不认为蓝、李把主义理解为“理想”与他的看法有什么冲突。他说,他之所以认为主义是“救时的具体主张”是就主义初起时说的,任何主义产生时都是一种救时的主张。这是没有真正领会蓝、李为何要把主义说成是“理想”。其实,蓝、李绝对是把主义当做“救时的具体主张”的。在现代中国,不这样理解主义的人少之又少。蓝公武和李大钊把主义理解为“理想”,是希望救国不能过于功利,而也还要有某种原则立场,用蓝公武的话说,就是“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能背离这种标准或趋向。李大钊明确看到了主义的价值内涵,对于主义的理解可以不尽相同,但背离其根本的价值内涵,就不是该主义了。这的确是主张工具主义观的胡适见不到的。 胡适见不到主义具有理想的方面,是因为他对理想的理解都与蓝、李不同。他不是像一般人那样把理想理解为一种价值意义上追求的完美境地和目标,而是理解为假设,他把它叫作“想象”(和常人的用法不一样):“譬如一个科学家,遇着一个困难的问题,他脑子里推想出几种解决方法,又把每种假设的解决所涵的结果,一一想象出来,这都是理想的。”(52)他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最后的一段话为例:“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算不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53)这段话本身从杜威的思想五步法脱胎而来且不说,胡适理解的“理想”与蓝、李二人讲的“理想”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也许的确没有他们讲的那个“理想”的概念。所以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都是“具体的主张”。(54) 他也反对蓝公武提出的问题的抽象性,他否认有抽象的问题:“凡是能成问题的问题,无论范围大小,都是具体的,决不是抽象的。”(55)如果我们不管“问题与主义”所讲的问题主要是像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这样的社会问题的话,我们真要怀疑胡适是否学过哲学。但即便如此,胡适的观点也是错误的。问题是人思想的产物,而思想就离不开一定的抽象,此其一。例如,人力车夫日子过不下去,这只是一个事实,但我们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或从社会公正的立场去思考这个事实,它就成了一个问题。否则它永远是一个人们熟视无睹的事实。其次,即便是社会问题,也会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例如,男女平等的问题、文化多元的问题、宗教宽容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像赈济灾民那样,采取某个具体措施就能解决的。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理解为像解决人力车夫生计问题那样的简单具体问题的肤浅问题观,不但使得我们对于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严重忽略,更使我们无法产生有深度的思想和理论。百年中国,不乏实干家,却缺少理论家。 胡适对蓝、李二人最厉害的反批评就是说他们都犯了“目的热”和“方法盲”的毛病。(56)抽象谈主义,不管中国的特殊问题和特殊情况,这是“目的热”;相应地,不顾具体情况,把主义作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拿来就用,这叫“方法盲”。撇开蓝、李二人的具体主张不谈,胡适对“目的热”和“方法盲”的批评基本是正确的。“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试看现今世界上多少黑暗无人道的制度,哪一件不是全靠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替他做护法门神的?”(57)衡诸历史,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对于当时的人们,也是一个非常警策的提醒。但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深入研究主义和学理,这样才能“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58)没有对主义和学理的深入研究,它们永远只是教条,不可能成为启发心思的工具。即便我们把它们当作“一些假设的见解,”(59)它们也只是一些抽象名词而已。 也许是不愿让别人觉得他不重视主义和学理,胡适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主要谈论主义和学说的输入。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不是谈研究学说,而是说“输入学说”,这说明他觉得学说是现成的,只要输入就行,不需要研究。他谈了三点意见。一是“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都是当时的某种不满意的情形所发生的”。(60)因此在输入学说时要注意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二是“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61)三是“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每种学说已经发生的效果”。(62)这三条意见真可谓卑之无甚高论,但他之所以郑重其事提出,说明当时很多人在“输入学说”时连这也做不到。胡适只字不提对各种输入的学说要深入研究,也许他根本就不觉得有提出的必要。中国近代以来输入的学说不可谓少,可几乎没有几个是得到深入研究的,这与只管输入、不重视研究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启蒙者缺乏苏格拉底“我知我之不知”的智慧,总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缺乏研究的人输入他们缺乏研究的学说,后果不问可知。之所以今日人们还忙于输入,与此传统有莫大关系。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虽然规模不大,却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它非常典型地让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的缺失,论辩各方(本文只限于胡适、蓝公武和李大钊)暴露出的一些共同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在中国思想界完全消失。首先是哲学修养都比较缺乏,这场争论各方论辩方式都有可议之处,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概念定义的能力,都有明显缺失。照牟宗三的说法,“在五四运动期间,哲学系最热门,大家都念哲学。……可是念哲学的人虽多,真正登堂入室入者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人哲学之堂奥”。(63)胡适与蓝公武也不例外,他们虽已不是学生,但都是从东西洋著名大学的哲学系毕业,可从他们的论辩文章中几乎难以看出他们的专业背景。相比之下,蓝公武要好一些,但其文章还是可以挑出不少论辩说理上的毛病。对哲学的不重视必然导致哲学思维水平不高;哲学思维水平不高,争论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成果。不是各讲各的,谁也不服谁,就是流于扯皮,甚至意气用事。“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是办不到了。 其次,对哲学没有兴趣一定会导致对理论和学理不重视,乃至没兴趣。这次论辩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论辩各方都没有将研究理论和学理作为自己的主要主张,最多虚与委蛇地说一下主义还是要研究的。这也难怪,“理论”一词本身就是外来的。古人并无“理论”的概念和意识。《北史·崔光韶传》说“光韶博学强辩,尤好理论,至于人伦名教,得失之间,榷而论之,不以一毫假物”。这里的“理论”是指“据理论辩”的行为,不是我们现代作为概念、原理之体系意义上的理论。“理论”在中国古代还有“追究”(64)、“道理、理由”(65)的意思,但都与现在那个实际来自西方的理论概念有明显不同。近代人讲学理,也只是讲讲而已,真正研究学理的成果不是很多。这使得近代中国主义满天飞,却特别缺乏理论。胡适看到了各种流行主义的空洞,却以为是因为没有研究具体问题,而没有看到,没有学理支撑的主义,才是抽象名词。这样的空洞主义,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或“参考资料”是极其危险的。 西方的理论概念(theory)来自古希腊文theorein,意为“观看”。理论是对事物全面、深入、思辨的“看”。没有理论的实践犹如盲人骑瞎马,很少可能达到自己要想达到的目标。所以西人恒认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6)就是秉承了这个传统。“理论”最基本的意思当然是思想、学说(学理)、说明,但一定是有系统的、全面的、合乎逻辑的特征。理论是众多个别与普遍命题的有机整体的系统。它不是对对象的纯粹描述,而是说明对象的理由,解释和理解对象。这对于我们认识对象的性质从而把握现象是必不可少的。理论既然是原理的体系,它当然是由一定的学理组成。而主义若不是空洞的抽象名词和意识形态教条,就一定都是某种理论,都有其学理在。 第三,由于对理论的重要性没有深刻的认识,当然对研究主义和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就无法很好把握。“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各方的论辩重心都放在对“主义”的不同理解上,都没有很好说明主义与具体问题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没有看到主义首先应该是一种理论,一种指导实践、包括指导研究具体问题的理论。他们都没有看到,没有赤裸裸的问题,问题之所以为问题,就因为它是我们对思考对象有一定的理解的产物。作为理论的主义,当然会支配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因此,同一个问题,不同主义的人的理解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例如,对于卖淫问题,文化保守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各自有各自的理解,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会很不一样。因此,可以说主义支配着问题的解决;主义的一般原则包含它的方法论原则。把主义视为单纯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材料”,完全无视了主义的决定意义。另一方面,把“主义”视为“理想”看到了主义对于解决问题方向性的指引,但没有看到主义对问题性质的理解和规定。虽然蓝公武也说主义与方法有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偶然而不是必然的,因为他说一个主义可以有互相冲突、决不相容的方法。因此,主义与方法的关系还是没有说清楚。李大钊接受胡适对主义“工具”的说法,因而也和他一样把主义与问题的复杂关系付之阙如,没有正面处理。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最后没有留下什么理论成果,因为这场争论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许多争论一样,本身的学理含量不高,而之所以学理含量不高,是因为近代中国对于主义的确是工具主义的心态,能拿来用就行,学理上不甚讲究,大概觉得没有必要。结果邓小平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其他在近代中国流行过的各种主义就更不用说了。但没有对理论的参透和思考,实践难免会迷失方向。对待具体问题采取完全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态度,也可以解决问题,但后患无穷。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已近百年,但这场争论所针对的弊病与问题和它本身暴露出来的缺陷与问题,从未在中国思想界消失过。空谈主义和抽象名词照样大行其道,自觉掌握万能灵药者依然不少。学理仍然是说的人甚多,研究者绝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百年将过,中华已无救亡之迫,若再不能静下心来研究和思考,而使后人复哀我们,岂非太不长进了吗? ①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0页。 ②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 ③罗志田:《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1~64页。 ④“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⑤林毓生:《“问题与主义”论辩的历史意义》,《二十一世纪》第8期(1991年12月)。 ⑥周德之:《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晨报副刊》1926年11月4日。 ⑦傅斯年:《心气薄弱之中国人》,《新潮》1卷2号(1919年2月),第343页。 ⑧胡适后来对自己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有如下交代:“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4页)。 ⑨萧功秦便指出过“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有“超越政治的意义”(氏:《严复与胡适对“主义”与“问题”的思考》,见沈寂主编:《胡适研究》第1辑,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79页。 ⑩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11)(12)(13)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2、249~250、249~250页。 (14)(15)罗志田:《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第69、70~81页。 (16)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50页。 (17)陈独秀:《随感录·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18)陈独秀:《敬告广州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册,第286页。 (19)(20)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第252、252页。 (21)(22)(23)(24)(25)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第252、252、252、252、252页。 (26)(27)(28)蓝公武:《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第253、253~254、254~255页。 (29)(30)(31)(32)(33)(34)(35)(36)(38)(39)《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第255、255、256、256、256、256、254、257、258、256页。 (37)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第250页。 (40)(41)(42)(43)(44)武:《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第258、258~259、258、260、260页。 (45)(46)(47)(48)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第261、262、262、265页。 (49)罗志田:《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第92~117页。 (50)(51)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第265、262页。 (52)(53)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第267、268页。 (54)(55)(56)(57)(58)(59)(60)(61)(62)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第269、270、272、273、274、274、274、275、276页。 (63)牟宗三:《谈民国以来的大学哲学系》,《时代与感受》,台北:台湾鹅湖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 (64)《英烈传》第三十一回:“那周颠日日在帐中闲耍,太祖也不十分理论。”此处“理论”,便为“追究”之义。 (65)曾瑞《留鞋记》第三折:“你既是个女子,怎生不守闺门之训?这绣鞋儿却揣在郭华怀中,有何理论?”此处“理论”便是“道理、理由”的意思。 (66)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