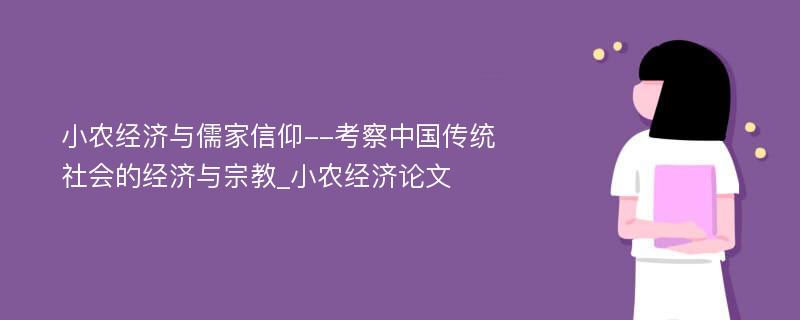
小农经济与儒家信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与宗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小农经济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宗教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B920;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2-0079-07
当韦伯(Max Webber)论及中国宗教时,我们会发现颇为耐人寻味之处:这部从书名上来看是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著作开篇却撇开宗教不谈,先谈经济问题。这是为何?
进而具体到中国的经济和宗教,我们又会发现种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中国历来是小农经济为特征;中国在19世纪前商品经济发达不亚于欧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①(《论语·颜渊》)“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彖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特征究竟如何,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又扮演何种角色,为何关于二者会存在截然相反的论断?以上诸问题构成了本文论题的出发点。
本文将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宗教特征入手,理解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路径中宗教信仰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特征与宗教特征
(一)经济特征
“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绩,男人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2](P1)这段话既是对一种理想经济形态的向往,也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现实经济秩序的侧面写照:农业经济。
《易·系辞传》有言: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据此,吕思勉先生认为,“我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之基,肇于此矣”。[3](P2)不过,农业经济真正成为中国的主体经济形态,则迟至两汉。战国时期虽多有重农思想,②但自秦商鞅变法后,始将农本思想切实执行。汉承秦法,从汉代至近世,精耕农业遂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特色,历两千年不变。[4](P404)
然而,承认农业经济为一种主体经济形态,并不就此否认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性。正如赵冈与陈钟毅所推测的,独立的小农户经济单位很难真正做到自给自足。[5](P429)《易·系辞传》在述及农业为本之后紧接下来就提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这就表明中国的农业经济自古以来就需要商品经济与市场贸易相辅助。春秋时期商人虽属家臣身份,但已势力渐起。③及至战国,更有史家论言,“始终存在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即发展出一种主要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经济”。[7](P3)汉时的重农抑商促成了一套围绕着精耕农业的农业市场经济系统,这一市场经济系统以农舍工业为商品生产基地,依托于精耕细作的小规模集约经济,通过逐级集散市场网络,依赖相应的道路系统,形成市场贸易的经济共同体。[7](P148-149)[8](P81-85)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主体经济形态是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小农经济。
但是,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存在,只要有市场发展的空间,“斯密动态”(the Smithian Dynamics)就一定存在。④因此,尽管中国的商业与市场贸易一直在农业经济体制下艰难而顽强地发展,在历经唐、宋、元时期数次兴衰之后,到明朝中国的商业经济又再度进入了繁荣时期。明中期以后,中国俨然已站在了现代经济制度的门槛之前。韦伯从两方面——货币和人口——切入中国的经济问题,其发现,“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之特性来说,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在‘物质的’条件上并无重大的差别”。[1](P344)⑤或许韦伯得出这一结论就史料考察上来说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其他的历史学者,如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以彭慕兰、王国斌、李中清、王丰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the California School)以及国内经济史学家李伯重等,在新的史料证据下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世纪以前,无论是从人口增长的马尔萨斯陷阱(the Malthusian trap)方面来看,[10](P401)还是从整体的生活水平、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等方面考察,[11]抑或是就工业化发展情况、[12](P32-41)市场体系发展情况而言,[13]中国与西欧无太大差别。而最新的对于17至19世纪西欧与中国250个市场谷物价格的协整分析也发现,直到18世纪晚期,中国与西欧的市场总体运行情况是相当的。[14]
不过,所有这些关于近代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相似性的观点,都只是说明了当时二者之间经济绩效的相近,却并不能代表中国与欧洲处于相同的发展水平。远在19世纪之前,中国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道路。这条“内卷化增长”(involutional growth)的道路使得中国在19世纪达到了其经济、政治以及其他社会制度所允许的增长极限。中国经济站在了世界门槛之前,却无法迈过这道门槛。换句话说,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内生地从中国社会内部生发。这是为什么?
韦伯回答说,“基本上,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Gesinnung)。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Ethos)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最是阻碍的因素”。[1](P161-162)
(二)宗教特征
韦伯的回答把我们的视角转移到了社会意识层面,而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质集中体现在宗教信仰层面。
中国宗教无疑是最难把握的特征性事实,但为了本文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从两个问题着手尝试理解中国的宗教特征:其一,中国社会有没有宗教;其二,儒学是不是宗教。
首先是中国社会的宗教性问题,如果以西方基督教那种制度性宗教的观点来看,毫无疑问世俗性是中国社会的特征,因为既不存在宗教教义也不存在教会。[15](P5)但是要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确信中国社会不存在宗教在直觉上看来却又是不可能的,宗教现象弥漫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宗教场所的数量、功能、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宗教性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神学思想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必须确认中国社会的宗教性。[15](P6-20)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缺乏如西方社会那样的高级宗教——拥有系统的制度、教义和组织形式,但是分散性宗教⑥却遍及整个传统社会,其信仰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意识的基础。
然而如果细究中国社会诸宗教信仰,便会发现无论是佛、道等制度性宗教还是混杂的民间信仰都与儒家思想不无干系,这就使我们必须要面对第二个问题:儒学的宗教性。“儒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其为根本的中国制度——上至国家,下至家庭——奠定了建构原则并提供了关键性的行为价值”,[15](P244)这一点应当能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而在一个缺乏制度性的神学意识权威的社会中,任何占据社会文化关键地位的意识形态,都必定无可避免地会被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这或许就是儒家的宗教面向。因此,杨凤岗认为“西汉皇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改造成为基本具备了四个条件的准宗教(quasi-religion)而非完备宗教(fully developed religion)”,[16]儒家思想的担当者也就具有了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17](P2)
对以上两个问题的思考折射出中国宗教的主体特征:宗教地位的模糊性。由此中国宗教在制度演化的进程中非但未取得一种中心模式,反而呈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模式,“宗教普遍地通过分散性宗教的形式服务于世俗社会制度,来强化其组织。宗教通过将自身渗透入世俗社会制度之中,其神学、神明以及仪式从传统社会的制度结构得到支持……”[15](P340)
不过即便如此,作为中国主体的宗教承当精神,历史上儒家似乎也引致了一种与现代经济制度相当的精神。换句话说,传统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似乎也曾站在现代世界的门槛前。这就是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的主题。
韦伯从宗教伦理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发展所作的分析普遍影响了东西方学术界。但当有了东亚经济成长的经验之后,学术界也开始对韦伯所论述的儒家经济伦理问题提出疑问。余英时和杜维明等人便对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发展历史作出了重新思考并予以概念化。[18](P171)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篇长文中,余英时对韦伯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回应。其运用大量史料,从中唐的新禅宗“革命”,到宋时的新道教影响,进而是从韩愈开始至宋明理学的“新儒家”之发展历程,指出新儒家所受禅宗的影响以及儒家思想中所具有的超验世界观念和入世苦行。[19](P474-519)然后,余英时分析了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精神,指出商人儒家伦理中具有“勤”、“俭”等资本主义兴起所需之条件以及“理性化的”贾道。[19](P519-574)由此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业精神已有深刻的变化,其与中国传统宗教理论结合在一起,已有能力发展出现代性的经济制度,已走到了传统的边缘。[19](P577)
对于余英时的论断,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的商业精神不能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混同。⑦韦伯并不否认儒家思想中的商业精神:儒家伦理,是一种“功利的伦理”,“儒教产生了极具现代意味的需求与供给、投机与利润的理论”。[1](P229)但关键的问题是,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最后的论断就足以回应余英时的观点:“光是与‘营利欲’及对财富的重视相结合的冷静与俭约,是远不能代表和产生从近代经济里的职业人身上所发现到的‘资本主义精神’的。”[1](P332)
我们认为余英时仍然是沿着韦伯的理路探索中国社会文化中可资利用、发展出现代经济制度的资源。而且儒家思想中确实存有为现代经济制度正名的迹象,[20]特别是出现了如邱浚那样鲜明地主张自由贸易、协调市场功能与国家责任的观念。[21](P241-247)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发展出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制度与文化。然而显然这条道路并未走通,余英时最终把未能突破传统的原因归结到了政治体制上,“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有如天网地罗,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19](P578)
由此我们又重新回到韦伯的道路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与宗教的共同关联存在于一套特殊的政治体制上。
二、皇权制度下的宗教与经济
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宗教特征的概览式考察,我们会有一个直观的感觉:无论是经济还是宗教,在中国社会内部皆孕育出了相当高级的形式,却同时又包含着原始古老的成分。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同时具有“先进”与“落后”性质的制度,皆在现代世界面前止步。似乎,中国社会的经济与宗教都无形中受到某种强势力量的羁绊。
这种力量当属政治的力量,谢和耐研究中国历史,韦伯研究中国宗教,布迪(Derk Bodde)与莫里斯(Clarence Morris)研究中国法律,尽管领域不同却都发现政治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特征。[10](P25)[22](P7)自汉以来,中国就开始了政治至上的一元结构,因此,王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乃是皇权政体的法理基础、组织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统治权力运行方式”。[23](P2)中国政治权力早熟,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已使得经济与宗教皆属该权力运行系统中的一部分。
(一)皇权下的经济
我们在第一部分曾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主体经济形态是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小农经济。但是更确切的说法是皇权制度下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小农经济。如果没有皇权制度这一前提,中国的农业经济不会如此稳固,市场发展不会始终依附于土地,更有可能不会演变为一种“小农”形式的精耕农业。
如韦伯所言,“政府的军事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改弦易辙,决定了农业经济里的根本变迁”。[1](P113)国家对农业经济的控制,根据王国斌对明清时期的分析,表现在三个方面:(1)促进农业生产;(2)调节商业性分配,以达到各地内部经济的均一与地区之间的平衡;(3)通过移民使得人口与资源基础维持了相对平衡。[12](P16)在稳固农业的同时,工商业的控制就更是苛刻。中国2000年来工商业兴衰循环的关键因素就在于皇权制度。自汉武帝开始采取的禁榷制度以及“算缗”、“告缗”等抑商政策成为后来历代王朝控制工商业的范例,被屡屡效仿和采用。[24](P128-137)抑制工商业的原因就在于皇权制度本质上与自发扩展的经济秩序不相容。因为“商业活动创造的财富,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会成为一种由不受政治控制的商人集团所固定把持的资源,这是统治者不能容忍的”。[7](P3)既然商业经营之所得随时有遭受政府掠夺的风险,自然土地就变为最为可靠的资产,⑧“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如此一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自然只能依附于农业经济之上。
但是政治权力对于经济最严重的影响还是催生了一种“小农”经济形态,从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之不可能。从一般的经济理论上而言,只要私有土地制度存在,允许土地买卖,农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便会出现土地兼并,市场运作的力量不可能使农村长久地维持小农特征。然而中国的农业经济却数千年来始终保持小农特色。因为就基层权力控制而言,大地主是国家权力首先要侵犯的对象;[25](P30)就国家财政而言,小农经济确保了帝国税收。[26](P112)这样,从两汉限民田之论,到晋施户调式、魏行均田令,及至唐代的租庸调法,皇权始终致力于分散农业经济集聚。然而,“小农”是不可能演变为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经济模式,“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27](P8)现代经济制度在皇权经济下自然孰无可能。
(二)皇权下的宗教
自然,在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中,我们不会见到欧洲中世纪那样“上帝之城”的景象。相反,宗教沦落为皇权统治的工具,“专制政体迟早会成为唯一的主宰者,从而把宗教作为支撑自己权力工具来随意使用”。[28](P101)
欧洲从中世纪迈向近代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信仰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威,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发展的进程;而史景迁先生告诉我们,中国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更为有效地实现了权力的集中和对宗教信仰的控制,中国政府不可能允许与之比肩的权力中心存在。[29](P8)中国政治制度的早熟,理性的官僚体制先于高级宗教出现,遂掌控了古代社会原始宗教之发展趋势,这样宗教制度只能依照政治制度的发展模式而演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让西方人讶异的“鞭打城隍”的习俗。⑨城隍信仰是对世俗官僚体制的模仿,地方官员死后的亡灵担任城隍,世俗官员可以因为城隍是否灵验而鞭打城隍,世俗权威始终凌驾于宗教权威之上。
皇权制度对宗教的掌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宗教制度以及宗教教派的管理政策,二是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培养与扶植。前者主要表现在对祭祀等宗教活动以及佛教、道教等宗教教派的管理上。例如祭祀仪式有等级区分——“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祭祖的世代数目和身份地位有关。[30](P209)而宗教教派管理则一直都是礼部的重要职能,包括控制寺庙道观兴建,用度牒制度控制僧道数量等。但是后者则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宗教信仰所表达的神圣秩序,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正因为如此皇权必须掌控宗教,必须培养、扶植与皇权制度本身相适应的信仰:天命信仰与祖先崇拜。“天”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是政权合法性的象征,[15](P127)由天命信仰转化而来的世俗道德权威为皇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神圣基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天命信仰是政治理性化的产物,其意义主要是针对士人阶层而言的:正是由于政治之理性化促使中国宗教的理性化信仰。但正如韦伯所言,这种理性化是不彻底的。极具“现代”意义的理性信仰不可能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精神需要的一部分,对民众来说更为实际的信仰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其一方面联系着家族血缘,一方面则是鬼神信仰。一直以来,祖先崇拜都是中国宗教的基本形态,也是中国社会分散性宗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格鲁特(J.J.M.de Groot)称之为“中国人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核心的核心”。[31](P109)在中国,高级宗教——诸如佛教——的渗透并没有破坏这种原始信仰,相反承纳了祖先崇拜思想。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仍在于皇权的扶持。皇权不仅需要理性化的天命信仰支持,更需要一种原始信仰作为“中国平民大众惟一一份极具效力的大宪章(Magna Charta)”。[1](P243)
而儒家思想恰恰能够成为这种“理性”与“原始”兼备的信仰系统的载体。一方面,从天命信仰中发展而来“道统”观念,成为与君权的“治统”相平衡的唯一途径。[32](P1-31)另一方面,其同样承认原始信仰作为民风归化的手段,“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儒家重“事人”,但对原始信仰则持一种工具化的态度,理性信仰虽不能合乎原始信仰,但就社会统治而言,祖先崇拜也是必要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因此,对于民众而言,“民无信不立”,为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便是对我们在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悖谬的回答。
(三)皇权、经济与宗教
在理解了皇权制度对于中国经济与宗教的影响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与宗教为何呈现那种先进与落后并举的演化形态,也才有可能认识为何现代制度在中国社会迟迟未出现。在制度演化分析的框架下,皇权体制对于经济制度、宗教信仰演变的控制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皇权对国家经济的控制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管理方式,同时它也是建立在对国民的人身监控、对国家的思想和宗教等一切重要的社会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上的”。[23](P90)因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三方面表现出更为复杂的逻辑情态。
皇权、经济与宗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关联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之间的直接影响,即宗教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三者之间在制度型构、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联。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仪式”,宗教仪式往往附带政治和经济功能,而在传统社会,有些时候仪式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的重要性反而超越了宗教性质,但是宗教信仰的存在却能够促使相应的政治与经济功能得到发挥并进一步成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比如“礼制”、“庙会”等。另一类则是更为微妙也更为重要的间接影响,皇权、经济与宗教通过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之精神气质的塑造,进而形成整个社会制度演化的路径,例如韦伯的主题,宗教信仰对整个民族气质的形成。另一个典型的中国例子则是“捐赠”,根据卜正民的研究,捐赠这种具有浓厚宗教涵义的经济行为,在晚明社会中演变为一种对权力的追逐,[33](P211-217)成为士绅社会政治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因此,就制度分析而言,在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特性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对于政治和文化的依赖。例如“小农经济”、“祖先崇拜”与皇权制度三者之间就存在一种特有的发展模式。皇权对于原始信仰的培育促成祖先崇拜以及围绕家族观念而形成的地方宗族,宗族制度支撑了皇权体制在基层的维系,支持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宗族势力始终未能形成一股有效的经济集聚力量,相反始终在不断地分化。因为“祖先崇拜”的信仰维系的家族观念促使在宗族内部平等对待处于同一地位的家庭成员,这样分家析产就成为明以后一种普遍的继承制度。分家析产制度致使财产难以集中,维持着很高的结婚率,同时农村劳动力人口不会由于丧失财产而被转移到农村以外。这样,大量人口集聚在农村,分散了农村土地和资金的积累,强化了小农经济的运行。
在此,限于篇幅我们尚不可能对上述这些特征性事实详细分析,但是我们已经可以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基础。中国社会的经济模式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基于原始信仰的“礼物经济”模式。在人类学研究中,礼物交换曾是古代世界一种普遍的商品经济模式,而这种经济制度与原始信仰不可分离。在礼物交换中,商品作为一种物是与人身关系不可分离,因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信仰,支撑起礼物经济的整个法权基础。⑩同样,在中国交易模式中显而易见的“人格化”特征,与礼物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三、余论
从制度与文化的一般关系而言,作为社会文化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因素,宗教信仰必然成为一个社会制度的精神层面的拱顶石,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11)因为,现实制度倘若要行之有效,那么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下都无可避免地要以一种为社会文化意识所认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当宗教表达了社会中个人普遍遵循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共同的直觉上的伦理要求的时候,宗教与制度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必然的同构性:每一种社会制度都需要有一种因与其意见一致而相互结合的宗教信仰。(12)
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与宗教进行的粗浅梳理来看,尽管许多问题尚有待深入分析,但我们仍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特有的经济制度其背后蕴含着支持这一整套经济模式的文化和政治特征,这些特征深深地烙印在中国的传统之中,必然决定着中国现代制度之发展路径。
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曾经与西方世界相似。中国的历史越往上追溯,越能发现中国文化与西方的相似之处。[1](P314)[7](P3)[12](P80)这或许意味着西方世界现代化所走的道路或许很久以前就摆在中国面前,但是中国为什么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是否,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联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思虑历史是为了面对未来。现代经济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中国是否已经真正接受了现代经济制度,抑或是能够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另一种属于中国的现代经济体制?这仍然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现代的中国人,是否孕育出一种与现代经济制度相容相励的心态?
注释:
①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对于“信”的理解采取了不符规范的解释。我们仍然使用了韦伯的理解,即社会秩序需要依靠信仰维持。[1](P209)按照通常理解,“信”指的是对政府的“信赖”、“诚信”。但是如果我们应用西美尔(Georg Simmel)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和韦伯的“卡理斯玛”(Charisma)概念,那么很明显这里的“信”实是将皇权卡理斯玛与宗教信仰的卡理斯玛联系在了一起。
②例如《管子·治国》曰:……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③例如弦高犒秦师、郑桓公与商人互相盟誓以及子贡鬻财于曹、卫之间。[6](P244)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瞿同祖所引的这几例源自《史记》的例子。
④我们将“斯密动态”理解为市场扩展秩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即“市场交易源自分工,并会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则受市场规模大小的限制。市场扩大会加速和深化劳动分工”,[9]因此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成为经济成长的动力。
⑤出自杨庆堃为《中国的宗教》英译本所写的导论。
⑥这里“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我们采用杨庆堃的界定,参见[15](P294-295)。
⑦我们这里所言的“资本主义精神”,特指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阐述的涵义,指的是一种具有神圣伦理内涵的时代精神气质。
⑧当然这种可靠程度依然是相对而言的。中国的土地,尽管许多学者引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段话表明君主对土地拥有权利。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中国的土地观念并非严格的所有权概念,而是一种“占有”制度。这样从一方面来看可以说是产权制度不完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这种产权制度下土地较容易控制:实际占有使用土地者,便可表明对土地拥有权利。这也是中国农村地主与农民两阶层界线模糊的原因之一。
⑨这一习俗在杨庆堃、卜正民的书中都有记载。
⑩对于这一点,可以参考莫斯的著作。[34]
(11)该论断取自笔者的博士论文,《经济制度的信仰基础——制度演化分析视角下的宗教之维》。
(12)在本文中,笔者采取一种宽泛的“宗教”定义:宗教是对于各类神圣体验的反映。
标签:小农经济论文; 儒家论文; 韦伯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经济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业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