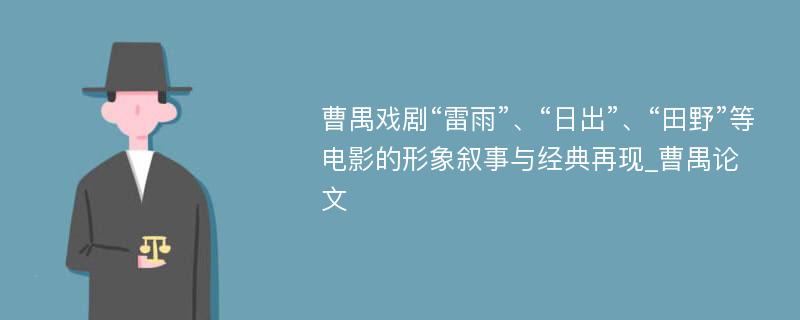
曹禺剧作的影像叙事——论《雷雨》、《日出》、《原野》等电影改编兼论经典的再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论文,雷雨论文,原野论文,日出论文,影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1-0114-04
经典产生一段时间以后,面临的就是对其再生产与消费的问题了。今天,对经典的再生产与消费日益丰富多样,借助影像作电影电视剧的改编,或制成电视综艺节目如百家讲坛;借助网络建立网页或建网上论坛;借街舞、说唱等青年亚文化形式作另类的演绎,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经典的《雷雨》、《日出》、《原野》等,自其产生以后就不断被各类艺术家予以重新演绎、改编,予以再生产。单是就电影改编而言,就有1936年的黑白片《雷雨》,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雷雨》(孙道临改编、导演并主演),198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日出》(曹禺、万方改编,于本正导演),1988年南海影业公司出产的《原野》(凌子改编、导演),以及2006年张艺谋由《雷雨》演绎而成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个人倾向于认为,在这些影像加工品当中,1984年上影的《雷雨》,1985年上影的《日出》,1988年南海的《原野》是比较成功之作,它既充分调动电影语言的功能,用镜头对剧场进行了有效的再生产,又基本忠实于原著,将曹禺在原作中表现的深刻内涵,将曹禺所揭示的“焦虑、苦闷、残酷”[1]等生动地传达出来,外化为生动的影像。也即是说,这种再生产对原产品没有构成多少破坏。而在笔者看来,对于像曹禺《雷雨》、《原野》、《日出》这样的经典作品,还是少加工、少戏说、少颠覆的好。像电视连续剧《雷雨》(李少红导演)将结局作了极大修改,周萍、四凤、周冲都没有死,繁漪也没有疯,我以为这样一来,《雷雨》的味道就没了,一个不那么具有震撼力的《雷雨》恐怕不成其为《雷雨》。正是基于此,本文倒是拣出上述三部老电影,来谈谈曹禺的经典话剧在转换成影像时,一些富于特色的时空叙事形态,以及对曹禺经典作影像再生产时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 闪回,插入:时间空间化
电影可以充分发挥远大于戏剧的时空自由度,将剧作中属于过去时态的内容、作为背景材料的事件、在人物的讲述、转述中呈现出来的情节,推到“前台”,变成与现在的场景一样直观的、生动的画面,借助于闪回、插入等蒙太奇方式将“过去”复现,将时间空间化,那些经人物的台词讲述的,在过去的时间流程上的重要背景事件,变成空间的影像(或者严格说,是一定时空中的影像)后,更具视觉上的冲击力。
在原话剧中,对于过去时态的内容,曹禺往往借助于如论者刘家思所说的“泄露”[2]的方式,由鲁贵、王福升等仆役,或由当事人自己如侍萍、仇虎等不断泄露出来,它是一种复述、转述,转换成影像后成为一种呈现,如上所述,这种呈现借助于闪回、插入等蒙太奇方式来完成。
《雷雨》的主要背景事件有二:1、侍萍、周朴园30年前的恩怨;2、多年前周萍与繁漪的不伦之恋。对于事件1,原剧本是由侍萍讲述的,电影则用“闪回”来表现。侍萍的讲述退而成为画外音,并随即消逝掉,画面呈现为两个空间形态的景象,先是侍萍被赶出家门后在河边意欲自尽的凄凉之境,紧接着快速切换到周公馆周朴园新婚的喜庆场景,构成一个对比蒙太奇。在《雷雨》的故事里,这个制约着两代人、衍生出第二代人的悲剧、一直缠绕着周朴园内心,一直隐隐地盘旋在周公馆的上空,在原话剧里一直作为一个若隐若现的事像推动着故事的进程,然后由侍萍在重新面对周朴园时伤心而平静地说出,自有其独具的匠心。到了电影里,它化为一个特定时空的具象,侍萍的不幸以及周朴园的心结都外化为一两个空间影像,30年前的不堪往事浓缩在两个对比蒙太奇的镜头里。电影用镜头语言将原剧本的“过去事件”召唤出来,清晰而又尖锐(因为鲜明的对比)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对于事件2,电影处理得更具匠心,先是开头,四凤煎药时,鲁贵给她讲小客厅“闹鬼”的事,鲁贵的讲述变成画外音,画面是听讲的四凤前往小客厅,接下来切入一个闪回镜头,四凤“看到了”鲁贵讲述的情景:小客厅要灭不灭的蜡烛,繁漪和周萍亲热的情景。然后又回切现在的四凤,面对着这一幅过去景象的四凤。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奇异的时空叠合:声音是鲁贵的讲述,视角是现时态的四凤,切换的画面却是过去时态的繁漪和周萍。四凤的眼睛、摄影机的眼睛、观众的眼睛相统一,穿透岁月“看到了”鲁贵讲述中的过去。将现时态的四凤去小客厅查看,与过去周萍繁漪在小客厅幽会进行快速拼贴、切换,在叙事功能上,构成过去与现在时空叠合、交错、混融,在意义功能上,则强化了周繁乱伦事件对四凤造成的直接的巨大的冲击。在小客厅幽会的周萍与繁漪,可以说是四凤的主观镜头,是四凤在鲁贵的讲述中产生的幻视,是这一事件对四凤内心刺激的外显,是四凤内心忧虑与危机的外显。
此后,在繁漪与周萍对决一场,繁漪谴责周萍诱骗了她,又恳求他带她走时,有几个插入蒙太奇将他们过去的相好直呈出来。周萍低头回避繁漪的逼问时,插入过去小客厅的蜡烛的特写、以及两人在烛影里相偎的近景;在繁漪问他“你怎么可以一个人走”,而周萍辩解“你是冲弟弟的母亲”时,穿插进过去两人在花园约会的远景,在楼梯里激动地相约的近景,这几个不同空间的插入镜头,概要地叙述了他们过去的交往,并与现在两人的尴尬构成交叉蒙太奇、对比蒙太奇。
《原野》对于焦仇两家过去的恩怨,原剧作在仇虎与焦母的对白中揭示出来,转换成影像后,主要以仇虎的主观镜头,借插入蒙太奇来表现。并安排在剧中许多地方,相同的镜头和场景分3次以重复蒙太奇不断推出,以渐进与积累的方式,将焦阎王杀害仇虎家人夺仇家田地等事件逐渐浮现出来,让观众对这一事件的把握渐渐变得清晰。第一次是仇虎回来寻仇时在原野偶遇金子,金子离去后,仇虎视角里远去的金子叠化出以前的金子,随之火车声响起,在火车的音响中,画面现出焦阎王的凶相,切换成仇父被活埋的近景,又快切为焦母的凶相,再跳切成仇妹被抢走的近景,几个眺切镜头简洁地完成了对仇焦过去恩怨的交待;第二次是仇虎与金子在屋里偷情时,仇虎凝视躺倒的金子,眼前叠化出过去的金子,前一个插入镜头以重复蒙太奇在此重又出现,依然是仇虎的主观镜头,依然是焦阎王、焦母的凶相与被害的仇父、仇妹交替切换。但重复中有变化,在前一个插入镜头里,火车只作为背景音响出现,这一次火车的声音来到前景,火车来到画面中。而受害的仇父仇妹由前一次的近景变成特写;第三次是仇虎与焦母在屋里相遇,仇虎看一眼墙上焦阎王的遗像,这次的“插入”被省略成焦阎王遗像的特写和骤然响起的作为背景音响也是仇虎幻听的火车声。三次插入的闪回镜头重复、积累、叠加,成为一种很有节律的重复性叙事,又极富层次感,由远及近,由模糊而清晰,不断加深了观众对这一在原剧中由人物对白泄露出来的过去事件的把握,也不断地强化了这一事件对仇虎的刺激,成为仇虎复仇的动机,不断地作用于仇虎的行动。
《日出》的一个背景事件是陈白露与诗人丈夫的离异,也即是陈白露的过去,在原剧作中由陈白露讲述来完成,她把这一经历讲给方达生听。转换成影像后,电影作了比较大的改动,这一事件成为整个影片的片头,镶嵌在电影的最开头。第一个镜头即是过去的陈白露的头部特写,然后切换成她的诗人丈夫的头部特写,接着镜头交替打他们的头部,然后推出他们死去的“爱儿之墓”,先是墓碑的特写,镜头下移,再是墓地的近景,而后拉成墓地的全景。回打二人的特写,埋葬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后,也即是埋葬了陈白露的过去后,是二人分手的场景,陈白露要丈夫留下他的诗集《日出》,由诗集《日出》的特写切换成一轮红日升起的空镜头,推出片名。接着就切入火车声,以变焦距的镜头处理方式,显示陈白露穿着旗袍,拎着行李包走在铁轨上,走进城市,走进她的交际花人生。这一“楔子”是电影在对原剧作进行再生产的过程中加上去的,它把原剧中在陈白露的讲述中呈现出来的“过去”,变成一个悲剧意味浓厚的空间影像:墓地。同时这一空间影像又富含象征意味,即是如上所说的对陈白露过去的埋葬,对陈白露曾有的青春、理想、梦幻、爱情的埋葬。表面上,陈白露是在剧末死去,实际上,由片头所呈现的空间影像看,陈白露在影片一开始即死去。
这些经由闪回、插入、交叉等蒙太奇方式,将原剧中由台词讲述出来的“过去”转换成镜头语言后,繁漪的焦虑,仇虎的愤懑,陈白露值得凭吊的青春,命运对侍萍的残酷,焦阎王对仇家虐杀所显示的残忍,及至周朴园的隐忧等等,都外化为特定时空的具体影像,焦虑、苦闷与残忍都被放大、彰显,产生视觉上的冲击效果,也相伴随地带来人心灵上的震颤。
二 慢镜头、长镜头:空间时间化
三部改编电影都比较充分地调动了各种电影语言,借特写、空镜头、慢镜头、长镜头、运动镜头、景深镜头、变焦距镜头、交叉蒙太奇、积累蒙太奇等,将静态或动态的空间影像定格、拉长,把空间影像变成一种缓缓的,或者急速的时间流动,镜头里的每一个空间性元素都在银幕上展示了一个时间的流程,由此营构或者强化一种沉闷、压抑或者紧张、逼人的气氛。在镜头与镜头的组接当中,在空间与空间的转换当中,叙事进程被推动,空间的交叉、并置显示出时间的流动来。
电影《雷雨》的片头,一连串的蒙太奇,将许多个镜头组接、转换:苏州河,宅院,宅院长长的走廊,屋里桌上的药碗,屋外院子里的荷塘,塘边的雕塑,屋子里的佛像,桌上的油灯,宅院的尖顶。这一系列物象被摄影师以慢移、慢摇、慢推、慢拉的镜头运动方式,逐一呈现出来。镜头慢移,逐渐展示出宅院长长的走廊,并构成一个景深镜头,在这个深深的宅院里包藏了几多故事。镜头慢推,进入到院子里桌子上的药碗,药碗的特写持续几秒钟后碎裂到地上,叠化成荷花,又慢摇,呈现荷叶、荷塘,再慢慢上移,扫过院外的雕塑,再切换成屋里的佛像,镜头慢摇至桌上的油灯;然后又慢拉成宅院的全景……时间就在对这些静态的空间物像慢推慢移的镜头运动中缓缓流动,慢镜头的拍摄和定格处理使这些静态的物像具有了一种时间长度,故事的进程已经在这些物像的慢推慢移中行进着。这一系列慢镜头的组接不止是交待和设置了一种环境,更是在一种缓缓的流动中渲染了沉闷、压抑、乃至令人窒息的气氛。
《日出》的片头,在对陈白露夭折的婚姻作了简洁的描述后,用了一个变焦距镜头展示陈白露拎着行李箱越过铁轨走向城市。实际生活中比较快就能完成的行为,由于变焦距的处理,使陈白露看上去一直在铁轨上走。陈白露走在铁轨上的这一空间影像因为变焦距拍摄而拉长时间,似乎是要传达陈白露的这一步迈得多么滞重、艰难。紧接着伴随演职员表字幕的推出,电影运用了一组积累蒙太奇,将陈白露涂口红、涂指甲油、挂耳坠、戴戒指、戴项链等动作叠加,分别推出陈白露唇、指、耳、手、颈等部位的特写,多角度积累起来打造陈白露交际花的形象。这些分散的各个部位的特写,呈现出时间的流转,巧妙地完成了陈白露从单纯的妻子向复杂的交际花的角色转换。
片头之外,原话剧剧本《日出》有两个大的场景转换,从第二幕的陈白露寓所到第三幕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将两个场景连接起来的线索人物是“小东西”。由于舞台特有的幕与场的转换,由于舞台的限制,作者将相关的故事断开来,分别放在两个场所展开。电影艺术家们(包括作为编剧的曹禺本人)以特有的电影语言对《日出》予以再生产时,充分借助于蒙太奇思维,对有关场面自由调度,将原有的两个空间并置、交错,形成平行交叉蒙太奇,故事在两个空间(陈的寓所与翠的妓院)不断交错地展开:方达生在公寓寻找不见了的“小东西”,接着镜头就立即切换到翠喜处,翠喜在跟“小东西”说话。将原剧作中王福升劫走“小东西”与方达生寻找未果都省略掉,带给观众以悬念:“小东西”是怎么从陈的寓所到了翠喜的妓院的?然后又切入方达生与陈白露四处找寻“小东西”,继而回切翠喜处,胡四去玩,黑三打“小东西”;再以胡四作为中介,转切同一时间的陈白露寓所,顾八奶奶说胡四“没良心”……这些在两个场所发生的故事,在原剧中分散在两个空间集中展开,变成影像后,把它们作为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既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个事件,既平行又交叉,既并列又交错地叙述,既并置又对比,空间的不断转换展示事件的发展、时间的推移,还显示境遇的差异、情绪的对比,突出地传达了原剧作彰显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内涵。
长镜头的运用也在这三部电影里发挥了独特的艺术功效。所谓长镜头,是指在一个统一的时空里不断地展现两个以上的动作或一个完整事件的镜头,是指从摄影机快门开启到关闭的连续的不间断的胶片运动的成像。在一个统一的空间影像里,人物或事件不断地持续,这样一个统一的固定的空间,由此充满了时间上的动感。《日出》里李石清接了一个电话,从报馆主编那里得知潘月亭破产后,电影来了一个长镜头:李石清急跑,穿堂,登楼,拿信去给潘,以此来报复、讥刺潘。电影在一个空间里,一个完整的镜头里(一间寓所的厅堂,厅堂旁边的楼梯)记录了李石清去找潘月亭的全过程,这样一个长镜头里李石清的持续动作,正是李石清当时报复的快意的极好的外部呈现。《原野》里多处在同一片原野上,摄影机紧紧跟拍在草丛中嬉戏的仇虎与金子,或者在焦母“小黑子,你回来吧”的凄紧的喊声里乱窜的仇虎,使静穆的原野充满了一种骚动感。镜头是完整统一的,没有组接、转换,空间没有位移,场景没有转换,但因为对人物行动或事件的完整摄录,从而虽然统一封闭固定的空间,却富于时间的动感。
这几部电影如上所述的空间影像的设置,成为电影所特有的一种空间叙事形态,在空间的转换、并置、交错中,时间流转,情节推进,情绪流动。
三 对曹禺经典作影像再生产时相关的问题
在检视了上述三部老电影后,由此谈谈曹禺经典在转换成影像时的一些问题。个人认为,在将曹禺经典进行影像的再生产时,似乎有必要避免两种极端化倾向。一是用阶级论的视点、极“左”的视点、过于意识形态的视点,对人物、剧情等作修改,如将周朴园过于鬼化,将原剧中明显存在的周朴园的忏悔、周朴园对侍萍的真心一概否定掉抹杀掉,将侍萍改写成无产者反抗者,将原剧中鲁大海的行动充分放大,将《日出》中的方达生改写成地下党或者最后投奔革命等等,这些都是将“革命”硬添加进原剧中,严重偏离原文本,也将原作中巨大的艺术空间人为缩小,将原作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人性内涵大为缩减。
二则是趋于另一极端,呈现一种泛人性、泛宽容倾向,以“人性”为标杆,过分添加所谓“人性”内容,而对原作中所呈现的比人性丰富得多的内容构成了遮蔽。如《雷雨》,原作中客观存在贫富对立,乃至阶级分别,周朴园分明淹死过工人,也分明压制鲁大海等矿工,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雷雨》将这些都淡化乃至抹去,过分加大周朴园身上的“人性”内容,过分将周朴园“人情化”,这样事实上是将原来极为丰富复杂的、圆形的周朴园变得单一化、变得扁平,这样一种泛人性、过于抽象的人性事实上掩盖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还有,在繁漪、仇虎的复仇之外,树立一个“宽容”的维度,固然视角独到,固然为缺乏宽容的人、乃至民族树立了一个高的精神向度,但将这种宽容过于泛化,不加分析地施于任何人,问题就出现了。我以为,宽容必须以被宽容者是否值得宽容为前提,或者说它起码要以被宽容者的忏悔为前提,如果他一点不忏悔,继续作恶,却还将宽容加给他,那么是否会引起基本价值判断基本价值标准的混淆呢?其实曹禺早就在原作中隐隐地树立了宽容这一维度,但曹禺又清醒地意识到,仇虎的深仇大恨也确实要报,这样就有了一个深刻的悖谬,尤其当仇虎要杀的焦阎王已经死了,仇虎无处申冤,将仇报在焦大星身上后却引起了深深的不安,曹禺展示了人生的深刻的悖论。现在我们过分放大其中之一,过分张扬宽容,那么原作中深刻丰富的人生的悖论就被简单化了。再者,如果过分强调对作恶者的宽容,那么那些真正的受害者该如何得到补偿?将曹禺经典过分阶级化过分意识形态化固然很糟糕,但过分“人性化”是否也造成了对原剧作丰富内涵的削平或遮蔽?
正是基于如上所论,个人认为,对曹禺以及类似的经典(如眼下正筹拍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还是尽量尊重原著的好,不宜太过解构、戏说。
收稿日期:2008-06-18
标签:曹禺论文; 陈白露论文; 周朴园论文; 雷雨论文; 日出论文; 蒙太奇论文; 雷雨电影论文; 法语电影论文; 艺术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