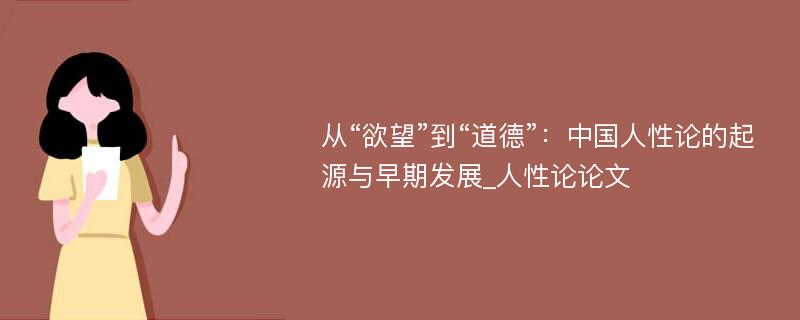
从“欲”到“德”——中国人性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论文,中国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5)02-0010-06
人性上承天道,下启人伦,实乃中国哲学之根蒂,中国文化之命脉。就像中国哲学至宋明时期而日益精密一样,中国人性论亦在斯时返本开新。当时人性二元论的提出,无疑是中国人性论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理学家们将性分为两类,他们或谓之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或谓之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或谓之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或谓之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名称虽异,但所指略同。在这几对名称中,恐以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最为合理。就其本原和本性而言,所谓气质之性未尝不意味着是一种天地之性、天命之性和本然之性。也就是说,其他分类,蕴含着某些混乱。
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虽然作为概念至宋代才明确提出,但作为事实却一开始就已然存在。笔者甚至认为,中国人性论正是在这两种人性的激荡中萌芽和发展的。若用这种思路来考察中国早期人性论,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纵观先秦人性论史,盖以天、命、心、性、情、欲、道、德诸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为基本内容。其中,德与欲分别代表人之为人的本质和人生而即有的本能,可分别归之于宋人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二者的关系,可谓先秦人性论的核心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人性论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儒释道三家人性论,无不以德欲之辨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只是各家之“德”的具体内容不同而已。
本文认为,在春秋以前,先民的人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欲”到“德”,或者说从人的本能到人的本质的过程。以“德”即人的本质界定人性,是中国人性论成熟的标志。
一,以“德”御“性”——孔子以前的人性论(上)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性”的本字为“生”。按照《说文》的解释,“生”的本义为生出、生长,“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由这个本义,自然引申出所生出者,即生命;又进一步引申出与生俱来者,这就是“性”。后来随着人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古人才创造出“性”字,来代替作为“性”的“生”字。这两个字字形虽异,但当时的读音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新字形产生后,旧字形仍并行不废。也就是说,在先秦典籍中,有许多“生”字应该读作“性”。可见,“性”和“生”是密不可分的,以致古人亦多以“生”解“性”。如告子说“生之谓性”,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董仲舒云“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刘向“性,生而然者也”等等。
那么,“性”作为“生之所以然者”、“生之自然之质”或“生而然者”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徐复观指出:“由现在可以看到的有关性字最早的典籍加以归纳,性之原义,应指人生而即有之欲望、能力等而言,有如今日所说之本能。”[1](P6)这一见解是正确的。笔者进而认为,在孔子以前的漫长时期里,这个意义上的“性”,几乎就是人们对人性的全部理解。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人们观念中的人性,仅属于后来所谓气质之性的层面,而义理之性的层面尚未进入人性领域。
当时和“性”息息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德”。何谓“德”?“德”的本字是“惪”。许慎《说文解字》对此字的解释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从直从心。”徐复观考察的结果是:“这依然是后起之义……周初文献的‘德’字,都指的是具体的行为;若字形从直从心为可靠,则其原义亦谨能是直心而行的负责任的行为;作为负责任行为的魋,开始并不带有好或坏的意思,所以有的是‘吉德’,有的是‘凶德’;而周初文献中,只有在喭字上面加上一个‘敬’字或‘明’字时,才表示是好的意思。后来乃演进而为好的行为。”[1](P23)
那么,如何才能“敬德”、“明德”呢?笔者以为,“敬德”、“明德”的主要途径,便是以“德”御“性”。这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消极的方面看,是以“德”来节制、管束人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即“性”。如《尚书·召诰》曰:“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节性”,即节制情欲。何以“节性”?途径是“不可不敬德”。这里其实已点破了“节性”与“敬德”的关系。又如《尚书·西伯戡黎》:“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郑玄注曰:“王逆乱阴阳,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据此,正如阮元所说:“‘度性’与‘节性’同意,言节度之也。”看来,“虞天性”和“迪率典”是相辅相成的。“迪率典”当然属于“好的行为”,所以郑玄以“明德”解之。按照春秋时师旷的看法:“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弗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司保之,勿使过度。”[2](《左传》襄公十四年)“失性”,即放纵情欲。与此相应,“过度”,亦过分宣泄情欲之意。
从积极的方面而言,“德”又有培育“性”的作用,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以“德”“厚”“性”。如《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谏周穆王曰:“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用其器用。”《国语·晋语》四:“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一方面讲“节性”,一方面讲“厚性”,这表明古人已经认识到作为情欲的“性”有积极、消极之辨,或善、恶之别。积极或善的“性”需以“德”“厚”之,而消极或恶的“善”需以“德”“节”之。
在古人的观念中,人由“天”所生,当然人与生俱来的“性”亦由“天”赋予。与此相比,虽然“德”可以“节性”和“厚性”,俨然凌驾于“性”之上,但其实它既不像“性”那样具有人性的特质,也不像“性”那样具有来自“天”的显赫身世。它不过是“好的行为”,既非生于神灵,亦非源于天地,而只是形成于人自身。
另一个和人性论有密切关系的概念是“礼”。“礼”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根据徐复观的研究,在《尚书》周初文献中,“礼”只是祭祀的仪节,而常法、规范的意义用“彝”字来表达。后来“周公所制之周礼,其内容非仅指祭祀的仪节,实包含有政治制度,及一般行为原则而言……到了《诗经》末期之所谓礼,乃是原始的‘礼’,再加上了抽象的‘彝’的观念的总和,而成为人文精神最显著的征表。”[1](P42-45)
“彝”也好,“礼”也好,最初似乎都没有什么神圣性。后来到了《诗经》时代,似乎开始萌生一种新观念。《诗经·大雅·蒸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则”,法则,即“秉彝”之“彝”。这几句诗是说,“天”生出人民,便有法则,而人民遵守这些法则,就会喜欢有美德的人。这里已经朦胧地表达出“彝”与“天”的关系。
到了春秋时代,人们便直接将“礼”本之于“天”,从而明确地赋予“礼”的神圣性。如《左传》文公十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昭公二十五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礼以奉之。”[2]在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礼”由过去的普通道德规范一跃而为绝对的道德命令,“礼”既然是“天之道也”、“天地之经纬也”、“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便意味着它是人人必须遵守的绝对的道德命令;二是,民如果放纵情欲,便要以“礼”来对付。也就是说,在控制“性”方面,“礼”和“德”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礼”虽然为“天之道”,但它仍然是外在的社会规范,而非内在于人自身的特性。这意味着,对于人来说,它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
二,以“气”释“性”——孔子以前的人性论(下)
孔子以前人性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以“气”释“性”。“气”是一种自然主义哲学观。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用“气”来解释自然现象。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近而不能丞,于是有地震。’”在伯阳父看来,阴阳为“天地之气”,天地的正常运转,取决于阴阳二气的协调。以“气”释“性”论同样表现了自然主义的特点,它至少在四个方面促进了人性论的发展。
其一,内“性”(“气”)外“情”观念的产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引子产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2]“好恶喜怒哀乐”为已发之情,“六气”乃“好恶喜怒哀乐”六者之气。这说明,子产已经把情分为内、外或未发、已发两个阶段或两种状态,并把内、未发者称为“气”。此说对后世尤其子思和《性自命出》的人性论影响至为深远。
其二,本性之“性”的产生。同情欲相比,“气”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作为一种内在因素,人们逐渐意识到它规定着人的本性。所以以“气”释“性”,自然导致“性”字产生了新的词义,这就是本性之“性”。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其中的“小人之性”,徐复观已经注意到是本性的“性”[1](P58)。从上下文看,这个本性之“性”侧重于人固有的气质性格,而“足其性”的“性”仍为“性”的传统含义即欲望。照理说,人的情欲、气质性格、天资等等都属于人与生俱来的本性,都可归之于“性”。这是“性”的内涵的扩大。
其三,万物有“性”观念的形成。如果说作为情欲的“性”只适用于人和动物的话,那么作为一种自然因素的“气”则适用于天地万物。所以,自从以“气”释“性”以后,人们开始用“性”来讨论天地万物的本性。上引《左传》“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二语富有深意,它似乎直接来源于伯阳父的“气”说。“哀乐不失”之“不失”,与伯阳父“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之“不失其序”类似,亦相当于后来子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之“中节”。伯阳父所强调的是“天地之气,不失其序”对天地的重要性,子产所强调的是“哀乐不失”对人的重要性。人如果“哀乐不失”,便可与“天地之性”协调一致。何为“天地之性”?依愚见,“天地之性”也就是伯阳父所说的“天地之气”,只不过子产把“天地之气”即阴阳二气当作“天地之性”而已。此“性”当然不是情欲,而应该解为本性。
其四,以“气”释“性”带来的另一个现象是,以“气”论思维来进一步探索“天”赋予“性”于人的过程。如《左传》成公十三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2]“天地之中”,按笔者的理解,就是“不失其序”的“天地之气”或“天地之性”。前一个“命”字为动词,谓民被“赋予”“性”;后一个“命”字为名词,谓所“命”者,亦即“性”,这个作“性”解的“命”当指本性。这段话是说,民在承受天地和谐之气或天地之性以生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性”,所以需要有各种道德规范来稳定“性”,能者培养“性”可以得福,不能者会败坏“性”足以取祸。这仍然反映了“节性”和“厚性”的思路。
三,纳“德”于内(上)——老子的人性论
到了春秋末期,“德”时来运转,不但具有先前“礼”的神圣性,而且拥有“礼”所缺少的内在性。所有这些,都来自老子和早期孔子的贡献。
形成于殷周之际的中国哲学至春秋末期趋向于成熟,其标志就是老子和早期孔子各自建立了一套分别以“道”和“天”为最高概念的形上学。他们都以“德”为人的本质和本性,并且都认为“德”来自最高形上实体,而内在于人,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他们以“德”为人的本质和本性,但并没有把“德”作为“性”。其实,根据“性,生而然者也”这个定义,老子和早年孔子的“德”可以理解为“性”。他们之所以不以“德”为“性”,主要是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性”即情欲,而他们的“德”却是与情欲完全对立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按照笔者的研究,郭店楚简《老子》属于一个早已失传的传本系统,出自春秋末期年长于孔子的老聃;帛书本和各种传世本属于另一个传本系统,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3](第二卷第四篇第一章)。所以在这里根据简本《老子》来研究老聃的思想。
简本《老子》中没有“性”字,但“欲”字多见,盖“欲”为“性”的主要内容,便以“欲”代“性”了。简本《老子》多次提到“德”。什么是“德”呢?王弼有一个著名的解释。今本三十八章王弼注曰:“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五十一章王注:“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王弼的解释,堪称不易之论。在老聃思想中,“德”即人对道的禀受(动词),或者说是人所禀受自道者(名词)。
老子说:“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于江海。”对于这两句话,注家多有误解。依笔者之见,意思是道存在于天下,就像小河的水流到江海从而存在于江海一样,无所不在。“道之在天下也”的“在”字和万物之“德”是相辅相成的。道之于天下万物即为“在”,万物之于道即为“德”。当道落实于人,就使人拥有了生而即有的、固有的本性,即“德”。这种本性是内在于人自身的,或者说是内含于人的,所以老子才说“含德之厚”。笔者曾经说过:“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创生的;天地万物被创生出来以后,道便存在于一切万物之中了。这样,道其实就存在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天地之根、万物之母、具有创生能力的道,我们姑名之本原道;二是存在于万物,或者说为万物所得的道,姑名之次生道。”对于万物来说,次生道也就是万物之“德”[3](第三卷第四篇第一章)。
人之德禀自道,所以人的本性或本质同道的特性是完全一致的。道最根本的特性是自然,因而人的本性、本质也是自然,所以“自然”就是老子之“德”的具体内容。所谓“人法地……道法自然”,就是说,归根结底人是以自然为法则的。
老子将“气”用于他的“德”论。他说:“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蜂虿虫蛇弗螫,攫鸟猛兽弗扣。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然怒,精之至也。终日呼而不忧,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气”是一种和谐的、维护“德”的东西。所谓“心使气曰强”,即“心”有意地指使“气”,对“气”有所作为,结果就破坏了“气”,以致违背了“德”,从而走向“德”的反面——“强”。
“心使气”的具体途径,在老子看来主要是知识和欲望。所以一旦发生“心使气”的现象,即人们一旦违背了自己的自然之“德”,就需要以减损知识和克服欲望来回归其“德”。他说:“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或损,以至无为也。无为而无不为,绝学无忧。”通过“日损”、“损之或损”、“绝学”来达到“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即回归“德”。老子又说:“视素保朴,少私寡欲。”“视素保朴”和“少私寡欲”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视素保朴”便可“少私寡欲”;另一方面,“少私寡欲”便可“视素保朴”。所谓“素”、“朴”,即“自然”,即“德”。可以说,这和“德”制“欲”的传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老子的上述返朴归真之说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实为后来“复性”学说之所本。
四,纳“德”于内(下)——早期孔子的人性论
关于孔子,依笔者的看法,其思想有一个可寻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和晚年。尤其孔子晚年学《易》以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3](第三卷第二篇)。所以在这里以孔子学《易》为界,将孔子思想大致分为早期和晚年两个阶段。早期孔子的资料以《论语》为代表(其中也杂有少许晚年言论),晚年孔子的资料主要保存在今、帛本《易传》当中,包括今本《易传》中的《系辞》、《说卦》前三章、《乾文言》第一节之外的《文言》,以及帛本《易传》全部[3]。在本节先讨论早期孔子的人性论。
在对待殷周之际以来人文主义传统的态度上,老子以“道”代“天”,并赋予“德”以全新的内容,可谓另辟蹊径,新创一统。与此不同,孔子不但继续以“天”为其最高概念,而且还继承和发展了“德”等一系列传统道德范畴。
在孔子学说中,“德”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属概念,象“仁”、“礼”、“中庸”等一切优秀品格皆可称为德。“德”自何来?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生德”意味着“德”由天生,“于予”意味着“德”内在于我,与生俱来。因而,和老子的“德”一样,孔子的“德”也是人的本性、本质,只不过二者之“德”的具体内容完全不同。
《论语》中出现了两个“性”字,其中一个是孔子本人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如何理解这个“性”字?朱子引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朱子本人也说:“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4](《阳货》)看来,人人之性,并不相同,只是相近,且后天习染可以改变“性”。在这里,“性”与“习”是相对的,就是说,与后天的习染相比较,先天的个性还是相近的。孔子接着说了一句话“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不可忽视。“上知”与“下愚”是两种个性,拿这两种情况来看,同样属“上知”的一些人或同样属“下愚”的一些人,虽然其个性是分别相近的,但其后天习染却会相当不同。“上知”、“下愚”属气质之性中的天资,对此孔子多有论述,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等。
孔子也注意到了气质之性中的气质性格层面。如:“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4](《阳货》)。从后一段引语看,人的气质性格是可以丧失或改变的,如由“肆”而“荡”,由“廉”而“忿戾”,由“直”而“诈”等等。至于人性为何和怎样丧失或改变,孔子没有论及。
当然,孔子也没有忽视欲望这一气质之性的重要内容。大家都知道孔子和颜渊关于克己复礼的那段著名对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颜渊》)所谓“克己”,其实指克除私欲。所谓“非礼勿视”等,即是指以礼节欲、以德节欲。但是,孔子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一切欲望。他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4](《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对于富贵之“欲”,是可以追求的,只不过要得之有道。否则,“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放于利而行,多怨”。一种欲望是否可以追求,要看它是否符合“义”、符合“德”。
孔子没有明确地说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但从其具体论述来看,似乎有善的一面,如“肆”、“廉”、“直”等等,也有恶的一面,如“荡”、“忿戾”、“诈”等等。另外,符合“义”的欲望应该是善的,否则是恶的。
五,以“德”为“性”——晚年孔子的人性论
尽管老子和早期孔子已经将“德”规定为来自最高形上实体的、内在的人的本性和本质,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德”就是“性”,就是人性。早年孔子的“性”,仍然是以情欲、气质性格和天资为基本内容的气质之性。事实上,他们已经承认人与生俱来的两种本性,一种是“性”,是人的本能,另一种是“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
数年以前笔者曾经提出,孔子晚年“学《易》”后创建了以“易”为最高形上学概念的哲学体系。也就是说,保存于今、帛本《易传》的孔子易说中,许多“易”字为孔子的最高概念,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易》之书[5]。在这套哲学体系中,人性论也有新的突破,这就是明确地将“德”规定为性,在事实上确立了义理之性在“性”(人性)中的地位。
从帛书《要》篇看,孔子通过反复研读《易》,终于发现此书“有古之遗言焉”,即文王遗教。孔子称之为“德义”,认为这是《易》的最高境界,并强调“我观德义耳也”。今观现存孔子易说,多以“德”解《易》,可见“德”在晚年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
那么,在晚年孔子看来,“德”与“性”乃至“易”是什么关系呢?和老子二样,晚年孔子也是通过宇宙生成论来探索人性的秘密。先让我们看晚年孔子的宇宙生成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2](《系辞上》)在这种宇宙生成过程中,“易”是如何作用于天地万物的呢?孔子说:“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又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2](《系辞上》)《易》以乾坤喻天地,故这里的“乾坤”、“天地”实为“两仪”。从这两段引文看,“易”中具有创生功能的“太极”生出天地以后,“而易立乎其中矣”,“而易行乎其中矣”,即“易”也随之存在于天地之中了。这种思路颇似老子的“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于江海也”。这样,也可以将孔子的“易”相应地分为“本原易”和“次生易”两类。和老子不同的是,孔子径直地将存在于天地之中的“易”称为“性”。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说这种存在于天地的“易”,即次生易实际构成了“性”,并成为各种“道义”的根源。
在《系辞下》,孔子又说:“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2]笔者以为,这里的“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是对“成性”的进一步落实。“易”之在乾,“成性”为“阳”,故“乾,阳物也”;“易”之在坤,“成性”为“阴”,故“坤,阴物也”。换言之,“阳”为乾之性,“阴”乃坤之性。有意思的是,孔子又把“阴阳”称为“德”。所谓“阴阳合德”,即乾之“阳德”与坤之“阴德”相合。这分明是说,乾坤的阴阳之“性”,就是阴阳之“德”,“性”就是“德”。
乾坤之“性”或乾坤之“德”又是如何落实于万物的呢?孔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2](《系辞上》)“一阴一阳”即“阴阳合德”,而“一阴一阳之谓道”是说乾坤的阴阳之“性”或阴阳之“德”,便是“道”。阴阳本来是乾坤之“性”,而这里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可见此“道”是对乾坤之“性”的另一种表达。下文“继之”、“成之”、“见之”的“之”字,都指“道”,即乾坤之“性”。万物在天地间产生,所以能延续和成就“道”即乾坤之“性”的当然是万物。所以,“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说万物延续“道”即乾坤之“性”以为其“善”,成就“道”即乾坤之“性”以为其“性”。“道”落实于万物,即为“继”,即为“成”;万物正是“继”、“成”天地之善性,才得以成自己之性。由于一阴一阳之道广大悉备、深不可测,故“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但百姓缺乏对道的自觉,故“日用而不知”,而真正能够实现对“道”的自觉从而具有“君子之道”的君子实在太少了。
“显诸仁”一段的主语仍然是“道”。“道”在其运作过程中,能显示其仁德,掩藏其创生万物之作用,虽鼓动万物,而无所用心,故“不与圣人同忧”,而这正是“道”的“盛德大业”。从“继之者,善也”、“显诸仁”、“盛德”等描述中,我们可以推知乾坤之“性”或乾坤之“德”是善的。对此我们还可以证之于“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2](《系辞上》)等语。万物之“性”来自天地之“性”,其“性”当然也是“善”的。这种见解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谓石破天惊,实为义理之性之渊源、性善说之滥觞。
在《说卦》首章,晚年孔子对其新形上学作了进一步阐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所谓“性命之理”,我以为指“易”“命”“性”于天地万物之理。正因为这里所讨论的是“性命之理”,所以下文的“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可以分别理解为“天之性”、“地之性”、“人之性”。也就是说,孔子已经以“仁与义”为“人之性”。
在同一章,晚年孔子从另一角度对这种性命思想作了说明:“昔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2](《说卦》)“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分别相当于“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理于义”的“义”,即帛书《要》篇所说的“德义”,而“仁与义”当然皆属“德义”。“穷理”之“理”即上段的“性命之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说穷竭“性命之理”,便能极尽“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即“天之性”、“地之性”、“人之性”,从而达到“性”的来源“命”。
从现存的孔子易说看,晚年孔子所说的“性”为义理之性。至于以“欲”为代表的气质之性是不是“性”,晚年孔子似乎没有表态。
讨论孔子的人性论,大家总要提到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名言。自古对这句话的解释虽洋洋大观,但又莫衷一是。依愚见,此语实同孔子晚年思想的重大转变息息相关。子贡所“不得而闻”之夫子言“性”,乃晚年孔子一反以欲为性的传统,倡导以德为性;其“不得而闻”夫子之言“天道”,乃晚年孔子以“易道”论“天道”也。对此,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所载孔子与子贡的辩论已经提供了详细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