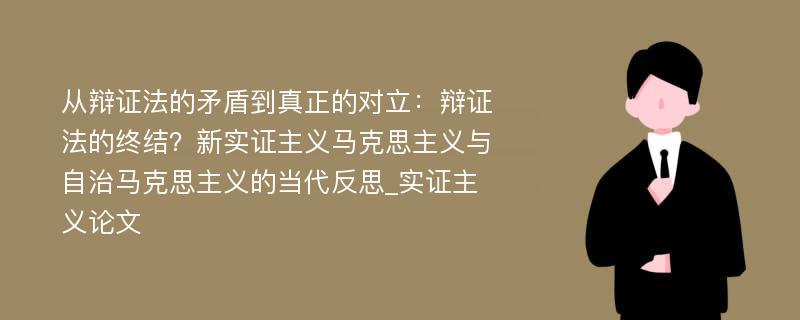
从辩证矛盾到真正对立:辩证法的终结?——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实证主义论文,辩证法论文,对立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4]10-0012-07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内在关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纵观整个哲学史,大部分学者都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承认二者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然而,也有少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主张二者之间的彻底决裂,这主要表现为两大流派:一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以德拉—沃尔佩、卢西奥·科莱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①;二是以奈格里等人为代表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里,笔者主要围绕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展开比较分析,客观评价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和不足之处,以期为国内学界继续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思考。 一、新实证主义与自治主义:意大利传统内部反辩证法的两条路径 从起源来看,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意大利传统,他们都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路径,拒绝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任何继承关系,力图从根基上彻底终结一切辩证法。不过,在历史起源和建构路径上,他们又完全不同:前者是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外在嫁接的理论产物,而后者则是意大利工人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相融合的内在结果。 苏共二十大之前,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直是黑格尔主义的解读模式:一个是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模式,另一个是由卢卡奇和葛兰西所开创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在前者那里,黑格尔是以中介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后者那里,黑格尔则被奉为鼻祖。然而,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上述两种模式遭到了巨大质疑,在意大利则直接演化为党内的理论危机。为了重建党的理论权威,以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力图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之中,建构一种完全不受黑格尔主义污染的新型解读模式。于是,他们以科学主义方法为后盾,上演了一场彻底反辩证法的滑稽剧。 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辩证矛盾观是一种与形而上学相适应的“否定的神学”,它的“经典表达方式是‘A非A’。在其中,一方离开另外一方将无法存在,反之亦然(对立双方的互相吸引)。非A是A的否定,其自身只是一种空无,它只是另一方的否定……这两极自在或自为地都不是任何事物,每一极都是一种否定”②。这种矛盾观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第一,思维的否定性。思维不再遵循传统的同一律和无矛盾原理,而是成为充满矛盾和否定的逻辑本体,后者是它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二,现实的矛盾性,即所有现实存在物都包含矛盾。最后,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基于此,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神学虚构,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将这种形而上学视为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来源,简直是荒谬之极。殊不知,单纯地把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颠倒为物质辩证法,得到的并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仍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因为在后者那里,观念的矛盾同时就是存在的矛盾,二者是内在同质的。由此出发,他们主张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彻底决裂,认为前者从来没有继承过后者的方法,力图从根基上彻底颠覆一切辩证法,由此走上了实证主义的不归路,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为后盾,上演了一场以无矛盾原理和真正对立来反叛辩证法的悲喜剧,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证化转向。 首先,他们用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思维否定性学说。他们指出,科学思维应当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和无矛盾原理,思维一旦出现了矛盾,就变成了谬误。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的思维否定性学说是与一切科学原则相悖的。其次,用实证主义来反抗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他们指出,经验是所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只有得到证实的命题才有意义,反之都是形而上学的虚构。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他们提出要抛弃一切本质概念,把现象作为科学命题的出发点,强调用伽利略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一切社会科学,将实验视为检验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途径,以此来反叛黑格尔的思辨方法。最后,用康德的“真正对立”理论来拒斥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以及现实的矛盾理论。他们指出,思维与存在完全是异质的,决不能像黑格尔那样从思维的矛盾推导出现实的矛盾,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本质上,它们遵循不同的逻辑:前者是无矛盾原理,后者则是康德的真正对立。现实中存在的只是冲突和对立,而不是黑格尔的辩证矛盾。通过这些变形,马克思不再是黑格尔的嫡系传人,而是成为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和康德的门徒,由此证明了马克思的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内在同质性,实现了马克思与辩证法的彻底决裂,开启了彻底反辩证法的理论先河。 如果说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苏共二十大所激发的一种外在效应,那么,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的内生产物。20世纪60年代后期,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工人运动,也是在此影响下,出现了一种特别激进的左翼思潮,即工人主义或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马里奥·特隆蒂、保罗·维尔诺、安东尼奥·奈格里、拉扎拉托、哈里·克里弗等。与以往的工人运动不同,工人主义或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再强调工会和政党的领导作用,而是强调工人自身的独特作用。特隆蒂指出:“我们的工人主义和意大利共产党官方工人运动的真正区别在于,工人这一概念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③在他们看来,工会和政党已经异化为统治工人的官僚机构,无法代表工人的真正利益,因此主张将工人运动从政党和工会中解放出来,直面工人本身,强调工人的自治作用。从这种立场出发,他们必然反对过去将工人和资本理解为对立统一的观点,力图从根本上超越辩证矛盾的解读思路,强调工人和资本之间的真正对立,建构一种与历史辩证法相对的、直面工人实践的激进政治哲学。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辩证矛盾的解读思路呢?他们并没有像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那样,回到科学主义的老路上来,因为在他们看来,用这样一种方法建构出来的马克思哲学,完全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纯理论研究,既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品质,也抹杀了工人的自主性,根本无法适应新时期工人运动的需要。这也是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中后期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对后者的扬弃,他们在方法论上走向了一种全新的道路,即以尼采、福柯和德勒兹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道路。“在我们的武器中,是否存在一种建构分离的方法?是否存在一种建构集体主体性和社会关系的非辩证理论?这些问题直接促使我们思考过去30多年以来在反黑格尔主义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的政治相关性。在现代性的核心之处,我们发现了一条激进的批判传统——从斯宾诺莎、尼采到福柯和德勒兹——它建构了一种取代辩证法的替代方案,为我们建构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方法论提供了开放空间。通过反辩证法的否定运动,这一传统展现了一种肯定性的建构过程。”④后者构成了整个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的方法论根基。后来奈格里也明确地指认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把马克思和福柯结合在一起了,或者就我自己的发展历程而言,我可以说我在塞纳河里‘洗过我的衣服’,把我的工人主义和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了……此外,我们确信,而且现在仍然坚信,马克思可以被运用到后现代性的分析方法中来。”⑤通过这一嫁接,他们也就把马克思与黑格尔清晰地界划了开来:如果说黑格尔开创了一条辩证法的解读模式,那么,马克思则是这一模式的批判者和终结者,是后现代主义的同路人。 他们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代表的是一种以辩证矛盾为动力、以客观必然性为表现形式、以同质性的“一”为主导的线性发展逻辑,与它相对应的理论和政治诉求是“总体性的辩证法、历史发展的线性目的论、共同利益的先验主张以及个人和自主主体对中心权威主体的屈服”⑥。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将这种辩证法,诠释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内在本质,重新将马克思拉回到黑格尔的怀抱之中,抹杀了二者的本质差异。马克思决不是黑格尔的同路人,更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诠释的马克思形象,而是彻底反辩证法的后现代哲学。由此出发,他们上演了一场反抗历史辩证法、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实现了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首先,在他们看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决不是辩证矛盾:既不是黑格尔的观念矛盾,也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是现实主体的冲突和对抗;历史的发展也决不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主体对抗和自主选择的开放过程,是一种反必然性和反目的论的自主建构过程。其次,工人与资本的关系也决不是历史辩证法所断言的那样,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是一种彻底分离的对抗关系。再次,工人决不是历史辩证法所界定的同质性的“一”,即由工会或政党领导的具有统一意志的工人阶级,而是由多元差异构成的大众工人,他们拥有“不同的文化、种族、族裔、性别和性取向;不同的劳动形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欲望”⑦,因此,决不能将他们还原为单一的身份,这是一种真正的差异,而不是被同一性制造出来的差异。最后,决不能将虚假的总体性或共同利益凌驾于个人之上,更不能强迫个体屈从于所谓的权威,在这里,每个个体都是自主的、平等的。结果,历史辩证法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一块遮羞布,被全面解构了。 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大纲》:反辩证法的两部“圣经” 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这两股思潮也不例外。纵然他们在理论路径和实践导向上存在本质区别,但他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即祛除一切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建构出来的马克思形象,回到那个原原本本的马克思,通过对他的著作的重新解读,来寻求自身理论的合法性。不过,他们在文本的选择上又存在重大差异:如果说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强调《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那么,自治主义学派则更加强调《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他们称为《大纲》),特别是其中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一片断(他们简称为“机器论片断”)。 在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主要表现为一种方法论变革,即对黑格尔先验辩证法的全面拒斥,形成了一种与辩证逻辑彻底对立的科学方法。德拉-沃尔佩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包含着以批判黑格尔逻辑学(通过批判伦理—法的黑格尔哲学)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的最一般的前提。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揭露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的而且一般说来思辨的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这些神秘方面是黑格尔的基本的逻辑矛盾或实际上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毫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它们来自这种辩证法的概念结构的类的(先验的)特征。与此同时,马克思创立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的革命的‘科学的辩证法’”⑧。虽然他们也用“科学的辩证法”来称谓马克思的方法论,但这里的“辩证法”既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也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由矛盾、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构成的辩证法,更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主客体统一的总体辩证法,而是由无矛盾原理和真正对立构成的科学主义方法。 德拉-沃尔佩指出,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思辨方法的批判,得出了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逻辑:“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⑨那么,何谓“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呢?他认为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原理和康德的真正对立。它包含三重内涵:第一,思维的无矛盾性。任何科学思维都不包含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矛盾,否则的话,就是一种谬误,这是一切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根本原则。第二,任何现实事物也不包含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矛盾,而是一种真正对立关系,“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就是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极端。同时,它们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它们既不相互吸引,也不相互补充”⑩。科莱蒂认为,康德是“现代真正对立理论之父”(11),而马克思只不过是对康德的继承和发展。第三,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这一原理颠覆了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逻辑,恢复了存在对思维的优先性,建立了一条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这一方法经过《哲学的贫困》,最终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得到了完美阐述。也是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是沿着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道路前进的,只有从无矛盾原理和真正对立入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真谛。 到了70年代,科莱蒂开始反思德拉-沃尔佩和自己前期的观点。他指出:“在德拉-沃尔佩看来,黑格尔似乎与《资本论》没有任何联系,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是真正的对立,即原则上与伽利略、牛顿所分析的那些力相似的冲突。”(12)刚开始时,他对这一结论深信不疑,这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69年)中有着集中体现。但通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他开始意识到德拉-沃尔佩的缺陷所在。他指出,马克思用来解剖资本主义的方法论,绝不是德拉-沃尔佩所说的无矛盾原理和真正对立,而是黑格尔的辩证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到所有其他矛盾——并不是‘真正对立’(就像我紧随德拉-沃尔佩,直到昨天还相信的那样),即不是客观的无矛盾的对立,而是辩证矛盾”(13)。这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德拉-沃尔佩的理论错误,肯定了辩证矛盾的存在,体现了一定的理论进步性。然而,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颠覆德拉-沃尔佩的问题式,而是在坚持无矛盾原理的前提下,对后者所作的一点修正和让步。他指出:“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特征,正是这一点将它与其他社会形态区别了开来,同时也与其他宇宙现象界划了开来。”(14)以此来看,虽然此时科莱蒂承认矛盾的存在,但他只是把后者视为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外,他始终不承认矛盾的存在。从这个角度而言,辩证矛盾并没有取代无矛盾原理或真正对立,成为他诠释马克思哲学的主导范式,他的根本观点即无矛盾原理是马克思哲学的主导原则,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基本原则仍是无矛盾原理。科学的现实并不包含辩证矛盾,而是两种力之间的真正对立和冲突,是一种对立关系……即无矛盾的对立,而不是辩证矛盾”(15)。虽然科莱蒂与德拉-沃尔佩在具体观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他们在根本原则上却是内在同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著作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圣经”,它开创了一种无矛盾原理和真正对立方法,彻底终结了一切矛盾辩证法,实现了方法论的根本变革。 与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同,自治主义学派则选择《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作为自己理论建构的合法性基础。“重要的是探讨当前面临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探讨的基础上,我们才会去寻找支持我们的观点的理论文本。这一过程决不是从详尽的理论分析走向实践活动的问题,而是相反,是从一种理论观点出发,来重新思考现有的实践活动的问题,这是我们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极为重要”,它“突出了60年代以来我们在‘工人自治’运动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方法论(因此也是主观的、认识论上的)特征”(16)。它不再强调工人与资本之间的辩证矛盾,也不再强调“辩证的总体性或逻辑上的统一性”,更不是强调由矛盾推动的、单向度的“线性的连续性”,而是力图在对抗的基础上,寻求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绝对意义上的不可克服的对抗贯穿了《大纲》整个概念体系……这是作为理解《大纲》(通过《大纲》的范畴)的唯一基础的全部内容。”(17)因此,必须要全面抛弃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法的理解,从《大纲》出发,重构马克思的方法论及其政治哲学。这一主张在奈格里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奈格里指出,整部《大纲》实际上就是工人与资本对抗逻辑的生成史。如果说在价值和货币阶段,工人与资本的对抗还是潜在的,那么,到了剩余价值和利润阶段,这种对抗就以尖锐的形式呈现了出来;而到了“机器论片断”(工资阶段)中,随着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这一逻辑最终生成。在这里,工人彻底摆脱了资本的限制,成为与后者完全对立的自治主体。于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不再依赖于资本与工人之间的辩证矛盾,也不再基于传统的客体主义逻辑,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而是取决于工人本身,“如果说共产主义采取了过渡的形式,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遵循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主体的对抗性……主体性的道路正是将唯物主义带向共产主义。劳动阶级是主体,分离的主体,是他们催生了发展、危机、过渡,乃至共产主义”(18)。这一切都不再是历史辩证法的发展结果,而是工人自主建构、自主选择的产物,于是,“所有辩证的、延续的逻辑的残余都消失了……唯物主义成为唯一的水平线,完全由对抗逻辑和主体性赋予活力……这是所有辩证法的否定和颠覆”(19)。它彻底“终结了所有的二元论,绝不在其范围里接受敌人的经济现实。它拒绝辩证法,哪怕是在简单范围内。它拒绝所有两面性的客套话。对立过程在此倾向于发展为霸权:它要摧毁、镇压其敌人。拒绝辩证法: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的主导原则,或者委婉地说是(西方世界的)理性”(20)。 到了这里,奈格里的逻辑已经非常清楚了:辩证法在本质上仍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残余,而《大纲》则开创了一条全新的历史道路,彻底终结了一切辩证法。由此出发,“我们最终会达到一个中心点,即对所有强调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找到马克思思想的实践特征。终结辩证法?是的,因为思想行为在这里并没有任何来自集体力量的自治,来自使主体能动地朝向共产主义集体实践的自治。敌人必须被消灭。只有共产主义实践能够而且必须消灭敌人”(21)。也正是基于此,奈格里将《大纲》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高点,而其他自治主义学者则将《大纲》,特别是其中的“机器论片断”,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部“圣经”。(22) 三、抛弃历史辩证法意味着什么:对两股思潮的当代反思 就方法而言,这两股思潮无疑是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具体投射,他们都反对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彻底决裂,来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重构。不过,前者的目的是为了恢复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而后者则是为了服务于工人主义运动的需要,力图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来证明工人自治策略的合法性。在特定的年代中,这两股思潮都产生了应有的理论和实践效应,对于推动意大利工人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自治主义学派,他们通过对“机器论片断”的当代解读,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提供了有益启示。(23)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两股思潮也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首先,他们都坚持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不存在任何继承关系,实际上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一开始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就是沿着黑格尔的道路前进的,通过自我意识向世界宣称对自由的渴望。经过物质利益的难题之后,马克思开始反思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并力图通过对后者的批判来确立自己的哲学道路,也是在此基础上,他写下了一系列的著作,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神圣家族》等等。在这些著作中,他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一般唯物主义的转变。但由于此时他水平的限制,他并没有真正领悟黑格尔的深刻之处。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他逐渐理解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妙之处,也是在扬弃后者的基础上,他创立了自己的历史辩证法,实现了哲学观的第二次转变。到了19世纪50、60年代,当黑格尔被当作一条“死狗”时,他却毫不吝惜对黑格尔的褒扬,并在《资本论》中公开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同时打算写一部关于辩证法的著作,澄清辩证法的内在精髓。以此来看,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决不是一种彻底对立关系,而是一种扬弃关系,那种把马克思完全黑格尔化,或像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治主义学派那样,彻底否认二者之间联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其次,他们都没有理解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本质。作为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传统,而现代西方哲学恰恰是从对他的反叛开始的,其中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就是两种不同的反叛路径,而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治主义学派只不过是这两条路径的进一步延续。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点,即都只是简单地抛弃了黑格尔的问题域,而不是真正解决后者的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恰恰开创了扬弃黑格尔的另一条道路,他没有简单地抛弃黑格尔的方法论,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后者的全面变革。他认识到,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由观念矛盾推动的,而是奠基于客观的物质生产之上的。他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4),“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5)。这样一种不断的运动就“表现为‘历史’”。在这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不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矛盾,而是历史本身呈现出来的客观矛盾。到了《大纲》和《资本论》中,他依然利用这种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和灭亡的客观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讲,马克思恰恰是沿着黑格尔的道路前进的,他决没有抛弃辩证法,走向无矛盾原理和自治对抗,而是始终坚持从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入手,来揭示人类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26)因此,当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原理、康德的真正对立和伽利略的实验逻辑,来诠释马克思的方法时,已经将后者扭曲为一种唯科学主义的经验方法,在灵魂深处深深地背离了马克思;同样,当自治主义学派紧紧抓住《大纲》,将马克思的方法界定为一种彻底对抗的自治逻辑时,也抹杀了这一文本的方法论特质及其应有的理论贡献。总之,二者都试图运用新的资源来重构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试图将后者与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区分开来,但当他们在解构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却一并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抛弃了,这不能不说是一桩理论“冤案”:马克思反对的是思辨辩证法,而不是辩证法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决不是辩证法的终结者,而是历史辩证法的真正开创者和奠基者。 再次,一旦忽视了历史辩证法,必然带来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实践后果。就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而言,由于他们放弃了历史辩证法,单纯地从无矛盾原理和真正对立来理解马克思的方法论,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异化、颠倒和拜物教现象。德拉-沃尔佩甚至天真地以为,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没有正确运用科学方法导致的,进而认为只要他们使用了正确的方法即无矛盾原理,就能够消除这些异化和拜物教现象。(27)这是多么的幼稚和天真啊!他根本不理解这些现象并不是一种主观错觉,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产物,要想揭示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历史辩证法,显然他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否则的话,他就把他的整个合法性根基全部刨掉了。此外,他们借助于经验方法,将马克思哲学诠释为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完全阉割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就自治主义学派而言,他们存在一个重要观点,即似乎只要承认历史辩证法,就会陷入到虚假的总体性或线性发展的决定论之中,抹杀了工人的主体性。如果就正统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这一判断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就马克思而言却是错误的,因为后者真正实现了阶级斗争与历史矛盾的内在统一,在强调历史规律的同时,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主体能动性,而他们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径直抛弃了历史辩证法,走向了自治对抗的主体哲学,甚至天真地认为,单凭工人的自治就能实现工人的解放,殊不知,这种自治恰恰是资本统治形式的转型,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这种自治是不可能自发地长出共产主义的。就像齐泽克评价的那样,他们的政治是一种“不讲政治的政治”,而他们的革命是一种“没有革命的革命”,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一流派在政治立场上无疑是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前马克思主义的”(28)。这一判断一针见血地刺中了自治主义的要害。他们不仅没有达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高度,反而陷入到充满伦理色彩的主体政治学之中,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唯心主义;他们对马克思的重构,实际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虽然他们自诩为共产主义者,但决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最后,他们过分放大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大纲》的历史地位。在前一著作中,虽然马克思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价值的理论观点,但必须看到,它在理论立场上仍是一部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它只达到了一般唯物主义的层面,在整体范式上仍没有克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从这个角度而言,无限地把它放大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变革的一部“圣经”,有点言过其实了,完全抹杀了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内在区别。另一方面,自治主义学派仅仅依据《大纲》,建构了一种彻底反辩证法的逻辑体系,并将其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高点,过分夸大了这一文本的历史地位,抹杀了它的理论特质:《大纲》决不是一部反辩证法的理论“圣经”,而是历史辩证法的具体体现,在方法论上,它与《资本论》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注释: ①关于这两个学派的比较研究,请参见拙文:《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两条路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②Lucio Colletti,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New Left Review,September-October,1975,p.4. ③Mario Tronti,Our Operaismo,New Left Review,January-February,2012. ④Micheal Hardt,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286. ⑤[意]奈格里:《帝国与大众》(上),黄晓武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2期。 ⑥Michea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286. ⑦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xiv. ⑧[意]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8-35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5页。 (11)Lucio Colletti,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New Left Review,September-October,1975,p.6. (12)Lucio Colletti,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New Left Review,September-October,1975,p.19. (13)Lucio Colletti,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New Left Review,September-October,1975,p.23. (14)Lucio Colletti,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New Left Review,September-October,1975,p.27. (15)Lucio Colletti,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New Left Review,September-October,1975,p.29. (16)[意]奈格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转型》,《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2期。 (17)[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9页。 (18)[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196页。 (19)[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212页。 (20)[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 (21)[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 (22)Paolo Virno,Notes on General Intellect,in Marxism beyond Marxism,New York:Routledge,1996,p.265. (23)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分析,请参见拙文《自治主义的大众哲学与伦理主义的主体政治学》,《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41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页。 (27)John Fraser,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Galvano della Volpe,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7,p.152. (28)[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许纪霖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5、91页。标签:实证主义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思维品质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辩证关系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资本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