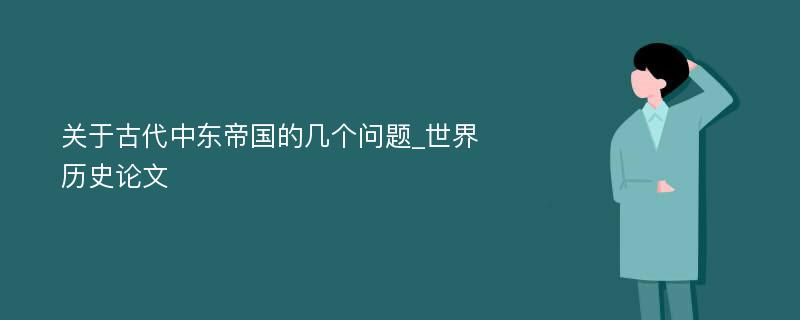
关于上古中东帝国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帝国论文,上古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2731(2000)04—0035—05
关于中东的古代帝国,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教科书或著述中仍有一些较为陈旧的说法,其中也不乏涉及古代史的理论问题。笔者不揣浅陋,现就所见资料,略作分析如下,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关于古代帝国的社会经济基础问题
在这方面,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两篇著作中众所周知的下述论断仍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查理大帝等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
“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的集合体。”
“居鲁士帝国或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是历史上所形成,虽然是由一些不同的部落和种族所组成,但无疑地不能称为民族。这不是什么民族,而是些偶然凑合起来、内部很少联系的集团混合物,其分合是以某个侵略者的胜败为转移的。”[1]
苏联学者伊里因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即认为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萨珊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均是“以军事手段把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许多部族和民族联合在一起的结果”[2]。
上述观点也用于解释古代中东欧洲帝国的短命,作为比较,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华帝国寿命长达2000年,与地中海世界完全不同。然而,上述观点明显存在偏颇之处。
第一,古代帝国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例如,中东金属工具和武器(尤为铁器)日益广泛的使用、生产的发展、外贸的发展、货币的使用(小亚的吕底亚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交通的发展(如驿站、马匹的使用)等。
同时,各个地区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中东素以商业的发达而闻名于世(一些学者甚至据此认为,地中海世界与中国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演化模式,在早期国家形成方面分别以社会经济和政治为动力)[3]。例如,两河流域与黎巴嫩、叙利亚、小亚、高加索、 中亚、印度、波斯湾和埃及均存在频繁的贸易联系,以此获取木材、金属、宝石、马匹、石料、象牙等物资。
第二,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事实上,古代帝国已经拥有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尤其是波斯帝国,它已形成了“管理帝国的比较成熟的制度”,如行省制度、赋税制度、铸币制度、驿道、邮政和烽火制度、军事制度、情报体系、宗教政策、对被征服地区的政策等。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制度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发展和继承,如亚述帝国已有省份和驿道制度。
从历史上看,中东各个帝国的政治体制存在以下的继承性: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塞琉古帝国—帕提亚帝国。德国政治学家罗曼·赫尔佐克指出:“拥有像阿黑门尼德帝国或汉帝国那样的幅员的国家,如果没有一种运作灵巧的行政管理机构,是根本不可能长期保持其内部凝聚力的”[4]。
第三,军事技术和组织的发展。(1 )兵器的改进:如亚述军队使用大量铁质兵器和攻城槌。(2 )多兵种部队的建立:马匹的引进和骑兵的建立使部队拥有更大的机动性和攻击力,使军队和国家机构更趋复杂;波斯和埃及拥有海军;一些国家如亚述还组建了工兵、攻城部队和辎重队等。因此,早期以步兵和战车兵为主的军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3)军队从公民军向职业军队的发展,即雇佣军, 这使士兵更加熟悉战争技能。(4)后勤供应的改进。 如亚述军队在各省设立军用物资供应站,军队不带辎重,就地获得给养,因此机动性大为提高。(5 )驿道和烽火体系的建立使军事情报及作战命令的传递和部队调动十分快捷。
由此,帝国只需少数军队即可统治众多民族和辽阔的领土,一些国家如亚述帝国和帕提亚的军队以能征善战而著称(亚述军队甚至在帝国即将解体之时仍能取得个别战役的胜利)。
第四,文明交往的发展。随着古代文明的发展,一些落后的游牧民族迅速接受先进民族的文化,在短时期内即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拥有较发达的文化,并利用游牧民族的军事特长建立起帝国。
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均是如此,前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便完成了从部落到王国、再到帝国的发展过程。而且,中东在语言和宗教方面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如腓尼基的字母对希伯来、阿拉伯、阿拉米和希腊文字的深刻影响,其中阿拉米文在公元前6 世纪以前即已成为西亚的通用语。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都发源于中东。这些都为中东大帝国的建立提供了条件,而大帝国本身包容了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等古代文明的中心,进一步促进了其文化向落后地区的传播。
第五,古代帝国存在的时间并不短。虽然新巴比伦帝国只有88年的历史,但新亚述帝国为324年,波斯帝国为220年,塞琉古帝国为250年,而帕提亚帝国更长达470年。 前引的苏联学者伊里因也不无正确地指出:“关于古代帝国昙花一现的概念被大大夸张了。”
“事实上,这些帝国存在时间之长并不亚于中世纪的帝国,而又明显地超过近、现代的帝国。”[2]因此,真正令人惊奇的问题是, 这些帝国在古代交通运输落后、境内拥有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语言、文化、风俗各不相同的民族的情况下何以能维持如此长的时间。
相反,古代中国从来不是一个连续的帝国,而是分为不同的朝代(也可称“帝国”),其间同样遭到外来民族的入侵和统治,只是中华文化基本上保持了自身的特征。
由此观之,中东帝国是古代历史和文明交往发展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并不纯粹是军事征服的后果(即就军事而言,它本身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而使得帝国的建立成为可能)。
随着上古帝国的解体,拥有共同语言(阿拉伯语)和宗教(伊斯兰教)、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的大帝国最终出现了,此即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
二、关于亚述帝国的“残暴论”
这一论点与帝国的军事征服论密切相关。许多教科书提及它的杀戮和抢劫、无情的移民政策、对被征服地区的残暴统治和镇压等,然而,近年来国外的研究却揭示出一些不同的方面。
其一,亚述的人口迁移是有选择的,实为人口交换,并且常以家庭迁移和定居形式进行。他们在新的定居地区往往垦荒务农,并为国家提供劳动力和士兵;其社会地位与亚述人区别不大,他们在军队中形成特别部队,并提升为军官,在民间则有的成为宫廷的工匠或文书。
在皇帝辛赫那里布时期,出于尚不明确的原因,政府开始区分亚述人和强制移民,后者被送往神庙,或成为农牧民,或继续在军中服役,但与过去并无明显变化。当然,也有数量可观的战俘成为奴隶,或赏赐给官员和大臣。
另外,亚述的统治集团中包括大批阿拉米人,他们也被认为是“亚述人”[5]。不仅如此,迁移人口的政策并非亚述一家, 其他帝国也有类似做法。像新巴比伦曾将犹太人迁移到巴比伦,此即著名的“巴比伦之囚”。
其二,亚述在被征服地区的政策是比较温和的。帝国在这些地区实施间接统治,即任命原国王以帝国总督的名义继续统治,一般只有在发生叛乱时才建立直接统治。政府在一些被征服地区修复著名的古城,补充人口,发展文化贸易。
萨尔贡二世宣称在埃及修建了一座海港,在列万特(地中海东岸)修建了2座港口,并为大马士革和撒马利亚补充了人口。 地中海沿岸城市成为帝国重要的贸易中心,据希罗多德说,腓尼基人将亚述商品运销希腊,其他资料说当地的亚述商人“多如繁星”[5]。
此外,亚述对被征服地区的神灵也较为尊重,如与该地区的原国王关系较好,则会归还神庙中掠走的神像,允许原神庙僧侣返回。
亚述也曾拨款重修一些地区如巴比伦的神庙。关于亚述残酷镇压被征服地区的叛乱贵族,另有一种说法,即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一般以亚述长官的身份留任,但必须在神像前宣誓效忠亚述皇室,因此举兵叛乱是背弃对神许的诺言,理应受到严惩。
三、关于中东帝国频繁地进行对外战争的原因
这也与帝国的征服性相关。其实,上述现象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
正如前述,中东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其贸易的高度发达,而这源出于当地资源的单一性,包括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在内,因而不得不通过贸易的手段获得之。而且,一些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如小亚的铁和中亚的马匹及锡。
其次,中东地处三洲五海之地,位于中亚、南亚、北非、巴尔干、东欧之间,因此过境贸易也相当发达。可见,控制贸易和商路对于中东各国政府的财政和国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可谓命运攸关。
新巴比伦帝国末期,新兴的波斯控制了通往小亚的商路,而帝国统治下的腓尼基的商业霸权则受到希腊、埃及和吕底亚的制约,这使称雄一时的新巴比伦受到沉重打击,立国仅88年即告灭亡。塞琉古时期曾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进行过5次战争, 其目的之一即控制作为重要商路的叙利亚。
第二个原因也与中东的地理位置有关。由于中东连结欧亚非三大洲,并拥有两河流域、埃及、叙利亚、小亚等物产丰富的地区,因而成为民族迁徙的必经之地和异族入侵的理想场所。
因此,这里刀光剑影,兵连祸结,硝烟不断。例如,两河流域在上古曾先后遭受加喜特人、阿摩利人、埃兰人、亚述人、米底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帕提亚人等民族的入侵和蹂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谋取商业利益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必然把军事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之首。而且,为防不测,主动占据战略要地、扩大战略纵深、控制周边小国就成为必然采取的手段。
至于一些拥有充裕的财力和强大军队的君主,则难免受到土地和战利品的诱惑,走上黩武扩张的道路。
频繁的征战和民族入侵、冲突,导致古代中东文明交往、文明更迭和社会发展的加速,战争成为本地区文明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
四、关于古代帝国的城市自治
自远古以来,西亚即出现大量城邦。个别地区如腓尼基的城邦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其他较早出现统一王国的地区,城市也仍然保持着自治地位,从而维持了相当的活力。例如,两河流域的一些王国往往是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在它们衰落之后,其他城市便乘机勃兴,取而代之,建立新的王朝,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伊辛、拉尔萨和乌尔均是例子。
异族统治也未能改变这一格局,尽管征服者替代了被征服城市的多数市民或建立了新的城市。
在帝国时代开始后,形势大体依旧。第一,城市保持了自治的市政机构,并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市政机构由长老委员会组成,其中许多长老是神庙的僧侣(这似乎与西亚城邦普遍起源于神庙有关)。在塞琉古帝国,巴比伦城仍旧保持传统的政治结构,市政府由名为“萨塔姆”的神庙大祭司和“巴比伦厄萨吉拉理事会”组成。该理事会为神庙领导机构,实际负责巴比伦及邻近的波尔西帕、库沙三城的行政及司法事务。同时,城内另有一名代表帝国的官员和一名法官。
在同一时期的乌鲁克,也存在一个以行政官员为首的神庙委员会,以及代表帝国政府的总督(萨克努)[6]。 至于马其顿征服后建立的希腊城市,也都是自治城市。
长老委员会的权力包括司法审判权。一些长老本人即是法官,或与法官共同商讨决定判案。另一项权力是决定城市的对外政策。
公元前1776年,亚述国王沙姆西阿达德去世后,许多城市纷纷脱离亚述控制,而向本地区新的盟主马瑞国王金瑞林表示臣服。在敌军包围城市时,长老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是战是降[7]。
第二,城市继续享有传统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免税权和免除劳役的权利等,此外,国王还有义务向神庙馈赠礼物、重修神庙和公共设施。
在巴比伦尼亚出土的一份文献中,市民们宣称他们拥有某些权利,如果国王不遵守,他们将起而反抗,遭殃的将是国王。文献表明存在国王与城市关系的正式文件。这份文献在公元前7世纪广为流传, 说明该地区所有大城市大概均享有类似的特权,《圣经》中提到的撒马利亚也是如此[5]。
在塞琉古时期,除了前述旧的城市以外,新的希腊城市同样享有自治地位,只是所有的当地城市和希腊城市均不再享有免税权[6]。
第三,城市保留了对城郊大片土地的控制。中东城市的土地大量掌握在神庙和贵族之手,在异族统治后其中许多得以维持原样。
例如,亚述皇帝萨尔贡二世在北方修建新都沙鲁金堡时,发现当地居民拥有先王赐予的土地,并享有免税权,其义务是向神庙供应物资。在查验了地契和王室颁发的文件后,萨尔贡二世以另批新地或收购的形式予以居民补偿,并颁发了新的王室文件作为证明。
塞琉古帝国初年曾将巴比伦的大片土地没收,作为王室土地,但安提柯二世的王后和王子把许多没收的土地又归还给巴比伦市民。长老委员会的主要事务之一即涉及土地。
在古巴比伦时期,尽管长老委员会的权力不断缩小,但西帕尔的长老委员会仍有权出卖城内无主土地、重新分配士兵份地、向挖渠工人分发口粮,并处理涉及土地的纠纷。
第四,城市往往保留了原有的宗教和文化。古代中东为多神教,每个城邦均有自己的保护神,其中最强大的城邦在发展为王国和帝国后,它的保护神便成为王国和帝国的主神,如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和亚述帝国的阿淑尔神。
但是,正如前述,新的统治者一般尊重原有宗教,像马其顿人在东方修建的新神庙仍保持原有的东方造型,他们还拨款修整旧的神庙,并在神庙中祭祀。
虽然希腊城市在外观和文化方面均为典型的希腊式,但东方城市仍保持了其固有文化,即使在有部分希腊人定居的城市(如巴比伦)中也是如此。
宗教传统的延续,意味着僧侣阶层的精神和世俗权力未受削弱,这在他们对市政机构的把持中即可窥见。
因此,帝国时代的城市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均保持了相当的自主。城市的自治体制说明,上述间接统治的方式可以较好地确保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和经济利益。
同时,城市的自治也使皇帝获得了遏制各省总督权力的手段。
有时,由于首都的自治地位,一些皇帝感觉行动受到限制,便以另建新都的办法来对付。这是中东古代帝国往往有多个首都的原因之一。
总之,城市为我们理解素以“专制”闻名的古代东方帝国政治体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也为与位于东方的中国古代帝国政体的比较开拓了一个重要领域。
五、关于巴比伦“解放论”
据史书记载,居鲁士大帝和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两河流域时,均在当地民众和僧侣的欢呼雀跃下,兵不血刃地进入巴比伦城,而此前的新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则被视为专制独裁政权,受到地方人民的唾弃,这一观点相当流行。
然而,新近发现的史料证明这只是巴比伦僧侣和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的统治上层及一些史学家的臆造,旨在美化后来的统治者。特别是本阶段的大量历史资料来源自希腊,而希腊史学家认为东方国家均为专制政体,波斯帝国为其代表。这充分反映了他们的希腊中心主义思想。
如前所述,巴比伦长期以来保持了其自治地位,并通过与新的王朝立约确保自身的特权。因此,改朝换代只是换了一个君主,基本上不影响城市的各项权利和日常运作;只要新的王朝保障城市的原有地位、宗教等不变,人们乐意接受其统治。
从帝国的统治阶级方面看,上述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他们的利益,因此和平移交政权符合双方的利益。
收稿日期:2000—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