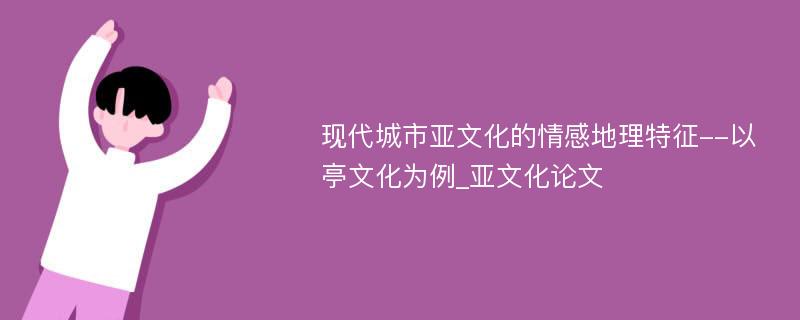
现代都市亚文化的情感地理特征——以亭子间文化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亭子间论文,为例论文,特征论文,地理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情感地理”(Emotional Geographies)①是都市空间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它是情感表现与地理空间关系的具体化。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都市亚文化的情感—空间—身体结构呈现出“杂糅感”和“抵抗欲”等包容性特质。同时,传统文化中的“游民心态”也参与到了地理身份的构建,并且借助“群落生态”的亲缘聚合效应在亚文化中重构了社会关系。这种激进的人文地理学孕育出了集体主义均分式的空间观,进而形成对“五四”传统中指向个体解放的存在主义空间观的压制。这对当下都市亚文化的研究和规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文化的大繁荣很大程度得益于亚文化的大勃兴。随着一大批“薄海民”(小资产阶级流浪文人)在上海聚集,一个激进的都市青年亚文化社群初具雏形。
这些“浪子”基本生活在租界亭子间中,并且抱有“左倾”的观念。经过毛泽东两次讲话的界定与重申,“亭子间来的人”一度成为上海文人代名词②。这一时期,上海亚文化弥漫着颓废、抵抗、悲哀、亢进、屈从、团结的复杂情调,这既来源于历史的观念、作家的灵感,同样来源于亭子间和租界的空间创造。在批判人文地理学视野下,这个“他者”被视为外在于“城市共同体”,但作为城市的一种要素却不可或缺。如曼海姆所说,社会学研究中知识分子的共性在于往往“不是把精力集中于环境的积极的潜在性上,而是成了潜在于环境中的诱惑性的俘虏”③。在错综复杂的理想、主义、人事、口号之争的背后,基于“情感—空间—身体—社会”差异结构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超越琐碎,理解都市亚文化潜在的人文地理脉络。
一、杂糅感:情感与空间
在都市人文地理学中,租界和亭子间在某种意义上都代表一种“定位政治学”无法看清的领域,具有包容性和混杂特质。都市亚文化是“大都市精神”的体现。现代大都市居民具有在情感上亲近亚文化的冲动,他们往往以隶属于某一亚文化空间为荣,以期获得一种新的文化、性格和身份。
在不同的环境、居所有着不同的历史想象,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看见各种情感地理的社会结构。虽然被家人几番催促北上投考北平女师大,谢冰莹却割舍不了上海这个“文人的摇篮”,宁可躲在亭子间喝自来水,“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那里的一切是活跃的,进步的,她爱这所‘社会大学’”④。作为城市边缘和灶披间的上层建筑,上世纪20-40年代的上海亭子间是一个多方杂处的市民社会的底层。穷学生、失业者、妓女、小贩、佣工借此生息,这里也是滋生青年作家、流浪艺人的域外飞地。在同一空间中,不仅通俗文学和左翼的边缘知识分子日渐成长,即使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新感觉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也翻译出版过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而且还“转向”写过一些普罗小说。
作为早期的带有全球化色彩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飞地,上海都市文化带有鲜明的“杂糅”色彩。贾植芳先生说:“要定义海派文化或海派文学确实是个难题。”⑤我们不必讳言这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物,西方世界用一种“异托邦”的幻象来陪衬和确证自身的优越,并且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侵略扩张服务。但在部分知识人的心中,这恰恰是“必要的邪恶”,边缘文人于其间可以实践知识的挑战者的角色。1850年代以后,上海租界便成为商人、政客、激进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聚居的城中城。无论“云里雾里的第三种作家”“跳舞场里的前进作家”,还是“亭子间里的无名作家”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这个控制松散的空间,却充满了活力和能量。徐志摩在《新月》的发刊词中,将当时的上海“思想市场”分为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攻击派、偏激派、淫秽派、热狂派、标语派、主义派等等十三个派别。至于鲁迅的杂文更是拉拉杂杂,报刊新闻电报信手拈来、随意拼贴,更加从形式上衬托了租界文化的混杂色彩。因此,当1927年南京政府设立上海特别市为收回租界做准备的时候,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并不响应,他们并没有因对租界外国势力不满而迁入特别市。
先有现代都市“矛盾特色”,方有早期的都市公共空间形态,这激发了“小群”与“大群”之间的能量转换。1930年2月16日,夏衍、鲁迅以及一批亭子间文人在公共租界的公啡咖啡馆秘密集会。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域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便宣告成立。租界为亭子间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宽松自由的语境。当然租界也不完全是一个安全地带,但是正因为它始终处于危险的边缘,这个反抗的社会更需一个乌托邦理想照耀他们前行。如小派正之所见,社团已经是“日常生活的社会依托”⑥。沈从文也痛感,如果底层文人不参与社团,门路便会越来越窄,感情自然越来越坏,终有一天会在“都市病”中一蹶不振。租界和亭子间作为亚文化飞地的重要特点就是,这种居住区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愿意临近亲密关系群体而聚居的偏好。底层阶级在这里聚合,以左联为代表的租界社团和亭子间文人群体因此具有了天然的“邻里关系”。这是带有革命文化亲缘性的亚文化团体的标记。
要言之,都市公共空间的包容性为多样化的亚文化群体提供寄居的家园。虽然在“新月”的号召下,精英文化人依然保持着骄傲的姿态。但是在左联的周围,新兴的亚文化社群因为空间的“亲缘性”正逐渐聚合,这里才是孕育着希望的“另一度空间”。
二、抵抗欲:情感与身体
寓于亚文化空间中的底层文人生活呈现杂糅性特质——一种“色—魔—幻”的杂糅。这体现出现代都市亚文化中身体解放与革命激情互为表里的关系。亭子间是一种开放的空间的边缘,一个意义深远的边锋。这一亚文化空间需要诉诸一种挑战性的身体姿态完成自我的建构。
早期的“享乐主义青年”的形象,例如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的王曼英、《追求》中的章秋柳,醉心于到跳舞场、到影戏院、到旅馆、到酒楼,甚至于想到地狱里,到血泊中感觉一点生存的意义,追寻时时刻刻热烈的痛快。并且章秋柳的“要求新奇刺激的瘾是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了”,这一点和海派的性爱作家以及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异曲同工。性的刺激和身体的迷向是新生的都市诱惑的最好表达。沈从文在《论海派》中讥讽海派文人既关心“现代人的悲哀”,也关心“十月革命”,也经常谈到小说的内容与技巧的问题,谈到没落的苦闷,以至于还大谈嘉宝的“沙嗓子”“眼珠子”和“子宫病”,追究“沙嗓子的生理原因”,以及她的“性欲的过分亢进”。可见,亭子间青年作家选择文学道路更多的出于革命“热情”,而不是对文学的“热爱”。这一激进的人文地理风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青年亲近政治多采取“恋爱”的态度,所以很容易成为“社会主义追求者或信仰者”。成仿吾们对斗争哲学的“机械的地运用”,也不仅仅因为他们脱离国情,还与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浪子”的劣根性有关。鲁迅先生批之为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至于京派文人更是以“流氓和妓女的文化”形容海派激进的抵抗欲。
在激进的都市亚文化浸染下,上海的胡适一派也以“反动文孽”的姿态激烈批判国民政府侵犯人权、“党权高于国权”,但这不失为一种苦口婆心的规劝。胡适认为,“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而政府也需要训练”,这背后仍然是一种对精英主义立场的坚守。在胡适领衔的《新月》周围则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绅士”,以“健康”和“尊严”作为文学评判的标准。尽管在史沫特莱笔下,他们依然是一些“体面和高雅的文人……行将死亡的和颓败的社会阶级的知识贵族”,但是精英群体“健康”的身体观在抵抗欲上却与左翼殊途同归。
概言之,由于都市亚文化具有“杂糅感”和“抵抗欲”的情感特质,都市空间才可能包容“欲望的真正的英雄”。精英文化、租界文化和亭子间文化的摩擦亦可表明,亚文化的突起在最终导致传统的君王/父权体系迅速崩塌的同时,身体解放和“人的文学”也在以一种激进的姿态崛起。
三、游民心态:激进地理身份的构建
亭子间文化与新生租界文化同样禀有“杂糅感”和“抵抗欲”的情感特质,但不同之处在于,空间的差异与排斥为亭子间文人感受最深,亭子间文化因此具有更为激进的青年亚文化气质。
亭子间亚文化的主体是边缘的学生和知识人群体。由于中国科举制度的崩塌,不仅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模式彻底被打破,而且连带摧毁了传统的乡村结构。“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之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⑦。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因而轻视乡村,进而产生了整体性的城乡“文化之中梗”。城乡分化已是必然。既然乡土不再,两千年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便不再是社会的轴心。知识青年的“离村问题”便异常突出出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也看到,乡村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都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
青年亚文化的激进姿态也是“跟着少年跑”这一时代风尚的折射。胡适说梁启超:“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鲁迅宁愿自己肩负那“黑暗的闸门”,劝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钱玄同更主张将四十岁以上的人全杀掉。年仅三十五岁的胡适慨叹自己也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结果是“学生”与“老师”分化为两个社群,学生群体中多有“自成一阶级”或“自创一政派”的“学客”⑧。到1946年,闻一多自问道: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学生”与“老师”的分化逐渐演化为“青年”与“老人”之争、“新”与“旧”之争。以“青年”傲视“老人”的高长虹难以掩饰自己的优越感。20年代末创造社青年文人则直接以“老生”代称鲁迅,30年代杨邨人的公开信中也不加掩饰地大书特书鲁迅的老态。鲁迅在情感上俨然已经是“不中用”的老头子形象。在学生的眼里,他是需要被“浪子”们起来反抗的“浪子之王”。进而言之,鲁迅以及“五四”权威文人所代表的文学体制及其政治经济基础更是需要被颠覆的对象。因此,以“新月”一派为代表的精英主义者们,自然不太赞赏激进亚文化群体的“伤感”“狂热”和“偏激”,并且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股恶浊的清泉。徐志摩讥之为“无方向的激射是一种精力的耗费”。
瞿秋白较早论述了这一20世纪20年代以来上海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他指出:“‘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地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⑨根据李健吾译作中对近代巴黎“浪子”的描述,右翼的郑学稼在《论我国文学家及其作品》中也注意到一般左翼文化人身上类似巴黎“浪子”的气质。鲁迅同样深刻揭示了都市浪子的一种劣根性。建立在封建奴性基础上的“暴民乱治”和“游民意识”随时会以新时代“大众”的面目卷土重来,扭曲异化革命。所以鲁迅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这些革命阿Q那黄黄的小辫上又增添了几分上海滩洋场投机的气息,“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在勒庞眼中,这种集体症候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保守的,它深深地厌恶发明和进步,对传统怀着无限的崇敬之情⑩。一些亭子间文人的革命不过是和传统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一样“争夺一把旧椅子”。如果奴才成了主人还是要做“老爷”。他们的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大还可笑。可见,亭子间文化作为现代上海都市的新生儿,却始终伴随着一种“原始冲动”,这一冲动就是:回归游民运动的传统。激进的浪子好像在反压迫、反传统、反抗不义、反抗皇权,其实是意在恢复压迫和野蛮的传统,制造着新的不义和另类的皇权。这一“另类皇权”是指革命者虽属于距离皇权最远的底层,但无论在心理结构、行动规范,还是在终极理想上始终以皇权为摹本。以往,全社会对于这一游民亚文化缺少反思,还把它作为革命精神传扬,实际上这是一把极易走偏的双刃剑,会给改革与建设带来意想不到的破坏。
进而言之,“薄海民”文化在情感地理上有亲近乡土“游民文化”的心态。鲁迅与浪子之争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启蒙理性与乡土游民心态之争、租界主流文人和亭子间文人之争。这是一种地理身份的深刻冲突。
四、群落生态:社会关系的构建
亭子间文人心态是一种“有组织的游民心态”。亭子间中并不孤单,青年文人聚居在一起形成人文地理学上的“群落生态”(Biotope)。边缘知识人既带有与生俱来的“游民心态”,同时在空间上形成聚合效应,进而围绕在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和人格权威的周围,参与社会关系的构建。
亭子间文化是聚居形成的小群落文化。欧阳山住的北四川路一间亭子间中,张天翼、沙汀蒋、朱凡、牧良、韩起、杨骚等人时常聚会、彼此接济。罗烽、白朗夫妇先与萧军萧红同挤一间房,后又与舒群、陈凝秋同住法租界美华里一间亭子间。在丁玲租住虹口青云路青云里一间小亭子间中,瞿秋白等人是这间亭子间的常客,他们纵谈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谈普希金、徐志摩、郁达夫以及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争论(11)。亭子间文化具有鲜明的暗示和感染作用,并且被暗示的观念有直接转化为行动的倾向。在鲁迅、郁达夫等人的人格魅力的号召下,一个个底层的文学青年个体在亭子间形成小型的聚居群落,直到最后团结在左联周围。由避免孤独、谋得生存,到从集体中获取力量,即使最终陷入到某种意识形态的迷狂,也坚信错觉才是真理。特别是到了后期,伴随着鲁迅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日渐孤立,周扬及其追随者成为左翼文化组织内的主流。这不仅因为周扬是组织的领导,也因为身居亭子间的他和亭子间文人有着贴身的情感地理联系,容易获得众多浪子的认同和拥护。
鲁迅批评周扬等人是“工头”和“奴隶总管”,其暗指的是,维系作为一种“群落生态”的亚文化空间需要一种力量,那就是“威望”。这是一种由一个人、一部作品或一些观点点燃起来,并且支配我们的东西。而勒庞区分了两种威望,一种是获得的威望,另一种是人格的威望。总结鲁迅与亭子间文人群体的合作与分歧,我们发现,周扬的威望属于前者,他是获得体制认可的文学权力。在“四条汉子”阶段前后,与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的矛盾更多地带有宗派色彩,彼此的妥协、融合是主流。而后期周扬与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的斗争则体现了背靠体制排除异己,维护自己权位的企图。1936年,周扬等人不发表公开的声明解散左联,另组“文艺家协会”,提倡“国防文学”,并诬蔑鲁迅“破坏统一战线”。鲁迅则愤而带病参战,揭露浪子们“左得可怕”的本来面目。
这种集体主义的“群落生态”是革命力量的源泉,但也便于被无意识所控制,具有容易冲动激怒的情感特质。空间上的局促导致压抑愤懑继而狂狷。集体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集体群落中情感和行为都有极大的感染性,它甚至能使一个人欣然地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服从集体的利益。这会造成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是顺从权威,一方面又非常褊狭、不容人。一批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革命青年”以成仿吾为首展开了对鲁迅等新文学作家激烈地批判。他们以日本共产党福本和夫“左倾”狂热的“分离结合”为圭臬盲目清算,将几乎所有新文学作家一网打尽。鲁迅却对这一国民性有着深刻的了解。亭子间“群落生态”以“获得大众”为目的,其实是在制造“多数人的专制”,浪子们“飞跃又飞跃”,连鲁迅都只能“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接下来“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亭子间文人的这种“新”“旧”意识的转换,折射了集体性心理学中一种心理原型的转换过程。阿Q式的劣根性随时会重新在心理的河床上奔涌成大江。激进知识分子缺少与某一阶层的根本结合,因而更需要从集体中获得一种心理补偿。亭子间文人因此有着普遍的狂热特征。要言之,都市底层文人的狂热心态与日常生活空间的极度压抑所造成的剧烈反弹有关,他们借向传统的游民意识的复归获得一种摆脱物役的愿望满足。
五、“公”空间与“私”空间:两种情感表现模型
鲁迅一生对租界中的公寓保持好感,并且对亭子间的“群落生态”和“公共空间”保有警惕和规避。于鲁迅与亭子间文人的矛盾之中,我们更应当反思,情感地理如何决定了一个群体的文化传统与精神家园。
晚清以来,从“个体解放”进而展开“公共空间”在启蒙话语中是否是一种预设?而这一预设是否真的水土不服?换言之,近代以来,寻求明清文化中的“私欲”与“个人主义”的相似性,往往成为底层知识分子倡行自由理念的最佳路径。明末到清中期,李卓吾、顾炎武、黄宗羲直到戴震对“私”的正当性的辩护中,可以发现由于对皇权“大私”的质疑是随着君民一体化统治的解体而出现的。这一民权思想,究其实质并不是抽象的平民思想,与其说这个“私”代表个人性的“私”空间,不如说指向“均分式”的“公”空间。亭子间中的边缘文人仍然抱有以平均主义为内核的朴素平等观念,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思想在现代都市空间中的继承和发展。
以此看鲁迅与左联情感关系的恶化,我们也可以辨别都市文化中公共空间观的差异。鲁迅心中的公共空间是回归本体论的一种存在主义空间观,他试图守护一种“私”空间,而亭子间文化指向一种功利性、均分式的“公”空间。唯有在一个自由的“私”空间中,鲁迅才能守护一个精神界战士的孤独。即“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文化偏至论》)。鲁迅的思想更亲近于基尔凯郭尔和尼采,强调“人之内曜”“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文化偏至论》)。这是一种个人化的致命的自由,因为这种孤独是无证据的,也是无用途的。这种“文化偏至”的历史辩证法把“人国”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它作为一种未来的乌托邦,意味着对一切压抑或物化的社会秩序、文化形态和思想理念的否定。在鲁迅眼中,左联能够唤醒青年知识分子的热情与才情,亭子间亚文化群体最终围绕左联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运动,是因为这是一个能够包含精神自由和个体差异的组织。个体的意志与组织的权力之间不应该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而“奴隶总管”意味着对个体意志、个体自由的蔑视和剥夺。即使茅盾在参加了两次全体会议后也感到“左联”与其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12)。如果威望始终是一根横在头顶的“鞭子”,那么鲁迅的“反抗绝望”就是要抵抗这种错觉,一种置于集团心理下以激进夸张掩盖“潜伏着的数千年的精神创伤”。
总而言之,正是基于对国民性的深刻认识,鲁迅才警觉到一种缺乏个人主体自觉的政治激情最终会导致个性的压抑。这折射了都市亚文化群体在情感-地理上的深刻分歧。杂糅感在赋予都市文化“多元化”和“异质性”的同时,也激发出一个“抵抗的空间”。激进的亚文化社群以“游民心态”召唤彼此,获得认同,并在“群落生态”的掩护下完成了社会关系的构建。在现代上海的公共空间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空间观:主流文人的“私”空间与边缘文人“公”空间。主流都市文化与激进都市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于:宣传不可替代文学,文化中的“群体情感”不能完全替代“个体情感”,而均分式的“公”空间更不能覆盖守护孤独的“私”空间。历史当为镜鉴。当下网络“粉丝文化”兴起,任何思潮可能结成亚文化“迷群”,都有可能成为游民骗子的“避难所”。都市亚文化愈加呈现出在包容和激进之间摇摆的趋势,如何趋利避害,以和谐化解断裂,乃是所有人应当进一步思考的命题。
①福柯、列斐伏尔、苏贾为代表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派认为,“情感地理”是对情感表现与空间性的诸种关系的具体化。参见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前言和后记第11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情感地理研究主要关注三方面:一是情感定位于身体与地方,即探索情感在何处产生的问题;二是人与环境的情感关联,即研究情感如何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其中涉及地理身份与社会关系要素;三是情感地理的呈现,即通过建构情感表现的模型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情感地理的本质内涵。参见Joy Davidson.Liz Bondi,Mick Smith.Emotional Geographies[M].London:Ashgate Publishing,Ltd.,2007.
②现代上海底层文化人和边缘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亭子间。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都用亭子间文人指代上海的左翼文人。亭子间文化因此成为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代名词。
③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159页、黎鸣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④阎纯德:《谢冰莹及其创作》,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⑤贾植芳:《海派文化长廊·小说卷·总序》,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⑥小派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⑦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载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第82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⑧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42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⑨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上海青光书店1933年版。
⑩《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83页,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11)张小红:《文坛之光》第79页,百家出版社2000年版。
(1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