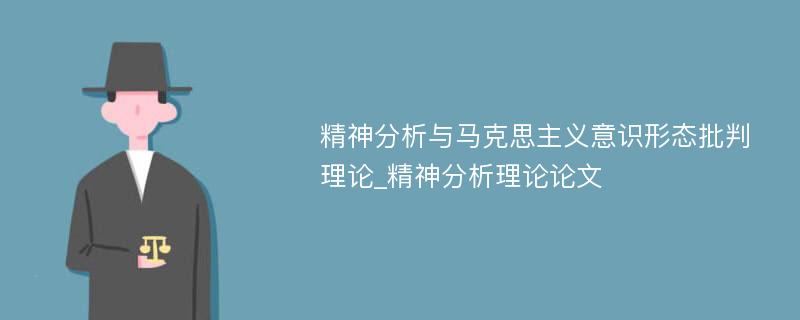
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精神分析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批判”新解 何谓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概念自其出现开始到现在已经争论了二百多年,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还是在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论是在文化和文学研究中,还是在政治思想研究中,意识形态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意识形态之所以在当代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意识的存在物,人的行为具有动机和意愿的性质,因而,观念和思想是人行动的条件。同时,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无法摆脱历史的肉身和制度的限制。事实上,意识形态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观念或思想,而是那些既是人类生活的构成条件又是社会权力中介的观念和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在诸多解释中,威廉斯所指出的三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定义颇具代表性,我们不妨将其作为讨论的路标。威廉斯认为,意识形态可以指一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信仰体系,也可以指由错误观念或错误意识构成的幻觉性的信仰体系,还可以指社会生活中一般的意义和观念的生产过程。①这三种意识形态概念可以分别指向意识形态起作用的三个领域,即政治领域、人类的认知领域和自我认同领域。 在政治层面上,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是它与权力之间的相关问题。韦伯曾指出,在每一个统治结构中,那些由于历史偶然性或暴力而获得特权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拥有权力,相反,他们还“希望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有所改变,把纯粹的事实的权力关系转变为应得的权利体系,并希望看到自己因此而受到尊敬”。②布迪厄将其视为“社会炼金术”,因为它通过自己的操作已经实现了事实性权力向“应当的权力”的华丽转向。不得不说,把意识形态视为社会秩序或权力关系的合法化机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研究路向。然而,约翰·汤普逊认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既不是单纯地研究权力问题,也不是简单地研究符号和意义的问题,“研究意识形态就是研究含义(或意指)以哪些方式被用于维持统治关系”。③吉登斯认为,“考察意识形态就是要识别将意义同合法性联系起来以巩固统治者的利益的最基本的结构要素”。④在政治实践层面中,意识形态或者通过布迪厄意义上的“社会区分”,或者通过制造跨阶级的共识来掩盖社会不平等和等级秩序。 从意识形态概念的第二种含义,即把意识形态指认为一种虚假意识构成的幻觉性的信仰体系来看,其重视的是意识形态概念的认识论批判意义。在《致梅林的信》中恩格斯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⑤一般认为,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虚假意识”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在认知上的否定意义,应该通过客观性知识的发展来超越。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层面和认识论层面并没有截然分开。我们知道,马克思既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又把它视为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意识。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是指纯个人的任意幻想或胡言乱语,而是指特定社会中由阶级地位或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社会必要幻想,虽然意识形态在内容上与科学的认识相反,但它产生的原因却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⑥因此,一旦我们深入到虚假意识形态产生的客观根源,我们就必然越过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批判,进入到对意识形态合法化的政治批判。 与前两种意识形态概念不同的是,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意义和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具有多重内涵,它既指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可以指意识形态在肉体的塑造和自我形成中的作用。无论意识形态是朝日常生活批判方向发展,还是朝主体批判方向发展,它都超出了前两种意识形态定义。吉登斯在谈到意识形态理论重视日常生活和符号意指活动的原因时说:“传统处理意识形态的方式过分夸大了命题形式的信仰诉求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所具有的重要性。”⑦“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和‘纪律’,包括但不限于产业工人的生活常规,可能被认为是当代社会中内涵最丰富的意识形态特征。”⑧詹姆逊在谈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机器理论的意义时说,意识形态首要和最主要的是制度,随后才是它对意识的影响。最为直白地表达意识形态研究中日常生活重要性的瑟伯恩说道:“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最好通过大城市街道上的声音和符号的吵吵嚷嚷的声音,而不是与孤独的读者交流,教师或电视主持人面对安静的观众讲话来认识。”⑨从这些论述来看,强调意识形态是观念和意义的生产过程,不仅是突破意识形态概念传统定义的需要,也是认识意识形态在主体生产中作用的必然。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意识形态把个体转变为主体,主体不是通过观念和思想的灌输生产出来的,而是通过意识形态机器的质询实践塑造和建构的。在这里,主体生产的意识形态与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已经交叉在一起,正如福柯所强调的,现代社会的统治不是建立在国家的主权之上,而是建立在社会的治理权之上,对肉体的塑造和人口的管理已经成了权力合法化的手段。因此,自我的生产也就是社会秩序的生产。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批判可谓纷繁复杂。与一些学者在意识形态研究中采取排他性的立场不同,笔者认为,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容纳和借鉴不同的研究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迷失于对意识形态现象或形式的外在描述和类型分析之中,而失去对它的本质和普遍特征的把握。今天,我们在把由社会原因所产生的虚假意识视为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接受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机器概念;在意识形态研究中既涉及权力问题,又涉及自我问题。为什么这些对象各异的研究可以分享“意识形态理论”或“意识形态批判”的概念呢?这是因为各种意识形态除了具体的、不同的特征外,还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把历史地形成的事物非历史化和自然化,不论我们讨论的是观念与思想,还是制度和行为,抑或是自我与主体,它们都可以被意识形态化,而意识形态化又都体现为对历史形成的事物及其关系的非历史化和自然化。 从这一共同特征来看,意识形态既是描述的,也是批判的。在一般的权力层面上,意识形态意味着对历史形成的社会秩序的自然化,“把纯粹的事实的权力关系转变为应得的权利体系”⑩,因此,意识形态是社会权力自我美化的“炼金术”。在观念层面上,任何观念和思想的产生都依赖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主体在社会中的特定立场,因而都具有无法根除的历史性和特殊性。然而,意识形态总能够找到理由把观念和思想理解为是现实的客观的自然表象。正因为如此,斯图亚特·霍尔明确把意识形态与观念和思想的正常化和自然化联系起来。他指出,意识形态活动就是把具体的、历史的、偶然的关系构建为必然的、正常的“现实性”。在这里,“意识形态就是把具体的历史文化链接正当化”。在霍尔看来,意识形态的秘密是观念和思想的自然化,“意识形态就是声称某具体的文化活动是对现实的表征”,“意识形态把某类社会认同和具体的社会的体验联系在一起,仿佛后者注定是前者的派生物”。(11)在这里,“声称”是自然化的手段,“仿佛”是意识形态自然化所追求的以假乱真的状态。最后,在自我层面上,意识形态也是通过自然化起作用。总之,意识形态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也可以有与特定社会领域相联系的特殊功能,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承担何种功能,它们总是把某种历史地、偶然地形成的事物和观念的秩序转化成自然的、必然的东西。按照霍尔、拉克劳等人的理解,意识形态是一种缝合的实践,观念与行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制度、符号与思想、自然与历史等等之间不可避免的裂缝,通过意识形态的缝合变成了虚假的同一、和谐和确定的现实图景。 一旦我们把握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就不难理解意识形态批判的概念。如果意识形态的目的是要让你相信你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及其制度是天然合理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意识到你所认为的自然事物和制度其实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变化发展的结果,因而具有历史暂时性。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是观念和事物的“自然化”,那么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就是“解—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解—自然化”就是要打破意识形态塑造的观念、秩序与自我幻想的同一性、正常性和非历史性,揭示它们在自我形成和维持中存在的偶然性和暴力的痕迹,从而打破自然化的假象,让人们真正面对真实世界。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意识形态批判,那么,意识形态批判与意识形态研究的元逻辑一样,可以在其批判方法的多样性中保持统一性。意识形态是广泛存在的,但意识形态从来不自称自己是意识形态。只要文化观念、社会秩序和自我认同存在着有意和无意的非历史化和自然化操作,它们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不是意识形态理论家的专利,只要一种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原以为是自然的观念、事物和制度中的非自然的痕迹、历史的痕迹、暴力的痕迹,无论这种理论是否自认为是意识形态理论,它就起着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我们这里讨论的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如此。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意识形态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理论影响巨大,影响了众多思想家如阿尔都塞、拉克劳、齐泽克、巴迪欧等人,而且还因为他的理论本身包含着对自我认同的自然化之意识形态性质的解释和批判。拉康传记的作者格尔达·帕格尔说:“‘我是他人’——这乍听起来自相矛盾的论题,却像红线一样贯穿在拉康的全部著作之中。”(12)拉康毕生的研究意在表明,人类的一切经验和表达不是源于自我,而是植根于先于主体而存在的无意识语言结构。在拉康看来,人类自我或主体从根本上说是分裂的,为了弥合这一分裂,人们不得不一再地被迫投入到一系列误认形式之中,这些误认形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原型,因此,拉康已经看到,任何自我认同都是自然化意识形态操作的结果。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并没有明确地使用“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批判”等概念,但他的理论和方法却可以转译成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无论是阿尔都塞,还是齐泽克、拉克劳等人,都未重视这一工作。笔者认为,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翻译和转换成意识形态理论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不仅可以推动精神分析的发展,还可以深化对意识形态的研究。 二、镜像认同与象征认同 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框架是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的三元拓扑结构,一切自我的误认都是在上述领域中展开的,并通过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到理解。在拉康的理论中,他把儿童的精神发展分为前镜像阶段、镜像阶段和后镜像阶段,镜像阶段既是认同的开始,也是误认的开始。 拉康的镜像理论受到弗洛伊德自恋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启发,它的提出源于对儿童行为的经验观察。拉康观察到,婴儿在6-18个月时特别爱照镜子,并力图从镜子中辨认出自己的形象,从这时开始人与动物之间就开始显示出差别。拉康说:“对于一个猴子,一旦明了镜子形象的空洞无用,这个行动就到头了。而在孩子身上则大不同,它立即会引发一连串动作,他在玩耍中想搞清楚镜中形象的种种动作与被反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虚拟的复合体与它复制的现实之间关系,也就是说,小孩自己的身体、他人和围绕他的物之间的关系。”(13)认同需要是人类的本体论需要,它从一开始就包含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之中。在镜像阶段,人类有了第一种认同形式,也有了第一个意识形态的原型。镜像认同虽然是在婴儿阶段发生的,但它的结构和特征具有普遍性,儿童以镜像中的完满来掩盖其现实中动作的不完满性,就像用美图工具来美化照片一样,本身就带有自我掩饰的意识形态特征。在镜像认同中,一个不能自如行走甚至无法站立的婴儿,兴奋地极力挣脱支撑物的帮助,把自己的头探到镜子前,在凝视中捕捉自己瞬间的形象并把自己固定在那里,这一场景实际上包含着一切认同形式的象征母体(symbolic matrix)。“镜中形象对孩子来说,充当的是统一性和持续性、存在和无所不能的担保,而这些性能是他的身体尚不能给他的。”(14)镜像阶段是儿童的自恋阶段,在这里自恋不是对真实自我的力比多投入,而是对想象中的自我的迷恋。通过对想象界的解读,拉康让我们了解到,认同与误认的辩证法始终伴随着自我,任何的自我形象都带有误认的因素,不仅如此,误认对自我来说不是来自外界的干扰,而是自我的构成性条件。 在拉康看来,镜像类似于身体的整形术,它把破碎的、不协调的身体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协调的身体。这一理想化操作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无助和缺陷,回避与生俱来的脆弱性这一创伤性现实。在拉康看来,镜像阶段是一出戏剧,“它为沉溺于空间认同诱惑的主体生产出一系列的幻想,把碎片化的身体纳入到一个我称为整形术的整体形式中——最后被抛入到想当然的异化身份的盔甲之中。这一异化身份将在主体的整个心理发展中留下其坚实结构的印记。”(15)关于拉康对镜像阶段自我认同的解释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诊断和批判意义,帕格尔做了很好的解释:“拉康对自我的想象结构的发现势必成为一切思想潮流、学说和意识形态的肉中刺,这一发现预示着,拉康提出质疑的自主、自立自足和自我发展——这些口号迎合的是每个人的自恋倾向,它们诱发的只是他自己实际上所缺乏的东西。但是,正是在这一领域,我认为拉康的镜像理论具有社会政治意义。”(16)因此,我们可以把镜像认同理论转译成意识形态理论,把它视为意识形态自我美化的最初形式。 拉康自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向弗洛伊德的回归,实际上,他的理论意义不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拉康在精神分析传统中进行了一场方法论变革,这一变革的根本特征是把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引入到精神分析领域,为这一理论传统打开了新的理论视域和解释空间。帕格尔指出:“拉康对无意识的新解释认为,无意识具有语言形式的结构,因而也是适用于语言学分析的,这样,拉康就赋予了精神分析一种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科学形式。”(17)在我们看来,不仅拉康的想象界理论可以转译成意识形态理论,他在语言学基础上提出的象征界理论也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新的解释。关于如何理解拉康象征界理论的意识形态理论内涵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无意识是他者的语言”与“欲望是他者的欲望”这两个核心命题入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命题。拉康的无意识概念不是弗洛伊德生物主义意义上的无意识概念,而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无意识概念,在这里,无意识是语言的。斯特劳斯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出发强调,个体的言语总是受无意识的语言支配。拉康在斯特劳斯工作的基础上把这一命题运用于对欲望的分析,把结构主义方法运用到非话语领域,正如弗朗索瓦·多斯所解释的,“对于拉康的主体的欲望而言,不再是存在着任何器质之物,它与一切生理学现实都摆脱了干系,就像语言学的记号断绝了它与指涉物联系一样。”(18)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自我之所在,精神分析的目标是要把自我从本我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理性和成熟的自我。而拉康认为,无意识与语言一样都是有结构的,语言不能理解为主体内在性的自我表达,也不能理解为外在现实的观念表象,而应该理解为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症候”,在这里,索绪尔的语言学同样可以成为精神分析的工具。在索绪尔看来,任何符号系统都存在着组合关系(syntagmatik)与聚合关系(paradigmatic),这两种符号间关系又被雅各布森表述为修辞学上的转喻(metonymie)和隐喻(metaphor)。拉康认为,这两类符号关系可用于重解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总是通过伪装的形式出现的,伪装有两种最基本的形式,这就是“转移”和“浓缩”。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的“转移”的症状类似于转喻,它是以其他的表征来掩盖原初受挫的欲望,让无意识骗过自我的审查;而“浓缩”的症状类似于隐喻,它以一个能指取代另一个能指,但原来的能指并没有消失,而是与新的能指叠加在一起。于是,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概念与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的结合,拉康创造性地把精神分析学中解释的症候理解为符号学的能指概念,在这里,语言的主体不是自我,而是无意识的他者。在《菲勒斯的意义》(1958)一文中拉康说:“正是弗洛伊德的发现为能指与所指的区别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因为能指在决定那些效果时发挥着主动作用,借助这些效果,那可被表意者看上去就服从了它的标记,并通过这种激情而变为所指。”由于能指对自我的先在性,符号与主体的关系被颠倒了,“这种指能的激情于是变为人类状况的一个新的维度:因为不仅人说话,而且在人身上且通过人,它也在说;因为人的自然本性由那些于其中显示了语言结构的效果来编织,而人则变成了语言结构的材料;也因为在人身上回响着言语的关系。”(19)在这里,拉康不仅通过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和偶然性瓦解了观念和思想的透明性和自足性,而且强调人是符号的动物,同时也意味着人是无意识的动物,由此,我们就理解了拉康的著名命题:“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 正如想象性认同一样,象征性认同也产生出特殊的自我幻想。拉康把自我的认同区分为“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两种形式,前者产生于对镜像中完满形象的误认,后者产生于对象征秩序中符号意指活动主体的误认,前者是把自己的理想形象投射到外部对象身上,后者是把大他者的符号结构内化到自我之中。从发生学上说,想象的自我认同先于象征的自我认同,但从存在论上来看,人一生下来就处于象征秩序之中,并在他者的凝视和命名中获得身份和社会地位,因此,象征性认同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它主宰着自我与他者的一切关系。拉康说:“正是象征性关系决定了作为观看者的位置。正是言语这种象征性关系决定了想象的完善程度、完整程度和近似程度。这一表象使得我们可以区分出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自我理想主宰着关系的互动,而所有与他人的关系都有赖于这一互动。”(20)在镜像阶段,自我认同的对象是小他者,即幻想的自我形象,这一认同具有自恋特征,它把镜子中的他者作为自我,阶段性地满足了自己的认同欲望。但人不能永远停留在自恋状态,一旦进入到社会,就必须与他人交往,他就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象征秩序之中。从想象界过渡到象征界,意味着精神的新组织原则的诞生,社会世界是一个权威世界,如果说想象性认同是在母子关系中展开的,那么象征界则是在父子关系中展开的。进入象征界意味着人接受了共同的语言,进入到以大他者为中心构成的象征秩序之中。大能指(master signifier),或者说“父之名”(the name of Father),在拉康那里是关键的隐喻,它代表着法律和社会秩序。从想象界到象征界的过渡,意味着自我加入到能指链之中,受能指链的差异结构支配。然而,正如想象的认同是一种误认一样,象征认同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误认:“借助于语言可以进行互动和交往,但是,语言同样也可以把人的行为用意识形态来迷惑,用逻辑来歪曲。那些妄想能够留住真理、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人常常不知道,他是钻进了空洞的语言套子里。”(21)关于象征认同的意识形态特征可以这样来把握:“意识形态是男男女女被塑造成参与一个他们自己不是创造者的过程,意识形态通过给予他们以幻想履行了这一功能,让他们相信历史是为他们而创造的。”(22)“无意识是他者的语言”这一命题揭示了自我在象征领域的意识形态误认。 不仅“无意识是他者的语言”这一命题有意识形态的解蔽作用,“欲望总是他者的欲望”也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分析意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欲望批判理论立足于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的二元区分不同,拉康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对欲望做任何自然主义解释的诱惑。拉康对欲望的意识形态性质进行解释的出发点是柯热夫的名言:“欲望总是他者的欲望”。其实,对拉康来说,“欲望总是他者的欲望”这一命题不限于象征界,它从一开始就进入到人的精神结构之中。我们知道,在想象界中,儿童的欲望是成为母亲的欲望客体,但这一乱伦欲望一旦进入社会就会被阻止,因为父亲是儿童乱伦欲望实现的障碍,也是促使他的欲望转移的条件。人是语言的动物,一旦进入社会,人就必须把自己的欲望“嵌入”到社会的象征秩序之中。 拉康指出,父亲对儿童来说代表着阉割,父亲是自己欲望的竞争者,父子之间围绕着欲望展开的斗争类似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主人”(lord)和“奴隶”(bondage)的斗争。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奴隶是最终的胜利者,而在拉康这里,失败者是小孩。拉康指出,主体的生成就是欲望的表达,当一个欲望被说出来时,就在世界上造成了一个新的主体存在,但是,在社会中人的欲望是无法表达的,它必须得到象征秩序的承认才能迂回地得到表达。关于欲望与象征界的关系,拉康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如果欲望是由话语条件在主体身上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说,它是由话语的存在施加给它的,那么欲望就不是直接的需要,而是能指化的欲望;第二,如果欲望必须通过变形才能进入到话语秩序之中,并承认大他者是言语展布的核心,那么“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23)这两个观念包含着对欲望的意识形态性的指认。 对“欲望是他者的欲望”之命题,西方学者有大量的分析,这对我们理解其意识形态的论断和批判意义有所帮助。在《拉康与语言》中,穆勒和瑞恰森指出,“欲望是他者的欲望”这一命题至少包含着以下几个维度:首先,“欲望之所以是‘他者的’(主格),是因为他者被视为他的自我意识的‘他人’,就是说,主体的存在因此是欠缺的”,人被规定为非实体的否定性,在此意义上,拉康的欲望概念类似于萨特的意识概念,它总是“是其所不是”。其次,“欲望之所以是他者的(宾格),是因为主体欠缺的存在其实是他者的存在;他者的存在将填补他自己的有限性,重新恢复因为进入象征秩序被粉碎的充裕的幻觉”,在这里,他者是自我欲望的对象。最后,“欲望之所以是他者的(宾格),鉴于他的有限性,主体认为只有在他者的承认中,他才能获得合乎自己的自我意识。他者的承认刺激并部分恢复了对原初统一的基本肯定”。(24)在这里,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是指一个欲望只有成为他者的欲望才能成为我的欲望,欲望必须通过他者之镜才能产生和得到承认。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拉康的象征界理论对意识形态理论有重要的启示价值。首先,“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意味着欲望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生理性的事实,这就为超越生物主义对欲望的意识形态分析打开了一条道路。其次,主体是欲望剧场,意味着欲望总是由无意识的语言所中介,它是能指的效果,而不是先行给予的东西,因此,欲望的真正意义不能独立于意识形态的象征话语而得到理解。再次,人的欲望对象是他人欲望的欲望,意味着欲望不仅是由符号秩序所产生的,而且是由他者的目标所定向的。最后,“欲望是他者的欲望”还意味着主体性中包含着以他人的欲望来填补主体的欠缺的幻想。所有这些方面都表明,自我的透明性和自主性是不可能的。 三、实在界与创伤弥合的不可能性 拉康的精神分析破除了传统意识哲学中有关自我的自足性和透明性的幻想。根据上述论证,不论在镜像阶段的理想自我中还是在象征阶段的自我理想中,异化和误认都是自我认同的本质特征。理想自我是想象的投射,而自我理想则是对象征秩序的摄取,在前者中人们从理想的小他者那里获得了幻想的理想自我,在后者中人们在大他者的凝视中形成了自我理想。然而,在拉康看来,无论什么形式的认同,都无法弥合自我本身的内在分裂以及个人与他人的分裂与对抗。为什么自我始终是对分裂自我的一种误认呢?关键原因在于,人的精神始终面对一个无法完全能指化,同时又限制着人类一切能指活动的实在界。在拉康那里,实在界既是认识自我幻想产生的原因,也是导致自我认同的最终不可能性的界限。在拉康的主体拓扑学结构中,实在界(the real)不是经验性的“现实性”(reality),它不能在想象界中被形象化,也不能在象征界中被表征,因此,拉康说:“实在是不可能的”。(25)但恰恰是这一从来不能与人直接照面,却又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人的言语和行动的实在界构成了一切欲望的根源。基于此,拉康建议把黑格尔所说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改写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实在的”。 拉康认为,实在界抵制一切能指化,它只有在人们遭遇“创伤”(trauma)或在做梦时才会偶然照面。实在界被视为一种缺场,一种失败,一个裂缝,或者一个空洞,它抵抗一切象征化,当我们想遭遇它时它已经转身离去,但它离去时却又留下了一串串痕迹,这些痕迹可能表现为精神病的症状,或梦中的表象。不论这些痕迹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出现常常改头换面。这些源于实在界而又改头换面的东西,拉康称之为“幻像”(fantasm),“幻像常常被理解为是对真实的一种歪曲或伪装”。(26)也就是说,实在界只有通过幻像才能曲折地表现自己。 “自我是他者”,自我在想象界中被想象成满足母亲欲望的客体,在象征界中被误认为大他者的理想自我,而在实在界中,自我则以一种特殊的他者形式出现,这个他者就是拉康理论中最复杂的概念,即“对象a”(object a)。“对象a”既是一个欲望对象,又是欲望的原因,可称为“对象—原因”。关于对象a的性质,有学者解释道:“如果说非要说它也是一个对象,那这个对象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不可能性,是不可能之物,用拉康的话说,是一种彻底的匮乏。”(27)以性欲概念为例,拉康曾经说:“性欲并不存在”,因为实在界的欲望从不现身,它只能通过人们对乳房、情人脸上的斑点等之类的对象a的依恋来表现。这表明,作为欲望对象的“对象a”与欲望本身永远是分裂的。人永远不可能体验到欲望本身,而只能通过“对象a”来填补欲望的空洞。但是,“对象a”毕竟不是欲望对象本身,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本体论的差异,这种本体论差异既成了欲望满足的不可能性的原因,又成了对实在界欲望与“对象a”的同一性幻想批判的可能性条件。 拉康的实在界理论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有重要的意义,它揭露了一切意识形态都是替代性的快感生产机制。作为欲望之“原因—对象”的“对象a”是淫秽凝视的对象,实在界这一不可能之物只能通过对象a这一曲折形式出现,人们不能满足欲望本身,只能从“对象a”这个替代者那里获得剩余的、替代性的快感。因此,一切意识形态最终都是对“对象a”的幻想。在想象界中,自我以充满着欲望能量的形象出现,在象征界中,自我以力比多的象征形式出现,意识形态不论是作为一个想象认同,还是象征认同,总是围绕着对象a组织起来的。因此,以“对象a”取代真实欲望的对象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秘密。 “对象a”的概念不仅对揭露欲望自我的幻想来说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其他意识形态的解释和理解也具有范式意义。齐泽克指出,以“对象a”取代欲望对象本身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特征。比如,在封建时代,王权是空的,它只能通过国王的身体这一“对象a”来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中,人们并不特别在意民主本身,只是迷恋议会和选举等其外在形式的“对象a”。拉康的现实界理论一方面揭示了意识形态幻像的动因,一切意识形态都想填补因脱离原初的自然同一性而带来的空缺和分裂,把现实重构为一个幻想的整体。“意识形态的功能不在于为我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现实本身,这样的社会现实可以供我们逃避某种创伤性的、真实的内核。”(28)然而,意识形态对创伤的缝合是不可能完全的,由象征和符号建构出来的现实时时都面临着不可能性的实在界的侵蚀,因而总是存在着断裂和崩塌的威胁。精神分析不应该仅仅为人们提供适应现实的方法,更要在否定的意义上消除我们对现实的完整与和谐的幻想。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不仅是一种元意识形态理论,而且是元意识形态批判方法。 四、意识形态与精神分析的自我批判 在拉康看来,精神分析并非自我放弃,而是人类自我解放的事业:“在本世纪所有的事业中,精神分析是最崇高的事业,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它构成了忧虑的人与绝对知识之中介。这就是为什么精神分析需要承担漫长的,也许是没有尽头的苦役的原因,因为有训练的分析自身的目的是不能与主体对他的实践的介入相分离的。”(29)在宽泛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拉康的精神分析视为启蒙事业的继续,在具体意义上,可以把精神分析视为意识形态批判的继续。 正如弗洛伊德把人格理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冲突结构一样,拉康也把人的自由理解为无法解除的困局。在《精神分析中语言和言语的作用和领域》中,拉康说:“人的自由完全被限定在下面的构成性三角关系之中:一是为了享受奴役他人的成果,他通过以杀死他人相威胁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欲望;一是为了那些他认同的赋予人类生命以价值的理由而自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一是被征服者的自杀性放弃,这就剥夺了主人的胜利,使他处于非人的孤独中。”(30)在这里,以杀死他人相威胁而迫使他人放弃欲望是一种强制,选择为了大他者的理想而放弃自己的欲望是一种自欺,只有被统治者的自杀性自我否定才是唯一具有肯定意义的欲望形式。在拉康看来,自我总是否定性的,它只能以自杀来达到自我拯救,只要人类没有达到普遍承认的状态,这一欲望的否定辩证法就不会终结。与弗洛伊德一样,拉康认为人的存在是悲剧性的,人的自由具有悖论性质,精神分析不是通过提供虚假的幻想来摆脱人的存在的悲剧性,相反,它指认出这种悲剧性具有不可根除的本体论性质,从而要求我们承受其不可承受的否定性之重。拉康明确说:“自我的本质就是挫折,而我们的理论家现在却以其承受挫折的能力来界定自己的力量。挫折不是主体某个欲望的挫折,而是主体的欲望于其中异化的对象的挫折;这个对象越是发展,主体就越是异化于他的快感。”基于这一理解,拉康明确拒绝以霍妮为代表的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把精神分析人道化和社会化。拉康认为,以霍妮和弗洛姆等人为代表的精神分析是修正主义,它弱化了弗洛伊德的本能概念的本体论意义,试图把它改造成了人类适应现实的意识形态工具。拉康说:“美国精神分析观念已经染上毛病,热衷于个人对社会的顺应,追求行为模式的研究,以及暗含于‘人的关系’的对象化研究,这已然是无可争议的事实。”(31)为了避免使精神分析成为适应现实的意识形态工具,拉康呼吁:“回到弗洛伊德!” 在拉康那里,精神分析是自我幻想的彻底批判,它不仅是对他人自我同一性幻想的批判,也是对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者本身的自我批判。拉康曾问:“作为一种真理的方法,一种破除主观迷雾的方法,精神分析是否雄心过大,以致要对它自己的行业运用这种分析方式?”其回答是肯定的。拉康拒绝赋予精神分析者一个非意识形态的特权地位,在精神分析中,分析者与被分析者一样是身临其境的介入者,他必须投入到自己的分析对象所面临的困局之中,承受与其分析对象同样的困扰。他明确说:“我们要说,在这项共同投资的账户中,病人不是唯一的付账有困难者,分析师也必须付账。”(32)如果不把自己纳入到批判的对象之中,分析者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精神分析有自己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并不为人提供至善的目标,而要人把自己完全地交给真理,即使这种真理是残酷的、令人难堪的。在拉康看来,精神分析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角色游戏,它有四个角色:即分析者的自我、被分析者的自我、分析者的他者、被分析者的他者。分析的目的不是矫正或巩固分析者的自我,而是揭示“自我就是他者”这一根本的悖论结构。拉康把精神分析的程序和原则概括为六个方面:(1)一切精神分析都是语言的分析,言语在这里拥有特殊的权力,它既是要分析的症状,也是分析的手段;(2)分析的目的不是把主体引向完满的自我,或者塑造连贯一致的话语,而是给病人以自由,让他尝试进行自我分析;(3)赋予患者以自由是主体不能承受之重,也是主体试图逃避的;(4)因此,分析者不可能满足被分析者的要求,相反,他必须打破被分析者对他者依赖的幻想;(5)在主体拥有欲望的道路上不存在绝对的障碍;(6)欲望与言语是不相容的,因此,分析总是会遇到抵抗,这种抵抗不是分析的失败,而是它成功的条件。上述六条原则非常隐晦难懂,但可看出两层意思,一是精神分析是一门与语言有关的理论和实践;二是分析者在分析中并不具有特殊的优势,他只能帮助病人面对人类精神的困局,让他自己通过精神分析达到自我解放。对拉康来说,精神分析的症状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非知”:“主体以自己的行为使这个形象显现,这个形象不断地重现在他的行为中,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形象。不知有两层意思。他不知道这个形象解释了他在自己的行动中反复做的事,不管他是不是以为是自己做的;再者,当他提起自己回忆中的这个形象,他不知道这个形象的重要性。”(33)也就是说,患者不知道反复出现的形象与自己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这一形象的意义。因此,分析者必须帮助被分析者辨认出这个形象,并把这个形象的作用告诉被分析者。分析者并不拥有特殊的真理,也不具有特殊的权威,他只是被分析者自我分析的拐杖,分析的最终目的不是告诉病人特殊的真理,而是帮助分析者,让他获得自我分析和批判的能力,因此,任何治疗归根到底是病人的自我治疗。 在拉康看来,分析者不是真理的占有者,而是真相的见证者,“作为主体的真诚性的有责任的见证,作为他的话语的记录受理人,作为他的准确性的坐标,作为他的正直的保证,作为他的嘱托的监督人,作为他追加意愿的公证人,分析者具有书记官的性质”(34)。把分析者称为书记官,而不是称为法官是意味深长的。在这里,精神分析在实践中不仅是分析者对病人的分析,也是分析者对自己的分析。分析师必须把自己放到被告席上,因为他与被分析者一样被卷入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局面之中,分析的最终结果不是解除病人的症状,而是使他认知到自己的症状,从依赖于他者的幻想中解放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分析类似于启蒙实践。但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不同,拉康没有陷入启蒙和被启蒙者的二元论中。拉康承认,精神分析者是分析治疗过程的主导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给病人以指导。他明确地说:“天主教徒所熟知的那种道德指导意义上的良心方向是与精神分析水火不相容的。”(35)精神分析如何才能给病人以指导而又不以真理自居呢?拉康认为,分析者应该把自己视为“假定知道的主体”(subject supposed to know),而不是现实知道的主体。要了解拉康对精神分析的特殊理解,“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一概念是关键。关于这一概念,艾文斯解释说:“术语‘假定知道的主体’还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与知识的特殊关系构成分析者的独特位置;分析者知道,在他和归于他的知识之间有一道裂痕。换句话说,分析者必须知道,他仅仅占据了假定知道的主体的位置,而不能自我愚弄,以为自己真的拥有归于他的知识。分析者必须知道的,他对被分析者归于他的知识其实一无所知。”(36)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师并不拥有病人不知道的特殊真理,他拥有的唯一优势是关于精神分析的知识,特别是关于语言与症状之复杂关系的知识,以及关于病人实质状态的知识。与一般人不同,精神分析者知道,语言不是它自身,而是大他者的讯息。“让我们再次强调,主体的言语对他来说是讯息(message),首先,因为它是在大他者的位置(locus)上产生出来的。从这个位置上产生并如此这般地被言说,不仅因为他的要求服从于大他者的规则,而且因为他的要求是由他人的位置(甚至时间)得到标注的。”(37)精神分析是自由谈话的艺术,分析是一种倾听,它在病人的抗拒中把握其症状的意义。拉康强调,精神分析师是能指的分析者,“我们关于能指的学说首先是一门学术。通过这门学术我们培养的人要熟知在所指出现时能指的各种效果的方式”。(38)因为无意识是语言的,符号或能指不是自我的表达,而是实在界作用于自我的方式,通过分析揭示实在界对主体的影响是精神分析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精神分析理解为自我幻想的消解。关于这种自我消解的分析实践,杜兰德在其文章中有较好的分析。他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解构式的自我批判,这一自我批判包含“穿越幻想”(tranversing or crossing of fantasy)、“认同征兆”(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ymptom)和“主体的抽离”(destitution of the subject)三个维度。 关于如何“超越幻想”,拉康在其讨论班中指出,主体的真理并不存在于他自身之中,而是存在于一个本质上被隐蔽的对象上,这里的对象就是“对象a”。拉康的意思是,除非借助于主体与对象的特殊关系,否则真理是无法辨认的,而分析者要确认主体的“对象a”就必须穿越主体的幻想,因为主体的幻像正是“对象a”上演的剧场。在这里,“所谓穿越幻像是要意识到不可缺少的对象的必然存在,因为它的存在决定着主体与他或她的快感和语言的关系。这个对象是主体无意识地承认为是其自身的唯一特质,这种特质决定着他或她对待现实的态度。”(39)主体之所以固执于对“对象a”的幻像,是因为“对象a”是实在界的欲望通过主体的幻想认同给人留下的剩余快感。对象a表达的就是那未被满足的实在欲望本身,而穿越幻像意味着人们认识到对象a不是欲望本身,它只不过是实在界用以维持主体幻想的诱饵,是填塞实在界空洞的赝品。对拉康来说,穿越幻像可以归结为这一发现:承认大他者中的欠缺(lack in Other)。虽然实在界是空洞(void),但它需要他或她对“对象a”幻想的快感来表现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不能“为了那些他认同的赋予人类生命以价值的理由而自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主体”。(40) 在超越幻想的进程中,“认同征兆”是关键。精神分析不是对征兆的旁观式分析,而是自我投入的实践。何谓征兆?在早期文本中,拉康认为征兆是主体发给大他者的加密信息。“征兆被设想成一个符号性的意指构成,设想成某种发送给大他者的密码或加密信息,可后来又假定大他者赋予征兆以真正的意义。”因此,精神分析的目的就在于破解这一加密信息,消解由语言与意义的短路所造成的语义混淆。拉康晚年对征兆概念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发现,某些征兆即使经过分析找出了真正的原因,但仍然固执地存在着,这时他发现,征兆不是一种语义学的错离,可能是情感的无意识依恋。齐泽克指出,在拉康那里,“征兆不仅是加密的信息,它同时还是主体对其快感进行组织的一种方式”。征兆作为快感的组织形式,源于实在界的剩余快感和人对能指的激情,实在界超越了语言和象征,但它包含着不可知的、但又是根基性的剩余快感。因此,征兆就是围绕着被压抑到实在界的剩余快感而形成的关于欲望的幻像。“征兆是我们作为主体‘逃避疯癫’的一种方式,是我们‘挑选某物而非乌有’的方式,而‘挑选某物而非乌有’是通过把我们的快感捆绑在某种意指符号构成上完成的,它向我们保证把最小的一致性赋予给我们的在世中的存在。”(41)具体地说,征兆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特定个体相联系的征兆,如广场恐惧症、虐待狂、受虐狂,等等,另一类是与人类本质相联系的征兆。第一类征兆是可以通过分析消除的,但第二类征兆与第一类征兆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第一类征兆可以视为是经验的、个体的,而第二类征兆则是本体论的、人类的。对待这种征兆我们必须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所谓认同征兆本身就意味着它是不可消除的,我们必须承认欲望与快感的分裂是人类的生存论处境,我们必须承受这种征兆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并把它从非知转变为知。在拉康看来,精神病患者的症状并非完全与分析者无关,就人类对能指的激情和偏执而言,征兆是分析者与病人共同拥有的。认同症状意味着精神分析不仅是治疗的知识和技术,而且也是人类的自我反思知识。 “主体的抽离”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对主体意义的特殊理解。在他看来,精神分析的结果不是肯定性的,而是否定性的,主体必须抽空自己,放弃自己,才能成为合格的精神分析者。它意味着超越第一种自由(奴隶主的自由)和第二种自由(奴隶的“自由”)而达到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所追求的真正自由,即通过自我否定而达到自我的肯定。如何达到这种自由呢?杜南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在分析中,主体必须被建立,正如症状必须出现,幻像必须建构一样。而到结尾,主体必须把自己灭绝……这意味着假定知道的主体的灭绝,也反对从这种转变中得到的满足;它剥夺了主体在对自我理想的沉思时把自己作为理想自我的可爱之处。”(42)拉康在这里已触及一切意识形态批判的困境:相信存在着超越意识形态的主体恰恰是意识形态的症状本身,而意识到主体的终结或主体的自我幻想必然失败并非标志着精神分析的失败,恰恰是精神分析成功的前提条件。 当精神分析完成了上述三个步骤,分析者与病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当主体(病人)达到这个边界时,她或他就不再追问分析者欲望是什么,而是他或她自己的欲望还剩下多大范围。”(43)病人在认同征兆中实现了从消极的被分析者到主动的自我分析者的转变,因而摆脱了对大他者的依赖;与此同时,分析者也通过认同症状达到“假定知道的主体”的消解而实现了自我解放。事实上,真正的意识形态批判最后都会引向自身,精神分析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拉康以“我无法接受让别人而不是我自己来解放自己”(罗歇福柯语)作为精神分析的基本信条。(44) 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拉康处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启蒙与后启蒙的暧昧地带。在启蒙和批判的意义上,拉康的“不可能性的真实界”概念终止了普遍与特殊、主体与客体、知识与情感的自然同一性的幻想。换言之,它表明了意识形态终结的不可能性。“按照这种观点,普遍相信我们已经最终到达意识形态终点的情感这一事实本身可视为意识形态的在场及其控制力度的证据。”(45)因此,精神分析的意义在于对现代性残留的自我同一性的幻想的意识形态批判。“对于拉康来说,这个精神分析治疗的结尾处发生的事情就是,准确地说,我不得不接受‘不存在大他者’——没有人在远方,可以让我依靠他/她那保护性的关爱。换句话来讲,这个治疗的结果,即‘跨越’这个根本的幻想,无异于接受激进的无神论的结论。”(46)这表明,拉康的精神分析具有反权威主义和激进批判的立场。但是,拉康的不可能性逻辑也为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解放和积极的自我理想提供了概念工具,从而把自己的理论引向暧昧和危险的方向。在拉康那里,实在界是空无,象征界和大他者不过是结构这种空无的符号,我们永远无法遭遇到实在界本身,只能拥有“对象a”这一实在界的替代品,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关于自我整体性和同一性的理想都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拉康关于自我分裂和非一致性以及主体误认的必然性的观点,既可以是教条主义的解毒剂,也可能成为启蒙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融化剂。如果自我就是他人、认识即误认,那么人类任何摆脱意识形态幻想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公正地说,拉康本人并没有陷入启蒙的失败主义,也拒绝接受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但是,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确实包含着摧毁人类自我认知和理性改造世界的信心和力量的因素。 拉康的理论遗产之所以陷入上述暧昧不明的状态,根本原因在于,他把对近代的理性人道主义和主体形而上学幻想的批判转化为对理性和主体本身的批判,把现代性的困境本体论化为人类的本体论困境。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说,拉康学派排除了所有社会地获得意义的准则,其结果是把前社会的先验条件视为社会构成的条件。(47)就意识形态批判来说,拉康理论的基本困境就在于,排除了自我统一性的意识形态幻想后,也就取消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条件。 ①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8-59页。 ②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Pierre Bourdieu,The State Nobility: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X ③约翰·B.汤普逊:《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④Anthony Giddens,The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p.191-192.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⑦Anthony Giddens,"Four Theses of Ideology," Arthur and Marilouise Kroker,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Lenin in Rui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23. ⑧Anthony Giddens,The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society:Action,Structure,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192. ⑨G.Therborn,Ideology and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London:verso,1980,p.19. ⑩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Pierre Bourdieu,The State Nobility: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p.X. (11)Lawrence Grossberg,"History,Politics and Postmodernism:Stuart Hall and Cultural Stud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10),1986,pp.66-67. (12)格尔达·帕格尔:《拉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13)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2,p.3. (14)格尔达·帕格尔:《拉康》,第23页。 (15)转引自吴琼:《观看与认同:以拉康的角度》,郝立新主编:《哲学家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16)格尔达·帕格尔:《拉康》,第34页。 (17)格尔达·帕格尔:《拉康》,第53页。 (18)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19)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274. (20)转引自吴琼:《观看与认同:以拉康的角度》,《哲学家2009》,第65页。 (21)格尔达·帕格尔:《拉康》,第59页。 (22)Alex Callinicos,Altrusser's Marxism,London:Pluto,1976,p.70. (23)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p.252-253. (24)转引自马元龙:《雅各·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206页。 (25)Lacan,"The Seminar," Book XI: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London:Penguin,1979,p.167. (26)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27)吴琼:《观察与认同:以拉康的角度》,《哲学家2009》,第65页。 (28)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29)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102. (30)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102. (31)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p.42,39. (32)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p.35,216. (33)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79页。 (34)拉康:《拉康选集》,第522页。 (35)拉康:《拉康选集》,第327页。 (36)Dylan Evans,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East Sussex:Brunner-Routledge,2001,p.197. (37)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257. (38)拉康:《拉康选集》,第531页。 (39)Anne Dunand,"The End of Analysis," Jacques Lacan,Critical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I),New York:Routledge,2003,p.253. (40)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102. (41)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102-104页。 (42)Anne Dunand,"The End of Analysis," Jacques Lacan,Critical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I),p.255. (43)Anne Dunand,"The End of Analysis," Jacques Lacan,Critical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I),p.255. (44)拉康:《拉康选集》,第103页。 (45)Jason Glynos,"The Grip of Ideology:A Lacanian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Ide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6(2),2001,p.193. (46)齐泽克:《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47)朱迪斯·巴特勒、欧内斯特·拉克劳、斯拉沃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标签:精神分析理论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镜像理论论文; 自我认同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弗洛伊德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他者论文; 无意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