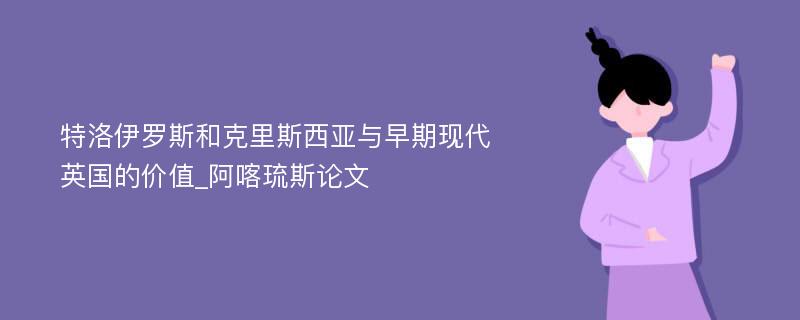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与早期现代英国的价值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洛伊论文,罗斯论文,英国论文,价值论文,克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早期现代英国剧作家而言,古我希腊和罗马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然而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1601-1602)——剧中,作为“美”之象征的海伦、“勇敢”之象征的阿喀琉斯、“智慧”之象征的俄底修斯,以及“忠贞”之象征的特洛伊罗斯,均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形象蜕变。借历史和古人抒发现代人的情怀和幽思,这本是人之常情。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由于对明日生活充满疑虑和不安,过去被想象成简单而美好的,现在则被认为是复杂、人心不古的,这样的情结也在情理之中,而且亘古有之。然而莎士比亚却拒绝将传统简单地等同于美好,或者将过去与现在进行二元对立。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过去非但不是简单美好的,而且充斥着现代价值观念,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形而上学基础亦荡然无存。 一、“荣誉”的价值重估 “荣誉”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如果把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作品做一整体考量,则会发现:荣誉时而意味着一种尚武精神或骑士风度,时而意味着高贵的出身或体面的生活方式,时而则意味社会财富的占有;荣誉有时代表着勇敢、守信、忠贞、忍耐、节制、爱共同体等个体美德,有时却是一种流动易变、虚无缥缈的舆论名声。①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荣誉”更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时代,因而经历和见证了漫长的社会价值变迁。到了莎士比亚的早期现代英国,“荣誉”的传统话语依然在延续,但其词义内涵正在悄无声息地经历着一场变革。可以说,对于“何为荣誉”这一“老问题”的讨论往往是出于解决新问题的需要。 乔纳森·多利莫在其名作《激进的悲剧: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者戏剧中的宗教、意识形态与权力》中指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剧中有两场哲学大辩论,一场有关秩序,发生在希腊军营(第1幕第3场);另一场有关价值,在特洛伊阵营展开(第2幕第2场)(Dollimore 42—43)。不过,无论是希腊人的秩序话语,还是特洛伊人的价值主张,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特洛伊战争本身。希腊人关心的是如何重整秩序,赢得这场旷日持久的远征战;而特洛伊人则必须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是否归还海伦,尽快结束战争?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战争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而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特洛伊战争的正义性却变得十分可疑。在古希腊世界,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荣誉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标准,作为指导希腊英雄们生活行动的金科玉律,无任何含混或可质疑的余地。愤怒、神明、英雄是史诗的三大主题(程志敏160),而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神明隐退、阿喀琉斯的愤怒在剧中的比重可以忽略不计,英雄则更是无从谈起,战争毫无意义:“争来争去不过是为了一个忘八和一个婊子,结果弄得彼此猜忌,白白损失了多少人的血”(2.3.65—66)②。 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是改变和决定特洛伊战争的关键,诚如有研究者指出:史诗中的阿喀琉斯退出战场是源于荣誉受到不公正的侵犯,返回战场的直接动因则是好友帕特洛克罗斯之死,因此无论是阿喀琉斯退出战场,还是重返战场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和伦理意义(萨克逊豪斯15)。在莎士比亚戏剧中,阿喀琉斯重返战场全拜俄底修斯一人的计谋所赐,与正义及城邦共同体观念几乎风马牛不相及。如该剧中涅斯托所说,“制伏两条咬人的恶犬,最好的办法是请它们彼此相争,骄傲便是挑拨它们搏斗的一根肉骨”(1.3.383—384)③。通过极力吹捧傲慢、愚蠢的埃阿斯,俄底修斯成功地打消了阿喀琉斯的气焰,而且令后者不堪羞辱,重返希腊军营参加战斗。尽管俄底修斯把这一计谋自诩为“运筹帷幄的智谋”(1.3.200),但这样的智谋与荷马、柏拉图笔下的美德和智慧完全是两码事,反而更接近马基亚维利主义式的“权谋”(policy)(Hamlin 167—183)。 更为重要的是,俄底修斯在挑起阿喀琉斯与埃阿斯之间的嫉妒纷争的同时,把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的荣誉观念偷换概念成为现代人更加关注的“名声”,或名誉,究其实质,莎士比亚笔下的俄底修斯不过是一个披着希腊人外衣的伊丽莎白时代人(Harris 106)。当名声成为荣誉的代名词,对荣誉的竞争随之成为一种“零和游戏”:某人获得某些名誉头衔,则意味着必定有人因此无法得到该名誉。正如剧中阿喀琉斯或埃阿斯注定只有一个人才能配得上希腊第一勇士的名声,而阿喀琉斯与赫克托也必须分出高下一样;其结果必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而非俄底修斯口是心非地描绘出的和谐景象。“不要放弃眼前的捷径,光荣的路是狭窄的……要是你略事退让,或者闪在路旁,他们就会像汹涌的怒潮一样直冲过来,把你遗弃在最后”(3.3.147—154)。 剧中的另一场大辩论在特洛伊阵营中展开。主帅赫克托坚决主张特洛伊人把海伦归还给希腊人,原因有二:第一,海伦本不属于特洛伊人;第二,特洛伊每一个战士的生命都像海伦一样宝贵(2.2.17—24)。赫克托的话音未落,特洛伊罗斯便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伟大尊严的父王的荣誉”岂能“和微贱的生命放在一个天平里称量吗?”(2.2.25—27)赫克托所谓的“理性”只是一种庸俗的功利计算,是恐惧和懦弱的委婉语。当赫克托反驳说,海伦不值得特洛伊人花如此代价保留下来的时候,特洛伊罗斯于是把话题转向了有关价值的讨论。特洛伊罗斯认为,所谓“价值”并非事物的固有属性或禀赋,而是“按照着人们的估计而决定的”(2.2.51—59),换言之,价值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人类的后天建构,价值与本体无关。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段价值辩论每每为后来的莎士比亚研究者当作是价值相对论(绝对论)问题的经典案例,但剧中特洛伊罗斯与赫克托其实无意于哲学论辩,他们更加关心是否“放海伦回去”(2.2.16)。因此,即便当赫克托指出,特洛伊罗斯的“价值”如果完全抛开本体对象,有可能堕落为一种“疯狂的崇拜”(2.2.55),后者也并没有就此罢休。于是二人的辩论又引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即责任与荣誉。为了说明保卫海伦是特洛伊人的责任与荣誉所在,特洛伊罗斯使用了两个十分有趣的比方:人们不能因为把绸缎污毁了以后再向商家退换,也不能因为吃饱了,“就把剩余的食物倒在肮脏的阴沟里”(2.2.69—70)。即便是抛开现代女权主义者的反感不计,“污毁了绸缎”、“剩余的食物”的意象无疑进一步加强了剧中海伦的娼妓形象,更把特洛伊人曾经珍视的荣誉价值贬低为形而下层面上的口腹之欲。不过特洛伊罗斯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此中的反讽和悖论,反而指责赫克托和特洛伊人“变成一个胆小怕事的懦夫,汩没了他的英勇的气概”(2.2.48—49)。“啊!赃物已经偷了来了,我们却不敢把它保留下来,这才是最卑劣的偷窃!这样的盗贼是不配偷窃这样的宝物的”(2.2.91—92)。 到此为止,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叙事已经完全演变为一个强盗故事。然而,彻底撕掉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块道德遮羞布的是整场事件的始作俑者——帕里斯。作为“既得利益者”,他当然主张要誓死捍卫海伦,其理由也十分简单: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为美人而战能够给人带来更大的荣誉了;相反,把海伦归还给希腊人将是特洛伊人的耻辱,让特洛伊人永远蒙羞。尽管帕里斯满口尽是中世纪骑士英雄式的豪迈语言,逻辑上却是漏洞百出:为海伦而战是光荣的,但却是不光彩的“拐骗”行为;为了洗刷由此带来的羞耻,特洛伊人不是归还海伦,而是不惜一切代价留住海伦,因为这是特洛伊人的“荣誉”。面对如此自相矛盾的论辩,赫克托也忍不住说:“你们所提出的理由,只能煽动偏激的意气,不能作为抉择是非的标准;因为一个耽于欢乐或是渴于复仇的人,他的耳朵是比蝮蛇更聋,听不见正确的判断的”(2.2.167—172)。赫克托无非是说,帕里斯真正关心的其实并不是所谓特洛伊人的“荣誉”,而是完全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和复仇欲望。而在赫克托看来,人一旦受制于血气和情欲,所谓的“荣誉”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赫克托明知:无论从道义角度,还是现实利益考虑,特洛伊人卷入这场战争浩劫,都是完全错误的行为。然而就在他即将以压倒优势赢得辩论,说服特洛伊人归还海伦、结束战争之际,却突然话锋一转:“可是虽然这么说,我的勇敢的兄弟们,我仍旧赞同你们的意思,把海伦留下来,因为这是对于我们全体和各人的荣誉大有关系的”(2.2.188—192)。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赫克托从辩论一开始就认为,这场战争压根就是一场不道德的、违背自然法的无妄之灾。早在展开这场辩论之前,他已经向希腊人发出战书。“我已经向这些行动滞钝、党派纷歧的希腊贵人们提出挑战,惊醒他们昏睡的灵魂”(2.2.207—209)。 二、欲望剧场:“这是克瑞西达,又不是克瑞西达” 从一开始,特洛伊罗斯的“爱情”就被潘达洛斯比喻成为“吃面饼”,因此与口腹之欲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吃到面饼,特洛伊罗斯不但要“先等把麦子磨成了粉”,还要有足够的耐心等“面粉放在筛里筛过”,然后“再等它发起酵来”,之后“还要等面粉搓成了面团,炉子里生起了火,把面饼烘熟;就是烘熟以后,您还要等它凉一凉,免得烫痛了您的嘴唇”(1.1.21—24)。勒内·吉拉德认为,潘达洛斯是该剧中真正的一号人物,他仿佛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告商,无休止地制造着欲望(Girard 122—123)。作为一个经验老到的皮条客,潘达洛斯深谙人类欲望的悖论:欲望来源于拖延和求而不得,实现的过程越迟缓,欲望激起的动力就越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劳伦斯神父撮合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为了化解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家族的世仇,而潘达洛斯从事的则是寡廉鲜耻的皮肉生意。挑起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彼此的欲望不但是潘达洛斯唯一之能事,也是他在剧中唯一所做之事。 第3幕第2场,潘达洛斯成功地安排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二人幽会。在特洛伊罗斯等待克瑞西达出现,初尝禁果之前,有一段独白堪称英国文学中情欲描写的绝唱:“我觉得眼前迷迷糊糊的……我怕我会死去,昏昏沉沉地倒下去不再醒来;我怕那种太微妙渊深的快乐,调和在太芳冽的甘美里,不是我的粗俗的感官所能禁受;我怕,我更怕在无边的幸福之中,我会失去一切的知觉,正像大军冲锋、敌人披靡的时候,每个人忘记了自己一样”(3.2.16—27)。评论者往往对于剧中克瑞西达的从开始时的贞洁形象突然转变到后来的荡妇形象感到手足无措,甚至会把前者的性格不一致归咎为莎士比亚创作中的瑕疵。然而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克瑞西达忠贞与否根本无关该剧之主题宏旨。在特洛伊罗斯的想象中,克瑞西达的美貌远超过被帕里斯拐走的海伦,或者毋宁说是代表着完美女人的另一个“海伦”。作为特洛伊罗斯“完美女人”的幻想投射,也许该剧中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克瑞西达,而不是后来特洛伊罗斯亲眼目睹的与狄俄墨得斯调情时所说的两个克瑞西达:“这是她吗?不,这是狄俄墨得斯的克瑞西达。美貌如果是有灵魂的,这就不是她;灵魂如果指导着誓言,誓言如果代表着虔诚的心愿,虔诚如果是天神的喜悦,世间如果有不变的常道,这就不是她。……这是克瑞西达,又不是克瑞西达”(5.2.137—146)。 值得一提的是,男欢女爱中的“情欲”与俄底修斯对“名声”的“箴言”遵循同样的逻辑:为了持久地拥有名声,那就需要不停地获得名声,否则就难逃被遗忘的命运。学者周小仪则援引鲁迅先生的名言,将之称为“爱情的再生产”(133)。在克瑞西达看来,男人对女人的情爱同样如此,女方为了获得男人持续不断的欲望,就要让后者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克瑞西达早就对特洛伊罗斯青睐已久(1.2.260—263),然而唯有通过拒绝的方式,她才能成为康德意义上的崇高的对象,而不是沦为一个欲望的对象或工具。不幸的是,一夜鱼水之欢过后,克瑞西达便开始满怀焦虑地询问特洛伊罗斯:“您已经讨厌我了吗?”(4.2.9)在多次恳请特洛伊罗斯继续留在自己的身边被拒绝以后,克瑞西达再次重复了二人幽会前她所信守的恋爱“箴言”(1.2.264—265):“我应该继续推拒您的要求,那么您就不肯走开了”(4.2.19—20)。克瑞西达的悲剧在于她必须对自己心仪的男子反复说不,才能挽留住自己的“爱情”,而特洛伊罗斯的悲剧性则在于,由幻想支持起来的欲望一旦被完完全全地实现和满足,他并没有感受到先前所期待的那种应有的满足。恰恰相反,欲望实现的那一刻也正是其幻想破灭的时刻。克瑞西达不再是特洛伊罗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完美女人,而是一个“会受寒的”(4.2.157)普通女人。作为完美女人的克瑞西达此时已经丧失了她原本所提供的那块幻想的空间。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普通女人还会进一步蜕变成一个人尽可夫的风尘女子。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双重颠覆意义则在于,该剧一方面彻底暴露了情欲满足后的虚空,另一方面则在于揭示出欲望对象本身的空虚。 莎士比亚从未表现过任何纯之又纯、超越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上的爱情。无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还是《仲夏夜之梦》,甚至《暴风雨》中,爱情必定与城邦和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这并不是说,莎士比亚将他的“爱情”故事设置于种种政治或价值空间和情境之中,或者说政治、战争、王权充当了爱情故事的政治“背景”,而是说爱情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即便是所谓的超越一切世俗束缚之上的“爱情”主张,也未尝不是一种价值判断或道德立场。如果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爱情悲剧讴歌的是誓死不渝的“爱”,《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则描写的是与爱如影相随的“欲”;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超越于世仇暴力,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爱”和“欲”则是暴力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源泉;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剧作家是一个神话制造者,而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莎士比亚成了一个偶像破坏者。从爱到欲,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夷平。爱情常常被当作批判战争、超越世俗利益,甚至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一种价值准则。 作为一种文化和价值建构的“爱”,其实隐含着若干隐在的伦理观念:爱意味着与短暂、多变的欲望相对立之永恒的时间观和超验的生命体验;爱超越于平庸、功利、琐碎的日常生活经验;通过生命审美化的独特方式,爱在政治生活的疆界之外开辟一片权力辖制之外的道德和伦理世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之爱充其量是一种“相遇”,或者借用西美尔的名言,这种“爱情”最终只是“卖弄风情”,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意义的悲剧性。④ 三、早期现代社会的秩序观念变迁 一般认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全剧由特洛伊战争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爱情故事两条主线组成,但正如哈罗德·戈达德指出,两个故事是其实是一个故事;爱情与战争、情欲与暴力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同视角下的同一主题(Goddard 5)。阿兰·布鲁姆也认为,“爱欲生活与最严肃的政治活动(即战争)之间的对立”(89—90)是该剧的核心主题。希腊人与特洛伊人因为争夺海伦而刀兵相见,但战争开始后又因为战士的恋爱而陷入僵局。特洛伊罗斯在全剧开始时称“自己心里正在激战”,根本无法“到特洛伊的城外去作战”(1.1.1—3)。接近尾声,特洛伊罗斯经历情变,赫克托阻止其参战,却被反驳说,“除了我自己的毁灭以外,我不怕任何的阻力”(5.3.59—60)。赫克托挑战希腊人的原因不是其他,而是为了“证明他有一个比任何希腊人所曾经拥抱过的更聪明、更美貌、更忠心的爱人证明”(1.3.267—269)。如上文指出,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拒绝参战,以及后来重返希腊军队,乃是出于一种原始的荣誉和正义观念,而在莎士比亚剧中这个象征着尚武精神的勇士竟然也是为情所困而拒绝参战:“伟大的赫克托的妹妹征服了阿喀琉斯”(3.3.205)。纵观全剧,莎士比亚几乎赋予了剧中所有人物以情欲与荣誉双重动机,忒耳西忒斯的愤世嫉俗之语不幸言中了该剧的悲剧内核:“我希望整个的军队都遭到灾殃;或者让他们一起害杨梅疮,因为他们在为一个婊子打仗,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2.3.15—18)。 早期现代英国对于正义、秩序、美德等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乃至西方现代社会秩序观念的演进和变革,均不是以社会制度的方式,而是以人性和欲望话语方式提出的。罗宾·黑德勒姆·韦尔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秉承着一个重要的信念:人们若希望建立一个公正社会,那就必须回到现实的人性本身。这种普世人性观念不但对莎士比亚影响至深,而且广泛植根于每个文艺复兴作家的心中(Wells ix)。培根在《学术的进步》中即批评传统道德哲学家“在上帝、美德、职责和幸运的眷顾下,他们给出了构思巧妙、美好的范例和范本;……但如何调整和驯服人类的欲望并使之与这些追求相一致,他们则完全忽略”(转引自赫希曼16—17);马基雅维利虽未系统讨论过人性问题,但已经开始意识到现实的国家理论离不开人性的知识;霍布斯则在《利维坦》中用了10个章节讨论人性问题;斯宾诺莎更是在《神学政治论》中抨击某些哲学家“他们不是按人的真实存在想象人,而是随心所欲地想象人”,并高调宣称:“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像我考察线条、平面和体积一样”(转引自赫希曼7—8)。无独有偶,对人类激情的挖掘和表现可谓是贯穿了莎士比亚创作生涯的始终,以至于哈罗德·布鲁姆甚至认为,莎士比亚“发明了人性”⑥。诚然,人类激情与城邦正义关系的哲学探讨,早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即己蔚为大观,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可谓莎士比亚以戏剧诗学的方式对早期现代社会价值建构的回应和参与。所不同者,莎士比亚在该剧中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灵魂类型,而是采用了一种“价值夷平”的方式,取消了高贵与自大、勇敢与野蛮、爱情与情欲等伦理规范的本质差异,人成了血气与情欲的混合体。 剧中忒耳西忒斯的形象颇能说明莎士比亚对荷马和柏拉图等古典美德和价值观念的改造。⑤忒耳西忒斯在《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原型叫作提尔塞特斯,也是荷马史诗中唯一来自平民的声音,但荷马出于对平民阶层作乱的本能憎恶,把他丑化成了一个形容猥琐、卑贱无耻之徒。柏拉图也在其著作中提及过忒耳西忒斯,同样对之没有任何好感。在《高尔基亚斯篇》中,忒耳西忒斯是被苏格拉底斥责的罪犯,“不配在专门为身居高位做坏事的人才准备的永恒煎熬”;在《理想国》中,忒耳西忒斯也是作为丑角出现的,藏在猿猴的躯体里准备去转世(转引自斯东42)。荷马歌颂的是贵族和英雄的勇气与武力,提尔塞特斯是一个犯上作乱者,自然与荣誉无缘。在莎士比亚笔下,忒耳西忒斯扮演了一个类似《李尔王》中的弄人(jestor)角色,既参与到故事发展之中,又超越于戏剧之外。《伊利亚特》中的提尔塞特斯只有寥寥数语,而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忒耳西忒斯的评论几乎响彻全剧,成为该剧中唯一“不偏不倚”的道德观察者。总之,荷马美化贵族,丑化了平民,而莎士比亚则既丑化了平民,也丑化了贵族。 尽管忒耳西忒斯的视角常被当作是该剧的“价值”基点,并时时以某种貌似中立的立场讽刺挖苦各路“英雄”,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可以信赖或褒奖的全知视角。恰恰相反,忒耳西忒斯本身未尝不是人性建构或欲望话语中虚构的“自然人”。人类共同体应该建立在等级秩序的基础之上,这本来无可厚非。关键问题在于,这一“自然”的等级秩序又应建立在何种“自然”的基础之上?在荷马的世界里,城邦的自然秩序建立在“荣誉”之上,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雅典奴隶制才是“自然”的。进入早期现代社会,霍布斯则把人与人彼此为战看作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洛克、马基雅维利等哲学家也分别设想了各自的“自然”概念。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无论是希腊还是特洛伊人阵营的秩序都建立在血气与情欲之上。无疑,这也是莎士比亚建构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自然”。 查尔斯·泰勒指出:在前现代社会,等级秩序不但是稳固不变的,任何僭越的行为都将受到谴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等级因其功用的不同而被赋予内在的价值。与此相反,在现代社会,尽管社会成员之间会为了彼此的需求而互相合作,但这种合作所带来的专业性本身缺乏内在的价值,利益和交换原则成为一种新的想象社会的方式。⑦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因功用不同而被赋予不同价值的社会等级秩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自我不再是生存链上的组成环节,而是一个欲望的集合载体;荣誉的原则不再是对于原来社会秩序的继承和肯定,而是成为个体对名声和地位的“私欲”。在旧秩序中,顺服和忠诚是最大的美德;在新秩序中,所有成员彼此之间都是竞争和替代关系,整个社会秩序表现出极大的流动性。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时间”成为流变的代名词,这几乎表现在剧中所有主题内容上:情欲、荣誉、名声、价值。时间不再划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只有当下的瞬间,而“瞬间”则始终在消逝的过程之中(Harmon 67)。俄底修斯对阿喀琉斯的“激将法”之所以奏效,究其本源在于它恰好戳中了后者内心深处的身份焦虑:“怎么!难道我的威风已经衰落了吗?”(3.3.68) 古希腊和中世纪荣誉与爱情叙事背后实际上是对“忠诚”、“勇敢”等传统美德的礼赞。按照巴迪欧的说法,爱是对忠诚的训练(27),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爱情故事展现的却是“忠诚”品质的陨灭;如果战争是对勇敢、克己、守信等美德的训练,那么《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展现的战争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消耗。荣誉、爱情,这些曾经赋予个体生命意义的价值信念分别变成了转瞬即逝的名声和永远无法真正满足的情欲,随之而来的是个体灵魂深处对生命本身的幻灭感和无聊感。西美尔对于生命意义有过一段非常深刻的形而上学批判: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而如今对金钱的渴望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然而导致“生命本身的无聊感”的并非是货币本身,而是货币被误认为是生命意义的价值“错位”(13)。在此种意义上,莎士比亚所关注的并非是早期现代或现代、后现代的文化特征,而是人类的生存和价值世界本身。 ①以上种种荣誉观念在《威尼斯商人》、《裘力斯·凯撒》、《亨利四世》、《克里奥莱纳斯》、《哈姆雷特》、《奥赛罗》等剧作中均有体现。 ②本文所引译文均采用朱生豪译本《莎士比亚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引文后所标幕次、场次、行次均采用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Stephen Greenblatt,ed.The Norton Shakespear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7)]为准,后文将随文标出该著作名称首词和幕、场、行次,不再另注。 ③着重号为笔者后加,以示强调。 ④如刘小枫在《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一书的“导读”中指出,“卖弄风情”这样的两性关系现象,在西美尔那里也成了一个严肃的形而上学命题(转引自西美尔13)。“这种关系自身已经将生活中或许最黑暗、最悲剧性的关系,隐藏在生活最令人陶醉和最魅力四射的形式背后”(西美尔169)。 ⑤荷马史诗中,忒耳西忒斯(Thersites)的名字来自小亚细亚北海岸的伊奥里斯方言“thrasos”,意为“鲁莽、蛮横大胆”。 ⑥参见Harold Bloom,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New York:Longman,1999)标题。 ⑦如查尔斯·泰勒指出:新教改革以后,个体的工作职业都被看做是上帝对于个体的“呼召”/职业(calling)。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不但在上帝看来都是平等的,而且都有其尊严和意义,建立在不同社会功能而具有等级差异的社会秩序越来越不受欢迎(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