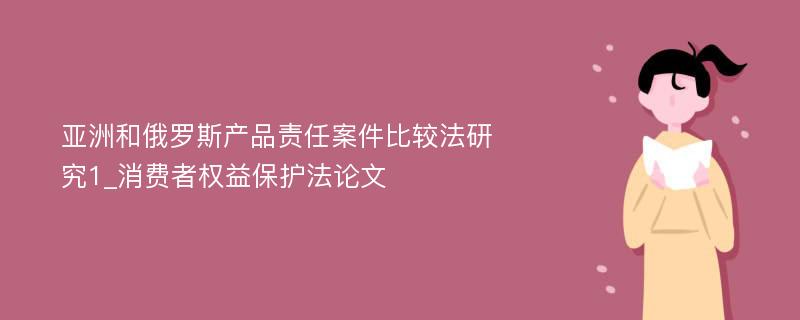
有关产品责任案例的亚洲和俄罗斯比较法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法论文,俄罗斯论文,亚洲论文,案例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082-17
一、有关产品责任法的亚洲和俄罗斯比较法的一般性问题
在产品责任立法方面,亚洲和俄罗斯8个法域的基本情形是:
(一)产品责任法在形式上表现为成文法和判例法
在进行比较的8个产品责任案例法律适用的法域样本中,有6个样本是成文法立法,即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大陆、台湾地区、澳门地区以及俄罗斯;有两个是判例法立法,即印度和马来西亚。在这两个不同的立法传统的法域中,体现了鲜明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侵权法有关产品责任立法的传统和特点。
不过,即使在英美法系的亚洲法域,目前也有成文法的产品责任法。例如马来西亚1999年《消费者保护法》规定了比较全面的产品责任法规则。在大陆法系法域的侵权法中,也逐渐出现判例法的影响,法院通过典型案例,指导和协调产品责任法的具体适用,统一法律适用规则。在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最高仲裁庭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和仲裁庭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下级法院或仲裁庭不负有法律义务遵循先例,也不必去探寻不遵循先例的理由;但在近20年来,最高法院的判决或其他决定在司法实践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法律渊源的作用;联邦最高法院和最高仲裁庭都定期发布公告,最高法院对司法实践的观察和命令可以被认为是俄罗斯侵权法和其他法律的渊源之一,因为它们意在统一对制定法的司法解释。
(二)在规制产品责任的成文法中有多种不同做法
亚洲和俄罗斯的大陆法系法域制定产品责任法,在立法上也有不同。在日本,《制造物责任法》是专门的产品责任基本立法。在中国大陆地区,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主要由《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立法作出规定,产品责任的一般规则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五章,但产品的概念、免责事由等,规定在《产品质量法》中,警示说明缺陷(经营缺陷)规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中。在中国台湾地区,规制产品责任的立法有“民法”的有关规定,还有“消费者保护法”,特别是后者在规制产品责任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中国澳门地区,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生产者的一般民事责任规定在《民法典》中,对生产者适用风险责任即无过失责任原则的产品责任,则规定在澳门《商法典》中。韩国的《产品责任法》于2001年1月12日制定,2002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规定了生产者的无过失责任即危险责任原则。在此法之前,因产品瑕疵导致的损害是通过一般侵权行为法或者合同法来救济的,但这并不能完全保护受害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特制定了《产品责任法》。俄罗斯在《民法典》之外,也规定了《消费者保护法》,规制产品责任。
在采用英美法系的两个亚洲国家中有关产品责任的法律,马来西亚有英国普通法、本国司法判例和已经法典化的制定法,例如《合同法》、《消费者合同法》、《货物买卖法》以及《消费者保护法》等;印度实行普通法,除了有大量的判例法之外,还有成文法,如《消费者保护法》和《竞争法》等,但对产品责任制度还缺少具体的制度规定。
(三)对产品概念范围的限定不同导致产品责任法调整的范围不同
尽管产品责任法已经被全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接受,但8个亚洲和俄罗斯法域产品责任法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其中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各国产品责任法对产品概念范围的限定不同,导致各法域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不同。正因为如此,对于本次会议讨论的三个典型案例,也出现了适用法律各有不同的情形。
1.产品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8个法域的产品责任法在对产品概念的界定中,确定产品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的立法例较少,只有中国台湾地区采此立法例。其“消费者保护法”没有对产品的概念作出界定,但“消费者保护法施行细则”第4条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所称之商品,系指交易客体之不动产或动产,包括最终产品、半成品、原料或零组件。按照这一规定,该法域的产品责任不分动产或不动产,均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关于无过失责任的规定。因此,对于会议讨论的桥梁垮塌案中的桥梁虽为不动产,但适用其“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关于产品责任的无过失责任规定,属于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
2.产品只包括动产,不包括不动产
在8个法域的产品责任法中,多数不认可产品中包含不动产。日本《制造物责任法》规定产品范围只包括动产,不包括不动产。如果建筑物的缺陷是由其构成部件、材料的缺陷引起的,受害人可以向构成部件、材料的制造者追究产品责任,但建筑物本身造成的损害应当适用《民法》关于土地工作物损害责任的规定,或者《国家赔偿法》关于公共营造物的规定,确定侵权责任。中国大陆地区的《侵权责任法》以及《产品质量法》都认为产品是经过一定加工的动产,不包含不动产;在制定《侵权责任法》时,专门制定了第86条,将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的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规定为设置缺陷责任和管理缺陷责任,类似于日本法的土地工作物损害责任或者公共营造物责任的规则,不适用产品责任的规定。马来西亚《消费者保护法》关于产品范围的规定也不包括建筑物、构筑物等不动产。中国澳门地区《商法典》第86条第1款将产品界定为“任何动产”,包括“与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组装的动产”,将不动产排除在产品范围以外,至于何为动产,何为不动产,则由作为一般法的民法典规范。②在澳门,商法典第86条第2款与修改前的葡国第383/89号法令相同,规定“来自土地、畜牧、捕鱼及狩猎之产品,如未加工不视为产品”。为了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修改商法典的咨询文本建议废止第86条第2款规定,以扩大产品的范围。韩国《产品责任法》规定产品的范围仅限于动产,不动产不能成为产品责任的客体;但构成不动产的一部分则可属于产品,如电梯或冷却设施等,是构成不动产一部分的动产。
3.关于血液和血液制品是否为产品
多数亚洲法域不把血液包括在产品责任法的产品概念范围之内,不适用产品责任法的规定。不认可血液为产品的法域,一般都区分血液与血液制品的界限,血液制品造成的损害适用产品责任法。但有的法域认为,如果血液经过一定的加工,可以认定为产品,例如韩国《产品责任法》认为,血液或身体器官不属于产品责任的调整对象,但如果并不是血液本身,而是从血液中提取某种成分后进行加工的血液制品,即用于输血,例如血液中添加保管液或抗凝固剂等进行人工加工处理的,则属于产品。《血液管理法》第2条第6款规定,血液制品是指“以血液为原料进行生产的医药品”[1](P12)。中国澳门地区认为,血液不是产品,但是经过一定加工的血液以及血液制品属于产品范畴。
关于血液制品,多数法域认可其为产品。日本在制定《制造物责任法》时,有一部分意见认为,考虑到血液制品对社会具有的有用性,在血液制品缺陷的认定时应进行特别处理,如果把血液制品作为制造物归入制造物责任的对象之中,会给从事血液供给的事业者带来极大负担,导致医疗机构所需血液制品的稳定供给十分困难,故除经高度加工处理的之外,不应作为制造物责任的对象。但日本政府与国会却都表明了“既然血液制品和疫苗都是加工而成的动产,当然属于制造物”的立场,《制造物责任法》采纳了这一立场。
中国大陆地区的《药品管理法》认为血液制品是药品,适用产品责任法调整。对于血液,《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在缺陷医疗产品概念之中,在理论上有不同看法,但认定供医疗使用的血液为准产品,是比较贴切的[2](P413)[3](P355),与欧洲的非标准产品的概念相似。
(四)关于产品缺陷的界定
对于产品缺陷,8个法域的产品责任法都认可产品责任的缺陷主要包括:(1)设计缺陷;(2)制造缺陷;(3)警示说明缺陷。这种缺陷也叫作经营缺陷、标识缺陷或者市场缺陷,对于存在合理危险的产品应当进行必要、充分的警示说明,防止危险发生,未进行必要、充分的说明警示的,即为经营缺陷或者警示说明缺陷。在8个法域的报告中,讨论产品缺陷的直接论述不多。以中国大陆地区的规定为例,中国大陆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规定:“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经营者违反这一法定义务,即构成警示说明缺陷。某化工厂生产喷雾杀虫剂,说明中没有警示说明不正常使用的损害后果,造成喷洒过量引发爆炸,法院认定构成警示说明缺陷。③
中国大陆地区还认可跟踪观察缺陷,对于在产品推向市场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无法确定产品有无缺陷的,应当确定生产者的跟踪观察义务,并确立召回制度,违反者,为跟踪观察缺陷。[4](P717-718)中国大陆地区《侵权责任法》第46条规定:“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国澳门地区规定产品缺陷比较严格,《商法典》第87条规定:“一、考虑到包括外表、特性及可作之合理使用在内之各种具体情况,一项产品于开始流通时未能提供合理预期之安全者,则视为有瑕疵。二、产品并不因后来有另一更完善之产品在市场上流通而视为有瑕疵。”在考虑了所有情况后,若产品未给人们提供有权期待的安全程度,该产品就是有缺陷的。《产品安全的一般制度》对于产品瑕疵的定义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赋予了消费者更加给力的保护。④其第3条规定的产品安全的定义几乎接近极限:安全产品的定义是指“产品未显现出任何危险”,或者“仅显现出轻微危险,只要该等轻微危险与产品的使用兼容且根据保护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的严格标准判断其为可接受者”。“安全产品”意味着要么不存在任何危险,要么它最小程度的危险是在消费者的把握之中的。对于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来说,似乎显得有点苛刻,因为其中认定产品安全的标准相当高,即便轻微的危险也可能被认定为缺陷产品。
对于案例中讨论的自行车刹车片存在的问题,8个法域都认为属于设计缺陷,对于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五)对不同物件造成的损害的不同救济方法
由于各法域对于产品概念的界定不同,因此对于造成损害的不同物件,法律规定了不同的救济方法。下面归纳的是主要情形。
1.不认可为产品的物件损害责任
对于产品责任法不认可的物件损害责任,各法域侵权法都有救济的办法。例如,日本《制造物责任法》认为不动产不是产品,对于不动产所造成的损害,因土地工作物(建筑物等,包含其他和土地在功能上成为一体的设备,比如铁道道口设备、轨道设备;以及在对土地加工时所做成的、与土地成为一体的设备构成的“土地工作物”,例如高尔夫球场、采石场等)的设置或者保存中存在瑕疵而造成的损害。第一,依照《民法》第717条第1项第一句规定,由该工作物的占有人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占有人能证明自己在土地工作物的设置或者管理上没有过失的,则依照该条第1项第二句规定,免予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土地工作物的所有人对被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所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无过失责任。依照判例,土地工作物的瑕疵是指对于通常预计到的危险,该土地工作物处于一种缺乏通常所应具备的性质的状态。第二,对于因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所管理的“公共营造物”(不仅限于不动产,也包括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所管理的动产、动物)的设置或者管理上的瑕疵所造成的损害,依照《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由管理它的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种侵权责任营造物责任为无过失责任。依照判例,营造物的瑕疵是指,对于通常预计到的危险,该营造物处于一种缺乏通常所应具备的性质的状态。国家或者公共团体即使证明自己在“营造物”的设置或者管理上没有过失的,也无法免除责任。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情形与日本的规定大体相似。
中国大陆地区的《侵权责任法》认可动产和血液为产品和准产品,但不认可不动产为产品。对于不动产设置缺陷和管理缺陷造成的损害,适用该法第85条和第86条规定,前者是不动产脱落、坠落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后者是不动产倒塌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是不动产存在瑕疵,例如存在的其他危险,所有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依照《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规定,确定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对不认可血液为产品的法域,对不合格的血液造成的损害,不适用产品责任法进行救济,但可以根据一般侵权行为或者合同法的规定确认民事责任,应当遵守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韩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的法律都是如此。
2.对认定为产品责任的产品损害的不同救济方法
在亚洲和俄罗斯,即使产品造成了损害,除了产品责任法的救济方法之外,还有其他救济方法。对于产品造成损害的通常救济方法是:
(1)产品责任的方法
对于产品责任,各法域的立法都认可适用无过失责任(亦称为风险责任、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确定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不须具备过错要件。如中国澳门地区法律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及专业化分工的深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生产者的合同责任及过错责任并不足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而无过失责任则提供了一个偏向于对消费者保护的解决方法。
(2)一般侵权行为的方法
即使认可某种物件属于产品的法域,对于产品造成的损害,多数准许受害人通过一般侵权行为的救济方法予以救济。在马来西亚、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构成产品责任,可以依据一般侵权行为或者疏忽侵权而提出诉讼请求,证明对方在造成自己的损害中存在过失,因此得到损害赔偿救济。只有在中国大陆地区,产品责任与一般侵权行为的救济方法相同,不论受害人提供产品责任的证明,还是一般侵权行为的证明(不证明过错或者证明过错),在损害赔偿的后果上并无二致,因此,受害人不会不顾自己的证明负担以及诉讼成本而刻意证明产品责任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要件。这样的规则是比较僵化的,不具有法律适用的适当弹性,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在尚未建立产品责任制度的法域,例如印度,没有专门的详细规定产品责任全貌的成文法。在近期的一个高等法院的判决中,法官称,印度目前没有认可严格产品责任的法理,但是在Bhopal燃气案中,最高法院称有必要进行合适的立法,当不同的国民在印度的土壤上开启其活动时,他们应受到各自不同条件的约束。有见解积极倡导采纳严格责任(或无过失责任)的立法,鉴于印度大众民智未开和司法救济的水平,考虑以下策略,应制定规范市场准入产品的立法,而不是赋予消费者依产品责任主张救济的权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Donoghue v Stevenson案的判决及其蕴含的原则(即邻人原则)被引入到法律领域,此后,生产者对缺陷产品的责任一直在增长中。毫无疑问,生产者对产品的终端使用者负有注意义务。终端使用者或者是产品的消费者(即以支付价金购买产品或货物的人),或者是免费的使用者(未支付对价的人)。购买产品的人可能会向特定的“消费者争议救济机构”提出诉求,1986年《消费者保护法》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个有效的机制。
(3)合同责任的方法
对于产品造成的损害,如果主张依据合同进行救济,可以根据加害给付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例如,中国澳门地区认为,与产品瑕疵责任不同,如果依据合同进行救济,则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权利主体只包括消费者,即与产品的提供者有直接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不包括因产品缺陷受害的第三人,这也是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在权利主体上的区别。中国大陆地区法律认可产品责任的受害人如果是合同当事人,可以基于《合同法》第112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依照该法第113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对于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普遍的规则是,按照合同责任进行救济的模式,受害人的请求权基础是合同关系。对于不属于合同关系当事人的受到损害的第三人,依据合同法不能获得必要的救济,必须依照侵权法的规定,才能够获得损害赔偿责任的保护。
3.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的不同赔偿责任
在亚洲和俄罗斯法域中,有的法域明确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实行无过失责任,不证明或者不能证明生产者、销售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进行索赔,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的赔偿责任是限额赔偿;受害人能够证明生产者、销售者对于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的,可以依照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实行全额赔偿。这样的规定是特别有道理的,原因在于,受害人能够证明过错和不能证明过错,其支付的诉讼成本不同,而且生产者、销售者的可受谴责程度也完全不同。
中国大陆地区的产品责任法并未实行这样的规则,无论受害人是否证明生产者、销售者有过错,都予以全额赔偿。只有在高度危险责任的场合,才规定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限额赔偿,且只要有限额赔偿的规定,也不许在证明了行为人有过错时可以全额赔偿。这些做法存在较大的缺陷,应当借鉴其他法域的科学做法予以改进。
(六)在产品责任中引进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
在本次会议讨论的典型案例中,没有涉及产品责任的惩罚赔偿责任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在大陆法系侵权法以及产品责任法中并不是主流的问题,但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采用了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对于遏制产品和服务欺诈违法行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以提供给世界各国的侵权法予以借鉴。
中国大陆地区《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在这个规定中,没有规定究竟应当怎样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正在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此制定了新的条文,正在讨论中。内容是: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的,仍然向消费者提供的欺诈行为,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两倍以下的民事赔偿。在讨论中,学者普遍认为这个赔偿标准过低,建议规定三倍以下为好。立法机关特别重视这个意见,最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草案已经规定实际损失三倍以下惩罚性赔偿金的条文。
中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51条规定,因企业经营者之故意所致之损害,消费者得请求损害额三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金;但因过失所致之损害,得请求损害额一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金。这个规定,比中国大陆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的规定更重。
二、关于刹车片故障案的法律适用
刹车片故障案的简要案情是:X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开始使用其经过测试后发现比传统材料更便宜、更耐用且总体而言更有效的新材料来生产刹车片,知道在特别情况同时具备时可能存在突然失灵的微小风险,但仍然采用了新刹车片制造自行车,仅产品使用说明书中用小字体对失灵的可能性做了说明。A使用这种自行车时造成自己损害和路人B的损害。⑤这是一件典型的产品责任案件。对此,亚洲和俄罗斯8个法域的认识完全一致,几乎没有例外,都认为自行车属于产品,由于其存在缺陷而造成使用人和他人的人身损害,应当依照产品责任规则确定侵权责任。在法律适用的细节上,则存在较多的不同。具体问题是:
(一)关于确定责任的归责原则
关于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7个法域采无过失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只有印度尚未建立完善的产品责任制度,不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
中国大陆地区《侵权责任法》第五章专门规定产品责任,其中第41条至第43条规定,产品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无论是中间责任还是最终责任,都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只要产品有缺陷,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害,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产品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的中间责任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承担最终责任为过错责任原则,但在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生产者或者供货者的,仍然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5](P308-309)日本原来由制造物引发的责任适用《民法》第709条规定的过失责任,1995年7月1日正式实施《制造物责任法》,采纳无过失责任原则。马来西亚对于产品责任,可以根据疏忽责任法认定责任,但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不必证明生产者一方的过错,这正是将严格产品责任引入该法的原因,即减轻消费者的证明责任。中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规定,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的企业提供商品投入流通,须确保其安全性,商品或者服务具有危害可能性时须为必要的警示说明,该条第三项还特别规定:“企业经营者违反前二项规定,致生损害于消费者或第三人时,应负连带赔偿责任。但企业经营者能证明其无过失者,法院得减轻其赔偿责任。”这一规定确认,产品责任一般采无过失责任,其特殊的“企业经营者能证明其无过失者,法院得减轻其赔偿责任”的但书规范,被认为是“具有台湾特色之无过失衡平责任”[6](P257)、“轻度、相对无过失责任”[7](P202)。这一规定极具特色。中国澳门地区《商法典》第85条第1款规定:“作为生产商之商业企业主不论有否过错,均须对因其投入流通之产品之瑕疵而对第三人所造成之损害负责。”在澳门法律制度中,无过失责任为例外性规定⑥,产品责任适用这一归责原则。俄罗斯的产品责任法从“买者责任”转变到“卖者责任”,即卖者对缺陷产品所造成的人身损害承担严格责任,除非生产者或销售者能够证明损害或伤害是由不可抗力或消费者未遵守使用或存储产品的规则造成的,否则责任将会被推定。
印度的产品责任由普通法原则调整,没有专门的详细规定产品责任全貌的成文法。在学说上有积极倡导采纳严格责任立法的建议,但意见是制定规范市场准入产品的立法,而不是赋予消费者依产品责任主张救济的权利。从总体趋势观察,产品责任法的发展必然是从过失责任向严格责任发展,但目前印度法院或消费者救济机构适用严格责任规则裁判案件还有待时日。
(二)使用有缺陷的零部件构成产品设计缺陷还是构成发展风险抗辩
在产品责任领域,生产者将更便宜、更有效但在特别情形下存在突然失灵微小风险的新材料做成的零部件应用于产品中,造成使用人和他人损害,究竟属于产品设计缺陷还是属于发展风险(开发风险)抗辩,8个法域产品责任法的意见基本一致,这不属于发展风险抗辩,而是产品设计缺陷。
日本法认为,即使生产者对此提出了开发风险的抗辩,但因在一定条件下自行车的制动器垫不发挥其功能的风险已被认识到,故开发风险的抗辩不会被认可。这是因为,将自行车投放流通,具有对相关人的生命、身体造成损害的危险性,具有以创造危险源的责任,属于缺陷。在中国大陆地区,发展风险被《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3款所确认,即“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产品的零部件在特殊情形下可能失灵是已经被发现了的缺陷,生产者不能以发展风险进行抗辩,属于产品设计缺陷。
韩国法认为,刹车片故障案例中的产品缺陷是设计缺陷,而非标识缺陷(警示说明缺陷)。同时,也不认为存在发展风险的抗辩。澳门法认为,自行车刹车片在特殊情况下失灵属于产品缺陷,因为该危险与产品相结合,并在可预见的情况下会发生失灵,且在说明书中只用了小字提醒未能达到让消费者明确知悉的效果,其危险并不能说是在消费者的把握之中,构成缺陷,对受害人A和B都需要承担过错侵权责任。
马来西亚法也认为产品存在缺陷,生产者由于提供了带有缺陷刹车片的自行车,可以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32条规定,以违反默示担保规则责令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也可以认为该自行车的安全性不符合通常有权期待的安全性,能够证明《消费者保护法》第68条(1)所规定的要件,即可确认该产品存在设计缺陷,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包括使用人和受到损害的第三人
关于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人,8个法域多数认为既包括产品使用人,也包括并非使用该产品的其他第三人,但也有少数法域认为受到损害的其他第三人不属于产品责任法保护范围,不享有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日本《制造物责任法》第3条规定,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不仅向使用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也要向造成损害的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理由是产品的安全性不仅关乎使用人的生命、身体安全,亦涉及其他人的人身安全;且一般理性人对于产品的安全性期待中,既含有使用人的期待,也含有其他第三人的期待。中国大陆地区《侵权责任法》第41条规定的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为“他人”,在解释上认为既包括缺陷产品的使用人,也包括受到缺陷产品损害的第三人,并未将请求权人局限于合同当事人。[8](P247)中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违反前两项规定,致生损害于消费者或第三人时,应负连带赔偿责任。”只要消费者和第三人因商品欠缺安全性导致损害的,均可以请求赔偿。韩国法认为,产品责任的受害人不仅限于购买人,也包括第三人。购买人免除对造成损害的第三人的责任,生产者对第三人的损害承担责任。中国澳门地区《商法典》第85条第1款规定:“作为生产商之商业企业主不论有否过错,均须对因其投入流通之产品之瑕疵而对第三人所造成之损害负责。”这与《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一样,法例并没有指定索偿人的范围,只说因缺陷产品导致他人损害,生产商要对第三人所造成之损害负责。俄罗斯《消费者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结构、制造、配方或其他货物(工作、服务)的缺陷给消费者生命、健康或财产造成的损害,应予充分救济,任何受害人均有权请求上述赔偿,无论其是否与卖方(实施人)存在合同关系。
在印度,认为路人在同一场事故中受到伤害主张赔偿,起诉直接造成其损害的自行车主最为容易,因为很容易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是自行车主的行为的直接后果。但自行车主的经济能力有限,较难获得充分赔偿。如果路人选择起诉生产者,唯一的路径就是到普通的民事法院依据普通法进行诉讼,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以使法庭采信刹车片使用了缺陷材料等情况,这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而且印度也不存在这一类型的明确先例。学者认为,印度缺乏产品责任法,会阻碍因缺陷产品受到损害的第三人的索赔。这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同时也说明了产品责任法对于救济受害人损害的必要性。
马来西亚法规定,对于缺陷产品致第三人受到损害,可以根据疏忽侵权要求赔偿,因为第三人是这同一事故中被卷入的行人。如果第三人根据《消费者保护法》规定的产品责任进行索赔,将十分困难,因为该法仅确认消费者的求偿权,而消费者被界定为产品的购买人或使用人,路人不是该产品的购买人或使用人,因此不能根据该法对缺陷产品的生产者索赔。
在俄罗斯,买受人可以选择依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起诉,第三人只能依侵权起诉。不过,无论是侵权法的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作为第三人的受害人和作为买受人的受害人不存在差别,受到同等保护。
(四)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是否包括产品自损
在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中,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缺陷产品在造成他人损害的同时造成的产品自身损害即产品自损(也叫产品自伤),是否包括在产品责任的损害之中,能否依照产品责任法进行救济。对此,亚洲和俄罗斯各法域有肯定主义和否定主义两种立场。
中国大陆地区《侵权责任法》采明确的肯定态度。该法第41条规定产品责任构成要件中的损害要件,与《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的内容不同,区别在于,前者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后者为“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差别十分明显。《侵权责任法》改变损害表述的立法意图是,这一损害既包括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损害,也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这样有利于及时、便捷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9](P226)多数学者赞成产品责任的损害范围包括产品自损的解释,即产品责任的损害是指缺陷产品造成的产品本身的损害以及产品以外的人身和财产损害。[2](P226)不过,这是两种不同的损害,一是侵权法救济的损害,一是合同法救济的损害,这种界限还是应当严格区分的。
马来西亚法对此的态度比较折中。法院判例的原则不允许赔偿产品自损的损害,因为这被认定为纯粹经济损失。不过,对于瑕疵建筑物可以要求赔偿纯粹经济损失,如果该损失是可预见的。有学者提议,如果法院准备像在瑕疵建筑物那样适用同一原则,对缺陷产品索赔就是可以的。中国台湾地区学说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是否包括自损有争议,但通说采否定见解[10](P80),理由是,消费者对于商品享有的经济利益,属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或不完全给付责任等契约责任法保护的法益范围,不宜由本质属于侵权责任的产品责任法予以规范。这是更多的法域采纳的立场,例如日本《制造物责任法》第3条后段规定:“但损害仅发生于该制造物时,不在此限。”
(五)产品提供的小字体提示可否作为免责事由
产品生产者在制造产品时,知道其材料或零部件有造成损害的一般性危险或者合理性危险,采取在产品上提供风险警示及避免风险的说明,否则为警示说明缺陷,这是亚洲各法域的基本立场。对于产品中存在的危险构成设计缺陷,不能以已经做出了小字体的警示而免除责任或者减轻责任;不过,也有的认为这种微小缺陷属于合理危险,通过充分警示说明可以免除责任。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产品责任法都认为,既然已经明知产品的零部件存在缺陷有可能造成他人损害,即构成设计缺陷,因此不论其是否进行警示,都不存在警示缺陷的责任,而应当承担设计缺陷的责任。因此,对于产品设计缺陷做出小字体的警示说明,并不对缺陷产品生产者承担侵权责任发生影响。中国澳门地区法律认为,在本案中,即使生产者在自行车的说明书中明确标明了刹车片可能存在的危险,也不可免除其责任。
马来西亚法认为,警告是关于产品中已知危险进行警示的信息,对于保护消费者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消费者避免产品中的风险。生产者未遵从警示而发生损害时,警示能够使生产者免担责任。用小字进行产品危险的警告,不符合警示说明充分的要求,公众会期望这一重要警示是以消费者容易看到的大小作出,根据该警示的尺寸,将认定该警示有缺陷,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产品责任法对此的一般原则是,设计缺陷和警示说明缺陷的区别,在于产品中包含的危险性的大小。如果产品中的危险已经构成不合理危险,即为缺陷,警示说明不能免除生产者的责任。如果产品中包含的危险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而是合理危险,通过充分的警示和避免危险的使用方法的说明,就可以避免危险发生,则是构成警示说明缺陷的事实依据。产品的零部件存在危险,并且无法通过使用正确方法就能够避免,就不存在通过警示说明免除责任的可能性,不能适用警示说明缺陷的规定。[4](P717)
(六)产品责任的承担规则
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构成产品责任,究竟由谁承担赔偿责任,涉及缺陷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责任问题。至于生产者和销售者究竟应当怎样承担责任,8个法域的规定有所不同。
中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第3款和第8条明确规定,企业经营者包括设计、生产、制造商品的企业经营者,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事经销的企业经营者,就商品或者服务所生损害,与设计、生产、制造的企业经营者连带负赔偿责任,但其对于损害的防免已尽相当注意的,或者纵使加以相当注意仍不免发生损害的,不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承担连带责任的明确规定。
中国大陆地区《侵权责任法》规定生产者、销售者承担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在损害发生之后,受害人可以请求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这属于中间责任;承担了中间责任的责任人如果不属于应当承担最终责任的责任人,可以向最终责任人请求追偿,实现最终责任由应当最终承担责任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负担。
韩国依据《产品责任法》第3条第1款,生产者应对受害人的人身、财产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马来西亚《消费者保护法》既规定货物销售者对消费者负责,也规定生产者对消费者负责。消费者依据该法第3条规定,有权根据该法第五和第六部分向产品销售者索赔,或者根据该法的第七部分向产品生产者索赔。
在俄罗斯,《消费者保护法》序言中定义的生产者、出售者或执行者(《民法典》第1095条和第1096条),按照《民法典》第54章“商业特许经营权”第1034条规定,如果产品质量不符合标准,特许权人可能要为针对被特许人提起的诉讼承担替代责任。对缺陷产品所造成的损害,原告可以选择向出售者或者生产者主张救济。
按照法理,即使立法规定生产者与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这种连带责任的性质也应当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因为在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最终责任的时候,必须是一个人独自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不是由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各自的赔偿责任的份额。
(七)设计人属于生产者的雇佣人的责任
本案在讨论中提出一个假设,即如果设计人受雇于在生产者的实验室工作,或者设计人独立承揽了该研究,却隐瞒了新材料存在的危险,在产品责任法的适用中会出现何种不同的情形。亚洲和俄罗斯各法域的情形是:
按照中国大陆地区《侵权责任法》规定,设计人属于生产者的组成部分,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按照产品责任的一般规则确定赔偿责任承担。如果设计人独立承揽该研究,且隐瞒缺陷,致使造成损害,应当适用该法第44条规定,先由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责任,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了责任之后,可以向设计人等第三人进行追偿。这样的规定可以更好地保障被侵权人的权利实现,但存在一个缺陷,即在生产者和销售者都丧失赔偿能力的时候,会出现索赔僵局,对此,应当准许受害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对设计人进行索赔。[11]
中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规定,无论设计人是生产者的研究人员,还是独立承揽人,缺陷产品的受害人都有权向商品制造人请求赔偿;不同的是,如果设计人是生产者的研究员,为替代责任;如果设计人为独立承揽人,则商品制造人在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有权向设计人追偿。
中国澳门地区认为,如果设计人是受雇于生产者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其隐瞒了新的刹车材料可能失灵的风险,该案件的损害赔偿责任依然由生产者承担。如果设计人是独立承揽了该研究,隐瞒了新的刹车材料可能失灵的风险,则该损害赔偿责任就由设计人承担。
在日本,设计人属于生产者的成员时,在适用《制造物责任法》的时候,因为产品责任是无过失责任,即使生产者提出无过失抗辩,其责任也得不到免除。如果设计人是独立经营者时,其对于明知却隐瞒新材料的缺陷存在过失,受害人可依据《民法》第709条请求设计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况,即生产者针对新材料的研究与开发向设计人做出了具体指示,并且将设计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下时,受害人才能追究生产者的责任。
对于设计人的责任,韩国区分雇主责任和承揽人责任。如果设计人是公司的雇员,原则上由雇主承担侵权责任,如果雇主能够证明对工作人员完全履行了选任、监督上的注意义务时,可不承担雇主责任。如果设计人独立承揽了该研究,隐瞒了新刹车材料可能发生失灵危险的情形下,定做人单独或者与承揽人共同对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定做人若对承揽人的作业进行实质性的指挥、监督时,成立雇佣关系,由定做人承担雇主责任。⑦
马来西亚的规定是,既然设计人是生产者的雇员,生产者就须对设计人的不法行为负责,雇主甚至要对未获授权的雇员行为负责,因为这是一个雇佣合同,生产者因而要对设计人的过错行为承担替代责任。如果设计人是一个独立的签约研究者,则生产者不必对设计人的过错行为负责。
按照俄罗斯法律,作为侵权人的公司不能将其责任转嫁给雇员或次级合同当事人。公司是生产者,是唯一的侵权行为人。如果合同允许,公司可以为因刹车故障所导致的损失(如产品召回、消费者诉求)起诉次级合同当事人。不过依据俄罗斯法律,支持公司向雇员追偿的人即使有,也很少。
三、关于输血感染案的法律适用
输血感染案的简要案情是:A于2005年在X医院由于输血被感染了N型肝炎。血液提供者是Y公司,是从捐赠者Z采集的。当时在献血中存在N型肝炎的风险只有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有所说明,只有少量的研究室有能力检测其存在,多数的科学团体并不相信N型肝炎病毒的存在。⑧对于此案的法律适用,8个法域的差别较大。
(一)血液感染是否适用产品责任法的规定
在认定血液的性质属于准产品的中国大陆地区,输血感染案件的法律适用被纳入产品责任领域。中国大陆地区《侵权责任法》将输血感染纳入医疗损害责任中,在第七章第59条中规定为医疗产品损害责任,是产品责任在医疗领域内的具体应用。[5](P437)即便如此,在确定血液感染案件的法律适用时,尽管适用《侵权责任法》第59条,但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属于产品责任的特别法,原则上应当以《侵权责任法》第41条至第43条规定的产品责任一般规则为指导。[12](P326-327)
韩国关于血液是否属于产品的问题有过较大争议,用于临床输血的血液,如果添加了保管液或抗凝固剂等进行人工加工处理的,属于产品。不过在实务中,《产品责任法》施行以来,血液及血液制品相关的案件都适用因过错引起的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来解决,适用产品责任法无过失责任规定处理与此相关的案例至今还没有出现。
多数法域并不将血液纳入产品概念的范畴,因此,对于输血感染案不适用产品责任法。中国台湾地区认为血液不属于产品,不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而是定性为医疗服务纠纷,适用“医疗法”第82条关于“医疗业务之施行,应善尽医疗上必要之注意。医疗机构及其医事人员因执行业务致损害于病人,以故意过失为限,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以故意、过失为归责标准。[13](P293,294)中国澳门地区《商法典》第86条认为血液不属于产品,不适用产品责任的规定。马来西亚与此立场相同,认为医院对患者提供的服务由服务合同调整,医生和医院所提供的服务由疏忽责任法和医疗方面的制定法调整,不涉及《消费者保护法》规定的严格产品责任问题,因为该法第十部分并未对血液供应者规定责任。印度也是这样,由于医院没有过错,因此不承担责任。
(二)临床用血液中含有N型肝炎病毒是否为缺陷
在采用产品责任法调整输血感染案件的亚洲法域,中国法律不将血液中存在的问题称为缺陷,而是称为不合格。只有血液不合格时,血液提供者与医疗机构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9条将不合格血液与缺陷产品并列的立法本意,只要输血造成患者损害,医疗机构或血液提供机构即应承担无过失责任,而不区分血液缺陷形成的原因。在血液不合格的情况下,只要造成患者损害,血液提供者和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责任,而不能以发展风险(即依据现有科学技术不能发现和避免的缺陷)作为抗辩事由。立法者作此规定的目的在于强化对患者的保护,督促医疗机构和血液提供机构采取措施预防损害的发生。[2](P417)
韩国判断经过加工的血液有无缺陷,是根据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如果根本不能发现N型肝炎的存在,患者因输入该血液制品而感染N型肝炎病毒的,生产者的产品责任并不成立,依此可予免责。这里的科学技术水平,是指对判断感染产生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提供血液制品的当时已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知识水平,包括最顶尖的知识水平,并不考虑生产者主观上是否已经认识到的问题。[14]即使生产者很难发现N型肝炎之事实,亦不能主张发展风险的抗辩。
俄罗斯法认为,在2005年输血时,N型肝炎并没有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疾病。在缺乏法规或其他规定的情况下,要想取得一份有关此问题的可信赖的并压倒其他反对意见或观点的专家意见是极其困难的。用受N型肝炎感染的血液输血本身并不必然是一个可救济的损害。
由于其他亚洲法域不将输血感染案纳入产品责任调整范围,因此没有讨论血液的缺陷问题。印度法同样如此,认为对于这种病毒的研究,仅发表了一篇科研论文,全球只有一小部分科研实验室有能力在定量的血液中检测出N型肝炎病毒的存在,学术界大多数不认为存在这种病毒,因此不能认为属于缺陷。
(三)血液提供者、医疗机构和献血者是否为承担责任主体
对输血感染案适用产品责任法调整的法域,认可血液提供者同为生产者地位,是符合要求的不合格或者有缺陷血液的赔偿责任主体。中国澳门地区法律认为,如果输血经过加工作为血液制品,则血液的生产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进行输血的医疗机构的主体地位,各法域的做法则不相同。中国大陆地区《侵权责任法》第59条明确规定,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血液提供机构追偿。在日本,这种责任属于产品责任,而医疗机构没有过失,因此没有责任。中国台湾地区认为,与一般产品是由商品制造人设计、生产、制造,制造人能控制危险的情况不同,非大量生产、大量制造、大量销售的形式,无法借由将风险损失计算在成本上,转嫁由所有消费者以分散风险,既不能把血液作为产品,也不能把这样的血液作为缺陷对待,原因是基于公共利益,避免课与制造人严格责任后,无人愿从事血液供应事业,危害医疗输血制度与医疗知识的进步。
韩国依据《血液管理法》的规定,只有医疗机构与大韩红十字会才允许采血。生产血液制品的生产者只能从血液管理者(医疗机构与大韩红十字会)处取得血液。血液管理者若向生产者提供已被感染的血液时,依照零部件生产者或原料提供者都有可能承担产品责任的规定以及《产品责任法》第5条规定,二者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医生对投入的血液制品可能感染疾病的危险未做出任何说明的,这就是侵害患者自主决定权(患者具有选择是否投入血液制品的权利)的侵权行为。⑨在中国澳门地区,医院对受害人实施的行为并没有过错,医院只是按正常做法在给受害人输血时,N型肝炎的检验并未能在医院检验出来,且N型肝炎是否真正存在,在学界也是存疑的,据此可以认定医院对于该损害没有过错,已经尽了适当注意义务,并且对于受害人治疗中未有其他过错,受害人不能就这一损害向医院索偿。
对于提供血液的献血者,各法域均认为不应当是责任主体,理由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血液中含有N型肝炎病毒。例如日本认为,血液提供者在当时既无法认识到N型肝炎病毒的存在,也无法认识到N型肝炎病毒混入血液制品的风险,故无过失可言。
(四)关于诉讼时效问题
在分析输血感染案的法律适用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2001年因为输血导致感染了该病毒,但是直到2012年才发生损害后果,对本案的法律适用将会出现何种不同结果呢?中国大陆地区《产品质量法》第45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10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本案受害人虽然2001年输入不合格血液,但其损害后果在2012年方显现,故其在2012年知道其健康权受到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日本《制造物责任法》第5条规定:“第3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自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道损害及赔偿义务者时起3年内不行使的,时效消灭。生产商等自交付该产品时起计算,经过10年期间的时效消灭。”“前项后段的期间,对于由储蓄在身体中对人的健康有害的物质引起的损害或者经过一定潜伏期间后显现出症状的损害,自损害发生时起计算。”这些规定十分清楚。
中国台湾地区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自2005年输血到2013年尚未逾10年,受害人于现在科技发达而得知受感染的损害与赔偿义务人时,2年内均得请求血液提供者赔偿。马来西亚1953年时效法第6条(1)规定,基于侵权提起的诉讼,当诉讼事由发生届满6年,则不得再提起诉讼。
中国澳门地区关于产品责任在时效方面的规定相对特殊,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效自受害人知悉或应知悉损害、瑕疵及生产者认别资料之日起3年。⑩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自企业主将造成损害之产品投入流通之日起经过10年而失效,但受害人所提起之诉讼正待决者除外”(11)。产品进入流通满10年后,生产者对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不承担责任。在本案中,受害人感染了该病毒直到输血11年后才显现,血液提供者不对此损害承担法律责任。
韩国民法第766条第2款规定“自侵权行为之日起10年内”未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其诉讼时效消灭。侵权行为之日并非加害行为之日,而是损害结果发生之日。(12)《产品责任法》第7条第3款规定,产品责任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自生产者提供缺陷产品之日起10年以内行使。第2款规定,累积在体内的、侵害他人健康而发生的损害或者经过一定潜伏期以后出现症状的损害,都从损害发生之日起计算。
俄罗斯法认为,如果受害人在2001年接受输血而直到2012年才知晓被感染,应适用10年的时效期间。时效期间不会因责任基础的不同而改变。
(五)对于输血感染案的多种法律救济方法
对于输血感染案的法律适用,亚洲和俄罗斯各法域在立法和司法实务都存在多种责任救济形式,救济的效果各有不同。
对于输血感染案受害人的民法救济,以产品责任进行救济最为有效。中国大陆地区对此适用产品责任法进行调整,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确定赔偿责任,最能够保障受害人得到救济权利的实现。中国《侵权责任法》坚持医疗损害责任中的医疗机构承担过错责任,但医疗产品责任和输血感染损害责任则适用无过失责任,正是考虑到过错责任在医疗产品责任领域对于患者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患者对于所输入血液是否存在缺陷完全没有辨别、控制和预防的能力,其接受输血完全是基于对血液提供者和医疗机构专业技术能力的信赖;而医疗机构和血液提供者作为具有专业能力者,具有远较患者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要求其对患者的损害承担无过失责任,可以更好地督促其严格履行职责,将输血的风险最小化。另一方面,在输血感染案中,患者的损害极大,应当保障患者的索赔权利得到满足,否则不符合社会公平与正义原则的要求。
输血感染案同样可以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或者侵权法的疏忽责任法进行救济,但同样都会由于基于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而使受害患者无法证明血液提供者或医疗机构的过失,因而受害人的损害尽管无辜,但无法获得及时、必要的救济。例如马来西亚的法律区分了货物买卖合同与提供服务的合同,医疗的专业服务合同显然是提供服务的合同。血液感染案不适用《货物买卖法》,因为提供被感染的血液不属于该法第2条规定的提供“货物”;也不由《消费者保护法》调整,因为该法将专业服务合同排除在调整范围之外。
即使在认可输血感染案适用产品责任法调整的法域,也不排除适用合同责任或者一般侵权责任救济受害人的可能,但须证明血液提供者和医疗机构的过错,因此受到救济的可能性较小。例如日本,如果以医疗过失为由提起过失侵权责任诉讼,或以违反医疗合同为由提起违约责任诉讼,即使对血液受到肝炎病毒的污染,医院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在医院对患者使用血液时,即使有理性的医师既无法认识到N型肝炎病毒的存在,也无法认识到含有N型肝炎病毒的血液的风险,故可以认定医院既没有过失,亦不构成医疗合同的债务不履行。在中国大陆地区,输血感染也构成责任竞合,受害人可以选择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救济,但无法得到法院支持。
四、关于桥梁设计缺陷案的法律适用
桥梁设计缺陷案的简要案情是:Y委托X有限责任公司在Y所有的土地上建造的桥梁垮塌而受伤,造成A的损害,桥梁垮塌的原因是Y委托的Z建筑师的设计图有缺陷。(13)对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多数亚洲法域认为产品责任不调整不动产的损害问题,只有中国台湾地区认可对其适用产品责任法。
(一)桥梁设计缺陷是否属于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
在8个法域中,只有中国台湾地区认可不动产为商品(即产品,下同),适用产品责任法的规定。其“消费者保护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产品责任的商品概念的范围,但“消费者保护法施行细则”第4条规定:“消保法第7条所称之商品,系指交易客体之不动产或动产,包括最终产品、半成品、原料或零组件。”因此,中国台湾地区的产品责任不区分动产或不动产,均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采无过失责任规定。桥梁设计缺陷案中的桥梁虽为不动产,亦适用无过失责任的规定,施工单位应负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施工单位能够证明其无过失,法院得减轻其赔偿责任,以降低企业经营者负担过重的责任,但仍无法免责。
在其他法域,由于不动产不被认为是产品,不适用产品责任法调整,因此采用不同方法确定桥梁设计缺陷的责任归属问题。
中国大陆地区《侵权责任法》规定,不动产缺陷不适用产品责任法,而适用该法第86条规定的物件损害责任规则。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发生里氏8.0级大地震,大量房屋倒塌造成巨大损害,其中部分建筑物涉及质量问题,引起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并单独就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设置缺陷损害责任单独制定了该条规定。(14)该条第1款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该规定的特点是:第一,直接责任人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建设单位是指建筑工程的投资方,根据《物权法》第30条的规定,对合法建造的建筑工程享有所有权。第二,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不适用无过失责任,与产品责任有较大区别。第三,不使用不动产设计缺陷的概念,而使用设置缺陷的概念,凡是因设置缺陷导致的不动产倒塌所致损害,都适用这一规定。第四,设计人不是不动产倒塌损害责任的直接责任人,概括在“其他责任人”之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再向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追偿。[4](P700-701)该条第2款规定的是不动产管理缺陷所致损害的责任,与本案无关。
日本的不动产(土地及其定着物)不属于《制造物责任法》的适用对象。在制定《制造物责任法》时,基于以下理由,不动产被排除在《制造物责任法》的适用对象之外:一是不动产具有很强的个性,与具有很强同一性的动产不同;二是与动产不同,不以大量生产、大量流通、大量消费为前提。因此,一般的土地工作物等不动产损害适用民法关于土地工作物损害责任的规定;公共营造物损害责任则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都不属于《制造物责任法》的适用对象,但并不会因此产生特别不妥之处。无论是制造物责任还是土地工作物责任,二者都从是否“具有通常所应具备的安全性”来判断瑕疵或者缺陷,故即使修订法律,把土地工作物等不动产纳入制造物责任的适用对象,也不会使个别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变化。
韩国产品责任法上产品的范围仅限于动产,不动产不能成为产品责任的客体。但构成不动产的一部分则可属于产品,比如电梯或冷却设施等是构成不动产一部分的动产。桥梁虽然是由人来建造的,但不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产品。桥梁坍塌致使第三人受到损害的,可依据《韩国民法》第758条关于建筑物占有人或所有人责任的规定得到救济。如果建筑物由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进行管理,应适用《国家赔偿法》第5条规定确定责任。这样的规定与日本的做法基本相同。
马来西亚的产品责任法适用于产品,桥梁与产品无关,《消费者保护法》中产品责任法的规定就不能适用。桥梁坍塌造成他人伤害,根据侵权法的规定,受害人可以对三方当事人起诉,即施工单位、土地所有人和建筑设计师,法院将就责任分摊,以及受害人应得的赔偿进行裁决。一旦证明是因为设计师的方案导致坍塌,施工单位和土地所有人均可以向该设计师索赔。
澳门的产品范围不包括不动产,《商法典》第86条第1款将产品界定为“任何动产”,包括“与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组装的动产”。至于何为动产何为不动产,则由作为一般法的民法典规范。(15)《商法典》第86条第2款规定:“来自土地、畜牧、捕鱼及狩猎之产品,如未加工不视为产品。”为了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修改《商法典》的咨询文本建议废止第86条第2款的规定,以扩大产品的范围。但在现阶段,桥梁并不能看作产品,所以建造桥梁的施工单位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印度因为没有完善的产品责任法,因此应当适用侵权法的规定确定责任。除非证明施工单位没有遵循设计人递交的方案,其责任非常小。但事实表明设计师的设计是有缺陷的,因此施工单位一方没有责任。对于土地所有人,法院明确了土地占有人的责任,这个责任等同于绝对责任,比严格责任原则还要严格得多。根据这样的规则,土地所有人有可能存在责任。设计师对所有人或受害人的责任都非常清楚——因为设计被证明是有缺陷的。如果受害人以设计人知情为由选择起诉他,设计人应继续对受害人承担责任。
(二)桥梁设计图是否为产品
在中国大陆地区,建筑设计图不属于“产品”,而是作为一种服务,是设计人向建设单位提供的一项服务,适用合同法规定的责任制度。在《侵权责任法》第86条规定的情形下,建筑设计人被纳入“其他责任人”的范围之内,在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不动产致害承担了连带责任之后,可以向设计人进行追偿。[5](P567)
在日本,由于设计书以及设计服务不属于制造物,故建筑设计师不承担《制造物责任法》第3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建筑设计师在设计时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受害人可以设计师存在过失为由,依据《民法》第709条追究损害赔偿责任。在裁判实务中,要求建筑设计师承担作为专家的极其高度的注意义务,对于保护受害人的权利比较有利。
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91-1条第2项规定,商品制造人系指商品之生产、制造或加工业者,虽未明文规定设计者,但通说认为设计师亦为危险的制造者,与生产、制造或加工业者一并纳入同一规范。桥梁设计者设计的桥梁欠缺安全性,依“民法”第191-1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如果依照“消费者保护法”规定的商品责任,虽然第7条规定的责任主体为从事设计、生产、制造商品或提供服务之企业经营者,包括设计单位及企业经营者,但建筑师如果是个人而非企业经营者,则不适用该条规定负无过失赔偿责任。
在中国澳门地区,建筑设计图虽然是动产,但按照法律界的主流观点不是产品,而属于服务。原因是,设计图本身意义并不在于其载体上,而在于其客体是智力成果,因此不具有物质形态,不可视为动产,应受知识产权法保护,不属于产品责任调整范围。建筑设计图的本质是设计人依据委托合同而向委托人提供的一项服务。由于委托合同的关系,所以该设计图所造成的损害赔偿,由委托人承担,并且适用合同责任制度。
在韩国,设计图纸作为知识性产品,并不属于产品责任法规定的产品范畴。信息或软件等知识性产品本身并不存在致使人身损害或火灾等发生的危险性,受害人可以通过合同法上的瑕疵担保责任得到救济。知识性产品的概念、内容、功能等具有多样化特点,很难对该类产品课以无过失责任。[15](P31)依据韩国《建设产业基本法》第28条规定,承包人建造的建筑物发生瑕疵时,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承担建设工程瑕疵担保责任。但依据该法第28条第2款第2项的免责规定,若依据发包人的指示进行施工时,承包人对发生的瑕疵不承担担保责任。承包人依据设计人设计的图纸进行了施工,双方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只有土地所有人与设计人之间是直接的合同关系,设计人向土地所有人交付设计图,土地所有人再向承包人提供该设计图纸,承包人并不承担桥梁坍塌的瑕疵担保责任。如果承包人明知设计图存在缺陷,仍由于故意或过失未告知土地所有人这一事实时,依据《建设产业基本法》第26条第5款规定,项目管理者在履行职务时,因故意或过失导致发包人产生财产损害的,应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承包人与设计人是在相互协商或相互监督下建造该桥梁的,则应共同对桥梁坍塌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俄罗斯法认为,建设方案本身不属于消费者保护或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对其不应适用严格产品责任。在合同法中可将其看作服务,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处理。
(三)动产责任与不动产责任的区别
中国大陆地区在整体法律规则设计上,严格区分动产和不动产规则,在立法上体现为《建筑法》(1997年通过,2011年修订)与《产品质量法》(1993年通过,2000年修订)并行,《合同法》单独设立第十六章“建设工程合同”。《侵权责任法》将产品(动产)致人损害规定为产品责任,将不动产倒塌致人损害规定为物件损害责任。中国法动产责任与不动产责任在责任规则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区别。在不动产设置缺陷责任,主流意见认为适用过错推定责任[2](P31),而不同于产品责任的无过失责任。第二,“自损”纳入损害赔偿范围的区别。产品责任的产品自损可以纳入产品责任赔偿范围,但不动产的物件损害赔偿责任则不包括不动产的自损。第三,是否存在管理缺陷责任方面的区别。不动产责任除了存在设置缺陷责任之外,还存在管理缺陷责任,但动产责任基本上不存在这一特殊责任类型。中国法不动产责任与动产责任存在上述差异的正当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责任理论上的差别,不动产责任与动产责任在理论上的差别体现在缺陷类型不同、预防成本不同和自损的价值大小不同;其次是责任制度上的差别,抗辩事由不同,对内责任承担的基础不同;最后,中国法不动产责任与动产责任的这种区分与行政管理体制有一定关联。[16]
中国台湾地区的不动产属于产品,适用无过失责任。学者认为,这样的立法虽然较能保护消费者,但不动产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应考虑商品责任的正当性系因科技发展后,消费者处于大量生产、大量贩卖、大量消费的环境,而动产的特性在于可以规格化、大量制造、容易控制其质量,故课以商品制造人较重之责任;相较于不动产,欠缺被替代性,且因涉及因素众多、时间久远,难以论断其损害原因为何,故建议,于未来修法时应当明确不动产不适用商品责任。
(四)提供产品与提供服务的责任的区别
中国大陆地区法律认为,提供服务的责任和提供产品的责任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相对性要求的差异。提供服务责任造成损害的对象为服务合同的相对人,可以根据《合同法》第122条选择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产品责任没有相对性的要求,既包括合同当事人,也包括第三人。第二,归责原则的差异。提供服务导致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人损害的,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承担侵权责任,但缺陷产品责任适用无过失责任。第三,责任主体的差异。提供服务的责任人是服务提供者,而中国法将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共同作为产品责任的责任人。中国法区别提供服务的责任和提供产品的责任存在差异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流通性的差异。产品存在流通性,从生产者到最终的使用人,可能经过多重的流通;而服务具有直接性,一般不存在流通问题。第二,发现和证明产品责任人过错的困难性。现代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具有专业性,受害人难以证明产品责任人主观上存在过错,进而可能导致求偿的困难,因此适用缺陷产品严格责任;提供服务的责任人其过错的证明则相对容易。第三,相对性要求带来的求偿困难。中国疆域广大,如果仅由产品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则可能导致高昂的求偿费用和诉讼成本,因此立法者从方便诉讼和求偿的角度,将销售者纳入责任人范畴,并由其承担向供货商和生产者的求偿不能风险,能够更加切实地保护产品的最终消费者;而在提供服务的情形中,不存在这种求偿困难的问题。
日本在制定《制造物责任法》时,将服务(即劳务)排除在制造物责任的适用对象之外,其理由,一是提供服务时,每项服务内容各不相同,有很强的个性,与具有很强同一性的动产不同;二是服务之中因其缺陷造成他人的生命、健康危险的情况较少,缺乏一律使提供服务者承担严格责任的根据;三是在通常情况下,成为问题的并不是服务的安全性,而是该服务本身的质量;四是由服务中存在的瑕疵引起的损害通常发生在接受服务者一方,但因为接受服务者与提供服务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接受服务者可向提供服务者追究违约责任来寻求救济。
中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规定,产品责任包括服务,提供服务之企业经营业者,于提供服务时,应确保该服务符合当时科技或专业水平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若违反,致生损害于消费者或第三人时,应负连带赔偿责任,一律适用无过失责任,唯学说与实务肯定医疗服务不适用这一规则。学者也认为服务的种类繁复,内容千变万化,一律课以无过失责任恐非适当,服务的本质与商品利用机器能大量生产、销售之模式不同,在立法上服务不宜适用无过失责任,应回归一般注意义务与过失为判断。
中国澳门地区法律将设计图作为服务对待,依照《民法典》第493条关于委托人责任的规定,将其作为现代侵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对其受托人在执行职务活动时致第三人损害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委托人之责任制度之设立在于平衡委托人、受托人和受害人的利益。在本案中,土地所有人是委托人,设计人是受托人,土地所有人即委托人对于设计人的设计图有问题而导致桥梁坍塌造成受害人的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五)施工单位是否有责任无偿再建一座新桥梁
关于施工单位是否有责任无偿再建一座新桥梁,各法域报告中较少讨论。日本法认为,根据施工单位和土地所有人之间的合意,土地所有人负有无偿建造新桥梁的义务,其结果是施工单位须负担筹措建设新桥梁所需工作人员及原材料的费用。相当于该费用的损害是因建筑师做出的具有瑕疵的设计,而在施工单位的财产上产生的损害为一种纯粹财产的损害,且日本侵权法对于认定该种损害赔偿并不存在任何障碍。因此,施工单位可依据《民法》第709条,以设计师的侵权为由,请求赔偿上述费用。若有其他损害,只要该损害在相当因果关系范围之内时,就可以请求赔偿。韩国法认为,承包人由于设计人的过错向土地所有人履行了最初的约定,即在原建筑费用的范围内,重新建造了一座新的桥梁,由于承包人对土地所有人并不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如果不是由于设计人的过错,承包人并不需要支出这些费用与劳动力,因此,承包人可依据《民法》第750条的一般侵权行为规定,向设计人请求因其过错而导致承包人的损害赔偿。中国澳门地区法律认为,施工单位虽然因为设计人的设计图问题,需要无附加报酬地建造一座新的桥梁,但这仅仅是基于其先前与土地所有人的约定,施工单位与设计人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所以设计人不对施工单位承担责任。设计人作为土地所有人的受托人,设计人造成的损害由委托人即土地所有人承担法律后果,但土地所有人对于替设计人承担的风险责任对其有追偿权。根据澳门《民法典》第493条第3款,土地所有人可以就所作出的一切支出要求设计人偿还,但施工单位本身亦有过错的除外,如果施工单位也有过错,其就根据《民法典》第490条规定,与设计人一同承担连带责任。土地所有人对设计人的追偿可以提起直接诉讼。
编者按:本文中提及的中国法报告,请阅杨立新,杨震:《有关产品责任案例的中国法适用——世界侵权法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的中国法报告》,载《民商法学》2013年11期。
①本文有关产品责任案例的亚洲和俄罗斯的比较法研究,依据的是参加世界侵权法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的相关代表就会议讨论的产品责任三个案例的8个法域报告,报告人分别是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潮见佳男教授,韩国庆熙大学法学院苏在先教授和宋正殷,印度国立大学法学院奥姆帕拉喀什·V.南迪马斯(Omprakash V Nandimath)教授,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法学院艾妮莎·吉·娜(Anisgh Che Ngah)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和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杨震教授,辅仁大学副校长陈荣隆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唐晓晴教授和梁静姮,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大学基里尔·特洛费莫夫(Kirill Trofimov)教授。笔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形成本报告。上述报告刊载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编辑的《世界侵权法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本文关于各法域法律适用情况的引用,均采自该论文集刊载的上述报告,文内不再一一作引文注释。就此向上述报告人致以谢意!
②澳门《民法典》第195条和第196条。
③该案例请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
④澳门《商法典》第87条规定:“一、考虑到包括外表、特性及可作之合理使用在内之各种具体情况,一项产品于开始流通时未能提供合理预期之安全者,则视为有瑕疵。二、产品并不因后来有另一更完善之产品在市场上流通而视为有瑕疵。”
⑤详细案情请见[英]肯·奥利芬特:《三个产品责任案例》,《法制日报》2013年9月4日第9版。
⑥《民法典》第477条第2款规定:“不取决于有无过失之损害赔偿义务,仅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方存在。”
⑦韩国大法院判决1991.3.8,90 da 18432。
⑧详细案情请见[英]肯·奥利芬特:《三个产品责任案例》,《法制日报》2013年9月4日第9版。
⑨医生说明义务的代表性案例,见韩国大法院2011年3月10日判决2010 da72410。
⑩参见澳门《商法典》第93条。
(11)参见澳门《商法典》第94条。
(12)韩国大法院1979.12.26判决77da1895,全员合一体判决。
(13)详细案情请见[英]肯·奥利芬特:《三个产品责任案例》,《法制日报》2013年9月4日第9版。
(1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9年12月2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15)澳门《民法典》第195条及第196条。
标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论文; 产品责任法论文; 合同风险论文; 法律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无过错责任论文; 比较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