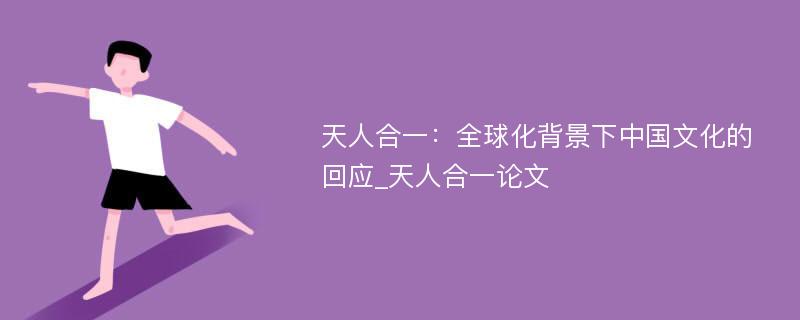
天人合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人论文,中国文化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2)02-0098-04
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纪的交汇点。当此之时,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生活都发生了显然不同于以前的改变,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文化与文明的论辩也空前醒目,文化视角倍受关注,传统文化资源在被重新梳理后得到新的认识和整合。在这种氛围中,重新检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认真探讨跨世纪文化重建的必要性及前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既成的事实
关于全球化,或许不是什么全新的话题。至少自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从而使东西两半球达成文化意义上的结合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如此说来,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冷战结束以后的全球化实际上是“新全球化”。李慎之先生认为,在过去的500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等,但都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所引起的冲突和磨擦。而现在,我们分明清楚地看到了跨国界、全球性力量的滋长,全球性问题正在蔓延。
从1989年柏林墙坍塌到1991年苏联瓦解,再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及随后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可以说正是这种“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显著标志。
全球化是一个综合谱系概念,除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外,还有其他种种全球化,如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此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猖獗,乃至垃圾处理等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早在1992年就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这种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危机不同以往。一方面,就危机的范围和程度而言,具有世界性和深刻性;另一方面,就危机的根源来说,它不同于以往由天灾人祸等非健康原因所造成,甚至可能源于人们美好的愿望,如为了发展工业而大规模开采资源,致使不可再生资源迅速耗竭,或为了增强家族或民族的实力而多生超生子女从而加大了地球的人口负荷等等。总之,人类为了自身的暂时利益而从事的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活动,多把主体的设想强加给对象,使得本已脆弱的环境与心灵变得更加险象环生。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对人类社会来说,自从文明发祥以来,除细菌和病毒以外,屠杀人类的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身。
由此可见,尽管后工业化时代把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普及到了全球,最大可能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把人类财富的总积累提高到只要使用得当就可以迅速改变一个或几个国家面貌的程度,把生产力发展到确有可能满足全人类基本需要的地步,极大地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殖,但是它也给世界留下了文化堕落、道德败坏、贫富差距拉大、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升温、民族主义与文化磨合凸显、人口膨胀与环境破坏加剧等全球性问题。截止目前,人类既未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新近开辟的种种可能性。因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伴着人们生活水平和个人自由度的提高,牛仔裤、可口可乐、迪斯科、摇滚乐等连同海洛因和爱滋病一起狂飙突进般传播到全世界。在这种背景下,既有的人文准则和理想信念被颠覆,人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失落和目标混乱之中。这就是人们业已感到并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全球性文化危机。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以不断扩展物质消费为主导的发展理念,不仅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结构,而且对“生物圈”也构成了威胁。人类的危机在本质上来源于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局限性以及人性中的贪欲。数千年来,人类一直把自身以外的一切都当作环境,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前西德总统魏茨泽克认为,“环境”一词来自这么一个信条,即存在一个中心,而中心就是“我”。人类从来都把自己看作宇宙的中心。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都宣扬“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主宰世界”。中世纪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也认为地球居于宇宙的中心。甚至被法国启蒙思想家发扬光大了的人道主义,也主张人是高贵的,自然应该为人类服务。正是这种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心态,统治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每当取得一点进步,人类便陶醉在“人定胜天”的自我欣赏之中,仿佛在人类面前,没有不能征服的对象。人类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创造的文明引向了困境。
“同化”或“异化”:当下中国文化的困境
世界文化面临危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也不例外。具体说来,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困境主要体现为陷入了“同化”或“异化”这种非此即彼的文化观念上的误区。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商业文明”的转型。长期以来,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点,即使是在都市,乡村文化也常常通过人们的日常习俗、审美爱好、语言方式等显现出来。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今天,包围着我们的是浓郁的城市文化气息。在众多表现当代城市生活的影视片中,充溢着眩目的霓虹灯、瀑布似的彩挂、蠕动的车辆,人不过是城市之光的投影。在小说中,城市被描绘为卡拉OK厅、立交桥、麦当劳等现代空间物象的快速移易以及幽灵般飘忽的人流。这种现代生活造成的生活节奏和思维惯性使人对往常日复一日的刺激已不感到新奇,现代人已从传统和理性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直接感官刺激的接受者,既不对事件意义作更多的思索,也不就价值选择作理性的判断,个人经验与当下快感成为时尚。这种娱乐性、消费性城市文化的兴起,无疑给历史进程引入了一种新的激素,它消解着既有的一切,同时又以其巨大的包容性,通过兼收并蓄,熔铸着新型文化——广告引导人们如何消费,电影劝告人们及时生活,讲究实惠的享乐主义代替了作为社会现实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教伦理观。现代规则与传统道德、世界与本土、皮尔卡丹与中山装、西餐与中餐、西方芭蕾与东方歌舞,都成为城市文化橱窗的一部分同时陈列在人们的面前。在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换言之,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被现代都市文化所遮蔽,相反,在现代大众传媒的再创造中,在城市族群回返自然、寻求精神家园的渴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另一方面,在粉碎西方文化霸权同化本土文化神话的同时,本土文化中的诸多异质因素也不容忽视。层出不穷的历史片、庙堂音乐、仿古建筑,以及兜售旅游纪念品的仿古宫廷侍者,已使被复举的传统文化完全改变了内涵,在现代文化渗透下,它们不过是“无底”传统的某种象征。
究其实,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华夏文化区,客观上已经出现了一种中西混合文化。它部分地放逐了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价值及深度的部分,如道家文化崇尚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信奉使命感及对物欲的自我约束等。这种混合文化,很容易使我们漠视现代化给当代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消费主义、自我主义、无序竞争、对历史的漠视与践踏,使我们变得麻木不仁,使我们忘记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优长处,使我们盲目地以西方标准为标准、以西方价值为价值。
众所周知,在目前的中国,所谓洋货有着巨大的魅力。吃、穿、用等,除直接进口外,国产商品也冠以洋名,借此招徕顾客。麦当劳在美国是价廉、便捷、安全、卫生型食品的象征,但在中国,麦当劳的文化表达意义与祖源地有很大不同。在北京顾客的眼里,麦当劳是悠闲消遣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因为它毕竟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它也不大符合中国老百姓的饮食口味。目前,广东少数几家彩电生产企业,如乐华、TCL等己生产出了彩电业的“巨无霸”——界面50英寸,9厘米厚,体重不足50公斤,标价25万元人民币的等离子“壁挂式彩电”。这种彩电采用等离子发光技术,依靠电极气体放电所产生的紫外线轰击荧光粉发出各种颜色,能再现1670万种色彩,图像细腻轻柔。尽管国内仅卖出少量几台,但厂家依然生产了500台。这是中国彩电业技术竞争的产物,自然也是企业实力的象征。但据透露,这是向日本付出高额“专利费”后联手合作、共同开发生产的。因国内尚不具备大规模发展等离子彩电的技术和市场,所以盲目跟踪西方及国外最新成果,必将付出相应代价。这再次表明,任何异质文化现象之间尽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互补性,但是,本土及区域文化的积淀性、传统性和本质规定性使它们之间很难完全同化或异化。任何同化他者或被他者异化抑或异化他者或被他者同化的简单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
交往与融汇:全球文化发展大势
由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剧变,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百年来各自主流文化的弊端,寻求横向开拓的发展契机。伴随着日益增多的由西方文化引致的流弊,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建制正在衰落。反之,随着文化殖民流弊的不断揭穿,各民族都在重新发现自己合理的文化内核,并努力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因为没有差异就没有发展,保存并发扬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世界文化之幸,亦即人类之幸。不同文化的交流过去已被反复证明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新的增长点。以世界文化发展为例,无论是非洲音乐对当代通俗音乐的影响,日本绘画对梵高、莫奈的濡染,还是中国建筑对欧洲建筑的借鉴意义,都可说明当代欧洲艺术的发展,确实得益于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着的文化差异。同理,汉唐之际中国对印度、西域文化的吸纳以及中国文学中词、曲、白话小说的成长都包含吸收了俗文化的因素,也说明了不同文化差异构成的文化级差对文化演进的极端重要性,它们不断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性而导致革新。如果没有了这些差异,也就极大地失去了激发人的灵感和创造性的文化资源。
事实上,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这些贡献的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因此,人类的文化宝库应该是由众多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打造的“文化多元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更需要各种异质文化的交往与融汇,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发展、成长、衰竭、消逝的过程,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和功能。人类之所以能不断进步,不断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保持自己文化精髓的大前提下,追寻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
然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确实正受到各方面的威胁,最明显的就是顽固存在的各种文化中心论,其中首推西方中心论。西方世界的许多人总是顽固地认定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包含最合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最应普及于全世界。美国黑人文化的速变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犯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自黑人被当作奴隶入住美国以来,他们的语言、习俗和信仰都已在接受美国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被打磨了。帕森斯博士和佐拉赫斯顿女士认为,就在美国北方各州快速发展的同时,黑人文化正在逐渐衰弱。隔绝的苏里南布什—尼格罗人在文化上最具有他们非洲老家的特性,南方黑人区则保留了一些特质,而北部城市黑人居民实际上与他们的白人邻居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当然这得先排除使这种或那种特质固定化的社会樊篱。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原始部落文化在全新的欧洲影响下,持续着自己古老的观念,并产生了对强加其上的文化的再调整。如新墨西哥普韦布洛印第安部落,他们有意识且尽可能地使自己与生活在周围的美国人隔绝开来。但实际上,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因为使用美国制造品而发生了改变,他们的一些旧有的生活方式已有所“同化”。尽管如此,他们坚持保留着古老的房屋样式,甚至尽力保留先前的服装款式,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坚持在沙砾地上种植玉米,他们各种古老的宗教信仰与仪式对现实有着很好的调试作用,使得普韦布洛人并不产生严重的内心冲突。这无疑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总而言之,我们主张扬弃西方中心论,也并非是要以别一种文化中心论来代替它。任何文化上的吞并或侵略,都有悖于历史潮流,不利于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
当然,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不能不面对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所带来的挑战,高速发展的电子信息时代正在极其深刻地改变着人类思维和生存方式。但信息的流向远非对等,而是大多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与科技信息的流入,也会同时发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的“整体移入”。这意味着,文化交往过程中的融汇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
在强调文化多元共存的声音中,还出观了文化相对主义。它强调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近代社会,特别是以电脑电信为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原有强势文化的影响力相对减弱,因而相对于过去的文化征服(教化或毁灭)和文化掠夺来说,无疑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因为认识到自身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危机,进而奋起保护本土文化,而忽略本土文化的缺失,反对与其他文化的沟通,就有可能发展为封闭、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义。其实,这种“未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文化发展实际上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文化中心论和高科技使文化的多元发展受到威胁,文化的多样性被削弱;另一方面是文化相对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孤立和隔绝。这两种倾向都会导致世界文化资源的耗损和无可挽回的流失。
优势与前景:中国文化重建的前瞻
既然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危机既成事实,那么,在八面来风的情况下,中国的文化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危机及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话语便成为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被摆上桌面。在这方面,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有用的部分显然不失为明智之举。
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尽管中国传统哲学包含着丰富的有关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但中国哲学并没有明显经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重点转移,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人生和人格道德理想的培育,是对天人关系与人际和谐的追求,即所谓“天人合一”。
我们知道,儒道文化哺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传统的民族,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的道德哲学尤其重视人的修养,要求每个人都要自觉地扩充内在的仁善本性,提升精神境界。所谓“仁者与万物同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天人合一”,是儒道哲学所期许的道德修养和人类生态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孟子·尽心》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主张天人相通,并以心性作为沟通天人的桥梁,将天与人统一了起来。《老子》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还特别强调“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天与人相胜,是谓真人。可见,“天人合一”这一思想的深刻含义,在于揭示了天人之间的统一法则和变化规律,承认人与天地万物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共生同处的关系,应该和谐相处。
当今,人类社会正在趋近地球的生存极限。非常现实的威胁表现为沙漠扩张、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这些正在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类认为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程式中居于中心地位,自然不过是人类创造与演绎其历史的舞台与道具,致使这些发展对人类本身构成了威胁。日益逼近的危机,迫使人类在自然界的惩罚面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整个自然界中的位置。结果发现,人类的生活和行为不可能脱离自然,要达成一个可持续的优化型社会模式,我们的基础思想、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都必须与自然保持一致,放弃人类作为自然主宰的观念,将人类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承认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方面的局限性,以科学的态度敬畏自然,甚至要感受到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唯其如此,才能爱慕世间万物,才能真正做到“天人合一”。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西方的传统文化态度有所不同。西方文化遵从“天人相分”的原则立场,在分析型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暴烈夺取的方针,结果有目共睹。而中国(东方)文化的主导思想则基于综合型思维模式,主张与自然交好,提倡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此基础上期盼着自然的公正回报。但是,伴随着工业文明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的传统价值理念被严重颠覆,在谋财逐利的过程中伤害了自然,天人关系空前紧张。在这种情势之下,重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信条就显得十分必要。
老子倡导回归自然以克服异化,就是要努力减少那些人为规范,彻底清除那些无用的繁文缛节,使人从异化的文明枷锁中挣脱出来,还其自然的本性。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在自然的怀抱中去寻求一种精神的宽解,以达致“庄周梦蝶”——物我两忘的无为之境。
怎样达致无为之境呢?老子提出“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庄子主张返朴归真。《至乐》说,“大道无为而自然”;《渔父》云,“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老庄哲学追求任自然以适情,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实际上就是“物我合一”、“物我一体”。文人陶渊明在其创作中也鲜明地表现了“回归自然”的倾向与心声,在《归园田居》中他写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心态,在《饮酒》诗中再次得到袒露:“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不独陶渊明,魏晋时代的其他士大夫如阮籍、嵇康等,其实都具有这种“不为形役”、“桀骜不驯”的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所以说,在建构中国文化方面,“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根基,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现代意义。
客观地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历无数战争、饥饿而绵延不绝地生存下来,并相对完好地保存着自己的文化遗产,这本身就已经显示了较之于其他古老民族的高明所在。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中所说,就中国人来讲,数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这种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由此可见,我们确有必要回眸历史,把持传统,将其作为文化再创造的基本源泉,经过创造性转换,力求在全球化背景下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型文化。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是武力征服的时代,20世纪下半叶是经济竞争的时代,那么21世纪可能是多元文化兼容发展的世纪。不准预期,21世纪的文化将会在更广泛的领域、更深刻的意义上影响人类社会的前景与走向,文化的整体力量将对人类生活具有超越军事、政治、经济乃至民族、地区、国家界限的沟通和含容作用。届时,文化因素既能提升人的道德素养,又可缓解天人矛盾。承此背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正可扮演承前启后、贯通中西、指向未来的桥梁作用。在这个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只有努力总结和发扬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借鉴外域文化的精华,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才能有效重建全球文化新秩序。
收稿日期 2001-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