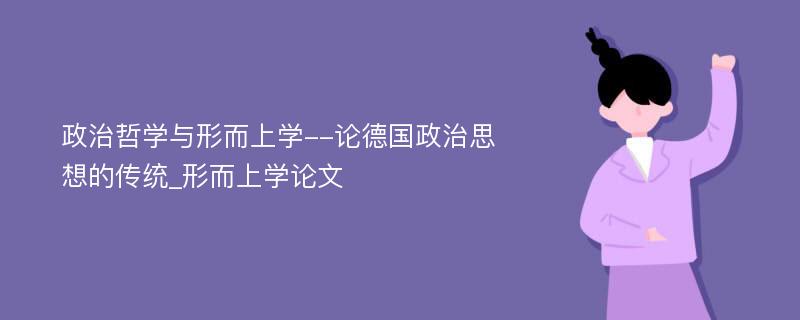
政治哲学与形而上学——略论政治思想中的德国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德国论文,政治思想论文,哲学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8)01-0056-08
政治哲学界普遍认为,近现代的各种政治学说可以划分为两种传统:其一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其二是法国理性主义传统。比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第4章中专门阐述说,前一传统主要由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以及埃德蒙·伯克等为代表,这一传统重经验而不重体系,强调制度来源于传统和实践,而不是设计或构造;后一传统以笛卡尔、卢梭等为代表,认为人类社会制度是人的理性发明出来的。他认为自19世纪中叶起,法国理性主义传统压倒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造成了莫大的危害。
我现在冒昧提出,在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德国理性主义传统之间也可以作出同样的划分。作这样的补充有以下理由:第一,德国理性主义传统和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特征以及在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第二,德国思想与法国思想相比具有某种丰富性和深刻性,在理性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引入德国传统进行比较,可以对两种传统的差异有更好的理解;第三,德国传统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更大,中国人对德国传统的迷恋更深。如果说认识理性主义传统是有必要的,那么对德国传统的解剖就很有必要。
中国哲学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西方思想传统中德国哲学最深刻,因为德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气味最浓。这种看法和评价也推及政治哲学,许多人认为英美政治哲学理论中可取之处颇多,但根本的缺陷是肤浅。这些理论虽然阐述了人类社会在政治制度安排方面的正确原则,但缺乏形而上维度的言说,缺乏道德和价值判断,缺乏安身立命的教诲,总之一句话,不能满足中国人对终极关怀和审美、道德情操的浓厚兴趣。
也许可以把德国古典哲学的专门研究者邓晓芒对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一书的评价作为上述倾向的代表。邓晓芒认为,他对此书总的感觉是很清晰,具有分析哲学的严格和明白,但缺乏形而上的探讨,因此不能深入内在矛盾性,不能更深地揭示各种分歧的内部关系。
中国哲学家对德国哲学及其形而上思辨的推崇,对英国经验论的轻视往往表现为情绪,缺乏文本可资研究、争鸣。而在西方学术界,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已经就具体问题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论战。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批评被视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哈贝马斯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概念的批评被当成是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传统对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批评。这两种批评都指责罗尔斯的理论预设了一种人的“自我”概念,它是赤裸裸的,不承载社会、历史、文化内容,不具有形而上学的、道德的属性,他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哈贝马斯更是明确断言:探讨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回避不了形而上学。
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政治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具有形而上学内容和特征的政治哲学学说是否一定优于形而上学内容和特征较少的政治哲学学说?为此,我们将具体考察、比较以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经验论哲学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优劣高下,看看它们的先验性、思辨性和形而上学性是否使它们具有某些十分高明、不可替代的东西。此后,我们还要在抽象层次上进行理论性讨论,看看形而上学论证是否为政治哲学所不可缺少,或者是否会赋予政治哲学一些优良的素质。
请注意,在进行对比研究和探讨时,我们判断高下、利弊、得失与优劣的标准是这样的:我们看各种学说对于人类获得政治文明成果和取得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或者与之一致、相近的程度。我们不会独立于文明、进步而另立标准,比如某种抽象、玄虚的“深刻性”,因为一旦承认这样的标准,形而上学政治哲学的深刻性就是同义反复、不证自明的。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哲学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制度安排提供原理和标准,不是作概念游戏,所以判断其价值的依据只能是实际作用,是对促进实际进步的理论贡献,而不是某种特殊的、神秘的心理满足。
在宏观地比较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经验论哲学在政治学说方面的成就时,首先应该说明,英国经验论政治哲学是17至18世纪的学说,而德国唯理论政治哲学是18至19世纪的学说,我们有理由期望后者比前者内容更进步、形态更发达,因为时代在进步,后人的理论思维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甚至相反,那么其高下立即可以判定。
英国经验论政治哲学的代表首推约翰·洛克,他在出版于1690年的《政府论(下篇)》中,就比较全面地提出和比较周密地论证了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政治哲学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阐明国家或政府权力的来源,洛克基于自然法和契约论原理提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同意让渡部分权利,他以“主权在民”的思想驳斥了“君权神授”的观念。
康德虽然也说:“人民根据一项法规,把自己组成一个国家,这项法规叫做原始契约”,但他同时又说:“一方面是一个普遍的统治者,作为国家的首脑,另一方面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作为臣民的群众。在这种关系中,前一种人员是统治的权力,他的职务是治理;后一种成员构成该国的被统治者,他们的任务是服从。”[1](P143)
费希特在谈到根据契约个人结合为整体时,他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语焉不详、不得要领,作出的最好解释,也不过是接近洛克的观点。[2](P206~207、Ⅺ~Ⅻ)
黑格尔的国家观则充满神秘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气息,他说,“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在国家中获得自己实体性的自由,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所以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3](P253、261)
由于权力来源于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同意让渡,所以洛克认为,当统治者违反契约时人民有反抗的权利,他说:“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就无需再予服从,而只有寻求上帝给予人们抵抗强暴的共同庇护。”洛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反抗的人民。而是专权者、掠夺者在造反和叛乱。[4](P133~134、137)
康德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人民如果抗拒国家最高立法权力,都不是合法的……对人民来说,不存在暴动的权利”,“人民有义务去忍受最高权力的任意滥用,即使觉得这种滥用是不能忍受的”。[1](P148、149)
黑格尔主张王权,“即作为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的权力,它把被区分出来的各种权力集中于统一的个人,因而它就是整体即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在他看来,王权是单向的,即只行使权力而不承担义务、不负责任,君主作裁决,“只有这些谘议机关及其成员才应该对此负责,而君主特有的尊严,即最后作决断的主观性,则对政府的行动不负任何责任”。[3](P287、306)
洛克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必须分立的原则,并深刻地阐明了权力分立的道理:“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在他之后,盂德斯鸠更精确地表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并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虽然孟德斯鸠是法国人,但他的思想被公认为属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是在学习和熟悉英国政治思想之后形成的。历史证明,权力制衡原则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最重要方法。
康德承认三种权力各有不同职能,立法权不能同时又是行政权,不论立法权或是行政权都不应该行使司法职务。但他强调这三种权力的联合或合作而不是分立与制约,他还认为在最高一级这些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最高立法者的意志……被认为是不能代表的;最高统治者的执行职能要被认为是不能违抗的;最高法官的判决要被认为是不能撤销的,不能上诉的。”[1](P144~146)
费希特在论及权力分立问题时,其观点显得简单、混乱。他只同意行政权与行政监察权的分立,同时表示并不赞成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认为这样做是毫无目的的,仅仅在表面上才可能,他完全没有论及立法权和其他权力的关系。[2](P164~165)
黑格尔则完全反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他说:“所谓权力独立的观念包含着根本错误,以为独立的权力仍然应该互相限制的。殊不知这种独立会取消国家的统一,而统一正是所企求的第一件大事。”[3](P318)
洛克对于私有财产权的起源与合法性作出了一种重要的说明,其核心是“个人所有”(serf-ownership)这个概念,我们即使不能说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至少可以说是最重要和意义深远的,即使在当代,当诺齐克和柯亨(G.A.Cohen)讨论有关问题时,还是从洛克的说明开始。[5]
康德关于私有物初始获得的原则是这样的:“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我根据外在自由法则把该物置于我的强力之下,并把它作为我自由意志活动的对象,我有能力依照实践理性的公设去使用它,而且,我依照可能联合起来的共同意志和观念,决意把一物变成我的,那么,此物就是我的。”这样的表述显然太玄虚,在进一步的解释中,康德强调两个因素:一是“在时间上占先,在法律上也占先”;二是单方面的意志和宣示。[1](P72~73)
康德的主张尽管使用了形而上的思辨语言,但简单地说就是“先下手为强”,相比之下,洛克用质朴的语言阐明的道理却合理和深刻得多。洛克为财产的初始私人占有提出的条件包含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劳动渗入被占有物:“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劳动的改进作用造成价值的绝大部分”。二是个人的占有应该只占同类被占有物的很小一部分,一个人的占有应该留下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以便不妨碍他人作同样的占有。[4](P27-29)
费希特的论述则没有触及财产私人占有的核心问题,即要满足什么条件,财产的初始占有才具有合法性,“这里所说的也不是原始的获取……这种原始获取直接以原始财产契约为条件。”他只讨论“两种财产相互进行交换……我们的考察就从这里开始……国家必须知道特定的财产所有者。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任何人都不是这种客体的合法占有者”。[2](P255~256)
黑格尔的观点及表述与康德相同,首先使用形而上的词句宣扬一种占有意志:“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该物成为我的东西;人具有这种权利作为他的实体性的目的,因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与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这就是人对一切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我把某物置于我自己外部力量的支配之下,这样就构成占有;同样,我由于自然需要、冲动和任性而把某物变为我的东西,这一特殊方面就是占有的特殊利益。”与康德一样,他也宣扬“先来先得”原则:“物属于时间上偶然最先占有它的那个人所有,这是无待烦言的自明的规定,因为第二个人不能占有已经属于他人所有的东西。”[3](P52~59)
德国思想传统中对暴力的态度也引人注目,康德一方面说:“我们必须承认:文明民族所承担的最大灾难就是被卷入战争”,呼吁并论述世界的永久和平,但另一方面却强调战争其实是一种常态:“在人类目前所处的文化阶段里,战争乃是带动文化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他的想法甚至和后来德国军国主义证明自己有权扩展“生存空间”的理论一致:“当大自然照顾到人类在大地之上到处都能够生活时,它也就同时专横地要求人类必须到处生活……为了到达它的这一目的,它就选择了战争。”[6](P75、122)
黑格尔则肆无忌惮地讴歌战争:“战争不应看成一种绝对罪恶和纯粹外在的偶然性……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通过战争……各国民族的伦理健康就由于他们对各种优先规定的凝固表示冷淡而得到保存,这好比风的吹动防止湖水腐臭一样;持续的平静会使湖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甚至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3](P340~341)
费希特的以下说法表明,他主张用武力征服一个“落后”或“未开化”的民族:“对于一个没有政府,因此没有国家的民族,邻国有这样的权利:或者使它服从自己,或者强迫它制定一部宪法,或者把它从自己邻近驱走。这么做的根据是:谁不能为自己的权利的安全而给别人提供保障,他本身就没有任何保障。因此,这样一个民族会变得完全无法无天。”[2](P372)
在了解了这些德国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观点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思想与德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全民屈从于当权者、整个国家充满强力占有精神、推行军国主义路线和战争政策是否有关系?
在衡量某种政治理论或社会制度时,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和妇女参政问题是重要尺度,我们来看看德国的形而上学哲学家的有关论述是什么样的。
康德认为,男性力量强于女性这一事实反映在婚姻关系中就是妻子服从丈夫:“人们会质问,当法律以任何方式对待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时,总是说:‘他将是你的主人’,于是他便代表命令的一方,而她就成为服从的一方,在此情况下,是否违背了婚姻当事人平等的原则?如果这种法律上的优越地位仅仅是基于考虑到丈夫与妻子的能力相比,在有效完成家业的共同利益方面具有自然优势;此外,如果丈夫的命令仅仅是根据这种事实来作出的,那么,不能认为这违背了人类结合成双的自然平等的原则。”[1](P98)
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婚姻观失之为只是一种契约观,他断言“婚姻实质上是伦理关系”,从这一点出发,离异是不应该的,也是从这一点出发,在婚姻出自父母安排和自由恋爱问题上,前一种更符合伦理。“就男女关系而论,必须指出,女子委身事人就丧失了她的贞操;其在男子则不然,因为他在家庭之外有另一个伦理活动范围。”妇女的伦理性情绪就在于守家礼,家礼是妇女的法律。妇女“天生不配研究较高深的科学、哲学和从事某些艺术创作,这些都要求一种普遍的东西。妇女可能是聪明伶俐,风趣盎然,仪态万方的,但是她们不能达到优美理想的境界……如果妇女领导政府,国家将陷于危殆,因为她们不是按普遍物的要求而是按偶然的偏好和意见行事的”。[3](P177~183)
费希特关于婚姻、性爱、男女关系的论断中也充满了男尊女卑的观念,比如,“未婚妇女受父母支配,已婚妇女受男人支配”,“在婚姻的概念中,包含着妻子对丈夫意志的最无限制的服从……妻子不属于她自己,而是属于她的丈夫。”“在婚姻的概念中,还包含这样的意义:献出自己人格的妻子,将她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和她在国家生活中独享的各种权利都同时转交给了丈夫。”“根据她自己的必然抱有的愿望,丈夫是她的一切权利的管理人,她所希求的,是仅仅在她丈夫希求的范围内维护并履行这些权利。丈夫是她在国家和整个社会中的天然代表。”“妇女命中注定不能为公务供职”。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论断和费希特关于人的形而上学前提和先验演绎方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家庭法概论”的第一章就是“婚姻的演绎”,一开始就说:“为了能深思熟虑地把法权概念应用于婚姻,我们同样必须通过演绎去认识婚姻的本性。”他的演绎步骤大致是这样的,在生殖活动中,男性是能动的,女性是受动的;自然的本性规定,男性把满足性欲作为自己的目的完全与理性不矛盾,而女性这么做则绝对与理性矛盾;在女性那里,性欲采取道德的形态,道德律要求她们忘我和献身。[2](P302~348)
我们知道,英国的政治理论家在男女平等问题上大多持开明态度,许多人还积极投身于争取妇女解放、妇女参政权的运动中,比如密尔(John Stuart Mill)。
现在,我们来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看看在政治哲学中,形而上学是否必要。在一次讨论费希特的政治哲学的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以下论点:
首先可以作这种一般性的思考:从哲学史上看,形而上学体系不计其数,很难(也没有标准)对它们作出是非、高下的判断,它们是不可公度的,对待它们,只能采取多元的态度;我们也许对某种形而上学情有独钟,但我们清楚地知道那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偏爱,决不能说它是各种形而上学中正确的或公认的。
但一个较少争议的事实是,对于政治哲学中的许多基本原理,对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安排的基本方式,人类具有相当的共识,我们把这称为全人类的宝贵遗产和财富,我们据此说某些思想、学说,某些制度、政策是进步的或落后的。
如果在进行政治哲学思考时,在开端是形而上学,那是多元的、见仁见智的,而在终端是一些可以用人类共识来判断的具体原理,那么这种矛盾如何化解?[7]
我的同事黄裕生在发言中与我磋商,提出了至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对于政治哲学需要形而上学的最深入和强有力的论证,其关键论点如下:
必须从经验领域之外,即从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所处理的超验领域去寻找人类一切权利的最后根据。如果说政治学就是关于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的科学,那么,政治学最后必须以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为基础,否则,一切政治学就只不过是一套应景的权宜之计。由康德开创的整个德国超验哲学传统,对于政治学和法学而言,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贡献的话,那就是它开辟了一种为政治学和法学寻找第一哲学论证,从而为它们奠定可靠基础的可能性道路。
的确,人类在各方面都会达成各种共识,最广泛的共识也就成为所谓主流意识。在政治领域同样如此,在这一领域,根据主流意(共)识来进行制度安排的国家被称为主流国家,由这样的国家组成的社会被称为主流社会。但是,一个国家制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难道就来自一种政治上的主流共识?或者说来自一种主流的政治理念?这岂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只要会赶国际政治的时髦就能担保自己的正当性?……把形而上学排除在自己视野之外的政治学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是:对于那些迄今仍拒绝接受被主流社会当作共识的政治理念的国家及其领袖们,人们该怎么办?难道政治学家们只能对他们说:“这是当今人类在政治领域形成的共识,你们必须接受,否则你们就是异类,就是不文明,就没有正当性?”可是,这些异类们却同样可以振振有词地回应道:什么人类共识!那至多只是“你们”的共识,而不是你们与我们之间的共识,更不是“我们”的共识;在我们(哪怕是少数)没有认同与接受的情况下,你们有什么权利声称你们的共识就是人类的共识?而我们的共识就是野蛮的、不文明的?
个人的这种权利来自什么地方?为什么每个人作为公民个体都拥有同样不可侵犯、同样必须得到尊重与维护的绝对权利呢?这种公民个体在绝对权利上的平等的根据是什么?唯一的答案只能是:每个个人的绝对权利就来自他是自由的理性存在者,因而他是自由的。[7]
以上论述,总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下大工夫、花大力气来论证人生而自由。这个第一原理如果没有牢固确立,后面的论证就理不直、气不壮;这是政治哲学理论大厦的基础,只有夯牢了这个基础,政治哲学理论的大厦才经得起风吹雨打。以上论证还隐含地认为,政治哲学理论是一种演绎体系,第一原理的真理性确保以后推论的真理性;第一原理的不可置疑性将传递给后面的结论,使它们也成为不可辩驳的。
我认为,这恰恰就是一条唯理论的思路,德国的形而上学哲学遵循的是这一条思路,而笛卡尔之所以被视为唯理论的代表,则是因为他的以下主张更典型地阐明了这条思路:首先找到完全自明、清晰,绝对无法怀疑的真理,然后演绎出整个体系。
而按照英国经验主义的思路,人生而自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它得自人们的经验、直观或常识。两条思路的分岔在于:按德国传统,为了确保和增强第一原理的真理性,需要调动一切思辨的手段、先验的力量,在形而上学的维度彻底地、根本地解决问题;英国经验主义的思路是,自由不能仅仅依靠思想上认清、肯定人性是天生自由而确保万无一失,事实上人只有在一种社会性的法律体系中才能真正享受自由,因此,论证的工夫应该花在说明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方面。
可以说,德国唯理论的思路与中国传统的“内圣开出外王”是同构的,怪不得中国人对此心领神会、情有独钟。而英国经验主义的思路并不对人性问题沉潜往复、探微索幽。而是把目光转向制度的安排。
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在捍卫“人生而自由”时也打过一场正面的遭遇战,这就是洛克在《政府论(上篇)》中驳斥罗伯特·菲尔麦爵士的观点:“人类不是天生自由的”。由于对手的理论是简单、粗糙的,不过是用父权来比附王权,把人民比喻为需要家长监护的小孩,所以洛克的反驳也比较容易,只是简单明快地以“所以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也是生而具有理性的”为结论,没有形而上的沉重与深奥。
除了这一次交锋,政治思想史上似乎没有其他捍卫“人生而自由”,反驳“人类不是天生自由”的重要事例,这也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要复杂深奥的思辨。顺便指出,康德、黑格尔虽然从自我到理性,再到自由,对“人生而自由”作了一番形而上的证明,虽然在德国一定有罗伯特·菲尔麦爵士那样的人鼓吹“人类天生不自由”和“君权神授”的反动观点,但却未见他们像洛克那样针锋相对地批驳,这两位大思想家都是十分依附王权的,他们的形而上思辨和形而下的实际考虑是完美的一体两面。
我想进一步指出,人类对自由的论证、捍卫与反对侵害自由的斗争,基本上不是发生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双方不是在比赛谁能更深刻地证明人天生自由还是不自由。其实,就算说明了人有形而上的自由本性,反对自由的人就算承认这个出发点,也还会从“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角度,用诸如“自由不是绝对的”之类的“辩证观”来消解这个出发点。现代反对自由的人从来不是反对这个出发点,而是首先虚伪地承认自由的价值,然后用集体的价值来对抗和偷换,用文化和传统的特殊性来拒斥。因此,在出发点上的绝对胜利并没有解决问题。
对“人生而自由”的思辨性和形而上学论证看起来很有用,就像给一栋建筑加上了许多支撑性的脚手架,保证它永远不会垮塌。但实际上,这些脚手架阻止了人们的进入,与其说是支撑,不如说是障碍。因为特定的思辨和形而上学的证明依赖于特定的先验论形而上学体系,不熟悉这样的体系,就无法理解那种证明,如果不全然接受这样的体系,就难于接受那种证明。同意德国思想家的政治观点,需要太多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准备,而同意英国思想家的观点,只需要一种健全的直感和常识。
要害不在于“第一原理”是否站得住脚,而在于“第二原理”向哪个方向发展:天然人的自由处于社会状况会怎样?个体的自由与其他个体的自由相撞后会怎样?洛克对此作了出色的阐述:“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但是自由,正如人们告诉我们的,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怎样的那种自由(当其他任何人的一时高兴可以支配一个人的时候,谁能自由呢?),而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他强调:“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4](P36)
这个思路一直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主线,比如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其名篇《论自由》中说:“究竟应该怎样在个人独立与社会控制之间做出恰当的调整?这就是一个几乎一切工作尚待着手的题目了。”他提出了论证自由的著名的“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能够违反其意志对之施加权力而不失为正当的,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其他人的伤害。
反观德国传统,康德、黑格尔在“深刻”论证自由的天然性之后,在社会实际层面应该继续坚持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价值时,却对自己的初始观点大打折扣,出发点的生命力被他们深深服膺的整体论所窒息,被他们摆脱不掉的国家至上的观念所扼杀,而不像英国思想家,以正确界定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范围的方式使自由从个人价值转化为社会制度。
形而上学的传统对自由和个人权利提供的是一种“内在化”的证明,虽然一般来说,人们易于认为内在比外在深刻,但应该看到的是,有的时候过于内在和深刻的东西会掩盖甚至歪曲事物的本质,形而上学的玄奥会把简单、清楚的东西弄得复杂和模糊。比如,按照英国式定义,自由就是行动不受人为的外部阻碍,这似乎太浅显明白,而黑格尔的定义“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则相当深刻,但却深刻得不合常理、违反常识。就像罗素曾经质疑过的,按照黑格尔的定义,一个人被关进监狱,当然是失去了人身自由,如果他刻苦学习、研究,最后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程度,难道他是自由的?甚至反而比监狱外的人还要自由?
在“人是理性的因此是自由的”这个论断中,如果赋予理性太强的——例如像德国唯理论那样的——意义,那么这个命题与“自由即对必然的认识”就有明显的亲缘关系。从这里可以派生出:人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这种自主性概念又可以推导出,有些人比别的人更能认清人的真实需要,认清世界的本质,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就达到了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的观念。如果一个人对必然的认识达到这个地步,以至于他比一般人更了解他们自身和他们的需要,那么他就可以指导他们,甚至强迫他们去实现他们认识不到而只有他才认识到的目标,这些目标代表了这些一般人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这里,我们发现了20世纪历史性悲剧的思想原因:先知们有权强迫群众为乌托邦献身。
中国的传统是“向内之学”(当然向内也是浅尝辄止,受累于实用理性),长于作心性、道德文章,拙于向外开拓,疏于对社会性、制度性安排的精思巧辩。人是一种有惰性的存在物,我们总是惯于在相同的思想文化中求得共鸣与印证,而不愿在异质的传统中寻找变革的借鉴和启发。自从20世纪20年代起,我们在西方思想的学理输入和研究方面,工夫下得最深的是德国哲学。不用说,德国哲学的博大精深,确实为其他民族的哲学所不及,但中国人长时间吃德国哲学的亏,却不太为人们所认识。在这方面作一点反思,可能是没有害处的。
收稿日期:2007-04-19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康德论文; 政治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家论文; 洛克论文; 经验主义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