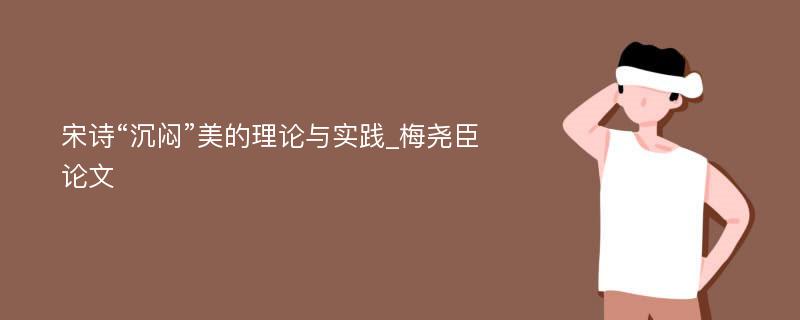
宋诗“平淡”美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淡论文,宋诗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宋人“平淡”诗观是与梅尧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梅尧臣“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①]的诗句是宋人“平淡”诗观中的经典表述。关于梅尧臣“平淡”诗风的主张和实践应从其与“西昆体”为代表的宋初诗风的比较中去把握。宋人有一段关于梅尧臣诗歌地位的精辟之论:“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②]这“古淡”是梅尧臣自己的主张,欧阳修有诗载:“子(梅尧臣)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荠。”[③]“古淡”也是其他诗人一致推尊的境界。如欧阳修认为“辞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④]苏舜钦称“会将趋古淡,先可去浮嚣。[⑤]所谓“古淡”,是指为了反对晚唐五代以来时体之情思浮靡、形式雕绘而提出的一种审美主张,它是宋初以来追还三代之风的复古主义思潮在审美理想上的反映,要求诗人摈弃晚唐浮艳雕绘的作风,追踪唐之中盛尤其是韩孟等人的诗风。因此,所谓“古淡”意在复古,并无诗风上的统一定义。苏舜钦自称“笔下驱古风,直趋圣所存”[⑥]是一种;欧阳修学李白横放展宕也是一种,而当时真正“古”而能“淡”者以梅尧臣最为典型。梅诗笔尚朴拙,意象清雅,立意平实,又多用五言,尤长于五古,相对于西昆体之七律秾丽密致,相对于苏舜钦七古宏壮豪健,都显示出十足的平淡气质。他的这一实践使“平淡”理论的探索具有了初步明确的方向。
欧阳修对于梅尧臣,生而序之,死而铭之,对梅尧臣的诗歌造诣深心称阐。晚年,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指出:“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在《梅圣俞墓志铭》中,欧阳修进一步总结道:梅尧臣“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问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盖老以劲。”不难看出,他是认定“平淡”为梅诗基本风格的。
这种风格虽“以闲远古淡为意”,却是“苦于吟咏”,“构思极艰”,[⑦]“覃思精微”的结果。其形成过程融合了多种艺术风格因素,如中晚唐五律诗的清丽婉细和郊、岛等人的怪巧。因此,它是一种外示“平淡”与内含艰巧表里殊致的特殊构型。反映为审美感受,便是“如食橄榄”,津意见于咀嚼的风味。
欧阳修对于梅诗之“平淡”深心推阐,固然是因为梅诗艺术成就的客观魅力,然而也与欧阳修本人的整个艺术主张相吻合。欧之擅长在“古文”,倡导“文与道俱”,“简易自然”,标志着新一代“古文”精神和作风的成立。欧言“平易自然,”这是他从艺术的角度推阐“平淡”之义的原因。在他的“古文”艺术论中,也不乏艺术上“进其业,修其辞”,[⑧]而至“平淡”的主张,指出了“平淡”是艺术精进的结果。这与梅尧臣所言“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相一致。
然而,“平淡”不只是个艺术问题,更是个情感问题。梅诗平淡有味的情感基础,可以用谢景初称赞梅诗“苦语有淡工”[⑨]一语来概括。所谓“苦语”是指梅尧臣诗歌以“贫贱”之士的身世之感为主,正如欧阳修所说,梅诗之“工”是“穷”的结果。庆历六年(1046),梅尧臣与当时显达闲适之士晏殊之间围绕“平淡”问题曾有过思想交流。[⑩]梅尧臣虽尊重晏殊关于闲雅平淡的见解,然实践上表现出明显的不惯。梅在诗歌中写道:“微生守贫贱,文学出肝胆。……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11)]心虽属之然意实难造。“相公(指晏殊)贵且事翰墨,我辈岂得专游嬉。”[(12)]既然游嬉闲适不起,“适情”“平淡”之诗便无缘任真。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改革急流的退潮,尤其是诗人心意的“老大”,梅尧臣逐渐领略到了陶渊明诗歌具有的高古野逸意趣,同时对隐逸诗人的风格表现出欣赏的态度。宋初在“白体”、“昆体”缙绅诗人之外,本来就有僧侣隐士组成的在野诗人群体,继踪晚唐五代栖隐苦吟之流的疏淡清远诗风,后人称为“晚唐体”。逸民在野的风气于宋初政权建设有所不利,因此“宋兴,岩穴弓旌之招,叠见于史。”[(13)]但随着政权的巩固,隐士的形象便由政权建设的消极因素转变为道德风教的积极因素。种放被召,不久又求归,宋真宗认为“能守分恳让,益可嘉”。[(14)]范仲淹作《严先生祠堂记》称严子陵“归江湖,得圣人之清”,“能使贪夫廉,懦夫立,则是有功于名教,”[(15)]都见出复古思潮中儒家政教思想对传统静退野逸情趣的融摄隐者之诗以山水优游为主,相对于红尘浮嚣,台阁富贵之语,以“格调清卓,辞意平淡”[(16)]为胜境。梅尧臣晚年对这种“平淡”也有了一定的理解,他称林逋:“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于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趣尚博远,寄适于诗尔”。[(17)]可见梅尧臣对这种早年无缘的境界现在已是深心知赏了。梅尧臣这一变化,预示了“平淡”诗观开始具有了审美情感方面的规定。
对于欧、梅等人来说,晚年的情感“平淡”,主要属于越过生命鼎盛期之后心意的“老大”和“淡泊”。欧阳修说:“狂来有意与春争,老去心情渐不能。世味唯存诗淡泊。”[(18)]这种“淡泊”包含了社会时事、自然生命和心理规律等多方面的体认。王安石晚年始终不似少壮时“以意气自许”,而是“深婉不迫”。[(19)]这种“少小”“老大”的迥然异格,包含了更多艺术上博观约取、深思渐进和诗家工夫。因此,王安石对“闲淡”中的“不淡”有着深切的体验:其“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20)]这是“平淡”诗论中抉发此义最精辟的措语。
(二)
继欧、梅、王之后,苏轼和黄庭坚把“平淡”诗美的探索推进到高度自觉的阶段,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平淡”诗美的最高成就。然而,细加寻绎,两个人的视野是有所分别的。
苏轼侧重于从审美情感上把握“平淡”的韵味和风神。他特别强调“平淡”中的“至味”、“奇趣”,因此他高度评价司空图关于“韵味之致”的观念和实践。他说:“司空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景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荫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21)]可见苏轼所谓“至味”“奇趣”,主要是一种萧散野逸之趣。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平淡”诗观较之梅尧臣更为明确地与陶渊明联系在一起,同时适当吸收了与陶相近的“韦、柳”等人的风格因素,把他们作为“平淡”美的典型,发明其“简古”、“散缓”、“枯淡”中的“至味”、“奇趣”和“腴美”。[(22)]
苏轼之大量赞陶和陶,提倡“平淡”,是在带罪出贬黄州之后,与生命历程的挫折密切相关,因而包含着人生境况的人生态度转变的深刻内涵。苏轼曾这样分析自己贬窜之际的生活:“仆行年五十,知作活大要是悭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辈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23)]这种面对人生困境冷静乐观、任真自适的态度,赋予“平淡”以特殊的人格品味和哲理深意。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24)]正是品格妙识上的高度吻合,使苏诗多“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25)]而其学陶和陶也最为会“意”得“真”。把“平淡”诗风与陶渊明紧密相联,标志了“平淡”诗观的成熟。
黄庭坚侧重于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把握造于“平淡”的艰难历程,把“平淡”视作含纳“大巧”而又纯熟无迹的艺术极地。黄庭坚的这一立足点是由江西诗家的诗学精神决定的。黄庭坚“喜作诗而得名”[(26)]因奉杜甫为鹄的,追摹其命意曲折句法精深。但是,江西之学杜摹古,又别存心裁,并非学杜全体,而是重在老杜夔州以后诗。他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27)]杜甫夔州前后诗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晚节渐于诗律细”与“老去诗篇浑漫与”,“用心精密”与“出乎纯熟”[(28)]的高度统一。黄庭坚所属意的正是这种艺术上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老至之境,所以他强调的是“简易”中的“大巧”,“平淡”中的“山高水深”。
为了说明造于平淡后的“奔轶出尘”之义,黄庭坚把陶渊明引进了自己的描述系统。他说:“宁律不谐不使句弱,宁字不工不使句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29)]同样的意思,用陶诗来形容比杜诗更加醒豁,因为黄庭坚也看到,“渊明直寄焉耳”。[(30)]有时,黄庭坚用“遗句中有眼”与“彭泽意在无弦”[(31)]分别代表诗家次第由法度至于自由的两个不同阶段,以表达“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完整过程。与苏轼相比,黄庭坚的“平淡”诗论主要侧重于把握艺术创作中自由与法则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
从梅尧臣、欧阳修到苏轼、黄庭坚“平淡”诗美理论和实践构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代表了“平淡”诗美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流与最高成就。但在宋代,“平淡”之作为最高诗美理想不只是成就于少数诗人的天才发现和创造之中,而且有着普遍的社会心理和创作实践基础。
宋初有一个“白体”流行的现象。虽然由于白居易诗歌实践的丰富性,自中唐以来,所谓“白体”的概念就歧义纷纭,但就宋初诗坛的实际情况看,以浅近的语言从事闲适的吟唱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文士中的显贵之流如李昉、李至等人更是如此。至真宗朝,“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32)]但是,雕绘满目,反见膏腴害骨,浮薄乏理,至真宗这种风气便受到一定的裁阻。景德四年(1007),“枢密直学士刘综出镇并门,两制馆阁,皆以诗宠其行,因进呈。真宗深好诗雅,时方务竞西昆体,磔裂雕篆,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止得八联”。[(33)]此“平淡”是相对于昆体诗雕绘涂饰、襞积密塞的诗风而言的。真宗所选如晁迥“夙驾都门晓,微凉苑树秋”,刘筠“极目关山高倚汉,顺风雕鹗远凌秋,”都气象清远,语言淡雅。真宗朝后期,盛度、晏殊倡学韦应物,正是这一“平淡”意向的发展。晏殊喜好韦诗“全没些脂腻气”,又“集梁《文选》以后迄于唐别为《集选》五卷”,“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34)]晏殊的诗虽以富贵宴游为主要内容,但对人生宠遇采取了一种超越优雅的把握方式,诗中“不言金玉锦锈而唯说气象”,[(35)]因而在昆体之外自得其“闲雅而有情思”韵致。“庆历新政”后,边鄙安绥,朝政一时难于作为,大批志士闲置,富弼、韩琦、宋祁、文彦博、司马光、韩维等纷纷“人安闲淡内”,[(36)]以洛阳为中心,形成了山水优游诗酒闲适的风气。这种风习与白居易“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37)]的“闲适”诗,具有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
正是在这相沿已久的闲适诗风的传统中,孕育了“邵康节体”这一“理学诗派”的代表。“邵康节体”的精神实质正是闲适。朱熹曾指出“他诗篇只管说乐,次第乐得未厌了。”[(38)]这乐便是“乐天四时好,乐地百物备。[(39)]“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须惊”;[(40)]“忽忽闲拈笔,时时乐性灵。”[(41)]总之,安时处顺,随缘适性。邵雍把诗酒雅吟,岁月优游的闲适之意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难怪当时党争中人羡他“在急流中”,“安然取十年快乐”。[(42)]
宋诗闲适情调之普遍性有着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宋开国之初便确定优待士大夫的政策,鼓励士大夫“多蓄歌儿舞女”,以弥息觊觎之志,侣导清虚淡泊的品格气质。其后更从各类制度上保证厚禄与法权。宋人退休,例有祠禄,即便获罪远窜置闲,也能粗了伏腊。在这样的情况下,进退无虞,富贵闲人的心志便易养成。这种人格理想因其逸愉保和、循默无为的消极因素,在天圣至庆历年间的变革思潮中受到一定的批判。然而,改革急流退落之后,高明虚淡、恬退闲雅的人格追求更为坚定、明确,理学便以融佛老入儒的理论形式体现了这种人格追求的思想水平。作为“理学”“花草”的“理学”之诗因而也实现了真正的“平淡”之境。其“平淡”由于根基于理学思想的成就,闲适的情调中流溢着儒者宽仁、以理自律的“忠厚和平”气象。理学家自来以文章为“闲言语”,以学文为好道,[(43)]朱熹观点稍为通脱,认为文从道中流出,“大意主乎学问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间以数句适怀亦不防”,“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44)]这种自然流出,平淡适怀的主张是理学家关于诗歌最为流行的观点,也是与一般诗人闲适诗风神理符契之处。理学家作诗,反对各种雕饰奇巧之笔,语言平易浅切,甚至不避俚俗。清人指出“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45)]正是有感于这种平易浅俗与“白体”闲适诗有许多相近的因素。理学诗可谓实现了从情感到形式的真正“平淡”。
由宋初以来的闲适诗经过理学思想的洗礼,终致“平淡美”理论的成熟,是谓又一条清晰的线索。在这一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吟咏性情”的创作态度,尤其是理学家无意为诗的文学价值观,起了实质性的作用。“平淡”不可以风格求之,它首先是一种诗学价值观,一种对待诗的准虚无态度。这种无为的诗学态度,至南宋因理学的昌炽而显示了大势普及的倾向。元代袁桷曾指出,北宋诗以苏、黄为宗,至南宋“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也绝。”(《清容居士集·书汤西楼诗后》)诗人田雯批评道:南渡后“竟趋道家,遂以村究语入四声,去风人之旨实远。”(《古欢堂集·杂著》卷一)这些意见都从反面道出了理学“平淡”之诗的特征和在南宋的流行情况。
(四)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宋人“平淡”美理论和实践有着多维的展开序列,其中通向“平淡”的理想心路和实践取径更是因人因时歧义纷呈。但作为被宋代诗人普遍确认的诗美理想。共同的社会背景和统一的文化基础又决定其必然包含统一的规定性。
1.“平淡”美的情感规定性
“平淡”的概念不同于“自然”,它包含了明确的情感要求。“平淡”美对情感的要求便是平静淡泊。情感的这一要求是与宋代整个士人精神建设的整体方向相吻合的。早在宋初,针对五代干戈、文儒荡然的局面,广开科举,宽养以待,以期唤起广大士人奋身当世的热情。然士气振作的同时也带来了文人奔竟浮躁之弊。“躁进者多,知止者少”(《续资治通鉴》卷20宋纪10)。于是为了倡导一种恬退寡求、清虚淡泊的士人品格,“人性贵乎平淡”,[(46)]便成了当时士人之间、官僚之间评品鉴量的标准。于是,宋人援佛入儒反求于内,种种淡泊明志、虚静求理的学说便应运而生。“诗本道性情,不须大阙声”。[(47)]这种“情感”上的“平淡”要求,是与宋代整个士人精神建设的整体方向相吻合的。“平淡”之上升为最高的诗美理想,带有更多以理遣情,以理制情的理性主义性质。因此,“平淡”不同于传统士人之放逸而更倾向于儒者之闲适和萧散。然而,大多数情况下,通向“平淡”的路径却是不平淡的。在实际的创作中,情感的“平淡”多见于历经磨难后的生命逆转或越过鼎盛期的投老赋闲。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伟大诗人几乎都经历过早期的豪健清雄,在其生命后期归于清旷闲远、自然平淡。可以这么说,真正的“平淡”之诗属于人生的“老”境。这种“老”境,一方面反映了“老之将至”听命于自然规律的意兴萧瑟,另一方面,“老去唯存诗淡泊”中又未尝不积淀着厚重的人生经验,包含了对世事一种更为通达、冷静的态度。而从“欲造平淡”的角度看,它又是人生修养功夫老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产物。晁补之说:“鲁直治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陶渊明之自然,故其语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学渊明者,外喧为淡,例作一种不工无味之辞,曰吾似渊明,其质非也。[(48)]“平淡”终究不是一个风格问题,更不是诗法问题,而是人格境界问题,只有人格上圆成一种淡泊渊如的境界,才有诗意的“平淡”。
2.平淡美的形式规定
无论是黄庭坚等人的“出则奔轶绝尘”,还是理学家的“无意为诗”,都表现出对诗歌形式层面的超越和否定,虽然其立足点大相径庭。任何否定最终都要落实为某种肯定,于是我们看到,宋人在建构“平淡”诗美时把目光投向晋宋以前的“古诗”时代。与唐人力求恢复汉魏古诗“风骨”及中唐以来主张效法《诗经》、汉乐府之“风雅比兴”不同,宋人之重古诗在于其“意象简朴足镇浮”[(49)]的平淡效果。吕本中:“大概学诗,须以三百篇、楚辞及汉魏间人诗为主,方见古人好处,自无齐梁间绮靡气味也”。[(50)]理学家张栻说:“古诗皆是道当时之实事,今人做诗都爱装点造语言,只要斗好,却不思一语不实便是欺。”主张象古诗那样直道其事,别无所求,这代表了理学家否定艺术独立价值的极端派的观点。苏轼则从诗歌艺术形式的发展上看到了古诗“高风绝尘”的风神。苏轼说:“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51)]所谓“高风绝尘”就是指诗艺声色未开,各类诗格未立之前,诗歌形式无拘无束,古雅自由的风采。朱熹也认为:“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52)]其意大致相同。他们都认为下逮陶渊明的古诗与陶之后追蹑其风的韦、柳等人,其形式简古朴素,“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澹之趣”。[(53)]所以宋人多推崇魏晋古诗的古雅简妙,而“平淡”之诗也多以五言古诗为常式。
3.“平淡”美的美感形态规定
苏轼说:“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54)]宋人之于“平淡”美的抉发,最显著的贡献就是分别出“中边”或“内外”。“平淡”是容易被人认知的,但要体认出其中的“真味”,就需要有很高超的艺术修养。欧阳修最早把梅尧臣的“平淡”诗“比以为橄榄,回甘始称述”。[(55)]王安石也在“寻常”、“容易”中看到了“奇崛”“艰辛”。这种由表及里的鉴赏,并非一般地强调不停留于意象之表作细致的品味,而是要超越外部,深入体认其与表象不一致甚或迥异的内蕴。范温曾经提出一个具有宋代特色的韵味理论。他说“有余意之谓韵”,为文众善“一不备焉,不足以为韵。众善皆备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是之谓矣。其余一长有余,亦足以为韵。故巧丽者发之乎平淡,奇伟有余者行之于简易,如此之类是也。”[(56)]所谓“有韵”就是“有余”而能自我“韬晦”,“奇伟”而行之简易。这与其说是艺术的观点,莫如说是人生的态度。“平淡美”正是以外在枯槁而中存腴美,“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内敛结构成了淡泊韬晦的人生态度和内敛沉潜的文化人格的艺术载体。
注释:
①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
②四部丛刊本《宛陵先生集》附录
③《再和圣俞见答》,《欧集》卷5
④《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欧集》卷2
⑤苏舜钦《诗僧则晖求诗》
⑥苏舜钦《夏热昼寝感咏》、《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卷3
⑦《六一诗话》
⑧欧阳修《与郭秀才书》
⑨《冬夕会饮联句》,《全宋诗》卷245
⑩(12)《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6
(11)梅尧臣《依韵和晏相公》
(13)(14)《宋史》卷457
(15)范仲淹《与邵餗先生书》
(16)释智圆《联句照湖诗序》
(17)《林和靖先生诗集序》,《梅集编年校注》拾遗
(18)欧阳修《病告中怀子华原文》,《集》卷13
(19)(20)《石林诗话》
(2①苏轼《书司空图诗》
(22)苏轼《评韩柳诗》、《书黄子思诗集后》、《书唐氏六家书后》
(23)苏轼《与李公择书》
(24)《王直方诗话》引
(25)苏轼《录陶渊明诗》
(26)《临汉隐居诗话》
(27)《与王观复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6
(28)黄庭坚《答洪驹父书》
(29)黄庭坚《题意可诗后》
(30)黄庭坚《论诗》
(31)黄庭坚《赠高子勉四首》之四
(32)苏舜钦(一作石介)《石曼卿诗集序》
(33)《玉壶清话》卷1
(34)《青箱杂记》卷5
(35)参见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十六)
(36)韩维《自静教院晚步氵异上》
(37)白居易《序洛诗》
(38)《朱子语类》卷100
(39)《乐乐吟》
(40)《龙门道中作》,《集》卷5
(41)《闲适》,《集》卷4
(42)程颐《河南程氏补书》卷11
(43)《河南程氏遗书》卷18
(44)《朱子全书》卷65
(45)《四库全书总目》卷153《击壤提要》
(46)《王氏谈录》
(47)梅尧臣《答中道小疾见寄》
(48)晁补之《书鲁直题高求父杨清亭诗后》
(49)陆游《闰二月二十日游西湖》
(50)《竹庄诗话》卷2引
(51)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52)朱熹《答巩仲至》
(53)《鹤林玉露》甲编卷6
(54)苏轼《评韩柳诗》
(55)梅尧臣《答宣阗习理》
(56)《潜溪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