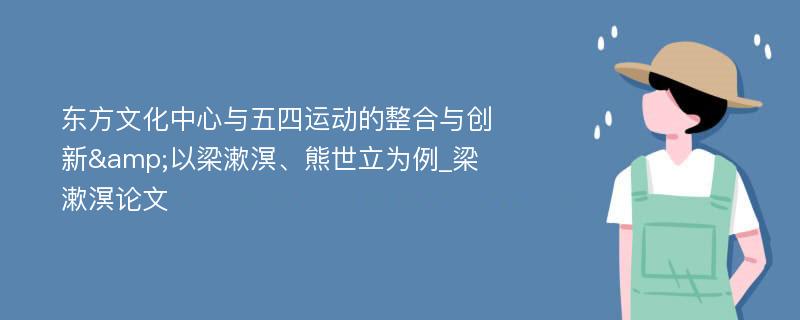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中心与融合创新——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中心论文,力为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681(2006)06-0052-06
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化是在参照中西文化的异同,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两橛的思维模式,有选择地吸取和消化西学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创造性文化重构与熔铸。五四时期学术文化的勃兴表征的正是中西文化彼此认同并进而融合创新的特征。当时的各家各派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尽管标举了不同的文化创新主张,但在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创建新文化的途径上则是一致的。主张东方文化中心的梁漱溟就很自信地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融合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同样,新儒学的代表熊十力也强调立足儒释道,吸纳西学精华,构建所谓“内圣外王”的新学体系。他们分别标举“意欲中心”、“生命本体”说,从“昌明东方学术”着眼,强调立足本土,化合中西古今,来构建崭新的民族新文化,实现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
一 梁漱溟的“益欲中心”说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山人物。梁漱溟一生思想多变,曾自述其思想有三变:“(1)近代西洋功利思想,(2)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3)中国古时的儒家思想。”转变之关键在于对“人生苦乐”之觉悟[1] (P841-848)。“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2] (P126)冯契据此断定梁漱溟“形成了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同时糅合印度的佛学和西洋的生命派哲学的哲学思想体系”[3] (P808)。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著作中形成了以东方文化为主融合中西印的“益欲中心”说。在学术方法上,梁漱溟主要推崇传统儒家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并在学术实践中予以批判吸收和创新。
(一)诘难唯科学主义,提出理智与直觉两种方法
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蔓延到东方,五四期间的中国思想界成为了科学主义的乐园,并表现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唯科学主义倾向,科学和科学方法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超级“神圣”。陈独秀、胡适、丁文江等人是急先锋。在他们看来,应该将科学领域无限地扩大,从自然界推延到社会人生,用自然科学领域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原则来研究解决“一切社会人事问题”,认为科学与哲学、宗教没有什么区别,有了科学,哲学和宗教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更为甚者,在1923年展开的“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江、王星拱竟公然宣称“科学就是哲学”。
最先对唯科学主义思潮提出批评和诘难的,便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而梁漱溟用来批判这一思潮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就是当时输入中国的柏格森生命哲学。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将世界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一是生命,一是物质。在他看来,整个世界可归纳为两种相反的运动,即向上攀登的生命和向下降落的物质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与之相呼应,人类的认识也可划分为理智和直觉两种类型:科学的理智的认识不能施于生命之上,它只能获得作为假象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对生命的认识,只能依靠本质上与生命同一的非理性的直觉。
梁漱溟认为,如果不对科学本身所含有的有害的生命观、粗糙的功利主义和过度的行动主义加以节制,而将科学的作用无限扩大,并运用它的方法来指导和解决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一切宇宙人生问题的话,那么,其结果不仅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造成它们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会使人放弃对生命意义和道德价值的追求,导致人性的沦丧,使本来富于情感的人变成一味追求物欲的动物。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坚决反对将科学与哲学(玄学)混为一谈、以科学代替哲学的观点,认为科学与哲学无论是研究的对象,还是使用的方法,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而哲学(玄学)研究的是生命本体。从研究的方法来看,科学研究的方法是“理智”,而哲学(玄学)研究的方法则是“直觉”。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的特点在于奋力向前取得所要求的东西,克服一切障碍以满足人生的需求。这种文化表现出一种对于自然界的征服态度,所用的认识方法为理智的方法。而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反身向内调和持中,它所追求的不是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征服与控制,而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自觉。这种自觉具体表现为对人类道德情感的体认,只能诉诸直觉体悟,而不能为理智所分析。
最后,梁漱溟进一步指明了理智的缺陷。他认为,理智只能认识自然,不能认识生命。因为理智的作用是分析的,其认识的工具只是一些僵死、固定的概念;以理智认识生命,必然置生命于四分五裂的境地,失去生命的本来面目与意义[4] (P38)。而且,“理智计算”还引发了另外一个极为消极的后果,使人有了以生理之“我”为中心的观念,造成了人之“真我”与精神的丧失。因此,必要直觉来弥补理智之缺陷,并以之来提升人类生命和精神之价值。
(二)直觉与理智之轻重决定中西文化之差异与优劣
梁漱溟在论述为什么中西印文化发展存在三条不同路径时,指出:“(一)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5] (P168)这里,仅从中国和西洋来看,中西文化之差异与优劣就决定于直觉与理智之主次轻重了。这其中自然包含了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路向的肯定与对西洋文化路向的否定的态度。在梁漱溟的心目中,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第二种人生路向,其根本精神是“理智运用直觉的”。中国“礼乐文化”,将这种源自直觉的人生态度条理化和规范化,形成高度理性化的文化。显然,这里梁漱溟所谓“理智运用直觉”指的是一种“价值合理性”。因此,梁漱溟极力主张中国要走第二条人生路向。他还指出,尽管西方人走第一条路向可以开出科学与民主,但这第一条路向走到后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问题,因而必须折回到第二条路向上来。
由此他分析西方文化的弊病,根源于它的文化心理或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叫做“直觉运用理智的”。他声称,西方文化的特点是“理智的活动太强太盛”[6] (P391),举凡西方文明的一切成就,如科学的发达,民主的进步,物质生活的富裕,等等,无一不归功于这理智活动的发达;但唯其理智过于发达,西方文化发展到十九世纪以后,精神上也受了伤,生活上也吃了苦。
(三)融合中西且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直觉观
梁漱溟的直觉主义认识论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柏格森哲学的影响,1916年前后,他开始把柏格森哲学与佛教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写作《究元决疑论》;接着他在撰写《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著时就直接把柏格森哲学作为评价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根据之一;1920年以后,他吸收并改造柏格森的创化哲学而构思《人心与人生》。在《中西学术之不同》一文中,梁漱溟本人就坦言:“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7] (P126-127)由此可见梁漱溟学术的融合创新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他用“直觉”解释明代王阳明的“良知”,并以直觉方法的认知功能和道德实践功能来诠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合一”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王阳明的所谓“良知”即是他所说的“直觉”。但他发挥了王阳明有关良知的个体性原则的思想,摒弃了有关良知的天理抑制个体及理智的规范作用的思想,明确指出:“所谓感觉作用和概念作用(即理智)者都非良知。”[8] (P708)这样,普遍的理智一旦被剔除,则良知即被等同于纯粹的个体意识,而这种良知在梁漱溟看来也就是直觉。他之所以强调把直觉理解为纯个体的感受,其目的就是要否定直觉受制于理智,而主张将直觉置于理智之上。这一点,梁漱溟显然偏离了王阳明突出理智活动作用的理性主义倾向。他将理智等同于分析而加以贬抑,实际上是企图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改造“王学”。他反对将知行问题视为理性之知与在其指导下的实践之间的问题。在梁漱溟看来,直觉认识为知,与其相连的带感情意志为行。这种直觉认识与其所引起的情感活动,即是中国传统哲学上所谓的知行问题。当人们错以西方哲学中的知识与行为、认识与实践等问题来解释儒家传统的知行问题时,便产生了知行合一与不合一的问题了。
总之,梁漱溟在吸取王阳明对良知的个体性规定的同时,又剔除了良知中包含的普遍理智,从而将良知个体化为直觉。这一过程同时在逻辑上又与引入的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相交错。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将柏格森的思想与王阳明的良知说相会通,才使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打上了直觉主义的印记。
同时,与柏格森以“使人们置身于对象之内”的直觉认识不同,梁漱溟认为直觉是一种“本能的得到”。同时,在直觉认识的功能上他也不同意柏格森的看法。他认为,直觉认识的对象不是外在世界的本体,而是人的主观情感,尽管两人都以生命为直觉的认识对象,但各自的生命概念却大相径庭。在柏格森的哲学中,生命是现象背后的本体和本源;而在梁漱溟看来,生命既非宇宙本体,也不是现象,生命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因此,柏格森的直觉要“进入”世界的本体,去认识物质世界背后的本原;梁漱溟则要“得到”一种主观的意味。为此,他在批评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对宇宙本体的认识时说:“然我们对他(柏格森——引者)实难承认,因为他的方法可疑。直觉是主观的、情感的,绝不是无私的,离却主观的,如何能得真呢?所以直觉实为非量如前已说。我们必要静观无私的才敢信任。”[9] (P406)应该指出的是,梁漱溟在吸收和利用柏格森哲学的直觉主义时,特别注意到了柏格森哲学的反理智主义特征;而且,梁漱溟的直觉主义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较大的差别;从二者的差别上可以看出,中国儒家哲学与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四)“世界未来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融合西方的民主和科学
梁认为,作为“全世界向导的西方文化已经有表著的变迁”[10] (P488),世界文化的未来是不难测的,有其必然的发展形势,而这种发展形势由事实、见解和态度三方面来指示。事实一面是经济现象说,见解一面是心理学说,态度一面是哲学。在梁看来,事实、见解和态度是不断变迁的,其中,事实的变迁是最重要的,“事实的变而后文化乃不得不变”[11] (P488)。梁指出,西方由机械的发明导致小规模的生活组织破坏和大规模生产的勃兴,进而导致资本集中和全不合理的经济现象。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现象“其戕贼人性——是人所不能堪”[12] (P492),必须坚决改变,而经济现象的改变必然导致文化、见解和态度的改变。梁认为,“人类将从人对物质的问题之时代而转入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13] (P494)。
与之相应,“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14] (P493),而文化的变革将导致见解即心理学的变迁,即西洋生活将转为注意情志的活泼和乐的生活即孔子“仁的生活”,集中体现为礼乐。认为“未来世界完全是乐天派的天下”[15] (P520):在物质生活方面,“必想法增进工作的兴趣,向着艺术的创造这一路上走”[16] (P520);在社会生活方面,“统驭式的法律在未来文化中根本不能存在……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17] (P521-522);在精神生活方面,“成功一种不单是予人以新观念并实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这便是孔子的路”[18] (P523)。梁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趋向。他指出,“此刻正是从近世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也。现在的哲学采色不但是东方的,直截了当就是中国的,中国哲学的方法为直觉,所着眼研究者在‘生’”[19] (P504)。所以“理智与直觉的消长,西洋派与中国派之消长也”[20] (P505)。可见,梁对生命派哲学的借用是为了指明中国哲学才是西方人的惟一救星。
根据文化的三路向说和三重现说,强调要排斥印度的态度,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同时,要把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全盘承受过来。由此得出他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复兴。”[21] (P525)
那么,如何才能持这种态度呢?梁指出:“我要提出的态度便是孔子之所谓‘刚’……刚的动只是真实的感发而已。我意不过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才真有力量,才继续有活气,不会沮丧,不生厌苦,并且从他自己的活动上得了他的乐趣……弥补了中国人素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若如孔子之刚的态度,便为适宜的第二路人生。”[22] (P531-539)这便是梁的最后结论,也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评定。在梁看来,中国的文化路向是意欲调和持中,历史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但他认为这种路向已不适于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必须把这种生活批判地拿过来,即在批判地接受这种生活的基础上把孔子原来的态度拿过来,从而创造一种适宜的第二路人生,这也就是“刚”的态度。在梁看来,只有持孔子“刚”的态度,才能奠定一种踏实的人生态度,才可以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而这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二 熊十力的“生命本体”说
熊十力一生以融合中西印、“昌明东方学术”为志:30岁前,“厌儒书平易,而深志于道”;30岁后,“更探佛氏大乘法,而酷嗜之”;40岁后,“卒归于儒”[23] (P3)。成中英在界定与评价现代新儒学时指出,在融合中西,“从事新儒家哲学之创造最有成就者要推熊十力先生”,“熊氏的哲学博大宏深,自成体系。他的哲学是深造于大乘佛学及易经哲学的结晶。他解悟佛学大乘之蔽,乃反归于易道之生生思想,这有类于宋明理学之承受佛道影响而归本于儒家易学。但他较诸宋明诸家更能正用佛释,吸收其精华,但在根本上却认同儒家,积极地开创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宗的哲学网络。”“他的思想,据他所言,实立足于他自己对真实本体的‘体证’,而此一‘体证’显然则由承受易经哲学的启示而来。”“更有进者,熊氏对本体真实的‘体证’并未造成他对知解说明、逻辑分析的忽视。”[24]
(一)对柏格森直觉主义的扬弃
熊十力以一种惊人的“直觉力”洞悉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力图重建儒家的天人统一观来回应西方哲学问题和现代人的生命安顿问题[25] (P40)。他一方面批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重逻辑分析、轻直觉体悟,见物不见人,完全脱离人的社会生活和生命体验而片面地追求事物之真;另一方面,对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思想作了合理的扬弃,即:“在吸收柏格森关于变化的绝对性的思想,关于宇宙过程乃是无限发展的生命之流的思想,关于生命本体的能动性、创造性的思想的同时,却明确拒斥和批判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26] (P199-200)熊十力指出:“柏格森《创化论》的说法,不曾窥到恒性,只妄臆为一种盲动,却未了生化之真也。”[27] (P397)所谓“恒性”,在熊十力看来,生命、主体、价值是有其确定的法则和意义的,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有则而不可乱”、“毕竟不失其恒性的”都是这个意思。在论说方法上,熊十力采取的是形式与内容、本体与方法、“境论”与“量论”合二为一的直觉方法,并表现出一种把儒家学说理论化、系统化的倾向。
(二)区分哲学与科学、性智与量智
五四以后,科学至上,科学愈益被强化为一种文化规范、一种权力话语,科学意识形态化的直接负面结果则是科学命题对人文言述的代换与消解,其现实含义是当以人文手段解决的问题反而嫁接到物化的方法途径上来了。这种代换与消解更多地表现在方法上,熊十力不无痛心地指出,“哲学与科学其所穷究之对象不同,领域不同,即其为学之精神与方法等等,亦不能不异,但自西洋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皆倾向科学,一切信赖客观的方法,只知向外求理而不知吾生与天地万物所本具之理元来无外。中国哲学究极的意思,今日之中国人已完全忽视而不求了解。”[28] (P145)“弟以为今日考史者,皆以科学方法相标榜,不悟科学方法有辨”,社会科学“非能先去其主观之偏蔽”,必不能采用纯客观的方法,“而须有治心一段工夫”,否则,精神之学就会沦为技术操作[29](P118)。而以科学之法治哲学,便“无法了解哲学,尤其对于东方的哲学更可以不承认他是哲学”[30] (P58)。在给张东荪的信中,熊十力写道:“中西学问不同,只是一方在知识上偏重一点,就成功了科学;一方在修养上偏重一点,就成功了哲学”[31] (P68)。
对熊氏来说,中西的会通及新文化的重建当以中西之辨为基础,而区分中西学各自的思维方法,以期达到各自的还原,当是熊氏中西之辨的首要含义。熊氏有鉴于有以西学方法治中学最终会导致中学精蕴的瓦解,故特别强调,“治西洋科学和哲学尽管用科学的方法,如质测乃至解析等等;治中国哲学必须用修养的方法,如诚敬乃至思维等等”[32] (P68)。
如果说,哲学与科学的不同表现在对象上,哲学穷究浑全、绝对的本体,科学探讨分殊的、具体的现象,那么,二者在方法上的不同则是哲学依赖性智,科学的工具则是量智。熊氏《答谢幼伟》一书集中谈论性智与量智,熊氏开始便云:“每以为东西学术之根本异处当于此中注意”。缠绕熊氏心怀的仍是东西文化问题,民族的危机使其更为迫切,熊氏一直在寻求一种解决之道。熊氏写道:“抗战前,友人欲与吾讨论中西文化,以为二者诚异,而苦于不可得一融通之道。吾时默而不言,因《量论》未作,此话无从说起。实则,中学以发明心地为一大事(心地谓性智),西学大概是量智的发展,如何使两方互相了解,而以涵养性智,立天下之大本,则量智皆成性智的妙用”[33] (P675-678)。中学的终极目标在于亲证本体,与之合一,真实的把握自我与宇宙的真实。熊十力坚决主张,本体的亲证唯恃性智,不兼量智[34] (P677),性智是一种自向、内反,不能加以对象化的修养方式,它与本体,乃是自见自明;本体与它,乃是真实的呈现。量智则是一种认知方式,它指向客观化了的经验世界,以无限分析的态度把握分殊的具体。张东荪尝言:“西方人所求底是知识,而东方人所求的是修养。换言之,即西方人把学问当作知识,而东方人把学问当作修养。”熊十力以为这是见到了东西文化和哲学的根本不同处[35] (P65-66)。量智活动如果脱离了性智,就会发生侵夺自然、物化自我的情况。西学任量智,致力于“支离破碎”,成就了科学,但却不见本体。因而熊十力对西学颇有批评。
由此,熊十力指明了新文化建设的理路与方法:立足于文化之本根,开发量智以成性智之妙用。熊十力说:“哲学不仅是理智与思辨的学问,尤在修养纯笃,以超越理智而归于证量。《新论》根本精神在是,中土圣哲相传血脉亦在是。”[36] (P349)在他看来,开发利用量智当以性智为主,若无性智为主,纵使量智发达,也不足以利人生,反足以害之。“量智”重在分,“性智”重在合。二者的关系是“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如何自“性智”启发“量智”,自“量智”导入“性智”?入手处即在整体与部分、一与二两个层次上。“量智”不能直接导向“性智”,故科学不能直接推出形而上学;同样,“性智”也不能导向“量智”,故形而上学也不能直接推出科学。但,科学与形而上学,“量智”与“性智”,却能从把握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中启发出来。此一把握可视为“性智”之用及“量智”之体的反省,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思想之圆环,亦即成中英所谓“本体思考之圆环”(circle of ontological thinking)[37]。人已在此圆环中,如何善用此一圆环,同时开拓智慧与知识,并促其相互增长与充实,则有待人求证于本体而不泥于本体的体验了。熊十力所谓“体证本体”而“融合量智”,其义即在于此。
那么,如何求得“体证”呢?熊十力认为,关键就在修养工夫,即努力修养,使神明昭彻,不为物役,不受形累,不溺于私欲,不囿于偏见,臻于此境,则自然达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体证”境界。“体证”的对象及结果为本体真实,此当是就“体证本体”之后的反省而言。“思辨”的对象及结果为知识。本体是整体一如的,知识则是“支离破碎”的。此点即说明“体证”与“思辨”有本质上的差异。同时,熊十力认为,“体证”与朱子所称“亲切体认”亦有差异,因朱子所言“亲切体认”只用于读书穷理之事,而不及于本体;即如程颐“体认天理”也只是基于涵养察识,就“天理”之发用处体会,与本体之呈露的“体证”不尽相同。熊十力的“体证”与王阳明之“良知本体”相类,实际是结合佛家之“寂照大明”之境与易道之“生生不已”之境而成。总之,“体证”为一修养工夫及修养境界,是私欲净尽、知见脱落之后,觉悟到人性最深处的本心本体。这种本心获得自证自明后的终极体验就是性智显现。体悟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广大和谐境界,彻内彻外,只有本体流行,翕辟成变,无所谓主体小我,无所谓客观宇宙,造化的玄机,天人的奥蕴,尽在一点灵明,当下即是的透悟中展现无遗。此一境界既是湛然虚明的,又是万理盎然的[38]。
(三)立足儒释道,吸纳西学精华,构建“内圣外王”的新学
熊十力认为,世界上的学问可分为科学和哲学两大类。科学凭籍理智(知识理性),向外部世界追求,其发现无有穷尽;哲学涵养、显发性智(智慧与道德理性),向内深入人的内部世界使真正的自己觉悟,从根本上洞察宇宙人生。熊十力不反对、不排斥科学和知识理性,但他认为如果将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当作人生的终极意义,人生就迷失了根本。他指出,人生当务之急在于“志乎体道而实现之”,亦即“内圣外王”。
熊十力认为,以儒、释、道三家为主要代表的东方古学有一共同特点,即同为日损的“为道之学”,也就是哲学。三家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反己实证之学,不同于“日益之学”的科学。他指出:“余以为科学日益之学,其根柢在物。不独以发见物质宇宙的秘密为务,而其变化,裁成乎万物,俾宇宙富有日新,是其任甚重也。古哲日损之学,其根柢在心。盖损除一切碍心之物,不容自欺自蔽。故日损之功,发于自我改造之本愿,所以全性保真,毋失人生至高无上价值,日损之学,不堪废坠者,诚在此耳”[39] (P27-29)。日益的科学的任务是探索和改造外部世界,使之富有日新;日损的反己之哲学的任务在于深入和改造人的内部世界,使人体认到人生至高无上的价值。哲学能使人达至“内圣”。熊十力认为,改造人的内部世界达至“内圣”与“辅相”、“裁成”(改造自然与社会,实现民主与科学)开出“外王”是一体不可分割的。不过“内圣”是头脑和关键,若不能“内圣”,则“吾人丧失灵性,而陷于迷乱之惨境”。因为,开出科学之花的知识理性很有局限,单凭逐物不返的知识理性无法使人体认到宇宙人生的真源,找到生命的源头活水,发现生命的伟大意义。熊十力借老庄思想反复强调,科学应受到哲学的统领,知识理性应受到智慧道德的监督。只有这样,人类在运用知识理性向外探求,发展科学的同时,才不至“物化”,失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显然,在构建新文化问题上,熊十力无疑是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来融合西学的。
熊先生和梁先生一样,要寻求自己的安身立命处,从佛学向儒学的转化,归宗于陆王心学,又比梁先生进了一步,在道德的实践、心灵的开拓、生命的探原、本体的体证各个层面上都常有“吃紧处”,独到处。他还第一个提出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一用性智(走内证的道路)、一用量智(走外向的道路),而不是一主非理性、一主理性的问题。这是其创新处。熊十力先生以直觉体认方式提供了一个有关中国哲学思想方式的模式。他把易传“体用不二”、“天人合德”的观念,中庸“道合内外”、“物我一体”的修养,玄学体用不分的思想,宋明理学、心学标榜的“天人合一”的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等思想观念凝聚并组成一个完整且具有相当系统性的本体哲学体系。他依据直觉体证的方法论的基础建立起他的本体论,不但结合先秦及宋明诸家思想以彰显“体用不二”之理,而且融会道释以充实其本体论。他讲本体为流行亦为主宰,为翕亦为辟,为变亦为不变,从不同角度来彰显其“体用不二”的命题。最后,他把体用关系运用于“理气”问题与“心物”问题上,为此等问题开拓出新义与新境。从而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坚固有力的本体论、方法论的模型。
标签:梁漱溟论文; 熊十力论文; 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柏格森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本体感觉论文; 国学论文; 良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