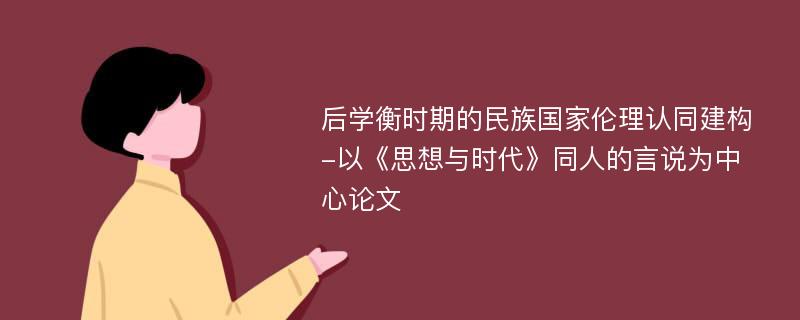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都萧雅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摘 要]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 《思想与时代》;学衡派;国家认同;民族主义
《思想与时代》从1941年8月发行第一期开始,到1948年发行最后一期即第53期之后停止,中间经历了接近两年(1945年3月到1946年12月)的停刊。其所发行的时间横跨8年,是学衡派学人群体在1940年代的主要思想阵地。其核心作者群为张其昀、张荫麟、钱穆、谢幼伟、郭斌和、贺麟、朱光潜。实际上,《思想与时代》的作者群与《学衡》《国风》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像张其昀、张荫麟、郭斌和等典型的学衡派成员之外,另有两股不同的血液。一股即几位早期新儒家学者,如贺麟、冯友兰、熊十力;另一股则为一批科学家,如竺可桢、卢于道、张文佑等。沈卫威以1941年《思想与时代》创刊为界,分出了“学衡派”的前后两个时期。从尊重《思想与时代》与《学衡》《国风》在学脉以及文化立场上的相承性与超越性出发,本文采用沈卫威教授的定位方法,认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是继《学衡》《国风》所构成的“学衡派”之后的“后学衡时期”的学术期刊。
就主旨而言,民族建国问题贯穿着《思想与时代》的始终。民族建国问题反映在理论层面,就是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一种深层反映。建立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在民族的范围内组织国家,不仅需要构建国族认同,同时也需要构建国家认同。维斯特伐利亚体系成立后,客观上在近现代国际秩序中,民族国家成为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单元。而民族国家是一个以启蒙理性原则为基础的现代性概念。启蒙之后,封建王朝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政权的组织形式由封建王朝演变为民族国家,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则由君权天授变为了政权民授。“正如威默指出的,现代性是由族群与国家主义原则所构成的,因为公民权、民主以及福利制度都与族群及国家性的排他形式联系在一起。”(1) [英]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严春松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页。 这就意味着,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具有两张面孔,其一为民族共同体,亦即历史文化共同体;其二为国家共同体,即民主的法律政治共同体。所以民族建国在理论上不仅有着民族主义的要求,还有着民主主义的要求。《思想与时代》同人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努力是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双重思想主导之下的。1940年代的中国,清王朝已经被推翻,形式上的中华民国建立起来以后又几度经过复辟和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虽然最终形成了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局面,但是日本又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所以近代化的国家认同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这一时期,强调满汉之争的种族民族主义也已经失去了意义,民族主义的中心议题已经不再是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之争(梁启超语)。中华民族的概念业已提出,但却远远没有建构丰满并深入人心,形成全民共识。《思想与时代》同人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历史任务就是建构强化对于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
一、国族伦理认同
《思想与时代》同人在使用民族一词时,是在几种不同的含义之下使用的。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近现代之前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话语,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存在于以华夏为中心文明的遵循文化认同原则的天下秩序之中,(与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对应的国家形态是王朝国家。)“地理上的‘华夏中心论’、种族上的‘华尊夷卑观’以及伦理秩序上的‘天下’价值观”(2) 徐嘉著:《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59页。 是其基本特征。除此之外,在《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当时民族情况的论说中,“民族”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又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霍布斯鲍姆“原型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民族(ethnic group),即“享有共同风俗习惯的一群人,他们是享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大部落”(3) 许纪霖:《国族、民族与族群: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如何可能》,《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这是自然形成的民族,是一种自然共同体,与组建民族国家没有必然的联系。另一种则是与组建民族国家密切相关的民族概念,是国家或者希望成为国家的共同体,在中国即“中华民族”,这实际上是一个国族概念,是具有建国冲动的,与建构一个作为近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是这两种含义中的哪一种,民族平等都是其应有之义。在国族的意义上使用民族概念时,其中一个基本诉求是国家民族与国家民族之间应当平等;在民族国家内部的自然民族的含义上使用民族概念时,其中一个基本诉求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
小学数学的学习,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而且还是学生学习其它学科的一把钥匙。因而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并巧妙地将数学知识渗透到生活里,延伸到实践中,从而让学生参与知识产生的整个过程,进而提升小学数学教学的有效性。
仅以王焕镳《春秋攘夷说》一文为例,就可以找到以上几种民族的不同含义。“韩愈谓春秋谨严,何谓乎,盖莫谨于华夷之辨矣。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守礼义则谓之中国,尚残贼则谓之夷狄。中国为文明之称,夷狄乃野蛮之目。”(4) 王焕镳:《春秋攘夷说》,《思想与时代》1942年9月第14期,第14页。 在这句话中,“中国”“华”“夷”“夷狄”都是民族话语。但是这些词语所指代的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民族,也不是以血统或者种姓作为标准对不同的民族进行区分,而是以文化为界,分为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这里所谓文化,再明白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诸夏是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城市国家,凡不以农耕为生活基础,又不组织城市国家的,则不为诸夏而为夷狄。”(5) 钱穆:《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思想与时代》1943年6月第23期,第12页。 “中国”或者“华夏”是对农耕文明民族的称呼,“夷狄”则是对游牧野蛮民族的称呼。“世界古国独中国得存于今日,独中华民族能同化各民族而成一国族,夫岂无故。”这同样也是《春秋攘夷说》(第10页)中的一句话,这句话里的三个民族语词——“中华民族”“民族”“国族”是民族的另外两重不同含义。其中“民族”一词指的是自然形成的民族,“中华民族”和“国族”在这里是同义词,指的是与中国成立民族国家密切相关的国家民族。
尽管在多重含义上使用民族这一概念,但是《思想与时代》同人所希望建构的民族伦理认同是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的统一国族伦理认同。不同于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大多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建国理念和现实,中国的历史现实为长期多民族共存。《思想与时代》同人在建构强化民族伦理认同时,其所用的民族概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应的真实含义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而不是单指汉族之类的某一个民族。1937年以后,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断丧失,中国仍是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战争的现实激发了新一轮的民族意识,面对帝国主义的剥削战争,中华大地上的人民亟待团结起来,一致抗敌。“一个硬实力和软实力皆优于自身的异族的出现,是中国三千年所未遭遇的大事件,一个绝对的‘他者’的出现,真正刺激了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觉悟。”(6) 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2月,第50页。 这个时期,几乎已经不会再听到提倡满汉之争的小民族主义的呼声,联合国内所有民族一致对外的大民族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也是《思想与时代》同人的一致立场。如杨联升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36期上的一则书评《富路特 中华民族小史》;钱穆的系列文章《中华民族之宗教信仰》(第6期)、《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第11期)等;谢幼伟的《论民族生存权》(第16期)等文章都是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
《思想与时代》同人中,对国族认同的建构主要是由钱穆、谢幼伟完成的。他们所建构的国族认同首先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意义上的认同,期待解决的是“我们如何来理解自己”的问题。在人们理解自己的过程中,族性因素是不可排除的。“人们不仅仅是因为利益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感情而活着,他们要靠气愤、悲痛、焦虑、嫉妒、友爱、恐惧和热爱生活而活着。”(7) [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人民 民族 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21页。 对于民族的感情是人们感情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费孝通认为,民族认同就是处在同一民族中的成员感觉到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心理感受。文化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国族认同强调伦理的民族性,旨在回应人们的这种情感需求和纽带,为国族共同体成员提供一种基于历史与文化的归属感。
所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国族认同建构呈现出了寻找属于“我们”(指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的共同特性以期巩固中华民族国族认同的特点。如果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20世纪梁启超提出之初还是一种“伦理虚体”,那么经过“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战建国作为最高目标成为中华民族的全体共识,中华民族已经逐渐由“伦理虚体”向“伦理实体”转变。在《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论述中,“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层次的综合概念,它将国内的各个族群和自然民族囊括其中。而《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建构强化民族认同所做的主要努力便是站在1940年代的立场上,回溯历史,寻找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同一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描述历史,发扬这种同一性,从而强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国族伦理认同。
首先用高速粉碎机将钼精矿粉碎,用80目标准筛将粉碎后的钼精矿进行筛分,取80目筛下;其次,称取一定量去离子水,80筛下钼精矿加入2 000 m L的高压反应釜内,盖好釜盖;第三,向反应釜内预充一定压力的氧气,并保持一定时间,检测反应釜是否泄漏,若无泄漏,将反应釜内氧气排出;第四,开启搅拌、加热物料,待温度升至试验温度后,缓慢充入氧气至试验氧气分压,保温、保压一定时间后降温泄压;第五,打开反应釜釜盖,取出物料,用真空泵、抽滤瓶进行固液分离,并用一定体积的热水洗涤滤饼,废水取样检测,将滤饼送入热风循环烘箱烘干脱水,烘干后的滤饼取样检测。
谢幼伟主要通过梳理柏烈德莱的伦理观,借助其“文化趋势”的说法来阐释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他认为,纯粹的个体是不存在的,每个个体都无选择地天然生活在民族中,民族性与民族诉求深植于血液之中。“其实,任何一个人,一生下来,即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他是父母之所生,而父母又是某一民族的血统,这民族的血统或民族型(National Type)决不是他所独有,而必与同一民族之人所共有。假如‘文化的趋势’(Civilized tendencies)可以遗传,那他所得的‘文化趋势’又必与同一民族之人所共有。到了他逐渐长大,能语言,受教育的时候,则整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必侵入他的生命而为其要素。这样,整个民族的生命充满了他的生命,他是生活于民族的生命中,与民族的生命或普遍的生命为一。”(8) 谢幼伟:《柏烈得莱的伦理观》,《思想与时代》1941年9月第2期,32—33页。 这与现代自由民族主义者柏林和耶尔·塔米尔关于人性中民族性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将民族性当做个体生命的要素来对待,尤其是将个体希望处于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之中,按照自己的民族习惯生活的意愿当做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诉求。
在这些文章里,钱穆基于历史分别从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法律观念、政治思想、宗教信仰来强调中华民族的独特民族性,阐述了为什么“我们”是“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不是“他们”,以及为什么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他们”不是。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后来经过编辑修改即为《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钱穆自称是从为《思想与时代》撰稿开始了由历史研究向文化史研究的改变。这一系列文章的一个显要特点就是: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文化史进行研究,文化史研究与民族史研究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918’之后,日寇入侵中国的狼子野心日渐暴露,民族日益危急,引起众多学者对中华文化存亡的担忧,于是,他们把一腔热血诉诸文化史研究。”(9) 郑先兴:《20世纪的文化史研究》,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9-240页。
本组收治的患者共20例,男14例,女6例,年龄在17-62岁之间,平均年龄(42.26±2.15),全部患者均符合肺脓肿的诊断标准。其中吸入性肺脓肿患者13例,血源性肺脓肿患者4例,继发性肺脓肿患者3例。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起病急骤、高热、寒战、咳嗽、胸痛、气急等。
如果说谢幼伟主要致力于论证普遍人性中民族诉求的合理性,那么钱穆则主要论述了作为“中华民族”的“我们”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我们”独特的民族性。钱穆是《思想与时代》月刊的主要撰述人之一,在总发行期数为53期的《思想与时代》上发表的文章有43篇,几近每期都有。在这些文章中,涉及民族认同建构以及中华民族民族性的文章占有较重的比例,多达13篇。这一系列文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对“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历史的梳理,主要包括《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第23期)、《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第27期)、《新民族与新宗教之再融合》(第29期)、《宋以下中华文化之趋势》(第31期)、《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第32期)这5篇文章。在这些文章里,钱穆主要采用回溯的历史方法,站在1940年代回望之前的历史,区别于以前以正统王朝为中心,将其他民族看作敌对民族的历史叙事方法,他将“中华民族”整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重新叙事,发掘民族同一性,从而希望从历史事实方面建构强化对于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的伦理认同。另一类为对“中华民族”的“族体—符号”的梳理,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第3期)、《中国社会之剖视及其展望》(第4期)、《中华民族之宗教信仰》(第6期)、《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与教育制度》(第7期)、《中国人之法律观念》(第8期)、《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第11期)、《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续)》(第12期)、《古代学术和古代文字》(第26期)这8篇文章。
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而不是欧洲民族或者其他别的民族,正是因为其稳定且独特的文化风俗以及生活方式。钱穆对这些独特的风俗和生活方式的总结可以看做是对安东尼·史密斯“族体—符号的”(ethno—symbolic)方法的应用,具有族裔民族主义的某些特点。这种方法认为传说、价值、神话和符号对于民族成员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像法国大革命时和西方的公民的、地域的民族主义那样将民族视为共有一部法律,共享一个公众文化的公民的地域集合,而是将民族看成是一个拥有统一谱系,拥有本土语言文化、历史和人口流动性的共同体。”(15) [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人民 民族 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2-63页。 钱穆同样珍视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承担着巨大的情感负载,它的成员意识到他们高度参与其中。”(16) [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人民 民族 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本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字、伦理价值、风俗习惯等都是本民族的伦理符号,这些伦理符号对于民族成员来说具有象征意义,是民族成员个体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为民族成员提供着情感联结和支持。
钱穆认为,中国民族是由多数族系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逐渐融合、渐趋统一的;在统一之后,仍然不断扩大。我们之所以能够具备形成“中华民族”统一伦理认同的基础,是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的。其一是“同姓不相通婚的风习,使异血统的各部族间经长时期的互相婚媾而血统益臻融合,感情益臻亲密,一切文化方面亦益臻协调”(11) 钱穆:《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思想与时代》1943年6月第23期,第11页。 ,以致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中国人之间似乎根本上便没有一种很清楚的民族界限存在。蛮夷狄戎“并不是一种或几种异族盘踞在中国的外围。他们的远祖尽可能全是与姬姜子姒诸部族同姓同宗一样是中国人,一样是诸夏神明之胄,而全错杂夹居在中国的内地,只是他们的生活,(即他们的文化)依然是较原始较野蛮,并不能像当时诸夏般之一样进步到同一的水准而已。”(12) 钱穆:《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思想与时代》1943年6月第23期,第17页。 其二就是历史上的中国人以文化作为华夷分别标准的观念使得整个社会逐渐高度同质化。而整个“中华民族”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不断向农耕生活方式与文化靠近转变,并学习其“宫室宗庙社稷衣冠车马一切文物制度”(13) 钱穆:《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思想与时代》1943年6月第23期,第16页。 ,最后同质化的历史。
通过实验研究了脉宽为2.5 ms的单脉冲毫秒激光对铝靶材打孔过程中的熔融物喷溅情况。实验结果表明:随着激光能量的增加,喷溅物的速度持续增加,随后又趋于稳定。当激光能量为7.5 J时,气化及喷溅现象在1.38 ms即截止。当激光能量为46.2 J时,熔融物喷溅速度达到约12.6 m/s。进一步的模拟计算得到的喷溅速率在数值上与实验结果比较一致,在变化趋势上略有差异,考虑到实验误差与理想的计算模型所带来的实验误差,实验结果与模拟计算结果总体是相符的。研究结果对毫秒激光打孔过程中熔融物喷溅迁移现象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激光打
钱穆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认为夏商周几个部族之间存在着互相通婚的事实,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早期的民族融合。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具有商部族的血统,而周武王的母亲太姒则具有夏部族的血统。而周朝的文告中也没有明显的将各个民族相区分的观念。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左传》与《史记》对晋国历史的记载间接考察了对于戎的称呼,认为戎与诸夏从血统上来讲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晋献公有三位夫人分别叫大戎狐姬、骊姬、小戎子,狐姬和骊姬姓姬,与晋同宗;小戎子姓子,属于商代的后羿,但当时这三者所在的部落都被称为戎。这些都可以证明,中国人从古代起便没有血统意义上的民族界限,中国历史上所提到的异民族,其实也只是就文化不同而言。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东汉末年匈奴、鲜卑、氐人与羌人被正统王朝视为异族,但是在他们相互之间的传说中却能够发现他们其实共享着诸夏相同祖先。而这些当时所谓的异族后来也已经采用中国的农事生活方式,教育程度也有很大提高,他们在当时已无异于是中国人之一部分了(14) 钱穆:《新民族与新宗教之再融合》,《思想与时代》1943年12月第29期。 。即使是在南北朝时期,南北两方也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地,那时候没有随着东晋王室南渡的士族在北方延续着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就导致虽然隶属于不同的政权,但却共享着同样的文化,从而为后面重建统一的伦理认同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宋元明清同样也是“中华民族”不断进行再融合的时期。自宋开始,虽然不断有异文化的族群入侵中国,但是这些族群最终全部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女真、蒙古、满族原本都是与传统的农耕中国文化异质的游牧文化,但是最后都全部或者部分地为中国文化所同化,消融在中国民族的大炉里。如果说一直到晚清以前,中华民族都处在不断的民族融合过程中而不自知,那么晚近以降,中国文化与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相遇并且备受凌辱,而当时中国的农耕社会又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工业社会,不再有同化的能力,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才渐渐地产生了自觉的民族意识。
站在1940年代回溯历史,钱穆认为,从上古时期一直到1940年代都是整个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不可否认,“中华民族”的概念与满蒙汉藏回这些自然形成的原生民族概念不同,是到近代才出现的,甚至直到现在,中华民族仍然处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是一个被创造的概念,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凭空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凭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得不到认同的。“你必须有一种虚构般的过去,这个过去还必须是真实的。”(10) [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人民 民族 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就中国的国族认同建构来说,国际现实和知识阶层的创造性联手打造了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但是,“中华民族”的背后仍然是对世代历史传统的融合与继承。钱穆回溯历史的工作,实际上也就是沿着历史的脐带寻找“中华民族”肚脐眼的工作。
钱穆认为,秦朝开始,中国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而由文字作为媒介所能够达到的认同是不可小视的。中国文字是中国民族独特之创造,有着特殊的面貌与精神。“中国文字有其特殊之优点,其先若以象形始,而继之以象事”,又能“以甚少之字数而包举甚多之意义”(17) 钱穆:《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思想与时代》1942年6月第11期,10—11页。 ,而后来形声字的发明则将文字和语言联系了起来。有些文字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本来有着不同的读音,但是虽然语音不同,文字却是通行的,这样本来不同地区和族群相差甚远的语言在通行文字的影响下也渐渐变得相似。“在中国史上,文字和语言的统一性,其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性者为功甚大。”(18) 钱穆:《古代学术和古代文字》,《思想与时代》1943年9月第26期,第41页。 除此之外,中华民族也有着独特的宗教信仰与法律观念。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有两大特征:其一是政治与宗教合流,而中国宗教在社会上之功用处于比政治次一等的地位;其二是中国民族宗教信仰的对象,“并非绝对之一神,又非凌杂之多神,乃一种有组织有系统之诸神,或可谓是等级的诸神,而上以一神为之宗。”(19) 钱穆:《中华民族之宗教信仰》,《思想与时代》1942年1月第6期,第13页。 中华民族的法律观念与西洋民族也有不同,西方之法律观念常为权力的,而中国之法律观念则为道德的。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法律适用于防过闲非,而不能令人入于美德。法律是道德的补充,用来“补道德之不逮”(20) 钱穆:《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思想与时代》1942年3月第8期。 。 虽然说这其中有些观念未必是完全可取的,但是,它们毕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稳定的心理素质,是可以藉由区分“我们”与“他们”的历史文化因素,因此,发现并阐述这些因素,在它们的基础上建构的“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民族共同体”,在事实上起到了强化国族认同的作用,在抗战的背景下增强了国族凝聚力。
《思想与时代》同人希望建构强化的国族伦理认同不仅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意义上的伦理认同,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意义上的伦理认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族概念,是与民族自决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民族自决权的适用范围有着一致立场。他们认为,基于中国长期多民族共存的历史现实,民族自决权在中国的运用对象只能是作为国族的整个“中华民族”,而不是单个的自然民族。谢幼伟在《论民族生存权》(第16期)一文中明确将民族生存权的适用对象规定为民族国家或国家,“本文所谓民族,义兼国家民族与国家,虽有区别,然在本文中,可不必加以区别。”(21) 谢幼伟:《论民族生存权》,《思想与时代》1942年第11月16期,第5页。 张其昀也认为,民族自决权的应用范围应当限定为国家民族(或为主权国家)之间。“民族自治或民族自决之说,其应用国与国之间者,固属不移之理,至其应用于一国领土以内者,问题便并不简单。”(22) 张其昀:《战后国际关系之新思想》,《思想与时代》1947年3月第43期,第21页。 对于民族自决权能否应用于国家内的少数民族,则应当谨慎考虑。如果国内的少数民族也可以随便应用民族自决权,那么就很容易超出民族自治或者地方自治的范围,有分裂国家的危险。甚至有可能国内的少数民族势力与国外的分裂势力相结合,结成城下之盟,这对国家主权是极为不利的。
近代的国际体系只为两三百个民族国家留出了位置,这就意味着仅仅有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并不能够实现民族自决,国家民族必须建立民族国家,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自决,而国族伦理认同也必须进一步升华为国家伦理认同。而这种已经觉醒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民族意识在国际社会体系中要求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来建立民族国家,享有并行使国家主权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政治民族主义的特点,“政治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形态,它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与追求‘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属于特定民族的国家和政府。”(23) 徐嘉:《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75页。
换热系统循环热水(70℃)先经过缸套水加热到97℃后流入烟气集热器(需缸套水流量60 t/h),经过高温烟气加热至高温(159℃),热水流量43 t/h。
二、国家伦理认同
与民族概念的复杂性相对应,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概念,《思想与时代》同人主要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国家这个概念。其一是指近现代之前的王朝国家,其二是指晚近之后的民族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使用。如果说《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中华民族”国族伦理认同的建构和强化是在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但主要是在文化民族主义主导之下的话,他们对于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则主要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主导之下。国族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阶梯,“作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民族提供了共同体的独特形式,而民主提供了共同体的政治内容”(24) 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77页。 。
《思想与时代》同人中有一些学者也对我们生活于其上的土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史学与地学关系密不可分,同人的作者群中本来就有一批史地学者,钱穆、张荫麟、王绳祖、缪凤林、周一良、杨联陞等都是主要研究史学的学者,张其昀、竺可桢、任美锷、叶良辅、沙学浚等则为主要研究地理的学者,这也与他们出身的南高—东大重视史地的教育背景有深刻关联。他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上的土地的地理研究与抗战的背景相结合,就表现为对国防地理的特殊重视。《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领土(包括海陆空)的论述总是与国家而不是民族联系在一起。首先,由于中国式的民族认同是一种复合式的,即在中华民族认同的国族认同下还有具体的不同自然民族认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将领土与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话有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这与同人想要建构强化的统一国家是相左的。其次,“中华民族”的成员与“中华民国”的成员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包括了所有国内的中华民族成员以及海外侨胞,而中华民国的领土是由其国民所共同拥有的,海外侨胞属于中华民族的成员,却并不属于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以,将领土认同与国家认同而不是民族认同联系起来是相对妥帖的。
民族与国家是与民族主义联系最为紧密的两个概念,而不论是民族还是国家,土地都是其活动不可忽视的因素。西班牙学者胡安·诺格的专著《民族主义与领土》专门讨论了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土地、领土几者的微妙关系。他认为,“在当今已被国家占领的世界上,领土是民族构建过程中的政治资源。”他还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地理学视角对于理解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民族领土’(‘territorio nacional’)观念,是一切民族主义的根基”,“各种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领土意识形态形式”,民族主义“明确要求特定的领土,这块领土是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是其强调所谓特殊性、例外性和历史性的根据”,民族主义是按照这个特征对人们进行界定和分类的,“特别是确定一个人属不属于一块领土和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共同享有一块领土的人们,仅凭空间联系就应使他们拥有某种共同利益。”(27) [西]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许鹤林,朱伦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23页。
3)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采用先虚后实、虚实融合的教学方法,既提高学生实物拆装的规范性,又提高教学实训设备的可重复利用率,节约了教学成本,达到高效教学的目的。
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对于民族国家有一个经典定义:“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25)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立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47页。 可以看出,与对“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国族认同不同,领土、军事、法律、制度等因素是建构国家认同的必要条件。对于国家的“共同归属的意识不仅体现为,而且又反过来培养集体认同的情感符号,如国歌、国旗、仪式、礼节、和牺牲的英雄的纪念碑”,“它们是我们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共同体的象征,需要一种不会搞错的和可触摸的体现。它们将我们融入了共同体的生活,并把我们与其过去和将来联系起来。它们也煽动政治感情,并使哈贝马斯关于符合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那一高度睿智的概念有情感及文化方面的深度。” (26) [英]爱德华·莫迪默 罗伯特·法恩:《人民 民族 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培养国家认同的情感符号同样也有论述,主要集中在对于国都的讨论中。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主要包含了国家领土认同、制度认同、法律认同、国家符号认同四个层面,(领土认同、制度认同与国家符号认同可以说都是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的不同方面,)是在“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再建构一种“政治—法律共同体”,两者一起构成“民族国家共同体”。
是冰川湖湖浪对基岩及陡壁冲蚀作用的结果,和韩同林教授所认定的河北丰宁平顶山山麓地带冰湖浪形成的湖蚀龛相似。仅见于朗乡花岗岩石林地质公园,数量较多,可达60~70余处,最大的冰壁龛为朗乡花岗岩石林公园主峰792高地上的冰壁龛,由一连串4个较大的冰壁龛连接在一起,其底部是一组略向北倾斜的平直节理,单体呈半月型,高1.7~1.9 m,宽3~4 m,水平延深0.8~1.2 m,内壁光滑,构成“鳄鱼头”景观。另外的冰壁龛也构成多种奇特的景观,如朗乡地质公园的“雄狮怒吼”等。
在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人们主要是对出生的群体、氏族、部落等产生归属的感情,亦即一种族群认同。但是,随着近代国际体系的成立,《思想与时代》同人所希望建构的国家是一个被近代国际体系所承认的国家,亦即获得国际人格的国家,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民族国家成员的基本权益。这样的国家既不可能是曾经处于朝贡体系中的天朝上国性质,也不可能是当时半殖民地的国家性质,而必须是拥有独立主权,完整国际法律人格的主权国家。“古人称三十而立,民国三十一年以后,中国真能在世界上确立其国际人格么?这是我国民共同努力的鹄的。”(28) 张其昀:《国防中心论》,《思想与时代》1942年2月第7期,第32页。 在对外争主权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则被广泛地发动起来,“整个人民群体被视作一个维护自己根本民主权利的、反对上层帝国阶层掠夺的工人大众阶层。”(29) [英]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严春松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6页。 与建立民族国家相伴而生的是对领土和主权的要求,“由于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等概念开始成为社会凝聚的主要方式,‘从政治上界定的领土最后成为确定人们归属的因素;发生了由强调群体向强调领土的转移……以前,英国是英国人生活的地方;现在,英国人是指生活在英国的人们。’” 这种(30) [西]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许鹤林,朱伦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伦理认同的转移在中国也很明显。从晚清开始,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更是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这些不平等条约中,除了不平等的贸易条款以外,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割地赔款。“人类的领土意识也就是地理权力表现”(31) [西]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许鹤林,朱伦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一次次的割让土地以及列强对被割让土地的矿产等资源的掠夺使国人感受到屈辱,感受到权利被侵犯,这从反面促进了人们对于领土的认同意识,也激起了国人对于领土范围内各种资源的保护意识。张其昀在《中央与地方之均权制度》一文中明确指出:“宪法草案第四条,‘中华民国领土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之疆域。”(32) 张其昀:《中央与地方之均权制度》,《思想与时代》1941年9月第2期,第12页。 想要保护并利用这些资源,必须先做研究,所以以张文佑、叶良辅、任美锷为代表的地理学家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的文章对我国当时国界内的地理地质做了很多具体的研究,既有局部地理研究,如《蒙古之地质即瀚海地形(书评)》(叶良辅,第4期)、《叠部概况》(任美锷,第6期),《广西的石林》(张文佑,第22期);也有整体地理研究,如《李四光著中国地质撮要》(张文佑,第11期)、《中国自然地理纲要》(李四光著、张文佑译,第16期)、《中国之地形》(任美锷,第25期),《中国气候概论》(卢温甫,第28期);还有从国防角度关注地理研究的,如《国防地理(书评)》(沙学浚,第6期)等等。这些文章的发表既是知识传播的过程,是知识藉由纸媒被人们掌握的过程,是人们透过媒介对我国的领土更加了解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中国领土认同的建构和传播的过程。
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也是《思想与时代》同人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由《学衡》《国风》时期的民族话语转向国家话语是“学衡派”(指广义的学衡派)在《思想与时代》时期即后学衡时期的一个重大转变。在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上,《思想与时代》同人面对的是一个未竟的任务,即中国由清及之前的王朝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一直没有真正完成。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政治制度与每一个国民的政治生活关联甚深。如果说在国族伦理实体内部,共同的历史生活以及在伦理实体内部被充分意识到的对民族的情感是连接不同个体的无形精神纽带,那么在与国族伦理实体不尽相同的国家伦理实体内部,连接不同个体的必然是政治生活,政治生活又依托于一定的政治制度才能得以进行,这就必然要求对于国家的认同在国族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具体的制度认同。“近代民族主义之内在要求,其根本特征是国家的主权属于全民,即‘主权在民,政权民授’。在这一前提下,国家为民族独立提供外在的保障,民主权利构成了国家的实质内涵。”(33) 徐嘉著:《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76页。 民主权利又是通过法律来体现和保障的,所以同人对于制度的伦理认同建构是和对于法律的伦理认同建构并驾齐驱的。
从清末开始,中国的先贤学者们对于政治制度的设计就一直处在争论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立宪”与“共和”之间的抉择。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名义上是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但实际上却一波几折,始终没有真正踏上正轨。1928年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前,中国既经历过王朝复辟,也经历过军阀割据。所以《思想与时代》同人希望建构的国家认同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是顺应现代民族国家的潮流,建立一个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则是针对之前的军阀割据以及试图联省自治所造成的地方认同强于国家认同的局面,强调统一的国家认同,建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观。
以张其昀为代表的《思想与时代》同人首先希望建构的是一种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观,而不是地方联省自治的联邦主义的国家观。杜赞奇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以前,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一种是联省自治的联邦主义国家观,另一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观。1920年到1923年中国爆发了联省自治运动,坚持联邦主义国家观的人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全国性的宪法需要在省宪法制定以后才能在省宪法的基础上制定,而省宪法则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制定。这种国家观也不乏有名的学者支持。其中,章太炎就认为中央集权的适用条件只是在国家没有受到外部侵略的时候。欧榘甲的《新广东》和杨守仁的《新湖南》都试图以省为主体来叙述历史,各种以省为名称的杂志也纷纷出现并广泛传播。“在辛亥革命期间,许多省从在清朝独立之后制定了自己的省宪法。”(34)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 与这种联邦主义的国家观不同,处于全面抗战时期的《思想与时代》同人希望建构的是一种在中央集权制的前提下实行中央与地方均权的国家认同。张其昀在《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一文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论述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张其昀认为,建国大业的首要事务就是创造一个稳健强固而又具有高效率的政治制度,而这个政治制度首先是以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完整为前提的。“国家如不统一,即成地方割据之局,其彼此之关系只能称为均势,而不能称为均权。均权为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而均势则为国际之关系。均势乃暂时之政略,均权则为建国之宏规。”(35) 张其昀:《中央与地方之均权制度》,《思想与时代》1941年9月第2期,1-2页。 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要保持中央有充分的权威,同时地方又有自治的空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一种政治平衡。
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思想与时代》同人认为国家政治应达到的理想状态是使人民有自由,使政府有权威,而双方都各有相当之限制。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在启蒙理性的基础之上,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来源于人民的认同。同人对制度伦理认同的建构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价值理念的,主要思想来源则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强调的是伦理的时代性维度。首先,民有的对象是全体中华民国的国民。“民国之民权惟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以破坏民国。”(36) 张其昀:《我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1期,第9页。 其次,同人所希望建立的政权是遵守宪法的民治的政权,他们对于遵守宪法和施行民治两项达成了共识,但是张其昀和陈恩成、陈之迈对当时《五权宪法》的立法权归属却有不同的意见。张其昀认为依《五权宪法》的规定,“立法权为一治权,与行政司法相对立,而超然于国民大会行使政权之外。”(37) 张其昀:《我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1期,第12页。 陈之迈则认为,任何一种法律都必须有相对应的制裁(即今天所说的制定主体)。宪法与一般法律有别,普通法律的制定主体为国家相关机构,宪法的制定主体则必须是人民。“宪法的目的在厘定一条轨道使得政治上各种的势力可以循着这条轨道来竞争运用政权。”(38) 陈之迈:《最近五十年中国政治的回顾》,《思想与时代》1942年8月第13期,第19页。 陈恩成也对五五宪法中的一些内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将《五五宪法》与西方的三权分立相比,五权分立虽然更为精细,但是五权之间缺乏制衡作用。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当时的政治制度既不像英国的内阁制那样内阁由议会产生;也不像美国政党策动国会,而司法享有独立的解释宪法的权力。五五宪法草案规定宪法的制定与解释权不是归于代表人民的国民代表大会,而是属于司法院,司法院是一个官吏机关,并不体现人民意志(39) 陈恩成:《解释宪法之权与能》,《思想与时代》1944年9月第36期。 。最后,对于民治,同人均认为近代化的国家对于其公民也有着相当的要求,应该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以及政治上的训练,因为宪法不等于宪政,只有一部宪法是不足以真正实行民治的,对于现代民治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人民有实行宪政的能力和决心,而不仅仅在于追求制定一部几近完美的宪法。我国民国初年的乱象正是因为当时的人民不具备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能力和意识。
《思想与时代》的发行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所以其作者群对于各类问题的论述都带有非常浓烈的民族主义意味。同人对于中华民族国族伦理认同的建构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对于近代的国家形象的设计却依然非常模糊。虽然《思想与时代》中不乏对于政治和法律的精彩讨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念也非常诱人。但是,由于共和制度是西方舶来的,与我们传统的文化和政治精神相去甚远,再者中国几千年的积习使然,在努力实行宪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表现出了强烈的水土不服症状。此外在当时所处的非常时期之下,国家变得全能化,人民主体的地位实际上被消解了,国家机器反过来主宰着人民的命运,民众对于政治的实际有效参与率也很低。尽管从学术论证和思想深度的角度来看,同人对于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讨论显得质朴、零散、不成体系;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建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所做的努力,是中国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对于国族伦理和政治伦理的论述不乏亮点,是值得学习并借鉴的。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11X(2019)05-0137-09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KYCX17-0203);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学衡派伦理自信研究”(17ZXC0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儒家伦理的情感逻辑”(19BZX115)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都萧雅(1990—),女,汉族,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
(责任编辑 刘 英)
标签:《思想与时代》论文; 学衡派论文; 国家认同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