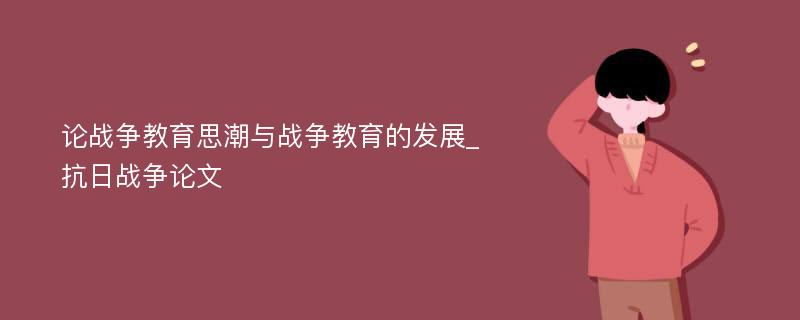
论战时教育思潮与战时教育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战时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奋起反抗,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帷幕。思想、文化、教育界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对国家何去何从的忧虑、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一部分人投笔从戎,一部分人则积极从事抗战文化教育研究,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强劲的战时教育思潮。战时教育思潮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时教育的维持,对抗战建国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
一、战时教育思潮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兴起了席卷全国的“国难教育思潮”,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等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赴国难。救国会同仁拟订了国难教育方案,规定国难教育的目标是:“甲、推进大众文化。乙、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丙、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① 1936年1月23日,国难教育社成立,同仁们拟订了《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国难教育社工作大纲》等,强调国难教育是民族斗争中最重要的工作,决不是少数人能够担负起来的,因为抢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是每一个不愿意做亡国奴或当汉奸的中国人所应有的责任。“宣言”指出:“执行国难教育的工作,最主要的,就在暴露并廓清一切歪曲事实麻醉大众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统一我们的阵营,用同一的步调,向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工作迈进。”②《国难教育社工作大纲》中,还拟订了16项工作要点,其中主要有:开办大众学校、读书会、时事研究会;开办新文字补习班;开办国难教育讲习班;举办军事、防毒救护、运用交通工具等常识技术讲习班;举办国难演讲、旅行演讲;组织巡回电影开映团、演讲团、歌唱团、戏剧团,组织弄堂、马路和乡村等流通图书馆;出版大众社会小丛书、大众自然小丛书;出版大众剧本、诗歌、小说、唱本、连环画等;出版大众国难读本、各级学校国难补充教材等。
上海“一·二八”抗战后,文化教育界彻底认清了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积极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面对日军侵犯上海闸北、江湾等地,炸毁学校238所,损失资产1029万元的暴行,蔡元培、邹鲁、蒋梦麟、王世杰、梅贻琦等国立大学校长联名致电国际联盟,要求“迅速采取有效方法,制止日军此类破坏文化事业及人类进步之残暴行为”。③ 国民党知名人士马君武、罗文干等强烈要求抗战。王造时出版了《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提出“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本拼命到底”的主张。爱国老人、教育家马相伯发表了《国难人民自救建议》的抗日言论。雷沛鸿发表了《民族自救运动下之民众教育析义》等文章,提出“民族斗争下之战争就是民众的教育”,要求带头并教育民众做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恤死”,“念念不忘东北三千万民众”,“努力于恢复东三省”。林砺儒提出了“到了现在,国难竟日深,外侮竟日亟,自然推想到以前的教育还未够防止国难的来临,很应该深刻反省一番”④ 的问题。
文化教育界国难教育运动直接影响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决策。南京政府调整了国防教育政策,1931年10月,教育部令发学生、童子义勇军教育和训练的有关文件,1932年1月29日,颁布了《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训练方案的通令》,1936年,教育部提出了《关于学校教育状况及今后如何改良以适应国防要求案》、《推进学校军事教育办法大纲》、《推进国防教育办法大纲》和《订定的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管理办法》等。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也拟出《军事时期全国学校动员准备概要》等一系列文件。⑤ 足见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文化教育界国难教育运动中提出的意见。
国难教育运动中关于国难教育问题的讨论,不仅是抗战教育思潮的直接源头,也是理论上的先导。实际上,抗战教育思潮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在国难教育运动中已经提出。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直接将国难教育转化为抗战教育。日本的大举进攻使中国人民面临的是自由还是当亡国奴的现实,已经不再是“国难”的问题,必须奋起抗争。文化教育界人士一部分积极参与讨论抗战教育的问题,一部分积极从事实践推进抗战教育的工作。陶行知创办了《战时教育》杂志,专门研究战时教育性质、形式、内容、方法诸问题,发表了大量关于抗战教育的理论文章。1938年5月,独立出版社出版了《战时教育论》一书,集中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抗战教育思想主张;论述了过去教育的缺失,目前教育的危机,提倡战时教育的同时,还要“对教育竭力维护”;政府在军事倥偬之日对教育应“作通盘的详密的计划”;关于抗战教育的特质,作者认为:第一,战时教育与平时教育的连续性和一元性;第二,教育需教学生锻炼体格、培养精神、注重知识、掌握技术、陶冶人格、坚定信仰;第三,抗战、建国同时并举等。
在《战时教育论》出版的同时,生活书店出版了由生活教育社编的《战时教育论集》一书,较集中地反映了文化教育界关于抗战教育的主张。该书分总论、分论、方案和方法、动员和附录五部分。“总论”提出通过教育,动员民众,全面持久地抗战。“分论”提出了改进与实施战时政治教育、农民教育、难民教育、军队教育、伤兵教育、边疆教育以及教育行政、战时教师、学校机构、学校课程改造等具体主张。“方案与方法”对抗战教育方案、战时民众教育、各级学校教育、儿童训练、技术人员训练诸方案,进行了具体设计。“动员”部分号召教育界、记者界、戏剧界、文艺界及全国各界同仁及家庭妇女,有智出智,无智出力,积极参与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
学者顾岳中出版了专著《中国战时教育》,指出:“新时代要求我们,使全国每一部门的工作重行修正步趋,来配合着全民族抗战建国的要求。教育部门自不能不检讨过去,对时需抓住时机,努力迈进。”顾岳中认为,中国所实施的抗战教育,性质和意义主要有八点:1.战时教育较平时更能针对时需;2.以战时教育动员全国军民;3.以战时教育促成更多新的教育机关;4.促进更多特种训练学校;5.促进全国教育合理布局;6.促进普及义务教育;7.促进民众教育发展;8.更能培养建国人才。在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教育虽是被动实施的,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抗战教育思潮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的教育思想主潮。在抗战思潮中,政界要员、文化教育界人士等,提出了丰富的抗战教育主张,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抗战教育思潮,对抗日战争时期教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真知灼见
抗战教育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运,要么中华民族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要么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界要员和文化教育界人士积极研究探索,为使教育能为抗战建国服务提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教育部长陈立夫说:“抗战二十四月以来,教育界人士之所竭智尽忠,贡其心得。而教育行政当局所赴以万分之诚意,谋有以副海内喁喁之望者。”⑥ 这些观点在抗日战争胜利后60年的今天看来,仍然是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真知灼见。
从总的来看,持“平时需作战时看”论者认为,教育要适当改进,不可脱胎换骨,但至少要注意到以下内容:其一,变更原有学科的教学时数,抽出时间教授战时新教材,诸如军事常识、救护常识、防御常识、消防常识、国际关系、群众指挥法等;其二,加设特殊学科,诸如国民训练、民众教育、中国地理险要、日本侵略史、日本外交史、日本政治大纲、军事化学、生物学与国防、军事工程等;其三,改进每门课程本身的内容,小学要注意激发儿童抗战情绪,培养儿童社会知识,灌输儿童战争常识;中学在国文、地理、历史、美术、劳作等课程都要作适当改进。如美术课程,黄觉民在《战时课程的编制》中指出:“战时描写及剪贴、忠勇战士的塑像、防空图、防毒图、救护图,后方工作图,战事经过的连续画等,都可以利用来配合美术的教学。”劳作课可以在以下方面演练:“战时模型、战壕模型、军械模型、障碍物的制造,简易防毒面具及口罩的制造,防毒药水的配制,地窖的建造,绷带的缚法,慰问品的调制,军用水瓶的制造等,都可用来配合的教学。”⑦ 在职业教育方面,“这次战争显然使教育主管当局集中注意力于职业训练的重要性,而这或许是我国现代教育中最弱的一环”。所讲授的科目应包括造纸、制革、染整、养蚕、电讯、汽车工程、畜牧和农业经济、会计、兽医、卫生行政等,“提倡轻工业,并且开发本国资源,以应付战争的需要”。⑧
“平时需作战时看”观点的提出,使教育有较大的改进,未雨绸缪,以防不测是其贡献之一;提高学生的生活能力、身体素质,是其贡献之二;术德兼修,全面发展,人格得到砥砺,是其贡献之三。
许多政府要员、文化教育界人士论及不能无选择性地让大学生去做应急的工作,不能以大学生作为兵员上战场杀敌。韦卓民认为,学校内迁措施是正确的。他说,学校内迁并不是为了校产,上海、苏州、南京和旁的地方,经验告诉我们,当地的妇女和儿童处于敌骑之下是不安全的。敌人对于知识分子和学生是不友善的。国外有人问他说:“何以这些学生不去从军或是参加其他战时工作以保卫国家,反而将他们迁入内地接受教育?难道政府不需要大学教授在战时提供技术的知识吗?”韦卓民解释说:“我们的军械多自国外输入,大学教授不能立刻变为工厂的专家,然而许多教授都参加了战时工作,而且成千成万的学生也参加了陆军和空军。有一件事中国不虞匮乏,那就是人力。政府认为将所有的学生派赴前线,其代价终究是太高了;试想把他们培育到大学程度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而且全国的人口中,大学生仅占万分之一。他们若都在战场上被屠杀,那么战后国家的精神生活中势将出现严重的缺口。……我们当前的口号是‘抗战建国’,假使我们的抗战忽略了复兴,那不啻自毁立场。”⑨ 这当是抗战教育目光深邃之至论。
此外,还有影响颇大的“教育须彻底改革”等主张,强调教育要全方位地去适应战争环境,为战争服务,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战时教育思潮中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抗战教育思想。这些思想主张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既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又有理智的思考;既有强烈的爱国感情,又有冷静的睿智,堪称是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真知灼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三、战时教育思潮呵护下教育的发展
思想是实践的前导,理论引领着教育的发展。波涛澎湃的战时教育思潮,对抗战时期教育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抗战教育思潮的呵护下,抗战大后方的教育始终是在十分理智的发展。大后方8年抗战期间的教育,并没有因战争的进展而大起大落,或者是中断,相反,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还取得了奇迹般的发展。
从高等教育方面来看,在战时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大学生没有被驱赶上战场,没有直接上前线与敌浴血奋斗。而他们绝对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不是不管国家前途命运的亡国奴,他们通过努力学习报答国家。在战时教育思想的引领下,全国公立、私立高等学校大多迁移到大后方继续办学。浙江大学迁徙达数省,行程达两万余里,所经之地堪称文化的荒漠,一支文军沿途播撒文化种子,走一路,实现一路的科技开发,造福于民,造福于当地。然而,浙江大学也得到了不小的社会回报——由一所影响仅及一二省的普通大学,发展成为影响达到整个南方,乃至大半个中国的知名大学;由3个学院发展到近10个学院、数十个系所,享有“东方剑桥”之美誉。
贡献与回报是对等的,正如韦卓民所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入内地并不是一种灾难。他们是迁移到了文化落后的地区。知识和技术意念的普及帮助了内地的迅速现代化。由于这些外地高等学府的迁入,促使落后地区的学校在教学水平上和效率上都获得改进。大专院校的师生大都是在沿海大城市中长大的,有机会和本国落后地区的生活接触,使他们能于亲身体会的经验中学习到重视祖国所面临的问题。许多教授由于环境所迫,要去应付新的问题,而这些答案绝非仅为西洋人使用的课本中所能觅得,更非彼等携归的欧美各大学课堂中所讲所做的笔记。简单而欠精确的设备也非全然无益,基于此理,教学也许更有兴趣而且更有实效。”⑩所以,在抗战期间的高等教育,无论是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得到了较大发展。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共108所,教师7560人,在校学生总数为41922人。(11) 而到战后的1947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共129所,增加了21所;在校学生总数为135738人,是战前的3倍多。教师人数和质量也都有明显的增长和提高。
在中等教育方面,在战时教育思潮的影响之下,全国中等教育并未因为大片江山沦入敌手就停辍,也未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将中等学校的学生统统作为兵员开赴战场,而是理智地处理好抗战与建国的关系,妥善地安置好沦陷区逃到后方的中学生,为他们继续完成学业提供保障。为了保证他们有学上,有书读,教育部破例地在后方办起了一批国立中学,如国立四川中学、贵州中学、山东中学等。中学生逃难到后方,与家庭失去了联系,在经济上无法得到家庭的支持,国民政府为使他们学业不致中断,推出了贷金制,而且学生的衣食住完全免费,或部分免费。陈诚在湖北实施计划教育,凡湖北籍学生,无论在湖北本省读书还是在外省读书,均给予一定的补助,毕业后回湖北建设新湖北,建设新中国。这直接使得许多中学生艰苦努力地学习,以报答国家对自己的关怀爱护。很多在抗战中接受中学教育的学生回忆,其时的中学教育并未因战时环境而降低教学水准,恰恰相反,教学水准还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抗战八年期间,全国中等教育能够紧张有序地进行,与战时教育思想的指导,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抗日战争期间,我国的中等教育同高等教育一样,并不是大面积滑坡,而是有较大的发展。据统计,抗日战争前中等学校校数最高年1936年,有中等学校1956所,班级共11393个,学生总人数为482522人。(12) 1937、1938年的抗战初期,中等教育各方面的数据有所下降,但是在战时教育思想的影响之下,很多战时教育的理论付诸实施,中等教育各方面的数据有明显的回升,到1941年反超1936年的水平。此后逐年递增,仅就学校数而言,1941年2060所,1942年2373所,1943年2573所,1944年2759所,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等学校校数飙升到3727所。在校学生数也逐年攀升,到1945年在校学生总人数达1262199人。(13) 战时教育对中等教育发展的引领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再从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方面来看,亦按照1937年8月27日制颁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仍应“战时要当平时看”,“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并“尽可能范围内,设法扩充容量,收容战区学生”。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随着战区日益扩大,沿江沿海各省区教育比较发达者,均遭日军蹂躏,小学校多在敌人到达之前数小时,教员携其教具避难偏僻乡村。这种播迁流徙之情形,使得小学教育损毁过半。但是,仍然坚持“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14) 为了使小学教育得以维持,国民政府实行新县制,同时将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合流,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实施“管教卫合一”、“政教合一”和“三位一体”的新县制教育制度,将乡镇一级的乡镇长、中心小学校长、壮丁队长定为一人担任,将保一级的保长、国民学校校长、壮丁队长定为一人担任,同时,小学教师分掌乡镇保的经济、文化、卫生、警卫等项建设事业,以小学为中心实行“自治”。采取这些办法,对小学教育得以维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这些办法评价不一,褒贬不一,但是抗战期间小学教育不但得到了维持、稳定,还小有发展。据统计,抗战前小学教育各方面的数据最高年为1936年,小学校达320080所,在校小学生人数18364956人。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的前几年,小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均锐减,1937年小学学校数减至229911所,学生人数减至12847924人;1938年218758所,小学生12281837人;1939年218758所,小学生12669976人。1940年后,国民教育制度开始实施,并很快收到效果。反映在小学校数上和在校学生数上,是数据全面回升。1941年224707所,小学生15058051人;1942年258283所,小学生17721103人。小学校数比1936年稍少,但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已经接近1936年的水平。1943年273443所,小学生18602239人。小学校稍稍不及,但人数已经跃升到1936年以上。1945年269937所,小学生21831898人;1946年290617所,小学生23813705人。(15)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国民教育制度推动了初等教育发展。尽管对这些数据的准确性有不少怀疑,但退一步讲,它稳住了小学教育的情况,不致使继续损毁,便已经功不可没了,何况还小有发展呢!
学前教育遵循着抗日战争时期学前教育方针:“幼稚教育,应使保育与教导并重,增进幼儿身心之健康,使其健全发育,并培养其人生基本的良好习惯。施教对象应推广及于贫苦儿童。”以后,教育部奉行“战时需作平时看”原则,于1939年12月24日公布了我国学前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法规—一《幼稚园规程》;1943年教育部对“规程”予以修正,经呈奉行政院令,改为《幼稚园设置办法》,并于同年12月20日以教育部令公布施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产生大量难民。而难民中有很多孤苦无着的儿童。为解决难童的收容、教养问题,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和保育院应运而生。1938年3月10日,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等为常务理事,在全国各省市、香港和南洋群岛设分会20多个;在各战区设立儿童保育院53所,总共收容难童3万多名。由于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抗战期间的学前教育得以维持。1936年,全国共有幼稚园1283所,共有1988班,在园儿童79827人。抗战爆发后,开始受影响较大,1937年仅有839所,1180班,46299名儿童。到1942年,幼稚园数达592所,1398班,51740名儿童。但到1945年,幼稚园数迅速攀升到1028所,2889班,在园儿童达106248名。幼稚园数虽然稍低于1936年,但班级和在园儿童数则远远超过1936年的数据。(16)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正义、理智、聪明、睿智的中国人民,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不利因素有为利因素,变坏事为好事,使中国人民对教育进行深入反省,从而使教育得以改进,使得教育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时能够维持并有较大发展。之所以有这些不菲的成绩,应归功于战时教育思想理论的正确引领。
注释:
① 《大众国难教育方案》,见《生活教育》第2卷第22期。
② 《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见《生活教育》第3卷第2期。
③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④ 林砺儒:《中国教育与国难》,见北京师范大学编:《林砺儒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42页。
⑤ 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21285页。
⑥ 陈立夫:《抗战二年来之教育》,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战时教育方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第38页。
⑦ 参见李定开:《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9—17页。
⑧ 韦卓民:《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见台湾《湖北文献》第54期。
⑨ 韦卓民:《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见台湾《湖北文献》第54期。
⑩ 韦卓民:《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见台湾《湖北文献》第54期。
(11)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296页。
(12)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31页。
(13)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第634页。
(14)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二章“抗战时期教育”。
(15)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二章“抗战时期教育”,第1455页。
(16) 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编:《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