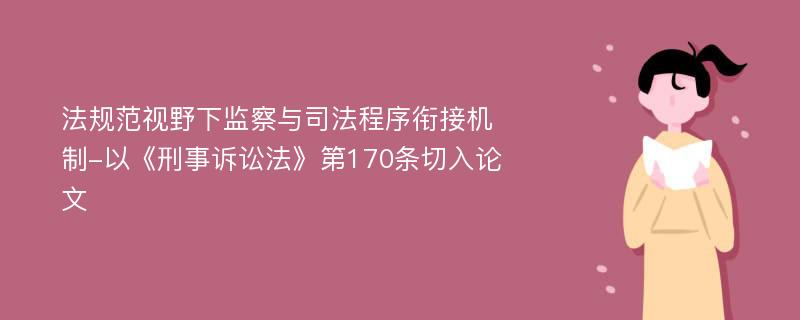
法规范视野下监察与司法程序衔接机制
——以《刑事诉讼法》第170条切入
董 坤
摘 要: 《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了监察与司法的部分衔接程序。其中,立案程序的缺失导致强制措施的启动缺乏正当性,不利于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诉讼程序运转的自洽。未来的司法解释中应确立“形式立案”,即以受案代替立案,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不再进行立案前的实质审查,但须明确受案具有开启刑事诉讼程序的功能。在留置与强制措施的衔接上,立法采用了“留置+先行拘留+强制措施”的模式,其中先行拘留具有过渡性,逮捕、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才是对接留置的最终措施。但立法上对于留置转先行拘留后最终可否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缺乏周延规定。依据案件系属理论,对于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的情形,系属关系并未消灭,案件仍系属于检察院,处于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嫌疑人应当继续沿用之前的强制措施,并继续保障辩护人的相关诉讼权利。
关键词: 监察 刑事立案 留置 强制措施 案件系属
从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来,法学界就开始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给予了重点关注。一些法学专家从监察立法、监察权属性以及改革逻辑等多个视角展开研究,促推改革前行。2018 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在宪法和法律层面得以确立。为了落实宪法的有关规定,配合监察法的出台,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专门对涉及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条文作出增删修改。
如果以2018年10月刑事诉讼法修改为时间节点,可以发现,修法前对监察与司法程序衔接问题的研究多以总结地方试点经验,创设衔接机制和协调模式为主线。这些机制模式的理论构想大多是在监察法未出台,刑事诉讼法未修改的背景下尝试的试点预案。随着立法条文的修改,这些预案除了作为今后再修法的参考外,大多已不具实践可能性。为此,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有必要及时转向,即从法规范的视角出发,调研,掌握相关条文在实践中的施行状况和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和突破口,通过现象描述和问题破解,诠释条文背后的法理逻辑,助推“纸面上的法”向“行动中的法”的转换。鉴于此,本文将以《刑事诉讼法》第170条为分析文本,结合实践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就人民检察院对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的审查起诉程序、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的衔接机制等展开研究,诠释制度机制设计的初衷和应有功能,破解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细化相关制度机制,为实践操作和下一步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一、监察案件的移送与受理
(一)程序衔接中立案程序的缺失
早在监察法出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就有学者对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是否还要先行立案进行过讨论。(1) 龙宗智:《监察与司法协调衔接的法规范分析》,《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 对此,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监察法》第45条第1款第4项规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与此衔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依照本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从上述规定看,无论是监察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未在具体条文中就监察机关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作出“检察院立案后依法审查”的表述。这似乎表明监察与检察在程序衔接上不必再经刑事立案程序。由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法规室编写的权威读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证实了上述理解,按照其对《监察法》第45条第1款第4项的解读,“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应由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直接依法审查、提起公诉,……不需要检察机关再进行立案。”(2)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法规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207页。
我国传统刑事诉讼承继前苏联诉讼阶段论的理念,刑事案件从其开端的时候起直到判决的执行为止是向前运动的,是逐渐发展的。(3) [苏]切里佐夫:《苏维埃刑事诉讼》,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56页。 这个过程中循序进行、相互连接而又各自相对独立的各个部分,称为“刑事诉讼阶段”。(4) 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与实现途径》,《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阶段,是刑事案件诉讼发动的起点和必经阶段。但是,诚如前文分析,本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监察与司法程序衔接的过程中,并未以刑事立案作为两套程序衔接的节点或标志,这显然是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一大突破。究其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公诉案件的立案标准是,“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的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反观《监察法》第45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监察机关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时,对案件的认定标准已然达到了“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这一标准远远高出刑事立案所要求的事实和证据门槛,在这种标准差异显著的情形下,检察机关再行立案已属多余。毕竟,传统的刑事立案具有过滤不合格案件,程序分流的功能,但对于监察机关如此高的案件移送标准,再进行立案前的审查不仅掣肘了程序衔接的效率;而且也不能实际发挥立案对案件过滤分流的功能。在这一认识下,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参照了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作法,对起诉的案件办理受案手续,立法上不再明确立案阶段。对此认识和做法笔者认为仍有可斟酌之处。
(二)程序衔接中立案的多重功能
比较监察案件移送和刑事诉讼立案,办案标准的差异化分析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两法衔接中立案程序缺失的部分质疑,但仍有不足之处。考虑到刑事立案远不仅仅是过滤案件、程序分流这一重功能,直接摒弃立案程序,可能导致立案的其他功能也被一并去除,由此引发监察与司法程序衔接中一些实践性问题的出现。
笔者认为,从我国刑事立案的多重功能出发,在监察与司法程序衔接中还是应当考虑给予立案一席之地。但鉴于监察机关移送案件和刑事立案两者标准存在高低降序的差异,继续以立案为门槛对监察案件做实质性审查确有程序上的重复建设之嫌,同时为了避免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产生“硬冲突”,笔者认为立法上规定立案已无必要,但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应增设审查起诉阶段的案件受理程序,构建“形式立案”。之所以要构建“形式立案”,一方面能够明确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不再做实质性的过滤审查,仅是对移送的案卷材料是否齐备做形式审查。另一方面,确保案件受理程序能够承担立案的部分功能,特别是明确受案具有开启刑事诉讼起点的性质。进一步的理由如下:
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嗜好烟酒,有嚼烟草或槟榔的习惯。饮酒和吸烟会增加患口腔癌和口咽癌的风险。研究表明,大约30%的口腔和口咽部肿瘤是由饮酒引起的。在英国,60%以上的口腔癌和口咽癌是由吸烟引起的。习惯于嚼烟草或槟榔的人群,由于在咀嚼过程中,烟草或槟榔会造成口腔内黏膜的损伤,长期的咀嚼是可以导致癌症发生的。
首先,立案具有限制强制措施或强制侦查手段随意发动的功能。与国外相比,虽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刑事诉讼都没有设立专门的立案程序,但这些国家如果采取强制措施,实施强制侦查手段,则必须在具备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司法审查获得令状后方能展开。反观我国,长久以来,刑事诉讼中流水线式的诉讼结构使侦查异化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质中心。除了逮捕由检察院审查批准以外,大部分强制措施或手段的发动都缺乏司法审查的程序控制。无论是对人身自由具有剥夺或限制功能的拘留、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物具有强制处分效果的搜查、扣押,还是对隐私权具有干预性质的监听、强制采样等都由侦查等办案机关内部管控,缺乏外部的监督和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了有利于对犯罪的打击, 没有采用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和令状主义, 而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尤其是强制侦查权限, 仅以立案程序作约束,”(5) 龙宗智:《取证主体合法性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通过前置化的立案程序过滤案件,提高刑事案件的准入门槛,抑制侦查追诉的随意发动。换言之,我国的刑事立案实质上已成为办案部门采用强制侦查手段、启动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反之,立案前的初查则不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或措施。然而,由于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监察与司法程序衔接中缺乏了立案节点的标识,一些强制措施的认定和控制就存在一定的困难。比较典型的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款规定,对于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此处先行拘留的性质如何认定,实践中就产生了分歧。有同志认为此处的先行拘留就是《刑事诉讼法》在强制措施一章中第82条所规定的符合法定情形下的先行拘留。但也有同志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先行拘留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的先行拘留的七种情形。而且,这七种情形只有公安机关才可以决定和执行,检察机关并非都有权实施。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款还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期间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且该期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比照刑事诉讼立案前的“紧急措施”,似乎宜将此处的先行拘留剥离出审查起诉阶段,也视为诉讼外、诉讼前的一种“紧急措施”。姑且不论上述观点的是非对错,但类似问题的出现至少暴露出在两法衔接中由于立案的缺失已经给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惑,乃至操作“乱象”。
其次,立案程序是开启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序幕。就我国而言,刑事立案不仅意味着刑事诉讼的开始,也意味着犯罪事实或追诉对象的初步确定。一旦立案时能够明确追诉对象,那么作为追诉对象的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随之确立,相关的诉讼权利也由此产生。具言之,无论是学理上所划分出的防御性权利,如申请回避权、辩护权、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有权拒绝回答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等;还是救济性权利,如复议权、控告权、申诉权、申请变更、解除强制措施权等,这些权利都是随着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确立而获得,而立案恰恰是犯罪嫌疑人身份确立的起点。反之,如果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缺乏明确的立案程序,犯罪嫌疑人身份确立的起点便可能产生分歧,基本的诉讼权利也可能面临保障不足或保障不及时的情形。仍以前文中谈及的《刑事诉讼法》第170条为例,由于两法衔接中缺乏立案这一标志性程序,加之监察调查取代了职务犯罪案件的刑事侦查,监察委办理的案件直接移送检察机关时,如果监察被调查人此前被留置,那么当案件移送后辩护律师何时介入在实践中就产生过争议。少数地方的检察院就提出需要留置转逮捕后,才可通知看守所解禁律师会见,允许律师阅卷。换言之,少部分同志认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既然留置案件移送到检察院需要先行拘留,而先行拘留期间决定采取何种强制措施的10天或14天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那么该段时间可视为游离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外的一个独立阶段,案件并未真正进入刑事诉讼,故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以及由此衍生的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等权利自然无从谈起。对于该观点,可驳斥的理由很多。但如果在修法时明确监察机关移送检察院的案件需要先行立案,便可据此作出有力回应:立案即意味着刑事诉讼的开启,刑事诉讼中不可能出现游离于审查起诉之外的“独立阶段”,上述的“个人解读”显然违背了我国刑事诉讼阶段论的基本格局,难言自洽。因此,先行拘留期间犯罪嫌疑人以及辩护律师的相关诉讼权利都应及时全面地予以保障。
再次,立案具有确立诉讼客体,推进诉讼进程的意义。“刑事立案程序所立之案件乃侦查与审查起诉的对象,没有案件侦查与审查起诉的基础便不存在了。”(6) 陈卫东:《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若干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案具有确立刑事诉讼客体——案件的独立功能。而且,一旦在立案阶段,先前的事件确立为案件,便会被纳入诉讼轨道,推动刑事诉讼进程不断前行。案件有立就有终,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从立案开始,当案件进入到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便会对公安司法机关产生约束作用,办案人员都应当履行相应的诉讼职责,或积极推动案件迈向下一个诉讼阶段,或作出相应的实体或程序处理,终结所立之案。例如,立案后案件进入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于案件的办理推诿拖沓,久侦不决,以罚代刑就会受到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再如,案件系属到法院,法官也决不能不为裁决,搁置不理,弃之不顾。可见,立案具有形成案件,推动案件不断在诉讼中前进,并最终走向结案的源动力效果。然而,由于两法衔接中立案的缺失,不仅导致刑事案件何时形成存在争议,而且还使刑事诉讼程序有尾无头,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法院作出生效裁判而终结案件的正当性因缺乏案件在起初“立”的明确呼应而存在争议。也恰恰是因为在监察与司法程序衔接中刑事案件没有明确的节点环节,实践中曾出现,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认为案件需要补充核实退回监察机关,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期间发现原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变化,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接利用自身权限做出政纪处理或监察撤案决定,未再移送回检察机关,导致刑事诉讼中的案件有始无终、始终处于未定状态,被搁置下来。之所以有如此操作,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有始才有终,既然监察与司法程序衔接中根本没有刑事立案,案件退回监察机关自行消化,刑事程序上自然也不必以结案的形式再予回应。应当说,正是在监察与刑事诉讼两法衔接中立案的缺位,才导致了监察案件可以自由进出刑事诉讼程序,来回穿梭于监察与司法程序之间。
(三)形式立案的确立:案件受理
南亚2017年的核电装机容量为8.5 GWe。该地区核电容量在2030年、2040年和2050年的高值情景预测值分别为34 GWe、60 GWe和98 GWe,低值情景预测值分别为22 GWe、31 GWe和50 GWe。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该条款规定了监察与司法在程序交替中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的衔接模式:留置+先行拘留+强制措施。其中,先行拘留是留置与强制措施之间的过渡性措施,具有剥夺人身自由临时性、强制性的特点,而逮捕、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才是对接留置措施的最终替代性措施。对于该条款有如下问题需进一步深入分析。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成年人在“打回去”之前,会下意识地合理判断自己打回去的后果是什么,如果发现打回去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就会控制住自己这种冲动,转向其他的解决方式。
其次,构建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的受理程序,确立诉讼起点,开启诉讼程序在国外早有先例。从世界其他国家来看,立案并不是刑事诉讼发动的起点和必经阶段,履行一定的程序,如案件受理,也意味着诉讼程序的开始,有学者将其称为刑事诉讼的“追诉启动模式”(8) 姚莉:《监察案件的立案转化与“法法衔接”》,《法商研究》2019年第1期。 。例如在意大利,警察和公诉人获取犯罪消息后即可开展初步侦查,同时《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335条还规定了“犯罪信息的登记”程序:公诉人对一切向他提出的报案、报告或其主动获取的犯罪消息应当立即在保存在其办公室中的专门登记簿上记载。(9)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其实,该条中的接受犯罪信息并履行登记程序其实就是笔者所谈及的案件受理程序。与此类似,德国的审前程序没有正式的起点。在大多数案件中,侦查的启动及其理由记录在警察局的日志或案卷中。(10) [德] 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90页。 在日本、法国等国家规定的侦查之前进行的报告、批准或登记手续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诉讼程序,但确是启动刑事诉讼的重要方式。(11)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5页。 随着监察委的成立,我国出现了针对职务犯罪案件由监察调查和和司法机关起诉、审判两个不同程序衔接递进的办案模式,传统刑事诉讼中的立案程序开始淡化,但借鉴国外的“追诉启动模式”,在未来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中设置审查起诉阶段必要的案件受理程序,以“形式立案”划定监察与司法的程序界限,明确刑事诉讼开启节点仍有现实必要。
二、留置与强制措施的衔接
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本身就规定案件受理也是立案的一种形式。《刑事诉讼法》第114条就规定,“对于自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该条虽然没有使用“立案”一词,但人们通常认为法院对自诉的“受理”也属于立案,直截了当的依据是这一活动被规定在“立案”一章中。(7) 张建伟:《刑事诉讼法通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5页。 而且,根据《高法解释》第263条第1款的规定,“对自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十五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决定立案,并书面通知自诉人或者代为告诉人。”可见,如果自诉案件符合受理条件就应当决定立案。显然,司法解释也认为此处的“受理”和“立案”可以等约替换。笔者注意到《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中就规定了案件受理的条件和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认为具备受理条件的,应当及时进行登记,并立即将案卷材料移送公诉部门办理;认为不具备受理条件的,应当商国家监察委员会相关部门补送材料。”如果按照作者对两法衔接中“立案”程序的设计思路,将该规定中的受理案件做“形式立案”解释,既不会触发检察机关对移送的监察案件再行立案审查的操作,同时还能明确此处的案件受理具有开启刑事诉讼程序,担当刑事诉讼起点的效果。这对于限制和正当化刑事强制措施,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理顺和推进诉讼流程具有现实意义。
(一)留置与强制措施衔接模式的创设背景
检察院审查起诉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认为需要补充调查核实的,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的程序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较为关注的问题。关注的焦点在于如果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捕羁押,那么退回补充调查期间,对被调查对象如果还要剥夺人身自由,是继续适用刑事诉讼中的羁押,还是要采取监察留置。对此问题,可谓观点各异、莫衷一是。其实,该问题争议的本质还是检察院将案件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的这段期间,案件究竟是倒流回监察调查环节,还是处于审查起诉阶段,仍然由检察院管控。如果是前者,那么自然应当采取留置措施,如果是后者则应继续沿用之前的强制措施,继续羁押。为了澄清这一问题,笔者先以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为例,分析退补期间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论出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时,案件所处的应然程序。
1.提前介入模式。该模式为,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调查终结决定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应当在留置期限届满10日前通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检察机关利用这10日进行“初查”,并在留置措施届满前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
2.事前审批模式。该模式为,对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在移送审查起诉前,先向检察机关申请采取强制措施,例如,提请逮捕,在检察机关批准采取强制措施后,再移送审查起诉。
3.先行拘留模式。该模式为,对监察机关移送的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在受案后经对《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进行审查,于受案的当日或次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先行拘留措施,然后在此期间决定是否采取逮捕或其它强制措施。
杨澜在访谈中提起了这段经历,她小心翼翼地问巩俐,经历了那样悲痛的事情,回来后又要立刻拍戏,会不会有种被撕裂的感觉。巩俐很坚定地说:“你拍完戏以后,回家想怎么去祭奠去哭,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在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你的时候,不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带给别人。”
综合评判三种衔接模式。提前介入模式的缺陷是程序交叉,权责混淆。监察留置与强制措施是监察与司法两套不同程序中的具体行为。首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在监察机关的留置场所讯问犯罪嫌疑人导致了监察与司法两套程序的交叠,使提前介入行为的性质处于监察与司法的模糊地带。另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10日是用来审查决定强制措施的,但又处于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监察程序环节,无形中挤占了监察机关正常的办案时间。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事前审批模式中,虽然该模式比照公安向检察院的报捕流程创设了一套类似的新程序,但因为对于逮捕的报请和批准本身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内容,却同时被包裹在监察留置期间,导致报捕和批捕行为有司法越界之嫌,其行为性质依旧混淆不明,还同时压缩了监察调查的时间。基于前两种模式无法调和的矛盾,立法者最终采纳了先行拘留的衔接模式,该模式既能保证两套程序的无缝对接,避免程序交叠,同时也不会导致某些行为在性质属性上的模糊混淆。而且,《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款中“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的专门规定也保障了检察机关有较为充分的时间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适当的强制措施,避免占用审查起诉期限。
当然,先行拘留模式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立法设置先行拘留的目的是将犯罪嫌疑人从监察调查程序转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本身在诉讼程序中的体系定位及性质为何?先行拘留期间决定采用强制措施的标准是什么?选择适用的范围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二)衔接过程中有关强制措施的两个问题
1.先行拘留的体系定位和性质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国家不再全额供养地方科研院所,大量单位转制为国有科技型企业,这就不可避免的要直面市场竞争。难以融资、体制机制僵化、人才队伍更迭严重等问题更是加剧了地方科研院所的困难。具体到改革过程中,需要进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单位正面临着理事会对单位的实际把控问题。行业性质的研究单位随着产业转移和更新转型压力更大,有一定规模的科研单位因二级法人单位业务、财务独立而难以有效集聚资源,完全按照政府部门的模式管理又导致科研单位体制机制僵化,致使盈收无法合法分配,这些问题有的是现实发展所致,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
先行拘留不是审查起诉之外的“独立阶段”“特别程序”,而是审查起诉阶段内的一个特殊环节。诚如上文所言,如果能够建立审查起诉阶段的案件受理程序,即通过“形式立案”明确刑事诉讼的起点,对于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一旦受理,案件即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作为对先前留置的犯罪嫌疑人的过渡性处置措施——先行拘留无疑是内含于审查起诉阶段的具体诉讼行为。支撑该观点的其他理由还有:其一,《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款规定的先行拘留处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三章“提起公诉”内,从其在刑事诉讼法中所处的编章位置,按照体系解释的方法可以推断,先行拘留显然可视为刑事诉讼内提起公诉阶段中某一环节下的处置措施或诉讼行为。其二,不能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先行拘留期间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就认为先行拘留是游离于审查起诉之外的“独立阶段”。一般而言,期间的不计入往往是因为有些诉讼行为本身带有不确定性,耗时长短不一,一概计入办案期间可能会挤占有限的办案资源,不利于办案的质量和效果。如果因为期间的不计入而否认某一诉讼行为内含于某个诉讼阶段显然属于对条文的误读。毕竟,不计入办案期限和不属于某一办案环节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49条还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但不能据此否认鉴定本身属于侦查行为的一种,需要遵循法定程序,并接受侦查监督。
明确了先行拘留内含于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的体系定位后,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先行拘留与《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一章中第82条和侦查一章中第115条规定的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的先行拘留是否同一。笔者认为,两者性质并不相同。首先,从适用对象上看,《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先行拘留仅仅针对先前被采取留置措施,后被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涉嫌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第82条和第115条的先行拘留则针对的是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涉嫌犯罪的案件范围并无任何限制;其次,从适用条件上看,《刑事诉讼法》第170条先行拘留所针对的犯罪嫌疑人在监察调查阶段被采取了留置措施的情形,《刑事诉讼法》第82条和第115条的先行拘留则是针对七种法定情形;再次,从先行拘留的适用阶段上看,《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的先行拘留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刑事诉讼法》第82条和第115条的先行拘留则适用于侦查阶段;最后,从先行拘留的决定主体上看,《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的先行拘留其决定主体是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第82条和第115条的先行拘留的决定主体可能是检察机关,更多情形则是公安机关。综上,笔者认为本次修法新增的《刑事诉讼法》的170条第2款其实创设了一种“先行拘留”的类型,其仍然属于强制措施中的拘留,但自身有独立的适用对象、条件、阶段和决定主体,本质上是对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对象在被转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所采取的一种临时、过渡性质的强制措施,(12) 李寿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402页。 不能将其与《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的先行拘留相混淆。
除此以外,《刑事诉讼法》第71条和77条也都规定了对于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两个条文之所以设置先行拘留主要是因为,实践中,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其遵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来看,两类强制措施已经不能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只能采取更为严厉的强制措施。但逮捕要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需要一定的时间,故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加了对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先行拘留的规定。(13) 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从当时立法的目的来看,两条文中的先行拘留就是先于逮捕而拘留,或者说是为办理逮捕手续,而在紧急情况下先行拘留。但就《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来看,其实质上是创设了一种新型的先行拘留,这里的“先行”是先于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而做的拘留,是对留置转强制措施的过渡,最终并非必然转向逮捕,还有其它强制措施的选择。至于如何适用强制措施,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选择标准和适用依据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款只设计了留置最终“转何种”强制措施的情形,并未有留置最终“是否”要转强制措施的规定。换言之,对于留置的被调查人转入刑事诉讼经先行拘留后可否最终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呢?至少从条文文义上看目前只有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三决一的选择,并无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可能。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似有失偏颇。因为,刑事强制措施的基本功能包括程序保障和社会防卫两大方面。与程序保障相对应的,主要是防止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防止妨碍查明案情,以及防止自杀、逃跑及发生其他意外事件;与社会防卫相对应的,主要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犯罪。如果根据案情,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进行任何干预,也能确保上述两大基本功能的实现,办案人员完全可以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这在监察留置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转换中是同样适用的。有同志曾提出可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款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这一条文表述作如下理解:对先行拘留后能否采用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都做“是否”判断,如果三种强制措施都做了否定性的决定,那么最终就可以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该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对由留置转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找寻正当化的法律依据。但笔者认为这一解释较为勉强,因为紧接上述被解释的条文后还有一句“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该规定明确指出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而不是“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可见,立法似乎是有意采取一种将留置对象最终转为某一强制措施的思路。虽然,实践中根据案情全然不用任何强制措施的情形极少,即使出现也基本以取保候审代替,但从立法的严肃性和实践的复杂性来看,未来还是应在相关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明确,对先前留置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不进行任何基本权干预,最终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这样不仅便于办案部门的人员适时把握、准确操作,也是对犯罪嫌疑人基本的人身自由权的最大保障。
从《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来看,先行拘留后决定采取的强制措施有三种: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从三种强制措施在立法条文上的排序看,逮捕处于首位,是先行拘留期间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第一选择。(14) 这恰如《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处刑刑罚的排序一样,故意杀人的首先考虑处死刑。 之所以如此设置,主要是因为关于留置措施的适用条件。《监察法》第22条规定,“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一)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二)可能逃跑、自杀的;(三)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四)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从该规定可以看出,监察机关已经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要么是重大、复杂的案件,要么是与逮捕的羁押必要性条件相当(15) 如《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1款第(三)项和第(五)项也规定了“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以及“企图自杀或者逃跑” 的情形,与监察期间采取留置的适用条件相当。 的案件。因此,检察机关先行拘留后,针对先前被调查人留置的适用条件和情形,较为匹配的强制措施自然是首选逮捕。实践中,对于监察期间一直被留置的被调查人当转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检察机关也大多予以逮捕。但不容否认的是,如果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或者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或是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逮捕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也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款的规定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措施。
2.先行拘留期间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标准
三、退回补充调查的阶段定位
早在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期间,为做好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案件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的衔接,对监察机关已经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检察机关如何在程序转换过程中处理好强制措施的衔接,不少试点地区总结地方经验创设出若干衔接模式,主要可归为三种:
早在元代,文人即围绕北曲审美体系,建构了对元曲成就进行自我推尊的论说集群。如当时的胡祇遹认为,“乐音与政通,而使剧亦随时所尚”,北杂剧所涉,“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5](P6);夏伯和也指出《伊尹扶汤》《剪发待宾》等大量杂剧“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6](P7)。他们通过揭示杂剧丰富的现实内涵,来提升其文化层级——在娱戏性质之外,杂剧肩负呈现政治得失、人伦风化的劝谕功能,标举杂剧乃至整个曲体文学具有关乎政治风教的雅文学属性。
(一)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期间案件的诉讼状态
从既往的司法实践看,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侦查终结,认为案件需要提起公诉的,均是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79条的规定,“对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制作起诉意见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连同全部案卷材料、证据,以及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院受理后即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期间如果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高检规则》)第380条的规定,检察院应当提出书面的具体意见,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检察院退回的材料主要是案卷材料、补充侦查决定书、补充侦查提纲和换押证(未被羁押的除外),没有起诉意见书(16) 实践中,大多数起诉意见书都与案卷材料分开单独移送,但也有将起诉意见书装订到公安案卷中一并移送的情形。如果审查起诉阶段退回公安补充侦查的,单独移送的起诉意见书都不再退回公安机关,但装订到公安案卷中的起诉意见书有时会因为不便拆分一并退回公安机关,但一定会有其他备份的起诉意见书在检察院留档备存。 。究其原因,当公安机关向检察院提出起诉意见,移送完起诉意见书后,案件即系属(17) 诉讼系属理论是指案件“系属”于法院,使受诉法院获得具体的案件管辖权并发动审判程序。诉讼系属理论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起诉效力问题,即原告或检察院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于诉讼系属后再行起诉;其二是贯彻追诉原则,实行有控诉或告诉才有审判,有控诉必为裁判的诉讼程序,即不告不理、告即应理。本文套用这一表述,仿照传统诉讼系属理论来阐释案件进入检察院审查起诉环节,补充侦查或补充调查期间,案件实质所处的诉讼阶段以及最终的处理方式。有关诉讼系属理论可参见,龙宗智:《论我国的公诉制度》,《人民检察》2010年第19期;谢佑平、万毅:《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重述》,《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5页。 于检察院,检察院只有作出起诉、不起诉的决定,或者允许公安机关将案件从审查起诉阶段撤回,上述系属关系才消灭。这就如同检察院向法院移送起诉书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后案件即系属到法院,只有检察院撤诉或者法院为之裁判才能消灭系属关系一样。
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分析会发现,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既不是检察院的起诉、不起诉决定,也不意味着公安机关从检察院撤回案件,虽然表面上看案卷材料等都退回了公安机关,但案件与检察院的系属关系实质上并未消灭,检察院只是要求公安机关为案件的起诉作“补充”,而且还有两次退补且每次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限要求,所以检察院并没有丧失对案件的处理决定权,起诉意见书自然无需退回。因此说,退回补充侦查期间,案件仍然系属在检察院,案件的最终决定权仍然需要在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院作出。
通过研究矿石以及主变围岩的相关特征,根据石英脉体的穿插关系以及矿石组成和矿物生成顺序等等,进一步对成矿过程加以分析。从而总结了矿场地质的相关特征以及控矿因素并得出相关找矿标志,以此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地质根据。
对上述观点能够加以佐证的是:如果认为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期间,案件又重新回流到侦查阶段,在此期间,公安机关发现原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变化,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完全可以直接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根据笔者的调研,实践中如果出现类似情况,公安机关会主动向检察院提出撤回审查起诉的函(盖公安局印),检察院在收到函后如果同意,会出具同意撤回案件的法律文书,并送达公安机关。对于从检察院撤回的案件,公安机关才能自行撤销刑事立案,并将处理结果通知检察院。(18) 对于从检察院撤回的案件,公安机关也可以继续侦查。因为检察院所作的同意撤回移送审查起诉的文书,只具有允许公安撤回案件的效力,并不是撤销立案的决定。当然,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公安机关撤案申请时,认为该案确属不够罪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监督部门可以做撤销立案的监督,要求公安撤销刑事立案。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85条第(三)项的规定,退回补充侦查期间,公安机关发现原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变化,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重新提出处理意见,并将处理结果通知退查的人民检察院。结合上述实践情况,此处公安机关“重新提出处理意见”“作出处理结果”前其实是要先获得检察院的准许,撤回起诉意见书,然后重新提出处理意见,如撤销案件等,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将处理结果通知退查的人民检察院。(19) 孙茂利主编:《〈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释义与实务指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1页。 换言之,只有公安机关从检察院撤回起诉意见书,才能将案件从检察院的系属关系中解锁,真正回复到侦查阶段,此时公安机关才有“案”可撤。这就如同检察院将案件起诉到法院,庭审期间案件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退回补充侦查之时,案件仍然系属于法院,诉讼法律关系并没有消灭,检察机关就案件提起的公诉仍然有效。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诉讼活动虽恢复侦查状态,但这种侦查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补充性的侦查,也不意味着诉讼就恢复到侦查阶段了”(20) 张建伟:《论公诉之撤回及其效力》,《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检察院只有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并获得法院许可后,案件才真正回到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才能名正言顺的作出不起诉决定。(21) 参见《高检规则》第456条,“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高检规则》第459条第2款,“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撤回起诉后三十日以内作出不起诉决定。” 两者的内在法理其实是相通的。
(二)退回补充调查:转为留置还是继续羁押
按照上述分析路径,笔者认为对于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需要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的,虽然相关的案卷材料、补充调查决定书、补充调查提纲等退回监察机关,但由于起诉意见并未撤回,案件仍然系属于检察院,本质上还处于审查起诉阶段、刑事诉讼程序之中。诚如卞建林教授所言,“因为退回补充调查并未改变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的事实,且无论是从便利与效率方面考量,还是基于对被羁押人监管安全方面的考量,都无必要再重新恢复适用留置措施。”(22) 卞建林:《配合与制约: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衔接》,《法商研究》2019年第1期。 综上,在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期间,如果要剥夺或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检察院还是应当沿用之前作出的强制措施。如果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决定逮捕,检察院应当在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同时,将退回补充调查的情况书面通知看守所,以便监察机关的办案人员需要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检察院作好协调工作。
(三)监察调查期间继续羁押所衍生的问题
虽然笔者借助案件系属理论回应了监察调查期间对犯罪嫌疑人要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究竟是留置还是继续沿用强制措施的问题。但在理论推演中也衍生出两个新问题。
1.补充调查期间案件虽然系属检察院并已实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所用的方法手段仍属于监察机关的调查行为,这会不会再次引发监察与司法两套程序的交叉重叠?笔者认为这一隐忧并不存在。首先,补充调查有单独的一个月办案期限,并不会侵占审查起诉阶段的办案时间;其次,在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期间,案件虽然系属于检察院,检察院对案件的最终走向有决定权,但并不会直接干涉补充调查期间具体手段方法的采用和如何实施,两者的界限仍然明朗;再次,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权并不依附于侦查权,而是公诉权所派生出来的应有权力。”(23) 同前注[6]。 套用这一认识,监察机关的补充调查权也不可简单等同于纯粹的监察调查权,其更亲缘于检察机关的自行补充侦查权,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补充性调查,两者都服务于公诉活动。但囿于检察院自身侦查能力的不足,故多数情况下只能求助于监察机关的补充调查权,以提供“场外协助”。因此说,补充调查基本还是附属于审查起诉阶段,并未侵蚀案件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的本质。这就如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吸收了解案情的公民协助调查一样,诉讼外行为的介入本身并不影响案件在刑事诉讼中推进的本色。
2.既然补充调查期间案件仍然被认为是处于刑事诉讼程序中,那么该期间辩护人可否继续行使辩护权呢?对此,笔者认为应当继续赋予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相应的诉讼权利。首先,退回补充调查期间,案件仍系属于检察院,已经实质进入刑事诉讼的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当然可以委托辩护人,获得相应的诉讼权利。其次,由于监察程序中的立案并不区分违法、违纪还是涉嫌犯罪的案件,如果在监察程序中姑且还可以以案件性质不明为由拒绝律师介入,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已经明确该案件的涉罪属性,即使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该案的涉罪性质并未发生变化,此时再次限制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缺乏程序正当性。再次,从实践层面看,当案件已经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基本意味着证据已收集完毕,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涉及的相关会见、阅卷等诉讼权利也大多完成,此时案件退回补充调查期间再以妨害取证、防止串供、干扰办案为由拒绝辩护律师介入,限制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意义也不大。
近年来,随着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发展,在国家供给侧改革和减肥增效等政策要求下,农资行业正在不断转型升级,在减少肥料生产量和使用量的同时提升其利用率,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双重效益提升。在这一背景下,作物生长不可或缺的大量元素肥料产品也在不断进行产品升级,传统肥料应用缓释和稳定技术以及与液体肥结合等都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推动了尿素等传统肥料利用率的有效提升并适应农业绿色现代发展的要求。
结 语
《刑事诉讼法》第170条就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的衔接机制等作了具体规定,这对于理顺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但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认为,在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程序衔接上,仍应发挥立案在程序转换节点、诉讼发动起点的标志性功能,这对于强制措施启动的正当性,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及时性,以及诉讼程序运转的自洽性都有重要作用。为此,应在司法解释或相关规范性文件中确立“形式立案”,即以案件受理代替刑事立案,对监察机关移送的犯罪案件不再进行立案前的实质审查,但须明确受案具有开启刑事诉讼程序的功能。在留置与强制措施的衔接上,为了确保监察与刑事诉讼两套程序的无缝对接,避免程序交叉,立法采用了“留置+先行拘留+强制措施”的模式,其中先行拘留具有过渡性,逮捕、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才是对接留置的最终措施。但立法对于留置转先行拘留后最终可否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缺乏周延规定,未来应明确先前留置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不妨碍诉讼推进,也无继续犯罪可能的,经过先行拘留期间的审查可最终不采取强制措施。另外,依据案件系属理论,对于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的情形,由于案件已经移送检察院并未撤回,系属关系并未消灭,案件仍是系属于检察院,处于审查起诉阶段。既然案件已实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对犯罪嫌疑人应当继续沿用之前的强制措施,并继续保障其辩护人的相关诉讼权利。
娘亲虽然对她娇惯,但这个时候,她一点也不愿意触母亲的霉头。她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教训一下青辰那小子,来给娘亲出这口气。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惯常以借鉴国外诉讼制度,比较研究的方法充实和完善本国刑事诉讼理论。本次监察体制改革引发的中国式问题对这种理论发展模式提出了诸多挑战。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应当以此次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实现对既往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自我反思,从既往的借鉴国外走向对本土经验智识的深度挖掘和提炼,以中国司法实践促推中国刑事诉讼理论的新发展,在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中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实现理论的本土自洽。
The Cohesive Mechanism between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and the Judicial Org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Rules ——Starting from Article 170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bstract : Article 170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tipulates part of the procedures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upervision and justice. Among them, the lack of case-filing procedures leads to the lack of legitimacy of the initiation of compulsory measure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parties’ rights and the self-consistency of the litigation procedure operation. In the futur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establish “formal filing”, replacing the case filing with case accepting. The criminal cases transferred by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the substantive review before filing, while the cases accepting should have the function of opening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term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ien and compulsory measures, the legislation adopts the mode of “lien-detention de bene esse-compulsory measures”, in which the detention de bene esse is a transitional measure, while the arrest, guaranteed pending trial and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re the final measures connecting with the lien.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stipulation about whether compulsory measures could be avoided after the lien is transferred into the detention de bene ess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litigation dependency, during the stage of review and prosecution, the litigation dependency will not be eliminated when the case is returned for supplementary investigation. The case will still belong to the procuratorate and remain in the stage of review and prosecution. The previous compulsory measures for the criminal suspects should be remain applied, and the relevant litigation rights of the defenders should remain protected.
Keywords : Supervision; Criminal Case Filing; Lien; Compulsory Measures; Litigation Dependency
作者简介: 董坤,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法规范下监察与司法的衔接机制研究”(19BFX100)和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一般课题“立法规范下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JL2019J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D915.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28( 2019) 06-0128-14
(责任编辑:薛向楠)
Dong Kun,Researcher of the Prosecution Institute of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Doctor of 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