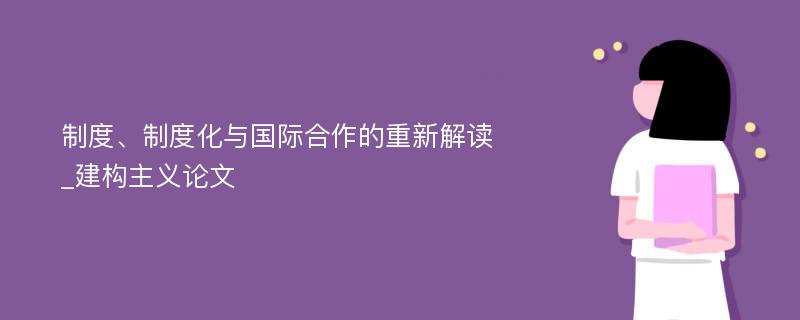
制度、制度化与国际合作的再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国际合作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9)04-0061-66
制度化是国际关系学界,尤其是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该术语通常用于衡量规范的活力(robustness),也有学者使用制度化这一术语研究观念的因果作用。① 但这一术语在使用中描述性强,分析性弱,这制约着学术界关于规范研究的开展。② 与此同时,丽莎·玛丁和贝斯·西蒙斯指出,尽管关于国际合作的经验研究存在研究设计的瑕疵,但都认为制度有助于促进合作。③ 但有些合作是心照不宣的,不需要沟通和明确的协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就属于这种类型。④ 有时存在制度,但并没有导致合作,比如罗伯特·基欧汉的研究就表明,尽管存在国际能源机构,但在能源危机时并没有避免纷争。⑤ 确切地说,制度有助于合作,制度化有助于合作的深化,但这种假设需要探索其条件性。在经验研究中,制度化合作是主要的合作形式,也是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本文就尝试对制度化进行界定,并在互动层次上对制度性合作的条件和制度化合作的动力进行探析。
一、制度化:概念辨析
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的研究起源于战后国际组织的研究。⑥ 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制度主要用来指代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研究也就是国际组织研究。70年代后,很多重大国际事件都发生在现有国际组织的框架之外,于是就有学者开始关注研究国际机制。到了80年代,国际机制逐渐取代国际制度(国际组织)这一术语,但是很多学者认为斯蒂芬·克莱斯纳关于国际机制的定义含义不清晰,难以操作。⑦ 至80年代后期,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国际制度一词又开始复兴。基欧汉扩容了国际制度的含义,认为国际制度就是持久的和相互关联的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职责,限制活动并塑造预期。国际制度包括国际组织(organization)、国际机制(regime)和国际准则(convention),其中国际机制主要指正式、明确的规则,而国际准则则指非正式的规则。⑧ 这是基欧汉对克莱斯纳关于国际机制定义的一个改进。但是很多学者指出,组织有其自身的特征,显然不同于制度或机制,⑨ 因此在研究中有必要做出相应的区别。一些学者也指出了机制与制度之间的区别,⑩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区别意义不大,在实践中往往互用机制与制度。玛丁和西蒙斯认为,尽管存在很多用法,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制度是用来管理国际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而规则就是用来禁止、要求和允许某种特定行动的陈述。制度的核心就是这些规则,两位学者都认为这样定义有三大优势:这一定义排除了抽象的原则和组织,避免了国际机制定义的混乱;这一定义使得解释变量(制度)独立于被解释变量(行为结果),从而避免了其他学者制度定义中的同义反复;这一定义相对独立于某种特定的理论视角,因此容易被接受。(11)
基欧汉没有给出制度化的确切定义,但其在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制度化衡量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指出了衡量制度化程度的三个维度:共同性(commonality),即体系中的行为体对适当行为的预期以及对行动解释的共享程度;明确性(specificity),即这些预期以规则的形式加以明确的程度;自主性(autonomy),即制度更新自身规则而无需依赖外部施动的程度。基欧汉进一步指出假如准则经过发展成为机制(共同预期成为明确的规则),或机制进一步发展成为组织(自主性增强),就标志着制度化程度的上升。(12) 约翰·杰拉尔德·鲁杰引用社会学家的制度化定义,认为制度化就是协调和模式化行为,从而使其导向一个方向而不是理论上或经验上可能的其他方向。鲁杰认为制度化并不等于正式的国际组织行为,提出了用国家的集体反应来区分制度化发展的三种水平:纯粹的认知水平,即认知共同体;国际机制;正式的国际组织。(13) 具有社会学视角的制度主义学者詹姆斯·马奇和乔安·奥尔森认为制度可以被视为相对稳定的惯例和规则的集合。这些惯例和规则不但界定特定群体成员在具体情形中的适当性行为,而且内嵌于意义结构和解释框架中。制度化就是制度的出现以及制度框架内行为体行为的模式化。(14) 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认为制度化就是行为体对于来自冲突解决机构或者集体决定的权威性的接受。(15) 亚历山大·温特没有直接定义制度化,但在论述国家时认为集体行动得以制度化意味着个人认为他们进行合作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合作的期望是深刻的,所以涉及集体行动的问题足以得到解决。(16) 迈克尔·史密斯认为制度化就是一个进程,规范或者说共享的行为标准通过这一过程被创造和发展出来。(17)
由以上定义可知,制度不同于制度化。制度可以指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而制度化则表示规则的正式化、具体化和明确化。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描述,而制度化则是制度的发展,(18)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制度化的发展程度往往用来描述和衡量规范的活力。制度化程度越高,行为体的遵从程度也应该越高。但如果把上述学者的理解按照时态进行归类,就会发现温特和克拉托赫维尔对制度化是一种完成时的理解,即行为体完全内化了某种制度(institutionalized),认为遵从制度是理所当然的,这时行为表现为一种适当性逻辑。(19) 当然,这是对制度化进程终点的描述。基欧汉、鲁杰、奥尔森和史密斯对于制度化是一种进行时的理解,认为制度化从程度上可以分成若干阶段,是一个制度逐渐被行为体内化的动态过程(institutionalizing)。如果按照概念的内涵对于上述学者的理解进行再次归类,就会发现基欧汉和史密斯关于制度化的理解并不包括行为体行为的模式化。基欧汉指出,一个制度的制度化程度与其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并不存在严密的正相关关系,一些制度的制度化程度很高,但在世界政治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比如海牙的国际法院。(20) 其余学者关于制度化的理解都包括行为的模式化,即制度化就意味着行为的模式化。为了区别两种不同的制度化,不妨把基欧汉和史密斯的制度化理解为制度本身的制度化,而其余学者的制度化理解为行为体行为的制度化。
这样制度化理解的分类就产生了。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和克拉托赫维尔是以完成时的方式理解制度化。这种理解可以解释行为体的某些习惯性行为。但如果解释的对象位于互动层次,比如合作现象,这种理解所能提供的就只是一种结构性解释。行为体之所以选择合作是因为其内化了合作的文化,视合作为理所当然。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无法把握合作中复杂的政治过程。因此,把制度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理解,研究互动层次的国际现象会更有学术价值。
如果把制度化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以制度化的水平来衡量制度的活力,那么对于制度化的定义就必须排除行为模式化的内容。这样可以避免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因为如果解释项不能独立于被解释项,那么就会造成循环推理以至于规范的效力问题难以获知。(21) 为便利实证研究,可能制度本身的制度化比行为体行为的制度化操作起来更有意义。因此,笔者拟将制度化理解为从国际准则到国际机制再到国际组织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制度本身的制度化。制度化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关系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不能把国家行为的模式化包括在制度化的定义之中。
二、制度性合作的条件
国际合作是位于互动层次的现象。但起初互动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层次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22)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学者肯尼思·华尔兹坚持系统的研究方法,认为结构的定义必须将单元的属性和联系加以省略,只有这样才能区分结构的变化及其内部的变化,因此互动对于结构现实主义来说几乎没有研究价值。(23)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学者肯定了互动作为一个分析层次的研究意义和价值。阿瑟·斯坦指出了战略互动作为一个独立分析层次的意义,认为战略互动的研究方法可以发挥系统研究和决策研究之间的桥梁作用。(24) 基欧汉也是从互动层次,利用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分析国际合作的,认为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其功能推动国际合作。(25) 温特也指出单凭行为体自身的特征无法解释结果,起关键作用的是它们如何互动,互动结果来自于单位层次,但不能还原为单位层次,所以互动作为一个单独的分析层次具有研究意义。(26)
海伦·米尔纳指出了行为体数目、未来预期、国际机制、不对称权力结构、认知共同体、相对获益与绝对获益的关注都会影响互动中行为体的合作倾向。(27) 其中国际制度只是促进合作的一个因素,不可能是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国际制度也未必是合作的充分条件,行为体推动制度化的动力可能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战略目的,避免制度约束自身行为,即制度设计之初的目的就是让制度不发挥或少发挥效力。因此逻辑上可能出现制度化合作(制度化与合作呈现正相关关系)的现象,但也可能出现制度化无合作(制度化与合作呈现无相关关系)和制度化不合作(制度化与合作呈现负相关关系)的现象。(28) 被爱德华·卡尔称为20年危机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制度化程度也很高,但依然无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实只有当存在共同利益困境和共同避免困境时,制度才会有助于合作。(29) 如果行为体将互动视为零和博弈,就不会存在任何合作空间。
合作始于决策的相互依赖,汤姆斯·谢林指出这是一种混合动机博弈。在这种博弈中,既存在个体目标的冲突,也存在决策的相互依赖,二者之间的关系既非对手也非伙伴。(30) 囚徒困境博弈是这种混合动机博弈的典型。在无政府状态中,由于缺乏中央政府强制协议执行,这种混合动机博弈又是一种无法达成有约束力协议的非合作性博弈。(31) 此时背叛是最优战略,即便存在共同利益,行为体也不会合作。只有当囚徒困境博弈重复进行,而且未来收益折扣率比较低时,行为体从长远考虑收益的最大化,才有可能采取合作行为。何种体系背景有助于行为体从长远考虑收益最大化呢?新现实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往往会基于无政府状态下冲突的可能性(possibility),从最坏情况(worst-case perspective)采取行动制衡潜在对手的军事实力。(32) 这完全是行为体在无政府结构压力下采取的自助式机会主义行为,在这种理论描述中,不存在未来阴影,行为体间的互动具有零和特征,自然也不存在共同利益。但在政治现实中,除非出现极端情况,冲突的或然性(probability)是存在的。这是行为体从长远考虑的第一个因素。基欧汉指出,在一个标准的预期效用公式中,国家不可能仅仅用可能性来决定它们的行为。(33) 其次,行为体从长远考虑还必须要求制度对相对获益提供补偿功能。约瑟夫·格里科指出,在共同的安排中,由于伙伴国获益更多,最终会出现屈从于合作伙伴国地位的国家,因此相对获益从长远来说会阻碍合作的努力。(34) 最后行为体从长远考虑还要求必须解决分配冲突问题。政治现实中,囚徒困境博弈如果重复进行,协作问题就有可能转化为有多个均衡解的协调问题,这样行为体不仅会关心制度的效率问题,还会关心制度能否解决分配性冲突的问题。(35) 当存在多个均衡解时,制度就需要发挥聚焦(focal point)功能。
因此,制度性合作的出现必须满足以下前提:体系层次的严酷性不足以要求行为体从最坏的情况制定战略;行为体间的互动具有混合动机博弈的特征,也就是说存在共同利益;存在政治市场失灵的情况,因为当信息完全透明和交易成本为零时,制度没有出现的必要;最后制度还须具备提供补偿支付和解决分配问题的功能。(36) 只有满足这些条件,行为体才会从长远考虑共同利益,制度的功能才能发挥,也才会出现制度性合作的现象。
三、制度化合作的动力
制度功能有助于行为体从长远考虑收益最大化,进而出现制度性合作现象。但制度性合作只是制度化合作的起点。制度化合作要求共同利益必须呈现更新和扩张态势。是什么因素促使行为体认为共同利益在不断更新和扩张呢?关于利益,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研究有不同的主张。理性主义研究大多假定利益外生于行为体互动,(37) 通过博弈方法研究利益给定下的互动结果。建构主义则认为利益是以身份(identity)为先决条件的,行为体在知道自己是谁之前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38) 身份就是行为体对于自身具体角色相对稳定的自我理解和预期。(39) 身份是在互动中形成的一种角色结构,处于一种关系中。行为体在互动中既可能出现正向认同,也可能出现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的情况。(40) 认同(identification)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超越。(41) 理性主义博弈论和建构主义互动论是关于互动的两种理论,前者假定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外生于互动。建构主义互动论则认为互动中身份和利益是否变化是一个经验问题,不能先验预设。即便身份和利益没有在互动中发生变化,身份也会在互动中得到强化。(42) 但是温特并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样的互动模式会产生正向认同或负向认同,换句话说,温特并没有强调在互动层次上制度化合作的动力来源。
如果共同利益是以身份结构为基础的,那么即便都处在混合动机博弈中,朋友间的共同利益肯定也会多于对手间的共同利益。如果经过互动,行为体间竞争者身份向合作伙伴身份过渡,就可以推知互动产生了正向认同,共同利益将呈现更新和扩张态势,制度化合作的现象就可以出现。这时,制度的制度化过程将导致合作的深化。如果产生零向或负向认同,则会出现制度化无合作和制度化不合作现象。因此,制度化合作的动力也就是特定的互动模式问题。不管互动模式产生的是正向还是负向认同,都涉及行为体的复杂学习的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会重新界定共同利益。如果是正向认同,就会出现共同利益的更新和扩张态势。杰弗瑞·切克尔也指出,建构主义学者必须在他们的分析中开发隐含的认知模式,以明确制度化的含义。(43) 因此,研究正向认同,无法回避复杂学习中的认知模式问题。安德斯·汉森克里夫等学者总结国际机制的研究成果时,认为存在认知主义的国际机制学派,并将该学派分为弱认知和强认知两种亚流派。克拉托赫维尔强调论争(arguing)的建构主义和温特强调身份(identity)的建构主义都是行为体在互动中重新界定利益的强认知主义的国际机制流派。(44) 两者区别在于温特借鉴符号互动理论,行为体在互动中处于无语状态,而克拉托赫维尔借鉴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45) 行为体在互动中处于对话状态。如果说温特的互动理论在认同方向上是开放的,即理论上可以出现正向、负向和零向认同,那么克拉托赫维尔的互动理论受规范语用学(46) 的指导,则只朝正向认同的方向发展。
温特的理论重身份认同,轻语言活动,克拉托赫维尔的理论重语言沟通轻身份认同,如果融合二者的理论,借鉴规范语用学和建构主义互动论的原理,就可以开发出行为体在互动中通过复杂学习进行正向认同的认知模式。沟通要取得成功,行为体必须遵循言语行为的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而且当对方提出关于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疑问时,行为体还要进行合理的解释以获取对方的理解。总之,对话必须通过协商一致完成。当然沟通具有规范内涵,而且未必每次沟通都能取得成功,但是这种互动模式与其他互动模式相比更有助于凝聚共识。这种互动模式的特点是共识在彼此同意的基础上经共同理解完成,因此制度或规范将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在规范合法性增强的同时,规范所界定的彼此间的身份也将强化,正向认同感会增强,这会成为强化合作伙伴身份的巨大动力。随着合作伙伴这一身份的强化,共同利益将呈现更新和扩张态势,进而推动制度的制度化与合作的深化相伴随的情况。正是因为对话潜藏有如此巨大的动能,哈罗德·穆勒才认为沟通行动理论可以发挥合作动机与具体合作行为之间的桥梁作用。(47)
四、结语
规范语用学指导下的互动模式促进制度化合作是一个兼具规范和实证意义的命题。该项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揭示了制度化合作现象得以出现的附加条件,其实践意义在于明确了对话在大国协调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国际体系中以制度为基础的大国协调机制。特定的互动模式可能在行为体间产生正向或负向认同,因此对于互动结果意义重大。但是乔纳森·默赛尔利用社会身份理论研究发现,群体间的竞争关系不需经过社会互动而天然存在。(48) 这种观点并不会危及本文的分析,按照默赛尔的理论,所有群体间都会存在竞争关系,但问题是为什么某些竞争关系可以通过合作进行有效管理,而其他竞争关系却难以通过合作进行管理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结合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合理要素,提炼出对于合作有益的特定互动模式。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在理性主义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制度化合作的附加条件或动力机制,这种努力将有助于增强建构主义合作理论的解释力。
收稿日期:2009-04-07
修改日期:2009-05-24
注释:
① 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O·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载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M],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② 相关批评参见Jeffrey T.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orld Politics,1998 Vol.50,No.2,p.340; Jeffrey W.Legro,“Which Norms Matter? Revisiting the‘Failure’of Internat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7 Vol.51,No.1,p.34.
③(11) Beth A.Simmons and Lisa L.Marti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2,p.199,p.194.
④(27) Helen Milner,“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Strengths and Weaknesses”,World Politics,1992 Vol.43,No.3,p.469,pp.470-480.
⑤(25)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纷争与合作》[M],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第6章。
⑥ Friedrich Kratochiwil and 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 State of Art on An Art of St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6 Vol.40,No.4,pp.754-760.
⑦ Stephen Haggard and Beth A.Simmon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7 Vol.41,No.3,pp.493-494.
⑧(12)(20) Robert O.Keohane,“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A Perspective on World Politics”,in Robert O.Keohane ed.,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Colorado:Westview Press,Inc.,1989,pp.3-4,pp.4-5,pp.6-7.
⑨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4页。
⑩ 奥兰·杨所做的区别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第81页;哈格特和西蒙斯所做的区别参见Stephen Haggard and Beth A.Simmon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pp.495-496。
(13) 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 wouldn't start from here if I were you’”,in John Gerard Ruggie ed.,Constructing World Polity: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pp.54-55.
(14) Jamees G.March and Johan P.Olsen,“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in Peter J.Katzenstein(ed.),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9,p.308.
(15) Friedrich V.Kratochwil,Rules,Norms,and Decisions: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63.
(16)(26)(38)(41)(42)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第189页,第290页,第287页,第420页。
(17) Michael E.Smith,Europe'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6.
(18) 制度或机制向更高级的方向演变就意味着它的发展。制度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机制的构成要素或“核心特质”的完善和广为接受,正式程度越来越高,影响范围越来越大;机制的行动指导和约束能力日趋增强,建立起各方接受的行为规则和程序;机制的遵从措施趋向完善,得到愈加坚定有力的贯彻执行。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M],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19) 适当性逻辑有两种制度内化的形式,其一是行为体从事角色扮演(role-playing),其二是行为体认为理所当然(takenfor-grantness)。Jeffrey T.Checkl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05 Vol.59,No.4,p.804.
(21) Jeffrey W.Legro,“Which Norms Matter? Revisiting the‘Failure’of Internationalism”,p.34.
(22) 戴维·辛格、肯尼斯·沃尔兹、詹姆斯·罗斯诺以及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都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但所有这些学者都没有把互动作为一个分析层次。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23)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4页。温特认为有目的的行为体在做行动选择时把“其他行为体考虑进来”,就产生了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这种关系可以呈现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就像市场上购物的顾客,施动者把其他施动者视为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这样互动只能通过行动产生的非目的性结果实现。另一种形式类似讨价还价,行为体得到的结果取决于其他行为体的选择,这样行动就具有战略性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88页。沃尔兹之所以认为互动没有研究价值,是因为他所理解的互动是第一种形式。而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认为互动具有研究价值,是因为他们所理解的互动是第二种形式。不过这两种形式的互动都是理性主义的互动论,不同于本文第三部分所谈的建构主义互动论。
(24) Authur A.Stein,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176.
(28) 很多情况下,冲突的产生源于国家目标的冲突性,而不是因为缺乏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制度不会增加合作。哈格特和西蒙斯也认为,有时机制会不经意地导致不稳定。参见Stephen Haggard and Beth A.Simmon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p.496。苏珊·斯特兰奇也指出,机制含有价值偏好,反应现状偏好的保守态度,这可能会孕育更大的冲突。参见Susan Strange,“Cave! Hic dragones: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in 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346。
(29) 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in 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p.134.
(30) 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1960,p.89.
(31) 门洪华:《博弈论与国际机制理论:方法论上的启示》[J],《国际观察》2000年第3期,第41页。
(32) 基欧汉和温特都认为现实主义认为行为体从最坏情况的视角采取行动,参见Robert O.Keohane and Lisa L.Martin,“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5 Vol.20,No.1,p.43;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 Vol.46,No.2,p.404。但斯蒂芬·布鲁克斯认为,并非所有现实主义者都从最坏角度考虑采取行动,他所列出的后古典现实主义就认为行为体是从或然性而非可能性的角度采取行动的。参见Stephen Brooks,“Dueling Re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7 Vol.51,No.3,p.455。
(33) 罗伯特·基欧汉:《制度理论和冷战后时代现实主义的挑战》,载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M],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34) 约瑟夫·M·格里科:《无政府状态和合作的限度:对最近自由制度主义的现实主义评论》,载《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117页。但安德斯·汉森克里夫等学者指出,制度可以增加补偿功能以减缓合作方对于相对获益的关注。参见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and Volker Rittberger,“Integra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0 Vol.26,No.1,p.15。
(35) Lisa L.Martin and Beth A.Simmons,“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 Peter J.Katzenstein(ed.),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p.105.
(36) 有多个均衡解的协调博弈也具有混合动机博弈的特征。囚徒困境博弈的困境在于行为体在执行协议中的背叛动机;多均衡解的协调博弈的困境在于如何达成各方满意的协议。基欧汉详细指出了制度通过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合作的功能。Robert O.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pp.155-161.但基欧汉忽视了现实主义学者所关心的制度解决分配冲突(聚焦博弈均衡点)的功能,本文在此予以补充。
(37) 约翰·杰拉尔德·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载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M],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
(39)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p.397.
(40)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349页。
(43) Jeffrey T.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340.
(44) 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67.
(45) 关于克拉托赫维尔的规范建构主义,参见惠耕田:《克拉托赫维尔与规范建构主义》,载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4页。
(46) 也称普遍语用学与形式语用学。普遍语用学是用来探讨以获得成功沟通为目的的语言使用的普遍规则,说话者必须能掌握此规则体系,方能于言谈之间恰当地使用语句,获致成功的沟通。具体参见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2页。
(47) Harald Mull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Communicative Action”,in Karin M.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xt Generation,New York:M.E.Sharpe,Inc.,2001,p.165.
(48) Jonathan Mercer,“Anarchy and Ident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5 Vol.49,No.2,p.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