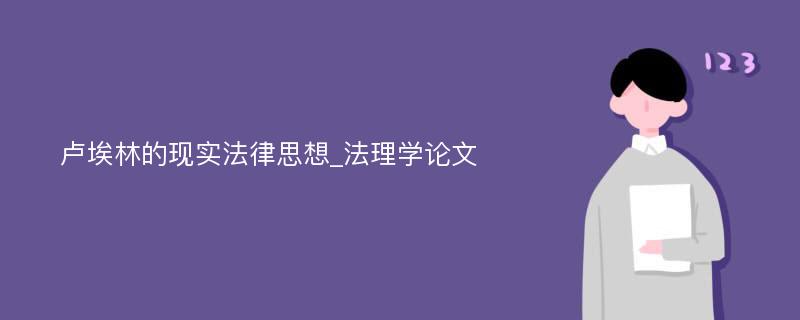
卢埃林现实主义法理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理学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思想论文,卢埃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28(2009)04-0003-17
法理学是关于法律事物的任何方面的缜密和持续的思考,假如这种思考并不局限于仅仅寻求对眼下问题的实际解决。因此,法理学包括对法律领域内的任何形式的真诚和审慎思考的概括。①
——卡尔·卢埃林
前言
在20世纪中期,卡尔·卢埃林和罗斯科·庞德对美国法理学的共同影响长达三十余年。卢埃林广泛的兴趣、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张扬的个性使得每一位严肃的当代法理学家都不得不予以关注。他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使他成为美国20世纪最为杰出的法学家之一。纵观其一生,不难看出卢埃林不仅是一位挥舞着改革旗帜和颂扬科学之美德的狂热的现实主义者,一位献身于转变基本法律技巧和从总体上提高法学教育的颇有造诣的法学教育家,而且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统一商法典》的起草人,还是一位为上诉程序的参加者提供常识性建议的睿智且富有经验的贤人,当然,也是一位无可救药的、充满浪漫情怀的业余诗人。[1]
著名法理学家罗斯科·庞德历经数十载写下了多卷本的宏篇巨制——《法理学》,而喜欢自称法理学家而非商法专家的卢埃林却从未发表过一部系统的严格意义上的法理学著作,他的法理学思想散见于留给后人的250余篇论文和多部专著之中。不过,庞德的《法理学》经过漫长岁月的风烛所剩下的恐怕只有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了,但卢埃林却以一部《统一商法典》为自己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只要这部法典还在调整美国的商事交易,卢埃林的法理学思想就不会被人们所遗忘。这也正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人们对他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卢埃林的思想表达得不系统,这给人们研究他的思想增加了难度。更有甚者,卢埃林常常夸夸其谈,言过其实,且表里不一,前后矛盾;其臭名昭著的散文式写作风格更是招人诟病,并成为误解的渊源。卢埃林之所以成为最有争议的现实主义法学家,其本人难辞其咎。
对于这位美国现实主义运动的代言人,我国学界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所见研究成果中不时夹杂着一些对其法理学思想的误解或曲解。在对大量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卢埃林的法理学思想作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介,以期澄清关于卢埃林的各种流行的误解或曲解。
此外,研究卢埃林的法理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美国《统一商法典》这部英美法系最伟大的成文法,而且对于法律形式主义初见端倪的我国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法律现实主义乃法律形式主义的死敌。[2]
一、现实主义法理学及其研究方法与立场
作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旗帜性人物,卢埃林鲜明地向世人展示了现实主义的理论研究进路:“在通往科学的道路上,知识并非必须是科学的;知识也并非必须是科学的才能极有效用。社会科学家该坦承这一点了,这样将会避免许多混淆,也会避免做更多的无用功。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大致表明的当前纬度的指引下,谨慎而精明地通向科学极点的知识。这才是通向科学的科学之路。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条道路上一步步地前进。”[3]
与穆尔、库克和英特玛等沉迷于纯科学研究的现实主义法学家不同,卢埃林似乎没有受到任何特定的科学模式的影响,他也不像前者那样沉迷于科学思维的哲学。正如卢埃林的学生英国著名法理学家威廉姆·特文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卢埃林很早就意识到了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僵硬类比所隐含的潜在危险,他认为:
首先,社会科学中的经验性研究最终可以达到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客观性标准是可以想象的,不过,就目前而言,也只是朝着该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而已;其次,“客观性”是一个程度问题,假如承认其局限性的话,那么,即使是漫不经心的印象性观察也胜过全然的无知;再次,强调与科学的类比可能是危险的,因为“科学的”这一术语也许会被贬低;更糟糕的是,未来的科学家可能仅把那些可以严格量化(一个狭隘且通常毫无成果的领域)的课题视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总之,卢埃林赞成一种建立在对急速前进中的障碍(如成本、多数工作单调乏味以及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所进行的现实评估基础上的常识性研究策略。[4](P96-97)
除了对观察立场进行有价值的探讨之外,卢埃林还为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研究法律现象而专门设计了各种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制度”方法及其著名的“疑难案件”方法。制度方法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毋宁说是一种总体上的研究思路。对此,卢埃林主张:“你所要做的全部,只是从社会学中借用制度这一概念,并且表明你使用这一概念时包含了相关的物质设施和整体上的组织方式;庞德关于法律的图式——法律制度——立即成为一种任何社会科学工作者均可以看到、理解、与之交友、从中学习并且可能为之做出贡献的东西。”[5](P355)这种思路为实现律师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进行具体的合作开辟了道路,因而对经验法律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当然,所谓制度方法并非卢埃林所首创。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研究方法即已十分流行,但以疑难案件方法的形式使其发挥实际效用却应归功于卢埃林。疑难案件方法基本上是由对一个争端从产生到解决的全部过程的深入分析构成的。卢埃林运用这种方法的背景是美国夏延族印第安人的法律制度,其形成是在《夏延族的习俗》一书出版之前与著名人类学家霍贝尔密切合作的过程中。
卢埃林认为,通过运用疑难案件方法,法律研究者能够考查解决争端所涉及的整个复杂的制度过程。“找出并经认真审查的疑难案件是发现法律的最为稳妥的主要途径。它们的资料是确定的,产出是丰富的,也是最发人深省的。”[6](P29)此外,在卢埃林看来,这种对疑难案件的全新关注无论对于法律研究所侧重于规则的思想方法,还是对于侧重于无掩饰的实务操作的描述性方法,都是绝对必不可少的补充。正如特文宁教授所言,卢埃林的疑难案件方法实际上就是:
通过研究实际判例,人们便能够察觉和理解规范相互冲突的现象;它克服了信息提供者拒绝或者无力清晰表达规范的困难;清晰表达的规范与争端解决程序的结果之间的吻合或分歧程度可被核查;疑难案件表明已确立的形式事实上是如何被运用的,这比对形式的空洞陈述更具启发性;研究纠纷可以显现出群体的“法律”与其中的每一个小群体的“次法律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在危机中可以实际看到文化在起作用;最后,疑难案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现象。[7]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卢埃林从未将其精心设想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对运行中的法律制度的研究。相反,他在《夏延族的习俗》一书中所分析的,是发生在1820至1880年间的案例,这些案例是由夏延族的老人通过翻译提供的。换言之,整个研究课题的材料完全建立在关于150年前所发生的事件的道听途说上。特文宁教授曾为《夏延族的习俗》的思想的完整性进行过辩护,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信息提供者所讲述的故事是有意义的(即使是虚构的),因为它们是以夏延族的概念,并且是以实际制度为背景而讲述的,因为“理解一个社会的制度所必不可少的乃是理解构成其制度一部分的该民族的思维方式”。[4](P162-163)不过,特文宁教授的辩护恐怕不适用于《夏延族的习俗》的具体情形。虽然了解盛行于一种文化中的概念对于真正理解法律制度是绝对必要的,但承认这种了解对于系统审查这些制度只是一种补充同样是重要的。遗憾的是,卢埃林对夏延族的习惯法体系的重建不是系统的历史研究的结果,而是建立在几个年长的信息提供者所转述的粗略信息之上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并未经历过夏延人的法律程序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特殊情形下,很难理解特文宁教授是如何断言这些被采访者的故事是以“实际制度为背景”而讲述的;可以肯定地讲,卢埃林在这方面没有可靠的信息,他的分析和判断只是根据最佳资料来源做出的。[8]
不仅如此,卢埃林也从未将其一再鼓吹的疑难案件方法运用于现代法律制度的研究。也许对于研究一个复杂的社会的争端解决程序来说,这种方法很可能不太实用。不过,对一个适度简单的发展中的法律制度而言,这种方法显然具有一定的潜力。特文宁教授就曾宣称,疑难案件已成为学者从现代人类学视角研究“原始”法律制度时所关注的一个要点。[4](P164)尽管如此,关于疑难案件方法已成为这一领域进行现代研究的方法论中的主要工具的观点还是难以找到证据支持的。哈里·琼斯教授认为,这种方法已经影响到(虽未支配)这种研究。[8](P450)这一说法可能更为准确、客观。总之,不管疑难案件方法目前状况如何,在现实主义法学家当中除了穆尔以外,只有卢埃林事实上形成了用以研究法律制度的具体方法。仅仅这一点,本文以为,疑难案件方法在美国20世纪法学史上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经验法律科学的另一项重要前提是,确立一个适当的概念框架。卢埃林明确意识到了确立此类概念框架的需要。正如他在1931年所言:
概念的形成以及对查明我们的状况的概念图式的整合,对于科学的进步永远都是必要的;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没有假定,则意味着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没有清晰地意味着某种东西的假定,试图对新旧数据进行观察或研究,90%到95%的工作将是徒劳的,因为科学的基本原则正是从中而来,只有提出有意义的假设的天赋才能引向某个地方。[9](P94)
但人们非常清楚的是,卢埃林自己从未能真正形成一套既能产生关于法律和社会制度的一般假设,也能指导将来的经验性研究的概念体系,他所使用的一些概念时常模糊不清。卢埃林关于法律运作的理论,只是对法律制度所履行的基本职能的分析,这一理论并未提供对于这样一些重大因素的研究,诸如社会和法律制度的结构、权力过程以及政策制定。在本文看来,卢埃林之所以未能提出一套概念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方法存在缺陷。正如上文所表明的那样,卢埃林用于疑难案件的方法有严重缺陷,因为它未考查夏延族印地安人部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缺乏这些信息,卢埃林自然无法提出关于整合法律和社会进程的综合理论。简言之,卢埃林掉进了常常困扰功能主义者的陷阱,即偏向假定一系列先验的功能,然后再寻找履行这些功能的社会制度。就卢埃林而言,对社会制度的研究不是在邻近的社区进行的,结果,产生的是这样一个概念体系,它只注意到了功能,对于实际制度只是作为一种事后思考来处理的。[10](P30-36)
可以说,卢埃林对发展经验法学的基本要求的洞察是极其敏锐的。然而,他在试图满足这些要求时,并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功。琼斯教授认为,当时的社会学家还没有将注意力投向将法的社会研究“具体化”的问题上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卢埃林才思敏捷,从不缺少想法,他所缺乏的是能够使这些想法服务于令人满意的研究的成熟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协作。[8]
此外,与其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不同,卢埃林非常关注人们争论不休的关于观察立场的问题。其全部主张的核心只是一个简单的前提,即在实际观察过程中,观察者必须刻意搁置价值判断。卢埃林发表《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些现实主义——答庞德院长》一文时,他心中所想的一切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信念。在这篇著名的论战文章中,作为改进法律科学的基本方法论的一种途径,他极力主张将“实然”与“应然”暂时分离。卢埃林早年在德国留学时曾深受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和哲学家胡塞尔的影响。他认为虽然价值也许会支配任何一项具体研究的目的,但不能允许它影响观察过程本身。他在同年发表的关于现实主义的另一篇文章中更为全面地阐述了这种观点:“关于人们应该想去哪里,我们不得不加入价值判断;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批评他们的实践和道德观。但我们所不能忽略的是,当我们进行价值判断时我们完全抛弃了个人理想和主观性的坚实领域……科学不会告诉我们何去何从,永远也不会。融合‘实然’和‘应然’实际上是将科学所必须依赖的逐渐积累的半永久性数据与关于社会目标的不断变化的舆论波动混为一谈。”[9](P85-87)
在卢埃林看来,法律观察者维护客观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将法律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制度”。[11](P183-185)他认为这种观点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将法律规则、概念和理想置于赋予它们意义和生命的制度实践的背景下。此外,这个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意义。“首先,一个运行中的制度是有工作要做的,其功能是要有效地和出色地完成这些工作。这就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目的和价值的支柱。其次,一个运行中的制度对生活产生效果,因此,也必须根据效果来检验它,而这些效果是可以探究、查明的。因此,对这一制度的衡量,即为对其实际效果的衡量。”[11](P185)
有必要指出的是,卢埃林的观点实际上要比其他现实主义者所持的观点更加开放。在1940年发表的《论阅读和使用新兴法理学的文献》一文中,他用了大量篇幅来反思现实主义者早期普遍持有的那种狭隘的观察立场。[12]在他看来,“新兴的现实主义法理学”几乎只是一种律师的法理学。具体来说,这种法理学所反映的是顾问律师的观点,顾问律师由于有责任就法律的可能状况向潜在客户提供法律意见,因而他们所关注的,是对法官如何裁判的预测。这种早期的观点在那些赞成霍姆斯法官的法律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者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此后,现实主义拓宽了视野,以便吸收辩护律师的观点,而辩护律师的精力主要用于说服法官相信其法律意见的“正确性”是不可辩驳的。在卢埃林看来,这种观点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激励人们对影响司法裁判过程的主观因素进行探讨和研究。卢埃林还认为,即使采纳这两种观点仍然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法律程序中最主要的参加者——法官的观点。由此可见,
关注法官和法官工作的法理学必须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法官。顾问律师不得不担忧法官将会怎样做,其做法正确,还是不正确,无论正确还是错误,它都对案件做出了裁判;无论适当与否,它都可能创制或者改变一项规则。因此,对于一位正在提供咨询意见的顾问律师来说,法院所做的就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这种做法正确与否。然而,法官不能那样看待法律;公民也不能那样看。这并不是说以预测官员行为的眼光来看待法律是种错误或者不好的方式,而是说这种预测方式是一种片面的看待法律的方式。[12](P587)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卢埃林是在提倡现代法学应当采取法官的立场,或者法律程序中任何其他参加者的立场。恰恰相反,他极力主张在法律分析层面进行彻底的变革。因为卢埃林坚信,要理解而非影响社会进程,法学家必须采取一种客观中立的观察者的立场,从严格的功能角度来看待法律,将法律作为一种运行中的制度来研究。卢埃林希望以此超越多数现实主义法学家所偏好的那种“参与者”的立场。
二、怀疑规则的确定性
正如卢埃林在《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些现实主义——答庞德院长》中所言,法律现实主义的出发点是,就法律规则和概念声称描述法院或人们实际在做什么而言,不相信法律规则和概念。在对此进行多年研究之后,特文宁教授得出结论认为:“卢埃林现实主义法学的核心信条,即不带成见地看,是要提醒人们密切联系实际和具体情况,以免陷入形式主义,即由于脱离现实生活而犯简单化的错误。”[13]
在描述自己投身其中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及其参加者的研究图景时,卢埃林指出:
参加现实主义运动的是些抱有温和理想的人们。他们要求法律与事物打交道,他们自己也要求与事物、与人、与有形的东西、与明确有形的东西以及明确有形的东西之间的可观察的关系打交道,而非仅仅玩弄语词。当法律涉及语词时,他们要求语词代表其背后隐藏的有形的东西以及它们之间的可观察的关系。他们要用事实检验思想、规则和程式,以使它们接近事实。他们将规则、法律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并且认为只有当它们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时,才有意义。在人类社会中,由于法律变化缓慢,而人们的生活变化迅速,因此,他们怀疑,某些法律已经与生活脱节。首先,法律做什么,对人们做什么,或者为人们做什么,是一个事实问题;其次,法律应该对人们做什么,为人们做什么,则是一个目的问题。[14]
比较而言,特文宁教授的前述结论与卢埃林的上述观点是基本吻合的。然而,多年以来,由于某些学者的误解和以讹传讹,卢埃林却背负着“规则怀疑论者”的恶名。
事实上,卢埃林并不否认规则作为法律的构成要素的重要性,他所怀疑的只是“书本上的法”。他认为,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实际规则是法官在将书面规则适用于所遇到的每个独特的实际纠纷时从对书面规则的重构中抽演出来的。[13](P675)换句话说,卢埃林怀疑规则的确定性有语言学方面的考虑,因为在他看来,规则是由语词表达的,而日常语言的含义是不确定的。这一点已为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研究所证明。
根据奥地利著名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语词的含义或意义是在人们使用它的具体语言环境中获得的,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语词的意义是不确定的。[15](P50)具体到法律的适用而言,未经法官解释的规则是无法适用的。
研究美国现实主义运动的美国学者加里·派勒教授将现实主义法学大致分成两个派别:“批评派”和“建设派”。批评派的代表人物有弗兰克、阿诺德等人,这些人强调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认为对社会生活的表述不可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解释。自由意志和强迫、公与私、人与社会的描述性暗喻是毫无条理的和语无伦次的,因为这种对立中的一方若无另一方的存在便没有意义。它们在主流活语中的关联性取决于它们与特定经验群体的实体化联系。这种实体化形成了这个神化(即被视为“私”的领域的社会关系由个人自由意志派生而来)的形而上的基础。[16]
根据上述《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些现实主义——答庞德院长》的那段文字,派勒教授将卢埃林归入了“建设派”,并且认为,卢埃林在许多方面是与对合同自由原则持否定态度的“批评派”存在区别的。因为卢埃林的论述所追求的不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所有陈述都是政治性的、带有偏见的,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而是要在语词之下可以达致的有形物中寻求新的表达方式。这种存在于语词之下的实在的、确定的现实的图式,暗示着一种围绕着共同和无差别的基础上重建法律知识的方法,以及识别和限制传统法学的批评者所发现的不确定性的方法。词语本身并没有确定的内容,因此,在具体案件中法官总是可以对纸面规则做出导致不同判决结果的矛盾解释的。[17]事实则是“确定的”、“有形的”、“可观察的”,是一个实然问题,而不是“应然”问题。简言之,事实是实在的和大量存在的,而不仅仅是语词所表达的话语的折射。
此外,卢埃林关于距离的暗喻又加强了含有独立于语词的物质的、实际存在的事实的图式。思想、规则和公式的语言上层结构既可以贴近事实,也可以远离事实;语词本身由于缺乏内容和确定性,因而是飘忽不定的。另一方面,事实、内容则是不言自明的,就存在于某处,因此,可以作为确定语词的准确性的指南。虽然语词因语言习惯而产生差异,但事实的存在却不带有这种社会痕迹。
根据合同自由原则的这一观点,这种解构式批评只适应于传统的形式主义法学。在形式主义法学中,对社会生活进行表述的法律语言和概念范畴因远离事实而变得过于概括和抽象。“旧的范畴太过宽泛以致于无法处理。它们容纳了太多异质的东西,以致于毫无用处可言。”[17]按照卢埃林的说法,在形式主义法学中,单纯的语词被视为似乎本身具有含义,而不是被看是作对真实的、可观察的经验因素的描述或表述。形式主义误将语词、规则、表述形式和话语当作现实的存在。正如庞德所批评的那样,形式主义者“拿着形式当事实,误把逻辑当生活。”[18]但原始事实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武断的过程,形式主义的法官拒绝将视野投向语词以外的事物从而导致了不确定性。[14]
解决办法就是缩小“描述范畴”,[14](P1250)使之与其所表征的实在内容直接联系起来,以保证法律表述范畴不与“生活脱节”。[14](P1223)将宽泛和灵活的可使具体案件具体对待的标准引入规范系统当中。[19]至此,卢埃林得出了与霍姆斯几乎完全相同的结论,即一般命题不能裁断具体案件。[20]
在卢埃林的概念中,法律论辩的不确定性是由于语言表达的法律范畴与它们所表述的背后现象之间缺乏一致性所造成的。[16](P1152,P1241-1242)司法判决意见声称阐明了判决理由,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官事后对其判决的合理性所进行的辩护,它们与案件的实际裁判过程并无必然联系。相反,判决意见旨在貌似有理、在法律上得体,而且其结论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对这种合理化的方法的研究表明,在疑难诉讼案件中,至少存在着两个权威性的前提可供法官选择;两个前提同时适用于眼下案件肯定矛盾、冲突。[14](P1239)换句话说,逻辑推理并不能解决案件纠纷,它只表明了所给定的前提的结果;如果存在着一个竞争的、同样具有权威的前提,那么,案件中就必然存在着选择;这个选择是需要说明理由的;这种选择只能作为政策问题来说明,“因为权威性的传统具有两面性或欺骗性。”[14]所以,卢埃林认为,现实主义者相信将案件和法律情境归入较窄的范畴是值得的,同时怀疑以语言表达的简单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常常涵盖不同的、并不简单的事实情形。[14](P1237)至此,卢埃林终于明确说出了其怀疑规则的理由和原因。
可见,不确定性仅限于语词本身,即传统法律技术中已有的权威性前提。假如人们集中关注案件中所呈现出的客观上可观察的有形的东西,便可以获得确定性,因为正是这些有形的东西决定了为法律范畴所模糊的真正的相同点或不同之处。因此,就法律活动根源于这些事实而言,可以视为确定的。法学研究就是要“寻求事实情境和结果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揭示何时法院会采纳相互竞争的某个前提而不是另一个”。[14](P1240)
建立在“事实情形与结果之间的联系上的确定性的图式或概念,揭示出一种将法律界定为追求某种社会政策的方法。尽管对待先例的标准权威技术为解释先例留下了大量空间或余地,但只有政策考量和面对的政策因素可以合理地说明以某种方式对相关的先例体系所做出的‘解释’。” [14](P1253)当然,政策焦点并不限于案件的正式当事人,“而且还关注规则对于那些不仅没有,而且也未被出庭的当事方公平代理的人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由于是可观察的,因而可以形成与单纯的思辩相对应的知识基础”。[14](P1255)
世界的真实的法律知识的基础是世界中可观察的、独立于主观因素的事实。与法律裁判有关的是事实与可观察的官方行为之间的联系。因此,人们应当关注司法和救济,而不是法理。就法律解释与这一联系相吻合而言,它表征了法律。法官的判决意见,即卢埃林所称的法官对判决理由的主观叙述,不过是一种模糊确定性的基础结构的上层结构。“他的理由是在行为之后作为解释说明而不是行动之前作为决定因素而给出的。[14](P1224)其行为并非由语词主观决定,而是由客观背景决定的。
这种独立于单纯语词的知识观念不仅取决于消除法律中的主观因素,例如,法官对判决意见的合理性所做的辩护,而且取决于抑制观察者所带进来的主观因素。在这一点上,卢埃林接受了庞德关于现实主义的说法,即“忠实于自然,准确记录事物本身,而不是人们所想象的或者所希望的事物”,是现实主义法学的一大特点。[21](P697)与此相反,“传统观点所依据的是语词。如果根本未言及行为,则暗示着假定语词实际反映行为;如果它们是表述法律规则的语词,则语词一定影响行为。”[22]卢埃林之所以指责兰德尔形式主义法学错误地表述了社会关系,乃是因为它用来描述这种关系的法律范畴,尽管声称反映现实,实际上却与“事物本身”不符。例如,形式主义法学家认为,合同自由意味着与所界定的胁迫的任何特征无涉,但他们这样主张时却将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存在混为一谈。因此,卢埃林公开声称现实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
为了研究而暂时区分实然与应然,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虽然价值判断在确立研究目的时总是有吸引力的,然而,在研究实然如何时,观察、描述和确立所描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应该尽量不受观察者的愿望的影响,不受他希望或认为(在道德上)应该怎样的影响。[14]
依据以上论述,卢埃林关于语言和表达习惯的概念图式将焦点由表征者或者符号转向被表征者(被认为不依赖不确定的和武断的表述习惯而独立存在的概念或事物)以期获得确定性。因为无论语词“树”的武断性如何,其意义总是根据存在于某地的带有树皮和树叶的可观察的有形物来确定或联想的。这里存在着一种默示假定,即对有边缘的有形物的“观察”本身并未镌刻着“语词”,未镌刻着确定一项特征或一种事物独立于其他特征和其他事物的社会语言。正如派勒所言,“在卢埃林所依赖的科学暗喻中,知识是经由消除语言的表征术语以达致被认为应当由范畴所表征的真实事物而获得的”。[16]
虽然承认构成我们称之为感觉印象的东西是无用的,除非以某种方式加以编排、整理;虽然承认“分类即为打扰”,[17]但这一观念是,存在着某些自明的、直接的经验,其中“观察”只是“感觉印象”。这一经验区别并独立于语言的分类过程。[17](P453)按照卢埃林所使用的暗喻,“原始事实”就存在于这一分类前的状态中。[17](P453)解释事实的社会过程,作为必要和另外的补充,是在“感觉印象”本身之后才出现的。在顺序上,感觉印象先于对事物所进行的区别的社会过程。[16](P1244)
在《现实主义法理学——下一步》一文中,卢埃林再次强调,兰德尔形式主义法学的不当之处在于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语词上。在该文中,他明确将对以语词为中心的法学研究或法律思维的批评与关于法律权利和规则的观念联系起来。卢埃林在回顾西方法制史时说,早期的法律思想视法律规则关注救济。正如语词和概念起初与实际存在相联系一样,卢埃林认为,法律规则起初也被视为与救济,与法院在具体情况下会做什么,与人们“可以观察到的东西直接相联系的。”[17](P436-437)然而,后来的法学家却以“目的”来看待救济,将救济视为对“权利”的保护。[17](P437)此时,法律规则被视为界定权利,救济则被视为只是实现权利的手段。正如随着语词和概念的实体化而失去了与真实世界的联系一样,卢埃林争辩说,权利和规则最终失去了与救济(其经验基础)的联系,并逐渐被视为流行于社会关系中独立于执行问题的实际事物。[17](P437-438)
卢埃林坚持认为,正像语词只有在能指可观察的事物时才有意义一样,权利只有从救济观之才有意义。[17](P438)就像语词所指的事物一样,救济是确定的,因为它是经验的、可观察的,而不像实体权利那样,“你既看不到它,它与事实也不沾边”。[17](P438)权利在没有转化为救济时是不确定的,其“形状和范围独立于偶然的救济。”[17](P438)所以,卢埃林主张,法学家的任务是“使权利和规则去实体化,迫使法律关注人造的东西(根据依法律声称既要管理也要服务的社会中于法律自身之外发现的更为重要的标准),可以批评、可以改变、可以改革的东西。”[17](P442)
以上分析显示,卢埃林的现实主义法理学通过将研究的重心从“语言”转到“行为”上,从而颠覆了传统的兰德尔形式主义法学。[16]他之所以怀疑规则,并非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要取消规则,不要规则,而是旨在将人们从对以语词表达的规则的沉溺中唤醒,以使人们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此外,卢埃林所怀疑的规则是与美国20世纪的物质生活条件脱节的、使布兰代斯在其著名代理词中已无话可说的传统普通法规则。遗憾的是,后来的学者对卢埃林所怀疑的这种美国的、传统的、普通法上的具体规则做抽象的解读,误解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三、强调行为研究的现实主义法理学
卢埃林非常重视寻找一种适当的法律研究的参照点。如前文所述,在他看来,规则从来就不应该成为法理学的研究重点;恰恰相反,如果法理学要想被归入社会科学范畴,就必须将行为作为思考的重点,尤其是将法律官员的行为和普通人的行为的相互作用作为思考的核心。更准确的说,卢埃林将“纠纷”置于法律研究的核心:“纠纷是法律永恒的核心。虽然纠纷的边缘并无标记,但它的中心总是有标记的。”②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卢埃林详细描述了此类法律事务,进而在描述过程中回答了“法律是什么”:
这种法律事务是关于什么的呢?它是关于这样一个事实的,即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实际的和潜在的纠纷;需要解决的纠纷和需要防止的纠纷;它们都有求于法律,都构成了法的事务。这种就纠纷所做的某种事情,合理地做的事情,就是法的事务,而那些负责做这些事务的人,无论他们是法官、行政长官、书记官、监狱看守,还是律师,都是法律官员。这些官员就纠纷所做的事情,在我看来,就是法律本身。[23](P2-3)
在《夏延族的习俗》中,卢埃林将这一研究重点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将他的思想集中在“疑难案件”的概念上。他认为,遵循这一探寻进路可以向任何一名社会学者阐明三个基本问题:(1)在一个特定社会中,谁实施官方行为?(2)获得了怎样的舆论支持或积极协助?(3)所给定的法律规范在何种程度上渗透到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
卢埃林表明,采用这一研究重点,法理学不应将精力仅仅局限于研究司法行为本身;在他看来,作为研究对象,其他官员的行为同样重要。在一篇早期的文章中,他曾这样写道:“法律研究的重点,法的核心,不仅仅是法官所做的对利害当事方产生影响的行为,还包括任何政府官员所做出的官方行为。”[17]然而,尽管卢埃林在研究夏延族的法律习俗时的确拓宽了研究重点,可是,当他将注意力转向美国现代法律制度时却没有明确地保持这一焦点。更令人遗憾的是,卢埃林在法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上言行不一,这是他不遵守自己曾极力鼓吹的戒律的又一例证。事实上,卢埃林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很少考虑那些被他置于现实主义法理学核心的因素。即使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法学事业的巅峰之作《普通法的传统》中,他依然随法律现实主义之波而逐流,固执地坚持仅对司法裁判例进行研究。琼斯教授对这种狭隘的法学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30年后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现实主义者的学术研究逐渐集中在司法过程上,只是偶尔才涉及到非司法官员的工作,几乎不涉及官方行为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的领域。”③
对于卢埃林放弃原则所可能给出的解释是,尽管“纠纷”是研究相对简单的社会制度(如夏延族印第安人的社会制度)的最佳焦点,但对于一个复杂的现代法律制度进行富有成效的考察,它便成为一个笨拙的工具了;当法学家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缺乏适当的概念把握时,则尤其如此。当然,这种解释不一定令人信服地说明卢埃林为什么忽视那些他曾频频宣称为他的现代法学研究纲领的核心问题。
尽管卢埃林在《棘丛》中曾经提出“这些官员就纠纷所做的事情,在我看来,就是法律本身”,[23](P2-3)但他始终尽量避免给法律下定义,然而,这个本非概念性的主张却被分析法学派当成了卢埃林给法律所下的定义,而这样一种“定义”在分析法学流行的普通法国家几乎成了一大笑话。[24](P276)实际上,许多人“既不阅读《棘丛》的上下文,也不阅读其余内容,这个句子,在国际上,被频繁引证以用来丑化现实主义”。[23](P2-3)难怪卢埃林对此忿忿不平,而在《棘丛》再版序言中将这种喧嚣斥之为“茶壶里的暴风雨”。[23](PX.)
其实,与其他现实主义者相比,卢埃林对于法律的实施与对法律的看法的强调恐怕更为平衡。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作为对一味偏重规则和概念研究的传统法理学的反叛,毫无疑问,卢埃林所强调的是法律的“实施”。正如卢埃林自己所说的那样,“现实主义者想与之打交道的是事物,是人,是有形的东西,是明确有形的东西,以及明确有形的东西之间的可观察的关系,而非仅仅是语词。”[14]尽管如此,卢埃林对待法律规则和概念的态度仍然有别于那些极端的行为主义者,他没有将法学贬低为纯粹物质行为的记录,也并未忽视社会进程中相关主体赋予它的意义。他所主张的是这样一种法学,它截然不同于摩尔等人的以严格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指导的法学。因此,卢埃林避免了曾使摩尔的大部分法学事业深受其苦的行为主义谬论,在重视法的动态和静态方面取得了较为充分的平衡。
正如我们从对卢埃林的研究重点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卢埃林坚信法理学必须以经验法律科学为基础才能牢固地确定下来。他的早期作品十分强调科学观察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尤其注重法律官员的言语和实际做法之间常常存在的巨大反差:
首先,尤为突出的是,官员的言语和做法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东西,而是实际所发生的事情,才是应该关注的核心。既不是任何法律规则的目的,也不是官方行为的目的,而是这一行为本身的类和质才是应当关心的主要内容……我们仍然首先关注的是官员所实施的行为及其后果(假如他们行为时所说的话起作用,当然也包括他们所说的话语)。④
这段文字清楚表明了卢埃林对于研究司法行为的迫切呼吁,但他并未主张必须同时放弃对法律规则和概念的研究。即使在30年代当他为现实主义法学摇旗呐喊时,卢埃林也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人们研究法律规则和概念,只是当这种研究使人们产生一种虚假信念时,即规则和概念在客观真实地描述法院或人们实际在做什么时,卢埃林才予以贬低,乃至怀疑这种研究的价值。[14]
例如,在被视为现实主义运动的宣言——《现实主义法理学——下一步》一文中,卢埃林即对法律规则的性质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这一探讨表明,所谓卢埃林“怀疑规则”实为一种误解。“我要再次确认一下我不会被误解。第一,我不是在争论说实体法规则没有意义;第二,我也不是在争论说使用利益—权利和规则—救济分析并仍能清晰和有效地思考法律是人们所做不到的;第三,我更无意主张将实体权利和规则从法律中排除出去。”[17]可见,他并不否定法律规则,只是要澄清规则在司法程序中的实际作用。
在卢埃林看来,为了弄清规则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必须将规范性的法律规则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的纸面规则,即在现实中没有可观察到的对应物的规则。所谓“纸面规则”是指“传统上被当作法律规则的东西,是特定时空所流行的法理学说,也就是那里的书本上所说的‘法律’”。[17](P448)另一类是“奏效规则”,即在现实中存在对应物的规则,亦即被人们实际遵守了的规则,或者被法律官员有意识地实施了的规则。卢埃林虽不赞成传统法理学,但并不反对它对法律规则的研究,只是反对它混淆单纯“纸面规则”和实际上的“奏效规则”。不过,他并没有说明法学家应当如何着手去发现“奏效规则”。但这种分析却将卢埃林的观点与预测说和行为主义的观点区分开来,因为行为主义仅将法律规则视为法官通过某种既无意识、也未予以说明的心理过程而对之做出反映的刺激。[8]
当然,卢埃林在这篇文章中还强调了研究法官实际行为的必要性,并把法院的习惯做法,即某种“潜规则”表述成“真规则”,这引起了不小的混乱和误解。但非常清楚地是,卢埃林的概念体系,即使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也不排除对动态的法和静态的法进行平行研究。
应该指出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卢埃林就完成了《规则理论》一书的初稿。特文宁教授认为,这部手稿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的《普通法传统》,当然,它也进一步证明即使在现实主义运动早期,卢埃林也未忘记适当平衡静态法和动态法的研究。
保持这种平衡在卢埃林后期著作中已成为一个明确的主题。例如,1940年卢埃林在一篇文章中对法律规则预测说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是不恰当的。他写道:“新兴的法理学必须在法官的实际工作中设计出我们法律制度中理想和意识形态因素与表述法律规则的语言的关系;与法院和法官所从事的制度实践的关系。”[12]在《规范性、法律和法律职业:法律方法问题》[25]一文中,卢埃林又明确区分了“法律—习俗”和“法律—质料”,依然强调以追求一种综合的法理学为目标的学者必须对两者都进行研究。卢埃林的“法律—习俗”指任何具有明显法律特征、特点、内涵或效果的行为或习惯;他的“法律—质料”则指任何可识别的与法律相联系的文化现象,包括法律规则、任何类型的法律制度、律师、法律图书馆、法院、守法习惯、联邦制度。简而言之,所谓“法律—质料”,在卢埃林看来,就是文化中任何与法律有关的东西。[25](P1355,P1357-1358)正由于此,人们将卢埃林归入社会学法学家之列。
四、法律研究中“实然”与“应然”的界分
在《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些现实主义——答庞德院长》一文中,卢埃林列举了现实主义法学的九项出发点,其中一项便是暂时区分“实然”与“应然”。对此,他解释道:
暂时区分实然与应然是为了研究。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尽管在确定研究目标时价值判断肯定总是会有吸引力的,然而,在研究实然的过程中,观察事物、描述事物和确立所描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时则应尽可能地不受观察者主观愿望的影响,不受他希望事物如何或者认为事物(在道德上)应当如何的影响。[14]
这段话日后招致了诸多学者,尤其是自然法学家的批评。不可否认,现实主义法学在诸多方面的确应该受到批评。具体到卢埃林来讲,他常常夸夸其谈,言过其实,有时甚至前后矛盾。然而,就应然和实然的区分而言,批评者大多误解了卢埃林的观点,“即使像富勒和庞德这样成府老道的批评者都未能避免为事实—价值术语所诱捕。”[13]
卢文发表后,赫尔曼、坎特罗维茨、弗里德里克和肯尼迪等人迅速起来捍卫法律的更高秩序,尽管他们自己对法律实施中的缺陷视而不见,他们的批评中同样充满了不实之词。总的来讲,多数批评者认为,卢埃林关注司法裁判中对事实的分离或区分放弃了以一种坚定的方式决定法律制度的正确结构和裁判案件的标准的责任;他将研究限于事实,坚持技术问题至上,轻视法律过程和法律实质的规范性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无法加以经验研究的,这是一种罪过。一句话,卢埃林的法似乎是无道德的、几乎是无法无天的。[13]
在对卢埃林上述观点的批判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弗里德里克认为“卢埃林发现了奏效的东西,那是他唯一关心的,确切说,表面上似乎是这样”;[26]肯尼迪比弗里德里克更为尖刻,他甚至认为“这一具体的问题是……原则、先例、理性、自由意志和无私的正义力量和效力与情感、非理性、偏见、环境和对法律秩序的法律怀疑主义的影响之间的竞争”;⑤ 德国学者坎特罗维茨则指责卢埃林不承认说明、证成、法律、伦理、现实与意义在分析意义上是些不同的概念,进而得出结论认为:“现实主义者关于法的概念(他们的实质性论点)是,法律不是一套规则体系,不是一个应然,而是实际的现实,是某些人的行为,尤其是法律官员的行为,特别是通过裁判造法的法官的行为,正是这些行为构成了法律。”[27]
对卢埃林的批评最为成府老到、也最具影响的当属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富勒教授,他认为:“首先,现实主义者假定严格区分实然和应然是可能的;在脱离道德的背景下孤立地研究法律也是可能的。第二,他们假定,区分应然与实然是如此明显可取的事情以致于无须证成这种区分所需耗费的人的精力。第三,他们显然假定在实然未被科学地和撤底查明以前,对于应然所说的一切只是浪费时间,毫无价值。在我看来,这些假定都是错误的,就它们所受到的认真对待而言,它们对美国的法律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⑥
关于是否可以暂时追求这种目的,富勒持否定态度。他诘问道,当法律中的规范因素被暂时搁置时,用什么来规制法律的运行?现实主义者在所有这些“事实”中究竟要寻求什么?富勒认为,实然—应然的区分导致了卢埃林前后矛盾,左右摇摆。“当代现实主义者在思想上仍然没有搞清楚他反对概念主义究竟是因为概念主义未能使原则获得准确的形式表达,还是因为它假装压根就是依原则进行的。”[28]富勒断定说,实然与应然的断裂使得现实主义者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因为他不清楚他所开具的药方是迫使生活符合一套更为认真地得出的规则,还是要让规则让位于生活。[28](P461)
抨击现实主义法学最为激烈、也最为过分的当属自然法学家露西教授,她坚决反对卢埃林关于应然和实然的区分,并且耸人听闻地写道:“就现实主义我们不能不这样说:如果人只是动物的话,那么,现实主义就是对的,霍姆斯是对的,希特勒也是对的。”[29]
从以上引述的批评来看,有些显然是未经深入研究而仓促提出的,是基于对卢埃林著述的错误的假定。首先,批评者假定卢埃林的根据有误,即抽象的规则并不能完全表明适用于解决法律纠纷的真正的规则;规则未能说明抽象原则对具体情形的实际适用。第二,他们假定卢埃林唯一感兴趣的是具体法律诉讼中所实际发生的事情;他认为对行为的考察与关于法的目的的具体观点无涉。第三,批评者还假定,在批评中概念思想提供唯一的真理判断标准;应然必然与实然完全不同。卢埃林自己强烈反对前两项假定,对于第三项我们还须单独进行分析。
其实,卢埃林为自己确立的任务或目标根本就不是忽视应然,甚至也不是在实际司法裁判中区分应然与实然。相反,他要在探讨过去的事件和案件中区分孤立的资讯和问题。按照批评者的说法,卢埃林的错误在于他相信,对法庭上的事实或上诉案件简介的静态分析可以在无价值判断或“客观”的状态下有意义地进行。[13]
但事实上,卢埃林关于实然和应然关系的立场和观点完全被他们误解了。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卢埃林只是提出了一项为现实主义法学家所普遍认可的前提。当我们将这段话与被认为是卢埃林等现实主义者所持有的假定进行比较时,则显示富勒等人的批评并无道理。我们知道,卢埃林是位具有强烈改良主义倾向的法学家,竭力鼓吹司法改革。他主张暂时区分“实然”与“应然”只是为了观察。与兰德尔不同,卢埃林认为法律是一种经验科学。这里卢埃林只是在使用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类似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即为了理解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实施的,有必要对现实司法过程进行客观观察;为了获得客观的结果,就需要搁置价值判断,或者如胡塞尔现象学所主张的那样,将主观的东西用括号“括起来”。卢埃林虽然在《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些现实主义——答庞德院长》一文中将区分实然与应然作为现实主义的出发点之一,但他同时强调这种区分只是暂时的,并且“仅在调查事实过程中”,而且是为了研究的需要。他认为,实然与应然的区分是不可避免的,对进行清晰的法律分析来说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动态的司法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裁判者的伦理价值乃是法律的重要渊源。[30]可见,卢埃林主张暂时区分“实然”与“应然”只是为了观察和研究。作为经验科学而不接受这种区分是不可想象的。这与分析法学拒不承认法律与道德有联系的观点是不同的。
事实上,富勒过去在他的著述中也曾使用过这种方法,而且还表现出与卢埃林近似的观点。例如,富勒在《法律拟制》一文中写道:
在结束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需要指出的是,区分发现社会生活(描述性科学)事实的过程与确立治理社会的规则(规范性科学)的过程,并非总是简便易行的。许多看似严格的法律性质和规范性质的东西,事实上只是一种表达,不是人们的行为规则,而是关于社会的结构的意见。人们必须确定现实怎样之后才能睿智地决定应该怎样。不过,在实践中,这两个过程是融为一体的,难分彼此。[31]
富勒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为了获得令人信服的客观观察结果,科学研究是可以暂时区分实然与应然的。至于实践中人们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则是另一个问题。因此,他对卢埃林关于“实然—应然”的暂时分离的批评如不是误解的话,则一定是他自己改变了先前的观点。
其实,卢埃林所说的实然(Is)和应然(Ought)并非分析法学意义上的道德与法律或事实与价值,而是指法律规则的规范效力与实际效力,即纯粹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凯尔森所说的“规则的法律效力与实际效力。”对此,琼斯教授做出了很有见地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卢埃林想要保留的分析性区分,与其说是分析法学意义上的学理实然与道德应然的区分,不如说是动态的法的实然(法官的实际做法)与书本上的(或静态的)法的规范意义上的应然的区分。”[32]当卢埃林坚持认为现实主义者没有规范性纲领时,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所有现实主义者都不关心法律中的道德因素,而是说完善法律的方式取决于充分了解法律的运行。[14]
由琼斯教授的分析可见,卢埃林所说的实然(Is)和应然(Ought)与分析法学所讲的法律与道德、事实与价值根本不是一回事。富勒作为一名自然法学家,自然见不得Is与Ought的分离,犹如唐吉珂德见不得风车一样,他在批评卢埃林时并没有深究卢埃林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的Is和Ought。果不其然,后来当哈特主张Is和Ought分离时,他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哈特。⑦
事实上,卢埃林不仅不反对法律表现道德,而且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他写于大危机期间关于瑕疵担保的论文⑧ 和后来起草的《统一商法典》中关于诚实信用和显失公平的规定,均极富道德色彩;他草拟的突破合同关系而将瑕疵担保扩大到第三人的条款,恰恰由于过于先进、过于道德而遭到商界的强烈反对,并最终被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和美国法学会所否定。
以上分析表明,诸如富勒、露西等自然法学家批评、指责卢埃林不讲道德,在法律研究中偏离价值并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充分理由和依据。
五、对法律的形成与功能的现实主义考察
(一)法的形成
卢埃林相当谨慎地描述了法的两个方面,即我们所称的“权威”和“控制”,但他不是将“权威”和“控制”作为两个独立的概念来看待的,而是将它们合成为一个单独的简明概念——权威。卢埃林的这一法理学思想的形成相对较晚,具体来说,是与霍贝尔合作时形成的。
卢埃林认为,所谓“法的”(the legal)这一术语预设了一个“社会意义上的规范性归纳”过程;一切社会意义上的规范性归纳,从渊源上讲,都产生于一个群体的纯粹生活的永恒过程;从构成上来看,这一归纳过程包括其精确性和概括性程度不同的“权利模式”的表现和反映。按照卢埃林的说法,这一过程取决于以下两个关键因素:“强烈驱向这种社会意义上的规范性概括的一个因素,可以视为是量的。如果相互联系的行为事实上形成模式,同时引起行为和预期的反复调整,那么,背离这一行为模式将会令人烦恼;关于正当性和权利的可概括的情形则肯定会出现。驱向这种社会意义上的规范性概括的第二个因素,可以视为是质的。疑难案件的压力、惊人的、难忘的戏剧性及其劳神费解,尽管它完全是特殊的,均以其全部的质驱向概括;如果该疑难案件成为意识到和表达已经暗中积累的规范性驱动的场合,如同许多疑难案件那样,则这种情形便会成倍增加。”[25](P1335,P1360-1361)
然而,规范性概括只是有助于构成“法的”东西的一部分。卢埃林指出,此种归纳、概括必须以某种方式被人们所接受,并对人们的行为有所影响或者与人们的行为一致。“它绝不会仅仅如此;而且已超出应当之规范性而进入必须之命令中。‘法的东西’必须与受到挑战时将会取胜的习俗和标准有关。……重要的是看到出现法的结构的可能性……这种结构自己宣称自己的各种应当性,而不过问其任何部分或全部影响的固有的正当性或正义性:对遵守、服从、权威以及有效性的诉求,因为,并且只因为,它是有关整体的公认的现存秩序的有效表达。”[25](P1364)
换句话说,就法律与“权威”和规律性相关而言,它是一个已经形成模式的规范性概括过程。卢埃林发现了可以综合为一个关于“权威”的简洁概念的四种特点。“第一,在有关整体中,且作为其一部分,存在着有效性的必要因素,即对命令或法令或疑难案件的处理存在着一定量的事实上的服从;第二,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因素:必要时,法的东西必须优于与之竞争的标准或权威;第三,存在着实施、制裁、可用来对付挑战者的明显的强制因素;第四,就所做出的、所命令的、作为命令或规范所确定的事情是有关整体的现行秩序的一部分,存在着承认因素;不仅仅是接受,还有为什么会接受的原因,即官方因素。”[25](P1367)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卢埃林试图揭示法产生或形成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但他从未完善这一分析以使之适应现代法律制度的经验性研究。事实上,他和霍贝尔所使用的具有谣传性质的资料意味着,其分析与其说是经验的不如说更多是推测性的,即使对于印地安人的原始法律制度也是这样。尽管如此,卢埃林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法的本质仍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二)法的功能
“法律进程和社会进程的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在于行为领域,这是无须证明的。”[17]自伊始起,卢埃林就着重强调有必要对法律与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考查。在他早年发表的《守法对执法》一文中,他就提出了庞德等学者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的学说具有局限性的观点。“法律若要得到普遍遵守,则要求首先形成符合法律目的的习俗。人们熟知的是习俗,而非法律,在我们当前对事务的安排中向学习和遵从的人们提供某种保障的也是习俗,而不是法律。”⑨ 而且,一旦人们明白遵守法律是习俗问题而非规则问题,就一定会意识到这些规则和习俗并不统一,在不同社会阶层是有差异的。因此,卢埃林认为,任何执法问题都必须视为一个改变某些特定个人的行为模式的问题。这一观点成了他后来在许多场合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思想。
卢埃林关注法律进程和社会进程的关系,在他的一篇文章《作为制度的宪法》一文中得到了证明,在这篇颇具启发性的文章中,卢埃林对美国宪政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功能分析,他不是将宪法仅仅视为一个法律文件,而是当作一个“有生命的制度”来对待。“一项制度首先是一套生活和行为方式。首先,它不是语词和规则问题……每一部活的宪法都是一项制度,只有当它是制度时,它才会有生命力。”[33]从卢埃林的观点来看,任何运行中的宪法,都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制度,最有裨益的是将它视为三类各异的人们的不同习俗和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1)从事管理的专家;(2)利益集团;以及(3)普通民众。在这些集团当中,卢埃林认为,从事管理的专家处于整个进程的核心。然而,他并没有继续从事这一分析,直到与霍贝尔合作时,他才真正地将这一探索性的制度方法发展成为一种充分综合的关于法律在社会中的功能的理论。[34](P253,P261-262)
卢埃林虽没有专心于研究结构因素,但他形成了关于社会制度的观念,因此,强调法的功能。他这样写道:“制度的核心是有组织的活动,即围绕着清理某些工作的组织活动。在主要制度(法律制度只是其中之一)方面,相关工作对于社会或群体的继续存在乃是至关重要的。”⑩ 卢埃林的基本观点是,假如一个群体要想生存下去,则其任何社会制度或亚制度都有某些必须予以满足的基本需求。卢埃林对法律目的的表达可以在他列举的五项所谓“法律—工作”中找到。在《我的法哲学》一文中,卢埃林将这些工作表述如下:
(1)对疑难案件的处理:过失、冤情、纠纷……
(2)对行为和预期的预防性疏导以期避免纷争,同时,以相似的方式对行为和预期进行有效的重新定位。
(3)分配表明行为具有权威性的权力并设立相关程序,这包括制度的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
(4)法律的工作的积极方面,这样被看待且并非从细微处着眼,而是从最终的整体上看: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最终的组织,以便提供整合、方向和激励。
(5)“法学方法”,用句口号来概括以下任务:处理和形成处理法律材料和人们为其他工作而开发的工具的有效传统,以期这些资料、工具和人们会一直做得更好,直至他们成为揭示新的可能性和成就的源泉。(11)
所有群体都发展出其职能系执行法律工作的制度。按照特文宁教授的理解,卢埃林晚年所使用的“法律—治理”术语指的就是这种机制。[7]“每一项‘法律—工作’都主要表现出‘纯粹—生存’的一面。这一任务必须执行得足够好以致该群体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但在这一基本方面以外,每一项法律任务还有一个‘探求方面’。一方面,‘探求方面’寻求更为有效的履行‘法的任务’;另一方面,它又在追求理想价值:组织形式和正义的理想能使生活更充实、更富足。”[6](P292)不过,卢埃林拒绝将这种终极理想作为他合法的研究对象。因此,他在谈到“法律—工作”的“探求方面”的第一个因素时便嘎然而止了。
除了“法律—工作”之外,卢埃林的《夏延族的习俗》一书中一个更引人瞩目地方是,它集中关注那些引起需要权威性决定之情形的事件。卢埃林强调理解多种矛盾冲突的必要,这些冲突、张力造就了法律并在权利主张中表现出来。根据卢埃林的观点,对权利主张的调查与研究揭示出许多与任何特定权利请求人所可能代表的关于社会群集的东西。认识到研究这种促成事件以及权利请求过程的必要性,对于我们理解法律进程与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贡献。
卢埃林逝世后,他的合作伙伴霍贝尔教授概括了他关于法律与社会的基本观点。“卢埃林是将法律和社会中的法律视作一个过程来看待和研究的。社会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形式只存在于变动不居的持久的行为关系中。关注法律—工作,作为理论—方法的一个特点,具有将法律(如社会—文化制度的所有其它组成部分一样)作为一个‘分制度’而与整体联系起来的优点。对于这位法学家来说,这是给将法律及其原理视为自成一体的法律中心主义倾向开出的一剂强有力的解药。但对于40年代的人类学家而言,它的价值是将法律直接带入人类学中不断壮大的功能主义思潮中。”[35]
虽然卢埃林关于“法律—工作”的理论的确说明了法律制度所执行的基本功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一理论还很难充分说明法律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我们知道,由于卢埃林未能将其疑难案件方法运用于运行中的法律制度,因此,他不得不回避许多关于社会结构和法律结构的关键性问题。此外,只关注法律的功能还导致他忽视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社会中所存在的控制模式以及理想和目的对制度发展的影响。[8]总之,卢埃林的概念框架是不充分的。如果人们认为社会进程在本质上是由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那么,显然一个系统的法理学必须能够将法律对资源的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概念化,并对此进行衡量,反之亦然。这一点恰恰是卢埃林的法理思想所未予考虑的。[8](P463)
卢埃林对待法律和社会过程的关系之所以存在以上问题,有学者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论述过于抽象。也正是这种过度的抽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卢埃林无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一个不断发展的法律制度。然而,这也是卢埃林很少检验严格的实地工作的结果。没有对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的日常认知的刺激,他的理论的表达形式也只能变得越来越抽象。[8]不幸的是,正如特文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卢埃林对于系统的实地工作恰恰并不热心:
就社会—法律研究而言,卢埃林与其说是步兵,不如说是参谋。不论是从性情上还是从所受过的训练来看,他都不适合于从事系统的资料搜集工作。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数学盲,并且对数学知识有些担心。一般而言,他几乎全凭头脑来写作;即使为了寻找相关权威判例而去查阅判例汇编这样普通的辛苦准备工作对他而言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尽管他常常严格要求自己去做;在方法上他并不足以成为一个拿手的实地工作者,尽管他的“艺术家”品质有时也能产生出惊人的结果。他打破了经验方法的多数规则,惊心设计的研究方案、严格的取样技巧或者一丝不苟地检验过的调查问卷对他自己都不适用。在写作他的主要著作时,他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在这种实地工作上花费多少时间。他在夏延族部落里只呆了10天,而其他材料的搜集工作是由霍贝尔完成的……只有一个重要项目,即对普韦布洛印地安人的研究,他确实做了不少实地工作;然而,他不仅没有保持超然的观察者的身份,反而对普韦布洛印地安人的事务逐渐动起情来,并积极介入其中。不过,这个项目从未完成,这恐怕不是一个巧合吧。[4](P193-194)
不管怎样说,卢埃林在探讨和挖掘法律与社会进程的相互作用方面要比其同时代的多数学者走得更远。他的努力之所以最终未能成功一个原因是,他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这种相互作用的一个方面上,亦即“法律—治理”的功能上。琼斯教授则更为宽容,他还从客观上去找原因,认为当时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智力支持与勉励不足兴许是另一个原因。[8](P465)
结语
1930年卢埃林在《哥伦比亚法律评论》上发表了极具影响的论文——《现实主义法理学——下一步》,[17]号召美国法学界摒弃传统的形式主义法学,积极采取现实主义研究方法。论文发表后引起了美国学界的广泛兴趣。1931年他又在《哈佛法律评论》上撰文——《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些现实主义——答庞德院长》——反驳庞德对现实主义的指责。[14]一时间,卢埃林名声大噪,一战成名,成了现实主义运动的代言人,头号现实主义者,[36]而他的《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些现实主义——答庞德院长》也被广泛视为现实主义运动的宣言书。
对于现实主义运动的这样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国内外学界向来褒贬不一,分歧甚大。一方面,卢埃林那常常言过其实的夸张表达,给分析法学派留下了把柄;而其强调客观观察的观点又成了自然法学派批判的对象。然而,仅仅分析卢埃林的只言片语,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现实主义法学思想的。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要真正理解卢埃林,就必须把他的思想放到美国法学界当时反叛传统法学范式的宏大背景下来考察和分析。
兴起于19世纪末、一心要把法律变成如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的纯粹科学的形式主义法学已经不能适应20世纪美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了;作为一种法学范式,形式主义已经基本丧失了指导法官从事“解迷”活动的正常功能。(12) 为了推翻这种传统法学范式,现实主义运动应运而生,这正是为什么卢埃林等现实主义法学家的论述很少离开其批判的对象的原因。脱离形式主义这一背景,不仅卢埃林不可理解,整个现实主义运动都难以理解。
在现实主义法学的猛烈打击下,形式主义遭到了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并最终为人们所抛弃;“形式主义”也因此而成为一个贬义词积淀在美国法学术语中。现实主义法学虽然颠覆了形式主义法学,但从总体上来讲,它并未能提供一个取而代之的崭新范式。然而,平心而论,“现实主义法学对于一个病态的、骚动不安的社会来说是一剂良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正是这样一个社会。但是,对于一个稳定的文明社会来讲,尽管现实主义具有解放人们思想的优点,却是不能当饭吃的”。[37](P453)因此,人们没有理由因为卢埃林等现实主义法学家未能最终解决美国法学的“吃饭问题”而对他们吹毛求疵、横加指责。因为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本来就只是“治病、疗伤”。那么,他们的这一任务又完成得如何?从约瑟夫·威廉姆·辛格教授发自肺腑的“我们现在都是现实主义者”[38]的自豪表白中可以看出,卢埃林等现实主义法学家毫无疑问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收稿日期:2009-01-30
注释:
① K.Llewellyn,Law in Our Society II,unpublished manuscript quoted by W.L.Twining in 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5.
② Llewellyn,Legal Tradition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cited in Simon N.Verdun-Jones,The Jurisprudence of Karl Llewellyn,Dahousie L.J.1(1978),p.79.
③ H.Jones,A View from the Bridge,Law and Society,cited in Simon N.Verdun-Jones,The Jurisprudence of Karl Llewellyn,Dahousie L.J.1 (1978).
④ Llewellyn,Legal Tradition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cited in Simon N.Verdun-Jones,The Jurisprudence of Karl Llewellyn,Dahousie L.J.1(1978)pp.80-81.
⑤ Kennedy,My Philosophy of Law,in My Philosophy of Law:Credos of Sixteen American Scholars,cited in Casebeer,Escape from Liberalism,Duke L.J.3(1977)pp.677.
⑥ Fuller,The Law In Quest of itself,cited in Moskowitz,The American Legal Realists and An Empirical Science of Law,Ill,L.Rev.(1966).
⑦ See Hart,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Harv.L.Rev.71(1957); Fuller,Positivism and Fidelity to Law-A Reply to Professor Hart,Harv.L.Rev.71(1957).
⑧ See Llewellyn,On Warranty of Quality,and Society,Colum.L.Rev.36(1936); Lelwellyn,On Warranty of Quality,and Society:II,Colum.L.Rev.37(1937).
⑨ Llewellyn,Jurisprudence,cited in Simon N.Verdun-Jones,The Jurisprudence of Karl Llewellyn,Dahousie L.J.1(1978).
⑩ Llewellyn,Jurisprudence,cited in Simon N.Verdun-Jones,The Jurisprudence of Karl Llewellyn,Dahousie L.J.1(1978).
(11) Llewellyn,My Philosophy of Law,cited in Simon N.Verdun-Jones,The Jurisprudence of Karl Llewellyn,Dahousie L.J.1(1978).
(12) 根据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托马斯·库恩的理论,范式的基本功能是指导科学家从事常规科学活动,即“解迷”。See 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