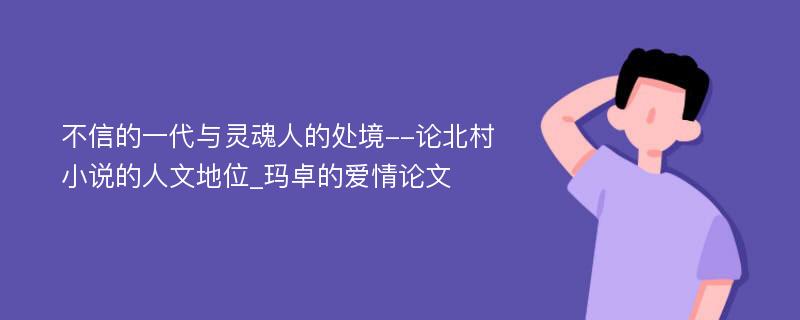
不信的世代与属魂人的境遇——论北村小说的人学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信论文,境遇论文,世代论文,人学论文,北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已多次评论过北村,它其实是我对北村小说的一种倾听和回应。这次我有再谈他小说的愿望,是起源于我对自身境遇的关怀。我许久以来都对我与文学的存在怀有一种本质缺席的恐惧,存在与本质的分离是可怕的。萨特说:“人的本质就是他的存在。”这是一句让人绝望的话。它的意思是,除非人能使自己成为所要成为的人,否则他就没有本质可言。萨特在否认了人有自救的可能的情况下,还把他的存在主义称为人道主义,就意味着他知道人的本质是什么,而这种本质又是人的存在,可见人创造了自己和自己的本质。每一位思索存在意义的人,都会遭遇这种悖论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人失去了该有的存在地位,文学也失去了关怀人的基本起点,长期被语言与形式的问题所代替,人无法再作为最重要的问题在文学中得到表现,到卡夫卡笔下,人卑琐得像虫豸一样地活着。我想起在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和启蒙运动时代,人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到现代人却悲观绝望到了如此地步!人的自我神话已经破产,我们很难再信靠自己以达到什么,因为以人为中心的一切都可能是虚假的,人脆弱到一个地步,会在丰富的物质面前出卖自己的人性与尊严。人类这条精神颓败的流,起源于自我,也终结于自我,对这一悲剧性的揭示,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世代思想文化界最重要的问题、唯一的问题。
1.魂的末世景象
人类的困境不在于自我不够发达,乃在于失去了一个更大的存在者的保护,失去了对自身内在危机的正确认识。人们普遍以为,当下人类所遭遇的危机也不过是思想与世界观的危机,它比肉身的灾难要内在、严厉得多。人肉身在地上生活、行动,都源于内心那套先存的观念所支配,这种观念是他作决定的根据。人的观念与他的情感、意志构成了人的位格(person),即人位。人在自己的人位里活着,这个范围就是人的魂(soul)。魂以肉身为载体。肉身就是体(body),就是人与这物质世界往来的部分;魂是人的天然生命,包括思想、情感与意志;此外,人里还有一个比体、魂都更内在的部分,那就是人的灵(spirit),灵里有良心、直觉与交通,是人与终极存在(神)相通的器官。灵是动物所没有的,所以动物不能敬拜神,而人却有崇拜的需要。灵把人与动物严格地分离了开来。中国人习惯地将人分为灵与肉两个部分,如果我们对人有更内在的认识,就知道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是一个三而一人。作出这个区别是相当重要的。若不把良心同思想、情感、意志区别出来,我们依旧无法知道人到底匮乏什么,无法知道思想危机的本源是良心的危机,即道德与正义感的危机,信仰的危机。
人有体比较好理解,但许多人不承认人有灵,都以为良心与直觉是知识积累到一个地步后正常有的感觉,依旧把良心所下的价值判断理解为是一种理性的判断。其实,灵(良心)不是一种理性,也不是一种非理性,它是生命本身,它呼唤正义、圣洁和爱。一旦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人就丧失了灵的品质,会在没有自尊与神圣品格的境遇下卑贱地活着。良心从来不会死,只会昏睡,它如果与周围的生存世界冲突到一定限度,人就会痛苦,以致于死亡。即使不愿死的人,里面也有自责,自责的程度表明的是良心觉醒的程度。
许多作家的写作并不具有良心这一维度,他们所抵达的也不过是魂的限度而已。在魂的立场上是无法找到终极价值的。终极价值就是灵所表征的价值,合乎良心标准的价值。魂(心思、情感与意志)只能出示一种对终极价值的猜想,无法与之达成一种真理上的和解。中国典型的属魂的作家主要有三类,一是韩少功、史铁生、格非和后期的王安忆等人站在思想的立场上写作,他们相信自身的智慧,是一些智者与思者;二是张炜、苏童、陈染、林白等人站在情感(表现为感觉主义)的立场上写作,小说中充满的是自渎的经验与自恋主义情结;三是张承志站在意志的立场上写作,他相信自己所建构起来的那种英雄主义式的强悍人格,所以他欣赏鲁迅那种以恶抗恶的方式。这些属魂的作家我又把他们称为属血气的作家,因为“魂”与“血气”(blood)这两个词在希腊文里都代表人的性质。
就此,北村曾说:“能写作的人都是属血气的人,而且是血气很旺的人,血气只会弄瞎人的眼,以致于全身黑暗。他以为自己能写尽人世沧桑与苦难,却不知觉自己是盲者。”〔1〕北村与前面那批作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站在属灵属乎良心的立场上写作。良心的品质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品质。即使在最冷漠的加缪与博尔赫斯那里,我们仍然可以体验到良心在那个时代里的痛苦经历。良心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在解读北村小说之先,我要强调良心(conscience)与魂(soul)这两个重要前提。我不是说中国小说中北村是唯一的,我甚至也常常为北村小说中一些艺术粗糙的部分,和一些人物模式及细节的雷同感到愤怒。但我注意到了北村的人学立场的独特性,以及那些人格所代表的精神向度。北村小说中所有的悲剧都是魂的悲剧。
什么是魂?魂就是灵与人的体相遇时所产生的人位,是人的自觉。我们会感觉到有一个自我的存在,这就是魂。魂就是我们人格所涵括的,凡我们人格所包含的那些叫我们成为人的要素的,都是属乎魂的。我们的智慧、心思、理想、爱情、意志、逻辑能力、判断力等,都是在魂里。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灵,是我们的真我,魂完全代表我们这个人。所以,圣经创世记称亚当“成了一个活的魂”。(此处中文和合本圣经把“魂”翻译成了“人”,是不合原文的)魂里除了有思想、情感和意志外,还有魂的生命在,这生命就是人天然的生命,这个生命最初受灵的管治,二者和谐一致。当人堕落之后,魂就膨胀起来,成了一个独立的自我的生命,并拒绝灵的引导。人类首先从神治堕落到自治里,用良心来管理自己,以亚当为代表;后来,人类的精神继续衰败,借着该隐的杀人再次从自治里堕落到人治里,这时城邦出现了,列国也随后起头了,到摩西在西奈山颁布法律,这一切都是为了约束独立的魂。
人类的所有困境都在魂里。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人类承认有一个终极信仰,承认以神为本位是人生存的凭据,这就表明,那时的人类在良心里还有一个敬畏的对象。到文艺复兴之后,人本代替了神本,人成了最高的存在,魂的生命便彻底失去了约束。人文主义者都说:人可以使自己伟大,人要从大自然中释放自己,最后的胜利终属于人。魂是人的中间部分,它若失去了灵的引导,一定是接受体的引导,主动给私欲和邪情一个地位。从人文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人类到了一个思想黑暗、情感放荡、意志消沉的重要关头,这就是末世的魂,这个魂已完全黑暗,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人的魂重新获得信心和能力,并在盼望中活下去?
北村警告我们说:“我们必须正视人的罪恶及其在文化中的后果。如果缺乏神圣背景,人文精神的实践是不负道德责任的,在西方有海德格尔的附逆,在中国有周作人的妥协;如果不从良心的立场,尼采的人文精神就会实践为法西斯主义,让良心告诉我们,并让我们看见,尼采的发疯和那个发了疯的时代的关系。在奥斯维辛死去的是人性,不是神;当人性杀害犹太人时,人性就杀害了自己。”〔2〕我们讨论文学, 越不过这个大的精神背景。每一种伟大的写作,都必须先与某种精神背景达成和解,进而找到存在的支点,找到说话的理由,以此来构筑魂的系统。魂的说话是一种纯粹个人性的说话,它以自我为起点,又以自我为终点,是完全封闭在自身之内的,缺乏神圣、超越的价值。魂的失败在于这种有限的存在与无限的存在发生了分离,使得魂能够发起许多事,但魂的有限不能保证这些事达到完美并继续到无限。人文主义者共同发起了对神的政变,使人维持了一种短暂、虚假的伟大,最后酿就了人变成虫的悲剧。想升为高的必降为卑。尼采想使人成为超人,最后却成了疯狂的人,就是死人。
谁都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越过魂的大限。属魂的作家只能在克尔凯戈尔所出示的二分法——理性与非理性里写作,没有第三个地位让他站。北村最初也不例外。他早期的《黑马群》、《谐振》里都有一种理性的自信,他为人类设计的理想图景是一套新的理性秩序,由此形成的理念成为他写作的中心点。他从自己的魂(自我)出发,企图凭着理性为一切事物找到一个统一的答案,让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统一在一起,康德曾想用知识理性来统一,韦伯想用价值理性来统一,最后都终结在失败者尼采身上。尼采是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北村接受了尼采,以及他那人死了的学说,但北村又不能站在死人的立场从事写作。这样的矛盾使他选择了悖论式的生存,像加缪一样的荒谬,以此来取消人生存的合理性。非理性出现了,它使北村与同一时代的先锋作家一道,在作品中充满着各种黑暗的感觉与体验,写作不再是某种自信心的表现,也不再仰望什么,它演变成了一种对魂里黑暗感觉的辨析行动。到《逃亡者说》、《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归乡者说》,人的气味不断减少,剩下的只是对物象的迷恋。写作一旦失去人这个中心,游戏规则就诞生了。
魂的衰败(思想黑暗、情感颓废、意志消沉)不能再认识是魂的人,到此,魂成了一种自恋的魂。魂的自恋就是非理性。一个以魂的自恋作为位格的作家,他要么在智慧里,像格非;要么在感觉里,像苏童;要么在语言里,像孙甘露。而智慧是冷漠的,感觉是黑暗的,语言是虚无的。北村选择了语言,魂的自恋成了一种语言的自恋,它的表现方式是聒噪。聒噪就是魂失去了肯定一种真实的能力之后,用自身的能力借着语言在思想里创造一种幻想中的真实。《聒噪者说》、《劫持者说》中的一切都是似是而非的,北村甚至在小说中采用了一种互相映射的镜象结构,通过一种形式法则的构筑,使事实与事实之间互相辨析、互相解构。同样一个事实,北村会使它以几种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反复出现,每次都有变化,这时的北村实际上放弃了他的意志,他拒绝选择这几个事实中哪个事实是真的。这种魂的活动只在观念中成立,它拒绝与现实相遇。就像我们在毕加索等人的绘画中看到了“割裂的实在”,可它只在图纸上成立一样。这种非理性的风暴加深了理性主义的悲剧。理性的时代还追求一种统一,到非理性,散乱、割裂、幻念代替了统一的世界观。人与理性分离之后,就成为一个无人性、无道德价值观的人,所以,“者说”时期的北村眼中只有语言及由它派生出来的游戏规则,没有人,语言成了作家的魂唯一投射的地方,这样的投射最终取消了作品中人物作为魂的存在。没有人只有语言的世界是可怕的,它是作家自我怀疑到了极限的表现,在语言里,北村根本就生活在疑幻疑真的世界里,有好几年时间,北村根本就分辨不清自己是生活在真实里还是活在幻景里。这就是迷津格局。迷津为魂提供了一个自足的系统,使它在理性与非理性这两条道路上都失败之后,满足于一些没有生命力的字词在游戏与聒噪中不断生长,膨胀。末世的魂拒绝关涉生命、情感与人性,末世的魂是一个冷漠的魂,迷津中的魂。末世(The end of the world)不是一个世代的终结,乃是所有世代的终结,在末世里,魂要遭受非常的痛苦。
2.属魂的人
在末世,所有的痛苦都堆积到了属魂人的身上。(属体的人不在我的讨论之列,因为他们的灵魂已经死去。)属魂的人就是凭魂而活的人,在人的三部分中,魂显得特别强大,生存完全受自身思想、情感与意志的引导。在这个末了世代、不信的世代,人总是喜欢挖掘自身魂的潜势力,从宗教方面说,佛教、道教、印度教、巴比伦人等,都在想尽法子,使魂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有了气功、参禅的盛行,气功的目的就是要使肉身顺服魂,使魂里掩藏的奇异能力被发现出来;从科学方面说,自从1778年,马斯麦尔主义开始后,心理学、精神学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心理学就是魂的学。各国的“心理学”这个词,都是从希腊文里得来的,不过是将魂(psuch)与道(log'os)两个字并起来,“魂”译为心理,“道”译为学,魂的学就成了心理学。
属魂成了每个人的精神境遇。魂是独立的生命,它要自己喜乐、自己痛苦。这样的结局相当严重。属魂的痛苦还在于魂与肉身(就是我们的体)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人离开了灵的管治后,魂就与肉身结盟,落到罪恶与痛苦之中。魂是一个人位,必须借助肉身来发挥它的能力。魂是我们的生命,肉身是我们的性情,性情乃是生命的自然原则,也就是生命的倾向与爱好,我们凭魂而活,就定规随着肉身而行事为人;肉身定规如何行事,魂便发出行事的能力;肉身(罪性)出主意,魂(生命)执行,这几乎是每个人的生存光景。
作出以上的分析是必要的,它是我们进入北村后期小说的解码口。否则,我们将难以理解《施洗的河》之后的北村,为何对在小说中建立人格,并对人格作出存在意义上的分析充满着热情。北村写作《施洗的河》、《伤逝》、《玛卓的爱情》、《水土不服》这些小说,重要的不是给了故事以地位,乃是给了人以地位。但北村要恢复的不是一套关于人的观念(那是人文主义学者做的),乃是恢复人本身。当然,文艺复兴之后,人走向了绝望、颓败,北村并不能从自身给出一种力量,使人从绝望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但同样是绝望的人格,在《孔成的生活》时代,作者是同孔成一同绝望的,那种迷津格局中的迷津人格,代表的是一种迷乱的价值观,进入这样的小说,读者只会与作者、人物一同陷落。必须获得一种新的动力与新的精神,使我们与人物的绝望境遇发生分离,不能只停留在对绝望的体验中,要在体验中获得一个悲悯、审判的精神立场,那就需要作家具备一种属灵的思想、良心的判断力,只有这种思想与判断力能够与绝望的魂相分离。魂的绝望在于魂无法满足良心的要求。
体的要求要由属体的事物(水、食物等)来满足,魂的要求要由属魂的事物(思想、爱情、理想等)来满足,灵的要求也只能由属灵的事物(公义、圣洁、光明、信心)来满足。魂无法满足灵,但灵的要求又恰恰是我们这个贫乏时代所匮乏的。这就是北村在后期的小说中所出示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悖论。北村写了一帮在末世里还有良心觉悟的人(如超尘、孔丘、玛卓、康生等),这种人的存在将证明我们时代还存在多少良知,以及我们所希望的存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痛苦产生在良心与现实相遇的那一刻,这种良心的痛苦是特别的。人类文学出现了几种有代表性的痛苦,一是博尔赫斯式觉察到智慧大限的痛苦,二是普鲁斯特式的在时间的追忆中想超越时间的痛苦,三是海德格尔式的为建筑一个系统来让自己居住而有的思想痛苦,四是加缪式的要忍受无休止的推石上山运动而有的意志上的痛苦,这些都是魂的痛苦,只有良心的痛苦是灵的痛苦。良心是人活下去的唯一依靠,它为人的生存提供信心,良心一昏暗,人就会将生存信心建立在魂里,当魂的不可靠被揭露之后,良心就要重新翻转过来执行公义的审判,自杀是自杀者的魂对这种审判的回答。
先说张生。张生(《张生的婚姻》)是将信心建立在理性(思想)上的人,理性为张生提供了一种强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能保证张生不骂人、不怀恶念,成为“学雷锋积极分子”、最年轻的教授,是一个少有的好人,这都是理性所能达到的范围,但理性在一加一等于二或在求证长方形的面积时是永远不会错,可它却不能解决爱情的难处,这就是充满理性的张生在小柳面前束手无策的原因。所以,笛卡尔之后的哲学对理性形而上学彻底失望,他们宁愿相信非理性的感觉、意识,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理性。比如,生存所需要的爱就不能由理性来度量和给出,理性也不能给出信任感,张生与小柳之间的难处不是道德出了问题,乃是找不到彼此信任的根据。
超尘(《伤逝》)、玛卓(《玛卓的爱情》)是一些活在情感里面的人,爱情的完美成了她们的终极理想。北村在小说中证明了情感的脆弱性。超尘对爱情的期待,在张九模身上遭遇到了第一次失败,在旧情人李东烟身上遭遇到了第二次失败,因为他们都是说谎者。超尘明知李东烟靠不住,还是愿意将理想投射到李东烟身上,甚至这么一个正直的人,愿意将身体献给李东烟,还甘愿用不义(向丈夫说谎)来维护这个虚假的理想。在一个充满欺骗、虚伪的属肉体的环境里,超尘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人性自尊也只能是一种浪漫主义。这个世界是非理性的,仿佛一切都乱了,是个真正的贫乏时代。可是,环境贫乏,不等于人的精神可以贫乏,超尘有理由对生活提出更高的期待,她死于不肯下降存在的标准。玛卓的存在标准则显得更高,她要求有一种一尘不染的完美主义式的爱情出现,这就酿就了她那充满焦虑与恐惧的神经症人格,这种人格所提出的要求在这个不法的世代里是病态的,因为它越出这个世代所能给出的限度。情感在这个世代是最高的理想了,可情感只向人提供一种温暖的感觉,它不向人提供信心;它只在人的经历与体验中,却不可信靠,玛卓只能信任情书所代表的过去的感情,却无法为将来的感情找到信心的证据,如同小柳一样。
孙权(《孙权的故事》)是一个意志刚强的人,他那建立在意志里的生存信心的摧毁,不是由于肉身将死的恐惧,乃是肉身的死提醒他有一个更可怕的灵魂的监狱存在。就这样,思想、情感与意志的防线都彻底崩溃了,它说出了魂的大限:魂不可能自我满足,魂的产物的非神圣性与永恒性,够不上良心的标准。良心都渴慕分别为圣,渴慕被称义,可属魂人的魂里所发出的能力只赞同和执行肉身的私欲要求,张生看黄色小报,超尘与李东烟之间的性关系,都说明了魂是背弃良心的。良心提出的要求,魂无法执行,它没有这个能力,这样,良心就要发出控告的声音,到一个地步,分裂一个人。
魂的失败在于魂是有限的、带着缺陷的,当它与肉身结盟时,肉身所代表的罪的原则就败坏了一个人的魂。魂里有罪,是属魂人绝望的内在原因。对罪的态度有三种:一是不知道有罪,那是泯灭良知、靠体活着的人;二是知道有罪,却不定它是罪,欺骗良心;三是定罪是罪,寻求公义的赦免。对于一个良心觉悟的人来说,他只能走第三条路。每个人犯罪,不仅得罪别人,更得罪了自己的良心,实际上就是得罪了那位有赦罪权柄的公义者。一个人的痛苦来源于有罪感的良心抓住了一个人的魂,使魂紧张。魂要不痛苦,罪就要得赦免,使良心获得一种平安圣洁的感觉。不是法官能赦罪(法官也可能是不义的),唯有那位公义者能赦罪。除神之外,人都是不义的,这也是康生(《水土不服》)犯罪之后,张敏原谅了他,他却依然不平安的原因——因为他的良心不会原谅他。佛教也讲罪,它是以忘记它的方式来解决,这其实是贿赂良心,就像刘仁买大衣给玛卓一样,是用贿赂良心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尽了一个丈夫的责任。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性质的罪,是指着不信神说的,是存在的罪。罪(sin)是单数的,是内在的,罪行又称诸罪(sins)是复数的,是外面的。先有性质的罪再有行为的罪,是罪人犯罪,不是犯罪后成为罪人。孙权不是因杀人才成为罪犯,乃是因他里面的罪支配他去杀人。行为是罪的结果,罪的原因在良心里。良心若失去看守,人立刻犯罪,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称义来自于赦罪,赦罪来自于权柄,可康生与孔丘(《消失人类》)在未蒙称义之前,却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他们几乎要接近那种完美了。这两人是属魂人中相当特殊的一种:想自以为义,像约伯一样。最终,康生还是背叛了妻子,孔丘面对妻子也爱不起来了,这说明人的义不可靠,只能以神为义才是罪得赦免的路。康生到死前向人认罪,连骨灰都要写上“这是一把有罪的灰”,这样的情节读起来令人心酸,可依旧没能满足康生内在的良心要求。罪的工价乃是死。我第一次在中国作家笔下读到如此深邃的死亡原因。
3.爱情与艺术的败亡
一个人胜过死亡,就是魂的得救,这来源于魂生命的失丧,接受是灵的神来满足灵的需要。魂里不能有生命,只能有功能,用来贯彻灵里那个圣洁生命的活出。孙权、张生、刘浪的得救,在于他们放弃自己魂那个独立的生命,站在顺服的地位上,让思想接受光照,情感羡慕圣洁与公义,意志拣选这些神圣所是,这就是得救的故事。得救不是道德改良,不是克制自己,而是从一个属魂人(soulish person)成为一个属灵人(spiritual person),是地位的更换;不是所为的问题,乃是所是的问题。属灵人是一个治死魂生命的人,复活的人,是不靠自己活着,凭灵活着的人,是有盼望的人。
属魂的人都是不信的人,又生活在不信的世代中,没有指望,没有神。显然,人不能凭着不信活着,信心一失落,人就不再与万物及生存间建立起生命的联系,他只能借着思想与之建立认识的关系,这种认识最终导致的是为万物所辖制,主体地位失去了。在思想文化界,许多就甘愿放弃意志,为语言所辖制,语言代替了主体。这在一个有限的系统里是成立的,因为人一生下来就受一种先在的文化系统所规范,可在一个更源头的系统里,人是先于语言存在的,人创造了语言,这种创造源于人接受了“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这个有位格的、无限的神的语言作背景,人与这个神圣背景一出现问题,人所创造的语言系统就倒回来辖制人,因为人一不活在神的启示里,就活在自身的思想里,而思想总逃脱不了语言所布下的圈套。这也就是福科、德里达等人的悲剧所在。
对人发起最后一次政变的对象是语言,之后,人似乎不再相信,也不能相信什么了。小柳对张生,玛卓对刘仁,孔丘对秀英,刘敦煌(《强暴》)对美娴,康生对张敏,都不是不想相信对方,乃是没有能力相信。这种信心的危机是严重的,它使爱情失去了美,艺术失去了歌唱。用北村的话说是:“美从艺术中退出,爱从婚姻中退出,艺术从圣殿中退出,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可怕境遇。”〔3〕
可以说,爱情与艺术是末世抵抗精神衰败的最后两道武器,也是最后两个带着诗意光芒的乌托邦。这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极度贫乏的矛盾的世代,思想与理性又不可靠,许多人转而相信金钱,而相信爱情与艺术的人,是超越的人。卡夫卡与梵高在书信中一再告诉我们,这两个不会给出爱的人,却强烈地需要被爱:海德格尔到晚年,找到了荷尔德林,想在他身上为艺术重铸诗性,他想在艺术里“诗意地栖居”。爱情与艺术的神话,到末世还有多大的力量?面对爱情与艺术,我们似乎只剩下缅怀的心情了,我相信这就是许多思想者现今纷纷转向海德格尔的内在原因。
北村在许多小说中都启用了爱情衰败作为小说的内在模式。与早年《诗人慕容》中那种颓废、虚假只存在于观念中的爱情不一样,《张生的婚姻》、《伤逝》、《玛卓的爱情》、《强琴》中的爱情是,有爱情的行为,但没有爱情的本质,想爱但达不到。张九模在雨夜中等超尘,玛卓在山上看刘仁在手电光下写的情书,刘敦煌与陈美娴在一把纸伞下散步,还有那些富有乡村气息的婚礼,用采来的花瓣缀成的新婚“喜”字,等等,都是一个巨大的理想,它同那个唱民歌的时代一同存在,这样的时代一变动、消失,爱情也随之瓦解。北村所揭示的爱情悲剧是,在变动的时代中,爱情缺乏一个不动的根基。玛卓与刘仁的爱情是情书所代表的,是理想,这种理想只持续了一个下午,而后就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婚姻生涯。这俩人都想在爱中建立起存在的意义,可他们缺乏使之成功为实际的能力。他们只会唱歌、写信,不会给出爱,刘仁甚至设想玛卓是个瘫痪病人就好了,这表明他想在假设中建立一种自己能做的爱情,因他在现实中做不到。然而,真爱是能在现实中建立起来的,否则就是假想。刘仁到日本买下房子,就是想重新构筑那个下午所代表的乌托邦王国,玛卓却醒悟过来。发现理想不是实际,它只是一些空中像雪片般飞舞的纸张——她一生只经历过纸上的爱情,在绝望与死亡面前,只有爱情能给人最后的力量。《施洗的河》中的刘浪,思想天如与躺在如玉的怀中是他唯一的安慰;程天麻(《消灭》)这么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绝症来临时,首先需要的是他的情人不要离开他的身旁,以抵抗他的害怕:
可人类失爱了。失爱的原因在于存在失去了本质,在存在的意义得到确立之前,爱情只能是一个虚构,爱从盼望中来,盼望从信心中来,可有罪的人,良心的破洞使他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爱的激情。属魂的人都是冷漠的人(在希腊原文里,“魂”与“冷”是同一个字),当它接受肉身私欲的引领后,爱情就成了性,从满足魂里的情感下降到满足肉体,没有任何神圣可言,誓言成了谎言,至此,爱情已彻底失败。
许多人开始转向艺术,想在艺术中重新找回激情,找回存在的意义。可那个古旧的艺术理想在我们这个充满荒谬、无意义和相对主义思想的世代是不合时宜的,这个世代只生长颓废与绝望的艺术。写《亲人》这种动人曲子的艺术家杜林(《最后的艺术家》)很快就成了个行为艺术的参与者,周朝与宋代(《还乡》)在哭墙下的杜林发起新诗运动的激情到国外也消逝了,全部热情都花在怎样挤进国外的主流文化中,而杜林这个诗歌发源地也成了一个酒吧——这似乎就是现代艺术的命运。
由于艺术不再表达神圣,以及世界在秩序中所显明的意义,艺术也就不再表现人。在现代艺术家的眼中,真实(reality)的观念已经瓦解,这种观念起源于卢梭,到康德、黑格尔、克尔凯戈尔等,普遍对知识的统一和生命的统一感到失望,这种哲学观念严重影响了现代艺术家,从而产生了割裂的艺术、机缘的艺术、拒绝表达人性的艺术。这不单是技巧的问题,更是世界观的问题。《最后的艺术家》写到了艺术的颓败。杜林原本相信世界有一个绝对尺度,有一个中心,这使他的音乐作品有赞美的对象,是以能够解决的方式创作,这样的音乐听起来让人感到安全,有感动的力量。当这个绝对尺度瓦解之后,道德尺度也就随着瓦解,杜林首先堕落到情欲里,接着,音乐里就开始出现不和谐音,出现恐惧与颤栗的感觉。直到后面,乐队面前出现了两个指挥。杜林拉琴只能在琴背上拉,艺术与人性彻底分离了,艺术成了反艺术。杜林的绝望,和宋代、海娃、东烟(《还乡》)的绝望一样,是因为他们想表达的与他们所表达的不一样,他们所表达的又与他们希望表达的不一样。杜林说,真正的艺术家是崎下村的人,可在他的婚礼上,却不敢请这帮艺术家来,因为这帮没有道德的艺术家将破坏他婚礼的宁静和幸福;他照顾孩子与妻子明明有幸福,可回到崎下村这爱却成了羞耻。这令我想起毕加索,这位用割裂手法绘画的大师,却将他的情人与儿女们画得充满人性。生活不是这样的。那些相信偶然、相对、机缘的艺术家,自己却不愿意这样活着,因为宇宙并不是由偶然与机缘构成的。
艺术从人性中退出来,让大便、月经带、猪登场成为艺术的主体,表明艺术家不仅失去了正常的想象力和对人性景象的正常感知,甚至连最后一点自恋主义都失去了,接下去,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呢?抽象派方面的表现派画家康定斯基在他一篇题为《关于形式的问题》的文章中说:“因为旧的和谐(指知识的合一性)已经失去了,现在只剩下两种可能,一是趋向极端写真,一是趋向极端抽象,这二种可能其实都是一样的。”〔4〕极端写真有照像现实主义, 都不能触及正常的人性,是艺术家想象力极度匮乏的表现。到行为主义,则宣布了艺术的死亡。如果这些也是艺术,我提议请一位大提琴家在水中裸着身体弹奏自己的音乐。
我相信,理性的失败宣告了海德格尔思的神话的破产,而艺术的失败则宣告了海德格尔晚年“诗意地栖居”的神话也已破产。当杜林只能用琴弓击打琴背时,当海娃烧毁自己的诗歌时,当东烟在海滩上看人如同浪花上的泡沫时,一个爱情与艺术的世代也已彻底没落。从来没有一个世代,精神问题像末世这般严重。凡有良知的人,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4.世代终结前的抒情
爱情败落、艺术死亡、心灵抽空、人生退席、道德沦丧、理想破灭、哲学崩溃……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人类在末世的精神背景。如果人类不能再获得一个有力的盼望,生存下去便是一种灾难。我们要质问,人类精神的没落是从哪里起头的?那么,人类精神的挽回也必须从哪里起头。文艺复兴开始,人本顶替了神本,本意是要给人一个崇高的地位,可不久之后,人本又被文本所顶替,语言与形式纂夺了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存在成了一种悲剧性的存在。要挽回这样的悲剧,不可能从文本直接回到人本,因为人瓦解、绝望后,已经失去了这种向上一跃的力量,必须首先恢复对神为本位的价值系统的确信,才能重新为人争取地位;先恢复灵,才能恢复魂的品质。文学要走这条恢复的路。
就是因为人类的失信,爱情与艺术才失去深情的品质。这种对象与本质分离的内在原因,乃是因神圣的背景隐晦缺度了,所以,北村小说中充满着对堕落与颓废的描绘,不是北村要故意让他们堕落,乃是现代的人主动选择了以非人的方式生存,并认为堕落是可以被接受的。我想起古罗马帝国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堕落与艺术畸形的发展,以赝品代替真品,狂热当作才能;我又想起古代以色列,当全国远离神,违背圣经真理和诫命的时候,先知耶利米起来大声呼喊,死亡将临到这城!这不但是指耶路撒冷居民肉身的死亡,更是指整个文化、社会的死亡,意义的死亡。现代社会经过一段漫长的路途后,仿佛又返回了衰败时期的古代。
更严重的是人的死亡,即人的神话的解构。北村小说坚决地反对了人,站在灵的立场上彻底否定了魂。人的激情来源于对人的自信,这点瓦解后,是致命的,使一切都变得苍白、冷漠、毫无生命力,抒情的对象消失了。文艺复兴之后,文学艺术的抒情性都建立在人这个自我的神话上,所以,1504年才有了那个压倒一切的大卫像,它代表着人文主义的理想——人是伟大的!那时的艺术家可以对人发出抒情。《最后的艺术家》中写到一个情节,杜林与张丽恋爱后,爱情的温暖贮满了他的胸怀,他幸福到一个地步,甘愿放弃很有前途的创作。那时的杜林有一个朴素的思想:人是为活着而活着,不是为艺术而活着。
这是最后一个抒情时代。北村的小说有力地揭示了抒情时代终结前的景象,《极地》、《还乡》、《最后的艺术家》都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挽歌。那些山歌、油莱籽、爱情、诗歌朗诵、弹琴、看海等抒情意象,都随着人的瓦解消逝了。抒情性的匮乏,在于作家无法再获得一种令他震惊的经验,只有俗常、平庸的经验,是无法建立起抒情性的。抒情的对象(震惊的经验)消失了,抒情的基础(正常的人性)也瓦解了,在这样的境遇里,一个好的作家、有使命感的作家,若能找回良心的立场,将会有下面三方面的表现,作品也将会重铸起另外一种抒情性。
第一,揭露。北村说:“我只是在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5〕这样的打量就是一种揭露。 揭露必须有一个高于现实的立场,就是良心的立场,才能与现实分离,进而审视现实。许多作家都承认这个堕落的事实,可他们对看这种事实只在体验,没有揭露。体验是表明自己也沦落其中,放弃价值态度,而揭露是给它一个批判的态度。批判的基本标志是冲突:现实自身的冲突、人与现实的冲突、作家与现实的冲突。我们在北村的小说中所读到的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是在其他作家那里读不到的。我相信,许多作家处理《伤逝》、《玛卓的爱情》、《水土不服》,到后面会找到和解的路,可北村拒绝这种妥协的和解,坚持向生存的终极攀援。“康生是必死无疑的。因为整个世代是不信的,或者说整个人类陷在罪里,康生也没有办法例外,他要让良心稍稍抬头,就要付出严重的代价。……我就是没写他跳楼身亡,他也就是一具活死尸了。”〔6〕死亡是人与现实最紧张的表示。 不是北村故意要紧张,乃是他的良心与现实的罪恶间是紧张的。北村是一个将揭露的力量贯彻到底的作家。
第二:缅怀。缅怀是一种废墟上的凭吊,是一种向下的抒情,或称向后的抒情。人本源地都想在时间的追忆中保持自己印象中的美好事物,这虽然无法让它在废墟中站立起来,至少还表达了一种怀念,这种情感是美好的。读北村的小说,仿佛回到了托尔斯泰的时代,这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哭泣。北村说,康生是一个哭泣的天才。中国作家连哭泣的能力都丧失了。超尘、康生、孔丘、早期的刘敦煌与陈美娴,他们的许多品质在过去是可以被歌颂的,在现在这个世代却成了滑稽可笑的东西,对它的抒情与凭吊,只会充满颓唐。北村一直地向后看,企图找回那些理想,所以他让小柳读童话,让陈美娴弹琴,让玛卓珍藏情书,让宋代在讲座上一遍又一遍地讲《卖火柴的小女孩》。可最终,童话、小人书被烧毁,琴声与爱情一同破灭,情书成了玛卓的殉葬品,宋代的讲座遭到了嘲笑。宋代的还乡和隐居小岛,都为了寻找一个像墓穴一样大的地方安息,可连这个最小的心愿都遭到了这个世代的拒绝。北村的缅怀包含着一种不相信,因为这种抒情并不会得着那些逝去的理想,只是哭泣。由此,我怀疑张炜以土地为中心的田园乌托邦、王安忆虚构的家族史、史铁生的冥思、张承志的愤怒能够使人居住下来。我怀疑。
第三:呼告。呼告是一种向上的抒情,或称向前的抒情,它要求作家的眼光脱离土地、人与现实的粘附,抬头与天空所代表的神圣价值的结盟。这是一种危险的写作精神,如果呼告中看不见实在的景象,作家将死于非命。荷尔德林、里尔克、屈原、海子都死于此。许多人不理解北村小说人物的死因,就是因为不理解人还有一种呼告的需要:人想达到永远,趋于无限。康生、孔丘、玛卓的理想在人里是给不出的,因为人里没有无限,当呼告又得不着实际时,只有死路一条了。呼告中的北村没有死是因为他信,而康生等人不信。中国人只会以某个具体目的到庙堂里祈求,他从来不呼告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最高的人生理想,可有合一的道,但没有合一的路,几千年下来,只好放弃这一理想,而转而构筑以儒家为代表的社会理想,在社会理想面前,只需奋斗,不需呼告。
呼告的对象就是作家抒情的对象。只有面对一位无限的、有位格的神,人才可能重新找到真正的抒情,即找到震惊的经验。在许多人都在讲终极价值的世代,我要指出,这个终极价值若不指证它为有位格的神本身,就会成为一些观念法则,甚至玄想。人要接近这位有位格的神,还必须注意到人是有罪的,若不先信基督作中保,让罪得赦免,断不能与神交通(一种能通的交流)。罪一得赦,抒情性就建立起来了,既有抒情的对象,又有抒情的基础,这是最高的文学。所以,北村将连篇累赎的祷告词写在小说中,就是一种自由的抒情,这是属灵人才有的抒情。我信那些祷告许多人不理解,但读起来让人感到安慰,这一点已经越过了文学本身,我为它无法被讨论感到遗憾,但我希望有人记住“信仰”这两个字,并认识它的神圣性。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点上,北村从写作中有效地分离了出来,他说:“许多优秀的作家的著作堆满了图书馆的书架,但他们都死了,没有一个人把永生的生命给我。现在,我对我仍在从事写作充满了疑惑和痛苦。”〔7〕我想,和属灵人的抒情一样, 这种疑惑和痛苦也是属灵人才有的。
1995年7月10日于福州
注释:
〔1〕北村:《施洗的河·后记》,花城出版社93年6月;
〔2〕北村:《末世: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载《钟山》1995年4期;
〔3〕北村:《缅怀艺术》,载《艺术世界》1992年6期;
〔4〕转引自薛华:《前车可鉴》第180页,香港宣道出版社1991年三版;
〔5〕〔7〕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4期;
〔6〕北村:《水土不服的世代》(创作谈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