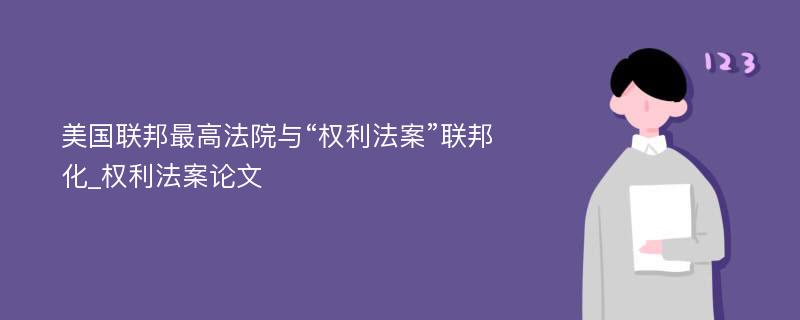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权利法案》联邦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最高法院论文,法案论文,联邦论文,美国联邦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学者阿希尔·R.阿马(Akhil R.Amar)曾经说过,“今天的美国人很难想象,《权利法案》只能约束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官员是无效的”①。事实上,在美国宪政史中,《权利法案》只能约束联邦政府却是一个被长期坚持的宪法信条。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权利法案》才开始借由“联邦化”进程,逐渐被运用于约束州和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
所谓《权利法案》联邦化(Nationaliz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是指原来仅约束联邦政府的《权利法案》,经由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逐渐被“纳入”(incorporate)到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中,用于约束州政府,从而把《权利法案》的效力扩大到了整个联邦。
自第14条宪法修正案生效以来,美国学者就开始对《权利法案》联邦化问题进行研究。当代美国学术界对该问题的深入讨论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当时,美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查尔斯·费尔曼(Charles Fairman)和威廉·W·克罗斯基(William W.Crosskey)都对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历史作了深入研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费尔曼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制定者打算把《权利法案》“纳入”到该修正案中,用于制约州政府。克罗斯基则认为,从第14条宪法修正案制定者们的言论中可以推论出,制定该修正案的本意就是要把《权利法案》“纳入”其中,以防止州政府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②。尽管费尔曼和克罗斯基的观点不同,但二人都试图通过探究第14条宪法修正案制定者们的“原初意图”(Original Intent),为各自的观点提供历史依据。这一研究路径,奠定了此后几十年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争论的基础③。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权利法案》联邦化问题的讨论,在拉乌尔·伯杰(Raoul Berger)、迈克尔·K·柯蒂斯(Michael K.Curtis)等学者之间再次出现,探讨的重点仍然集中在“原初意图”问题上,没有超越费尔曼和克罗斯基争论的范围④。
在国内学术界,少数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探讨,但重点在于追溯《权利法案》联邦化的过程,对《权利法案》联邦化发展的原因缺乏更深入的研究⑤。
本文无意参与美国学者们的“原初意图”之争,而是力图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权利法案》联邦化进程中的作用为切入点,分析推动《权利法案》联邦化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
一、《权利法案》与“巴伦诉巴尔的摩案”
在美国,1791年12月生效的美国联邦宪法第1至第10条修正案,通常被称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其主要内容是明确规定了政府不得侵犯的诸多公民权利,如公民享有宗教信仰和表达自由,公民的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公民的人身、住宅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刑事被告享有多项公正审判的权利等。《权利法案》的出台,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法案对政府的约束力,而且也使公民在诉求法律保护时拥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18世纪末,《权利法案》出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约束联邦政府,而不是限制州政府。正如美国学者亨利·亚伯拉罕(Henry Abraham)所言,尽管在《权利法案》中,只有第1条宪法修正案明确指出,“联邦国会”不得制定侵犯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法律,但就《权利法案》的立法理念而言,“毫无疑问它只是被用来制约国家政府的”⑥。
《权利法案》的这一立法目的,是在1787年9月至1788年7月美国各州批准联邦宪法的过程中被明确的。美国联邦宪法是在1787年5月至9月由费城制宪会议草拟的,起初并无《权利法案》。在制宪会议把宪法草案提交给各州批准后,是否应在联邦宪法中增补《权利法案》,成为各州争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当时美国政坛中出现的“联邦党人”(Federalist)与“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的重要分歧之一。
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等人为首的联邦党人认为,联邦宪法不仅规定联邦政府只能行使明确授予的权力,而且也包含了许多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规定,因此,联邦宪法本身即可被视为《权利法案》。如果在联邦宪法中专设《权利法案》,对并未授予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不仅无此必要,甚至可能造成危害”⑦。“反联邦党人”则认为,政治是权力与自由的竞争,宪法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要保证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受联邦政府的侵害,宪法中就必须专设《权利法案》⑧。正如反联邦党人领袖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言,“《权利法案》是人民反抗……政府侵犯其天赋权利的保障,任何政府既不能拒绝制定《权利法案》,也不能将人民的权利系于推论之上”⑨。
在反联邦党人的推动下,马萨诸塞、弗吉尼亚、纽约等州先后提出了增补《权利法案》的要求⑩。据统计,在批准联邦宪法的过程中,各州提出的有关《权利法案》的修正案就达124条之多(11)。最终,联邦党人作出了妥协,同意在各州批准联邦宪法后,另行补充《权利法案》。
在1789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联邦国会中,负责起草《权利法案》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试图使《权利法案》既约束联邦政府,也制约州政府。在他看来,“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一样,也会对人民的宝贵特权横加干涉,故必须予以审慎地扼制”(12)。但由于州宪法中大都已载有《权利法案》,因此,麦迪逊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多数联邦国会议员的支持,从而使《权利法案》的立法宗旨完全集中在约束联邦政府权力方面。1791年12月15日,经各州批准,联邦宪法前10条修正案正式生效,通称为《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的适用范围之所以被限定在约束联邦政府,主要原因在于早期美国人对国家政府权力的担心和恐惧。早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英国政府不断对北美英属殖民地采取强硬的殖民政策,殖民地就曾先后提出过“帝国联邦理论”(Federal Theory of Empire)和“帝国领地理论”(Dominion Theory of Empire)(13)。虽然这两种理论在殖民地主权问题上的观点不同,但它们都主张殖民地与英国政府实行分权,英国政府有权管理涉及帝国全局的事务,但不得干涉殖民地的内部事务,侵犯殖民地人的自由和权利。这说明,在独立以前,殖民地人就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所构成的潜在威胁。
殖民地时代的这种经历和认识直接影响了独立后美国的宪政发展。在独立之初,虽然美国组建了“邦联政府”,但并未赋予它作为一个国家政府所应有的权力。1787年联邦宪法也通过分权制衡、列举政府权力等方式,对联邦政府作了全方位约束。在此思想背景下,众多的美国人要求在联邦宪法中增补《权利法案》,以进一步防止联邦政府侵犯公民权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从《权利法案》的制定过程可以看出,早期美国人对联邦政府怀有极大的不信任,他们更愿意把保护公民权利的希望寄托在州政府身上,因为州政府最贴近人民,也更容易为人民所控制。但是,随后的美国历史发展证明,早期美国人对州政府的青睐是不切实际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州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远比联邦政府为甚。许多州政府不仅随意限制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陪审团审判等权利,而且还任意剥夺公民的财产。在此情况下,许多人便开始向联邦最高法院寻求法律保护,试图援引《权利法案》,禁止州政府侵犯公民权利。但是,这些诉求无一获得成功,1833年的“巴伦诉巴尔的摩案”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该案中,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政府在整修道路过程中,将砾石和砂土倾入河道中,致使约翰·巴伦(John Barron)拥有的码头无法正常营业。巴伦认为,巴尔的摩市政府的这一行为,违反了第5条宪法修正案所作的“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的规定,遂提出法律诉讼,并将该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4)。
该案的中心问题是第5条宪法修正案能否约束州政府。对此,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性意见。最高法院认为,在联邦建立之初,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是出于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护人民自由的目的,才极力呼吁在联邦宪法中增补《权利法案》的,这说明,“《权利法案》防范的对象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第5条宪法修正案只对联邦政府有效,而不能以其为依据,干预州政府的施政行为。如何限制州政府的权力,各州人民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15)。从上述观点出发,最高法院认为,巴伦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是由马里兰州政府造成的,属于州的内部事务,联邦最高法院无权过问此案,巴伦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
巴伦案判决是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对《权利法案》适用范围所作的司法解释,该案判决的作出不是偶然的。首先,该案判决反映了当时美国政治发展的潮流。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就任美国总统后,力主保护州政府的权力,反对联邦政府随意干预州的内部事务,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最高法院的巴伦案判决实际上就是“杰克逊民主”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该案裁判的理由符合《权利法案》制定者们的“原初意图”,即《权利法案》只约束联邦政府。因此,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并未对遭受财产损失的巴伦提供法律救济,但巴伦案判决却并不缺乏宪法依据。
然而,从长远眼光看,巴伦案判决使美国的宪政体制运作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之中。巴伦案判决实际上是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在公民权利保护领域中确认了一个双重标准,它只要求联邦政府遵守《权利法案》,对州政府违反《权利法案》的行为漠然处之。这就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当州政府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而公民又在州内无处申述自己的冤情时,如何强制州政府纠正其违宪行为?如果按照巴伦案判决,将州政府完全置于《权利法案》的制约之外,实际上就使州政府拥有了随心所欲滥施权威的能力,这不仅使公民权利面临巨大的威胁,而且也使司法机关无法切实履行其肩负的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责。从这一意义上讲,巴伦案判决带有非常强烈的保守性。在此后近一个世纪里,巴伦案判决始终作为一个重要的司法先例,影响着美国司法机关对《权利法案》的解释。如何突破巴伦案判决的约束,使《权利法案》也能够约束州政府,成为摆在美国社会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1868年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正式生效,使该问题再一次成为美国社会争论的焦点。
二、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与“纳入学说”的出现
第14条宪法修正案是内战后美国联邦国会在激进共和党人的推动下制定的,其宗旨是保护刚刚从奴隶制枷锁中解放出来的黑人的宪法权利。该修正案第1款明确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privileges or immunities)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凭借“特权或豁免权”和“正当法律程序”这两个重要的条款,黑人的宪法权利有了坚实的宪法基础。
但是,该修正案的出台,又一次将巴伦案提出的核心问题摆在了美国社会面前。如果说在三十多年前的巴伦案时代,人们还找不出确切的有关《权利法案》约束州政府的宪法规定,那么,在第14条宪法修正案生效后,这一难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措辞非常宽泛,其效力并不仅仅局限于保护黑人权利这一狭窄的空间。他们认为,该修正案中的“特权或豁免权”和“正当法律程序”两个条款,所保护的恰恰就是包含在《权利法案》中的公民权利。如果州政府侵犯了这些公民权利,实际上也就是违反了第14条宪法修正案,理应受到规制。换句话说,借由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上述两个条款,原来被认为仅约束联邦政府的《权利法案》,现在也必须被“纳入”(incorporate)到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中,规制州政府的违宪行为,从而使《权利法案》在整个联邦范围内都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这种将《权利法案》联邦化的思想,就是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在美国出现的“纳入学说”(Incorporation Doctrine)。
针对这一学说,在美国的学术界和法律界中出现了尖锐的分歧。“纳入学说”的反对者们认为,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宗旨,仅在于确保黑人拥有与白人公民相同的宪法权利,并无意将整个《权利法案》都“纳入”到该修正案中;如果该修正案的制定者们的确意在于此,他们就应当明确地加以规定,而不是用笼统的语言加以表达。但是,这一观点遭到了“纳入学说”支持者们的反对,他们认为,该修正案的制定者之所以采用宽泛性的词句,是在表明他们并不仅仅旨在保护黑人获得平等的宪法权利,而是要把整个《权利法案》所规定的公民权利都“纳入”到该修正案中,“特权或豁免权”、“正当法律程序”只不过是《权利法案》的“简略表达”而已(16)。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纳入学说”也成为大法官们争论的焦点。但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多数大法官都对“纳入”持否定立场。例如,在1873年的“屠宰场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就否定了通过“特权或豁免权”条款“纳入”《权利法案》的可能性。
在该案中,路易斯安那州因制定法律支持屠宰业实行垄断,遭到了财产受到损失的屠宰业主的起诉。在塞缪尔·米勒(Samuel F.Miller)大法官所作的判决中,最高法院认为,在联邦制下,美国人具有双重公民资格,即美国人既是“合众国公民”也是“州公民”。以不同的公民身份为依据,美国人拥有不同的“特权或豁免权”。最高法院认为,公民以“合众国公民”身份享有的“特权或豁免权”是有限的,仅包括集会请愿、寻求人身保护令状和在公海及海外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等为数不多的几种。但公民以“州公民”身份享有的“特权或豁免权”却是广泛的,包括有权“得到和拥有一切形式的财产”、“追求幸福和安全”等一切“自由政府中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由于第14条宪法修正案只是禁止州政府不得侵犯“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因此,该修正案“并无意”给“州公民”的宪法权利提供“任何额外的保护”(17),并不限制州政府在“州公民”权利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
按照该案判决的思路,《权利法案》所保护的那些普遍性的公民权利,自然是属于“州公民”而不是“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因此,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特权或豁免权”条款并不要求州政府必须遵守《权利法案》,“纳入”之说缺乏宪法依据。
斯蒂芬·菲尔德(Stephen J.Field)和约瑟夫·布拉德利(Joseph Bradley)等大法官对这一判决提出了强烈异议,认为尽管存在着“合众国公民”和“州公民”之分,但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应是平等的,否则,第14条宪法修正案就成了“徒劳而无用的立法”(18),但在随后的岁月里,“屠宰场案”判决一直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先例,阻断了借由“特权或豁免权”条款推进《权利法案》联邦化的道路。
不仅如此,联邦最高法院也同样否定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作为“纳入学说”的宪法基础的可行性。例如,在1892年的“奥尼尔诉佛蒙特州案”、1900年的“马克斯韦尔诉道案”和1908年的“特文宁诉新泽西州案”(19)中,最高法院都坚持认为,无论是根据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文本规定,还是从《权利法案》的立法本意看,《权利法案》只适用于全体美国人防范联邦政府,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并不具有“纳入”《权利法案》的宪法基础,州政府不受《权利法案》的约束。
在这一时期的联邦最高法院中,只有约翰·M·哈兰(John M.Harlan)大法官始终坚持“纳入”的合宪性。在1884年的“赫特杜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和奥尼尔案等案件中,哈兰大法官认为,《权利法案》所体现的“自由和公正原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20),虽然制定《权利法案》的初衷,只是为了防范联邦政府,然而,在第14条宪法修正案生效后,《权利法案》所保护的那些公民权利“也不得被各州否认或剥夺”(21)。
但是,哈兰大法官的极力呼吁,并无力使最高法院中的绝大多数大法官改变对“纳入学说”的认识。最高法院的否定立场,成为《权利法案》联邦化之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联邦最高法院之所以在第14条宪法修正案生效后,仍然否认“纳入”的合宪性,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大法官深受内战后的“形式主义法学思想”(Legal Formalism)的影响。该思想主张严格遵循宪法原则和法律条文,反对将法律与政治相结合,否则,法律就降格为了政治,法官也变成了立法者(22)。正如曾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的詹姆斯·C·卡特(James C.Carter)所言,人们在认识和运用法律时,应遵守法律条文的既有规定,重视法律“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23)。在前述的诸多案件中,大多数大法官关注的不是公民权利是否受到侵犯,而是如何恪守《权利法案》和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文本,这种司法理念显然是与“形式主义法学思想”一脉相承的。
其二,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大法官都深受第14条宪法修正案制定者的“原初意图”的束缚,不愿打破联邦与州的分权格局。在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制定过程中,尽管激进共和党人力主采取切实的措施保护黑人的宪法权利,但绝大多数议员都不主张过多地干预州权,以免违反联邦制原则。
例如,该修正案的重要制定者联邦众议员约翰·宾厄姆(John Bingham)就曾指出,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不能成为联邦政府干预州权的工具,“公民必须依赖州政府保护其宪法权利,这是一项现行的宪法原则”。另一名联邦众议员乔治·莱瑟姆(George Latham)也认为,联邦政府必须恪守与州政府分权的原则,因为“依照联邦宪法,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各州的内部政策”。新罕布什尔州的联邦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虽然他完全支持联邦国会制定第14条宪法修正案,以保护“黑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任何法律的歧视”,但他坚持认为,该修正案的权限“只能到此为止”,联邦政府绝不能以其为根据,任意钳制州政府在其州内的施政行为(24)。
第14条宪法修正案制定者们的上述思想,深刻影响了最高法院对该修正案的解释。例如,在前述的“屠宰场案”中,米勒大法官就曾指出,尽管内战给美国人的思想造成了巨大震动,“但我们并不能从内战后制定的修正案中看出,它们要消除美国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美国政治家们依然坚信州的存在,以及州政府有权管理其内部和地方事务……因为这对美国复杂政体的完美运作是至关重要的”(25)。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联邦最高法院拒绝承认“纳入”的合宪性,其实并不难理解。
尽管最高法院恪守了联邦宪法和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文本,也遵循了联邦国会的立法意图,但它却忽视了在内战后美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州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愈演愈烈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放纵了州政府的侵权行为。这就使这一时期的最高法院带有了非常强烈的司法保守主义色彩,它也并未真正发挥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
三、《权利法案》联邦化的启动与大法官司法理念的分歧
在1925年的“吉特洛诉纽约州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纳入”问题上的态度终于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该案中,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地把《权利法案》中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条款“纳入”到了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中,用于约束州政府,从而正式开启了《权利法案》联邦化的进程。
在吉特洛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一方面支持纽约州法院对上诉人本杰明·吉特洛(Benjamin Gitlow)所作出的有罪判决,认为吉特洛鼓动美国人推翻现政府、建立社会主义的言论和出版物,违反了纽约州的“反无政府状态法”(Criminal Anarchy Act)。但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又认为,“我们……确信,第1条宪法修正案禁止联邦国会侵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们受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保护,州政府也不得侵犯”(26),只不过吉特洛“滥用”了这种自由,其煽动性的宣传严重危害了纽约州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而不在该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罢了。
这寥寥数语对美国宪政发展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它标志着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采取了实质性的司法行动,把《权利法案》的具体条款“纳入”到了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中,正式迈上了《权利法案》的联邦化之路(27)。
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在吉特洛案中开启《权利法案》联邦化的大门,首先缘于20世纪初美国人对社会公正的不断呼吁。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内战后逐渐盛行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经济思想遭到了强烈抨击,美国社会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开始更加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很多美国人认识到,在经济大变动的过程中,必须确立统一的社会公正标准,使公民的宪法权利既不受联邦政府的剥夺,也不遭州政府的侵犯。要实现这一目标,用美国学者保罗·墨菲(Paul L.Murphy)的话说,“唯一可行的法律手段”,就是充分利用第14条宪法修正案,将《权利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州,从而建立起保障公民权利的“国家标准”(28)。最高法院在吉特洛案中对“纳入”的肯定,正是对这一社会呼声的积极反应。
其次,最高法院在吉特洛案中迈出启动《权利法案》联邦化的关键一步,也是最高法院内部司法理念逐渐转变的结果。如前所述,自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约翰·M·哈兰大法官就极力呼吁《权利法案》联邦化。进入20世纪以后,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大法官又成为这一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例如,在1920年的“吉尔伯特诉明尼苏达州案”中,布兰代斯大法官就在异议意见书中指出,第14条宪法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应该包括联邦宪法和《权利法案》所规定的“人”的“根本权利”(29),州政府也不得侵犯。
与忽视社会现实、主张恪守法律文本的保守派大法官们相比,哈兰和布兰代斯大法官对《权利法案》联邦化观念的坚持,是建立在关注社会现实基础上的,这无疑具有司法自由主义色彩,对最高法院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追求社会公正的时代潮流中,最高法院在吉特洛案中正式启动《权利法案》联邦化,明显是接受了上述两位大法官的思想,使他们的“异议”开始成为最高法院的思想主流。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又在其他几宗民权案件中,先后将《权利法案》中“和平集会”、“信教自由”、“政府不得确立国教”和“公民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等权利“纳入”到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中,约束州政府(30)。
联邦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步推进《权利法案》联邦化,是与这一时期最高法院司法重点的转变密切相关的。在内战后的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在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重点主要集中在审查联邦和州政府的经济立法方面。受“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影响,联邦最高法院对联邦和州政府的调控经济的立法,基本上都采取了严格审查的态度,防止政府立法阻碍经济自由发展,因此,众多经济立法都被最高法院以各种理由宣布为违宪。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New Deal)时期,罗斯福总统的多项挽救经济危机的改革措施也相继被宣布违宪,并由此引发了总统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尖锐对抗。在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从1937年3月开始,联邦最高法院终于改变立场,支持“新政”,并逐渐实现了最高法院司法重点的转移。
在1938年的“合众国诉卡罗林产品公司案”判决中,最高法院认为,尽管最高法院应当宽泛地审查政府的经济立法,但对某些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最高法院必须予以严格审查(31),美国当代司法审查的“双重标准原则”(Double Standard)由此确立(32)。这表明,在政府权力扩大已成为美国社会发展必然要求的情况下,最高法院放弃了严格约束政府调控经济的传统,把最高法院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发挥制衡作用的重点,由防止政府机构权力过度扩张,转变为严格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最高法院司法重点的转移,不仅扩大了政府调控经济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为此后美国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高法院对《权利法案》联邦化的推进,正是最高法院司法重点转变的集中体现。
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在《权利法案》联邦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对于如何推进《权利法案》联邦化,大法官们的态度并不一致。总体而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内部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选择性纳入观”(Selective Incorporation)。该观点认为,第14条宪法修正案并非要把整个《权利法案》都“纳入”其中,只有那些对自由和正义至关重要的权利才可以被“纳入”,以制约州政府。在1937年的“波尔克诉康涅狄格州案”中,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大法官就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卡多佐认为,在美国宪政中,约束联邦政府的《权利法案》一定约束州政府,“并不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则”。如果说第14条宪法修正案能“吸收”某些《权利法案》中的公民权利,那只是因为这些权利体现了“一系列有序自由的最本质的内核”(33)。
第二种观点是“整体性纳入观”(Total Incorporation)。该观点认为,《权利法案》中的所有公民权利都必须无条件地被“纳入”到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中,司法机关不作主观性的选择。这一观点最主要的倡导者是雨果·L·布莱克(Hugo L.Black)大法官。在1947年的“亚当森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布莱克在异议意见书中认为,《权利法案》并不是一件18世纪的“紧身衣”,由于在社会发展中,《权利法案》所禁止的那些所谓的“古老的罪恶”,总是会反复出现,因此,《权利法案》是任何时期的任何政府都不能拒绝执行的。在他看来,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初衷”就是要用《权利法案》保护所有美国人的公民权利(34)。
第三种观点是“行为得当和公正观”(Decency and Fairness)。该观点认为,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与《权利法案》之间不存在“纳入”关系,判断一项权利是否被州政府侵犯的标准,应是州政府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政传统中的“行为得当和公正”原则。在前述的亚当森案中,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集中阐释了这一观点。法兰克福特认为,从第14条宪法修正案制定和批准的过程看,无论是该修正案的制定者还是批准该修正案的各州,都无意把《权利法案》“纳入”到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中。“纳入”将会“严重破坏各州的法律结构”,也会“剥夺各州进行法律试验的机会”,从而违反美国的联邦制。在法兰克福特看来,第14条宪法修正案具有“独立的权力”,并不受制于《权利法案》。它是否禁止州政府的某种行为,不是因为那种行为是否违反了《权利法案》,而是要看那种行为是否符合“体现英语国家人们正义观的行为得当和公正标准”(35)。
大法官们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的意见分歧,首先是缘于第14条宪法修正案条文本身的模糊性。为确切把握“特权或豁免权”、“正当法律程序”等词句的含义,卡多佐、布莱克和法兰克福特都对第14条宪法修正案产生的过程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国会记录庞杂,修正案制定者们的言论有时也前后矛盾,要得出一致的结论并非易事。另外,由于在批准该修正案时,许多州的州宪法和州法律中都有违反《权利法案》的规定,因此,很难确定批准该修正案的各州也支持“纳入”,认可《权利法案》约束自己的施政行为(36)。在此情况下,大法官们在“纳入”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并不是偶然的。
此外,作为美国宪政体制基础的联邦制原则,也使大法官们难以对“纳入”形成一致的看法。大法官们在“纳入”问题上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在保护公民权利与尊重州权之间的两难选择。“纳入”无疑可以进一步保护公民权利,但也意味着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约束的加强,使联邦制原则面临挑战。如何在二者之间确定一个适宜的度,的确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宪政难题,这也直接导致了大法官们在“纳入”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由于大法官们普遍认为“整体性纳入观”有悖于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初衷,并极有可能损害美国的联邦制,而“行为得当和公正观”又比“选择性纳入观”带有更明显的主观性,因此,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选择性纳入观”逐渐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所接受,成为此后“纳入”进程中的主导司法理念。
四、《权利法案》联邦化的巩固与扩大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冷战的加剧和美国国内政治的日趋保守,《权利法案》联邦化进程在事实上处于停顿状态。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最高法院开始加速推进《权利法案》联邦化进程。在这一时期,最高法院不仅巩固了《权利法案》联邦化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还扩大了“纳入”的范围,进一步推动了《权利法案》联邦化的发展。
最高法院对《权利法案》联邦化既有成果的巩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最高法院进一步肯定了《权利法案》在禁止州政府侵害公民表达自由权方面的法律效力。例如,在1963年的“爱德华兹诉南卡罗来纳州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是第1条和第14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公民的一项神圣的宪法权利,在没有充分证据确认一种言论会对社会造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的情况下,州政府不得以任何手段阻挠他人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否则,“就使立法机关、法院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集团拥有了强制统一思想的权力”,从而严重违反了美国宪政传统(37)。
在1964年的“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和1969年的“廷克诉得梅因独立社区校区案”中,最高法院又分别强调,不论是公民对州政府及官员作了“令人不快的、措辞严厉的批评”,还是学生以佩戴黑色臂章这样的“象征性语言”(symbolic speech)抗议政府的越战政策,都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各州必须给这类言论留有足够的“喘息机会”,否则就人为地抑制了言论自由,从而与第1和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38)。
其次,最高法院进一步强调了《权利法案》禁止州政府侵犯公民宗教自由权的权威性。在1962年的“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即使州政府没有“直接强迫”人民信仰某种宗教或教派,但只要州政府以其权势、威望和财力支持了某一宗教或教派,就对其他宗教组织构成了“间接强制力”,并使它们在宗教事务中处于劣势地位(39),这显然违反了《权利法案》的“禁止确立国教”条款,联邦最高法院必须对此加以坚决制止。
在1963年的“阿宾顿校区诉谢默普案”和1968年的“埃珀森诉阿肯色州案”中,最高法院又先后将宾夕法尼亚州和阿肯色州要求学生在学校中诵读《圣经》,以及禁止在学校中讲授进化论的法律宣布为违宪,其宪法依据也是它们都违反了《权利法案》的宗教自由条款(40)。
在20世纪60年代,最高法院推进《权利法案》联邦化发展的最重要的表现,是它扩大了《权利法案》联邦化的范围,将更多的《权利法案》条款“纳入”到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中,约束州政府,这主要表现在保护刑事被告的宪法权利方面。
尽管《权利法案》中所占篇幅最多的是保护刑事被告宪法权利的条款,但由于这些条款长期被认为只限制联邦政府,因此,在州级刑事审判中,侵犯刑事被告宪法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随着最高法院加速推进《权利法案》联邦化,这种局面开始得到改变。
在1961年的“马普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开始启动《权利法案》约束州级刑事审判的进程。在该案判决中,最高法院认为,为建立“健康型的联邦制”,联邦与州必须在刑事审判方面采取统一的诉讼程序。由于第4条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住宅和财产等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因此,如果州政府违反了这一规定,它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刑事被告不利的“证据”,就必须被排除在合法证据之外。最高法院认为,如果允许州政府可以凭借违宪获得的证据指控公民,那么,这一法律诉讼的“捷径”就会“摧毁”整个“宪政体系”,从而使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变成一句“空洞的许诺”(41)。
在马普案之后,最高法院又在1963年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和1964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将《权利法案》有关公民有权获得律师辩护和不得自证其罪的条款,“纳入”到了对州政府的约束范畴。在吉迪恩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在以“对抗制”为特征的美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如果刑事被告(尤其是贫穷的刑事被告)缺少律师辩护这一法律保障环节,“就无法确保实现公正审判”。因此,第6条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刑事被告“有权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是一项“根本性的”的公民权利,州政府必须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严格遵守(42)。
在米兰达案中,最高法院认为,第5条宪法修正案所作的公民不得在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的规定,是“合众国人民最为珍视的宪法原则”,州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这一原则。不仅如此,最高法院还明确规定,在案件刑侦阶段,州警察必须在审讯前向嫌疑人正式宣布其所享有的四项宪法权利:他有权保持沉默;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以在法庭上用作指控他的证据;他有权要求会见律师;如果他无经济能力聘请律师,在回答任何问题前,将由政府按照其意愿为其聘任一位律师(43),此即著名的“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s)。
米兰达案判决在美国社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将完全颠覆州级刑事审判程序,破坏美国的联邦制原则,甚至在许多人的眼中,该判决无异于是在纵容犯罪,但是,最高法院在州级刑事审判领域内推进《权利法案》联邦化的立场是相当坚决的。在米兰达案之后,最高法院又先后在一系列案件中,判定州政府必须严格遵守《权利法案》确立的“陪审团迅速审判”和“一罪不二罚”等原则(44),从而在美国社会中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州级刑事诉讼程序改革。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在20世纪60年代推动《权利法案》联邦化快速发展,首要原因是美国当代平等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自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人就在支持经济改革的同时,迫切要求联邦政府保护公民享有平等的宪法权利。二战后,由于美国经济繁荣、高等教育普及,以及美国在国际上对“民主、自由”的标榜,人们对平等权利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不仅出现了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而且越来越多的民权利益集团也力图通过司法诉讼,加速推进《权利法案》联邦化。平等权利意识的提高和民权案件的增多,不仅为最高法院加速推进《权利法案》联邦化提供了适宜的社会舆论,而且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其次,最高法院大法官司法理念的变化是《权利法案》联邦化加速推行的内在动力。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最高法院内部人员的调整,以厄尔·沃伦(Earl Warren)、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和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为代表的自由派大法官占据了多数。他们不仅崇尚平等权利,而且也大都是司法行动主义者,主张最高法院不必完全拘泥于法律文本和司法先例,而是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创造性地行使司法审查权。正如道格拉斯大法官所说,不断地“重新审视”既有的法律和先例,“才是一个法院的良好行为”,唯有如此,才能“使古老的宪法适应时代的需求”(45)。正是在这种自由主义司法理念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的最高法院才得以冲破法院内外的重重阻力,推动了《权利法案》联邦化的快速发展。
《权利法案》联邦化的推进,使公民在联邦和州两级政府的管理中,都能够获得相同的宪法保护,实现了美国公民权利的统一,这就极大地拓展和提高了美国公民权利保护的范围和力度,在美国宪政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纵观《权利法案》联邦化的历史进程,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其一,美国主流社会思潮的变动和联邦最高法院司法理念的转变,在《权利法案》联邦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美国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不断追求,以及最高法院的主流司法理念从恪守法律文本转向实现社会需求,才使得《权利法案》联邦化逐步变为现实。其二,尽管最高法院是以“选择性纳入观”作为《权利法案》联邦化的基本原则,但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大法官们的推动下,除个别条款外,几乎整个《权利法案》都被最高法院“纳入”到了第14条宪法修正案(46)。可以说,在《权利法案》联邦化进程中,最高法院是以卡多佐的“选择性纳入观”为路径,达到了布莱克的“整体性纳入观”的目的。《权利法案》联邦化的进程几近完成,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还仍然保持着“选择性纳入”的外表而已。
注释:
①Akhil R.Amar,"Hugo Black and the Hall of Fame",Alabama Law Review,Vol.53,No.4,2002,p.1222.
②Charles Fairman,"Does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Incorporate the Bill of Rights?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Stanford Law Review,Vol.2,No.1,1949,pp.5-139.William W.Crosskey,"Charles Fairman,'Legislative Histor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on State Authori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22,No.1,1954,pp.1-143.
③Joseph B.James,The Framing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6.Louis Henkin,"Selective Incorporation in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Yale Law Journal,Vol.73,No.1,1963,pp.74-88.Frank H.Walker,Jr.,"Constitutional Law-Was It Intended That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Incorporates the Bill of Rights?"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Vol.42,1964,pp.925-936.
④Raoul Berger,Government by Judiciary: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nd the Bill of Rights,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9.Michael K.Curtis,"The Bill of Rights as a Limitation on State Authority:A Reply to Professor Berger",Wake Forest Law Review,Vol.16,1980.pp.45-101.No State Shall Abridge: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nd the Bill of Right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6.
⑤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任东来、胡晓进等:《在宪政的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胡晓进:《每个人的权利——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与美国民权的历史演变》。公丕祥主编:《法制现代化研究》第10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5-103页。
⑥Henry Abraham and Barbara A.Perry,Freedom and the Court: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3,p.34.
⑦[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27-431页。
⑧Alfred H.Kelly,et al.,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Vol.Ⅰ,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1991,p.106.
⑨Robert A.Rutland,The Birth of the Bill of Rights,1776-1791,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3,p.129.
⑩[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洪德、杨静辉译,潘华仿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页。
(11)Johnny H.Killian,et al.eds.,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2,p.1000.
(12)Raoul Berger,Government by Judiciary: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34.
(13)Alfred H.Kelly,et al.,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Vol.,Ⅰ,pp.46-47,53-55.
(14)Henry Abraham and Barbara A.Perry,Freedom and the Court: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pp.34-35.
(15)Barron v.Baltimore,32 U.S.243 (1833),250,249.
(16)Henry Abraham and Barbara A.Perry,Freedom and the Court: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p.39.
(17)Slaughterhouse Cases ,83 U.S.36 (1873),72-74,79,76,74
(18)Slaughterhouse Cases,83 U.S.36 (1873),95-96.
(19)O'Neil v.Vermont,144 U.S.323 (1892); Maxwell v.Dow,176 U.S.581 (1900); Twining v.New Jersey,211 U.S.78 (1908).
(20)Hurtado v.California,110 U.S.516 (1884),546.
(21)O'Neil v.Vermont,144 U.S.323 (1892),370.
(22)William M.Wiecek,Liberty Under Law: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Lif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p.112-113.
(23)Bernard Schwartz,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Legal Thought,Durham:Carolina Academic Press,1993,p.340.
(24)Raoul Berger,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nd the Bill of Rights,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9,pp.50-52.
(25)Slaughterhouse Cases,83 U.S.36 (1873),82.
(26)Gitlow v.New York,268 U.S.652 (1925),666.
(27)有学者认为,在1897年的“芝加哥、伯灵顿和昆西铁路公司诉芝加哥案”(Chicago,Burlington & Quincy Railroad Co.v.Chicago,166 U.S.226)中,最高法院裁定,政府在征用私人财产时必须给予“公平赔偿”,这是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所要求的,由于“公平赔偿”原则正是第5条宪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因此,该案应被视为《权利法案》联邦化的开始。但是,笔者认为,“公平赔偿”原则也是伊利诺伊州宪法的重要内容,最高法院的判决正是从芝加哥市政府违反州宪法的角度作出的,并未涉及第5条宪法修正案的“公平赔偿”原则,因此,该案不能被认定为《权利法案》联邦化开始的标志。还有学者认为,在1908年的“特文宁诉新泽西州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权利法案》中的某些规定是可以通过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约束州政府的,因此,该案应是《权利法案》联邦化的开始。笔者认为,虽然最高法院在特文宁案中承认了“纳入”的可行性,该案也直接涉及了第5条宪法修正案的公民“不得自证其罪”原则,但最高法院在判决中不承认“不得自证其罪”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未将该原则“纳入”到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中。因此,特文宁案并不意味着《权利法案》联邦化进程的开始。
(28)Paul L.Murphy,The Constitution in Crisis Times:1918-1969,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2,p.83.
(29)Gilbert v.Minnesota,254 U.S.325 (1920),343.
(30)DeJonge v.Oregon,299 U.S.353 (1937); Cantwell v.Connecticut,310 U.S.296 (1940); Everson v.Board of Education,330 U.S.1 (1947); Wolf v.Colorado,338 U.S.25 (1949).
(31)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Co.,304 U.S.144 (1938),155.
(32)Henry Abraham and Barbara A.Perry,Freedom and the Court: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p.17.
(33)Palko v.Connecticut,302 U.S.319 (1937),323,325-326.
(34)Adamson v.California,332 U.S.46 (1947),89.
(35)Adamson v.California,332 U.S.46 (1947),66-67.
(36)Charles Fairman,"Does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Incorporate the Bill of Rights?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Stanford Law Review,Vol.2,No.1.1949,pp.81-132.
(37)Edwards v.South Carolina,372 U.S.229 (1963),229-238.
(38)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376U.S.254 (1964),270-272,279-280.Tinker v.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393 U.S.503 (1969),505-511.
(39)Engel v.Vitale,370 U.S.421 (1962),430-431.
(40)School District of Abington Township v.Schempp,374 U.S.203 (1963); Epperson v.Arkansas,393 U.S.97 (1968).
(41)Mapp v.Ohio,367 U.S.643 (1961),655-660.
(42)Gideon v.Wainwright,372 U.S.335 (1963),344.
(43)Miranda v.Arizona,384 U.436 (1966),458,479.
(44)Klopfer v.North Carolina,386 U.S.213 (1967); Duncan v.Louisiana,391 U.S.145 (1968); Benton v.Maryland,395 U.S.784 (1969).
(45)Melvin I.Urofsky,"William O.Douglas as Common-Law Judge",in Mark Tushnet,ed.,The Warren Court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3,pp.82-83.
(46)最新的“纳入”案件是2010年6月28日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的“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McDonald v.Chicago,No:08-1521,2010)。最高法院在该案判决中认为,第2条宪法修正案中的“公民合法持枪权”条款同样适用于各州。
标签:权利法案论文; 联邦政府论文; 大法官论文; 美国最高法院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联邦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豁免权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