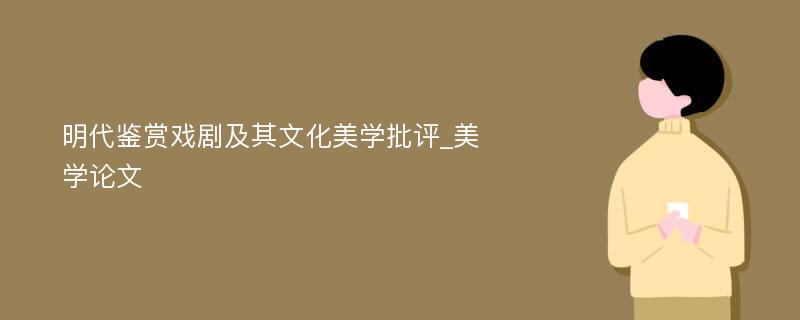
明代赏玩及其文化、美学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美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断代文化史、美学史重要标识的明代赏玩文化、美学,有其独特而完备的形态和内涵,既显示了感性主义的高涨、审美的发展,又体现了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式微和艺术的沉沦。对明代赏玩的形态、品类,明代笔记、艺术论著广有录载,文本资料丰赡,但缺少社会性文化、美学的解构。今人进人这一领域,研究成果值得重视,但尚需作为独立的现象、范畴加以审视,整合历时态与共时态,从文化史、美学史维度,思潮更迭、风习染化层面上,研究其前后代联系和形成基因及其所透现出的文化、审美品格。对明代中后期的所谓个性解放、启蒙主义过高估计的语境,遮蔽了对赏玩的文化、美学反思。坚守批判的立场,揭示明代赏玩所缺失的文化、美学精神及其对社会、历史的负面作用,就是一项新的课题。本文循着这一路向,展开探究。
一、历史坐标图上的赏玩
赏玩文化、美学在宋代已产生,北宋欧阳修等人是其开创者。王明清《〈挥麈录〉馀话》说:“本朝自欧阳子(修)、刘原父(敞)始辑三代鼎彝,张而明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言欧阳修“独好古石刻”。欧阳修积10年之劳,完成了集录千卷金石文的《集古录》,所涉猎搜集范围极广,“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以来圣贤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事伟丽工妙可喜之物”。袁燮《行状》记袁文“颇喜古图书器玩,环列左右,前辈诸公笔墨,尤所珍爱,时时展玩”。李清照那篇著名的《〈金石录〉后序》详尽介绍了与丈夫赵明诚节衣缩食于市肆中淘古玩的情形,洋溢着夫妇间赏鉴古玩的盎然情趣。据《宋史》本传,书画家的米芾也是古玩家,“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宋徽宗赵佶更是一名大玩家,“效(李)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五百有已”(《铁围山丛谈》卷四)。到了南宋,在粉汗如雨、脂腻成河的西湖杭州,偏安日久,不思恢复,直把临安作汴梁的社会环境所孕生的社会文化心态更使玩风大炽。据周密《齐东野语》卷六,宋高宗“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展玩摹拓不少怠”。宋代成为后代赏玩的直接源头。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就是这方面的记录,也成为赏玩的最早文献。明代的赏玩文化、美学正是承绪了这一文化史、美学史传统。
然而,明代赏玩文化、美学又有一个渐成气候,直至形态完备、独立成体的过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曾认为,“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从士大夫阶层开始“滥觞倾橐相酬”,发展到“真赝不可复辨”的地步。沈德符《敝帚斋馀谈》又写道:“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之大贾,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它有一个扩散过程,最终成为商业炒作行为,其历史区段被史家定在嘉靖年间。《万历野获编》说,“嘉靖末年,海内晏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终于蔚为大观;其区域则以江南为盛,于是,嘉靖时期江南地区便成为明代赏玩文化的时空标识。
明代赏玩文化、美学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和领域展开,涉及钟鼎、彝器、法书、画册、窑器、漆器、石印、琴瑟、剑器、古镜、坐几、椅榻、文房四件、小虫动物等等。高濂《遵生八笺》曾说自己“遍好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凡可加以玩弄、鉴赏的,均数纳入。古玩诚属其中,但非赏玩全部。它涉及历史遗存,又有当时鲜货;延续前代对象,又有新的扩展。它成了社会文化、美学风习,所谓“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袁宏道:《时尚》)。这些器物一开始兴起于吴中地区,经过“狷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以广泛存在的赏玩物质器物为基础,明代便出现了大量的赏玩文化、美学著说,具代表性的有:屠隆《考槃馀事》、高濂《遵生八笺》、张应文《清秘藏》、文震亨《长物志》、董其昌《骨董十三说》、陈继儒《泥古录》、谷应泰《博物要览》、周高起《阳羡名壶录》等(明人众多笔记中谈论赏玩的,亦归入其中,如谢肇淛的《五杂俎》),还有具备集成性的沈津所辑60卷《重订欣赏篇》,极一时之盛。形态和著述共同表征着明代赏玩文化、美学的繁博现象。
二、赏玩的形成基因.
明人赏玩文化、美学的兴盛跟整个社会风习的变化密切相关。明代中后期思潮出现重大更迭,“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说郛》)缺失晋宋的玄远精神,却于齐梁绮靡大有过之,足见当时的社会风习及其状态。《金瓶梅》便成为其全方位写照。而在具体的个体身上,张岱《自为墓志铭》的自我描述则极具代表性,他说:“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在惊人的一无遮拦的近乎供词的自我坦陈中,不仅体现了人欲的膨胀和泛滥,更在于其表现出了自我陶醉的心态。当然,这包括了“好古董”等赏玩在内的文化类型。这是感性欲望在相适存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又是人对自身欲望和需求的进一步发现。意识是先导的,当人处在严格的理性制约之中无法或不能萌发这些需求,即使偶尔有之或潜在出现,也会被自身的理性意识所抑制和消解,无需外在社会力量,遂成为意识的自觉行为。一旦感性颠覆了理性,欲望需求无法平抑和克服,就去寻求满足的对象,这是明代赏玩的心理背景。玩物丧志是理性规范,“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书·旅獒》)晚明人完全作了否定,在他们看来是玩物得志,费元禄在《晁采清课》中就直言不讳地说:“玩物采真。”.
赏玩文化、美学的兴盛又是明代人对自我精神加以塑造的结果。袁宏道在《与潘景升》中说:“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纵使易之,亦未必有补于品格也。”这是解读明代赏玩文化、美学的重要材料。最早关于名士的解释,有《后汉书·〈方术传〉论》:“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风流倜傥、恃才傲物、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不知外境、不通时务,作为名士要素是相粘合的。魏晋名士以药、酒显名,此后名士的自身涵值也便以其需求和欲望的延伸而得到发展。其中便如上引袁宏道所说,应当有一种嗜好,即癖好,而且终身不变;如果改变,或转移兴趣,那就改味。即使改变了嗜好,也未必能补充名士的品格。这种嗜求,不再是魏晋药、酒的口欲,而是增加了一项——物欲——玩物,如林逋(和靖)之于梅,米芾(元章)之于石。对名士构成条件的新规定,实在是晚明名士对自身特征的新确定,从而为赏玩文化、美学的出现提供了学理基础。
赏玩文化、美学还被解读和定位为生理需求和生活方式、情调的替代性对象。“饭余晏坐”时,“别设净几”,“辅以丹罽,袭以文锦”,“次第出其所藏,列而玩之”,且“玩古董,有助于祛病延年”(董其昌:《骨董十三说·八说》),获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健康效应。这便把赏玩效能自我提升到极具诱惑力和吸引力的层面,进一步确立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赏玩的文化、审美精神品格
赏玩的文化、审美格调,也是从宋代逐步形成起来的。赵希鹄曾诗性化地描述道:“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如亲见商周。端砚涌崖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洞天清录集〉序》)在赏鉴古玩中获得了身心的满足和超越。其超越性满足,提升了文化和审美的品位,进入精神层面。虽然有人认为明代人的这套玩意儿还没有玩出“洞天清录”的框架之外,但明人经过整合后,总体和分类形态均有所发展。
赏与玩的整合,建构成完整的赏玩文化—美学。明代士大夫出现了收藏家与鉴赏家兼备型的统一角色。收藏不是商品增殖手段,而是精神满足行为。赏玩——鉴赏、把玩,玩中含赏,构合为玩便是赏的行为方式。因为以赏作为内在的精神涵义,就使得玩并不流于一般水准,而居于风雅层面,正如文震亨《长物志》所说的“雅观”、“雅致”、“古雅可爱”,而沈春泽为《长物志》所写《序》中不绝于口地赞赏“爽而倩”、“古而洁”、“秀而远”、“宜而趣”、“奇而逸”、“隽而永”、“巧而自然”、“淡而可思”,也只有赏与玩相得、收藏与鉴赏相合才能达到,否则以奇货可居,收藏诚然丰硕,但也只是个肉头财主。高濂吸收了宋代著名书画家、古玩家米芾对好事家与鉴赏家从文化、美学的角度加以区分的理论,指出“多资蓄,贪名好胜,遇物收置……此谓好事”;而鉴赏家则是“天资高明,遇物收置,多阅传录,或自能画,或深知画意,每得一图,终日宝玩,如对古人,声色之奉不能夺也”,这才叫做“真赏”(《遵生八笺》)。沈春泽详尽描述了判然不同的两种赏玩态度:“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何也?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逾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挲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长物志〉序》)张岱也认为,“博洽好古,犹是文人韵事。”(《陶庵梦忆》)“文人韵事”便是对赏玩文化、美学性质的定位,于是,就出现文野、雅俗之分。基于这种文化、美学认知,明代的一些笔记小品中就多有对粗、俗的藏而无赏、玩而无识行为的嘲弄记载。例如郎瑛就曾记道:“嘉靖初,南京守备太监高隆,人有献名画者,高曰:‘好,好!但上方多素绢,再添一个三战吕布最佳。’人传为笑。”(《七修类稿》)笑话记载所反射出的思想是明代士大夫对赏玩文化、美学品位、格调畛域的坚持和固守。明人笔记和赏玩著录充满对“俗”的轻蔑,往往斥之为“恶俗”、“恶道”、“酸气”,并将之纳入以“韵”为核心范畴的明代美学语境之中。
这样,明代赏玩便以文化、美学为内涵和基因。名士们通过赏玩,形成了对某一具体对象的文化、美学定评,遂成为公论。例如张应文《清秘藏》对书法,尤其对颜书的评赏;高濂《遵生八笺》利用大量案例,对器玩的真伪、优劣、雅俗,反复加以品鉴,凝聚了许多真知灼见,其中对宋瓷汝、哥、官窑器的鉴赏极富眼识:汝窑“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哥窑质之隐纹如鱼子”。他在观照瓷品时,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感受:“余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顿令腹饱。”明代繁富的赏玩小品文不是收藏工具书,而是鉴赏经验凝结和导引鉴赏的文字。例如对文震亨的《长物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曾评述道:“震亨世以书画擅名,耳濡目染,与众本殊。故所言收藏赏鉴诸法,亦具有条理。”他们所做的是赏玩指导和兴趣指引,孰是孰否中包含着孰粗孰精的文化、审美评价。例如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对石的品鉴,认为灵璧石以韵胜,宜乎做磬材;端、歙右以质胜,宜乎做砚材。高濂《遵生八笺》对明代宣(德)成(化)等窑器的比较也极具文化、美学眼光和识鉴水平。他认为,“成窑上品”,“精妙可人”;又认为,青花瓷成窑不及“宣(德)五彩,宣庙(明宣宗朱瞻基)不及宪庙(明宪宗朱见深)。宣窑之青,乃苏浡泥青也,后俱用尽。至成窑时,皆平等青矣。宣窑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而成窑五彩,用色浅淡,颇有画意。”对这种富于穿透力的鉴赏收获,他颇为自得:“此余评似确然,允哉!”
文化和美学精神在赏玩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也有相应的体现,或者说以文化、美学精神对待,并进而借助其表达出来。摆弄的虽是具体物什,透发的则是提升了的精神品格。例如屠隆对盆景的描述:“盆景以几案可置者为佳,其次则列之庭榭中物也。最古雅者,如天目之松,高可盈尺,其本如臂,针毛短簇,结为马远之欹斜诘曲,郭熙之露顶攫拿,刘松年之偃亚层叠,盛之昭之拖拽轩翥等状,栽以佳器,槎牙可观。更有一枝两三梗者,或栽三五窠,结为山林,排匝高下参差。更以透漏窈窕,奇古石笋,安插得体,置诸中庭。对独本者,若坐冈陵之巅,与孤松盘桓;对双本者,似入松林深处,令人六月忘暑。”(《考槃馀事·盆玩》)虽然言说的是如何选材、操作,但支配这种行为的则是文化、美学意识。
赏玩的审美标准和理想是“清”,“清者,大雅之本原”(徐上灜:《溪山琴况》)。“清”的审美理想起于魏晋,是人的精神特质的范本;唐代之“清”,是“清水出芙蓉”(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诗歌审美理想的表征。“清”作为审美理想的文化诉求,氤氲着浓厚的士大夫气息,对应着独特的文化阶层——“清流”。清则净,清则高,于赏玩遂有“清玩”,元代欧阳玄《题山庄所藏东坡画古木图》诗云:“山庄刘氏富清玩,家有苏公旧挥翰。”这样,“清”便成为明代赏玩文化的主体美学精神,也是主流美学精神。其实,“清”是绚烂富贵之极复转平淡清雅的归返型精神体现,在思想、精神上有着看似奇特实属必然的原因。董其昌揭示道:“故浓艳之极,必趋平淡;热闹当场,忽思清虚。”(《骨董十三说·五说》)这与宋代苏轼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提法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体现了物极必反的转换型思想演化机制。董其昌就认为:“好古董,乃好声色之馀也。”这一现象只有在明代经过烈火烹油的繁盛之后才可能出现,有着具体的历史文化、美学涵值。
宋代以降,中国文化中的闲适气渐行渐浓,南宋赵师秀《约客》中的句子“闲敲棋子落灯花”,最能体现这种情调。闲中得清,“清闲”遂成一完整范畴。明代有不少小品就专以“清”命名,如张应文的《清秘藏》、程羽文的《清闲供》等;有些书题虽未直接标示,但内中的篇章却有之,如高濂的《遵生八笺》中便有《燕闲清赏笺》。他在《序》中具体描述和阐释道:“座陈钟鼎,几列琴书,榻排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妍,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于是,古琴成为居室摆设的第一选择,“无论能操或不善操”,也得“有琴”;没有古琴,“新琴亦须壁悬一床”。文震亨《长物志》亦有相同表述,并要求“琴轸”须“犀角、象牙”所制,才够“雅”。“清赏”成为明人审美品赏的范畴和标准。高濂就曾说:“闽中牙刻人物,工致纤巧,奈无置放处,不入清赏。”(《遵生八笺》)
“闲”为士大夫所固有,又成为其追求。高濂《遵生八笺》对“闲”做了具体阐解:“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闲可以养性,可以悦心,可以怡生安寿。”在明人看来,“闲”是人生、世间罕有的福祉。华淑在《题〈闲情小品〉序》中明确认为,“闲”是“清福”,跟“名墙利垄”相绝缘。他深情地描述了“闲”的各种形态:“晨推窗,红雨乱飞,闲花笑也;绿树有声,闲鸟啼也;烟岚明没,闲云度也;藻荇可数,闲池静也;风细帘清,林空月印,闲庭悄也。”更有“闲侣”、“闲编”、“闲想”、“闲辞”等等。有“闲”才得“清”,有闲适的时间和心态才能享受这份“清福”。清闲式赏玩的第一境界恍如禅境,如张大复所说,“意思虚闲,世界清净,我身我心,了不可取”(《梅花草堂笔谈》),禅的境界正是审美的境界。于是,又派生出“幽赏”的范畴,幽赏体现了清赏的特有内涵。幽赏在高濂看来,视觉上“娱目悦心,静赏无厌”;听觉上虽“不悦人耳”,却“惟幽赏者能共之”;在精神层面上,“市门未易知也”(《遵生八笺》),跟世俗绝缘。而明人的清赏又不具有类别的单一性,在他们看来,四时皆有清赏对象,无处不有清赏存在,显示出审美的宽容和兴趣的宽泛,这跟前代的选择性是有区别的。例如高濂的《遵生八笺》有《四时调摄笺》,四季均有名目繁多的“幽赏”节目,例如春季的西泠桥玩落花、虎跑泉试新茶等,夏季的空亭坐月鸣琴、步山径野花幽鸟等,秋季资岩山下看石笋、策杖林园访菊等,冬季扫雪烹茶玩画、除夕登吴山看松盆等。他们从心理需求和趣味出发,去寻求相应的对象,获得相一致的建构图式。这是就一年四季而言,就一天的安排来说,程羽文《清闲供》写道:“晨起,下帷,检牙签(按:藏书者系于书函作为翻检标志的象牙制签牌。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挹露研朱点校。寓中操琴调鹤,玩金石鼎彝。晌午,用莲房,洗砚,理茶具,拭梧竹。午后,戴白接幂,着隐士衫,望红树叶落,得句题其上。日晡,持蟹螯鲈脍,酌海川螺,试新酿,醉弄洞箫数声。薄暮……焚伴月香,壅菊。”这和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所描述的牛背牧歌式的闲适生活在情调上相承,在内容上有异,即增加了“玩金石鼎彝”的项目。同时,空间上,前者在田园隐居中,后者在园林市隐中,这正是明代士大夫生活审美化的特色。
要之,清流士人阶层,以清闲的生活状态,清(幽)赏着、清玩着清供,尽情享受着清福。诚然自得,不乏作秀;虽云清雅,亦含俗气。这便是明代人日常生活形态和方式审美化的流程和图像。
四、文化、美学批判
明代人是玩角、玩家,而且是大玩角、大玩家。整个社会、文化界红尘滚滚,竞相以赏玩为风雅、为时尚。这是一个既氤氲着清风、又弥散着俗气的矛盾交错的时代,不可用专一的审美形态形容之或用单一的审美理想概括之。文化的品位、审美的品格差距极大,不啻天渊。张瀚曾说,当时的社会“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松窗梦语》)。人性泛滥,光怪陆离,男风兴盛,前引张岱《自为墓志铭》中的“好娈童”,就是坦直的自画供。明穆宗朱载星就曾屡屡潜出宫门,寻欢于京城玩娈童的去处——帘子胡同。同性恋,其小说描写的人物形象在《金瓶梅》中就有几个——西门庆、玳安、“温屁股”。在这一点上,《金瓶梅》有着惊人的现实逼真性,应予足够评价。世风如此,玩得心跳,赏玩界便造假成风、颓靡成习,导致对象的真赝不辨、品位的良莠不齐。这倒用得着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学原理。因为有需求市场,才会出现赝品,低文化阶层又以庸者趋雅的特有攀附心理煽扬,这是古今时代共有共生之现象。播红飘绿、飞扬浮躁,是其社会温床。特别是文拙位高、品低禄厚者,生怕士大夫瞧不起而偏要钻进去,玩一回深沉,更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明代关于此类记述,不绝于书,也是缘由有自。高濂《遵生八笺》说:“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遗。”其造假物品覆盖整个赏玩界,明画冒充宋画,明玉标成汉玉,比比皆是;器物款式、花纹,足可乱真。即使本朝本代,也互相“克隆”,假冒宣德炉,伪造成化窑。晚明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说:“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绔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直可笑也。”造假方式五花八门,高濂《遵生八笺》详尽披露了当时假造古董的方法和流程。有些手段可谓想落天外,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刘心瑶《玉纪补》记道,为造假玉,“杀狗不使出血,乘热纳玉器于其腹中,缝固,埋之通衢,数年取出,则玉上自有土衣、血斑,以为‘土古’”。谢肇湖曾作小品《秦士》,写道:
秦士有好古物者,价虽贵,必购之。一日,有人持败席一扇,踵门而告曰:“昔鲁哀公命席以问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惬,以为古,遂以负郭之田易之。逾时,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远,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王避狄,杖策去邠时所操之箠也,盖先孔子又数百年矣,子何以偿我?”秦士大喜,因倾家资悉与之。既而,又有持朽漆碗一只,曰:“席与杖皆周时物,固未古也。此碗乃舜造漆器时作,盖又远于周矣,子何以偿我?”秦士愈以为远,遂虚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舍资用尽去,至无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终未忍舍三器。于是披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执舜所作之碗,行乞于市,曰:“哪个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钱,乞我一文。”闻者喷饭。
明代城市消费发达,赏玩已成为一种产业,进入并进而形成市场,但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一开始的缺陷,没有准备和缺少过程,使得市场缺少或没有规范。在市场货贸交流、交换过程中,维系信用的,还仅仅是传统的诚信理念。一旦现存秩序被冲决,传统被搁置,消费主义膨胀,市场变得失范,投附庸者所好,赝品、假货顷刻走俏,骗子、骗术大行其道。针对这种状况,明代还出版了三卷本的《杜骗新书》,列举了24种骗术行当。随着市场化、货币化的进程,连一些赏玩专书也坚守不住底线而退却,脱略了艺术审美评价标准,转而采用价格尺度。例如曹昭的《格古要论》对古玩的评判,最后都钻进钱眼——“价低”、“不甚值钱”等,即使是以清高自鸣的《长物志》也时现这类字眼。赏玩市场热闹而混乱的状况,倒成为一扇窗口,展现出明代繁华而虚热的整体社会、文化状况。器物的“克隆”也带来了述器之文的剿袭,分辨不清谁是原创的,难以坐实哪是剽窃的,这倒应验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名言,明代版本的复杂性、混乱性,也能由此探赜到部分原因。
明代人的赏玩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想得出,便能玩得出,他们玩的想头、功夫得到无所不及的开发和发挥。例如袁宏道有《斗蚁》一文,写道:“取松间大蚁,剪去头上双须,彼此斗咬,至死不休。问之,则曰:‘蚁以须为眼,凡行动之时,先以须左右审视,然后疾趋。一抉其须,即不能行。既愤不见,因以死斗。’试之良然。余谓蚁以须视,古未前闻,且蚁未尝无目,必恃须而行,亦异事也。”如此未有之奇事,袁宏道甚觉惊异,便录以存照。袁宏道还写有《斗蛛》小品,同样惊异于“斗蛛之法,古未闻有”,具体玩法是:
每春和时,觅小蛛脚指长者,人各数枚,养之窗间,较胜负为乐。蛛多在壁阴及案板下,网止数经无纬。捕之勿急,急则怯,一怯则终身不能斗。宜雌不宜雄,雄遇敌则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极易。养之之法,先取别蛛子未出者,粘窗间纸上,虽蛛见之,认为己子,爱护甚至。见他蛛来,以为夺己,极力御之。惟腹中有子及己出子者不宜用。登场之时,初以足相搏;数交之后,猛气愈厉,怒爪狞狞,不复见身。胜者以丝缚敌,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败走者,有势均力敌数交即罢者……其色黧者为上,灰者为次,杂色为下。名目亦多,曰玄虎、鹰爪、玳瑁肚、黑张经、夜叉头、喜娘、小铁嘴,各因其形似以为字。
还有斗蟋蟀,清人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中广为人知的《促织》,开篇第一句便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说的正是明代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录了当时一首歌谣:“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到万历年间仍如此。袁宏道作于其间的《畜促织》写道:
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每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跃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虫生于草土者,其身软;生于砖石者,其体刚;生于浅草瘠土砖石深坑向阳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黄不如青。白麻头青项金翅金银丝额,上也;黄麻头,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其形以头项肥脚腿长身背阔者为上,头尖项紧脚瘦腿薄者为下。虫病有四……其名色……不可尽载。养法用鳜鱼、茭肉、芦根虫、断节虫、扁担虫、煮熟栗子、黄米饭。医治之法:嚼牙喂带血蚊虫,内热用豆芽尖叶,落胎粪结用虾婆,头昏用川芎茶浴,咬伤用童便蚯蚓粪调和,点其疮口。凡促织之态貌情性,纤悉必具。嗟乎,一虫之微妙曲折如此。
越是花样翻新、名目繁多、匪夷所思,越是反映出人的沉沦、无聊、堕落。无所事事,便想出玩虫子、玩雀子的事儿来;餍足之后,再要逐异和寻求刺激,就只能标新立异了。
这是缺少志向的时代,失去了社会要求。从理性一下跌入感性、从桎梏猛然跳到放荡,失控后出现无序。人们在钻地而出的繁糜面前,晕头转向而不知所以,一切跟着感觉走。感性统治,成为社会主流话语,没有宇宙意识,亦乏自然科学精神,沉浸于身边空间,目之所即、手之所触,皆成乐趣,于是锢守成自我封闭空间。从上引袁宏道的两篇小品文不难看出明代人是何等会玩、会享乐。就袁宏道和蒲松龄的这篇同题作品而言,放在同一坐标上,袁氏要惭愧了,不知颜汗又添几重!蒲氏《促织》充满震慄人心的社会批判力量,但袁宏道在文章中那样津津乐道引以为趣,恰是表明了那个时代的人,其心田中社会责任感、历史忧患意识已无有几何了。
这是由自我封闭,进而自我沉陷、自寻乐趣的世界。他们较少民生关切、人文关怀、社会关爱,他们属于自慰性的身心满足。他们寻求的不是传统的人格理想的实现和文化批判实践,而是情绪、乐趣的自我陶醉,眼球的自我吸附。因为是回归一己之心,以得一己之乐,便极易满足。既不需要先辈唐人马上功名的意气,也不需要前贤宋人穷思究理的深思。袁中道《砚水楼记》曾记到袁宏道所言的最高志向是“聚万卷书”,“作老蠹鱼,游戏题躞,兴之所到,时复挥洒数语,以疏瀹性灵”,能得此,“志毕矣”。谢肇淛的最高理想,则是如其在《五杂俎》中所言,“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谈笑,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毕矣”、“极矣”,都表明是一种极致性的理想,从而又表明他们理想不高、志存不远,浅近得很。他们已没有或失去了“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目标设置委实有限,只是在方寸之内获得身心微醺式的快意,袁宏道在《与龚惟长》中所说的“五快活”即指此。悬置深刻、缺乏深邃,正因为如此,才会产生“性灵”派,“性灵”的最主要内涵就是感性需求。家居之内便是世事,便是自我的整体世界,正因为如此,他们便对组成这个世界的微部细件打理得精致细微、玲珑剔透。为什么会有文震亨的《长物志》呢?为什么会有袁宏道的《瓶史》呢?为什么会有盆景等等居室摆设呢?其思想追究的原由确实很深。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征。
盆景是缩化了的自然风物,在缩化过程中又有着人为的加工和扭变因素。前引屠隆《考槃馀事·盆玩》认为“盆景以几案可置者为佳”,其次才是“列之庭榭中物”。它失去了原生态的自然性和天然性,显得造作,然而却为明人所欣赏不已,正适存于明人有些扭曲的文化、审美心态。以此装点家居、庭院、园林,成为人造家居环境中最具有理想性自然生态的摆设和自我观赏的对象,主人也就以此来显示自身的自然、人文审美品位。文震亨的《长物志》列有专门的《盆玩》;陈淏子《花镜》辟有《种盆取景法》专节,提出用画意法置盆景:“随意叠成山林佳景,置数盆于高轩书室之前,诚雅人清供也。”盆景成了士大夫清供之一类,在这里,他们是不在意于对象的被扭曲和变形化的;或者说,扭曲和变形,才足以体现其心态和心理需求。
明人用极为细腻的审美机心观照并摆弄着一些具体而微的装点饰物,而其见解和做法则包含着许多具体而微的审美做法。就插花而言,文震亨《长物志》专列《器具》,他认为,插花器物质料“贵铜、瓦,贱金、银”,铜、瓦经风化后的土色古气可形成与花色的视觉感知对比,而金、银显富贵气,无雅味;对瓶的形体要求,“宁瘦,无过壮;宁大,无过小”,具有形式结构比例的审美原理。袁宏道的《瓶花》对插花艺术做了最全面、最完整的审美规定和描述。首先,把插花当成赏玩文化、审美行为看待。赏花应是清赏:“赏花有地有时,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皆为唐突。寒花宜初雪,宜新月,宜暖房。温花宜晴日,宜轻寒,宜华堂。暑花宜雨后,宜快风,宜佳木阴,宜竹下,宜水阁。凉花宜爽月,宜夕阳,宜空阶,宜苔径,宜古藤巉石边。”如果完全不顾及这些外在的环境和因素,其赏花就如同置身“妓院酒馆”中一样。其次,是形式美学的配置:“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青莲之诗不拘对偶,此真整齐也。若夫枝叶相当,红白相配,比……墓门华表也,恶得为整齐哉?”他所说的参差中求整齐,正有着一定的审美原理。又列“瓶花之宜、之忌、之法”,涉及几十种花类,对如何折花、如何配置、如何用水、如何分插、如何放置等,均有详尽规定,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例如对冬天插花,规定到如此具体的地步:“须用锡管,不惟不坏瓷瓶,即铜者亦畏冰冻。”但是,可操作性过强、过碎,便弱化了灵机活泼的审美性和可发挥的空间、可填补的余地。而以瓶花作为装点赏玩对象,则是对固有生机的戕害,同时,加进了过多的人工和艺术构想,反伤原初之自然性质。于此,可以看出明人心机的精致,会生活、懂艺术,精细、精约,但缺位的却是美所最具活力的“气韵生动”和原始生态以及中国文化、美学最基本的民生关切、人文关怀精神。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人物龚自珍写有一篇著名的《病梅馆记》,认为把盆景梅花“斫直、删密、锄正”,就变成了“病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正是明代赏玩的遗传,造成扭曲和病态。龚自珍则把所购“三百盆”病梅盆景,“辟病梅之馆”,加以“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这里正隐喻性地表现了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和人文关切精神,这才是正宗的启蒙主义,十分杰出、先进,反转来就比照出明人在盆景艺术中所透发出来的思想、精神是多么落后了。
程羽文《清闲供》提出情绪的六种表现形态:癖、狂、懒、痴、拙、傲。这些情绪表现形态有些是前代就有的,但在明代有新发展;有些是前代所未备的,为明代所新增;六种形态同时兼备,则是明代的首例。“癖”、“痴”作为专注性、专一性情绪形态,体现了长时间的投入程度,所谓积久则成习。其语初意义就有《晋书·杜预传》所言:“(杜)预尝称(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明人之“癖”、“痴”在于玩物,古往今来,种种物什,着迷入痴,身心难拔。
这是感性膨胀,欲望要求犹如百虫钻身,骚躁不安,人性复苏进而横冲直撞的必然结果。感性主义成灾是对理性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正如极端自由主义是对明初血腥专制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一样。没有规范、失去克制,任性所为,这种性,有的已沦为动物的本能性。对明代的所谓个性解放、启蒙主义思潮的评价,学界似乎过了。启蒙虽启开了过去被理学所压抑的“清”的人性,但也像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一样,“脏”的人性也纷然而出。其历史进步性和落后性并存。
这是绝意于世事后所寻求的一种耽乐方式。确实,经过启蒙,明人的许多审美感觉被唤醒,审美器官发达了,能发现一些新的对象领域,即如赏玩;也更能在发现中去玩赏,从而形成新的审美感知、经验种类。经过明代的综合整化,赏玩文化、美学构建成独立、完整的形态,或者说赏玩文化、美学是以明代为标志的,体现了审美在满足感性需求上的变化。于是,发展为清代八旗子弟的提笼架鸟、臂苍牵黄、抛石掷弹,玩雀子,斗蛐蛐,玩鼻烟壶,直至玩大烟枪,是翡翠嘴子,还是琥珀嘴子,抑或是其他。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方式长处和短处并存的集中体现。所谓赏玩,就是反复摩挲,再三品味,涵泳久之,有体认,也有直觉,但缺乏深究,更无法令人血脉贲张。尽管体认和直觉可以十分到位,直入本质,把握和解说审美优劣、真赝、高低的素质所在,然而,缺乏深究,便阻止了对审美对象物本体的缜密解说和理论、学说的建构。在大量的赏玩小品中,只有怎么做的介绍,而没有为什么这样做的理思。天阙九重,赏玩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美学的思维就到此重门前却步了。
这是审美的转移性手段。袁宏道在《给李子髯》信中说得十分准确:“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转入赏玩,是寻求另外一种生活、艺术方式,而不是冲决它、颠覆它、否定它;是为了换一种活法,活得更快活。关键是心态,高濂《遵生八笺》的《恬适自足条》列举了十种“自足”形态:穷通、取舍、眼界、贫困、辞受、燕闲、行藏、唱酬、居处、嬉游。对明代人和中国士人的心态说得颇为切当:“随在皆安,无日不足,人我无竞,身世两忘,自有无穷妙处。”他们不断找乐子,因此,不是突破,而是转移,其惰力也就在于此。即使前面得到正面肯定、评价的“清”“幽”格调,也非明人所创获,前代早已有之。虽在风调上承绪于宋,但不及宋以致元之高逸。沉湎于赏玩,当然就没有了东汉的热士,丢弃了魏晋的殉道,缺失了季宋的名节。明朝养士三百年,最终得来的,除了士群的文震亨等少数几人为之殉节、非士群的秦淮河边妓女们的几声呐喊外,却是钱谦益之流跪迎清王多铎的进城大军,以装戴花翎、染红顶子的场面。
这是把赏玩作为纯粹的文化、审美对象来看待的行为方式。其实,赏玩对象有不少门类是工艺品,有着自然科学的因子,但他们只用于玩赏,而忽略背后的科学解读和考量,因此,它助长了美学,却抑制了科学。纵容感觉,退场理思;助长情味,隔绝深刻。当明代人正汗流满面忙于斗蟋蟀、斗鹌鹑、香烟袅袅中静递古玩、煎茶小酌观赏器物时,西方思想家正潜心于自然、人文、宇宙科学的探究,为孕育并进而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工业(产业)革命提供思想先驱资源。这又不得不回到那句古训:“玩物丧志”——丧失的是民族的进取之志。以此冰山一角,可以读解晚期中国社会停滞、落后的原因了。
标签:美学论文; 袁宏道论文; 文化论文; 万历野获编论文; 明朝论文; 宋朝论文; 长物志论文; 金瓶梅论文; 遵生八笺论文; 清秘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