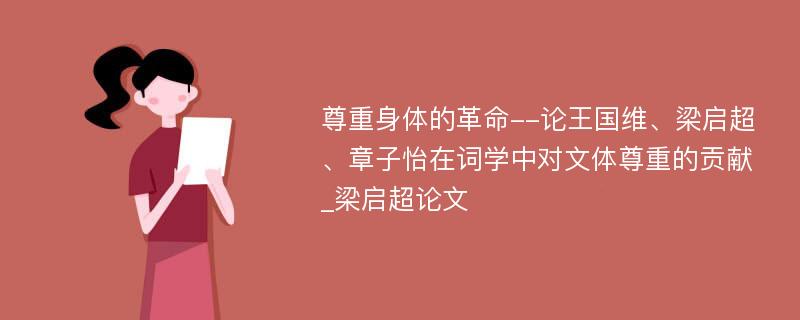
尊体的革命——试论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对词学尊体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试论论文,贡献论文,王国维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词学尊体模式的三种偏失
词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历时千余年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另一方面,词这种文学体裁自其产生之日始,地位就是十分低下的,一直被称作“小词”、“诗余”,被视作“余技”、“薄技”,从来没有过与其自身成就相适应的地位。因此,推尊词体就成为摆在历代词人、词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历代词人、词学家也确实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尊体思想,多方努力推尊词体。应该说这些努力对提升词体的地位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然而,近千年来,词体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个中原因复杂而深刻。平心而论,由于受客观条件所限,传统尊体模式确实多有偏失之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第一,推尊词体时过于强调词的功用性,而忽视其文学性。这种倾向是从宋朝南渡前后开始产生的。北宋后期词人黄裳的《演山居士新词序》第一次将道德、政治、事功等儒家所强调的价值伦理范畴引入词学:
演山居士……为长短篇及五七言,……因言:风雅颂诗之体,赋比兴诗之用,古之诗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含思则有赋,触类则有比。对景则有兴。以言乎德则有风,以言乎政则有雅,以言乎功则有颂。……然则古之歌词固有本哉!①
很显然,其所谓“歌词固有本”的“本”就是其所言的“德”、“政”和“功”,这样“歌词”就可以和“诗”一样成为承载政教的工具了,尊体之意自不待言。靖康之变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社会背景下,从政教功用角度推尊词体的思想盛行一时,竟成为当时的词学主潮,鲖阳居士②、曾丰③、强焕④、陈亮⑤等人的尊体思想都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其影响可谓深远。到了清代,词学复兴,掀起了蔚为壮观的尊体运动,在清代数家最有影响的词派当中,应属常州词派在尊体方面用力最多、建树最大,而常州词派推尊词体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以政治教化论词。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说:“(词)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⑥这明显是将词与政治教化相联系,强调词体的工具性与功用性,以求达到推尊词体的目的。应该承认,这种尊体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中对于推尊词体确实起到了相对较大的作用,常州词派的巨大影响就是证明。然而其偏颇也是非常明显并且无法克服的。词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而存在的,而文学艺术最本质的属性是其审美性,这是文学成其为文学的根本属性。而上述尊体思想没有从审美角度出发,而是从功用的角度入手,将词变成政教工具,阉割了词体的审美属性,终隔一层。常州词派的创作成就不及其理论成就,其实正是忽略文学性的不良后果。更何况词的特质是“要眇宜修”⑦,或者说是“轻”、“狭”、“小”、“隐”⑧,根本不适于用作表现政教的工具,这对于词来讲是“不能承受之重”。是为传统尊体模式偏失之一。
第二,推尊词体时过于强调词的诗化,而忽视其文体特征。这种倾向早在北宋中叶即已肇端,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是苏轼。苏轼提出“(词)盖诗之裔”,并认为词乃“古人长短句诗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轼“以诗为词”、拓展词径,用自己的实际创作为提升词体地位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宋南渡后,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苏轼的词学思想被更为广泛地接受。王灼、胡寅等在尊体理论上与苏轼相呼应;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豪放词人更是在创作实践层面沿着苏轼的道路继续发展。北方金源一代的词人也颇受“以诗为词”尊体思想的影响,王若虚即直言:“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⑨到了清代,同样提倡尊体的阳羡词派继承了苏辛的传统,其领袖陈维崧极力褒扬苏辛:“东坡、稼轩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⑩就是将苏辛之词比作杜诗和汉乐府。客观地讲,强调词的诗化、以诗为词这种尊体思想在词史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对提升词体地位也确实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有其偏颇不足之处,那就是忽视了词的文体特征。词本是一种配合流行音乐演唱的音乐文学,其最为显著的文体特征就是音乐性,“音乐性是词的生命”(11),是词之成其为词的根本属性。而上述尊体思想没有从词的文体特征出发,过于强调词的诗化,而忽视了词体的音乐性,将词变成诗的附庸或“句读不葺之诗”,毕竟隔了一层。是为传统尊体模式偏失之二。
第三,推尊词体时过度追求词体的雅正化。这种倾向最早产生于南宋。词在产生之初即带有明显的“俗”的特征,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词更是以俗著称,在当时流行极广,却被批评为“词语尘下”(12)。到了南宋初年,出现了一部署名鲖阳居士编的词总集《复雅歌词》,这一命名在词学史上第一次将“歌词”与“雅”联系起来。其后不久,又出现了曾慥编辑的词总集《乐府雅词》,直呼“雅词”,显然具有推尊词体的含义。南宋中后期,崇尚雅正成为词学思想主流,姜夔、张镃、沈义父、周密、仇远、张炎等人都力图从雅正的角度提升词的品格,使词由“下里巴人”上升为“阳春白雪”。南宋词论家从崇雅的角度推尊词体对清代的词学尊体理论带来深刻影响,浙西词派即高举“雅正”之大旗推尊词体,朱彝尊在《静惕堂词序》中即云:“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13)其中尊体意图非常明显。然而,通过提倡雅正推尊词体的方法的弊端更为明显。事实上,词自产生之日起即具有通俗性、娱乐性、活泼性等特点,即所谓“俗的一面”,而这种尊体角度忽视了词体活泼自然的一面,一味追求词体的雅正化,使词体日趋僵硬化、程式化、贵族化,而灵动性丧失殆尽。是为传统尊体模式偏失之三。
以上三种偏颇之处使古人的尊体努力如隔靴搔痒,没能根本解决尊体的课题。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三种偏失,其中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然而最为根本的原因恐怕可以归结为一个,那就是囿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人们无法正确认识词这种文学体裁的价值。应该承认,无论是尊体时过于强调词的功用性,抑或是过于强调词的诗化,抑或是过度追求词体的雅化,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且只要思想文化观念不改变,这三种偏失就无法得到根本纠正。
二、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对词学尊体的贡献
尊体的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历史发展到清末民初,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蜕变。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打开,西学东渐,此前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方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为古老的中国学术带来了新的空气,也为各种学术的革命提供了新的必要的条件,更为词学尊体的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初的三位学术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通过各自的努力探索,共同推动了尊体的革命。
(一)尊体革命的要素之一—王国维的尊体思想
王国维从文学性的角度提升了词体的地位。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较早地接受了西方先进学术思想的著名学者,他尤其热衷于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康德和叔本华都是极力鼓吹超功利主义美学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一章中为“美”下的定义是:“凡是那没有概念而被认作一个必然愉悦的对象的东西就是美的。”(14)王国维则全盘接受了康德和叔本华超功利主义美学思想,认为“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事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15),甚至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16)他也常用这种超功利主义美学来观照中国文学艺术(即其所谓“美术”),在谈到中国的文学史时,王国维痛心疾首地说:
(中国)美术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之著作,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17)
在这里王国维深刻地指出,中国的纯粹的文学艺术没有独立的价值,因此诗人必须将作品与政治教化相结合,使之成为政教的工具方能“解免”。在谈到当时的文学时,王国维说:
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求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18)
王国维还严正地指出:“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政治道德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19)因此他强调必须视文学“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王国维这些话当然是就所有文学而不只是针对词而言的,然而当时正是常州词派的词学观点笼罩词坛的时候,而常州词派正是将词“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的,这恰好暗合了王国维的批评。
王国维在1907年前后将学术兴趣转到词学方面,但他的词学研究依然以上述超功利主义美学观作为指导。王国维论文学,以“真”作为核心价值(20),在“真”的基础上,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境界说”。在王国维看来,“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21),一种文学,不管是诗、词,还是曲,只要有“境界”,即为上乘之艺术,可见其评价标准完全是非功利性的,完全是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的。正因为是从纯粹的文学与美学的角度出发,他提出“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22)的论断,将宋词与楚辞、汉赋、唐诗相提并论,给予了词应有的评价,无形中大大提升了词体的地位。王国维还从审美效果的角度将词与诗进行了比较,指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径阔,词之言长。”(23)这是将诗和词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加以比较,道出了词与诗各有所长,不分轩轾的道理,尊体意义自不待言。
王国维对词学尊体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尊体思想实际上是对上述传统尊体模式的第一种偏失做了有效的反拨。如上所述,传统尊体模式的第一种偏失是推尊词体时过于强调词的功用性,而忽视其文学性。而王国维正是在西方超功利美学的影响下,一改前人之失,单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推尊词体,有如操持“奥康姆剃刀”,将尊体中的非文学因素全部剔除。王国维从文学性的角度大大地提升了词体的地位,构成了词学尊体革命的第一个要素。
(二)尊体革命的要素之二——梁启超的尊体思想
梁启超从音乐性的角度提升了词体的地位。梁启超一生的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词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尽管如此,他对近代词学的贡献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关于这一点,近年来学界已多有论述。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新派学人,但与王国维只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不同,梁启超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有着强烈的改造国家、改造国民的社会使命感,为此他认真向西方文明学习,十分注意借鉴西方的经验。受西洋文明启发,梁启超发现音乐是陶冶国民品质的一个重要精神教育手段,他说:
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能知也。中国乐学,发达尚蚤。自明以前,虽进步缓慢,而其统犹绵绵不绝。前此凡有韵之文,半皆可以入乐者也。《诗》三百篇,皆为乐章,尚矣。如《楚辞》之《招魂》、《九歌》,汉之《大风》、《柏梁》,皆应弦赴节,不徒乐府之名如其实而已。下至唐代绝句,如“云想衣裳”、“黄河远上”,莫不被诸管弦。宋之词、元之曲,又其显而易见者也。盖至明以前,文学家多通音律,而无论雅乐、剧曲,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虽或衰靡,而俚俗犹不太甚。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有丝毫之影响耶?推原其故,不得不谓诗与乐分之所致也。(24)
在这里梁启超极力强调音乐的巨大意义,认为中国诗歌(梁氏所言指的是广义的诗歌,包括诗、词、曲等所有韵文)之所以没有对国民起到良好影响,根本原因在于诗与乐的分离。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十分推崇能够“入乐”的词,其女公子梁令娴在《艺蘅馆词选》自序(作于1908年)中援引了一段梁启超的话说:
令娴闻诸家大人(即梁启超——引者按)日: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在吾国古代有然,在泰西诸国亦靡不然。以入乐论,则长短句最便,故吾国韵文,由四言而五七言,由五七言而长短句,实进化之轨辙使然也。诗与乐离盖数百年矣,今西风沾被,乐之一科,渐复占教育一重要位置,而国乐独立之一问题,士夫间或莫语意。后有作者,就词曲而改良之,斯其选也。(25)
这段话就将梁启超的词学尊体思想表述得非常清楚了。梁启超评价诗歌文体的标准是“以能入乐为贵”,而长短句由于其文体特征之故,入乐“最便”,所以是最为可贵的文体。这就从“音乐性”的角度赋予了词体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事实上梁启超一向非常重视诗歌文学的音乐性,指出“音节是诗的第一要素,诗之所以能增人美感全赖乎此”(26),并认为词的兴起“无非顺应人类好乐的天性。”(27))。这里梁启超明显受到了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以为词乃是四五七言之诗之进化,要比四五七言之诗更为先进。他甚至将词提升到事关“国乐独立”的高度,希望今后的作者能够“就词曲而改良之”,实为此前论词家从未发明之论,具有极其深刻的尊体意义。
梁启超对词学尊体的贡献是具有独创性的,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对上述传统尊体模式的第二种偏失做了有效的反拨。如上所述,传统尊体模式的第二种偏失是推尊词体时过于强调词的诗化,而忽视其文体特征。而梁启超受西洋文化启发,从“以能入乐为贵”的角度推尊词体,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梁启超从音乐性的角度大大地提升了词体的地位,构成了词学尊体革命的第二个要素。
(三)尊体革命的要素之三——胡适的尊体思想
胡适则从表现风格的角度提升了词体的地位。胡适进行词学研究主要是在其早年,也就是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同梁启超相似,胡适的学术兴趣也十分广泛,词学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他的词学观念对后世的影响同样不能低估。胡适在近代中国文化领域的地位非同一般,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领袖和主将,所谓文学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文学的表现形式的革命,即以白话文学取代旧的文学形式,因此胡适几乎半生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为了给提倡白话提供依据,胡适从已有的古代文学中寻找例证,他找到了唐宋词。早在1916年,胡适便在日记中列举了李后主、苏东坡等人的七首白话词作为“活文学之样本”(28),并认为“吾辈有志文学者,当从此处下手”(29)。一年以之后,胡适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愚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白话文学之种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诗短词。及宋而喻录体大盛,诗词亦多有用白话者……宋词用白话者更不可胜计。(30)
这里他明确指出白话文学已见于唐宋词,至少已经埋伏了白话文学的种子。因为词(至少相当一部分)是白话文学,所以是应该提倡的“活文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正如谢桃坊先生所言:“由于将词体文学认作是……文学史上的白话,从而是中国白话文学的渊源之一;这样从新文学建设的观点来认识,词体文学的新的价值被发现了,真正达到了尊崇词体的目的。”(31)与推崇白话相关,胡适非常崇尚语言自然的文学,他说:
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轩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此绝非五言七言之诗所能及也。故词与诗之别,并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语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语之自然也。(32)
从自然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词优于诗,并认为“词之重要,在于为中国韵文添无数近于自然之诗体。”(33)胡适后来又说:
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34)
而词正是中国古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这就从更为深刻的层面揭示了词体宝贵的价值。在以胡适为领袖和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中,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与一切旧体诗赋都成为被挞伐的对象,唯有词因为被视为白话文学而得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推崇。胡适还在20年代为了标榜白话而编了一部《词选》,此书对词体地位的提升贡献极大,龙榆生先生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之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35)”于此可见一斑。
胡适对词学尊体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他所做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上述传统尊体模式的第三种偏失做了有效的反拨。如上所述,传统尊体模式的第三种偏失是推尊词体时过度追求词的雅正化,而忽视了其原有的通俗自然的品格。而胡适出于推动文学革命的考虑,从“活文学”、“白话”和“自然”等角度推尊词体,确实给词体的地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胡适从表现风格的角度大大地提升了词体的地位,构成了词学尊体革命的第三个要素。
三、结论与思考
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三位学术大师在20世纪的前20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五四运动之前的20年里,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词学,分别从文学性、音乐性、表现风格等角度推尊词体,用更为科学有效的尊体思想取代了延续近千年的传统的尊体模式,使词这种自产生以来即被低视的文体在20世纪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光荣地位。因此我们说,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对尊体的巨大贡献共同构成了词学尊体的革命,其中每人的尊体思想都是尊体革命的一个不可或缺要素,它们相辅相成、互补互救,三位一体,鼎足而立。
当然,是社会历史环境的巨变为尊体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的尊体理论说到底是新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在传统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产生尊体革命的,词的地位在20世纪以前的一千年里始终得不到本质提高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三人都是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新派学人,都是学贯中西、视野广阔的新型学术大师,只有这种新派学人才能完成尊体的革命,与其同时代的旧派词学家虽然词学造诣极深(如况周颐、朱祖谋等),却是没有办法完成这项使命的。
对于词学尊体的革命,笔者还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其一,近年来学界将20世纪的词学研究者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类:使用传统方法观照词学的学者属于“体制内”的一类,而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采用新方法的则属于“体制外”的一类。近年来学界的总体倾向是认同“体制内”学者是词学的“内行”,其词学研究价值更大,相反,认为“体制外”学者相对“外行”。当然,这种倾向也是针对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相反倾向的反拨。然而在词学尊体方面,推动革命性变革的正是那些“体制外”学者,而不是其对立面。受此启发,我们是否应该更为合理地评价“体制外”学者对词学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其二,词乃是中国一种特有的文学体裁,在西洋文学中是找不到与之对应的文体的,但如上所述,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在完成词学尊体革命的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上都汲取了西方的思想资源,西方新思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甚至是词学尊体革命的必然条件,这就足以说明一种道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生态会产生不同的文学,彼此之间或许是“不通”的,但完全可以用相通的思想来观照不同的文学,这就从一侧面印证了文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文学满足的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文学是人学。
其三,尊体的革命完成于20世纪初,词的地位在20世纪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这并没有给20世纪词体的创作带来新的辉煌。受各种难以抗拒的外力之影响,千年词史的发展轨迹在20世纪折断了。隐忍了千年的卑微之后,词的地位的革命实现了,而词的时代却结束了,这是词最大的不幸。对此我们只能感叹,尊体的革命同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革命一样,是一次迟到的革命。
注释:
①黄裳《演山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鲖阳居士,姓名、生卒年不详,南宋初人。编有《复雅歌词》,为大型词总集,兼有词话,原书已佚,今仅辑得词话十则。据现存词话,其论词挖掘“微言大义”,过度诠释词中的政治含义,对清代张惠言等人产生直接影响。参《复雅歌词》之《苏轼》条,《词话丛编》,59—60页。
③曾丰,生卒年不详,南宋前期人。著有《知稼翁词序》,认为词“与道德合”,鼓吹词与“道德”的关系。参《知稼翁词序》,见《知稼翁词》卷首,《宋六十名家词》,《四部备要》本。另参何尊沛《论〈诗大序〉“情志”说对千年词学的辐射》中关于曾丰的论述,见《中国文论的常与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四辑)》,36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强焕,生卒年不详,南宋前期人。著有《题周美成词》,论述词与政事“初非两涂”,鼓吹词与政治的关系。参《题周美成词》,见孙虹《清真集校注》,500—50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⑤陈亮,南宋中期著名浙东事功学派思想家,每于词中抒发经纶济世之怀,“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可陈矣!’”参《书龙川集后》,见叶适《水心集》卷二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张惠言:《词选序》,《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1617页。
⑦见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
⑧缪钺先生在《论词》中将词的特质概括为“文小”、“质轻”、“径狭”、“境隐”,参见缪钺《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二,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7页。
⑩陈维崧:《词选序》,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1页。
(11)徐培均:《待漏传衣意未迟》,见龙榆生《词学十讲》卷首,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2)见李清照《词论》。
(13)朱彝尊:《静惕堂词序》,见《静惕堂词》卷首,陈乃乾《清名家词》,上海书店,1982年版。
(1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15)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见《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以下引用王国维《静庵文集》皆系此本,不另注明。
(16)《教育偶感四则》,见《静庵文集》,第125页。
(17)《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见《静庵文集》,第120页。
(18)《论近年之学术界》,见《静庵文集》,第114页。
(19)《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见《静庵文集》,第121页。
(20)参孙维城《“真”——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核心命题》,见《中国文论的道与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八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88—105页。
(21)见《人间词话》。
(22)见《宋元戏曲考》。
(23)见《人间词话·删稿》。
(24)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见陈引驰编《梁启超学术论著集·文学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82—383页。
(25)梁令娴:《艺蘅馆词选序》,《艺蘅馆词选》卷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页。
(26)转引自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103页。
(27)同上注。
(28)胡适:《谈话文学》,见《胡适留学日记》,岳麓书社,2000年版,642页。
(29)同上注。
(30)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46页。此文发表于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3号。
(31)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2002年版,488页。
(32)胡适:《答钱玄同书》,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724页。此文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
(33)同上注。
(34)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5)龙榆生:《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见《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304页。
标签:梁启超论文; 胡适论文; 王国维论文; 复雅歌词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尊论文; 词选序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