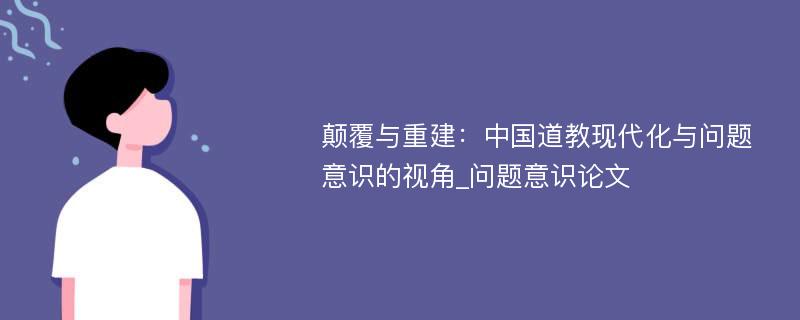
颠覆与重构:现代性与问题意识观照下的中国道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重构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意识观照下的中国道教
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一种僵化性的文化显然无法保持自身的活力。这种情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例如,世界上率先开创近现代新纪元的欧洲,就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等诸多深层次的文化变革,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根本性转型,并在这一社会转型中获得了新的生机。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就是如此。有学者认为,欧洲的新教伦理甚至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而普世化运动下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也跨越国别/民族文化系统的异质屏障走遍东西方世界,甚至成为文化传播的前驱者和承载者。
当近、现代社会形态作为一种外源性强力侵入到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后,致使产生并始终固守于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被迫置身于一种剧烈变迁、动荡不定、形态悬殊、内外交困的复杂语境中,从而陷入了整体的文化困境,已经无法继续按照传统的方式、理念、思路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整合,甚至面临着自我秩序系统崩溃的危机,更遑论发展。这一境遇对于身处文化核心层面的精神文化、思想文化乃至宗教文化而言显得更为严酷。因为,作为文化核心层面的精神文化、思想文化乃至宗教文化是支撑着一种文化系统大厦的支柱,当这一大厦的整体结构及重心已经产生巨大变化时,支柱的设置如果不作相应的调适,怎么能够保证该大厦的安全稳固而不至于倾斜坍塌?那么,置身在如此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中国道教界的行为究竟是怎样的呢?随机上网检索,竟然没有获得一项涉及近现代道教本身革命(改革、变革)的内容,只有极少数关于历史上道教改革活动的描述或讨论;然而,却有八万多条内容与近现代佛教改革运动有关。进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进行检索,结果也是一样(例如分别输入“人间佛教”和“生活道教”的篇名关键词,前者得五十三篇,后者仅得四篇,其中还有一篇重复)。此外,与“佛”、“道”并列而为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文化或者宗教文化三大支柱之“儒学(教)”的“革命”或变革,更因涉世深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而波澜壮阔,“新儒学”、“新儒家”的改革理念与行动不断涌现并且至今方兴未艾。这表明,在近现代乃至当代,危机意识和改革观念,已经成为“佛”、“儒”两界的普遍共识。然而,在中国的道教界以及关注道教发展的学术界,这种意识及观念却非常淡薄,甚至似乎根本就不存在。
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在近现代社会剧烈变迁的语境下,道教界并没有产生问题意识。何谓“问题意识”?撇开其中深刻的学理性内涵不说,就其最直接而又单纯的语义层面而言,就是对自身、对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进而解决问题,而不是总把“问题”当作负面对立的消极因素而加以回避和刻意掩饰,造成客观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从而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甚至还自我陶醉而将问题当作优势来看待并津津乐道。道教界“问题意识”的缺失,可以从内、外两方面各举一事例以证明之:
先看外部事例。自晚清直至民初,朝廷或政府当局及社会先后掀起了数次“(以)庙产兴学运动”,这就是张之洞所说的:“(学堂)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大率每一县之寺观什取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注:张之洞:《劝学篇》。)由此可见,这一运动的冲击对象并非单纯针对佛教而来,而是包括着道教在内。然而,同样受到激烈冲击和损害的道教界并没有像佛教界的广大僧侣那样产生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和忧患感,更没有如同佛教界那样掀起风起云涌的抗议和救教运动——这一救教运动,直接导致了佛教界对自身之行为、教义乃至僧团制度等多领域多层面的深刻反思,从而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理念,致使中国佛教能够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道教界的百年寂寞,说明了什么问题?怎么没有引起教界与学界有关人士的应有关注和思索?
再举内证。在古今中外的诸多宗教中,道教教义及思想体系之庞杂是众所周知的,其中当然不乏精粹,然而糟粕亦有不少,例如所谓道教仙学中的“房中术”。远在道教正式形成之前的先秦时期,房中术就已经产生,将其作为一种古代曾经存在的“性学”或者“性医学”看待和进行研究,并不值得非议或者苛责,哪怕其中有许多不能被当代认同的内容存在。但是,原本单纯朴实的古代房中术被古代道教徒吸收并成为“仙学”(修道成仙)中的一种方法和手段(“男女合气之术”)后,便产生了变异,例如宣称一个男性修道者如果御女(尤其强调御童女)若干便可以成仙。此说之教理性(或科学性)依据何在可以姑置勿论,但是,这一远在北魏时期就被道教改革家寇谦之极力革除的原始道教流弊之一,竟然被一些当代研究者在其中看出了道教的男女平等观和对女性的极端尊敬,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诧。这些研究者在其煌煌论著的下笔时,思绪中是否曾经闪忽过如此问题:既然说男女平等,那么女性是否也可以御男并通过御若干童男而成仙?怎么在道教的典籍中缺乏这样的内容?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够奢谈男女平等和对女性的极端尊重?从所谓“仙学”的角度看,明明是以女性身体为炉鼎来炼丹以达到某些男性的成仙目的;从世俗的角度看,则完全是对女性的践踏、蹂躏和玩弄,其中怎么能解构出比肩于现代的男女平等观念?当然,即使有女性御男的记载,也很难得出“男女平等”的结论。要知道,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笼罩下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决不可能产生如此现代的思想,生于兹、长于兹的道教怎么能一枝独秀?
类似问题还有很多。例如,被一些研究者津津乐道的道家(教)政治思想中的“无为而治”,就是封建专制政治的产物。在封建社会政治模型中,预先设定了“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所企求的只是高高在上的治人者“无为”一点,赐予治于人者较为宽松一点的生存环境。它与“有为而治”的唯一差异,只不过是一个经常鞭打羊群的牧羊人与一个在羊群边吹着短笛“无为而牧”的牧羊人的区别,但决不会改变牧羊人与羊群的主、从关系;而“有为”与“无为”的求得,仅仅寄希望于不受制约的治人者自身的道德觉悟。进步到现代社会,还呼唤道家(教)的“无为而治”,如同呼唤儒家之明君清官的“仁治德政”一样荒诞。这样的社会政治理念与政治模型,怎么能比肩于现代民主政治?怎么能在其中解构出丰富、发展甚至替换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内涵来?
作为一种产生于古代的宗教,存在一些问题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缺乏对自身的反省精神和问题意识。这不能不妨碍中国道教的健康发展。
二、“现代性”观照下的中国道教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并且还在持续着剧烈的社会形态变迁。关于社会变迁,笔者曾经作过界说:“就宗教的生存乃至传播环境而言,社会变迁有时间和空间两重涵义:其一为某一特定地域之社会形态转型所产生的历史变迁,……其二为不同地域之间的空间转换所导致的社会环境变迁……即所谓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所接触的社会变迁。”(注:详细界说参见万里:《社会变迁与台湾人间佛教的发展——从比较宗教学的多元视角着眼》一文,载《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作为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所面临和需要应对的主要是前一种社会变迁,也就是社会环境的历史变迁;道教之所以始终固守于地域性、民族性宗教而未能发展为一种世界性宗教,所缺乏的就是应对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之社会变迁所需要的文化因子。关于后者,将另文讨论,这里只谈道教的因时制宜、与时俱进问题。
相较于其它宗教、尤其是一些世界性宗教,产生于“天不变、道亦不变”之历史循环论氛围中的中国道教,如同中国土生土长的其它宗教或思想文化系统(如儒家)一样,缺乏一种社会时代变迁感;换言之,缺乏一种“现代性”意识。何谓“现代性”?“现代性”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广泛的语词,也是诸多学科的学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语词,至今还无法用简洁的语言来给它下一个规范的定义。但是,正如汪晖先生所说的:“现代性概念产生于欧洲,它首先是指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在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概念经常与古代概念匹配使用。……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的现代性,在十九世纪开始与一个迄今为止仍然流行不止的词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时代’或‘新时代’(new age)的概念。……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中就说过,在黑格尔那里,现代性概念成为一个时代概念,‘新时代’是现代,‘新世界’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发生于1500年前后的历史事件成为区分现代与中世纪的界标。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就把现代性归纳为一种态度,一种把自己与时代、与未来关联起来的态度。”(注: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答柯凯军先生问》,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一种宗教要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求得生存并且不会被淘汰,就必须适应社会历史语境的不断变迁而与时俱进。那么,处于旧与新、古代与现代、传统与时代(现实)乃至未来之“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轴线之上的中国道教要想展现新的生机并将道教中所蕴涵的思想精华奉献于社会与时代,不能只是固守传统而不求改革。
实际上,中国道教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史,虽然在历史上这种改革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例如,在东晋后期至南北朝时代,中国的南北方都出现了由门阀士族道教徒发动的道教改革活动。这种改革是针对原始道教中的一些积弊而来的。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道教改革家寇谦之(365-448)总结以往道教各派教义,吸收佛教的神学与活动方式,创建新的科戒与组织系统,整顿了北方的天师道,破除了其中一些旧的教义教规,从制度层面进行了大力的改革,革除了从五斗米道旧制沿袭下来的许多流弊,如二十四治、租米钱税以及“男女合气之术”等。与寇谦之同时稍后,南朝刘宋的金陵道士陆修静(406-477)则在南方开展道教改革。他的改革主要表现在总括三洞和提倡斋仪。当时,江南一带帛家道、李家道、天师道以及种种巫觋之道杂出,淫祀盛行,陆修静为开创一种适应统治者需要的宗教,吸取儒家的礼法以及佛教的三业清净思想以制订斋仪,使种种修真、祭祀之道得以规制化,将斋仪立为修道之本基,这对葛洪以金丹为主、上清系以存思为主、原五斗米道以符篆为主等是一大改革。寇、陆二人的改革,促进了中国道教发展。此后,南朝陶弘景(456-536)又注重吸收儒、佛两家思想用以改造道教,开创了道教茅山派(宗),成为上清派的代表人物和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唐宋以降,道教界继续有着一些改革,例如金元时期还掀起了一次道教改革的巨大浪潮,并诞生出一个至今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新道派——全真道。然而明清以降,道教界陷入了沉寂之中。当然,同时陷入沉寂中的还有已经完全被中国文化整合了的中国佛教;儒家则以明代王阳明之“心学”结束了自己的传统辉煌。
道教界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为了因应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变化而兴起的;而且都从其他宗教中吸取了可供借鉴的思想乃至仪规制度资源以丰富自身。例如,自唐代以来,开始逐渐兴起了儒、佛、道三教全面合流的社会思潮,三教之间互有吸收融摄,从而分别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至宋元时期,道教中更是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入世倾向。这种倾向无疑受到儒家与佛教的影响。当时道教各个派别的领袖人物都大力宣扬三教一家,并融摄儒、佛二教思想来充实自己的教理教义。例如,张伯端认为儒、佛、道三教“教虽分三,道乃归一”;王重阳也劝人课诵佛教的《般若心经》、道教的《道德清静经》及儒家的《孝经》等。
历史上的儒、佛、道三家,无不是因应了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在改革中求得发展。但是,在宋元以前,中国社会的变迁,还仅仅局限在权柄易手、朝代更换以及民族成分的分离融合等层面,社会形态的深层次变迁还根本没有产生。自晚明时期,中国开始了社会形态层面的剧烈变迁,而恰恰与此同时,三教都一道陷入了停滞不前甚至沉沦倒退的境地,而且这一停滞就是三百多年。一直到晚清至民国初年,佛教界与儒学界先后产生了“现代性”觉醒,如佛教界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人间佛教”运动,儒学界发起了方兴未艾的“新儒家”运动等,这些运动都是她们不断反省自身、反思传统的产物。但是,道教界却沉寂至今,并且由于缺少理论上的创新和活动上趋于保守,便逐渐脱离时代,呈现不断衰落和被边缘化的趋势。
必须承认,无论是道教界或是学术界,还是有一些人在思考着传统道教与中国现代社会契合的问题。但是,无论是从所切入的视角看,还是从所涉及的层面看,关注点尚仅仅涉及到问题的皮相,未能深入到本质要害。所做的工作不是满足于历史性的描述,便是寻章摘句似的将道教文本中的一些思想、概念、方法和行为等抽象出来,与现代社会或西方世界的一些语词、概念及社会行为进行比较,从中寻觅出某种“优势”性或“现代性”的东西来。然而,这些所谓对传统的解读或者诠释,怎么能够使得道教“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独特)意义”?
任何一种宗教,其教义、思想、方法和行为,都是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将其所谓“精华”脱离其特定社会历史语境抽象出来后,是否仍具有超越社会时代的普世性价值,尤其是具有经历了巨大社会变迁后之现时代的普世性价值,这是值得思考的。例如,关于生态伦理,关于人与环境之关系,它不止是某些兄弟宗教(如佛教)的已有话题而并非道教所独有,更是早就经国际上的各界非宗教人士宣传鼓动而成为了世界性的运动,反而在我们这个被自视为“早就怎样”的国度姗姗来迟而成为了新炒作的热点话题。那么,从道教的典籍中所寻觅出的那些片段语词或思想,能够替代现今流行于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现代生态伦理理念而被国人乃至他国人士所接受吗?显然不能,而只能成为一种停留于书斋中和文本上之自我陶醉的“自说自话”。更遑论我们这一“早就怎样”之有着“优良传统”的国度,无论是生态伦理还是自然环境,较之大多数现代化国家,都是满目疮痍、一片狼籍,至今仍在人口的急剧膨胀及急功近利之恶性的商品经济发展之情境下愈演愈烈而束手无策。而这种情境的产生,能够归之于是背离了道教精神而形成的吗?
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还会向历史(原始)回归,如此,道教便彰显出一种先源性的文化优势。笔者不仅要问,世界或者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真的应该回归原始、有可能回归原始并且将会回归原始吗?当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当人类的生存空间已经日益狭小,地球上还有那片净土可以让人们回归?面对这种世界潮流,道教的思想文化资源可否应对?又是否具有使人们认同并接受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三、建构道教与现代社会生活的互动模型是当务之急
一种宗教的存在基础,或者说它在社会中的生存乃至发展的基础,便在于它与社会广大民众的互动。说到底,它必须获得民众的理性认同而不仅仅是感性的信从。只有这样,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型才能够真正建构,这种宗教才能够不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助力。
教内外人士都津津乐道,道教是最贴近甚至融入民众社会生活的一种宗教。乍看似乎有理,细思却并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所认同的往往是某位尊神而非“道教”,虽然道教早就将这些尊神网罗到自己的旗下;换言之,许多普通民众既没有从某神联想到道教,也没有从道教联想到某神。因为道教神谱上的大部分神仙,都是民间俗信宗教的产物,而后被道教所收编。例如,某位因崇拜道教尊神(其实是民间俗神)而被视之为道教信徒的人,却可以对道教的基本教义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对道教的精义(例如关于“道”的涵义)有所认识了。他们大多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拜神祈福而已,并不具有道教信徒的自我身份认同。对民间俗信法事活动中的操持者,许多民众所认同的只是“师公子”——其原型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巫觋——而非道教的“有道之士”。而以符录斋醮为手段活动于民间的天师道或正一道的行为,恰恰是被政府或无神论者指认为带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之迷信活动并不时予以批判。而且,这一道教教派的行为方式及其思想内涵,是否能够真正提升社会民众的生存或者生活品质,也是一个问题,更不要说提升民众思想素质并引导其超越现实而追求生活乃至生命的终极价值了。佛教则不然,信众也可以不了解佛教的深刻教义,但一句“阿弥陀佛”,就具有其所信仰宗教的唯一指向性和自我身份认同,也为信众开启了渡向彼岸的希望之门(如佛教净土宗)。由此可见,道教在传统社会乃至当代中国社会中,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获得了民众的理性认同甚或是感性的信从,都是值得掂量的。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其他宗教的一些改革,或许可为道教提供某些启示。在西方,基督教是一种极端融入世俗社会生活之普世化程度很高的宗教,甚至经历过上千年的政教合一。然而,在十六世纪,一些教界的有识之士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等人因应社会时代的变迁,先后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创建新的教派,将“上帝”从壁垒森严的神龛上找回到人们沧桑而干渴的心灵之中,使人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而不需要神职人员作为中介;在此冲击下,罗马教廷也深深地觉察到天主教不改革便沉沦的危机,发起了普世化运动,这一运动至今还在持续进行之中。基督教的改革,既加强了信众对教义的理性认同,又促进了教会组织与信众之间的有机互动。
再看中国。如前所述,中国佛教在明清时期也同样陷入了鬼神迷信化的泥淖。然而,清末民初掀起的佛教革命,对自身进行了深层次的颠覆和重构,将佛教从鬼神迷信中解放出来,建构了具有普世化意义的积极倡导大乘佛教之自利利他精神的“人间佛教”社会互动模型,这一社会互动模型经历近百年的不断完善,已经结出了丰硕之果,从而使当代佛教初步展现出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主体化、理性化、普世化和事业化等鲜明特征。可以说,人间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佛教僧众的共同理念。人间佛教运动的精神实质,其实就是传统佛教精义与精神的现代化和人间化,是在新的社会时代条件下对佛教原典精神进行新的诠释与实践。这一运动的产生与开展,其实就是在当时自身衰败与社会环境剧烈变迁的内外交困之下,佛教界内部自救与救世思想的觉醒。在佛教经籍原典中,并非没有济世利生的思想资源,但在因缘观念的束缚下(只渡有缘之人),传统佛教的济世行为大多局限在消极被动而非积极主动层面上。原典文本基本精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就有行为,教义转化为一种集体的自觉理念与自觉行为,便是这一运动的最大功绩之所在。传统佛教的慈悲济世,是要求有缘者或者信仰者向佛祖靠拢;而人间佛教则是让僧侣走出山林、走出寺院、走进人间,积极济世渡人,建立“人间净土”。这是传统佛教与现代人间佛教基本理念的最大差异之处。在人间佛教所建构的教界与社会的互动模型中,不止是教界僧众的修证理念与行为获得极大的改观,在社会各界中生活的世俗信众也组织起目标明确、信仰纯正的居士团体。这样,便较好地解决了宗教既有着出世之终极关怀但又不漠视入世之人文关怀的问题。而类似的世俗信众团体,在道教界几乎根本就不存在。
道教界也提出了“生活道教”的理念。然而这一理念虽已提出多年,却回应者寥寥。其原因何在?笔者以为,“生活道教”之所以未能获得教、俗(学术界)两界普遍认同并予以关注,其原因便在于这一理念的提法尚有缺陷。例如,从语义层面看,何谓“生活”?按照《辞海》的标准解释,生活指的是人的各种活动,如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其实也可以将生活界定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普通民众的世俗生活是一种生存状态,各种宗教信众的宗教生活也是一种生存状态。即使是道教理想境界中的神仙,或者是庄子理想中的所谓“至人”、“真人”,也是一种生存状态,或者说是生存方式,即俗语所说的“神仙生活”,只不过是被道教界指认为最高的或最为理想的一种生存方式(生存状态),但它还脱离不了甚至哪怕是狭义的“生存方式”或者“生活方式”的语义范畴。由此可见,即使从单纯的语义层面上也无法区分“生活道教”与传统道教或所谓“出世”(山林)之道教传统的细微差异,更不要说是否存在着根本差异了。至于有人将“生活道教”诠释为融入世俗的社会生活,则不如“人间佛教”之“人间”一辞来得贴切和内涵更为深刻。因为“生活道教”只能使人理解为将道教徒的宗教生活日用化、世俗化,而“人间佛教”则是将宗教生活社会化、人间化(即走出“山林”以融入世俗社会,以及不局限于对来世的终极追求而走进人间并在人间建立“人间净土”,以区别于传统之脱离世俗的“山林佛教”的修证生活和相对于人间尘世之“彼岸的西方极乐世界”)。前者是将个人(道教徒)的修道(仙)生活融入本人的世俗生活之中,缺乏与社会大众也就是“他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内涵,是一种单向度的行为;后者则是将个人(佛教徒)的觉悟修证与对社会大众的拯救普渡紧密联系,建构起一种双向互动的宗教/社会生活模型,以凸显其宗教的社会性、普世性和对他者的终极关怀,从而能够奠定其在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基础,才能不断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助力。两者性质的迥异,因而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参与以及与社会各界的互动和融入社会的程度大不相同。
刘小枫先生写过一本名为《拯救与逍遥》的书,书名中的“拯救”与“逍遥”分别代表中、西方的宗教精神和文化气质。所谓“拯救”,指的是基督教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而“逍遥”则是指庄(子)禅(宗)的“空”“无”而借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语辞。中国的宗教或人文精神中并不缺乏“拯救”的理念,例如儒家所谓“大同世界”及佛家所谓“普渡众生”。但仔细思量,追崇老庄思想的中国道教似乎更在乎的还是独善其身的“逍遥”而缺乏对他者终极关怀的“拯救”意识。一种成熟的宗教,她必须具有对现世的人文关怀和对来世(或彼岸)的终极关怀。而在道教的世界观中,只有仙(天界)、凡(尘世)、鬼(幽冥)三界,并没有为凡人指明一条既可脱离尘世苦海又能免受幽冥之苦的终极之路,除非每个人都修道成仙。然而真正具有“仙胎道骨”的人究竟有多少呢?这正是建构道教与世俗社会双向互动模型的瓶颈障碍。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经历了社会时代剧烈变迁的今天,中国道教如果要不被继续边缘化而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具有反省自身、反省传统的问题意识,树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观念,积极建构起一种与当代社会/人间互动的普世化模型,通过自我颠覆与重构,脱胎换骨地走出传统、走进现代、走向未来,并与当代中国社会环境相适应。这是中国道教现代化发展的当务之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如同百年前中国佛教所经历过的那样进行深入到“教理”、“教制”等深刻层面的改革或革命。中国道教从来就是一种博采众收、来者不拒的宗教,这固然是其缺点,如内涵物过于庞杂而泥沙俱下;然而也是其优点,历史上中国道教每一次较大的发展,无论是教义(理)上的发展还是教制上的发展,都是大力改革或革命的结果。从这重意义上说,道教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时俱进的改革史。而其改革所借鉴的思想与行为资源,部分便来自于兄弟宗教和其他的思想文化体系。借他山之石而攻己之玉,所展示的只能是道教的博大襟怀和高明睿智。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是一个值得道教界人士、广大道众以及教外学者共同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标签:问题意识论文; 现代性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道教论文; 道教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人间佛教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