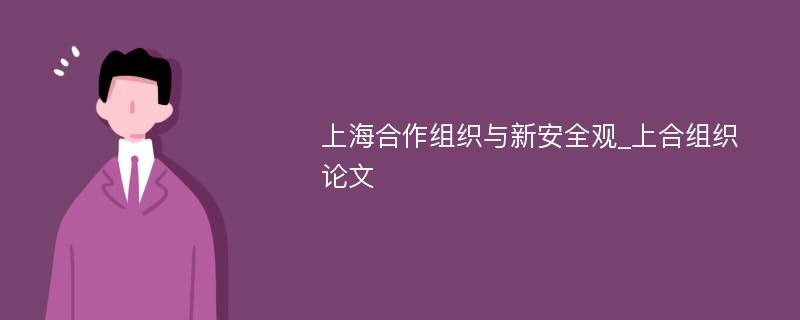
上海合作组织与新安全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世纪世界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围绕各国之间如何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共谋繁荣与发展这一时代重大课题,中国政府进行着气势恢宏的国际战略谋划和卓有成效的外交实践。其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俄罗斯和中亚邻国默契合作,积极推动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不懈探索摆脱冷战思维、超越传统安全观的新型安全观,谱写了我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辉煌一页。
一、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现
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格局转换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形势下,人类面临新的安全态势和安全挑战,最为突出的即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
一般而言,安全是指事物的生存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所谓非传统安全,显然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在国际关系史上,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社会制度以及国民生命财产不受威胁或损害,防范外部敌对势力的攻击。“安全不仅是国家最终生存的欲望,而且是国家生存在重要利益和价值观不受威胁的环境中的欲望。”[1](p.35)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心所在,安全关注的对象主体主要是国家,其强调主要以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来应对威胁。这种传统安全观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现,是国际局势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扼要地说,主要是下述四方面国际背景的产物。一是美苏两极对抗格局的终结,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三是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增强,四是人类科技尤其是信息通讯技术的腾飞。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世人遭遇的安全威胁及其形态发生变化,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各国和平、稳定与发展的严重威胁。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前苏联东欧地区掀起国家分裂和民族冲突的汹涌浪潮,非洲大陆惨绝人寰的部族屠杀此起彼伏;其次是9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东南亚和俄罗斯先后爆发严重的金融风暴,引起地区连锁性的经济危机;再次是世纪之交“9.11事件”等震惊全球的恐怖主义袭击,以及不久前蔓延多国的“非典”、“禽流感”等疫病肆虐。此外近10多年来,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跨国犯罪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生活的危害也逐渐上升。
随此,人们的安全理念发生转变。一方面是安全目标的纵向延伸,即安全主体由国家安全扩展到国民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乃至全球安全,而人的安全则是这些不同层次安全的交汇点;另一方面是安全内涵的拓展,即从军事和政治安全扩大到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科技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相应地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批判性安全研究”应运而生。如果说,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安全观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研究的第一阶段,那么“批判性安全研究”则为第二阶段,后者以建构主义安全观对前者的传统安全观发出挑战,质疑将国家作为安全研究的主要单元,把研究重心从主权国家的安全转移到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而“批判性安全研究”的主要流派——“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军人物、当代西方安全研究的学术泰斗巴瑞·布赞更是将安全研究的领域大为扩展,明确提出:“采用一种更加多样的研究议程,在其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事务扮演着与军事和政治安全相提并论的角色”。[2](p.9)
另外,非传统安全问题至少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奥尔利欧·佩奇等欧洲一批有识之士组成“罗马俱乐部”,立足于全球范围而非民族国家,研究一系列涉及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问题。其先后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震撼人心的历史性文献,尖锐地指出人类面临着人口、资源、污染、粮食等日益严重的困境,由此在开创了全球性问题研究的同时,率先提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3](pp.25-38)随后方兴未艾的世界全球学研究领域从生态环境、人口危机、资源问题扩展到世界经济危机、南北关系、战争与和平、国际恐怖主义、艾滋病、国际人权和民族主义等诸多全球性问题。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首先提出“综合安全”的概念,其含义为:国家安全除军事安全外,还包括资源、政治、经济、金融、科技、信息、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安全,并提出两个附属性的安全概念——“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4](p.24)“当然,冷战后国际社会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识得到进一步发展及认同。1994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表《人类发展年度报告》,提出有关涉及人类安全的七个方面,即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和政治安全。
由此可见,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已经超越国家层次,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全球范畴,其涉及内容已包罗万象,包括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恶化、民族宗教冲突、国内动乱与国家分裂、经济和金融危机、恐怖主义、信息网络攻击、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袭击、洗钱等等。于是,研究专家把这些近年来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5]与传统安全威胁相比较,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鲜明的非国家性、非军事性、跨国性、突发性和关联转换性。第一,虽然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涉及国家间的关系,但已非国家间政治、军事对抗的产物,安全威胁的来源通常是非国家行为体;第二,非传统安全威胁除暴力性活动外,还有许多是非暴力的活动,不仅后者不能以军事手段来解决,而且对前者事实上也难以用单纯的军事手段来应对;第三,非传统安全威胁从产生、发展到解决,往往不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而带有跨越国界、关系多国的性质;第四,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形成许多是经历一个长期积累的潜在性历程,而其爆发在表象上具有难以预知的突发性;第五,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少是彼此影响、作用和触发,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转换。然而我们认为,虽然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非国家性,但国家依然是受到安全威胁的主要对象,也是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角色,国家在解决安全问题上依然拥有自主决定权,而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更需要主权国家之间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双边、多边国际合作。
当然,对于冷战后的整体世界,传统安全威胁并未完全消失,其同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给人类带来复杂而多元的严峻威胁,迫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超越传统安全思维,有的放矢地探索新型安全观。不过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段,各国和各地区遭遇的安全威胁的表现重点又有所不同,应对举措在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各有差异。以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亚及周边地区来说,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是来自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危害。
二、“三股势力”的肆虐与上海合作组织进程中的安全合作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五个中亚独立国家在艰难坎坷的体制变迁中保持着基本的社会稳定,但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安全威胁,其中近年来最突出的即是来自“三股势力”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三股势力”又曰“三个主义”,即指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90年代前期中亚伊斯兰复兴浪潮的掀起和持续连年的塔吉克内战,可以认为是“三股势力”在中亚兴起的前奏。而从1997年开始,伊斯兰极端势力已越出塔吉克斯坦一国范围,向其他中亚国家的世俗政权发起严峻挑战,而且形成了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相结合的趋势。这些邪恶势力联成一体,利用中亚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宗教传统浓厚,以及中亚国家独立初期转轨进程中的政局尚不稳定、经济发展滞缓等因素,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幌子,以暴力恐怖手段煽动宗教狂热、制造民族分裂,而且与地区内外跨国犯罪集团沆瀣一气,猖獗肆虐,以求在混乱中推翻中亚各国的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国家,成为危害中亚及周边国家和平与稳定的毒瘤。
1999年“三股势力”联合发难更是甚嚣尘上。该年2月16日乌首都塔什干发生导致重大伤亡的连环爆炸案,事后据查系“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成员所为,其目标是暗杀乌总统卡里莫夫;同年8-10月,该组织约1000名武装分子又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巴特肯山区进行大规模恐怖骚扰活动,并挟持包括吉内卫部队司令在内的多名人质。2000年8月,这伙匪徒又在乌吉塔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进行多点小股的武装骚乱,与三国政府军和驻塔边境的俄罗斯边防军交火。另外,2000年和2001年还有极端势力和分裂组织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和南部进行绑架、爆炸、暗杀等恐怖暴力行动。
“三股势力”的为非作歹,对中亚有关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造成灾难性后果。1992-1997年塔吉克内战导致6万人丧生,80万人沦为难民,国民经济损失高达100亿美元,外债8.6亿美元。[6](p.93)“乌伊运”在费尔干纳制造的恐怖暴力事件仅对吉尔吉斯斯坦一国就造成5000多难民流离失所,该国为围剿匪徒耗资约500万美元。“三股势力”还猖狂从事毒品贩卖、武器走私、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活动,严重扰乱地区社会秩序。中亚“三股势力”不仅与中亚各国政治反对派沆瀣一气,频繁采用暴力恐怖的扰乱手段对抗、威胁中亚世俗政权;而且与周边地区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及其庇护下的国际恐怖主义集团“基地”组织、俄罗斯车臣匪帮、分裂中国新疆的“东突”势力、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者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对俄罗斯、中国等国的边疆安全和领土完整形成严重危害。
针对“三股势力”跨国作乱的国际化特征,中亚各国与周边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开展了遏制“三股势力”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安全合作。其中令人瞩目的是,中亚国家与中国、俄罗斯在“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具有前瞻性的打击“三股势力”的国际战略合作,而这种合作与新型安全观的积极探索相伴而随。
作为新世纪诞生的第一个新型区域性多边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在卓有成效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的基础之上。而“上海五国”合作机制最初又来源于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对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
八年来“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进程一脉相承。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地区局势,八年来这一合作进程走过了具有自身特征的发展道路,其合作机制的主旋律是以打击和防范“三股势力”为主的地区安全合作。
90年代后期以来,包括俄罗斯车臣和中国“东突”分裂势力和“乌伊运”等在内的三股跨国恶势力在中亚及其周边地区十分猖獗,同时其毒品贩卖、武器走私、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活动也愈演愈烈。另外在阿富汗,1997年塔利班攻取喀布尔后,不仅加剧了阿富汗战乱,而且与其庇护下的“基地”组织一起成为资助、策应中亚及周边国家“三股势力”的大本营。此外,外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冲突、印巴在克什米尔的紧张对峙以及外部觊觎中亚战略地位的各种国家势力的加紧渗透,使中亚国家及其周邻俄罗斯、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稳定面临严重威胁。鉴于这一地区安全的严峻局势,1998年7月五国阿拉木图峰会开始,五国合作进程及时将安全合作的领域由传统的军事安全合作扩展到包括非传统安全的更广领域的综合安全合作。
这次峰会通过的《阿拉木图声明》声言:“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排斥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各方将采取措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贩卖毒品和麻醉品以及其它跨国犯罪活动,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士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活动。”[7]1999年夏“乌伊运”恐怖分子进入吉尔吉斯南部制造武装骚乱和绑架事件后,哈、乌、塔、俄和中立即给予吉有力援助,使之能将这伙匪徒驱逐出境。根据1999年8月五国元首《比什凯克声明》精神,当年12月五国安全执法部门负责人成立“比什凯克小组”,并于2000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首次会议,就有效合作打击“三股势力”的跨国犯罪活动、共同维护五国安全与稳定的具体措施进行商讨。2000年7月五国元首《杜尚别声明》进一步明确宣布:“各方重申决心联合打击对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成主要威胁的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非法贩卖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动。”[8]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又将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作为首要任务,六国元首共同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做出法律上的定义,为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2002年6月六国元首又在圣彼得堡峰会签署《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决定正式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机制。同年10月中吉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举行首次联合反恐军事演习。2003年3月中俄哈吉塔成功举行了代号为“联合-2003”的多边联合反恐演习。2004年6月,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常设机构,总部设在塔什干的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正式启动,其主要任务是防范和打击本地区“三股势力”犯罪活动。
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发展,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外交实践。这一区域性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演进中,中国发挥了突出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中国领导人在积极倡导和实践新的安全观。
三、新安全观的倡导、内涵及意义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复杂多元的深刻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拓创新的精神逐渐推出与时俱进的新安全观。
1997年4月23日,在五国元首签署《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的前一天,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的演讲中,向世界阐明了我国关于维护国际安全的基本主张,并阐述了倡导新安全观的重要意义,指出“五国将要签署的裁减军事力量协定,就充分体现出完全不同于冷战思维的一种新的安全观,对于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与信任、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将会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开辟新的途径”。[9]在次日该协定签署后,他又高度评价协定“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促进五国间睦邻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为增进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开辟了一条有益的途径”。[10]同日中俄签署的《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中俄双方一致主张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双方认为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
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前夕,针对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表现形式的冷战思维又有新发展这一国际局势,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他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途径。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11]2000年7月5日,江泽民在杜尚别峰会上回顾“上海五国”合作历程时明确指出:“我们不仅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五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之路,而且也为国际社会寻求超越冷战思维,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经验。”[12]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之际,江泽民全面总结了“上海五国”五年历程的宝贵经验,指出:“‘上海五国’首倡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始创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提供了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3]几天后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再次强调了“新安全观”的思想,提出:“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14](p.183)这里他把“合作”改为“协作”。虽是一字之改,却是对“新安全观”更为精确的表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安全观及其相关的“上海精神”得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一致认同。在2002年6月7日圣彼得堡峰会上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确认“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该组织的指导精神,同时发布的《元首宣言》强调:“国际社会须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相互协商为基础的新型安全观。这有利于彻底消除安全破坏因素和新威胁的根源。”在同年7月31日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15]
至此,中国政府已经完整推出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互信、互利、平等、协商”是其内涵的高度概括。互信,就是以诚为本、以信为先,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就是将全球安全构筑在共同利益基础上,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就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就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求同存异,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有效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实现普遍和持久的安全。可见这八个字也是相辅相成,“互信”是基础,“互利”是目的,“平等”是保证,“协商”是方式。
中国政府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的涵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其内容由军事和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因此,寻求安全的手段趋向多元化,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新安全观不仅重视综合安全,而且提倡合作安全,认为合作模式应灵活多样,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各国应该在经济领域加强互利合作,消除经贸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逐步缩小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谋求共同繁荣,塑造全球和地区安全的经济基础。
因此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它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符合人类社会进步要求,必将为中国政府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国新一届领导人胡锦涛指出:“我们应该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和平。只有增进互信,平等协商,广泛合作,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安全。”[16]
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实践新安全观,具有多方面的重大现实意义。这是当代中国领导人总结世界历史上战争与和平的经验教训,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突破传统安全观,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新途径的一种壮举。事实证明,这些年来,以这种新安全观为指导,中国政府已在各种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中取得丰硕成果,不仅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而且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赞赏和认同,为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有力的贡献,八年来成效卓著的上海合作组织进程即是力证。21世纪的世界,天下仍不太平,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在发展的客观形势下,时代需要我们以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充实和完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