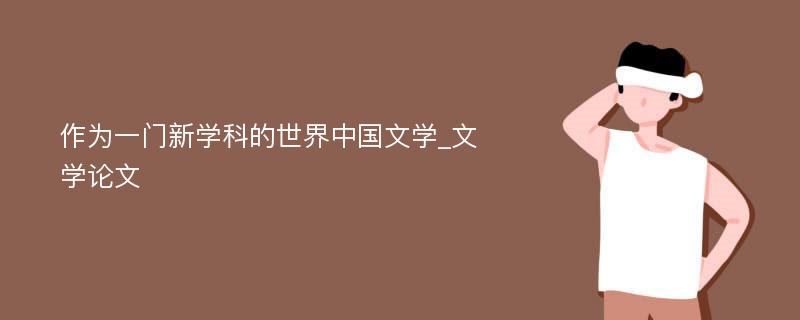
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门论文,新学科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在我国已有十多年历史。在这十多年中,参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各种团体、机构和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艰苦的努力,逐渐将世界华文文学由一种课题性的研究发展为一门独立的文学新学科。随着当代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相互渗透,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正在不断拓宽,从早期比较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向着文学史、文化史、民族史、国际关系史等方向纵深发展,使这一学科结束了“兴趣研究”和“秩序分散”的状态,初步建立起比较规范的研究体系。重视这一学科的建设,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以及中国海外文化战略的制定,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学科产生的背景
进入80年代以来,受传播主义、功能主义、文化模式论、结构主义、多元化主义等世界文化观念影响,我国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令人注目的新倾向:
其一是对语种文学的重视,观察范围不限于某一语种的母语国家或民族的文学,而是关心使用同一语种的所有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包括其后兴起的华文文学。
其二是有意“搁置”文学的通史研究,转而关心文学断代史或地域文学史,通过文学史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地域的文学、综合考察世界文学的整体面貌和时代风尚,如对当代拉丁美洲各国文学的热心推介与评价。
其三是恢复三、四十年代后曾一度中断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视各国各民族文学的“关系”和“影响”,在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里,通过横向比较,重视观察评价中国文学。
其四是文学的边缘性和跨学科研究,即超越学科的界限,以文学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它学科的相互关系,从而发展出某些新的学科,如文学心理学,文学人类学等。
其五是不以某种文学为尊,更不以某种文学的标准来判定另一种文学的价值,强调各种文学的平等,重视每一种文学的个性功能及对世界文学的积极贡献。
总的来说,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的后半期,虽然在地球局部地区仍有激烈的民族与文化纠纷(如巴以、印巴、波黑),但从整体上来说,人类社会是朝着和平与民主、进步与发展、对话与合作的方向,顺应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创作上越来越尊重个性和独创,在研究上越来越提倡宽容和交融。80年代以后我国在世界文学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研究倾向,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两次世界大战灾难记忆犹新的人类,渴望更深刻地认识宇宙、认识社会、认识人类、认识自己。人们说地球越来越小,只是因为我们对地球的认识越来越深,越来越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开展与发展,正是产生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中,而改革开放的中国。为这一新学科的成长提供了湿润的气候和土壤。
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实际上是古已有之。上世纪之前,受中国文化强烈影响,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属于“中国文化圈”或“汉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不仅有大量经、史、子、集等汉语文献流传,而且有大量的汉语诗文、剧本、笔记、历史演义和小说创作出现,形成古代海外汉语文学。19世纪以降,随着早期华侨和华工的流出,中国文学进一步传到海外。中经中国社会的历次变动和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国共两党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国际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其中还包括自1872年清朝派遣留美幼童以来的多次留学热潮,如清末民初的留日热、五四时期的留法热,20年代的留苏热、40年代的留美热等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强大的中国海外文学,并进一步发展为国际性的语种文学——世界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东南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受中国“五四”新文学影响,华文文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中心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新马两地,先有周容、苗秀,后有赵戎、方修、方北方等人,总结了华文文学在新马两地发展的历史经验,积极倡导了“马华文学”。从1948年周容掀起的“马华文学独特性”的讨论到1962年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的完成,标志着“华文文学”在东南亚已发展成熟为一种国际性的语种文学。此后,华文文学在亚洲、美洲、欧洲、澳洲不断蔓延滋长,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亚华文学、美华文学、欧华文学、澳华文学。到60——70年代,华文文学已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主要西方国家的许多著名大学(如耶鲁、哈佛、牛津、墨尔本、鲁尔、神户、九洲等大学)与研究机构(如巴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都相继开展了华文文学研究。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积极参与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与建设,遂使这一学科成为世界文学研究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学科发展过程
我国华文文学研究始于1979年。这一年5月,曾敏之在《花城》杂志创刊号上撰文《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向国内学界介绍了香港、澳门的文学,特别是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其时,“华文文学”概念对国内学界来说仍十分陌生,文章谨慎地使用了“汉语文学”这一概念,反映出我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发端之初的探索心理和状况。
早期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1979—1982)是从“台港文学”起步的。从1980年3月的中国当代文学首届年会(广州)到1982年6月首届全国港台文学学术研讨会(暨南大学),讨论的话题集中于台湾文学,尤其是小说领域。香港文学研究只限于个别专题,“华文文学”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国内被大力推介的美华作家如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等人的小说,被视为台湾文学中的留学生文学,而“台湾文学”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
这一阶段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适应了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中国结束了十年“文革”动乱,长期封闭的国门被迅速打开,一向“站在中国、放眼世界”的人们转而“面向世界,面对中国”,当外来的文学观念泥沙俱下潮涌而入,我们既来不及“拿来”也来不及“反刍”而只能“照搬”的时候,通过“台港文学”来认识世界进入世界,可以说是一种积极而符合实际的选择。
1983—1986年,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收获,是建立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体系,区别了“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不同性质,并提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
1983年,改革开放的大潮使我国学术界一片生机,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在秦牧、曾敏之、杨越、肖乾、毕朔望、冯牧等人的倡导和带动下,“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被广泛使用起来。1983年,广东省社科院文学所报告中,提议要设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建设“海外华文文学”新学科。1984年,汕头大学本着同一目的,着手筹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并着手创办《华文文学》杂志,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研究阵地。
1985年4月,秦牧在《华文文学》试刊号的《代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华文文学、是一个比中国文学内涵要丰富得多的概念”,并将华文文学与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作为一种语种文学相提并论,同期《编者的话》,对“华文文学”进行了明确的界定:(1)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2)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及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和香港文学。而华文文学除了中国文学之外,还包括海外华文文学。(3)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人用华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创作的作品,不能称为华文文学,但非华裔的外国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可称为华文文学。
到了1986年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四海》杂志第1期上,秦牧以《打开世界华文文学之窗》一文,正式提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文中指出,以中国为中坚,华文文学流行范围及于世界,我们应该打开窗口,关心世界华文文学的动向,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华文文学交流。同年12月在深圳召开的第3届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大会筹委会所作的论文综述中,继续重申了“世界华文文学”概念,强调要“吸收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经验,加强对各国的华文文学研究。”
中国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起步虽然较迟,但发展的速度却是很快的。第3届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后,“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的建设已成为历次会议的中心议题。1989年4月第4届全国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大会在工作汇报《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积极评价了10年的华文文学研究,指出世界华文文学的观念已初步明确,并且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方法,即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从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考察华文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考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从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考察大陆、台湾和香港文学。
到了1991年7月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和在中山市召开的第5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世界华文文学”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香港会议的主旨,是以香港为桥梁,沟通海峡两岸,沟通东南亚和欧美,凝聚海内外的力量,促进世界华文文学交流,推进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并产生了“世界华文文学协进会”的筹备组织。中山会议的主旨,则是探讨中国文学在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各国华文文学中的演变和传承,寻找华文文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规律,探讨华文文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趋势,总结华文文学发展的世界经验,促进华文文学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会后并决定将原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属下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改名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香港会议和中山会议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转折点,一方面,两会总结了10年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成果和经验;另一方面,两会结束了“港台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局面,开创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新格局。从这时候起,“世界华文文学”的观念已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接受,“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体系已呈成熟,“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已基本成型。随着世纪的交替,中经1993年庐山的“第6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和1994年昆明的“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以更坚实、更宽阔的步伐,向着新世纪迈进。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1979年—1985年的产生期,1986—1991年的成长期到1991年以来的扩展期,其兴起与成熟,发展与壮大,是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的。改革开放扩大了中国文学的眼界,加强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勾通往来,使一向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文学进入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主流,从而使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开展成为可能。10多年来,古今中外几乎所有曾对世界发生重要影响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尤其是西方现当代社会、哲学、文化思想理论,都在改革开放的气氛下集聚于中国学术论坛,这种多元开放的局面,从各方面为中国文学的创新,也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价值参考体系。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不同于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东渐时对西方文化冲击所采取的防御资态、也努力避免“五四”时代鉴于西方列强侵略和民族矛盾激化而对西方文化所采取的断然排斥或全盘肯定的偏激情绪,以一种主动的、积极的、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世界先进文化和文学遗产,对内重审传统,将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对外放开襟怀,将世界先进文化民族化,本土化、从而形成新的传统,使中国走向世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已成为中国文学世界化的一条重要途径,这是这一学科能得以迅速发展的内在原因。
学科的条件及性质
按照国际学术惯例,作为一门独立的文学学科,世界华文文学已完全具备学科成立的必要条件:
(1)在世界各地存在着大量的华文文学作品,可以广泛地对其进行艺术总结;
(2)10多年来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已为这一学科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文献和研究成果;
(3)在世界各地有一批为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阵地的专业杂志和各种报纸副刊,其中国内的《华文文学》(汕头大学)、《四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台港文学选刊》(福建省文联)、《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江苏省社科院)等,在组织世界华文文学研讨、开展世界华文文学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4)在世界各地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瑞士、德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国以及香港、台湾、澳门都有一定规模的华文文学组织,国内的各地如广东、福建、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都先后设立了世界华文文学专业研究机构,并发展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5)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学术活动,仅在国内,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会已进行8次,历时14年,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6)华文文学已在世界60多所大学、国内20多所大学进入大学课程,其中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著名学府。
作为一门独立的文学学科,世界华文文学与其他文学学科有着明确的区别和界定。
首先我们看到,华文文学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不同、英、法、德、西等语种文学是伴随着这些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以殖民文化甚至暴力征服的方式强行向世界各地推行而发展起来的。而华文文学与世界性的东方文学——比如阿拉伯文学——一样,是以一种内在生命力,和平地向世界各地蔓延的。当然,这中间又有区别,象阿拉伯文化,主要是依靠宗教和民族(或种族)的力量来完成传播的过程,华文文学却是以一种民主文化的力量,首先自发地产生在华人移民内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在历程的演变(时间)和关系的更替(空间)中,以一种平康正直、从容以和的精神,道并行而不悖的态度,与当地各民族文化和文学平等交融,“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从而超越国家和种族的界线,使自己能百物皆化,达于四海。
其次,英、法、德、西等语种文学、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或成为一种国家文学、(如英语文学中的美国文学、西班牙语中的拉美国家文学等等),或成为一种被国家认可的民族文学(如法语文学中的魁北克文学),它们独立于母语国家的文学之外,是与母语国家文学有着完全不同性质的“本土文学”。而华文文学,除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为国家文学的组成部分外,其他各国各地的华文文学或多或少与中国文学保持着难以分割的联系,是以中国文学为母体的一种语种文学,与中国文学存在不可改变的血缘。
同时,英、法、德、西等语种文学,由于完全“本土化”,其生存与发展,是创造该语种文学的各国家各民族内部“自己的”事,而华文文学由于以中国文学为母体,其生存与发展,受着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也受到各国家地区华人与当地关系的制约。中国与当地关系正常,华人与当地关系正常,当地华文文学就能正常发展,反之,则受到阻碍或破坏。因此,华文文学在各国家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并且常常出现起起伏伏的局面,这一点,尤其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
此外,受儒教文化影响较深的华文文学,在与儒教文化比较接近或比较相通的地区,例如佛教文化地区,基督教文化地区,其发展比之在其他宗教文化地区,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顺利一些。文学与宗教文化这种辅承关系以及如何沟通这些关系,是我们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不能不重视的一个课题。
上述诸种因素,决定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性质:
(1)世界性——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的人地方就有华文文学生长的环境。除了南极洲以外,世界各大洲都无法忽视华文文学存在的现实。华文文学已成为本世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而引人瞩目,相信在下一世纪或更远的将来,它会有更深更大的发展,成为世界文学中一支强劲的力量。
(2)本土性——华文文学随华人的足迹而流动,也随华人与当地社会、民族、语言、文化等诸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离开土厚水深的母亲国度,移居到异国他乡,华人走进了新的时空之中,要生存,要发展,必须适应脚下的土地,必须适应那片土地上的风风水水,落乡随俗也罢,落叶归根也罢,落地生根也罢,他必须与异国他乡的文化取得认同。“本土性”、“本土化”乃是华人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选择,也是华文文学生存发展的一种选择。
(3)延续性——自发生长,自生自灭,生生灭灭,永不止息,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生命形态,也是华文文学生命顽强和创造力量旺盛的表现。生存的渴望培植着生命的张力,养育着华文文学的创造性和创造力。不管气候多么恶劣,土壤多么贫瘠,只要生命的情感需要表达,华文文学就会破土而生。然而华人走到哪里都是华人,时空变了,身份变了,肤色和血缘不会改变,华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被顽强地延续着,“文化的中国”心态和“中国文学传统”在世界各国华文文学中随处可见。对传统的继承,正是华文文学个性发展最深厚的基础。
(4)交融性——人类相邻而居,人在众生中生存,不可能只跟上帝和自己说话,也不可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文化的交流,情感的融汇,不仅仅是一种沟通的手段,说到底要服从生存和发展的目的。作为华人心灵的产物和现实生活的反映,华文文学也必须具有这种交融的品格,它既需要别人以多元的眼光看自己,也需要自己以多元的眼光看别人,才能在互相交融的过程中创造生存与发展的良好条件,才能与别种文化别种文学共同进步。
世界华文文学的特性,也决定了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的性质:
(1)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是一种考察语种文学的学科——“世界华文文学”不是“世界华人文学”。“华人文学”是从“种族”、“族裔”方向规范的一种文学,“华文文学”则是从“语言”、“语种”、“文字”方向规范的一种文学,两种概念的内涵显然有着本体性质的差别。“世界华文文学”也不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是“中国”地域范围内的一种语言文学(主要的是以汉民族语言为代表的汉语文学,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在此不论),“世界华文文学”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语言文学(亦可称“汉语文学”、“华语文学”,约定俗成称之为“华文文学”),两种概念在范围上有着大小的区别。世界华文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也包括非中国的却使用同一汉语语言的文学,因而是一种语种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就是对世界各地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的文学事实进行观察和分类,在发现其一般规律、掌握其一般规律的领域中将这一语种文学的历史情状和规律系统化、条理化的一个学科。
(2)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是一种探讨民族文学的学科——首先,“世界华文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学科是研究与中国和中华民族(包括中国的各少数民族)不同的其他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学的学科,“世界华文文学”则是研究有着共同语言、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传统我们通常称之为“华人”或“华族”即广义的“中华民族”文学的学科。数千年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起源(例如黄帝、黄河、龙,以及中国伟大的过去)成为这一民族文学集体认同的重要基础。其次,“世界华文文学”也不以中国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为本位,把世界各地华文文学只视为中国的文学的支流,而是从世界范围内整体地描述、分析、考察、研究各国、各地区华文文学一般的、普遍的共同规律。在这一过程中,同时考虑各地华文文学所包含的一种或多种文化背景,也考虑在不同的环境或情境的压力下,这一语种文学所产生的可变性和选择性。
(3)世界华文文学是一种研究文学关系的学科——一种文学必须会与其他文学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世界华文文学便是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各国各地区华文文学相互关系的学科。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研究,但主要研究的不是中国文学本身。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主要由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学科来承担。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主要是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和演变,研究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研究中国文学对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世界华文文学虽然要倚重文学的关系和比较,却又不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所以法国比较文学理论和方针的主要制定者马·法·基亚说:“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基亚《比较文学》前言)“世界华文文学”则是研究同一民族语言、同一文化传统的文学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比较,只是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明确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基本性质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这样两点:
(1)由于信息的发达,传播的先进,由于多元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也由于世界华文文学所依据的复杂的文化背景和环境,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在方法上,既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比较的,既可以是地域的、社会的,也可以是文化的、民族的、语言的,多种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某些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综合运用其中。从这一点来说,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可以是一种综合性、跨学科、多方法的学科。
(2)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不仅是“考据之学”、“义理之学”、“词章之学”,也是一种“经世之学”。就是说,它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现实“功用性”。比如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繁荣枯败,明显地受着印尼国内政治、民族关系、宗教文化及其政府所推行的种族文化策略的深刻影响。有些地方,比如菲律宾,华文文学的发展不仅受着菲律宾本地各种关系的影响,还受到中国海峡两岸关系的巨大影响。台湾国民党势力在菲律宾华人社会各界一直相当深厚,直到我国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才有较大松动和改变。又如台湾地区文学界“统独”倾向问题,十分复杂。除了台湾笔会等少数有着明显“台独”倾向的团体和机构外,大多数团体机构(包括许多所谓的官方机构)并不参与“台独”。即使象笠诗社这样由清一色台湾省籍诗人组成并且“台独”倾向十分强烈的团体,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沆瀣一气,如许达然、非马、杜国清等美华笠社诗人的反应就相对冷淡,不可一概而论。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可以为我们制定外交政策和海外文化发展策略提供参考和依据,也可以对世界各地的政情、民情、社情提供咨询。
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
综上所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经过十多年努力,已经奠定了学科的基础,但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还不够成熟,也不够完整,重视这一门学科的建设,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应该加大步伐。为此,我们建议:
(1)我国学术领导部门在规划学术研究计划的时候,应该考虑将这门学科独立出来。过去那种把华文文学研究附设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方法,可以作为权宜之计,如今已不能适应这一学科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这一学科的特殊性质。独立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不仅扩大了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建设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2)各级学术管理机构应对这一学科给予积极的支持,扶植资助各种华文文学学术活动,改进各级华文文学研究组织,同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加强与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界的联系,为发展和壮大这一学科提供便利的条件。
(3)应该尽快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学术组织,加强对这一学科的引导。这样一个学术组织,不仅有利于凝聚海内外的力量,深化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也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在海外各地的影响。
(4)参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各级学者,应该努力更新知识结构,提高学术水平,努力开创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为本学科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基础已经奠定,研究局面已经打开,研究成果正不断丰富。我们相信,在一种建设性的氛围之中,只要我们认认真真抓紧时间做我们应该做的实实际际的事情,这一学科的发展必将拥有无限光华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