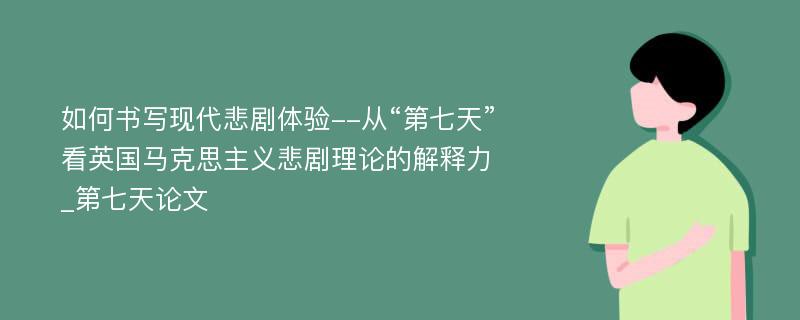
现代悲剧经验如何书写——从《第七天》看英国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阐释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论文,英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第七天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现代悲剧观念与中国语境 在漫长的西方文艺史上,悲剧一直是高贵而成熟的艺术形态,也正因其尊贵,关于悲剧死亡的论调一直以来被学界热烈讨论。就文体形态而言,相比之下,现代人的情感模式为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而非悲剧和诗歌。悲剧死亡的另一重要缘由则在于,作为一种经验,传统悲剧的崇高色彩已经不再具有适合的土壤,现代社会乱象丛生,促使人们在价值观念上出现多元取向。这样一来,每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悲惨事件是更为鲜活的悲剧,牺牲、痛苦也不再必须升华为一种悲壮的审美体验。从后一种悲剧消亡的表征来看,所谓的“悲剧死亡”,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悲剧经验不再处于主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关注个体和日常的悲剧体验。可见,悲剧不是死亡了,而是变异了。如夏志清所言:“人在兽欲和习俗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的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① 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另辟蹊径,提出了更有生命力的现代悲剧观念。与传统悲剧理论不同,威廉斯和伊格尔顿把悲剧界定为具体的经验或事件。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悲剧体验如何在文学中加以书写?他们举出诸如易卜生、田纳西·威廉斯、劳伦斯、贝克特等作家,一方面说明现代文学写作已经从崇高的审美经验中走出来,部分地显现了现代悲剧经验的美学特质;另一方面,他们从文体上解决了悲剧形式被小说吞噬的状况,因为把悲剧界定为经验或事件,则小说同样具有承载这一经验的合法性,甚至比戏剧样式更有展现的张力。 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解决悲剧观念从传统到现代转换难题的手段,主要是重新界定悲剧这一范畴。威廉斯认为,“悲剧是一系列经验、习俗和(机构)制度”②。伊格尔顿在悲剧问题上则试图实现名实之间的沟通,这是在意识到悲剧理论建构危机之后的有意识突围。例如,他在肯定威廉斯的界定之后,马上提出了这一疑问:“我们为什么要用悲剧这一个词同时来指称《美狄亚》和《麦克白》,一个少年的被杀和一场矿难”③。描述性的界定或许更能表达悲剧这一范畴的内在张力,实际上,伊格尔顿认为“十分悲伤”的情感体验最能精确地概括悲剧,这比威廉斯所钟情的共同情感结构更具体。总之,威廉斯和伊格尔顿正是在强大的悲剧传统中找到了更为贴近现代社会的悲剧言说方式,不仅在文体上解决了长篇小说对悲剧形式的强势占领,更从审美情感上使濒临理论危机的悲剧传统安全着陆。因此,这样的范式转换把悲剧研究引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对悲剧传统的反思中,威廉斯意识到悲剧理论无法与现代悲剧进行有效对话,甚至“现代悲剧理论对现代悲剧的存在持有否定态度”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悲剧理论先于悲剧创作,特别是用被学术系统化之后的理论规范考量现代悲剧,自然会出现格格不入的状况,这种“以古论今”的做法把批评理论与创作实践分离开来。虽然威廉斯在《现代悲剧》的第二部分把重点放在悲剧文本的批评实践上,但是,他所倡导的现代悲剧经验如何书写,这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那里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进一步,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念不再追求形而上的价值尺度,而是把普通人物的日常灾难和痛苦纳入其研究重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悲剧书写完全成为私人化痛苦的倾泻,相反,在普通公众的偶然遭遇背后仍然有普遍性的不合理结构。正如威廉斯所言:“正是由于它的极端重要性,悲剧经验通常引发一个时代的根本信仰和矛盾。悲剧理论的有趣性则主要在于它深刻地体现了一个特定的文化形态和结构。”⑤这些观点启示我们,需要在悲剧研究中转变视角,“不再寻找悲剧的新的普遍意义,而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发现悲剧结构”⑥。进而,我们可以设问,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悲剧应该如何书写?又如何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并解决根本性的价值冲突? 悲剧与中国的关系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真正的悲剧——在情节上追求大团圆的结局,悲剧主人公的人格体现“礼”多于“义”,虽多有牺牲的结局,却缺乏悲壮的色彩。这不仅影响了悲剧冲突的持续性,也是悲剧表达缺乏主体性精神的重要表征。当然,这些都是以西方悲剧理论传统为标杆所作的判断,而中国悲剧也不乏自身的独特性,如在苦情苦趣的情感基调中创造了浓郁的悲剧意境,使读者在忘我的审美观照中唏嘘感叹。⑦而如果以西方现代悲剧观念为参照,中国当代社会不仅存在滋生悲剧的土壤,更有大量悲剧文本的创作实践。 一般认为,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悲剧是唱主角的,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寻根文学,以至先锋文学,多以描写苦难、渲染悲剧色彩为主要特征。其中,余华的小说具有典型性。有人认为余华的《活着》标志着“后悲剧时代的来临”⑧,这一判断显然需要进一步说明:如果就中国文学发展的角度而言,余华的悲剧书写确实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人性深度和现实批判层面都具有突出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余华的《活着》引领了悲剧创作的转变。《活着》所展现的仍然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观念与偶然性命运之间的纠葛,除却主人公福贵的渺小外,其主体特征还是传统悲剧观念的重要体现。不过,纵观余华悲剧书写的变化,我们确实能发现其在悲剧观念上的嬗变。特别是在其新作《第七天》中,余华通过故事人物的经历把社会热点事件贯穿起来,没有刻意回避故事情节的公共性。尽管这部小说被诟病为“段子集锦”,但这样的公共事件的大集合也体现了作者对悲剧性表达的独特理解。结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悲剧理论,我们不难看出,《第七天》以当代“中国式悲剧”的写作模式恰好应和了现代悲剧经验,主人公具有小人物的社会身份,在沉重的现实面前,个体无奈地为此付出代价,甚至死亡。这一对日常生活的怪诞书写使得现代悲剧在喜剧表达中更具张力。在方法论层次上,一直以来,以理论阐释文本是文学批评的通行惯例,而文本呼应理论或印证理论的做法似乎并不多见。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妨把《第七天》作为分析重点,而目标是探究现代悲剧理论的阐释力、书写的可行性以及与当代中国的深度对话。 二 主人公群体:无罪的“草芥” 小说《第七天》以男主人公杨飞为叙述视角,讲述了他遭遇饭馆爆炸死亡之后奔赴殡仪馆火化的经过,在对自己生平遭遇的回忆中展现了多重悲剧景象。从主人公的身份来看,《第七天》这部小说已不再沿袭传统悲剧的套路,把人物的历史性身份看作重要因素。杨飞由一个单身铁路工人抚养成人,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公司员工。在他身上,看不到高贵与富裕,像大多数普通年轻人一样,他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每天的辛勤工作只为求得安稳的生活。但恰恰是因为平凡,才使他具有了社会性的身份。不仅杨飞如此,故事中的多数人物都是在社会现实中挣扎的小人物,如遭遇“强拆”被砸死在家中的夫妇,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情侣鼠妹和伍超等。这些小人物都是社会存在的主要群体,在物质生活上贫穷拮据,在社会生活中也难以奢谈尊严。如果这些构成某种必然性,那么这种必然性本身就是悲剧性的。 这里势必涉及悲剧人物与悲剧情节之间的关系。按照伊格尔顿的分析,人们对贵族的偏爱在于其命运是与社会甚至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在象征意义上能代表总体性的状况,因此更能产生历史性的影响。另外,高贵的身份跌落到厄运的底端,更能产生悲剧感。但是,就当代语境而言,问题可能正在于此,因为“在古希腊悲剧中,悲剧主人公的地位与继承、血缘及责任密切关联,这样的地位特征使得人物个性发展仅仅是为了满足普遍行动的需要”⑨,而人物的个性与社会角色的矛盾是形成悲剧冲突的张力。 当然,传统悲剧的英雄人物观之所以能够长期作为强势话语存在,根源在于其以艺术化的方式传播关于人生存在的正能量,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悲剧英雄通过其勇气和耐受力将苦难的神秘性转变成可理解性,改善它并且达成和解,我们对人类状况的信心因此而得到强化和重申”⑩。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悲剧人物地位的不同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情感的差别,更是政治身份的表征。在这一点上,威廉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论观点,而侧重实践层面人与人之间的区隔。在他看来,阶级仅仅是一个无定形的社会中的区分,而地位意味着秩序和关系。(11)这样一来,当下的悲剧形态就不再是威廉斯所概括的自由主义悲剧特征,不再把悲剧人物的自我否定与自我反抗作为主要呈现方式,而是回到自我与外部的关系。进而,我们不再把现代悲剧的产生归结为人,而是归结为社会环境。实际上,威廉斯在谈到米勒的《人民公敌》这部作品时,已经对此作了深刻解析,他认为:“社会不仅仅是供解放者挑战的不合理制度,它还主动毁灭和陷害人们,只是因为他们还活着。社会仍然是被看作是错误的和可以改造的,但现在仅仅生活在其中就可以使其成为受害者”(12)。从威廉斯的论述我们不难推断,《第七天》中杨飞等人的悲剧在于,即使遵从现实的法则,仍然无法逃脱厄运。 结合《第七天》这部小说,我们还可以承续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传统悲剧观念进行批判。英雄悲剧在历史上表现的是人们所固有的偶像崇拜的冲动,是尼采意义上的仪式体验;现代悲剧则从人物命运的表现(或者说展示)中介入社会现实,至少从《第七天》中我们不难发现其端持的激进立场。摘掉了悲剧人物高贵的光环,现代悲剧显现了大众化的趋向,这是艺术向日常生活的扩张,也是“悲剧作为经验”这一命题的重要支撑,当伊格尔顿宣称对悲剧主人公的唯一要求是“你是这种人当中的一员”时,他也是在昭示悲剧不是衰亡了,而是增多了。 三 无序与悲剧困境 主人公固然是悲剧性的承载,但悲剧的重心更多地指向事件而非人物。亚里士多德把悲剧艺术定义为对行动的描写,通过事件和人物的行动表现矛盾冲突,这是其悲剧情节论的重要理论关联。这说明,冲突是悲剧艺术的永恒主题,只是现代悲剧的冲突更多的是人与外部世界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现代悲剧事件界定为偶然性时,作为现实存在的必然性根源是更为深刻的矛盾缘由。 当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悲剧观念史上有一个历时性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期,个人的意志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或在对立的立场上通过革命推动社会的进步。而正如威廉斯所认为的那样,从契诃夫和皮兰德娄开始,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就不再像自由主义悲剧那样是积极的:“个人所应对的不是反抗某种社会状况,而是社会事实本身。如此一来,人们除了退却还能做什么呢?”(13) 这一变化的深层根源是什么?通过对悲剧观念的考察,威廉斯和伊格尔顿都发现了问题所在,这就是相对于人而异化存在的社会秩序。秩序与无序是相对的。现有的秩序往往被认为是合理的,受到伤害的或者反抗这一秩序的人似乎都是制造暴力和无序的动因。可是,威廉斯提醒我们:必须摒弃将革命理解为社会危机的看法。小说《第七天》中的人物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活着或者死亡,他们辛勤劳动,为人友善,即使如此,他们仍然无法摆脱与现实生活的对立。主人公杨飞的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在自己得了癌症之后拖垮了生活小康的儿子,最后放弃治疗,离家出走客死他乡。小敏的父母遭遇“强拆”之难,被自己的家园埋葬,从此与年幼的女儿阴阳相隔。给读者更为强烈震撼的,莫过于杨飞的“妈妈”李月珍的经历。老人一生善良和蔼,在即将去美国投奔女儿颐养天年之前,却因为正直地揭露出医院处理死婴不当事件而被杀害……小说中所阐明的这些故事情节本身就意味着秩序是部分的无序状态。在其积极意义上,如果小说人物批判和反抗秩序的不合理成分,这一过程的表现仍然是无序的,这是因为,“特别是在悲剧中,秩序的创造与含有行动的无序现实直接相连。不管最终得以认可的秩序有何特征,它的确是在这一具体行动中被创造出来的。有序和无序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14)。这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只不过小说中的悲剧主人公在秩序中承受无序是何等的痛苦与艰难。 小说把悲剧置于一个普遍的信仰缺失的时代,人们关注日常生活胜过对生命本身的思考,即使是拼命工作,也不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挣扎。当代悲剧已经把信仰看作一种奢侈的能指存在,而很难将之与人们的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在这一问题上,威廉斯仍然把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奉为圭臬,认为最常见的悲剧历史背景是某个重要文化全面崩溃和转型之前的那个时期,“它的条件是新旧事物之间的现实张力:体现于制度和人们反应之中的既定信仰与人们最近所明显经验到的矛盾和可能性”(15)。这一观点就与当代悲剧产生了距离,客观的秩序和客观的无序成了冲突的双方,而在它们互相挤压的中间部分则是悲剧人物,这就是《第七天》所要传达的悲剧性。 与信仰有关的一个话题是价值观念,这一点在小说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鼠妹”刘梅和伍超来自农村,同在一个发廊打工,干着钱少活累的工作。由于羡慕同村姐妹卖淫所得的高收入,也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而主动选择堕落。“干上几年后挣够钱就从良,两个人回他的老家买一套房子,开一个小店铺”(16),这是刘梅与男朋友商量去卖淫之事时提出的想法,由此可以看出小说主人公的价值取向: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追逐物质生活的丰盈比保留自身的尊严更为紧要,这无疑是“笑贫不笑娼”这一畸形价值观念的生动写照。在这里,传统的价值观念虽然没有站出来,但是作为隐形的存在,它的力量依然是巨大的。这就意味着,畸形观念的出现本身即是悲剧性的。威廉斯宣称“最有价值的东西与最无法挽回的事实被置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关系和冲突中”(17)这一悲剧表现时,我们不禁进一步追问,在小说世界中,“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在这一问题上的迷惘已经说明了小说人物是何等的悲剧。 威廉斯认为具有直接经验属性的悲剧感本身是对信仰的质疑,在这种情形下,“将无序状态和苦难戏剧化并解决的一般过程被深化为显而易见的悲剧层次”(18)。悲剧冲突的艺术化解决,这是威廉斯一直坚持的论调,只是这其中不免使人生疑的是,即使在悲剧艺术中,无序和苦难何以能解决?悲剧人物的死亡可以实现冲突的解决吗?在现代悲剧中,死亡固然是一种悲剧经验,但是悲剧绝不停滞于死亡本身。 四 “死亡”新解:现代悲剧的展示意义 在对《第七天》的诸多评论中,对余华“以死写生”艺术手法的关注并不多,人们多把这一点看作作者作文雕饰的噱头。实际上,余华试图赋予死亡以悲剧叙事的功能,这一点具有大于死亡的主题学意义。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方面,以死者为叙述视角,杨飞在死去之后回望人生,从容不迫地把生前的无奈与痛苦尽数展现,虽然是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者,但正因为是死去的人,在游荡中被赋予全知全能的视界。另一方面,一般而言,悲剧的高潮是主人公的毁灭,至于这一毁灭所带有的形而上或伦理学的悲剧意蕴,则是对文本的诠释,但是,《第七天》的故事却是从死亡开始讲述的,并且是通过死亡来讲述关于死亡的故事。“以死写生”不仅是创作手法的标新,更是通过这种荒诞的讲述,揭示艺术的真理。 死亡的意义是什么?这似乎是在传统悲剧中已经得到充分解答的问题,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悲剧英雄向死亡屈服,这看起来好像是命运胜利了。但是由于他自由地这样做,知道死亡是自己走向永恒的途径,因此可以说,他正是在这一看似屈服的行动中超越了命运”(19)。这些构成了传统悲剧的典型特征:客观意义上的死亡在效果上彰显了命运的主导力量;而主观意义上的死亡却是主人公的自由选择。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死亡在此都只是一种手段。这在现代悲剧中不再存在,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自身的毁灭既不能带来形而上的追问,也不会带来道德意义上的崇高,更重要的是,现代人更多的是“被死亡”。杨飞死于饭馆的煤气爆炸,他的父亲则在绝症中死去,交通事故,商场火灾……这些毁灭在传统悲剧的批评范式中是不能称其为悲剧的。但是在当代,死亡却可以成为悲剧的全部理由。 威廉斯说,死亡在悲剧表现中的意义在于以此来定义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命运的盲目性,可是在我看来,这仍是基于传统悲剧基础上的逻辑认知,因为现代悲剧更多的是对死亡的一种展示。对死亡的展示也即对无序的呈现,在这一呈现中揭露人的存在状态,把价值判断的权力交给读者,把对死亡的认知和思考也交给读者。因为死亡本身也是一次行动、一种经验,“无论人怎样死亡,这种经验不仅是肉体的瓦解和终结,也是他者生活和关系的一个变化,这是由于我们在自己的期待和结束中认识死亡的同时,也会在他人的经验中认识死亡”(20)。更进一步,我们通过死亡所了解的并非仅仅是它本身,更有我们周围的环境、人事,甚至人心。这样一来,在无序环境中,观看者对悲剧人物的怜悯和同情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造成悲剧的原因就像空气一样在我们周围,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不难看出,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研究相联系,现代悲剧观念无论是创作理念还是批评方法,都不再是精英主义的,或者说悲剧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表现,这在艺术流变史中是难得的。甚至可以说,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悲剧思想中,已经实现了悲剧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威廉斯在讨论革命与悲剧的关系时曾经指出:“一般形态的悲剧观念特别排斥社会性的悲剧经验,同样,一般形态的革命观念也特别排斥悲剧性的社会经验。”(21)这似乎构成了二者的悖论。但是,从生成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在具体的事件中找到其联系。在《第七天》中,社会性是这出悲剧的主色调,个人也因承载了诸多无序所带来的伤害而具有了普遍性。 总之,《第七天》是现代悲剧经验书写的重要文本,它突破了传统悲剧的固有范式,以社会个体的悲剧经历为主要内容,展示了整体秩序失衡下的悲剧事件和场景。它本身也是一种对话——作为小说体例的悲剧书写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理论的对话,悲剧书写的中国经验与西方当代理论话语的对话。 注释: 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第26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④⑤⑥⑨(11)(12)(13)(14)(15)(17)(18)(20)(21)Raymond Williams,Modern Tragedy,London:Chatto & Windus,1966,p.46,p.46,p.45,p.62,p.90,p.93,p.104,p.140,p.52,p.54,p.58,p.54,p.57,p.64. ③⑩(19)Terry Eagleton,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p.3,p.76,p.122. ⑦谢柏梁:《中国悲剧的美学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⑧李育红:《后悲剧时代的来临——从余华的〈活着〉谈起》,《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 (16)余华:《第七天》,第113页,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标签:第七天论文; 文学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英国生活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死亡论文; 余华论文; 伊格尔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