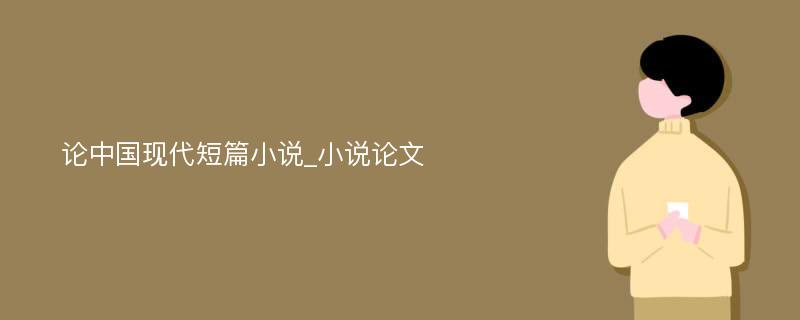
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年底我在韩国讲学,收到钱乃荣先生的来信,相告他和黄乐琴教授选编的六卷本《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以下简称《选集》(注:《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钱乃荣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将要付梓,嘱我作一序言,并讲明希望我能够结合本世纪短篇小说的发展谈点看法。钱先生是我所尊敬的朋友,他提出这个要求我无法拒绝,当时心里还存着一份侥幸,以为“小说界革命”以来的小说发展史,已经有不少学者在前头做出了很好的研究成果,我纵然没有什么独特的心得,大约讲些一般性的小说史知识还是可能的。去年2 月我回到上海不久即收到钱先生寄来的小说选目录和有关材料,看后才真正的感到了为难,因为编者在每卷前面都写了很好的前言,关于本世纪以来的小说发展情况多少都谈到了一点,所以我想说的“一般性的知识”也纯属多余了。好在当我把这个困难讲了出来时,钱先生表现得特别宽容,他说,那么,你就随便说点什么吧。那么,好吧,我也只好随便说些什么了。
由于对现代小说的形成一向没有特别关注,为写这篇文章我不得不临时抱佛脚去翻阅陈平原、夏晓虹编的《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随手一翻便翻到了邱炜薆《菽园赘谈》的“小说”条,其说颇为奇怪:“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其余谈狐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备取消闲,犹贤博弈而已,固永可与纪实研理者絜长而较短也。”什么才是小说的正宗?邱炜薆列出三类小说:一、“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一派,代表作有“本朝”的冯班的《钝吟杂录》、王士祯的《居易录》、阮葵生的《茶余客话》、王应奎的《柳南随笔》、法式善的《槐厅载笔》《清秘术闻》、童翼驹的《墨海人民录》、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等;二、“谈狐说鬼”一派, 有纪昀的《阅微草堂五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三、“言情道俗”一派,代表则以《红楼梦》。在邱炜薆的说法,第一类才是小说的正宗,其余两类不过为“备取消闲”的“小说支流”(注: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4页。)而已。陈平原先生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引用了这一说法,引申出“据实而录的笔记小说对粗人固然没什么影响,可在文人中却颇有市场,真可谓代有传人,源远流长。晚清小说理论家中也有以之为小说正宗,把它放在谈狐说鬼的《聊斋志异》与言情道俗的《红楼梦》之上者。”(注:引自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但从以后的发展而言, 即使在讨论笔记小说时,邱氏所列的正宗一派作品,也不见于现在的文学史或小说史著作。可能是研究者多把它们看作文史资料,而非小说。我手边的文学史书籍中,仅吴礼权先生所著的《中国笔记小说史》内。提到《两般秋雨盦随笔》:“八卷,所写内容较杂,类于《阅微草堂笔记》等杂俎派作品,只是与纪氏作品稍异的是梁氏所记少于鬼怪内容而详于历代文学轶事、诗文评述、风土名物等……整部作品较之纪氏作品又在艺术性方面有逊色了不少。”书中还简略提到《茶余客话》:“十二卷,阮葵生撰。自经史子集洎有清掌故,下及书画、金石、禽鱼、草木等内容。无不讲贯。”(注:引自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96—297,300—301页。)廖廖数语,都是将其列为《阅微草堂笔记》的余流。所以,“晚清小说理论家”(陈平原语)所推崇的正宗一派小说,现在完全不传,而当时仅视为聊备一格的“谈狐说鬼”派与“言情道俗”派如《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今则盛传。可见小说的生命力存在于读者当中,而非小说理论家所能操作,小说作为艺术作品其流传与否自有规律可寻,所谓讲究“据实而录”,可能对认识历史和风土民俗有一定的意义,但文学艺术恰恰需要虚构和想象的力量,“谈狐说鬼”与“言情道俗”两派,歪打正着地为清代小说创造了不朽辉煌。
但是陈平原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引用邱氏的观点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因为当梁启超辈发起“小说界革命”运动时,新小说家们所面对的传统小说,主要是章回体的长篇小说或笔记体的文言短篇小说。“小说界革命”。发轫之初,启蒙的呼唤声甚嚣尘上,其烟尘笼罩了新小说的发展,所谓“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引自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载《新小说》第1号,1902年。)、所谓“以稗官之体, 写爱国之思”(注:引自梁启超《本编之十大特色》,《清议报全编》,新民社辑印。),主要都是针对着章回体的长篇小说的弊病而提出的补救理论,而邱氏此刻所强调的“正宗论”,正与梁氏的理论遥相呼应,不过所涉及到的笔记小说的范围。引邱氏说无非证明了当时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无法避免时代风气。但是,与梁、邱等人所期望的相反,由于急功近利的政治革命的风气所致,新小说从一开始就暗暗地种下了病根,“据实而录”的笔记体小说并没有在现代小说的形成期提供多少积极的因素,倒是“谈狐说鬼”与“言情道俗”,虽然不属于什么正宗大道,反倒自由一些,表达出个人性的小说叙事的特点。
我这么说,也许有点故意拧着鼓吹“小说界革命”论者的意见而论,其实这也是20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的实践所证明的。本来中国古代小说就似粗服乱头的普通女子,活泼泼地生长在民间,而非什么“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倾城货色,无论是文人私下里的辛酸创作,还是与市民文化相关的话本说书,虽然难免有道德教化的成分,但艺术上终究是多了几分个人性的叙事因素,用今天的艺术语就是多少体现出个人的话语立场。但是戊戌年的维新运动失败,意在政治改革的士大夫们被驱逐出庙堂。开始了独立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萌芽时期,一时间,文学界的各种“革命”都随之思想启蒙的要求而提出。其中小说之所以特别受到青睐,也就是因为它在民间的特殊地位,可以被思想家所利用的条件多一些而已。今人常常引用康有为的名言:“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似乎对小说的功能极为重视,但仔细想想,康有为对小说自身的特点和功能价值毫不关心,仿佛是士大夫掠来一个民间女子为奴婢,用来做饭、扫除、洗衣一样,骨子里很瞧不起这样的粗俗女子。他接下来的话这样说:“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注:引自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载《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12页。)圉人是指养马者,在康有为眼中,小说也就是这么个地位,不就是因为它的通俗普及,易于宣传么?所以,“新小说”家们对来自民间传统的古典小说十分鄙视,斥之“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注:引自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载《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21页。)。 “诲盗诲淫”,再加上前面所说的“谈狐说鬼”,宣扬迷信,其罪莫大。他们引西方政治小说来纠中国小说之偏,以为是获得了灵丹妙药,其实所译介的所谓政治小说即使在西方日本也属三四流的东西,至今“诲盗诲淫”的中国小说仍然存在,而《经国美谈》之类的翻译小说倒已无影无踪了。
所以,以20世纪初的晚清十年小说论,虽然以文代政,新陈代谢,声势颇壮观,但真正留名于文学史的名著为数不丰。民初期间,革命既退潮,思想又沉寂,小说反而与市场结合,“诲盗诲淫”之风愈炽,于是有《玉梨魂》之类的缠绵于个人情事的骈体小说,也有各类适应文化市场而生的白话体“民国旧派小说”(注:“民国旧派小说”的提法源自郑逸梅先生,他认为“鸳鸯蝴蝶梦”只是指徐枕亚《玉梨魂》一派的骈体文小说,不能涵盖各类型的小说,所以他改用“民国旧派小说”,言其旧,是针对“新文学”而言,不一定说它们都体现了“旧”传统。请参阅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虽为当初“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所不满,(注:如梁启超对民国初期的小说发出“吾安忍言,吾安忍言”的抱怨。请参阅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7页。 )但从接近现代小说艺术的雏形而论,则是悄悄的回潮,也是一种曲折的进步。(注:这里用“进步”一词并不恰当,小说迎合市场的调节对艺术本身不一定是好事,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无法作详细讨论。所以这里说的“进步”只是指小说创作摆脱强烈的政治目的,把小说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而言。陈平原君在他的《小说史》里也认为“从小说摆脱政治思潮的搀扶,直接依赖于小说市场的自然调节这个角度来看,这又未始不是一种进步。”(见该书第7页))我正在指导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 她的研究题目是民国初期的《小说月报》,她向我提出过一种质疑:假如没有新文学运动,中国的小说创作是否也会走上现代白话小说的道路,而且在抵制过于欧化的意义上或许会做得更好?她是很聪明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我无法用轻率的态度来回答她的问题,也不赞成作这样的假设,因为历史无法证明不存在的东西,从旧派小说的后来发展看,即使以小说的艺术要素为标准来衡量,一些“大家”如张恨水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仍然不及同时期的新文学作家如巴金、茅盾、老舍、肖红等长篇小说形式上开创的“现代”意义。当然,这是以肯定西方小说艺术形式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为前提的答案,如果有谁认为章回小说也是现代小说的形式之一,那又另当别论。不过我并不想回避我的基本态度是:民国以后“旧派小说”脱离“新民”的宏大宗旨后,在艺术上的回潮仍然具有积累小说艺术经验的价值,只是这种经验还来不及总结,就被一场更为猛烈的新文学运动所淹没所取代了。其关键问题当然不在写小说是否用了白话,重要的是现代人的意识开始冲击传统文人的替天行道或者才子佳人的意识形态。
讨论新文学白话小说的创新价值之前,我还想饶舌讲几句短篇小说的传统。中国与西方在小说史上有很不同的地方,中国先有短篇小说的形态后有长篇小说的形态,志怪笔记到唐传奇为文人创作一路,宋元话本到“三言两拍”为迎合文化市场的民间创作一路,早在长篇小说出现之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审美形态和艺术模式。而西方则相反,史诗传统决定了来自英雄罗曼史的长篇传奇小说的发达,而短篇小说则到了文艺复兴才姗姗来迟,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与长篇小说抗衡。英雄史诗透彻着神的精神,形而上的力量暗暗支配了西方的长篇叙事作品,大多数的西方古典作家都持二元论的世界观,即使在笔底下涌现出来的是现实世界的过程,但在他们仁慈的胸怀里奔腾着的却是创造另一个想象世界的激情。这种现象一直到近代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罗曼·罗兰的英雄小说、乔伊斯的反英雄小说里都是存在的。有了这样一种神性普照的彼岸世界的观照,来自于民间传统中鬼怪传说故事的短篇小说似乎很难得到同情。在初期,西方的小说评论家们对短篇小说没有足够的重视,据伊恩·里德著的小册子《短篇小说》中对簿加丘《十日谈》等一批最早的短篇小说作品所归纳的定义,是“一种虚构的散文叙事,以人物或行动再现日常生活(有时是过去的,但大多是现在的——因此是新的,一种新奇的事物)的小说。”(注:引自伊恩·里德的《短篇小说》,肖遥、陈依译。昆仑出版社“文学批评术语丛书”1993年。)这个定义是针对了表现英雄罗曼史的长篇传奇传统而反其道行之,但在神性光照下的欧洲文学传统里,“日常生活”意味着它的凡俗性和此岸性。西方早期的短篇小说家大都离不开民间的古怪传统,如霍桑、爱伦·坡、果戈理、霍夫曼等人的早期创作,但这些出身低微的古怪精灵似乎不能作为伟大神性存在的证明,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这些民间的荒诞因素都应该从短篇小说里驱除出去,(注:伊恩·里德在《短篇小说》里记载:“正像艾尔弗雷德·G·恩斯特龙指出的,‘魔鬼、圣徒、神仙之类的传说和纯属妖术的故事等’罕有权力被认为是短篇小说。通常它们并不集中注意于人类的事物,而且无论如何,它们原本就并不意在小说。……使这样一些作品失去资格的并非题材本身,因为这类题材也能产生合格的故事,如福楼拜的《圣·玉莲外传》,它是经过了艺术加工而形成的作品,为的是传达丰富广阔的人性。”不难理解这种观点里包含的对民间文化成分的偏见。)短篇小说只能是一种再现现实日常生活的虚构的散文作品。因此,西方短篇小说的艺术价值与长篇小说并不一样,它既然失去了彼岸的观照,那重要的只能是突出故事和叙述故事的技巧,如莫泊桑的叙事框架、欧·亨利的小说结尾、契诃夫早期作品的幽默文体等等,得到了批评界多少有些庸俗的强调。(这并不排除任何时候都有杰出的小说家冲破叙事形式上的局限,从令人绝望的此岸性中体验和迸发出生命的意义,从而粉碎了短篇小说规范的自我束缚,创造出万千气象的短篇作品。)但是,这些特点在本来就缺乏史诗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存在的,章回体的长篇白话小说是在话本艺术充分发展了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初的长篇小说是短篇的连缀或者扩大,同样,优秀的话本小说在艺术结构上也可以说是缩小的长篇,从艺术表现上说,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异。因此,中国现代小说形成之初的迫切任务,是对于短篇小说的审美形态的重新确认,以便把它从传统的章回体的叙事方式中摆脱出来。
提出这项任务是有前提的。在晚清十年的白话小说发展中,虽然在翻译日多的西方小说影响下多少出现了新的叙事因素,但不足以改变传统白话小说的叙事框架。其诸种原因中,可能有一个是与章回体的长篇白话小说承担了特殊的政治任务有关。本来中国有着丰富的白话短篇小说传统,但在乾隆后期,“白话短篇小说基本绝迹。”(注:引自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 页。书中作者说明其说的依据为郑振铎把草亭老人著《娱目醒心编》(乾隆五十七年刊本)断为“最后的创作话本集”。)胡适曾分析其原因是因为长篇白话小说和文言短篇的兴起,窒息了短篇白话小说的发达。(注:请参阅胡适《论短篇小说》,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卷》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而在晚清政治小说泛滥的主流创作下,长篇白话小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章回体在流行文化市场方面获得绝对性的胜利。为了反拨这一主潮,民初的小说家们宁愿用文言来写小说,这就是为什么徐枕亚、苏曼殊的文言小说会风行一时,甚至鲁迅早期的小说创作也是用文言文来表达。同理,西方影响下的现代小说的崛起,它必然会在处于空白状态下的白话短篇小说领域发生根本性的革命,而这种突破的主要目标就是与章回体的叙事方式决裂,与传统白话的语言形态决裂,并通过大量引进欧化的名词、语法和句子结构,使现代人的精神感受通过陌生化的美感形式有力地宣泄出来。
传统白话是一种与说书人叙事立场相联系的语言,与新文学欧化语言相比较,差异是很明显的。第一,传统白话基本上是站在中国平民(包括农民、市民)的立场上看事物,所以能谴责官场政治的黑暗和揭露社会不平,但很难达到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省和自我批判;第二,叙事语言上的通畅、圆熟、生动,都是说书艺术必不可少,但偏于外部世界(即能用肉眼看得见的)的描述,而对看不见的心灵世界的剖析和开掘却是陌生的,通常只能通过外部世界的反应来暗示心理活动;第三,传统白话在审美上以大众接受为取向,语言的媚俗是难免的,所以很难产生陌生化的效果给人们一种意外的震动。而这三个不足的方面,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急需解决的文学启蒙任务。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把“现代性”从一部分士大夫意识中解放出来,转而成为全社会的努力目标的民众性运动,然而自波德莱尔始,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与心灵反应之间构成了巨大的自我分裂,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的大撞击中所获得的强烈的现代意识,也必然带有分裂性,这种极为复杂的感受用传统白话很难准确的表现出来。所以,虽然传统白话在晚清十年里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在民国初年又创造出很不错的小说,但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要承担起精神审美的重任,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以民国时期的白话小说《卖药童》(徐卓呆著)为例,这不仅是一篇充满了社会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的作品,而且也把传统白话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直逼人心的黑暗。小说写一个逃税卖刀疮药的孩子被警察抓住,警察明知故问:“这是什么东西?”孩子不敢承认是药,以儿童的说谎能力回答说这是“糖”,警察作弄孩子说“既是糖,你就吃吃看。”于是有了下面的一段精彩描写:
真是个残酷的命令。阿祥是个倔强的性情,哪里肯踌躇,解开包来,推入口内,虽有些粘着牙齿的,他竟一吞而下。警察长见了,也很惊异,冷冷地道:“甜么?”阿祥答道:“甜的。”这是势所不得不如此。警察长又道:“糖既很甜,你把他通通吃了,方始饶你。”此时僧侣、妇女、婢女们,见了这样子,大约也不知可怜。阿祥两只眼睛,恶狠狠的向众人看着,把第二包吃完了,于是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八包,到了九包,他的眼睛发白,呻吟起来。然而无用……十包、十五包、十六包、十七包,竟一齐吃了上去,塞得声音也发不出来,好容易说一声道:“如此,好了么?”
这段文字,简洁而生动,尤其最后“好了么”三字,具有很大的震撼力,控拆了人心的黑暗。作家也描写人物的心灵感受,用“恶狠狠”的眼神来形容,能起以一挡十之效。但是我仍要说,如果以上述三个不足方面来衡量,这段文字仍然不脱传统白话的局限,人物的冲突还是简单化了,没有进入心理层次上的较量,(可以对照《雷雨》里逼蘩漪吃药一幕的冲突描写。)而且这种冲突是单向的,人道主义的层面也是单向的,对被侮辱者自身的心理缺乏省思。不妨对照鲁迅用欧化语言翻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幸福》:一个老妓女为求生被迫裸体在雪地里被人殴打取乐,当由此获得五个卢布的报酬时,她马上由痛苦转而快乐:
在血污的手掌上,金圆像火花一般灿烂。五个,伊想,伊便抱了大的轻松的欢喜的感情了。伊迈开发抖的腿向市上走去,金圆在捏紧的手中。衣服擦着伊身体,给伊非常的楚痛。但伊并不理会这件事,伊的全存在已经充满了幸福的感情,……吃、暖、安心和烧酒。不一刻,伊早忘却,伊方才被人打了。(注:引自《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11页。)
欧化的文字自然没有前面所引的段落那么流畅明白,但读者在领略陌生语体的同时也领略了陌生的感情世界和心理世界,在重重的刺激后让人感到的不是浅薄的人道主义的一般同情,而是连带了自身血肉与灵魂的自审与忏悔:这种被侮辱者的健忘不正是每日每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阿Q精神吗?换了一种语言的方式, 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所隐藏的意义就赤裸裸地揭发出来,并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效果。虽然欧化的语言文体常常受到批评,但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它所起到的战斗作用,恰恰是圆熟的传统白话所不能达到的。
如果说,追求现代性以及同时感受以及现代性的分裂是“五四”新文学的特征,那么,与其说新文学提倡了“白话文”还不如说是提倡了“欧化”文,这就是被后来更激进的革命文学论者所病诟的“非驴非马”的语言文字,但当时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真正打开传统文学的缺口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不是流利的白话小说或白话诗,而恰恰是鲁迅那篇具有内在分裂特征的现代小说《狂人日记》。我有个极端的看法,认为20世纪的短篇小说创作,能超过鲁迅的几乎没有,而《狂人日记》正是其中难以超越的小说文本之一。它的意义不在于完美和谐,而表现在它的内在的分裂性。从语言上说,它是文言与欧化语体相交替,日记中大量拗口的西方语法的句子与引子部分流利的文言构成鲜明的对比,一下子就把绵软朴素的传统白话打下台去;从文本意义上说,狂人是将抗议传统“吃人”(呼唤人的独立意志)和揭露人自己身上遗留的“吃人”本性(揭露人的不完美性)又构成一对互为分裂的意义。这种巨大的分裂性本身就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不但与当时一般的白话小说拉开了距离,也与19世纪西方的短篇小说传统(如果戈理时代的《狂人日记》)拉开了距离。鲁迅自言他的小说不仅受到果戈理等继承民间古怪传统的古典作家的影响,还受到了尼采、安德列夫等创作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的影响。(注: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现代文化就是这样以其自身的分裂性来影响中国的现代作家。只有紧紧抓住了现代文化的内在分裂性,才能抓住新文学的根本,否则,单单从白话还是文言的区别上很难把握现代文学的要害处。古怪拗口的语言文体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殊的分裂现象。我们今天读鲁迅小说还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种分裂于作家心身所带的痛苦。如《伤逝》里所表现的知识者追求个人主义的反叛以及对其后果的悔恨,如《孤独者》,知识分子嫉世愤俗的孤军作战以致对自己营造的幻影的绝望,他的散文诗《野草》里的许多篇章更是生存于巨大分裂的两难之间的生命呼唤……,自我分裂都是在断断续续的回忆体叙事文体中得以宣泄,在鲁迅那儿,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就是这样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有力的实践。
自鲁迅的创作始,现代短篇小说在中国开始了自觉的进程。我们似乎还应注意到,鲁迅对现代性的内在分裂是通过他的独特的洞察力和敏感的个人气质感受到的,而不是时代的“共名”强加给他的。20世纪的中国文化在知识分子自觉参与建构之下形成了自身的规律,我把这种规律概括为“共名状态”和“无名状态”的相交替过程。(注:关于“共名”与“无名”的详细论述,请参阅拙作《共名与无名》,收《写在子夜》,上海人民出版社1886年。)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文化都是处于“共名状态”下,即在某种时代主题的笼罩之下,如晚清十年中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的是“革命和立宪”的“共名”,政治小说泛滥一时就与这种时代“共名”相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是最大的“共名”,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但很快又有更为激进的革命思潮取代之。1937年抗战爆发,“共名”与民族革命相联系,这以后,“共名”就在各种时代主题下一直延续着,直到90年代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转型以后,才初步结束这种状态。而“无名状态”在历史上总是很短暂,大体是一些理想失范,精神松弛的年代,没有强而有力的时代主题来统一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处于相对自由、甚至有些颓废的状态,“无名”即无以名之的意思。民国初期应该算一个“无名”时代,文化市场的规律开始对文学艺术产生支配作用,出现了较为多元的民国旧派小说;30年代初勉强也能算“无名”时代,它是以各种流派激烈争斗和自由发展为标志的;再就是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多元化的文化状态。现代短篇小说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成就最为辉煌的文学艺术品种,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共名状态”下的短篇小说很少能脱离“共名”影响,更甚而为时代主题的宣传演绎。如抗战以来的作品大致如此。凡能保持个人立场的作品,大致两类,一类如鲁迅,他是一位在创造“共名”的同时又消解“共名”的自我分裂者,如《狂人日记》所示,批判吃人礼教,张扬人性,时代“共名”而传播之,但揭示人类有吃人的遗传因素,必须自我忏悔,则是对现代性的质疑,虽不被时代所理解,但暗暗地隐藏于文本之中。这是个人性高于时代“共名”的典范,一类则另辟蹊径,躲开时代“共名”而不顾,为保持个人性宁愿忍受世人冷落,有时故意以保守主义自居。如20年代的冯文炳(废名)的小说,以描写田园风光和淳朴民情来保存现代社会发展中已经丧失了的理想,可以说是反现代性的文化代表。废名的创作后来启发了沈从文的田园抒情小说,不过沈氏出名在30年代的“无名”状态下,各种风格流派的自由发展已经不再受到“共名”的制约和遮蔽了,所以沈氏之名高于冯氏。在“无名”状态下的短篇小说则又是另一番样子,因为失去了统一的时代主题,个性比较自由地体现出来,短篇小说篇幅不长,更能体现出活泼的个人性,一些被视为“小”作家的作品,往往此时最为活跃。如30年代京派海派小说的众多作品,在20年代的革命时代和1937年以后的抗战时代都隐匿无迹,唯在“无名”的30年代初昙花一现,却给我们留下了较为可观的作品。
我之所以比较强调现代小说的个人性立场,这是因为个人性立场在文学实践中稀少而珍贵。现代中国文化是分裂的,作家的写作立场也是分裂的,有站在国家权力(庙堂)上用文学来宣传主流意识形态,这且不说,也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参与创造了时代“共名”后,写作立场成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惟有鲁迅这样少数作家能以巨大的个人性来穿透、包容、甚至解构时代精神,以达到时代性与个人性的高度一致。而大多数坚持个人性的作家都不得不蒙受各种误解和批判。由于20世纪的中国文化“共名状态”多于“无名状态”,人们习惯了以时代“共名”的立场来衡量小说作品,认为体现了时代“共名”的作品才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品,而表现个人性的作品,则于世无益,必须力加排斥。各个时代的“共名”虽有不同,但对个人性的排斥则是一致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围剿“个人性”运动可以追溯到20年代批评界对郁达夫小说的攻击。郁达夫的小说被后来的研究者解释为“反封建”,但我想这只是把郁氏小说“共名”化了,其实郁氏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个人性的叙事立场,他从不讳言自己爱金钱女人,也不讳言自己变态的情色观,他为自己的生理性骚动痛苦万分,却在痛苦的忏悔中刻画出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的人格分裂者。这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和人格的自我担当。如果说,郁达夫的小说有时代意义,这就是最深刻的时代意义,现代社会的分裂性通过一个痛苦灵魂的忏悔而活生生的刻画出来,个人性的叙事立场与时代性的深刻认识达到了浑然一体的表现。除了个人的立场外,任何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社会责任感都是可疑的。
最后,我还想讲一下对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特征的看法。它包含了以下几个相关的问题:如何理解现代短篇小说的审美形态?如何强调短篇小说形式的诗性因素?如何甄别它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之间的界线?这些想法从本文一开始写作就缠绕着我,之所以没有直接触摸它,是因为我对它的思考并非出于文学史的研究,而是对当下短篇小说创作的某种可能性的探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历史虽然不算很长,但是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中是最活跃、也是最具生命力的小说形式之一,它不仅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担当了先锋的作用,而且在紧扣时代主题和抒发心灵自由两方面能保持平衡和多样的发展。不过,这种多样化的繁荣多少是依赖了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的不发达,使短篇小说在自身展开的多种功能里,复杂地包含了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的因素。最典型的是茅盾的《春蚕》,作品记载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生产劳动过程,它包含了一种连续性的时间长度,其时间的无限制性决定了故事的无限制性。这一类小说结构上往往是开放、可以不断延续下去的,所以,《春蚕》的结构打破了短篇小说的形式限制,它已经成为一种连续性的中篇结构。但是在短篇小说发达以前,尖似《春蚕》那样的作品仍然被人当作短篇小说来阅读和分析的。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面是,在文学史的漫长过程中,因为短篇小说密切应和了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的信息,所以,任何时代都无法孤立地界定它在审美功能上的定义。除了短篇小说必须在篇幅上有所节制以外,似乎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定义来约束它。针对这两个问题,这无法依据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作品来讨论它的定义,而是采取一种当下性的立场,讨论当下的创作环境里短篇小说如何最大可能地表达自身形式上的优势和独特性。而文学史仅仅是作为我们讨论问题的背景才引上桌面。
文学史所展示的背景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起步之际同时面对了三种传统:古代话本体白话小说、古代笔记体文言小说、西方短篇小说的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现代短篇小说的主要资源来自西方短篇小说,对前两者则持否定态度。胡适把现代短篇小说定义为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注:引自胡适《论短篇小说》,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影印,第272页。 本文以下所引胡适的观点均出此文,不一一指出引文处。)这一定义本身来自西方大学的文学教科书。(注:请参阅美国哈米尔顿的《小说法程》,华林一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吴宓作序,言其:“简明精当,理论实用,两皆顾及,可称善本。”)胡适用这一标准来梳理“中国短篇小说史”,不能不把古代笔记体的小说传统全然否定,他强调了短篇小说的两个标准,一是结构上的“用全副精神气力惯注到一段最精彩的事实上去”,即所谓人生的“横截面”;二是强调写“琐碎细节”和人情世故,即所谓“写实性”。这两点均来自西方短篇小说的传统,经典作品是都德的《最后一课》和莫泊桑的《柏林之围》,但以此标准来绳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虽然在细节真实方面差强人意,但结构上总难以符合。所以胡适在论及中国短篇小说时完全不顾形式上的限定,把寓言、叙事诗都归为短篇小说,这实际上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标准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只有依据西方的小说榜样才可能出现真正的“现代短篇小说”。这种定义小说的方法虽嫌蛮横霸道,但对于新的短篇小说审美趣味的形成却是起到了最大的影响。周氏兄弟在1909年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所选均为西方短篇名作,可是出版后不受欢迎,究其原因,如鲁迅后来所悟:“《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注:引自鲁迅《〈域外小说集〉序》,收《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 )胡适在《论短篇小说》所提出的一系列小说定义和理论,正是为了改变这一传统审美习惯。
但我私下觉得,胡适与鲁迅在表述上的差异还是存在的。胡适根据西方教科书的小说定义来作阐述和发挥,虽然在理论上比较准确地说明短篇小说的特点,但是在审美把握上仍有含混的地方。譬如,什么样的故事才算是“人生的横截面”?从叙述方法上说至少有两类:一类是浓缩的故事,像徐卓呆的《卖药童》,作家把卖药孩子一生的苦难浓缩在一两天的时间里集中表现出来,故事里包含了孩子告别重病的母亲、卖药过程、被警察戏弄、被关进拘留所、母亲死去、孩子报仇、孩子死去等七个情节,如果叙述上稍再复杂一些,完全可以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像这样的作品在短篇小说里大量的存在,其基本的审美形态是讲故事,只是把所叙述的故事浓缩在一定限度的篇幅之中。阅读这样的作品与阅读中长篇作品的审美方式是一致的。第二类是长篇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胡适所称道的《最后一课》等就是样板,如果叙述历史过程需要几大卷长河般的篇幅,现在只勺其中一瓢,作为历史的一段插曲,通过以小见大的方法折射出历史的某种面貌,插曲本身是完整的故事,而且所要揭示的历史观念也是宏大的。如高晓声的《漏斗户主》也属于这类小说,从故事篇幅来说是短小的,但从这个故事所反映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长河来说,它又是发展的,所以作家可以把陈奂生的故事无限制地说下去。这样的小说,本来也具有长篇或中篇的审美内涵,只是作家叙述视角的巧妙,才可以由短篇来胜任。谁都承认这两种小说确实都是“用最经济的手段写了一段人生最精彩的故事”,而且新文学运动以来一直都是现代短篇小说审美形态的主流。
鲁迅关于“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的表述法,虽然说得比较简单,却直接涉及到短篇小说的新的审美形态,“才开头,就完了”,故事已经包含在里面了,这显然不是指具有完整故事程序的西方小说,而是《域外小说集》里安德列夫的《谩》和《默》一类的作品。前者写了一个怀疑受恋人,但他仍然没有获得“真话”(诚),因为“真话”与恋人一起死了,弥漫在世上的依然是谎言。后者写了一个牧师的女儿自杀了,牧师内心忏悔他曾粗暴干涉女儿的自由,却得不到所有人的原谅,他沉默在一片沉默的世界之中,两篇小说都笼罩在极凄凉的沉闷氛围之下,没有通常所谓的故事情节描写,也没有所谓的“开头”与“结局”。我觉得这种写法才对以章回体、大团圆为审美习惯的中国读者构成了真正的挑战。这些作品完全打破了故事的正常叙述程序,突出的是叙事者或被叙事者的心理片段,物理时间在叙述过程中只起了表层的框架作用,心理时间却任意地流动而不受任何约束。这样的叙事方法我们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已经看到,它被成功地移植为汉语作品。人们在感受狂人的心理时完全忘记了物理时间的限制,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的历史图景中去感受作家熔铸在叙事人身上的精神力量。“才开头,就完了”只是物理时间的自我局限,但叙事人所要表达的精神性却是无限的。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早在发表的当时就因为其形式的先锋性被人所称道,但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鲁迅所实验的小说叙事形式有一部分是对西方短篇小说传统模式的颠覆。我们比较鲁迅和果戈理的同名《狂人日记》就不难看到,果戈理是借狂人的叙事立场讲述了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狂人境遇的故事,而鲁迅则借助狂人的胡言乱语把人们引入一个超现实的感觉世界里领略生命的恐怖。在《白光》《长明灯》《社戏》等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里,故事情节几乎都是破碎的,抓不住的;在《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等重要作品里,就现实层面上的故事而言也是不够完整的,作家故意选择一种半是回忆半是感伤的叙述方式,把故事的逻辑完全打乱,却从叙事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诗性的存在。鲁迅的这一类小说篇幅都不长,但其所包含的精神容量却是说不尽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短篇小说的审美形态。这似乎关涉西方的小说传统的变异。短篇小说在西方的名称是short story, 直译的话就是短篇故事,西方文学传统认为短篇小说是非精神性的,其丰富复杂性都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故事,那么,要对丰富复杂的故事进行概括,就不能不强调它的叙述故事的技巧性,所谓“最经济的手段”——浓缩也好,插曲也好,都离不开“讲故事”的基本手段。但是,随着短篇小说自身的发展,它也逐渐不能忍受毫无诗意的世俗故事,开始尝试着摆脱“讲故事”的束缚,去追求真正的诗性。这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的美学观念的崛起有关,它意味着短篇小说将与精神现象发生一定的感应。鲁迅几乎是同步地从西方现代意识领域中感受到这种变化,他对小说艺术的实验是多方面的,既有对西方传统小说叙事方法的借鉴和继承,如《药》、《风波》《祝福》等;也有对前者的解构。而后一种实验所结下的硕果,我宁愿称之为“诗性小说”或“精神小说”,以示区别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量存在的匍匐于现实社会环境下的世俗故事以及某种“遵命”文学。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限于西方小说传统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五四”初期被否定的古代小说传统,即古代话本体白话小说和笔记体文言小说——谈狐说鬼的传统,在以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仍然对现代短篇小说的创作发生影响。最为明显的有:20年代冯文炳所写的古风犹存的田园小说,30年代吴组缃写的“《聊斋》体”白话小说《菉竹山房》,40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对民间话本艺术的学习,以及80年代寻根文学的崛起、以孙犁为代表的大量新笔记小说的出现等等,一再打破了现代短篇小说讲故事和纪实性的传统审美形态,使短篇小说创作出现新的生机。
我之所以要强调短篇小说的非故事化和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结合,绝对没有批评新文学以来的短篇小说的写作主流的意思,而只是基于当下短篇小说创作可能性的讨论。如前所说,“五四”以来的中篇小说创作不发达,短篇小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承担了多种功能,浓缩型与插曲型的短篇小说叙事得以繁荣,与此有密切关系。自80年代出开始,中篇小说在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遂即成为80年代文学的主力,而相比之下短篇小说黯然失色,由于篇幅的限制,在反映社会问题、涵盖社会容量等方面短篇小说终究不及中、长篇小说。自1985年前后,短篇小说的审美形态出现一次次“革命”,大量以“探索创新”为名的作品在形式上作了富有成效的尝试,其中有一路倾向于文化小说,代表作有钟阿城的《遍地风流》、张辛欣的《北京人》、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孙犁的《芸斋笔记》、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李锐的《厚土》、高晓声的《钱包》等等。另有一路走向更加个人化和实验化,如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陈村的《一天》、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等,如果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实验性作家的作品也列进去,那也是数量相当可观。探索性的作品自然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但它们追求的审美形态则是有相同之处:即追求文化性、个人性,空灵性,文体追求上也愈来愈散文化。“讲现实生活里的一个精彩故事”的定义,慢慢地让中篇小说的审美形态来承担了。中国短篇小说开始从西方小说传统中游离出来,与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实验性小说(反故事)相似,确立了与其他文类相区别的独立的审美形态。
短篇小说的新审美形态自鲁迅就开始创立了的,但长久以来被小说文论研究者们所忽视,没有从《狂人日记》《白光》《长明灯》等作品中提升出反故事的叙事特征。这些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作品所呈现的审美形态与通常的急功近利的社会使命感所要求的并不一样,可以说是拥有了一种在西方文学里只有长篇叙事小说里才可能有的神性和诗性,以致巨大的精神力量得以寄存。1985年前后出现的新的探索小说没有很好地从鲁迅那儿继承到小说的诗性传统,正是近十多年的短篇小说探索没有获得根本性突破的主要原因之。诗性不是技巧,精神性也不是技巧,小说批评领域过多地探讨小说的修辞、技巧、结构等要素时恰恰疏忽了:精神性的因素是无法用定量与技术来达到的。神性观照下的西方长篇小说常常是大气磅礴无拘无束,根本不能用技巧和故事来规范,而短篇小说的过于技巧化,正是它被驱逐出精神庙堂的结果。所以要恢复短篇小说的诗性因素,首先应该把小说从过于技巧化的叙事中解脱出来,重新界定它的审美特征。德国批评家基尔切曼在比较短篇小说与中篇小说的区别时有一处说到:短篇小说的情节“像网一般交错编织”;而中篇小说的情节则“追随上升而又陡然降下的曲线”,(注:转引自伊恩·里德的《短篇小说》。第20页。)我想是值得玩味的,只有当故事通过一种连续性的时间过程来发展的时候才会出现“上升又下降”的图表,然而当故事情节淡化,精神审美现象突出的时候,小说过程会呈现时间的无序状态,网状的“交错编织”显然不是指情节过于扑朔迷离,而是指另外一种万相并存的小说审美形态,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才开头,就完了”的真正美学内涵。短篇小说与其他小说文类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字数篇幅的多少,更不在于内涵容量的大小,一部好的短篇小说所追求的思想艺术容量应该与中、长篇小说是相等的,只要举《狂人日记》与《家》的例子就不难理解,在揭露封建传统“吃人”以及人的自审方面,《狂人日记》并不因为字数少而削弱其精神力量。两者之不可比是它们所表达的审美方式及其产生的效应完全不一样。用个不妥的比喻,长篇小说的审美感受如同人生的一场美满的婚姻,心灵之爱的通过一点一滴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艰难磨砺中,以呈其人性的伟大;而短篇小说的审美感受恰是男女相悦所爆发的一场惊心动魄、欲仙欲死的生命交响乐,在生命的刹那辉煌中获得永恒的意义。所以,诗性的小说即使是寥寥数页的篇幅,也应该是大气而无碍,自由自在地呈现它自身的美感。
90年代短篇小说创作仍然举步维艰。市场经济直接影响了人们的阅读兴趣,现代读物的涌现,包括各种杂志上的通俗故事旨在被改编成影视的文学性作品,都不可能给以诗性的短篇小说恰当定位。因此,讨论短篇小说的未来前景,已经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而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迫使我们正视小说的改革。必须让短篇小说从历史的发展轨迹中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以自身的独特性来应对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钱乃荣、黄乐琴两位教授选编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适时的工作,希望读者能从这一百年的现代短篇小说发展中得到某种启示。
标签:小说论文; 短篇小说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鲁迅论文; 读书论文; 聊斋志异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陈平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