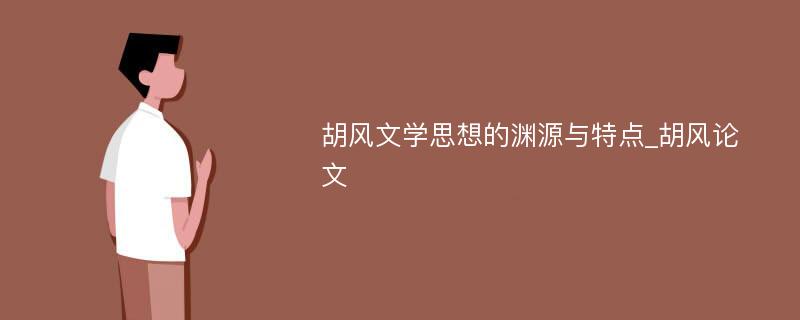
胡风文艺思想的源脉与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特色论文,思想论文,胡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1-0063-08
胡风的文艺思想与其成长于斯的以政治辖制文艺的时代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胡风文艺思想才显示出相对于时代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的获得,一方面应归功于胡风对于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强调和他的文艺本位观念;另一方面则得力于20世纪世界哲学文化思潮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内在浸润。唯其如此,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流派中最为重要的一支——胡风文艺思想才具备了较多的世界意义。
1
胡风的文艺思想,用胡风自己的话说,是渊源于“五四革命文艺传统”和“国际革命文艺传统”的。
胡风对“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他对鲁迅文艺思想的捍卫与发扬上,表现在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全面汲取和忠实维护上。也正是从这种继承、汲取与发扬上,胡风才提出了构成其文艺思想主要内容的“精神奴役创伤论”、“主观战斗精神论”等重要的文艺命题,从而使自己的文艺思想成为连接“五四”新文学与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承上启下的理论纽带。
那么,胡风对“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继承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义。作为一个影响深远却又是突然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发生并非起因于本国传统文化的内部,而是来自于异质文化的冲击。作为一个文化运动,它是由千差万别、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而使这些千差万别的学说、个性各异的人们组成为一个“新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的,据学者汪晖分析,乃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或通常所说的“五四反传统主义”。“五四反传统主义”作为一种对于对象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持续地存在于‘五四’以及其后的中国历史之中”。而“‘态度’作为一种心理倾向,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对象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和怀疑。”[1]
“五四”这种“反传统主义”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种种独特的文艺命题,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论”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胡风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理解与继承是从深刻认识鲁迅的价值与意义开始的。他曾经这样评价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的超人之处:
思想运动里面不知道有过多少的悲喜剧,有些人根本不懂中国社会,只是把风车当巨人地大闹一阵,结果是自己和幻影一同消亡;有些人想深入中国社会,理解中国社会,但过不一会就投入了旧社会底怀抱,所谓“取木乃伊的人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只有鲁迅才是深知旧社会底一切而又和旧社会打硬仗一直打到死。这就因为那些思想运动者只是概念地抓着了一些“思想”,容易记住也容易丢掉,而鲁迅却把思想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思想本身底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表现出来的是旧势力望风奔溃的他的战斗方法和绝对不被旧势力软化的他的战斗气魄。……鲁迅不是一个新思想底介绍者或解说者,而是用新思想做武器,向“旧垒”“反戈”的一刀一血的战士。五四运动以来,只有鲁迅一个人摇动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那原因就在他的从对于旧社会的深刻认识而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里面[2](P10)。
正是在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反传统主义”的深刻理解与继承的基础上,胡风才终其一生对“数千年的黑暗传统”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批判与怀疑立场,不断提醒人们要时刻保持对“亚细亚的落后”、“亚细亚的封建残余”的清醒认识与警惕,并且对此经常表示忧虑和不安。
也正因为如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民族解放浪潮蓬勃而起的火热年代,当人们正在渐渐遗忘或否定“五四”的时候,胡风才反复强调“革命文学”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在根本任务上的一致性:既要为民族的解放(反帝),更要为民族的进步(反封建)。尽管胡风强调“革命文学”运动使文艺在它所要反映的生活斗争里面找着了使民族力量的配合发生了变动的、新的动力,在对于生活的认识上获得了新的看法,但同时也强调反封建的传统、民族进步的目标,不能丢掉。所以,当“大众化”及“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出于政治功利需要和民粹主义心理而产生的对所谓“人民”、“大众”的严重的偶像化崇拜倾向,从而冲淡或者忘却了反封建的严重任务时,胡风便毫不妥协地给予了严肃的批评:
在“人民”或“群众”这说法下面所包括的是怎样广泛的内容,那里面占绝对大多数的农民却是小私有者(无论那是小到怎样可怜的私有),还正是在封建主义底几千年的支配下面生活了过来的。
……
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用快刀切豆腐的办法,以为封建主义和人民是光光净净地各在一边,那决不是咱们这个地球上的事情。[3](P348-349)
从这种认识出发,胡风进一步发展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学观,提出了“精神奴役创伤论”,提醒现实主义作家在发掘“人民”身上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美德——用胡风的话说,就是“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的同时,更要正视并揭露“把这些力量这些愿望禁锢着、玩弄着、麻痹着、甚至闷死着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而胡风的所谓“精神奴役创伤”,则是从鲁迅的“国民劣根性”引申而来,即是指“以封建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3](P349),“以中国的黑暗的统治阶级的意识本身以及这意识的奴役在人民身上造成的影响与创伤”[4](P47)。
“五四反传统主义”对胡风的深刻影响更集中地表现在胡风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在这场发生于40年代的被后人高度重视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战”中,胡风不避偏颇、极端之嫌,断然对中国封建社会里的传统文学、民间文艺等进行了全面抨击,甚至以忽略文艺形式的相对独立性为代价,将“民间形式”(包括“双关语、重字格”等)归为“封建主义”而大加挞伐,认为“否定人生斗争甚至地上生活的佛教文学”,“被封建意识的美学底格律所严格统制着的旧诗词”,“在它的构成要素如音乐、舞蹈等里面被封建意识的美学要求所完全统制着的旧剧,以及其它的封建散文如章回小说,封建韵文如口头诗谣,大鼓词等”,这些“落后的文艺成份”虽然在“战争底强大的动员力量”下参加了战斗,“各自在一定的理解、一定的限度上面反映了战争底内容”,但是“它们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不但在真实性上有绝大的限度,而且得接受落后意识以及落后形式底歪曲作用。所以,能够正确地反映战争底现实,通过内部的改造过程去实现对外抗战胜利的历史发展底内容的,就只有现实主义的革命传统的新文艺。”[2](P143)
正是这种对“五四反传统主义”的继承与坚持,使胡风对具体情势下的封建主义的遗毒及其破坏作用没有放松一丝一毫的警惕,直到解放以后。
第二,“五四”思潮的“情感性”特征。既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对象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与怀疑,那么“态度”的对象性特征就决定了这个思想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必然会在与对象的否定性关系中一致起来:重估一切价值,偶像破坏论成为“五四”时期的流行口号。而且,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的“民主”、“科学”以及“理性”,或作为一种衡量对象的尺度和价值标准、或作为对于传统文化与人格的挑战者和控诉者的面目,出现在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态度”之中。因此,当“五四”思潮在“态度的同一性”的支配下形成一个历史运动时,它的情感性判断就比理性分析来得更加鲜明和突击[1]。
“五四”思潮的这种“情感性”特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以鲁迅、胡适等人对“孝道”和“节烈”观的激烈抨击为例,“‘五四’文化批判经常不是从某种理论逻辑出发,而是和个人的独特经验相关,对于对象的分析是在独特而深切的个人经验中形成的。正由于此,理智的分析恰恰是以个人的强烈的激情为基础的。”第二个方面,则是“五四”人物对于传统秩序的自我流放感和叛逆者的批判心态[1]。
“五四”思潮的这种“情感性”特征同样在胡风身上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体现。众所周知,胡风本来就是以诗人的身份开始步入文坛的,诗人所特有的“情感性”特征一直洋溢在他的文学活动中;另一方面,胡风与中国现代文坛的大多数文学家相比,又是地道的农家子弟,但他对“农民文化”、“大众文化”的批判却又是最为激烈,最旗帜鲜明的。在胡风的文艺评论中,对“封建意识”及其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种种“精神奴役创伤”的分析是非常精辟透彻的,这原因同样在于胡风深切而独特的个人体验。与胡适、鲁迅等前辈启蒙思想家相比,甚至与茅盾、周扬、冯雪峰、何其芳等同代人相比,胡风与封建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广大的农村社会的联系都是最为紧密的,是地道的“血肉关系”。正如胡风自叙,他是“从田间走来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而且他耳闻目睹着自己的家庭由穷苦困顿走上温饱富裕,并终于成为一个“封建大家庭”。所以,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界,胡风对封建家族制度的了解是真正地“凭着实感”的,是有切肤之痛因而最为深切的。所以鲁迅对封建礼教、国民性的分析批判才最能引起他的共鸣与响应。况且,胡风之走上“读书人”的道路,也可以说正是封建家族制度所逼迫的结果。因为在他的家乡,家族斗争、宗法势力的相互倾扎是相当酷烈的,胡风的大哥张名山就是在封建宗族斗争中被人活活打死的,是封建宗法意识的直接受害者。所以“一向受着绅士们底威胁的父亲和哥哥也就决心让我做一个‘读书人’了”[2](P157),因此,封建主义的残酷与罪恶不可能不在胡风的心中刺下深深的伤痕。后来,在抗战期间,他那个“封建大家庭”本身又带给他以沉重、失望与伤感[5]。这些都迫使他不可能像那些没有“实感”的知识分子那样发出对“农民”、“人民”的民粹主义的偶像化赞美。这也是他始终坚持揭露与批判农民(人民)身上“精神奴役创伤”的现实的和深层的心理原因。
胡风对鲁迅的理解最具个人特色,他认为鲁迅“是第一个而且是致命地摇动了几千年的封建意识传统的巨人”。而之所以能够如此,胡风说,是因为“……人情底奸伪,礼教底桎梏,迷信底阴凉……封建社会用它底精神的冷水给这个幼儿施了洗礼,但它却没有料到,那效果不是皈依而是反叛底萌芽。从这个洗礼受到了的冻彻骨髓的颤抖,在这个幼儿底生理机构上留下了永不痊愈的伤痛;自那以来,成了愈成长就愈强烈的反抗的本能作用了。”所以,鲁迅“仇恨封建势力,他底人本主义(对被压迫者的感同身受的胸怀),是凝结着他底童年的梦想、童年的苦痛、童年的哀愁,是和他底肉体的成长一同成长,是熔化进了他底神经纤维里面的”[2](P328-329)。这种评述,与其说是对鲁迅的细心体察,毋宁说是胡风本人的自况。
当然,像“五四”启蒙者一样,胡风也曾告别故乡到异国接受西方文明的熏陶,所以在自我感觉上同样成了传统秩序的流放者,这就决定了他始终以一种完全游离于这个秩序的叛逆者的心态对传统社会采取批判的态度,对乡土秩序、封建意识的残酷与愚昧的否定也就更加坚决,更具有理性的力量与感性的激情。
汪晖在将“民主”和“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特征的同时,将对“理性”的崇拜作为“五四”的第三个特征,但却强调这一特征很少体现在“五四”启蒙思想的方法论之中,因此才又总结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比理性特征更为鲜明、更为重要的“情感性”特征。这一论断是很中肯的。不过对于胡风来说,他毕竟生活在从“五四”的起点上前进了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已经被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掌握,尤其是像胡风这样外文功底好,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知识分子,其理性的思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五四”的杂乱。胡风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曾经加入日本普罗文化联盟下的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对唯物辩证法做过认真的研究,其所受西方那种逻辑理性思维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第三,“五四”启蒙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由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精英层所发动的启蒙主义运动。启蒙的主体与客体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由“精神界之战士”来为广大“国民”启发蒙昧,使后者“从‘亚细亚的落后’(‘今天的状态’)脱出,接近而且获得现代的思维生活”[2](P48)。所以在“五四”时代,对知识界精英的先锋作用与主体地位的强调是最为明确的。而胡风对这一启蒙意识的继承则具体表现在他对“批评家”和“读者”二者对立关系的严格区分上。他认为,“批评家”就是具有正确的判断力、揭示力,或者说具有“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的特殊读者,而一般读者则是到处可见的、饱受封建主义精神奴役创伤的具体的人民,所以“批评家”就必须担负起“和读者斗争……在一般读者底惰性的意识状态里面提示出新的文艺生命”的责任,并“从这开发了反映一代的社会要求的文艺思潮”[3](P33)。
至于“五四”启蒙思潮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口号,胡风也有着更为具体的解释与落实步骤。他认为“意识斗争底任务是在于摧毁黑暗势力底思想武装,由这来推进实际斗争,再由实际斗争底胜利来完成精神改造”[3](P17)。而完成这一“任务”的主体,胡风通常将它具体化为“伟大的批评家”和具有“主观战斗精神”的作家。所以胡风的文艺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著名的“主观战斗精神论”,强调作家要加强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对现实生活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等等,这实际上正是“五四”启蒙意识在胡风思想中的一种独特体现。
2
因为自己与鲁迅非同寻常的关系,胡风对“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继承主要是通过鲁迅,通过他对鲁迅的深切理解与共鸣。胡风认为,与其他的思想启蒙者相比,鲁迅至少有两点突出的特征与贡献。第一,鲁迅“不但用对于科学的信仰来确定了丰富了对于封建势力的认识和仇恨,而且,通过对于科学的信仰,他把对于封建势力的仇恨和对于祖国更生的志愿统一成了一个二而一的战斗的意识立场”,“这就使他和当时各种各样维新知识分子,一鼓作气的绅、商、士大夫底子弟们有了决定性的分歧”[2](P330-331)。紧接着第二点,就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胡风认为,“这,一方面反映出了他痛切地关心到在几千年的封建力量底压迫和封建意识底麻醉下的人民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说明了他对于科学的真诚的追求终于使他接触到了意识斗争的课题。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上,这个问题底提出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控诉,几千年的封建意识第一次遇到了控诉。”[2](P332)
胡风对五四启蒙思想的继承更主要地表现在他对鲁迅的追随上。这种追随不仅仅表现在他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路的捍卫与发展上,也不仅仅表现在他以“精神界之战士”自命上,最重要的是,他继承了鲁迅的——用胡风自己的话说,是“当思想成了自己的生命机能才能算是思想”的——实事求是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深深地肉搏到了历史底核心”。其次是继承了鲁迅的特殊的“思想斗争方法”,这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本于真实的斗争要求,向着具体的斗争对象。前者是由于战斗人格底完成,后者需要对于敌情的透彻理解……真正的战斗,不能是和主观要求客观对象离开的‘思想’,非得是这两者底结合不可。”[2](P335-339)
正因为继承了鲁迅的“思想斗争方法”,所以与同时代许多人相比,胡风才能在自己的一生中,不太理会“观念形态上的闹声”,而始终坚持“实践”的精神与态度。胡风依据自己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原著的重要收获,参照现代西方哲学的“人论”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与方法,对社会生活实践主体作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明确而坚定地反对教条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笼统地把“人民”、“大众”看作是一个“善良的”、“优美的”、“坚强的、健康的”抽象概念。就胡风来说,这正是他的启蒙意识的一个认识根源。同时,胡风还主张对社会群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作辩证的分析。他从来不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抽象物,而始终认为人是“社会关系底总体”,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应该来源于被生动具体的历史条件规定着的有血肉、有性格、有命运的“个人们”。这虽然是创作论方面的一个问题,但不如此,启蒙思想在创作领域的贯彻是难以想象的。
说到“国际革命文艺传统”对胡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胡风的作家论之中。胡风在文艺评论中,始终关注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新旧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注意强调这些伟大作家怎样对待生活、怎样对待时代要求,尤其是怎样对待劳苦人民的态度,以及怎样对待将生活真实提升为艺术真实的艺术表现力,目的是要给广大的文学新军提供经验上的借鉴。关于这一点,在胡风的著述中论列颇多,无须赘述。不过,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胡风对作家(创作主作)“主观战斗精神”或“人格力量”、“思想力量”的反复强调,也正是从世界新旧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认识,这也是形成胡风文艺思想贴近现实文学创作实践的特征之所在。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哲学文化基础,其蕴含极为丰富,除马克思主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五四”启蒙学说中的生命哲学与个性主义。如胡风自述,早在20年代初,他便读到了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并且在思想上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在这本书里,厨川白村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释文学创作,把创作的动力归因于性的苦闷,认为没有精神上的苦闷(追求)也就没有创作,但创作的目的却又不是揭示这苦闷,而是为了超脱这苦闷,而且,正是人的内心个性表现欲与外在的社会强制两种力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的生活。
根据厨川白村的启示,胡风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作了批判的继承,并运用于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之中。胡风认为,厨川白村所说的:
……这个“苦闷”只能是社会学性质的东西,也就是阶级矛盾的社会生活造成的,决不只是生物学性质的东西。性的苦闷也是创作的动力,但这个性的苦闷也只能是社会学性质的东西,是阶级矛盾的社会生活造成的。各个作家和各个作家笔下的各种人物都是各种具有被自己经历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性质不同、内容不同的存在。创作的内容是根据作家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客观的东西积累起来,熔化出来的。而创作的动力是这些客观的东西引起的作家的主观要求(苦闷)。这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外到内的过程。但具体的创作过程总是从这种主观要求(苦闷)出发,不能自己的,通过发生、综合、熔化、升华的血肉实感而创造出人物形象。这是从内到外的过程。所以,厨川的理论在后一方面是对的,有积极意义的。但在前一方面就完全错了。鲁迅把它译了出来,而且作为大学教本,就是认为把他的立足点颠倒过来,把它从唯心主义改放在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可以克服文艺创作的自然主义的错误和机械论即庸俗社会学的错误,对作家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怎样结合起来这个主要问题取得健康的理解。[6](P247-248)
正是在对精神分析理论“凭着实感”的批判继承基础上,胡风对文艺的动力与属性提出了许多不同于流俗的见解,例如说伟大的作品都是“和一切社会人一样是活的、斗争的、有爱情快乐的、以及痛苦的作家”,“为了满足某种欲求而被创造的。失去了欲求,失去了爱,作品就不能够有真正的生命”[6](P223-224)。认为人是有本能活力与情欲的快乐和压抑的,文学在某种程度程度上就是作为人的作家的这种活力和欲望的外化。很显然,这种观点是带有明显的精神分析理论色彩的。但是,精神分析学说对性本能的无限夸大又是与胡风的革命思想和个人追求相矛盾的。所以胡风在后来越来越多地批判精神分析学说,将它改造成了艺术与人生的辩证论题。他认为一方面人生高于艺术,神圣的人生会促成伟大的艺术,“只有成了人生的战斗能力的东西才能够被提升为诗的表现能力而取得艺术生命”;另一方面,作家通过真诚的艺术实践可以自然地走向伟大的人生。“在现实主义作家,忠于现实如果不通过忠于艺术去实现,那不但是一句空话,而且只有害死艺术,害死作家自己的。”[7]艺术成了流灌着全人类热流和血液的人生的一分子,这就有把艺术当作作家身内的、个体化东西的意味,但又要求经由个人的人生通向社会的广大人生。这种思想与其他革命文艺家以外在观念来要求和统一作家的创作的流行理论显然是大相径庭的。胡风所强调的正是艺术对人生的升华或超越功能,是弗洛伊德文学观的另一种形式的“转喻”。
而正是通过厨川白村、弗活伊德,胡风将自己文艺思想的吸管伸进了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生命哲学之中,从而使其能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主观战斗精神”、“形象思维”等一系列建立在个体生命意识基础之上的文学命题,成为现代中国少有的重视生命感性形态的文艺理论家,并从而使其文艺思想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这,固然与胡风博览群书、学贯中西的学养与“拿来主义”的态度有关(他说:“能够丰富我们的都要”),但更内在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自己是一个诗人,对创作有着直接而丰富的生命体验,并且对“形象(的)特别敏感”。这种诗人特有的“生理——心理”结构,本来易于与生命哲学对人的感性直观的强调相共鸣——因为在生命哲学家们看来,只有感性直观是可靠的,它在对象与人的认识之间构成了一种没有中介的对应关系,对象的原始形态,只有在感性直观中才能保留它原有的面貌,提供最充分的本质显性形态,而且“直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命本身。”因此它非常合理地强调了人的生命本体与对象接触的绝对必要性,并且强调,这种接触不是一般性的接触,而是“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柏格森语)的[8],和对象相生相克的运动过程。
胡风正是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出发接受了生命哲学的观点并将之运用于文艺理论批评,指出“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血肉的现实人生,当然就是所谓感性的对象。”[3](P18)不仅如此,胡风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即现代认识论的主体性原则(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提出了“自我扩张论”,并以此作为“艺术创造底源泉”。他说:
在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里面,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然是活的感性的存在,那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底思维活动就不能够超脱感性的机能。从这里看,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底生命被作家底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底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底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艺术创造底源泉。
今天,作家要真诚地承认而且承受这个自我斗争。[3](P20)
实践证明,胡风这种对文艺创作过程的动态揭示,是非常切合于文艺创作的内部规律的,这一点构成了胡风文艺思想中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富有理论魅力的价值要素,而且也自然地成为我国经典“源泉论”的必要补充和完善。
胡风还从这种对生命感性的强调出发,提出了对生命的升华形态——“主观战斗精神”的独特认识,并以此说明“作家的主观和客观生活的关系”。胡风认为,作家要“把他底战斗精神潜入到生活对象底深的本质里面”,以百倍的热情“去肉搏客观的世界”,“深刻地认识生活对象,勇敢地征服生活对象,由这来提炼出一个人生世界,创造出一个艺术世界。”这就是说,生命的升华形态,是创造出一个艺术世界的前提——生命哲学的基本思想在胡风的创作论中得到了本质的体现。
当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论题——“主观战斗精神”与“自我扩张”的评论已经有过许多,而这并非本文论题。不过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胡风文艺思想所赖以生成并建立的哲学文化基石之一——生命哲学,它所体现的正是20世纪人类思维的最新转折,而胡风也正好在这里表现出了他的哲学意识的敏锐和先觉性。
众所周知,现代哲学的发生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尼采以一句“上帝死了”的警世名言,宣告了人类认识的新纪元的开始。在此之前的人类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代名词,以极其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自我超越的欲望,每一种形而上学理论都宣布自己是包罗万象的与人类历史共始终的永恒真理,这种一元论的形而上学往往与一体化的等级制度相适应,以至高无上的“理性”的名义从思想上对人类实行专制,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理性至上主义和关于“人”的乐观主义信念。这种形而上学直至现代生命哲学兴起才发生了崩溃与瓦解,哲学才以划时代的转折向着人自身复归。
在生命哲学那里,人类的深层心理、生理成为哲学研究的重心,作为形而下个体的人的直觉、本能等(而不是形而上的整体)受到空前的重视,生命的意义只能从最切身的生命体验中去升华,而不是通过种种先验的概念、原理去寻找,所以在生命哲学那里,抽象的共相遭到抛弃,个体的具体存在,自我等,得到高扬与开放,……正是在以生命哲学的兴起为标志的哲学转型中,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一步。
这种世界范围内兴起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也同样进入了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五四”一代在伦理方面虽然强调灵肉一致的古典和谐,但在情感趋向上,对于培根、笛卡尔、莱布尼次以至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却并不热衷,而对于卢梭、叔本华、施蒂纳、尼采、柏格森以至弗洛伊德的学说有着自然的亲近。“五四”启蒙者正是从卢梭等先哲们那里得到启发,特别强调个人的独特的感性存在和自由创造的能力,并以此对群体价值至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虽然说,“五四”启蒙者主要是用来自西方18世纪启蒙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来批判和否定中国的传统制度和伦理体系,从而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灵肉一致”的“完全的人”的理想,但与此同时,西方一些敏感的哲学家对启蒙哲学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批判,对人的悲剧性分裂的体验也深刻地影响了“五四”一代人,那种以“个人——主体”的个别性和不可重复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非理性主义思想体系,也无形中深化了“五四”一代特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人们对人的认识与反思。因此,“五四”启蒙者在宣传理性主义的“人”的思想时,却把思维的中心从“主体——客体”的关系转移到人与自身的关系,不是通过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掌握来发展人类的征服自然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而是通过自我(个别的和民族的)的“反思”来达到对自身的理解。
很显然,“五四”启蒙思想内部所存在的学说的相互混杂与矛盾也同样存在于胡风的思想之中。也就是说,“五四”思想内在的以集体性和文化的普遍性为其特征的民族主义与以个体和思维的独立性为其特征的“个体意识”之间的冲突,对“人”的悖论式的理解,个人自由与阶级解放的矛盾,如此等等,在胡风的思想中同样存在。这大概也是造成胡风的文章“晦涩难懂”的一个重要因素吧。这一因素,也导致了胡风思想的二重性:当需要他在政治上表明立场和态度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倾向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与所有的同时代人一样,将群体价值置于个体意识之上,认为“五四”时代的个性主义发展到了今天,就是一种集体主义[2](P151),只是要把“民族的进步”(在胡风那里主要是指民族的精神解放,是“改造国民性”的结果)放在“民族解放”的旁边,并且以一种时代流行的历史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释时代和历史以及各种外在的社会现象;然而,在有关“人”的论述中,特别是在研究文艺内部创作规律的过程中,胡风却又接受了20世纪哲学关于人的最新认识成果,选择了最能体现20世纪哲学成就的生命哲学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从而超越了同时代人在民粹主义、群体至上观念等深层文化心理的左右下对马克思主义理性原则和“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命题的绝对化、片面性和机械论的理解,从而使自己的文艺理论与世界哲学文化思潮相打通,并获得了一定的世界意义,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流派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分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胡风文艺思想正是因为其哲学文化基础中西合璧的复杂性,才最后呈现出了斑驳的色调与“晦涩”的外表。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这就是,包括“人论”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与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的生命哲学是胡风理论的两大基石,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则是他的文艺思想的直接源泉。
3
正是在上述哲学基础与思想渊源的决定下,胡风文艺思想形成了以下突出特点。
一、艺术属性本位论与毫不妥协的审美立场。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将文艺的政治属性与人的阶级属性绝对化的理论观点,胡风文艺思想最为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对文艺的艺术属性的本体地位与审美立场的坚持与维护。即使是在文艺的“从属论”、“工具论”甚嚣尘上统治文坛的时候,胡风也没有停止过对这种日趋狭隘与庸俗的文艺思想的质疑与批评。
从总的理论体系来说,胡风文艺思想仍然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是非常正宗的现实主义。他之所以在“从属化”、“工具论”日趋扩张的年代“不合适宜”地加以抵制,恰在他对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或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上,超越了“从属化”、“工具论”的狭隘与庸俗。他认为文艺所反映的生活,应该是“历史现实底内容和发展趋向”;文艺即使要服务于政治,那政治也不能是浅薄的“权变的政治战术的应付”。也正因为如此,胡风始终如一地忠实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真谛,始终如一地捍卫着作为现实主义艺术本质属性的真实性、典型性和形象思维等等以及艺术创作本身的特殊规律。
二、坚定的主体性观念及其对于人性的辩证理解。不同于当时颇为流行的以“阶级性”观察和描写人物的文学主张,胡风从未苟同将人的阶级属性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自始至终对人的非止于阶级属性的生命本能、文化积淀等予以特别重视与强调,在全面而辩证地理解“人性”的基础上,胡风更以对人的主体性、人体性的肯定与张扬作为自己文艺思想的核心。
在对人的本质与属性的认识上,胡风并不否认人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但他更认为“人的内容是历史底所产”,在它身上既有“昨天性的诸因素”,又有“明天性的诸因素”,世界上不存在万善的神和万恶的魔鬼,“人民”也同样如此,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存在”,文学只能以这种真实的活人作为自己的反映对象,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典型。所以胡风反对以“阶级性”观点将人物分为正面的、反面的、英雄的、中间的、落后的,而只强调各种各样的蕴含丰富的典型。
也正如此,胡风要求作家只有具备了“主观战斗精神”,才能“血肉地”突入“个人们”的人生之中,通过对“感性对象的感性活动”的把握,用自己的生命去消化他们具有鲜明性格的“个人的血肉”,从而反映出深刻的“现实的历史内容”。
胡风还从个体存在及其与社会连结的复杂性上论析了文艺创作中感性对象的复杂性,以及作家需要注意的问题。他指出:“如果对象是心理状态最复杂或精神斗争最激烈的对象,那就一定要从他的复杂性和激烈性去把握他,反映他”[3](P335),把艺术包容到具体的生活内容里去。他不认为现实中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具有典型的“阶级性”,或具有“类”高度意义上的人的能动性和丰富性的,他认为现实生活中既有精神斗争激烈的复杂对象,也不乏简单的对象,文学应根据对象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反映。
在研究胡风主体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胡风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马尔库塞有许多暗合的地方,比如他们都反对庸俗社会学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都反对将“每一个个体的主体性,他们自己的意识和无意识都趋向于被消融在阶级意识之中”,都认为“激进变革的需要必须植根于个体的主体性本身,植根于个体的主体性的智力、激情、内趋力和目的之中”,认为“这样的事实”在庸俗唯物主义那里都“被极度轻视了”[9](P334),如此等等。总而言之,胡风的主体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世界性的美学高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领悟与理解远远高出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对创作过程的独特理解与强烈的生命伦理意识。由于深受现代生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人论”的影响,再加上具有切身的创作体验,所以胡风文艺思想中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他的创作过程论及强烈的生命意识。在他那里,作家个体的感性活动在创作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他也常常使用“有血有肉”的形象生动的语言来总结那种神秘的创作实践过程,提醒现实主义作家要以生命特有的感性机能形成对于对象的活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又应该是直觉的,“非逻辑”、“非联系”、“非理性”的;在此过程中,作家要将创作中的感受力、想象力上升为一种内在的具有生命意识的感性,但同时,也要注意把握对象的“因果性”、“联系性”以及“内部世界”(精神)与“外部世界”(对象)的整体性。当然,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作家增强自己主观的判断力和融化力,也就是“主观战斗精神”中的把握力,既能够“入乎其内”,又能够“出乎其外”。这里正体现了胡风的强烈的生命伦理意识,说明胡风并未完全接受现代生命哲学的支配,在总体上还是从生命现象的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出发,将人,进而是文学归结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寻求。这也是胡风从根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证明。
收稿日期:1999-05-12
标签:胡风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文艺论文; 鲁迅论文; 封建主义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生命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