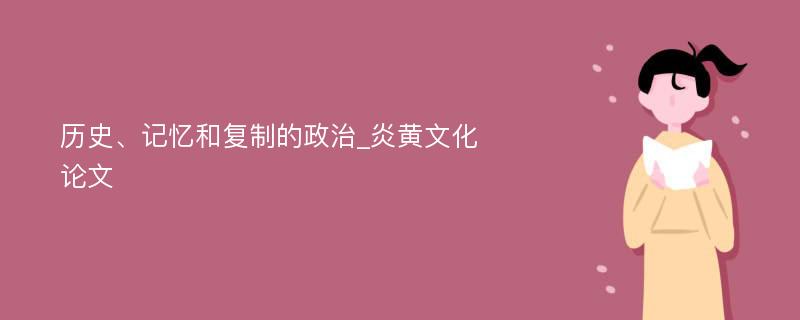
历史、记忆与再现的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政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1世纪之初重提“历史与记忆”的命题,并非旨在搅动20世纪诸多“浩劫”“大屠杀”的血色。尽管现代文明浩劫或曰“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确乎以一场又一场深刻而内在的“见证的危机”,令“历史与记忆”成为触目惊心的议题,但并非这一命题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全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冷战落幕,“短暂的20世纪”终结。于是,再一次通过对记忆的“校订”,以实现历史的“重写”,成为全球普遍而深刻的文化实践与事实。然而,在此显影的不仅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一般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后半叶,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诸多批判理论的重要论域之一,正是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我们或许可以将20世纪后半叶称为历史书写的暗箱机制大曝光。而在1917年革命后的俄国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历史书写则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建立,尝试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的意义上确立别样的历史观,其自觉地重写/改写历史的文化实践,不期然间暴露了历史书写的政治性与内在权力机制。与此同时,冷战时代的开启,尤其是在冷战对峙的前沿地带、冷战分界线的两侧,同一历史的不同甚至对立的版本,则不仅以相近的“曝光”效果黯淡了“历史”神圣的光冕,将历史揭示为特定的叙事行为,而且在两相对照中,清晰显影了历史的屏蔽功能。20世纪后半叶的另一个重要历史变迁是前殖民国家的独立建国及此后的解殖运动,在以第三世界的国别史写作改写整个世界历史格局的同时,显影了诸种历史写作的全球资本主义或曰欧洲中心之世界想象的底景。因此,当冷战终结,“不战而胜”的西方世界或曰资本主义逻辑再次主导着胜利者的历史写作,这一书写自身却必然遭到上述批判性防波堤的障碍和阻隔。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20世纪70年代,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以“历史与人民的记忆”为题直指战后西欧的主流文化策略之一,是以历史之名遮蔽、压抑人民记忆,以便想象性地消解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质询;而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之初,胜利者的历史书写,则是借重20世纪——这一革命与动荡的年代个人创伤记忆以实践历史的重写。当然,“个人是历史的人质”或“个人无法承担历史罪责”的老调,在“赦免”个人的同时,成就着审判失败者的内在逻辑。就电影——这一依旧极具大众性的文化工业而言,1987年,贝托鲁奇的好莱坞版中国故事《末代皇帝》,不期然间成了始作俑者;而1994年风靡全球的《阿甘正传》则“正式”以记忆之名开启历史书写所必需的遗忘机制。一如影片中那份特技奇观:一片飘飘洒洒、有形有影的羽毛掠过阿甘生命的天空,智商74、留着板寸头的阿甘穿越了“二战”后美国历史几乎所有的重要时刻,以其痛楚而限定的个人记忆修订或遮蔽了这段炙热的历史。继而,在记忆/历史书写的意义上凸显而出的,则是两德合并后的德国——或联系、围绕着德国的《窃听风暴》《朗读者》《帝国风暴》《柏林女人》等,以个人记忆或个人故事为新主流的重建虚构出必需却不可能的政治和解与“大团圆”。
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来说,历史与记忆的再现,呈现着更为繁复而颇具异趣的状态。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时期激变的政治文化启动路径之一,正是自觉的历史重写。无论是满怀悲情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庄严遗言“好的历史是人民写的”,还是不无犬儒意味的胡适名言“历史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或曰“历史文化反思运动”的政治批判与文化重构,无不清晰地显影着一份堪称怪诞的历史之文化政治意味的自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应对着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政治行为是以“平反昭雪”“补白”与“钩沉”为基本特征的历史重写。且不论所谓补白与钩沉的意义在于显影昔日特定历史书写的筛选与删除机制,断裂其逻辑链条以曝光出裂隙与空白,而且在于其重写过程深刻而内在地改写着历史书写的坐标与参数。首先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明确限定了历史视野及其书写框架,取代了此前的重要参数——五四时代(或被鲁迅称为“盗火者”时代)对世界上弱小民族的认同与参照、“二战”期间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及第三国际的深刻影响、1949年以降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70年代的第三世界主义①视野,进而将其纳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阶序之中;“现代化”作为“赶超”逻辑的新版本,抹除了共产主义之为愿景的世界革命想象。其次则是在倒置运甩了20世纪50年代以降中国历史书写特有的“翻案文章”之时,悄然消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逻辑及更为重要且基本的参数——阶级,尽管此处的“阶级”尤其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关于现代社会分析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而更多是在修辞意义上用以描述“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曾经,这一别样的历史叙述逻辑,不仅增补、凸显王朝历史之中/之间的农民起义之史实,而且强调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②,以显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于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重写,便成为对“再颠倒”的颠倒,历史恢复了其“本来”面目——不如说是历史叙述恢复了现代世界的主流逻辑。然而,于中国,这一有效的文化政治实践,同时建构并显影了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困境,即政党、政权的连续与政治、经济体制的断裂:前者要求意识形态的延伸以维系合法性表述,后者则缘于新的合法性需求而必须倾覆昔日的意识形态建构。于是,它直接呈现为历史书写自身的异质逻辑及其内在的冲突与叙述的碎裂,而且事实上无法确立任一版本的20世纪史的连贯叙述,尽管众所周知的是一部逻辑的、连贯的历史无疑是主流意识形态确立、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20世纪的最后20年,历与史于不期然间再度分离:若干昭然的空白或曰必须缺失的年份是某种史说成立的前提。与此同时,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所居的特定世界情势,亦强化着这份历史书写及意识形态再现的悖谬。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新时期”的开启,或者更准确地追溯,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使得中国已然置身于全球冷战结构内的后冷战政治文化状态之中;而80年代终结,西方阵营不战而胜,中国作为最后一个屹立不倒的社会主义大国,却陡然遭遇到全面的后冷战时代的冷战情势。这又一层面上的错位,则在谵妄/失语间强化了当代史叙述的破碎、悲情与犬儒。
此间,一个在诸种社会力量间颇具默契的文化策略,便是历史叙述的“蒙太奇”。通过“剪去”当代史的异质性段落,尝试绕过困境并建立新的霸权逻辑。然而,当需要剪去的不是某些特定的年份,而是当代史的主部:20世纪50~70年代(乃至40~70年代)之时,它便不仅因巨大的时间跨度、因诸多异质逻辑的横亘而呈现为叙述与文化的雾障,而且因当代史基本而重要时段的缺失,直接、间接地指涉着合法化危机。另一个或许出自多重政治潜意识驱动的书写策略则更为有趣或曰意味深长。如果说,“历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与文化政治的关键词之一,那么,此间以历史之名所指称的文化/政治实践却大都以非历史化为其主要特征。犹如五四时代寓言式历史书写的变形回声,再一次,没有年代的历史(关于历史真实的表述),成了针对历史(因果链条所编织的编年叙述)的参照与颠覆。此间,不仅是“历史在这里沉思”一度勾勒出“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而且是“寻根”式的、关于亘古依然的愚昧或注定死灭的民族寓言,令(包括当代史在内的)中国史呈现为一幅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空间图式而非时间/线性进程。于是,中国新电影的全盛期,所谓“第五代”导演的诸多重要作品都伴随着关于历史年代的有无、历史场景的具体与抽象的争端;80年代前期,这几乎成了电影的艺术权力与官方机构的文化惯例/审查制度间冲突的焦点。这事实上也成就了第五代电影导演的艺术标志与时代签名,即空间/造型对时间/叙事的压倒优势,为诸多的民俗、礼仪、服饰、器物所构筑的仪式美学成了历史或历史的“无物之阵”的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非历史化的历史书写,实践着文化双刃剑式的社会功能。若说作为五四时代的叙事主题与修辞的复沓——没有年代的历史作为真相或真理的所在,直接抗衡着有年代的历史(编年史/官方说法/谎言)——意味着一份激进变革的选择与姿态;那么,此时类似历史叙述所达成的非历史化效果同时负载着迥异的社会意图:当某种元中国史叙述事实上指向20世纪的中国,这一几乎经历了人类历史曾有过的所有革命样式的世纪,并将其涵盖在一幅不曾改变或无从改变的同质图景之中,便无疑成就着别样的、非政治化的政治实践——审判激进,告别革命。
此间,“个人”“记忆”之名下的历史书写,则作为另一个有效的策略,始终伴随着历史/当代史书写的逻辑置换与新主流建构。或许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个人”与“记忆”之名的凸显,是为了以“个人”对抗阶级/集体,以记忆对抗此时已近乎坍塌的官方说法;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以记忆之名将个人剥离于历史/刚刚逝去的现实。如果说,以记忆之名去规避记忆、历史的沉重与质询,是大时代——尤其是斑驳酷烈的大时代——之后寻常的社会心态,那么,或许需要提及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个人”只是一个想象性的集体称谓,“记忆”则更近似于白日梦式的社会心理补偿。个人成了一块历史的飞地,成了或需救赎、有待书写的白板。因此,曰“伤痕”、曰“反思”、曰“第四代”的文化书写,以记忆之名成功地启动了遗忘机制,令新的主流逻辑及历史叙述得以在尴尬间渐次起步。如果说,这份记忆的遗忘,只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政治潜意识的无心之果;那么,1987年于中国摄制的好莱坞/欧洲历史巨制《末代皇帝》,则同样在不期然间为中国电影(也许不只是电影)充当了个人、记忆、历史的主流书写的示范之作。在导演贝托鲁奇的世界里,个人,即使尊为帝王,仍只是历史飓风间的蒲草;他为历史的暴力绑架、羁押,只能或犬儒、或执拗……实则无谓地穿行于大时代的历史空间;末代皇帝的登基大典上,那如玩偶、似傀儡的三岁小皇帝溥仪(或日后的“满洲国”皇帝),无疑成了贝托鲁奇版的个人境遇的最佳象喻。或许贝托鲁奇叙事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其历史场景始终锁定于个人——这几乎是现代西方的叙事惯例,而在于个人。因为历史只是变动不居却无关宏旨的背景片,用以出演“个人”的故事,如以“儿子”的身份恋母、弑父,却最终为了皈依、获取“父之名”的故事。如精神分析理论最基本的症结不仅是高度预设,而且是非历史或反历史,贝托鲁奇的历史叙事所完成的,正是个人心理悲剧中的历史弥散。因此,尽管《末代皇帝》号称出自个人记忆——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后者无疑是一部具有鲜明政治性的作品,从某一特定角度记述并见证着历史),但在贝托鲁奇的影片中,无论是清廷大典还是红卫兵“忠字舞”这类可谓宏大且逼真细腻的历史场景,都不仅与中国无涉,亦与历史无关,凸显出的只是又一个贝托鲁奇式的“个人”:一个辗转在父名的威压之下,间或为恶母所胎化的儿子/儿皇帝。因此,无论是20世纪之交欧洲的风云激变(《1900》),或是近现代金戈铁马的中国(《末代皇帝》),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陆战场(《随波逐流的人》),或是20世纪60年代“最后一次欧洲革命”的中心巴黎(《戏梦人生》),对于贝托鲁奇的“个人”和他自讼/自辩、侵犯/孱弱的故事,历史时空因无法为其提供救赎而全无差异。
当然,与其说是中国电影人从贝托鲁奇那里学会了主流电影的叙事技巧与策略,不如说是贝托鲁奇的“中国故事”启迪了中国电影人如何在叙事中逃逸历史。因为彼时彼地,历史之名恰是现实政治的在场形态之一。或许只是偶然,正是《末代皇帝》于中国摄制的1987年,张艺谋执导的处女作《红高粱》在彼时的西柏林电影节上获大奖,标志着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引领的中国新电影(或曰中国电影新浪潮)的峰值与终结。也正是在这部电影中,故事的前半部发生在一处法外的、时间之外亦即历史之外的空间之中,却以一句举重若轻的旁白“日本鬼子说来就来,转眼公路修到了青杀口”,将具有反叛意味的“没有年代的历史”接续到“有年代的历史”中,从而标志着一个激进批判的、(反)历史书写年代的结束。而在20世纪90年代,不仅赢得了世界性声誉,而且取得了票房业绩的中国电影,如《霸王别姬》《活着》,无例外地选取了贝托鲁齐式的书写:故事的展开,人物或一个家庭命运的书写贯穿在现当代中国的历史之中,但这历史只是一幅幅背景片,除却狰狞酷烈、血雨腥风,其历史变迁几乎不提供任何差异或意义的表述。即使暂时搁置90年代前期围绕着中国及中国文化事件的后冷战的冷战情境,暂时搁置欧美世界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本质化想象或干脆说无知,在《霸王别姬》或《活着》的影像世界中,历史始终是人(大写的或小写的)的对立物。
在此,一个有趣的例外却最终印证了这份非历史化的历史书写的文化政治逻辑,那便是在世纪之交的近20年中,以其署名标志着中国电影艺术的贾樟柯的影片序列。在确立了其国际声望及地位的代表作《站台》当中,贾樟柯奠定了他标志性的关于个人/命运的书写方式,即小人物如蒲草般柔韧顽强地生存于飓风掠过的时代、穿行于激变中的社会空间的叙事。其作品曾因中国社会底层的显影,因其人物的边缘身份及电影作者的认同而呈现迥异的面目及魅力。然而,一旦贾樟柯的电影与叙事再度遭遇历史,其作为例外便再度为惯例所捕获。21世纪之初贾樟柯相继的两部作品《二十四城记》和《海上传奇》,均采用了准纪录片或曰纪录风格的形态,但这一次他的“个人”(小人物或大人物)孑然一身穿行历史的叙事,却再度成就了以非历史化的方式加盟主流历史书写的效果。《二十四城记》中,一个国营大厂几代工人的故事,事实上记述了共和国史的一个侧面,但其中无论是50年代,那相对于国营大厂工人来说“火红的年代”,或是80年代中国社会等级全面重组的岁月,还是90年代的激变、工人阶级的整体坠落的时段,或是21世纪劳动与资本的全面异化,劳动者的社会隐形与匿名的现实,在影片中,似乎都只是无差异的宿命性力量。而另一部“城记”《海上传奇》所负载的20世纪中国现代史则呈现了更为清晰、丰富的文化政治症候。在这部准纪录片里,在解放军攻占上海的前夕,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特刑庭”宣判死刑的地下共产党人王孝和的故事,与国民党军队千军万马溃退台湾时一个军人家庭的遭遇平行于同一命运与意义的层面上,在不期然间获得国家最高领袖接见的纱厂女工黄宝妹的叙述与女演员韦唯在拍摄电影《小城之春》时一段感情遭遇,亦无任何或可言说的差异。于是,白驹过隙、苍云白狗,一切只是岁月沧桑,造化弄人罢了。尽管略强于犬儒主义的睥睨嗤笑,但朝向无差异、抽象个人的认同和同情,成了对历史暴力记忆的埋葬与死者的二度死亡。然而,在此显现的不仅是所谓后现代历史的扁平化,而且是20世纪历史尤其是其中的冷战历史之纵深感的消失,自觉不自觉地抹去了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为壮阔的一次全球性的乌托邦实践,一次寻找资本主义之外的别样可能的尝试,抹去了造就这段极端特异的历史的苦难以及这一历史自身所制造的苦难。至此,一如全球及欧洲艺术电影,中国艺术电影曾携带或预期携带的社会批判性已濒于耗竭,文化精英的书写已不再根本有别于政治与经济精英们的主流选择,而与大众文化价值及非/反历史表述渐次趋同。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最重要且基本的事实,便是大众文化工业与大众传媒接替昔日国家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功能角色。其作为因危机与禁止而陡然真空的意识形态机器之替代品,同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仅就叙事艺术与大众视觉文化而言,则是电视剧取代电影开始充当大众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之发声器官。其经历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狂欢进发,“分享艰难”的力度与暧昧,“重写红色经典”的芜杂与尴尬之后,电视剧在多重历史叙述/历史故事中,显现了它穿越话语雾障、重塑主流价值的角色意义。固然,古装历史剧尤其是清宫剧的滥觞,如《雍正王朝》,标志着叙事主体的位置、中国的自我想象与象征性的性别角色的转移;《激情燃烧的岁月》则以“从上世纪下载激情”的开启,加入了回收、改写、重组当代史的文化进程,成为新文化霸权机制的确立尝试与成功试运行。历经新英雄传奇《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谍战片狂潮《暗算》《潜伏》,家庭情节剧《闯关东》《沙漠母亲》等,辅之以新军旅故事《士兵突击》,极为成功有力地助推着新的主流价值与国家认同的达成。当新的历史重返与切入路径终于显影于中国电影/大银幕之上时,这一事实标志着新的政治经济动力推动下的霸权机制的正式确立。因为,就通俗叙事艺术而言,若说电视剧是今日更为真切有效的大众文化典型的话,那么,电影尤其是大制作之A级片,则仍然是大众文化的别一层面上主流价值、霸权机制直观呈现的窗口。或者说就文化霸权机制而言,电视剧和类似于电影黄金时代的B级片,更像是一处多重社会力量/言说主体博弈或曰谈判并妥协的空间,而电影A级片则更像是获取了某种共识的霸权表述得以自我显影、言说印证的场域。因此,始自2003年《英雄》延伸至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古装大片序列,以华美的形态表明,在历史叙述之中,统治的王位再度安放在奴隶的脚蹬之上——尽管对权力的绝对崇拜与追逐和当权者地位的岌岌可危,共同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悖谬表述与新主流确立过程中的文化政治吊诡。
作为社会与文化的节点,2007年的一部战争片,或曰现当代史的电影——《集结号》——重装登场,不仅票房完胜,而且获得普遍的由衷认可,标志着主流文化对历史叙述或是政治文化困境的突围,以视觉、言说、书写之主体置换的完成,实现并证明了新文化霸权终于获得了曲折(尽管仍不甚稳固)的确立。在影片《集结号》中,个人再度与历史相遇并相对。有情有义的前九连连长谷子地(张涵予饰)独自直面着历史的巨轮,顽强固执、几近偏执地向历史索要着个人的姓名/位置、记忆的权力;他面对着“无名烈士”墓碑的执念“爹妈都给起了名儿了,怎么都成了没名儿的孩子了?”看似一次20世纪80年代历史文化反思命题的重现。为此,导演冯小刚大胆地运用了先锋、实验电影的镜头语言——让谷子地在夜色、火光中转身望向镜头。令人物直接望向影院中的观众,片刻间撕裂了电影叙境的闭锁,使观众犹如击穿历史时空与暮霭的阻隔,遭遇了历史中的牺牲者与蒙难者的质询。但其后,经由电影奇迹的实现,谷子地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他重获了九连的番号,索还了“历史中的失踪者”的姓名,为他们争回了应得的荣誉与位置。有趣的是,在影片中,这一电影奇迹的实现成了对其文化命题的有效消解;个人姓名/位置的失而复得,正是为了再度修复历史叙述的连贯与意义。于是,影片中唯一复沓重现的段落正是九连战士奔赴狙击阵地的夜晚,即谷子地望向摄影机镜头的场景,但当剧情完满收束,这一段落及镜头再度闪回,略事延宕的镜头长度却逆转或曰平复了视觉与叙事语义:透过夜色与历史望向我们/观众的谷子地再度转身跟上了步入画面纵深的队伍,渐行渐远,隐没在夜色亦即历史的深处。对历史的质询最终复归于历史的重建,以记忆之名向历史索还个人的姓名,只为了再度供奉给历史;但犹如影片循环往复的片头、片尾设置,当故事完成了它的“大团圆”,历史亦已完成了悄然间的置换;复归的历史已不复是故事开启时的历史。曾经的历史,标志着断裂,标志着一个完全异质性的历史时段的开启,于是,其中的“无名烈士”指称着“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而用以置换的历史,则意味着结束历史唯物主义及阶级论观点中的世界想象,在民族国家史的意义上,将死者呈现为蒙难者;而为死者讨还姓名与历史位置,则意指在现代中国曲折的现代化进程的叙述中为其重新赋予价值与意义,并将其再度还原为无名。新的、曰九连的墓碑事实上成为新的无名烈士纪念碑,只是这一次,它准确地成为奠基并标志民族国家历史的基石和起点。
《集结号》作为新主流价值确立的标志,不仅在于它在电影市场上取得了久违的全面成功;更在于它不期然成了新霸权叙述的一个象喻,即成功地借重并转化了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反思与批判的主题与动力,同时成功地吸纳并化解了90年代彼此对立的批判性叙述:成功地吸纳了所谓“自由派”的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拒绝与否定,同时挪用了所谓“新左派”关于50~7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成就的辩护性言说,在百年中国千回百转的现代化历程的意义上,回收当代史的重要段落,重建20世纪中国史的同质性的、连贯的历史叙述。
或许可以说,《集结号》的空前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成了2008年中国奥运年的边鼓序曲;那么同一年,自全球金融帝国心脏进发、陡然袭向欧美世界,进而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沼的金融海啸,则在巨幅低迷的底景上凸显并明确了一个新的世界议题,中国崛起。这一以GDP的增长速率、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排名位置、以全球奢侈品消费、全球豪华旅游标志的经济奇迹与资本主义活力进发,在开始改变乃至重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同时,改写着社会文化、认同政治与历史书写的参数。如果说,21世纪最初10年的世界变局开启了一个“后冷战之后”(after post-cold war)的时代,那么,凸显的国家地位,无疑有力地强化了在现代化逻辑中重获连续、连贯性的中国历史叙述,因此将中国文化主体议题推至前景之中。然而,也正是在这幅因新主流的确立而在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文化中涌动的现当代中国历史表象,却再度于主体与主体位置的再现中彰显了依旧绵延甚或加剧的文化困境与社会症候。
就中国文化主体的自我指认与自我言说而言,其最为突出的问题始终是一份强烈的自我意识及价值与意义的中空状态。笔者曾在旧文中谈及,现代中国文化的起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与口号——反帝、反封建——已然建构着这份主体中空。因为反帝之为文化命题,内在地呼唤着民族/本土文化的抵抗;但反封的命题则以决绝的姿态,要求断裂前现代文化的绵延、传承,渴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凤凰涅槃——于焚毁后重生少年中国。于是,在现代中国文化内部,一边是深刻的文化的自我流放,一边是鲜明的现代主体之我/他结构:以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现代科技为他者,以历史裂谷此岸的重生、稚嫩、空白为自我,他者之镜中映照出的未来图景,只能是西化、现代化之路。如果我们可以暂时搁置对欧美之现代/资本主义的勾勒:在其起点处,资本主义已然呈现为一次全球化进程,不仅开篇伊始,它便以已知的整个世界为其资源、劳动力及市场版图,而且以直接的战争、暴力劫掠、绑架整个世界加入其现代历史进程;那么,20世纪中国史的意义正在于复制西方逻辑的愿望并不导向任何成功复制的现实,现代历史的旋转木马拒绝上演同样的剧目。因为,尽管现代文化设定了以他人之眼观自我之身,故而丑陋的“中国文化”必须彻底摒弃;但美丽他者毕竟同时是狰狞敌手,且现代中国文化几乎在起点处,便意识西化之路并非通衢坦途。这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革命”之于中国的示范与启示意义。这也便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的内在动因与由来,这也便是导向1949年中国社会巨变的历史线索。换言之,即使以曲折的现代化道路为主脉,20世纪中国的历史所包含的诸多充满张力、遍布矛盾、裂隙的决定性时刻,已然在创造着不同于现代欧美的社会逻辑、文化自我与主体位置,一份具有充分差异性的历史记忆。因此,21世纪之初,于后冷战之后、中国崛起的议题中再度显影的中国文化自我的中空状态,并非五四文化裂谷于历史苍穹下再度横移,而是世纪之交又一次文化建构与意识形态实践的结果。
再次反观具有标志性的大众文化文本的《集结号》不难发现,叙事所完成的历史参数与逻辑的成功置换,同时是一次历史主体的自我抹除过程(或曰这一已经完成的自我抹除过程的大众文化显影)。仅就电影而言,冯小刚的最大成就,似乎是复活了50~70年代中国电影最具活力与社会感召力的叙事样式,革命战争题材;而重新激活这一沉寂已久的电影样式的直接路径,便是为其重装了美片《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及韩剧《太极旗飘扬》式场面调度、剪辑速度与战争奇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导演(与编剧刘恒)设置了情节中必需的桥段与逆转,令故事中九连不仅换用了其敌手(国民党军队)的美式军用装备,而且换上了其敌手的德式军装。同时,“兄弟”称谓取代了“同志”或“战友”,勇武、草莽、义薄云天的连长、军事指挥官的绝对主角取代了循循善诱、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指导员、政治指挥官形象。然而,当解放战争或曰1947~1949年的全面内战中的解放军/共产党军人以后冷战时代国际化(职业)军人的形象出现在中国银幕上之时,这场战争的历史,这场战争所标志的历史,这场战争所开启的历史,也同时悄然地被抽空或置换。当《集结号》成功地获取了国际化也曾是冷战彼端之战争片的奇观、节奏与魅力时,这场战争历史的差异性因素也就蒸发了。在历史的语境中,至少是在昔日主导性的历史叙述中,这不仅是一场现代文明史上司空见惯的惨烈内战,而且是一场中国未来之路的大对决;不仅是一场军事实力及背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实力的角逐,而且是一场民心向背之战,一场以弱胜强之战。在历史视阈中,令共产党政权、共产党军队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首先是通过土地改革所实现的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农村动员,是通过军队政治化——“党指挥枪”、“支部建到连上”,作为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前提的军队扫盲,然而,这一切在《集结号》的剧情里踪迹全无。与此相对照,九连故事的外在特征正是全无政治色彩与历史差异的军旅兄弟情,是指导员的或粗暴或无能,是官兵们勇武与文盲状态。于是,《集结号》成功且感人的故事悄然消解了镌有鲜明的冷战记忆的历史中政治主体,成就了记忆的改写与历史的重构。
然而,20世纪历史叙述中政治主体的自我抹除,势必同时意味着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差异性的抹除,意味着对其文化自我建构过程的否认,进而再度显影为一个新的主体中空化过程。其突出的例证,不只是历史大片(《英雄》到《无极》)中强权膜拜之外的叙事逻辑的苍白孱弱,不只是古典重述(《赵氏孤儿》)中故事与人物行为逻辑的不知所云与匪夷所思,更是自觉的、现代中国历史叙述中的主体缺席与言说困境。其中两部尝试向世界讲述南京大屠杀之历史记忆的大片《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以其惊人相像的叙事选择凸显了这一文化症候。对于这段中国现代史中最为惨烈的历史事件,导演陆川与张艺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段历史中的他者充当了叙事/视觉与意义的主体。前者选取了攻占南京的侵华日军的青年军官作为叙事视点的依据,后者则以一个美国殡葬人充当故事的主角。如果说,必须借重他人之眼方能一窥自我记忆的深处,是文化之内在流放的寻常表征的话,那么两部影片所设置的作为民族自我指称的中国军人形象,却再度不约而同地“准确地”在影片情节的三分之一处消失,便成为一处意味深长的文化困境之显影。一如在《南京!南京!》中,中国军人陆剑雄原本设计为影片的双重主人公之一,却苦于无法为其获取可信的叙事逻辑而终遭放弃;《金陵十三钗》中更为完满与谨慎的叙述,却因将故事空间设定在一座为红十字标志所铺陈的教堂之中,因几乎所有关键性的时刻都透过教堂的圆形彩镶玻璃窗(宗教建筑所谓的上帝之眼)而看到与被看,因而不仅直接显影了中国主体的缺席,甚至成就了南京大屠杀之特定历史的叙事/视觉蒸发。
固然,再现的政治不仅联系着历史与记忆,但21世纪之初,它的确成为再现政治中极为突出的命题。于今日中国,历史与记忆的命题不仅关乎过去,而且联系着当下,指涉着未来。毕竟,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且被压抑者从未回归。
注释:
①有趣之处在于,昔日鲁迅所谓“弱小民族”——东欧,正是以欧洲为世界版图之时,所谓“第三世界”之所在。
②毛泽东1944年1月9日致扬绍萱、齐燕铭信。原文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圃,所以值得庆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2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