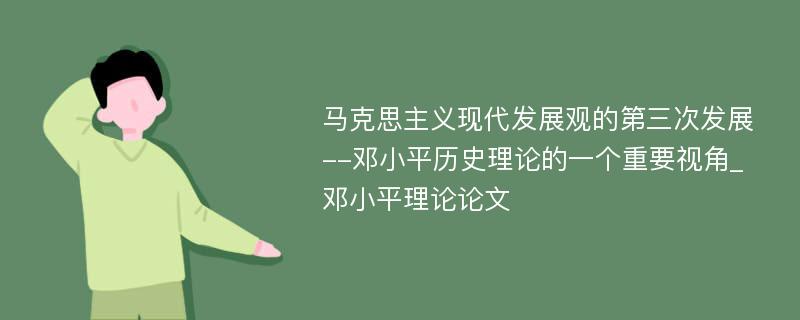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第三次开拓——关于邓小平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一个重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科学体系中,有一个关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重要理论部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倾向作分析时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卓越的、但是不完整的和试验性的理论中,有些空白已被发现和弥补,但他们分析中某些最有益的部分也被任其从视野中消失。”〔1〕“这种最有益的部分”,就是关于现代工业生产力对人类文明的伟大改造作用和由于这一伟大改造作用而引起人们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相互结构、思维方式巨大变迁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发展理论。〔2 〕这一理论的第一开拓者当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第二次开拓的是列宁,作出第三次重要开拓,使20世纪的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发生历史联系且结出丰硕实践成果的,是邓小平。关于现代发展、尤其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发展的考察,是邓小平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视野。邓小平的现代发展理论是他的全部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理解邓小平的现代发展理论,是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关键,是真正解放思想、领悟邓小平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一个关键。
一
在20世纪多数时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中,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关于现代工业生产力对于人类文明伟大改造作用的理论在视野中消失的现象密切相关,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过多地把理论注意力投注于财产所有关系以及由此而发生的阶级关系,以此来涵盖对一切社会现象的观察,由此出发作出关于一切社会运动的说明。这样,现代发展问题、世界的现代化进程问题就被排斥在视野之外,或者被笼罩在资本主义的阴影之中。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现代发展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重新收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之中,并把这一理论部门从用“财产——阶级关系”模式说明一切的思维框架中超脱出来,使我们从许许多多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中解放出来,从那种脱离实际、内容空泛但代价惨重的理论逻辑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思想方式上的一种突破。
指出这一点,并非是说邓小平的这种理论贡献仅是为了避免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而作出的一种逻辑推演。问题的实质是,现代发展,工业化生产力对于现代社会文明的改造作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是一种世界的潮流。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进程,它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引起传统的农业社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大转变,因而也是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在历史理论中这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范畴。
早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现代工业生产力对人类文明的巨大改造作用,并由此而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他们明确论证了存在着一个由蒸汽动力和机器使用引起的工业生产的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现代”时期。这个现代时期是从十六世纪以来世界逐步进入的“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个“现代”时期以大工业及其创造的世界市场为基本特征,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并实现日益广泛的和日益细密的分工,引起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其中包括从私有制到“现代私有制”,从中世纪手工业者到“现代工人”,从“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到“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从中世纪国家到“现代国家”等等。〔3〕同时, 他们也关注到当时非工业国家的现代发展进程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的论述,至今仍被现代化论者们反复引用。关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当时非工业国家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其双重历史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关于这一使命的理论,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获得很充分的发挥;但关于第二个使命的理论,后来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在19世纪,正是“建设性使命”的历史力量才使“破坏性使命”得以施其暴虐,真可谓历史真理在罪恶的世俗中行走。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正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强大力量推动着世界的现代进程,当然,这一进程在当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血腥罪恶。关于世界的现代发展,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测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的现代发展的观察,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第一次开拓。
当然,我们也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理论注意力的集中点有所转移。他们过高估计了19世纪中期西欧现代发展的成熟程度,对与这一发展相伴随的西欧资本主义的扩张势力估计不足,因而对现代社会走向的关注过快地集中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崩溃和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上。尽管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对非工业化地带的现代发展问题仍然十分关注,但事实上,这一理论视点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到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以后相当长的一个年代里,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理论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稍后则进一步集中在如何利用战争危机发起革命,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在此期间,列宁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考察中,对大工业的社会改造作用、特别是对落后的俄国社会的改造作用作了充分而宝贵的分析。罗莎·卢森堡对非工业地区将被迫采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工业化的分析,〔5 〕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不合理的体系变成合理的组织”的分析,〔6 〕也是这段时期现代发展问题上的思考成果。但其间最主要的成果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提出,俄国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方面,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7〕因而,“俄国人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 但是为了善于做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但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整个时代”。〔8〕而关于苏维埃政治体制, 他的评价是:“国家机构的一般情况:坏极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9〕俄国象“汪洋大海”一样存在的小生产势力使苏维埃政权陷入前资本主义力量的“包围”之中,社会主义“被资末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10〕所以,他称当时俄罗斯为“野蛮的俄罗斯”,认为“为了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尽快实现现代发展,就必须“更快地仿效西方主义”,甚至为此而“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11〕。基于这一观察,列宁果断地推进了新经济政策的试验,并且取得了公认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成就。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第二次开拓。
列宁关于现代发展的思考有一个突出特点,即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落后的俄国如何实现现代发展的问题。但列宁的基本思路是“利用资本主义”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工业物质基础,是用资本主义的“砖头”来构建社会主义的“大厦”。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难点,即在列宁的思路中,现代发展的“砖头”从总体上说还是资本主义的,只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因而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的联系是策略层面上的一种“利用”,是具体手段层面上一种联系,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这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一旦经济状况好转,就使现代发展问题立即从理论视野中淡去,甚至被插上资本主义标签而逐出。在实践上则导致对现代发展方针的放弃,如后来的苏联所做的那样,不是用现代方式,而是用落后国家特有的传统国家手段,搞了一个让人民勒紧裤带和剥夺农民的工业化,并酿就了后来发生的“俄国灾难”,但一度却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模式的“定尊”。第二个后果是当现代发展问题一提到议事日程,就面对姓“资”姓“社”问题争论的困扰。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8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讲,“在改革派(指中国在三中全会后坚持改革开放的人——引者按)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失败,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使‘封建主义的残余’而不是资本主义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因而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客观经济规律’要求一定程度上的资本主义。至于他们所提倡的资本主义手段与他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目的是否一致这个问题,改革派在多数情况下却缄口默言,否则,他们就很可能会陷入窘境。”接着他预言:“在一个至今依然以社会主义国家自居的国家的经济生活里,随着资本主义的方式和实践日益突出显眼,上述问题就会象一个幽灵一样越发困扰着后毛泽东时代。”〔12〕迈斯纳的“预言”后来还真有点“应验”的迹象,尽管迈斯纳自己事实上更极端地运用着这样一个错误的逻辑: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资本主义化”。
必须解决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的逻辑联系问题,必须明确现代发展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理论课题。尤其是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大国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现代发展成为国家存亡、民族存亡、社会主义制度存亡的关键,这个理论课题的解决就显得特别紧迫。这个历史性课题的解决正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第三次开拓的一个关键点。历史已经证明,抓住这一关键,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第三次成功开拓的中心人物是邓小平。
二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如果说毛泽东全部思维的意识中心是革命,是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那么邓小平全部思维的意识中心是现代化,是中国的现代发展。他认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13〕“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极其朴实但却包涵着巨大的历史份量,因而在20世纪,谁无视发展这个道理,就意味着谁放弃生存权。
但是,在邓小平推进中国的现代发展、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战略的几乎每个重要关头,都遇到姓“资”姓“社”问题争论的纠缠。邓小平的伟大恰恰就在于这些纠缠丝毫无损于他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决心,既往的经验、书本上的结论、空洞的但又代价惨重的意识形态争论绝不能成为束缚他手脚的绳索。他毫不犹豫地从书本中、从既往经验概括中走了出来,走到当代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当中,大胆地把现代发展,把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纳入社会主义的含义之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新阶段。在邓小平的理论中,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在逻辑上有着必然的统一。同时在实践中完成了成就辉煌的结合。围绕这一主题,邓小平在三个方面作了开拓性的理论努力。
其一,邓小平明确宣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在当代世界,“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象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14〕邓小平的这些结论显然是以20世纪现代发展的新的事实和新的规律为基础的。这个新的规律是当代的现代发展是取多种模式的,是可以在不同制度依托下实现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现代发展意味着以西欧工业化模式为典范的进程,非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发展道路事实上就意味着“西方化”、“欧洲化”。这是一种原发型的现代发展类型。20世纪的现代发展所走的是和这种原发型完全不同的多种模式的道路。西方社会学的一些学者(比如帕森斯)认为非工业化国家必须引进和输入“异质”的西方文明,并把它转化成自身的文明要素,才能实现现代发展。这种“他化”的过程,在19世纪表现为“美国化”。据此,他们提出了“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的公式。这种公式对于20世纪的现代发展进程来说是极为武断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历史宿命论,或者说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霸权主义。英国学者阿布拉姆斯批评帕森斯说,“他把美国视为特殊的现代化的体现者,视之为其他国家都要越来越趋近于它的领导国家,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他的一个先入为主的理论信念……而不是根据在美国实际发生过的变化的趋向所作的历史论证,更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来证明现代化的效益优势只能通过它归之为美国特有的那种结构和文化特性才能实现。在作这种论证时,帕森斯岂不正是堕入了最坏的那种反历史的历史命定论了吗?”〔15〕正是基于对20世纪世界生活新特点的科学把握,邓小平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16〕在这个新的世界大背景下,原发型现代发展类型的特点已成过去,现代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和“西方化”的命定式的联系已被否定。因而,毫无疑义必须走“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邓小平对在19世纪发展背景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开拓。
其二,邓小平明确把现代发展范畴和“财产——阶级关系”方面的范畴、具有意识形态对立含义的各种社会范畴区分开来,澄清了现代发展问题上意识形态争论的迷雾,从而为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的联系消除了主要的、也是最坚固的障碍。如果说对现代发展和“西方化”的命定式关联的否定还是建立在对20世纪经验事实作归纳的基础上的话,明确现代发展范畴和具有意识形态对立含义的诸社会范畴的区分,则在更基本的层次上铺设了社会主义和现代发展的通道。的确,在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理论家的著作里,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市场经济,因而与此相联系的一切社会体制和社会运行规则都不存在,比如具有强制意义的服从分工、包含个人利益机制的责任制管理、技术专家在生产活动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对资本的经营活动而引起的收入等等。这一切因为曾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存在而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物。然而这一切正是现代发展的重要内涵。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和商品货币关系高度发达的市场化,正是现代发展的两根最重要的支柱。一般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对工业化尚可兼容,而对市场化则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拒斥。然而,舍弃了这两根支柱中的任何一根,都意味着舍弃相关的另外一根。事实证明,试图舍弃市场化而追求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达到的工业化,等于是采用传统社会中的国家力量的手段,通过剥夺农民,建立一个很少实惠的工业化“空中楼阁”。所以,要工业化,就必须要市场化,现代发展是一个具有独立的和完整的规定性的整体性范畴,不能任意肢解。但由于市场化问题长时间里一直笼罩在意识形态对立的迷雾中,所以,现代发展也就难以显示其作为独立社会范畴的面目。
针对上述问题,当一些人仍然书生气十足地为市场经济姓“资”姓“社”而争论不休的的候,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有勇气,作出了一个石破天惊式的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7〕这个理论阀门一打开,就把长期以来云障雾绕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联系沟通了。以此来观察中国的现代发展,就不难理解改革开放的各种举措的合理性。与这种论证模式相通,还有经济特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有自己的经济特区;证券、股市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证券股市;现代经济和管理制度与方法不等于资本主义,同样也属于社会主义;高新技术不专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应该有高新技术,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富裕起来不等于就是搞了资本主义。如此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现代发展不专属于资本主义,同样也属于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应该有更高更优越的现代发展。这种不专属于资本主义,同样也应该属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立的规定性的社会范畴。这一范畴的核心层是现代工业化的生产力,同时也包括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外缘层的各种社会规范、行为规则、体制模式乃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毫不奇怪,这一范畴在外缘层上和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外缘层有时有交叉重叠,但这并不排斥现代发展作为独立的社会范畴的存在。
同时,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重要支柱的现代发展,不仅是具有独立规定性的社会范畴,而且也是社会进步序列中具有独立规定性的历史范畴,并呈现出历史进程中的不可超越性。如果说社会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阶段可以跨越,但以工业化文明为特征的现代时期不可跨越。所以,在落后的农业社会背景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无可回避地还必须实现本国社会的现代发展,创造自己的工业文明。以邓小平理论为旗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光辉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和现代发展的联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其三,邓小平以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指出,在中国,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因而应该而且可能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议事日程上,顺理成章地肯定了现代发展这一历史课题的优先性。同时,邓小平又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发生的新事实和新的特点,作出了现在不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科学判断。这一科学判断指明,争取和平条件下的现代发展毫无疑义是党和国家工作的主题。这两个论断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即从革命时期以“财产——阶级关系”模式为意识中心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转向以建设、发展为意识中心的思维方式,从而保证了现代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政策优先性。
这里必须指出,邓小平理论所引起的上述思想解放和思维方式的转换,并非仅仅是,甚至主要还不是政策层面上的保障性需要,更本质的原因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所必须有的对社会不同时期的不同运动规则的适应性。在全部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常态的(也是相对短暂的)变革性时期和经常性的发展时期是交替出现的。在非常态的变革时期,社会的运动规则常常表现出阶级政治关系、财产经济关系的变动走在生产力发展的前面,人们对于“财产——阶级关系”的优先关注及其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政策中的优先地位,是人们的思维对于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但是,在社会的经常性的发展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则处于优先地位,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适应的性质、有时甚至表现出滞后的状态。如果让社会变革时期的革命性的思维方式成为一种定势,坚持把“财产——阶级关系”为意识中心和观察模式的思维方式普遍化,坚持以这种观察模式的思维方式普遍化,坚持以这种观察模式来观察一切时期的一切社会现象,从而,以不断地发起“阶级斗争”、发起“革命”作为自己的政策支点,那就必定滑入唯意志论的泥潭,造成整个社会的灾难。所以,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讲,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也就是说邓小平的理论实际上开启了人们整个思维方式转换的契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观察模式,并大大拓宽了观察视野,从而使人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境界。
上述三个方面的开拓,可以简略地表述为三个区分,即原发型现代发展和20世纪现代发展潮流的区分;以生产力为核心层延及社会体制、社会运作方式、生活方式和观念、人口素质等外缘层的现代发展范畴,和以生产关系为核心层的社会制度范畴的区分;经常性发展时期的社会运行规则和非常态变革时期社会运行规则的区分。由于这三个区分,邓小平开拓了马克思现代发展理论第三防段,从而建立起现代发展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理论,建立起适应20世纪现代发展的全球性趋势的开放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发展战略和一系列重要方针。
三
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第三次开拓,同时又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当邓小平把现代发展从简单“财产——阶级关系”模式中区分出来,从姓“资”姓“社”争论中解放出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当然需要有一个新的水平。在这里,我们从与现代发展的联系这一角度来观察,先看看邓小平认为什么不是他所要搞的社会主义。
其一,中国搞的社会主义不是几十年前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结论中所说的那样。他说:“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象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18〕换句话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所要求的社会主义。
其二,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苏联搞了一个半军事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但后来崩溃了,所以邓小平认为,“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二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19〕
其三,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不是“四人帮”所鼓吹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对“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深恶痛绝,在许多场合下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20〕
其四,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也不等同于毛泽东思维框架中的社会主义。1978年,邓小平提请全党同志深思:“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21〕显然,邓小平这里所指的“很长的历史时期”,是指三中全会以前的二、三十年,这个时期中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中没有生产力发展的地位,没有人民生活富裕的地位。邓小平认为,这样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其五,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也不是邓小平自己在“中苏论战”中所说的那些“空话”。他在回忆这场论战的谈话中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2〕对于这场争论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23〕在邓小平看来,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都不过是“空话”,而“空话”决不能使社会主义巩固起来,而只能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接受贫困这一惨重的代价。
从邓小平认为什么不是他所要搞的社会主义,可以看出他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问题有一个新的思维框架。他所不赞成或反对的前述几种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或者是死搬书本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或者是附加了许多传统小生产社会因素的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或者是作为某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追求的社会主义。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共同点,即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某种意识形态原则的产物,仅仅把社会主义放在简单的“财产——阶级关系”框架中观察和认识,使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变成某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悬设。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大胆否定了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模式,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把握从某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悬设中走出来,走到活生生的观实生活实际之中,走到20世纪现代文明发展的潮流之中。
毫无疑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崇高的价值理想,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宣布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但是,这种崇高的价值理想,不是某种本质论命题中的悬设,而是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科学认识的结论。社会主义者努力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是为了某种价值观念上的满足,而是服务于现实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服务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服务于社会的文明进步。1988年5月18 日邓小平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说,“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24〕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和乌干达共和国总统莫塞韦尼谈话中说, “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在这方面,你们做对了。”〔25〕恐怕不会有人根据以上这些谈话认为邓小平不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为什么邓小平建议这些非洲国家领导人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因为在邓小平的思维框架中,搞社会主义不是某种原则、教条的要求,而是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旗帜,但社会主义关系的形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最终服务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即服务于现代发展的文明进程,并使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这一文明成果。所以,邓小平归纳社会主义的本质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6〕他批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7〕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框架,不是建立在某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教条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某种简单的“财产——阶级关系”模式的基础上,而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发展。在当代中国,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如果离开中国的现代发展这个立足点,那就或是重蹈覆辙,或是误入歧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新开拓,不仅在现代发展理论方面带来一次思想大解放,而且在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也带来一次思想大解放。
注释:
〔1〕参见《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2〕“发展”作为专门范畴, 用来表述以工业化生产力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运动和变迁,这是西方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概念,而在20世纪中后期,“发展”尤其专指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马克思关于现代工业生产力对人类文明的伟大改造作用的理论,和西方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的结论大相迳庭,但观察视野大体相通。所以,这里把自马克思开始的这一理论部门称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尽管马克思有明确的“现代”范围而没有明确的“发展”范畴。也许有研究者不同意这一提法,这可以商榷,但无论如何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体系中这一理论部门的存在,故暂名之,以免发生理解上的歧义。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页、第24页、第59页、第62页、第64页等。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5〕参见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34页。
〔6〕参见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 第7页。
〔7〕〔11〕参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第513页、第509页。
〔8〕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84页。
〔9〕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0页。
〔10〕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801页。
〔12〕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6页。
〔13〕参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第1版。
〔14〕〔16〕〔17〕〔20〕〔22〕〔23〕〔24〕〔25〕〔26〕〔27〕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39、359—369页、第360页、第373页、第10页、第291页、第294页、第261页、第290页、第373页、第372页。
〔15〕转引自刘钰、周毅之著《走出低谷之路》,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18〕〔19〕〔2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165页、第215页、第123页。WW金宁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