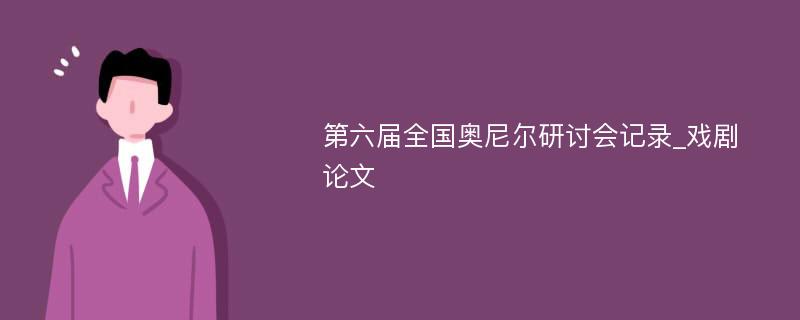
全国第六届奥尼尔学术研讨会纪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六届论文,纪实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奥尼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6月16日至18日,上海复旦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在复旦大学共同举办了全国第六届奥尼尔学术研讨会,共有60多位奥尼尔专家以及从事奥尼尔戏剧研究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并由上海戏剧学院上演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央戏剧学院上演奥尼尔的《悲悼》,其盛况实属空前。专家们早就盼望在研讨会上演出奥尼尔的剧本,以利于与会者的研究工作;但是前几次研讨会都未能满足专家们的要求,这次演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因此他们感到特别高兴。无论在会议室内,还是在剧场里面,自始至终都洋溢着赏析戏剧艺术的欢乐气氛。
在三天的研讨会上,有些专家宣读了他们的论文摘要,更多的专家则对这些摘要进行了讨论,他们有解释,也有争论,大家都是本着研究问题的态度,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决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是一次十分文明的自由讨论,学术空气甚浓。由于时间关系,与会者集中讨论了上演的两个剧本,主要是关于它们的缩编工作和演出问题。《悲悼》原来要演六个钟头,《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也要演四个多钟头,我们唯有浓缩其内容才能把它们搬上舞台。这两个剧本都是奥尼尔的代表作,很值得我们上演和研究。这次《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基本上演的是第四幕,由此可以看到全剧的核心内容;《悲悼》演的内容要多一些,观众对原剧的了解也就更清楚了。
对于这两个剧本,中央戏剧学院廖可兑教授作了一些比较研究,我想给它作一点扼要的叙述。第一,这是两部现实主义戏剧;评论家们称它们为家庭悲剧;但是它们反映的许多问题都超出了家庭生活范围,这是它们和一般家庭悲剧不同的地方,也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奥尼尔深刻地揭露了拜金主义的危害性。在《悲悼》里面,他无情地揭露了清教主义的残酷性。这两大主义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都具有典型意义。拜金主义不仅毁灭了杰姆斯·蒂龙的艺术生命,而且把他一家人都带进了黑暗的生活历程,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它阻碍了当时美国戏剧事业的发展。清教主义在美国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有着很大的政治社会势力,它浸透了许多美国人的灵魂,正如孟南家族那样,彼此仇杀,世代相传,谁要想摆脱它的统治,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第二,在这两部现实主义戏剧中,象征主义占有重要地位。像这样的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无疑地可以增加作品的表现力,同时也会给它带来某些抽象内容。在这里,让我们看看这两个剧本的生活背景吧。在《悲悼》中,孟南家宅是一座希腊庙宇式的大建筑,并混合着清教色彩,于是形成了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死亡之宫”或“仇恨之宫”,以显示这个家族的人们世代相仇的传统,仿佛冥冥中有希腊神话中的复仇神在这里活动,引导他们相继复仇雪恨,把他们一个个赶进了坟墓,最后只剩下莱维妮亚一个人,无人来对她进行报复,于是她就和孟南家族的全体死人一起住在那阴森森的房子里实行自我惩罚,直到她死亡为止。《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也有一个被涂上象征主义色彩的生活背景。剧本从早上八点半钟写到当天午夜时分,清晨的阳光很快就被大雾遮盖,最后越来越浓的雾便将阳光完全吞没了,房子外面变得漆黑一团。房子里面的楼上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蒂龙的妻子玛丽就藏在这里吸毒,看上去活像个幽灵。楼下的房间里也只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三个酒杯和两瓶酒,这也是个有象征意义的道具,与外面的大雾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一个黑暗的王国。如果说这个黑暗的王国将有一个光明的前景,那就是奥尼尔本人未来的艺术成就。奥尼尔是一位善于建立生活背景的剧作家。
第三,这两个剧本虽然都是现实主义戏剧,但它们的表现方式很不相同。《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重在反映生活片断,在时间和地点一致的情况下,总共写了四幕戏,第二幕分为两场,全剧都没有什么剧烈的外部动作,也没有生动有力的故事情节,最重要的是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创造醉生梦死的沉闷气氛,以适应创作主题的要求。相反地,《悲悼》的故事情节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生动有力,其中包括一系列外在的矛盾冲突和杀人流血事件,气氛紧张而阴森可怖。这是风格各异的两部悲剧,这次的演出形式也互不相同。两种演出形式都具有试验性质,值得研究,值得提倡,这也是与会专家们的共同意见。
1994年,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戏剧访问团参加了美国奥尼尔基金会与奥尼尔学会等组织在美国加州丹维尔市共同举办的国际学者会议,并上演了《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的第四幕。这次演出非常成功,受到与会学者和一般观众的热情赞赏。美国奥尼尔学者特·博嘉德说,中国演员忠实于奥尼尔的创作精神,他们的表演艺术光彩夺目,十分感人。观众们特别欣赏姚锡娟女士的表演,说她扮演的玛丽赢得了他们的眼泪。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姚锡娟前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于是一致要求她谈了她扮演玛丽的体会,并在听完她的精彩发言之后,对她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为国家一级演员,姚锡娟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修养,她认为,《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有着古希腊悲剧要求的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的净化作用,而玛丽又是最能产生这种作用的悲剧人物,一定要把她演好。开始研究剧本时,姚锡娟的思想感情是微妙的。她对我们作过这样的描述:“我感谢先行者们为我打开了奥尼尔的大门。那里面若明若暗,别有洞天,到处是深邃而又神秘的哲学迷宫,使我捉摸不定。于是我怀着崇敬而又胆怯的心情,轻声地呼唤蒂龙一家人,可是没有回响,因此我感到,也许是我离开他们太远了,离开奥尼尔太远了。事情不能急!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努力,我似乎和他们接近了些,朦朦胧胧地看到玛丽的身影,看到她失魂似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毕竟,我们的时代、社会、宗教思想等等都迥不相同,我一时还看不到她的全貌。然而,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与她的年龄相仿、也曾经历过沧桑的女人,我对她并不太陌生,我最后总会看到她的全貌的。”
姚锡娟反复咀嚼剧本和有关资料,越来越觉得奥尼尔确有过人的勇气和才能。他如此尖锐而深刻地揭露他家里的真实情况,揭露家庭成员的美和丑,完全没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作风。许多人根本不敢正视的家庭问题以及家庭成员的深层次的心理活动,都被他那饱含深情和痛苦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不愧为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学生。在表现人物的外部世界时,他更接近易卜生的细致入微的现实主义。在表现人物的内在世界时,他更接近斯特林堡的心理的现实主义或心理的自然主义。在奥尼尔看来,蒂龙家最严重的问题是玛丽吸毒的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祸根是蒂龙的拜金主义。奥尼尔毫不留情地揭发这些问题,也足以显示他的现实主义的高度。
为了演好玛丽这个人物,姚锡娟曾经去广州近郊一座戒毒所观察体验生活,窥探吸毒者的心灵。她既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感受到他们的软弱和无奈,当然,也能想象到他们渴求毒品刺激时的疯狂以及吸入毒品后的兴奋和飘忽不定。她希望从此寻找玛丽在第四幕的那种感觉。她认为,玛丽最可怕的问题是她的孤独感。这也是和拜金主义有联系的。没有人真正理解玛丽,也没有人听她诉说衷情。她的孤独感给她心灵上造成的痛苦,远远超过了疾病给她肉体上带来的痛苦。她吸吗啡与其说是为了医治生理上的疾病,倒不如说是为了麻醉她的心灵。毒品能使她忘却现实而进入美好的回忆。她说过:“这药能止痛。这药能带着你往回走——回到很远很远的往昔,直到再也不觉得痛苦为止。只有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才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玛丽的这种心态不是不可捉摸的。人们不也常有逃避现实逃避矛盾的思想吗?只是玛丽走到了极端,因而陷入痛苦的深渊。于是姚锡娟对玛丽的认同感产生了。
根据剧本的提示,玛丽吸毒后是处在一种追怀过去的美好状态之中。这种回忆使她时时出现少女的情怀,少女的羞涩。这是一种病态而又不全是病态。这里有角色本身不随年龄的增长而泯灭的本色。玛丽的本色是她始终没变的纯洁。她吸毒也是为了重返纯洁。姚锡娟在国内开始排练时,表演比较平淡,情感上很难投入,排练结束时也没找到角色准备的感觉,脑海中仍在琢磨人物。但是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表现玛丽情感的两个爆发点,并以此来勾画她那凄楚迷离的内心世界。第四幕出现的玛丽总是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她说:“我缺少了一样要紧的东西。我记得没有丢失以前我从来不感到孤独,也从来不觉得害怕。”那么这究竟是件什么东西呢?姚锡娟确认,这是玛丽的信仰。她年轻时曾经想当修女,为此她在圣母像前祈祷,圣母果然显形了;但是伊丽莎白嬷嬷却要她经受一段红尘的考验,结果她经不住尘世爱情的诱惑,终于放弃了当修女的神圣追求,和蒂龙结了婚,从此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当姚锡娟演到玛丽回忆见到圣母显形这段戏时,是把它作为情感的高点来处理的。姚锡娟力图再现玛丽少女时代的圣洁和幸福的情感,于是她的真诚热泪便夺眶而出了。
当埃德蒙告诉玛丽他得了肺结核的时候,她浑身发抖,大惊失色,接着发狂地大喊一声,说了个“不”!这是另一个情感的高点。一方面,玛丽流露出她对埃德蒙怀有深厚的母爱;另一方面,她又默默地告诫自己,她不能为了母爱而不去当修女。当修女意味着她重新获得她已经失去了的信仰,这对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作为演员,姚锡娟认为她应该强烈地表现玛丽对埃德蒙的母爱和舍弃这种爱的痛苦,同时也要表现她似清醒又似恍惚的精神状态。姚锡娟是这样构思的,也是这样表演的。
姚锡娟的表演艺术是受到与会学者的充分肯定的。她的玛丽一出场,便以她那深受其害的双手诉说吸毒给她的肉体与精神两方面带来的痛苦,全场观众在一片寂静中注视着她的每一动作和表情,直到全剧告终,立即对她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在姚锡娟前面发言的是从新加坡赶来参加研讨会的孙惠柱教授。他在美国波士顿塔夫兹大学任教,现正在新加坡讲学,工作十分繁忙。他带回来的论文是关于《送冰人来了》的研究;可惜来不及打印出来,在会上发言的时间又很有限,他只能讲论文中的一点基本内容——美国家庭剧的一个常见的模式。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呢?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父亲经常奔走在外,追求他的个人梦想,也爱寻花问柳,胡作非为,因此对妻子不能没有一种负罪感。母亲在家里带孩子,可怜巴巴,只是希望丈夫好好地回来。他们的儿子梦想破灭,没有出息。
美国家庭剧很多;但是奥尼尔却在他的《送冰人来了》里面较早地探索了这一类的家庭问题,思想内容也比较深刻。剧本里唯一“成功”的男人是五金推销员希克曼。他被住在一个酒店里的酒鬼们视作英雄,也仿佛是个父亲形象。酒鬼们总是盼望看着希克曼给他们带来礼物(酒和笑话);不幸这一次家里出了问题,他却没有带礼物来。因为他的妻子老是幻想着他能改掉在外面酗酒嫖娼的恶习,他要消灭她的这种白日梦,也不能忍受由于他改不掉他的恶习而对妻子所怀的负罪感,于是他干脆把她杀死了。希克曼也要酒鬼们从他们自己的种种白日梦中醒来,强求他们面对现实;他们一个个却无动于衷,反而更深地陷入白日梦中,并把他看成疯子,最后连他自己也不能从白日梦中摆脱出来。
《送冰人来了》对于后来的美国家庭剧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是最有典型意义的美国家庭剧则是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在这个剧本里,儿子碰见父亲在外面乱搞女人,这是他一生失败的主要原因。母亲琳达则是个贤妻良母的典型。最后,她既不能挽救她的丈夫,也帮不了他的儿子。
山姆·谢泼德的《痴爱》在美国也很有名,其中男人的自由和梦想更大更野(辽阔的西部是“美国梦”的更好温床);女人的生活处境却更糟。美国西部地域辽阔,工作很不固定,因此男人在这里好几处都有家室。这个剧本最深刻的一点是揭示一个儿子正在重复他的父亲的老路,而他的女友竟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
美国男人的流动性可以从下面的一段台词中窥见一斑:
一天早上你起来一看,发现感觉不对,就是在前门,找到一条路,又一条路,直到走到另一个地方。你难道没有听过那种行路谣吗?
这是写黑人的剧本《篱笆》中的一段台词,作者是奥古斯特·威尔逊。黑人因受压迫深重,有更强烈的离开此地去寻找乐土的冲动,常把老婆孩子留在身后,也因当奴隶时他们不被容许有老婆成家,现在美国大量的无父家庭中多数是黑人。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看成是对整个美国社会的写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篱笆》中写的是个不典型的男人,他偏偏修个篱笆把他自己的家圈起来。这一则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再则也使他自己更安于家室。但是即使是这种人也不免落入上述模式,搞出个私生女来。最后篱笆修成了,他也死了。
这样的篱笆究竟能圈住多少美国男人的梦呢?最近几年来,家庭价值已成为美国政界的重要话题。不久前,共和党领袖多尔(Rob.Dole)在抨击大多数影视破坏家庭价值的同时,又大大称赞了《真实谎言》,因为此片没有“破坏家庭”。但是自由派人士嘲笑说,那恰恰是一种病态的家庭价值,因为剧本里的那个在外执行特工任务的男人知道他的女人不安于家庭,竟把她当应召女郎召来,他则躲在幕后欣赏她卖弄色相。
另一部受到自由派欣赏的电影《捋猴子》则把上述家庭模式推得更远。影片中长期在外搞“事业”和到一地就换个女人的父亲强迫他的儿子放弃发展个人的机会,回家去照顾腿伤在床的母亲,结果闹出了乱伦的问题。
和奥尼尔在描写功能失调的家庭关系时所强调的沉重负罪感相比较,后来的美国作品对于这种关系的描写就显得越来越轻淡了。
在这次研讨会上,还有许多发言,可惜我来不及多加叙述。最后,我想介绍一位美籍教授巴巴拉·罗森柏格女士的部分发言。
我第一次是在太原市参加全国第三届奥尼尔学术研讨会时见到巴巴拉教授的。那一次我还见到原籍美国的吴雪莉教授。她早已来中国,长期在河南大学任教,成绩卓著,现任河南省政协委员。她是全国奥尼尔学术研讨会的热情支持者和参加者,第四届全国奥尼尔研讨会还是她发起由河南大学与中央戏剧学院共同在河南大学举办的。吴教授这次也来上海参加我们的研讨会,只是由于工作忙,未能写出论文,但是在会上发了言。她为人谦虚简朴,给她配备的较好房间她不住。她说得好,她没有必要住好房间,只想为中美文化交流多做些事情。这次吴教授给大会带来了由美国名演员罗伯逊主演的《琼斯皇帝》的录像带,大家看后非常高兴,感谢她为我们增加了观摩学习奥尼尔戏剧的大好机会。
巴巴拉前几年在复旦大学任教,现在华东师大任教,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有深厚感情。她很谦虚,一再表明她不是奥尼尔专家。她也说她不是爱尔兰人,也不是天主教徒,这是说她和奥尼尔也不一样。她是美国新英格兰人,欣赏奥尼尔的作品,认识他的人民。他们正像他的舞台人物一样,都是她所熟悉的普通人。据说,有一次她的朋友问她,为什么要关心奥尼尔的又长又沉闷又阴暗的故事呢?须知它只有一点点阴郁的喜剧轻松和模棱两可的戏剧解决啊!然而他们还是去看戏了。她同情奥尼尔世界里的受苦者。奥尼尔的艺术表现力加深了她对那些小人物的悲剧的了解,并使她深受感动。奥尼尔的戏剧艺术具有非凡的启发教育作用。比如说,谁看了《送冰人来了》而看不到他自己的白日梦或他自己幻想的真理呢?谁看了《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而不了解他们彼此需要的家庭之爱呢?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如果一个人不被奥尼尔引导到解决问题,也可以被奥尼尔引导到认识问题。这在巴巴拉看来乃是重要戏剧和伟大艺术的本质。她认为,奥尼尔往往是痛苦地给美国人揭示他们容易产生的乐观主义的另一面,他说的是一种不愉快的真理;然而他是迄今为止美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作品领导着新的20世纪的美国戏剧。
巴巴拉说,她来到复旦大学以后,在中国学到更多的有关奥尼尔的东西,并发现她的中国朋友龙文佩教授就是一位奥尼尔专家。通过龙教授,她了解到中国戏剧界和奥尼尔戏剧的密切关系,他的戏剧常在中国上演。她还和龙教授等几位女老师共同将上海戏剧学院刘明厚副教授写的一部反映奥尼尔生平及其创作成就的汉语剧本《迷雾人生》译成英语,并看过这个汉语剧本的演出。她认为,这不仅是研究奥尼尔的一种方法,也是研究英语的方法。这些中国妇女都很完美,专业知识丰富,工作讲求奉献,她感到和这些妇女一道工作,真正是一种几乎是没有什么美国人享受得到的特殊荣幸。她对此表示由衷的高兴和诚挚的谢意。
巴巴拉是个爱思考而又善于思考的人。当时她还不知道奥尼尔对老庄哲学有研究;但是她想过,奥尼尔的大量作品已流传在外,他享有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望,还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这一切都可能是他在中国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对奥尼尔探索中国哲学的了解,加深了巴巴拉对他的兴趣和敬意,同时也使她产生了这样的一些疑问:他的研究是表面的,还是实质性的?他是在为被他抛弃的天主教寻找替代物吗?老子的道给他带来了对于和谐与和解的循环性的认识吗?如果是,那为何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结束时几乎每个人物都陷入他自己的过去呢?
还有一些实际问题。例如,为什么中国人继续对奥尼尔发生兴趣?尽管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的新阶段,正如上海已如此戏剧性地有所说明的,这种兴趣还将持续吗?
对于这最后的一个问题,一些年轻的中国专家立即给巴巴拉提供了肯定的答案。他们说,原因很简单:奥尼尔的戏剧创作丰富多彩,中国人仍将可以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东西,以利于发展他们自己的戏剧事业。巴巴拉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表示她将努力帮助她的学生多学些奥尼尔的戏剧,使他们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能够为发展中国的戏剧事业多作一些贡献。
